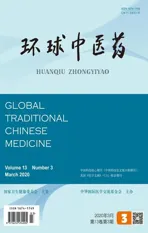理解中医古籍应秉持理性的怀疑精神
2020-01-10钟玮泽郭华
钟玮泽 郭华
1 中医学界自古以来存在着崇古的学术风气
中医学界自古以来的崇古风气主要表现为对医学经典的仰慕、推崇,后世对地位较高的中医古籍少有批评,而更多是引用、注释和阐发。针对崇古思想所带来的不良后果,现代学者多有批评,如中医史学家李经纬主编《中医学思想史》[1]指出“言必称经,就有可能因循经义而使自己的见解受到限制而不能自由发展,或因寻找经典理论支持而花费不必要的宝贵研究时间,甚至可能因一时找不到经典理论支持而放弃了自己原本闪光的见解”;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廖育群[2]指出:“‘尊古’之风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泯灭了学者的自信——他们似乎从来不敢想像:我也有能力创造出新的、更好的理论学说或实用技艺……一切新知识的形成无疑都不会被看作是对旧有理论与体系的批判,而仅仅是诠释。”由此可见,对中医古籍的非理性崇拜会扼杀研究者的创造力并对中医学术的发展造成严重的阻碍。下文将从多个角度论述中医古籍不应被盲目崇拜的原因。
2 中医古籍不应被盲目崇拜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医古籍所记载的内容普遍十分粗略
马继兴[3]指出:“愈是早期的古书,其内容趋于简朴和概括。”由于古代医家或文献编撰者尚未具备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加上古代社会物质条件欠发达,许多对于理解中医古籍至关重要的信息并未被记录下来。后世诠释者仅凭文字难以精确获知古籍所载内容的具体含义,亦难以评估古籍所载临床经验的可靠程度。中医古籍的粗略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各方面。
2.1 患者的临床表现、病史与转归欠详
临床表现具有“量”和“质”两个维度:“量”指医者在临床实践中所记录的临床表现的数量;“质”指医者描述临床表现的细致程度,包括部位、性质、程度、发作时间与持续时间、加重或缓解的因素等。在中医古籍中,临床表现的“量”和“质”普遍欠详,病史与转归亦多无记载,导致后人难以精确地重构出患者完整的疾病形象和接受诊治的全过程,亦难以准确评估治疗措施的疗效。现代学者对此已有批评,以古代医案为例,张再良[4]指出“流传下来的古代医案的描述大多过于简略”;何绍奇指出:“前人医案中的毛病是不少的……明清医案差不多都不完整,看不出疗效来,或有初诊而无复诊,或只有中间一段治疗记录,而首尾都不全。有的只记录一下脉象或病状。如:《未刻本叶氏医案》中,有的医案只有一句‘脉左弦’。”[5]345临床表现的记录欠详亦给疾病史研究造成了困难,如《疾病的历史》[6]指出:“历史文献经常未明确指出疾疫之名,对于疾疫症状、特征与病程的描述也往往不足,至于疾疫的发生率、盛行率以及死亡率、致死率、死亡分率,常常仅略述梗概,或甚至阙如,罕见精确的说明。”中医古籍对临床表现记录欠详还表现在临床表现之间的关系方面。许多文献有出现临床表现的堆砌,如《神农本草经》中对茯苓主治的描述为“治胸胁逆气,尤恚,惊邪、恐悸,心下结痛,寒热、烦满,欬逆……”,然而文中并未说明不同临床表现之间的关系:某些临床表现是否为某一疾病之下的一组临床表现,抑或临床表现之间相互独立?古代针灸文献亦有相同的情况,如《黄帝明堂经》将巨阙穴的主治描述为“心痛,气满不得息……心痛不可按,烦心”,而武晓冬等[7]经考证指出巨阙穴的主治病症实际上包括胸痹病的一组典型症状。
2.2 医者的误诊、误治案例缺如
即使是拥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者也难以在临证中确保万无一失。况且,每一个医者在临床实践中总有一个不断总结提高的过程,当中理应包含无数误诊误治的经验。然而,古代医者的误诊误治案例往往不被记录。现代医家对此有批评,如国医大师裘沛然[8]指出:“在历代盈车塞屋的医学著作中……大多是妙手回春的记录……我总觉得做医生是不大可能十全的,也很想能阅读有一本专记失败教训的医案,然而在杏林春满的医学文献中却还没有找到过。”何绍奇指出:“前人医案差不多都只记有效的病例,却很少有记失败的案例者。其实要说启发人,还是失败教训的总结更启发人……辨证与治疗的错误,虽在名家,亦在所难免。”[5]346对于中医文献少有记载失败案例的原因,贺学泽[9]认为“一是社会偏见和历史原因的负面影响,二是中医界自身对总结失误诊治经验的意义认识不足”。古籍普遍缺乏误诊误治案例的记录,使得后世无法准确评价古代医者的真实临床水平。
2.3 使治疗手段得以实施的各种具体条件欠详
古代医家理应详细记录使治疗得以实施的各种具体条件,包括所使用的器具、技术、药物等,使后人得以较轻易地重复前人的治疗经验。然而中医古籍对治疗条件的描述普遍不完整。以治疗技术为例,《灵枢·刺节真邪》记载了一种称为“发蒙”的针刺技术,并将其奉为“刺之大约,针之极也,神明之类也”,文曰:“发蒙者,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刺此者,必于日中,刺其听宫,中其眸子,声闻于耳,此其腧也。”然而,文中并未详细描述“听宫”的位置所在,若将其解释为手太阳小肠经之“听宫穴”则难以理解原文中的“必于日中”与“中其眸子”,更难以理解其被奉为“针之极也”的原因[10]。古代本草文献方面,早期由于缺乏精细的药物图,仅凭粗略的文字叙述难以精确描述每一种药物的性状,导致后世对某些药物识别困难,尤其存在多种同名药物时。如《神农本草经研究》[11]一书以表格形式列出历代本草文献中“矾石”的名实变迁,指出“矾石”一词在不同的时代含义不同,“在研究和考证中,极易发生混淆”。《中医文献导读》[12]亦指出:“在阅读中医古籍特别是中药、方剂或临床医著时,经常遇到某些不知其名的药物,而实际上却是已知药物的异名。”
2.4 医家从总结经验、搜集资料到构建理论、编撰著作的过程欠详
古代医者在临床实践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各种临床规律,并在规律的启发下构建新的医学理论。医者理应描述自己构建医学理论的过程,列出理论的临床依据,并明确交代理论中各种概念的定义。如此能使后人准确理解理论的真实含义,使理论发挥出应有的实用性。中医古籍对此难以面面俱到。以《伤寒论》为例,论中以六经(三阴三阳)为框架统摄复杂多变的伤寒病,并以三阴三阳之名列出了六个“提纲证”,如“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然而论中并未详细说明六经概念的具体含义,导致后世难以理解《伤寒论》六经框架的实质。如赵洪均[13]指出古人解读六经的难处有三,“其一,六经与经脉之关系难明。其二,《素问·热论篇》之六经与伤寒本论之说法不一。其三,《伤寒论》本身对六经含义无明训”。《伤寒论》本身对六经无明确说明,导致后世对六经实质产生各种联想。如《伤寒论理论与实践》[14]指出:“历代医家对于六经实质的认识不尽相同,可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从古至今,有关六经诸说,超过40种。”此外,古代医家或文献编撰者在编撰著作的过程中普遍需要引用前人有价值的医学文献,然而对引文的具体出处与引用方式未必加以详细说明。如《本草纲目导读》[15]指出:“《本草纲目》的缺陷最主要的表现方面,是引用文献欠严谨……‘注而不明’带来的麻烦是无法确定文字的来源……‘引而不确’的弊病是不能准确地体现原文的意思。”
3 中医古籍不应被盲目崇拜的主要原因之二:中医古籍的内容具有高度的歧义性
中医古籍内容的歧义性主要来自于古籍内容的文字上。中医学理论的语言具有自然语言特性,如邢玉瑞[16]指出:“整个中医理论主要借助于自然语言来表达。”根据《逻辑学》[17],自然语言是人类表达日常思维的语言。自然语言通常有歧义,在不同的语境下,同一概念可由不同的语词表达,同一语词也可表达不同的概念。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中“七损八益”为例,由于文中并未说明该词的具体含义,且“七”“八”“损”“益”皆属于自然语言而具有歧义性,后世对其产生了多种联想。如隋代杨上善认为“七损八益”指代《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中的15个临床表现。明代吴昆认为“七损八益”指代《素问·上古天真论篇》中所描述的男女生长发育的15个阶段。清代张志聪则认为“七损八益”体现的是“阳常有余而阴常不足”。然而,随着1973至1974年马王堆汉墓竹简《天下至道谈》的出土,“七损八益”的原意水落石出,指房中术中8种有益于人体的行为与7种不利于人体的行为[18]。此外,中医理论的语言尚具有自然哲学性质。《医学史》[19]指出,人类医学在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具有一个自然哲学模式阶段。在此阶段中,哲学思想与当时医学对人之本体和疾病本源的认识相一致。中医学理论普遍处于自然哲学阶段,因而理论中充满着各种哲学思想。然而,以自然哲学语言表达的医学理论具有笼统性和模糊性。如“命门”一词为哲学概念,而《内经》《难经》、滑寿、赵献可和孙一奎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了“命门”,分别指代目、右肾、两肾、两肾之间和肾间动气[20]。由于中医古籍文字具有高度的歧义性、模糊性,对古籍的非理性崇拜无疑会使诠释结果严重偏离原文本义。中医学理论的语言性质亦对中医学自身的发展造成阻碍,如国家文件《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指出:“中医以整体、动态和辩证的思维方式认识生命与疾病的复杂现象,但用传统概念表达的中医药理论的科学内涵难以被现代社会普遍理解和接受。”[21]
4 中医古籍不应被盲目崇拜的主要原因之三:中医古籍的部分内容未经过严格的临床检验
医学古籍所记载的经验与理论理应受到临床实践的检验以确保其真实性,然而中医古籍的部分内容明显来自于古人的主观推测,而非严格检验的结果。如《脉经·诊损至脉第五》曰:“一呼一吸为一息,气行六寸……二十息,脉百动,为一备之气,以应四时。天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一备之气,脉行丈二尺。”文中对不可观察的“气”的运行进行精确的定量计算,其计算的结果明显来自于“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观推测,而非基于临床观察证据的总结。又如中医古籍中载有各种推断孕妇腹中胎儿性别的方法,当中有以脉象、动作和身体部位的左右为依据者,如《备急千金方》曰:“妊娠四月,欲知男女者,左疾为男,右疾为女……遣妊娠人面南行,还复呼之,左回首者是男,右回首者是女……又,妇人妊娠,其夫左乳房有核是男,有乳房有核是女。”亦有以胎动出现的早晚与孕妇腹部形状为依据者,如《景岳全书·妇人规》曰:“胎有男女,成有迟速,体有阴阳,则怀有向背。故男动在三月,阳性早也。女动在五月,阴性迟也。女胎背母而怀,故母之腹软;男胎面母而怀,故母之腹硬。”以上有关胎儿性别的判别方法明显系根据有关阴阳的哲学思想直接推导而来,并未接受严格的实验检验。在针灸腧穴文献中亦有相同的情况,如黄龙祥著《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22]指出《黄帝明堂经》的腧穴主治病症存在着非实践内容。由于汉以前藏象学说并未成熟且藏象学说尚未与经络学说直接发生联系,腧穴主治病症中所带有的藏象学说内容大多具有主观推测的成分,而非直接来源于临床实践。中医古籍的目的理应是为后世医者的临床实践提供指导,然而古籍中未经严格检验的内容可对后世造成误导,严重者可使患者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而延误病情。
5 理性的怀疑精神是中医古籍诠释者所应秉持的基本精神
5.1 诠释者看待中医古籍的态度应在尊重与怀疑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
从古代流传至今的各种医学文献凝结着古人所总结的珍贵临床经验,编撰者的初衷亦往往是为了造福后世,因此后人理应对来之不易的中医古籍怀有敬意。然而,中医古籍作为医学文献,对其解读的方法与态度应当符合医学的性质与目的。《新编医学哲学》[23]指出,医学的目的包括预防疾病和损伤,促进和维持健康。《医学伦理学辞典》[24]指出:“医学是关于人的生命的科学、技术与艺术,旨在维护和增进人的健康、解除病痛、提高生命质量的人类实践活动与知识体系。”由此可见,医学具有明显的应用科学性质,追求在实际运用中的有效性。因此,中医古籍中的经验和理论应当要能够落实到临床实践当中,否则不具有临床意义。为了确保文献与实际挂钩,任何中医古籍的内容即使经过层层的严格考证,仍需要面临严格的临床检验。诠释者对于未经验证的内容需要勇于怀疑,如果内容没有得到足够临床证据的支持则应该对其持保留的态度,而非盲目推崇,此即理性的怀疑精神。如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建华指出:“前人留给我们的中医著作众多,既有大量的精华,亦有极少的糟粕。如何去粗存精,去伪存真?惟一的办法就是通过临床实践来加以验证。”[25]在古籍诠释过程中保持理性的怀疑态度是医学的目的和性质对诠释者的要求,是诠释者所应具有的基本素养。
5.2 理性的怀疑精神是中医学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
中医界虽然存在着浓厚的崇古风气,然而回顾中国医学史,理性的怀疑精神始终是中医学赖以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这在中医外感热病学史上可见一斑。以《伤寒论》为主导的外感热病体系发展至宋代已遭遇无数反例。许多医家观察到《伤寒论》所载部分治疗方法不能有效应对温热性外感病的某些病情,因此对传统学说产生了怀疑,对固守旧法的保守态度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发展和改革的主张[26]。改革者致力于阐明传统治法的适用范围,并试图对伤寒病与温病进行划界,如北宋庞安时于《伤寒总病论》曰:“四种温病、败坏之候,自叔和后,鲜有明然详辩者,故医家一例作伤寒,行汗下……温病若作伤寒行汗下必死……天下枉死者过半,信不虚矣。”对固守传统伤寒学说的态度的批判持续至明末,有吴又可著《温疫论》,序中叹言:“每见时师误以正伤寒治之,未有不殆者……守古法则不合今病,舍今病而别搜他书,斯投剂不效……千载以来,何生民之不幸如此。”正因为秉持着对传统的理性怀疑态度,吴又可对温病与伤寒作出了明确的区分,并从瘟疫的原因、感邪及传变途径、诊断辨证、治法方药等各个方面提出一系列新理论,使得温病学说正式成为独立的学科[27]。然而,以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为主导的传统温病学体系迈入现代后,临床证据显示其不能有效阻止某些急性感染病的传变。于是中医学家姜春华对传统温病学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怀疑与批判,如《姜春华论医集》[28]指出:“我们看过清代许多名医医案,治疗温病(包括湿温)过程中常险证百出,令人怵目惊心,其效果之所以不佳者,正是受此老(叶天士)用药轻淡如儿戏之教。”姜老认为,在现代医学已经阐明急性感染病的演变规律后,中医师在疾病初期应当截断病邪,阻止疾病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提出“扭转截断”的思想[29]。治疗应采取“先证而治”,在卫分阶段即重用清热解毒法[30],而不拘泥于传统的卫气营血辨证框架。国医大师朱良春[31]针对某些急性感染病亦提出“先发制病,早用通利”,认为在疾病早期运用下法可以缩短疗程,提高疗效,因此不必见病情发展至大便不通方用下法。由此可见,对旧有学说的理性怀疑是中医学外感热病学体系得以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中医学的未来发展也应以理性的怀疑精神为指导。
6 结语
中医古籍是指导临床实践的工具,而非崇拜的对象。各种历史原因使得中医古籍当中存在着各种不足,因此对古籍的盲目信奉必定是非理性的,亦有碍于中医学的发展。由于中医学属于医学而具有应用科学的性质,对中医古籍的理解必须始终贴合临床实际。若传统学说在临床运用中出现了大量反例,医者应当勇于进行质疑。中国医学史亦能表明中医学的进步正是依赖于对传统学说的理性怀疑。因此,理性的怀疑精神不但是中医古籍诠释者所应秉持的基本精神,亦是中医学未来发展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