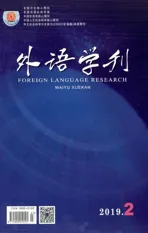60年翻译单位研究述评*
2019-11-26王福祥郑冰寒
王福祥 郑冰寒
(曲阜师范大学,曲阜273165;英国杜伦大学,杜伦DH1 3JT)
提 要:翻译单位是翻译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对其研究已形成产品和过程两种指向。本文综述60年来翻译单位研究两种指向的基本发展脉络,概括主要观点或研究发现,分析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指出未来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希望对翻译单位研究以及翻译过程研究有所启发和帮助。
1 引言
一般来说,翻译过程中译者需选择在一定的语言层面对原文进行切分,逐一转换为译文片段,在对各译文片段进行词法、句法、甚至篇章层面的调整和加工后,产出供目的语读者阅读的译文。这些译者操作的原文语言片段即为翻译单位。研究翻译单位对于揭示翻译活动的本质,描述翻译过程特点,指导翻译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自从1958年Vinay和Darbelnet在其专著《法英比较文体学——翻译方法论》中正式讨论翻译单位问题以来,学界对其研究一直热度不减。60年来,翻译单位研究逐步形成产品和过程两种研究指向(Malmkjær 1998:286; Carl, Kay 2011:953)。本文旨在梳理翻译单位研究两种指向的基本发展脉络,介绍翻译单位实证研究的新方法,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及未来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希望对翻译单位研究以及翻译过程研究有所启发和帮助。
2 产品指向的翻译单位研究
Vinay和Darbelnet是最早从产品指向研究翻译单位的学者,他们认为翻译单位与思维单位、词汇单位同义,是“必须作为整体而不能拆开翻译的最小源语片段”(Vinay, Darbelnet 1958:21)。之后,巴尔胡达罗夫提出类似的定义,认为翻译单位是“源语在译语中具备对应物的最小(最低限度)的语言单位”(巴尔胡达罗夫 1985:145)。 以Vinay和Darbelnet及巴尔胡达罗夫的定义为基础,产品指向翻译研究者从形式切分、意义确定、语篇—功能分析的视角或采用规定性或描写性的研究方法(司显柱 2001:96-99)围绕何种语言层次可以作为翻译单位展开热烈的讨论,总的来看主要有以下3种观点。
第一,翻译单位是介于语素与句子间的语言层次。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包括Vinay和 Darbelnet(1958/1995:22-27),Barkhudarov(1993:44-45),Catford(1965:24)和Newmark(1988:66-67)等。他们认为翻译过程中语素、词、词组、小句、句子均能充当翻译单位,因为它们在译语中均有某种形式的对应语言层次或单位,但从语素到句子任一语言层次均不能独自作为翻译单位,机械地将某一语言层次作为翻译单位无法有效地完成翻译任务。
第二,翻译的基本单位是小句或句子。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翻译转换操作主要在小句或句子层面进行。以小句作为翻译的基本单位是因为:(1)翻译中译者认知加工的基本内容是命题,而小句是命题的具体语言表达形式(Bell 1991:136);(2)小句的长度符合工作记忆容量限制的要求(Bell 1991:223,Malmkjær 1998:286);(3)小句是话语中最灵活的语言成分,译者可以根据话语分析的需要在翻译中灵活地转换,容易实现原文与译文的对等(罗选民 1992:32)。而Zhu则认为翻译单位是句子,因为句子具有独立的信息结构和完整的句法形式,以命题形式构成相对完整的信息结构,且能被短期记忆加工(Zhu 1999:6)。
第三,翻译单位是段落或语篇。Nida(1969:152-156),郭建忠(2001:51)等认为,以段落作为翻译单位能帮助译者注意句与句之间的连接和逻辑关系、段落之间的衔接以及段落与语篇的关系,只有照顾到这些关系,译文才能保留原文的基本结构和意义。Bassnett-McGuire(1991:117)、姜秋霞和张柏然(1996:17)、司显柱(1999:14-17)等坚持应以语篇作为基本翻译单位,因为译者不能因强调文本内容而牺牲整体结构,翻译应该是建立在文本整体意义上的语篇转换, 寻求的是语篇意义的对应。
以上学者关于翻译单位大小或语言层次的主张可谓言人人殊,所得结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实际翻译情况。总的来看,所有层次的语言单位均有资格成为翻译单位,在翻译任务中各司其职(Newmark 1988:67,曾利沙 2004:51)。关于翻译单位大小或语言层次的热烈讨论在笔者看来很大程度上与不少学者背离Vinay和Darbelnet及巴尔胡达罗夫的翻译单位定义有关。Vinay和Darbelnet及Barkhudarov所指的翻译单位是翻译的转换单位而非分析单位,不少学者有意或无意地将二者混为一谈。事实上,高级阶单位,比如段落、语篇可作为分析单位,低级阶单位可作为转换单位(Luo 1999:6)。将翻译单位分为分析单位和转换单位的观点有助于弥合学者们关于翻译单位大小不同主张的分歧。译者对翻译转换单位的选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译者要综合考虑文本类型、翻译策略等因素而选用不同级阶的翻译转换单位。Newmark认为,信息/权威型文本的翻译单位主要是词,信息型文本的翻译单位主要是固定搭配(collocation)和词组,召唤型文本的翻译单位主要是句子和语篇(Newmark 1988:67)。Teubert认为,新闻语篇的翻译单位是词和短语(Teubert 2001:144-5)。王云桥认为,召唤型文本散文和小说的翻译单位是段落(王云桥 1998:41-43)。司显柱则认为,无论是信息型文本(科技文本)还是召唤型文本(文学文本)的翻译单位都应该是语篇(司显柱 1999:17)。Catford(1965:25)和Toury(2001:92-93)认为,采用意译翻译策略时译者应以段落或语篇作为翻译单位,而采用直译翻译策略时译者应以句子、短语、词或者语素作为翻译单位。总之,产品指向的翻译单位研究围绕理想翻译单位的大小或语言层次展开热烈讨论,对翻译单位与文本类型、翻译策略等的关系做出初步的理论探索,而这些结论或主张是否或多大程度上符合翻译实际,则须开展实证研究加以检验。
3 过程指向的翻译单位研究
产品指向的翻译单位研究试图从理论上探讨翻译单位的大小或译者应以何种层次语言单位进行翻译活动的问题。与之不同,过程指向的翻译单位研究认为,翻译单位是译者的注意力单位或认知单位,重点考察译者选择翻译单位的过程及其表现出来的认知特点。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外一些学者以有声思维(TAPs)、击键记录(key-logging)、眼动跟踪(eye-tracking)等方法开展实验实证翻译研究,考察翻译单位的性质、大小及其与其他翻译过程变量的关系,描述译者的认知方式,得到一些重要发现。以研究方法的创新和使用为基础,过程指向的翻译单位研究可分为初期以有声思维法为主导和当前以击键记录/眼动跟踪法为主导的两个研究阶段。
3.1 以有声思维法为主导的翻译单位研究
将有声思维法用于翻译实验研究要求受试在完成翻译任务的同时口头汇报出大脑经历的所有思维活动。研究者收集受试的有声思维数据后依据一定的规范转写为文本,据此分析受试翻译思维过程,构建翻译过程的思维模式。过程指向的翻译研究者认为,翻译单位是翻译过程中处于译者注意焦点且能整体译为目的语的源语文本片段(Lörscher 1993:209,1996:30;Malmkjær 1998:286),在有声思维数据中表现为译者的“无标记加工活动”(unmarked processing)因注意转移至与翻译任务相关的具体问题而中断的那部分语段(Jääskeläinen 1990:173)。
有声思维法为主导的翻译单位研究主要发现如下。在翻译单位大小方面,研究发现译者实际采用的翻译单位包括语素、词、词组、短语、小句和句子,最常用的是词组、短语和小句,多数翻译单位长度在2至6个单词之间(Gerloff 1986:245-246,Krings 1986:263,Kiraly 1995:87)。这一发现基本支持产品指向翻译单位研究关于翻译单位是介于词与句子之间语言单位的观点,不支持翻译单位主要限于某一语言层面的观点。在翻译单位性质方面,翻译单位包括主观和客观单位两类。在有声思维数据中,译者初次尝试加工的原文语段为主观翻译单位,两个翻译停顿之间的译文语段为客观翻译单位,两类翻译单位不会固定在一个语言单位上(郑冰寒 谭慧敏 2007:151- 152)。在翻译单位与翻译经验关系方面,相关实验证明学生译者多以语素和词作为翻译单位(Gerloff 1987:152;Lörscher 1993:209, 1996:30),职业译者更多选用短语、小句或句子(Lörscher 1996:30;Séguinot 1996:80;Barbosa,Neiva 2003:148),随着翻译经验的增加,译者选用的翻译单位呈现增大趋势。但Kiraly(1995:87-89)发现,翻译单位大小不受翻译经验的影响,职业译者和翻译新手所用翻译单位在大小方面无明显差异,这与多数学者的发现不同,其原因值得进一步探讨。此外,有声思维翻译单位研究能深化我们对译者认知特点的认识。在翻译单位与翻译方向关系方面,Séguinot发现,外语译为母语时译者采用的翻译单位大,翻译认知加工更多地在篇章层进行;母语译为外语时翻译单位变小,翻译认知加工更多在词汇层进行(Séguinot 1991:79-88)。在翻译单位加工的影响因素方面,郑冰寒、谭慧敏发现,译者对翻译单位的选择和加工在诸如短期记忆容量、翻译熟练程度、文本理解难度等多种因素影响下不断变化(郑冰寒 谭慧敏 2007:150-153),在翻译单位与译者认知努力方面,Kiraly发现,翻译过程中非问题翻译单位能自动激活原文与译文间的一一对应关系,译者能自动加工并轻松完成翻译;问题翻译单位因语言或内容问题无法自动激活原文与译文的一一对应关系,译者须付出较多认知努力,借助相应的问题解决策略才能顺利完成翻译任务(Kiraly 1995:86-88)。在翻译单位加工顺序及方式方面,Bernardini发现,翻译单位的加工不是以序列方式而是以层级嵌套方式进行,低层次翻译单位的认知加工嵌套在高层次翻译单位的认知加工中(Bernardini 2001:249)。
总之,以有声思维法为主导的翻译单位研究描述作为译者注意焦点的翻译单位的大小、性质及其与翻译经验的关系,可验证产品指向翻译单位研究的一些观点,同时揭示翻译单位的认知属性及其加工方式与特点,拓展并深化人们对翻译单位的认识。但有声思维会改变受试思维过程的性质,能导致翻译单位数量显著增加,使翻译单位显著变小(Jakobsen 2003:30),有声思维数据是否是受试事后猜测或推论的结果,能否反映受试的真实认知过程等也遭到学者的质疑。有声思维法的先天不足要求我们在解读相关发现或结果时须非常谨慎。
3.2 以击键记录/眼动跟踪法为主导的翻译单位研究
为弥补有声思维法在采集翻译过程数据效度方面的先天不足,从20世纪末开始,学者们陆续将击键记录法和眼动跟踪法引入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中。击键记录法借助击键记录软件记录译者的键盘操作行为、鼠标移动以及翻译停顿等译文产出过程数据。在击键记录数据中,小于一定时长阈限(duration threshold)的两个停顿之间的译文片段与译者注意焦点非常对应,在很大程度上与译者认知加工的内容重合。因此,击键记录数据中位于两个翻译停顿之间、能够映射到某一原文片段的译文产出片段即为一个翻译单位(Alves, Gonçalves 2003:10;Alves,Vale 2009:254),也称作产出单位(Carl, Kay 2011:955)。眼动跟踪法借助眼动仪和眼动跟踪软件记录译者注视焦点、眼跳、瞳扩等翻译过程数据(Saldanha, O’Brien 2014:136-137)。根据Just和Carpenter的眼—脑假说(eye-mind assumption),处于译者注视焦点内的原文片段即是译者为产出译文而正在加工的翻译单位(Just, Carpenter 1980:331)。因此,在眼动跟踪数据中翻译单位表现为间隔时长小于一定阈限的连续两个或多个注视,又称注视单位(Carl,Kay 2011:955)。以击键记录和眼动跟踪数据为基础,Alves和vale把翻译单位定义为翻译过程某时刻与译者注意聚焦的原文片段相关的连续译文产出片段,其中(可能)包括译者注视(阅读)原文片段和译文片段情况(Alves, Vale 2011:107)。击键记录数据主要记录译文产出过程,眼动跟踪法弥补击键记录法无法记录译者阅读理解、监控译文产出等认知过程的不足,二者结合使用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全面分析翻译过程任一时点译者加工原文单位和产出译文单位的具体情况,了解译者如何协调这两种翻译认知加工活动(Carl, Kay 2011:955; Jakobsen 2017:35)。
借助击键记录和眼动跟踪技术,翻译单位认知研究发现如下:在翻译单位大小及变化方面,Dragsted发现,翻译单位主要包括词、短语、小句和句子(Dragsted 2004:189-193),这与产品指向研究学者Catford(1965:24),Toury(1986:83),Hatim和Mason(1990:132)等的观点基本一致。另外,Dragsted发现,小句是职业译者使用频率最高的单位(Dragsted 2004:141),这也部分支持Bell(1991),罗选民(1992)的观点。Englund-Dimitrova发现,随着翻译任务的推进,译者选用翻译单位有逐步变大的趋势,翻译单位大小受翻译促进效应(facilitation effect)影响较为明显(Englund-Dimitrova 2005:140)。在翻译单位与翻译经验关系方面,Jakobsen及Carl和Kay等发现,职业译者采用的翻译单位普遍大于学生译者(Jakobsen 2005:186; Carl, Kay 2011:973),这为有声思维研究关于翻译单位随翻译经验的增加而变大的发现提供新的证据。但Dragsted发现,无论职业译者还是学生译者,其大多数翻译单位均在2-4个单词之间,使用频率最高的翻译单位长度为3个单词(Dragsted 2004:129),这一发现既支持一些产品指向翻译研究学者坚持的翻译单位是词组和短语的观点,也印证Krings(1986),Kiraly(1995)等基于有声思维法得出的一些结论。在翻译单位与翻译难度关系方面,Dragsted发现,翻译高难度文本时,职业译者与学生译者所选择的翻译单位大小趋向一致(Dragsted 2004:276)。在翻译单位与翻译方向关系方面,Buchweitz和Alves及Ferreira等发现,与外语译为母语相比,在母语译为外语过程中翻译单位数量明显增多(Ferreira 2012:57)。
以击键记录/眼动跟踪法为主导的翻译单位研究也深化我们对译者认知加工方式及特点的认识。如在翻译单位加工过程特点方面,翻译单位认知加工随译者认知能力和加工需求的变化而变化(Alves et al. 2000:38)。在翻译单位平行/序列加工模式方面,Dragsted(2004:178)、Carl和Kay(2011:973)等发现,职业译者对原文片段和译文片段的平行加工情况较多,呈现相对明显的综合加工模式;学生译者对原文片段和译文片段的序列加工情况较多,呈现相对明显的分析加工模式。在译者认知节奏方面,Alves发现,职业译者在大小翻译单位间的选择转换节奏更稳定;而学生译者在大小翻译单位间的选择转换节奏更多变,其翻译认知管理、自我监控和评估产出译文等方面的能力相对较差(Alves 2007:25-35)。在翻译单位加工与译者认知努力关系方面,Alves和Gonçalves发现,在同一宏观翻译单位内,如某一微观翻译单位距离初始微观翻译单位越远,译者加工该微观翻译单位付出的认知努力就越多(Alves, Gonçalves 2013:116),并且Alves和Gonçalves还发现,在宏观翻译单位产出过程中,译者用于程序性加工的认知努力明显多于概念性加工(同上:121)。Schaeffer和Carl发现,如果某个翻译单位可供译者选择的目的语对应语越多,译者加工该翻译单位付出的认知努力就越多(Dragsted 2012:95; Schaeffer, Carl 2014:36)。
3.3 过程指向翻译单位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的努力方向
过程指向翻译单位研究能加深人们对翻译单位的认识,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在今后的研究中须要规范研究设计、拓展深化研究内容、深入挖掘眼动跟踪数据、开展历时研究和非亲属语言对研究等。
第一,规范研究设计。现有研究普遍存在翻译经验、翻译能力、实验文本难度以及用于确定翻译单位的停顿阈限标准不一等问题。同为探讨翻译经验与翻译单位关系的研究,Barbosa和Neiva,Dragsted与Kiraly的研究发现正相反。Barbosa和Neiva及Dragsted发现,经验丰富的职业译者所选用的翻译单位普遍大于缺乏经验的翻译新手(Barbosa, Neiva 2003:148; Dragsted 2004:134)。而Kiraly发现,翻译单位大小基本上不受翻译经验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职业译者和学生译者采用的翻译单位的大小差异并不显著(Kiraly 1995:87-89)。相同的问题研究却得到不同甚或相反的发现,这可能与以上学者对翻译经验水平的控制不同有关。虽被统称为职业译者或学生译者,不同的研究涉及的受试的翻译经验水平不一,这不利于学界对相关研究结果进行判断和对比。
再如,现有研究中用于确定翻译单位的停顿阈限标准不一,有的研究把阈限值设定为5秒(Jakobsen 2003:90;Alves,Vale 2011:111),有的设定为2.4秒(Jakobsen 2005;Alves, Gonçalves 2013:113;Alves et al. 2014:161),有的根据受试打字速度和翻译任务总耗时的情况将阈限值定为1-2秒(Dragsted 2004:103-104)。停顿阈限标准的不同会直接影响翻译单位的大小和语言层次高低,进而影响研究结果或发现,为判断同类研究结果的可比性带来很大的困扰。因此未来研究应规范研究设计,控制好翻译经验、翻译能力、测试文本难度水平,加强翻译单位的停顿阈限标准确定方法研究,提高研究的规范性和可比性。
第二,深化研究内容。翻译单位在翻译认知过程诸因素,如翻译能力、翻译策略、翻译经验、翻译难度、时间压力、翻译技术、译者认知方式、认知努力等研究中均处于核心地位(Alves, Vale 2009;Carl et al. 2016;Jakobsen 2017)。在一定程度上,翻译单位研究极大地推动翻译过程研究。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对翻译认知过程中最为核心的翻译经验、工作记忆(译者认知能力)和翻译难度3因素与翻译单位之间关系的研究还不够,需要进一步拓展、深化。如(1)在翻译单位与译者认知方面,有研究发现翻译单位的选择受工作记忆容量大小的影响(Alves et al. 2000,郑冰寒 谭慧敏 2007)。而Rothe-Neves(2003)、王福祥(2015)则发现,工作记忆容量对翻译单位数量的影响不显著。不同的研究发现客观上须要开展实证研究以进一步确定二者之间的关系。(2)在翻译单位与翻译难度、翻译经验和译者工作记忆关系方面,现有研究探讨翻译单位与翻译难度(Dragsted 2004,Jakobsen 2005)、翻译经验(语言学习者、职业译者、半职业译者、行业专家等)(Jakobsen 2005)间的关系,但翻译单位与翻译难度、翻译经验和工作记忆的关系研究(王福祥 2015)刚刚起步,需要深入开展更多实证研究予以考察。
第三,深入挖掘眼动跟踪数据。在以击键记录和眼动跟踪法为主导的翻译单位研究中,眼动跟踪数据多用于辅助证明由分析击键记录数据得出的研究结果(Alves,Gonçalves 2013;Carl et al. 2016),但自身未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眼动跟踪数据的庞大及其与击键记录数据的缠绕、重叠。数据丰富有助于拓宽研究面;但即使是开展小规模的人数较少的实验,眼动跟踪数据分析的工作量也很大。如果扩大被试数量,数据量肯定倍增。今后应该加强团队合作,深入挖掘眼动跟踪数据, 充分发挥眼动跟踪法在翻译单位研究中的作用,进一步探究翻译单位的性质、类别及其与翻译过程诸因素之间的关系。
第四,加强翻译单位历时研究。现有研究均为横断面研究,不利于探究翻译单位随译员学习和职业生涯发展而发生的变化(王娟 2015:73)。今后应加强翻译单位历时研究,确保同样的被试、有规律的间隔和较长的时间跨度,以此考察翻译单位随译者翻译水平提高的历时变化路径。
第五,加强非亲属语言对研究。当前过程指向的翻译单位研究主要涉及葡—英、葡—西、英—法、法—德、英—丹等西方语言对。这些语言属于近亲属语言,以其为基础获得的研究发现或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非亲属语言对还需要开展更多的实证研究予以证明。
4 结束语
60年来,翻译单位研究形成产品和过程两种研究指向。产品指向研究认为翻译单位是源语语言单位,主要从理论上对翻译单位的性质、理想翻译单位的大小以及翻译单位在文本类型、翻译策略等因素影响下的语言结构特征等方面进行探讨。过程指向研究视翻译单位为译者认知/注意力单位,开展翻译实验研究,在分析译者有声思维、击键记录和/或眼动跟踪等翻译过程数据基础上,重点探讨翻译单位与翻译过程诸变量之间的关系,界定译者常用翻译单位大小及变化特点,描述翻译单位选择与加工时译者的认知特征,深化人们对翻译单位本质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