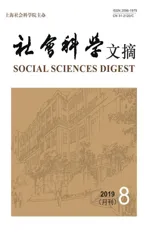探寻中国人的社会生命
——以《金翼》的社会学研究为例
2019-11-19渠敬东
文/渠敬东
研究中国社会,必要从人出发;人有其生命,且往往是被社会赋予的。费孝通晚年就曾对以往的研究做过反思,说自己“还是没有摆脱‘只见社会不见人’的缺点”。任何社会生活的逻辑和规则都不会自行空转,只有进入到具体的人的世界中,社会才会敞开、才会获得真正的生命。
生命史的白描法
通过返回我们的生活世界来重新发现中国社会,近些年来,社会学家再次表露了这样的心声。这种心声来自于田野工作中对“社会底蕴”的感受。这种感受让我们不会迷失在时下流行的概念和意见里,努力回到最质朴、最亲切的生活世界。
中国学者探寻自己所属的社会生活,自然少不了传统士大夫的那种同情与关切,“天下兴亡”之际,怎能忘掉“学以致用”的责任?社会学前辈们是“敢于”承认这样的情怀的。当年燕京大学的学生们追随吴文藻等从事社区研究,便是从物质、社会组织和精神等三个层面入手来构建多层次的文化整体。这一思想反映在燕京学派此后的整体研究和著述之中,而今天看来,其中“既见社会又见人”的代表作,当数林耀华的叙事体著作《金翼》。
《金翼》写于1940年,是林耀华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余暇生活中的信手之作,题材取自于家乡福建省闽江流域的古田黄村,虽然作者曾于三四年前做过两次田野考察,内容上却更多地融入了自己的生活历程。作者在四十年后的“著者序”中说:“《金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这部书包含着我的亲身经历、我的家乡、我的家族的历史。它是真实的,是东方乡村社会与家族体系的缩影。”此书1944年首版,腊斯克(G.Lasker)作序,题为“隐然浮现的伟大目标”。从此标题可以看出,腊斯克始终在努力把握此书隐而未彰的意图和风格,他说道,作者所运用的“非正统方法具有特殊的价值,可以使我们直接了解中国家庭的日常生活”。腊斯克隐约地意识到,林耀华采用的叙事策略,不仅没有照抄照搬西方人类学的规范方法,也有意躲避掉了一些学科既定的描述和分析概念,甚至平铺直叙的文风,像是在尽力避免情节上的跌宕起伏;似乎这样的风格不再是基于科学叙事的要求,而是中国人之社会生活的本质呈现。
首版《金翼》副标题为“一部家族编年史”。编年史的方法,本就是民族志的要求,即是对一种社会历程之详细完整的描绘。虽然学界对于华南地区之宗族社会素有研究,后来亦对《金翼》多有评价,但《金翼》采用的所谓编年史手法,即在特定的时空关系中追踪全面社会关联的方法,将“社会”的自然展开作为其构造的环节和脉络,则是独具一格。
不过,编年史的呈现并非仅是一种单纯的线性时间过程。一个社会周期,常常伴随着竞争、冲突、调协和同化四个阶段而展开,其中,竞争最为根本且普遍。林耀华借用齐美尔的说法,认为人们之间的互动常因情势的变迁,伴有无意识的、难捉摸的和未预料的情况发生,短兵相触,危机难以避免;可随着时过境迁,也往往会调协成就,达以和解,由此形成的新秩序渐渐深入人们的习惯风俗,传递后代,便又形成新的均衡态势。
《金翼》就是循着这样的节奏和过程来写的,可以说它是受了派克、库利等人的影响,但作者借由亲历的经验书写的毕竟是中国人的故事。社会之为社会,是因为以“文”化人,人在其中。社会研究失了人,便只剩下了空荡荡的躯壳,没了生命及精神。林耀华说,他是用生命传记法来研究社会的,即通过生活中人的生命历程来承载社会的生命历程。具体来说,是用黄张两家姻亲的生活流变,来呈现一个社会的生命周期。
从社会中见人,就要有特别的叙事方式。一方面,要完整描述个人的生命周期,“把个人生命按时代描叙,观察时代的变迁及他与众人关系的变迁”,将个人传记中的生命历程,如“出生、三旦、满月、周岁、断乳、入学、冠笋、婚嫁、寿长、死丧、葬祭等等”关键节点和重要转变逐一揭示出来;另一方面,正因为个人总是在事件化的过程里,需要用反常的形式来激活存于其身心之中的社会内容,因而“最好能够如影片般活跃地描写”,像小说家或戏剧家那样,“染着作者的性格和观点的颜色”。社会中的各个主体,都不是死寂的陈设,而是“心身功能所凑成的有机历程”,因而传记法不是解剖术,不是用死人的躯体来解析活人的生命,就像库利那样,“以其洞察行为之深,在形式上虽为非戏剧的,而实质上却是戏剧的”。
中国人讲一个社会的生命历程,没有亲身体验,不能娓娓道来,便不会有气息和血色。“未知生,焉知死”,燕京学派所说的社会学“中国化”,乃是由西方来的新科学向自身社会生命体验的内向转化:不理解自己的此生,就不能理解自己的过往和来世。因此,这样的学问也是从“内省”和“内观”入手的,必带入一种“投入感”:对于生活中那些命运捉弄、悲喜交加的故事,谁会不挂心动情呢?即便是一个所谓客观的观察者,也会生出“将心比心”的同情来。林耀华说:“我们日常所认识一个人的行为,莫不从视觉听觉以及在背后心理历程中的想象,拢合起来而成就的。假如没有这种想象,我们绝对不能够注意那个人,脑子里也失掉他的影迹。”
不过,研究者也必要有所自律,正因为逼近真实是他的职责所在,他须得根据扎实的田野工作反复琢磨,依照民族志的严格要求行事,一方面,“如非用活泼的文笔来描叙生活,则不能使读者感到兴趣”;另一方面,则“不要希望做出光辉灿烂的文词,以致分散作者或读者的注意力于庄严的真理之外”。《金翼》所讲的编年史,刻画的虽是平常人的生活,却也将这种“平常”放在了编年史的传统笔法中。腊斯克的感觉是对的,林耀华对于平常人的生活世界的书写,常常不温不火,倒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辗转动荡的经历,而在于社会生命的奥秘并不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微而显”,“志而晦”,行文不见起义,故事言简意赅,不讲大道理却能够见微知著,是作者追求的境界,却也是平常人的生命活动本身使然。
扩展的社会生命
林耀华的白描法,既是对中国人特有的生命历程之绵延性的时间暗示,也是有别于归纳和演绎之常规研究方法的学术探索。借白描法来绘制编年史,就是要削去那些用来烘托和粉饰社会生活的成分,用最精练且精致的笔触,勾画出最能表现社会生命之律动的线索,虽着墨不多,却余味无穷,让人与人之间互动、互构的生活机理,都能够转化成为内心里的印迹。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生命轨迹中,让每个有心之人,都能感受和意识到自己从来都不是纯粹的个体:“思想是社会性的,社会是在心灵之中。”
《金翼》开篇,就用这样的笔法,讲出黄东林这位故事的主人公,于时空中的关系构成。人的命运也与地理空间有着密切关联。东林的生活轨迹,是随地理上的扩展而带来的交往圈子的扩大过程。然而,一个人的地理学生命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还脱离不开政治的影响。东林的命运起伏,除了闽江流域所提供的生计线路,也取决于从内陆而来的外部影响。林耀华说:“一个人为了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必须与不同圈子中的人们发生多种联系。”中国乡间的普通百姓,大概不是基于自我意识来理解自己的,韦伯讲的社会行动及其意义筹划,行为科学中的理性选择,也不是他们构建社会生活的出发点。他们总是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在逐次发生和扩展的人际关系里,才会渐渐知道自己的位置和角色、身世和遭遇,从“不同的圈子”和“多种的联系”中来把握自己。
龚自珍作《农宗》说:“农之始,仁孝弟义之极,礼之备,智之所自出,宗为之也。”若明确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必先要考察他的家系与宗亲,所谓“明人伦”者,首先是从“至亲”的角度生发的。《金翼》开篇伊始即说明东林在“一体之亲”中的结构关系,便是要明确他一生的生命历程都将会在这样的人伦秩序之基本格局里发生。他对于自身的定义,就是靠这样的至亲关系及其延展出来的社会关联来确定的,无需一种抽象个体的假定。本质而言,人的存在是一种“格局存在”,这种格局是差序的,依照父子和夫妻关系的双系两轴来规定,其中,父子兄弟之伦最为基本。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历史维度,即依照家族谱系而确立的人伦关系,便是人的本身的优先规定,是其他社会关联的先行前提。
林耀华说:“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像是一个由用有弹性的橡皮带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构成的网,这个网精心保持着平衡。拼命拉断一根橡皮带,整个网就散了。每一根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就是我们生活中所交往的一个人,如抽出一根竹竿,我们也会痛苦地跌倒,整个网便立刻松弛。”就存在论来说,中国人原不是个体本位的,无论君亲师友,还是天地族群,都是人依社会连带关联而实现的自我构成。人因伦常关系由里而外、由近及远地加以扩展;“推己及人”,情感秩序与社会规范皆由此而来,也形成了自然、人际与天道之整全世界的关联。就此而言,每个人不是社会世界构造的原点,而是关系点,是联络点,依照相对应的亲疏远近来确定不同程度的关联,逐次外推。正因如此,那些在最里、最近、最亲、最尊的人的离世或关系上的断绝,就会产生最强的崩解效应。对东林来说,祖父的过世,会使他的“生活模式被全盘打乱”;兄长东明之死,他的生活格局“再次被硬性改变”,他不得不挑起整个家族的重担。
一个人的生命,是一家人的生命,也是同族同宗的世代生命。上至祖先,下至后人,也都在这恒常的生命谱系中,绵延相续不绝。所以,家族的维系至关重要,上有祠堂,下有家塾,祭祀、生存和发展,是永远不变的生活主题。时间上,崇宗祀祖,香火不断,是家族兴旺的前提保证;空间上,上风上水,好的地相形势,可聚拢山川气象,预示着家族的美好未来。
此外,人的社会生命当然也要在现实中发展延续,东林在由乡入城、由农转商的历程中,不仅要层层构建同侪关系的格局,甚至以他整体社会的基本构型作为模板,来确定家中各子的行业分布结构。家族的兴旺和绵延,也是将一个人的社会生命通过后代向诸社会领域不断扩展的过程,如同东林自己的生命史一样,从大哥到小哥的社会身份的培育和分配,本身就是这一生命史的延续,层层累积和推进,一个家族才会成为一种构成性的有机整体,成为一个活的社会体。
《金翼》要说的事情,并非只是诸如社会历程、文化周期或均衡论这些学说从中国经验中取得的一个论证,也不是遍布于世界的民族志个案中的一个,而是从社会学之新视角出发来重新发现中国社会的一种努力,即吴文藻所倡行的社会学“中国化”之要旨。中国人社会生命的底色,不是靠移植来的思想和制度便可以一蹴而就地加以改变,时下时髦的各色说法,反而是一种有色的障目。同样,任何世变与情势也非转换社会生命的根本理由;恰恰在思想激荡、世事纷扰的年代,才要重返社会生命的文明内核中,来探寻未来之路。
家族本位的社会格局
1935年10月,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于燕京大学讲学三个月,林耀华任助教“日夕追随左右”,并写下了《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一文,以示纪念。该文中,他就明确了这样的思想:无论是以宗族、家族或个人为叙述的起点,都不过是透视宗族社会各部分之互相关系的整体。这里的意思是说,就中国乡村普通人的社会生命而论,宗族、家族及其中的个人是一而三、三而一的并合逻辑关系,从未有单独存在的宗族、家族或个人。《金翼》虽以中国家族制度为题,当然也是对宗族及其之内的每个人的刻画,无有其外。相对而言,《义序的宗族研究》则从宗族分析起步,恰是《金翼》的前奏,两部作品互文相映,同出一解。
《金翼》所呈现的是社会生命的有机活态,不是从宗族到家族的结构解析路径。故事开场不久,便有了“事件化”的过程,黄家与欧家“林木争端”成为全书的情节枢纽。“林木争端”说明,普通人的社会生命全部都寄托于他的家族之中:“家庭就是这样一种生活圈子,是围绕着一个由习俗、责任、感情和欲望所精心平衡的人编织的强有力的网。”抽掉其中的任何一员,扯断他们之间得以维系的任何纽带,家庭便会面临着解体的危机。另外,也说明了理解家庭的生命和命运,必须将考察的范围拓展至宗族乃至更为广阔的关系系统之中,才能把握其中的要害和意味;东林与阿水之间的争斗,非是两家间的较量,而是两族间的比拼,这需要从整体的乡村结构出发来理解。
林耀华指出,在中国乡村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宗族与家庭的连锁体系。搞清楚这样的问题,就必须首先在理论上明确,宗族与宗法不可混为一谈。宗法是周代以来一种极精密宏大的制度体系,“与封建相互实行固结不解”,五服制与五等制并行不悖;其中,大宗小宗制度为其主轴,大宗为始封一系,百代相传,本为“收族”。相比来说,宗族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一,封建时代有井田之制,共耕公田,而宗族族内各自拥有私田,大小不一,贫富悬殊,即便是祖产祭田,也专在祭祀,轮换耕作;其二,与祀先庙制不同,宗族拜祖,乃是“祠堂合祀历代宗祖”,“以始迁者当之,与古义又相去甚远”;其三,宗法制度以大小宗为基本,宗族组织则以族房长为中心,前者“皆嫡长相继,父子相承,生来而身份定”,而对于宗族来说,族房长的产生,则以辈数和年龄为标准,“祭非长子专职,所以无宗可言”;其四,就宗族立后之制来说,“宗指祖先,族指族属,宗族合称,是为同一祖先传衍下来,而聚居于一个地域,而以父系相承的血缘团体”。
宗族与宗法之别,对于理解中国乡土社会的构成相当重要。首先,正因为宗族不再依照大宗的原理“收族”,不再循着等级制的封建体系施以分茅胙土制度,才会出现广泛存在的私田制度,以及形成社会分化和流动的机制。其次,宗族虽然在亲属制度上延续了五服制,却在祭祀上弱化了“五世则迁”的原理,扩大了族属的范围,万斯大有关“谱法和宗法原不相谋”的说法,便揭示了族谱相连的道理:“宗者,统族人以奉祀也,祭以往之祖,而收见在之族,祖分而祭亦分;故一族不止一宗。谱者,志族人之世次也,追以往之祖,而收见在之祖,祖分而族不分;故一族可同一谱”。再者,基于上述原则,通过围绕着祠堂来合祭历代宗祖,宗族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得以构成,与此同时,家庭也被解放出来,成为了社会组织的真正单位,承担起最基本的社会功能。
由此,社会构成的整体结构不再严格依照“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的规则,来确立一种宗法意义上的身份等级体系,而是依据从家庭到宗族的组织等级体系加以社会化。所谓“社区”,便是根据逐层聚合的方式来构建的,即以家、户、支、房、族的功能单元依次扩展为更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其中,家为共灶合炊的经济单位,以男子的辈数与年龄最长者为家长;户以住屋计,从诸家长中推最年长者为户长;支以支派计,支上有支,从祖父到高祖,直到房分为止;“房”通“旁”,即是后代子孙以自始祖以下分成的支派,并划地域为界,常以居地名而房分,乃为祠堂组织的中心;诸房长中再推年长者一人,便是全族的族长了。从乡村社区的总体结构来说:家是经济单位,户是社会交往单位,支是宗教祭祀单位,而族房长,亦即祠堂会,乃是上述功能的综合单位。从这一社会秩序看,东林最多不过是个户长或一个支派的代表,能与阿水这位族长争出高下,在乡里人看来恐怕是天底下最了不起的人了。东林的胜利,是以一己之家而胜欧氏全族的胜利,自然也是他自己所属的全族人的胜利。从此,东林既获得了全族的支持,也将这样的声誉扩散开去,宛若打赢了一场事关全局的战役。
有了宗族组织,才会有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规模较小的自然家庭便会发生更大的作用。由于宗族社会广泛实行族外婚制(exogamy),因而中表婚就成了最受族人欢迎的婚姻形式。林耀华认为:“亲属关系包括父系亲属和婚姻相连的戚属,父系亲属就是家族团体。家族团体是由于父子、夫妇、婆媳、兄弟以及其他近亲所形成的。”依照亲疏远近的规则,这些不同层级的亲属关系之性质及其伦理要求也就得到了界定。
中国的家族制度中,“人”是第一位的,即按上述血亲和姻亲的亲疏关系而界定的人伦秩序及功能作用。但“地”的地位也尤为重要,既然家以灶计,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生活维计所需住屋、工具、家当等一系列物质条件皆要以田地为依托。《金翼》故事的开始,便刻画了这样的场景:东林虽在城里做了生意人,可无时无刻不与自家的兄弟“谈起季节性雨水与灌溉,筹划犁田锄地、播种收获和交租纳税”的事情。
林耀华说,一个家族的生命史,是一种传续和裂变的社会历程。家庭是保存并传递文化的单位,父子相传是家族的实际制度,兄弟继承总是暂时的,因而必要分家。分家,如细胞分裂般,是家族的社会生命的自然过程,也是兄弟之间由竞争冲突再到协调和解的过程。分家总会产生生命的剧痛,金翼之家亦如此。一个家族的生命史总是由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写就,但这日常世界的背后,却是经由几千年、几百年层层累积和变换的社会构造之传统底色。这种叠合着多种格局的人际关系的体系,规定着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也为每个人赋予了社会生命。许多体系之间存在着内部的相互关系,无论是像店铺与家庭这种具有共同成员而并列共存的体系,还是像家庭、世系和宗族那样具有从纵面关联的体系,皆表明体系之间具有本质上的内在相互关系。
说林耀华是功能论者,倒也没错,不过这功能论是末,不是根本。学界总喜欢讨论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的宗族研究与林耀华的关系,其实两者间的差别很简单。弗里德曼关于中国宗族的“非对称分支”的发现,针对的当然是由埃文思-普里查德《努尔人》以降的田野考察而生发的人类学经典理论:即相比于非洲“对称分支”的均衡模式而言,中国宗族由于资源配置的不均等而导致的内部分化,使得不同支派出现差异化的形态,大宗族祠堂广布,公产丰厚,小宗族则所辖分支稀少,甚至完全萎缩。虽说弗里德曼的诸多发现从林耀华的研究中汲取了很多营养,但终究只是功能论的遗续,王铭铭称之为“汉学人类学的概化困境”。相比而言,林耀华的宗族研究是要回到中国社会的本体论中去,回到中国文明的基质里来考察宗族组织的构成问题。他尽管对于宗法与宗族做了区分,但也始终强调,在祭祖、继嗣以及家族公产等方面,宗族制度中无不有宗法制度的痕迹,而且,中国的宗族制度也从未像非洲的社会分支那样,处于一种非国家、无政府的形态中。林耀华要做的,不是为一般人类学的功能论提供一种中国范例,而是要从中国文明本位出发,来揭示宗族制度所内生的功能和均衡效应,以及中国人独有的社会生命的基本结构和存在方式。
祖先与神明:生命的护佑
关于分家,先是黄家分了东明和东林两支,后东明一支又闹着分家,两兄弟打得不可开交。不过,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祖母潘氏病倒,她知道自己活不久了,把攒下的私房钱全数给了二哥,大哥得知此事,竟在祖母的病榻前再度与二哥争吵,在一片打砸吵闹声中,老祖母终于咽了气。金翼之家只能搁置争端,为老人筹办了隆重盛大的丧礼。虽然这场仪式与家族矛盾并无关系,却产生了相当神奇的效果,之后兄弟几人就此休战。
在世俗世界的纷纷扰扰中,社会生命是要靠仪式和信仰来升华的。这就是老祖母的葬仪能够搁置争议、抹平争端的真正原因,两者看似无关,却是圣俗两界发生关联的真相。林耀华说,乡村生活中的祠堂与牌位,宫庙与神龛,都是涂尔干意义上的集体表象(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祖先与神明,才是宗族或家族真正得以凝聚和整合的象征枢纽。写在一个人身上的社会生命史,“自出生至于老死,恰好绕转一个圆圈”。
在《义序的宗族研究》之“个人生命史总结”的部分里,林耀华从义序地区的田野出发,依照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及与家族、宗族及亲属的关系,制成一张生命史的仪节总表,分列出人在一生中的几个重要转变期所必经的过程仪式。在出生、童年、婚嫁、寿辰、死丧、死葬、祭祀的七个时期中,所要经历的重要仪式便约有24项,而其中具体的仪轨则有100种左右。
《金翼》用最浓重的墨彩完整描述了红白两事的仪式过程。《金翼》对于丧礼的记述尤为详尽,在另一处也曾谈到过墓祭仪式。
可以说,丧礼、葬礼与祭礼,既代表着生命循环的周期性完成,也是家族凝集和规制情感关系、整饬人伦秩序的契机,藉此连同生者与死者的社会生命得以敞开,人际关系的差异性和普遍性原则得以展开。同样重要的是,上述仪式也突破了“人间”的界限,将人世与神鬼两界连通起来,通过生者操持亡灵的升降,来确立圣俗二分的纵向格局,从而融合了儒释道三教的因子,在最具体的仪式实践中确立了长辈和先祖的神圣地位,为社会生命赋予了真正的超越性的精神意涵。个人的生命有限,但可以通过缔结婚姻来维续家族的生生血脉,并扩展家族的社会联系,而通过丧葬祭祀,超度亡灵,却可以使一家一户一宗一族拥有不死的祖先,不朽的灵魂,而代代得以护佑。唯有如此,个人的生命不仅可以成为家族的生命来延续,也可以成为宗族的生命而永生;他可以超越日常的世俗域,借由各种信仰和仪式与祖先进行精神上的沟通,得以安慰、保护和心灵的提升,将自身的生命扩展至最广阔的世界里。
父母之灵,先是奉于支祠或神龛,待数世之后,神主迁往宗祠,便会得到全族的祭祀了。《金翼》虽以家族制度的研究为主题,但社会生命并非仅限于这一范围。家族于社会中的位置由宗族来确定,而家族的生命也必会延伸到宗族的范围里。林耀华说,祠堂为宗族团体生活的中心。明清以来的祠堂合祀历代宗祖,神龛供奉祖宗神主牌位,昭穆排列;宗祠后进,左为厨房,右为议厅。有了祠堂,族规家训便起了作用。族房长和乡长,以及地方上的绅衿遗老组成的祠堂会,则担负起统管宗族的公共责任。此外,在祠堂中,“公众意见由此产生,村规族训由此滋长,全族子孙皆以宗祠的教义信条奉为圭臬”。
林耀华认为,宗族举办的节期、迎会、社戏、祭祖、上坟等庆祝或娱乐活动,往往在一年之中会使日常规定的家族生活“有好几十度的突变”,平常单纯而机械的生活,会突然“改换方式,重振精神”,大家“聚会欢乐,彼此联络,重温感情,加重团结”。这颇类似于涂尔干所刻画的西方中世纪时期围绕法团建立的公共生活,集体意识形成于此,社会团结也凝结于此。只是这种公共生活之基础,中国人是基于宗祠而展开的。宗祠的公共性,既体现为祠堂公所、桥梁河道、族谱文件等为全族人所有,也体现为诸如祭田、园林、屋宇、祠堂、蚬埕等可以带来持续收益的公产。但所有这些,根本目的就是祭祀祖先。
对族人来说,祖先是他们的超验世界的构成,但神明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祖先被供奉在祠堂里,神明则居住在庙宇里;祖先是族内的象征性权威,神明则是族外的英雄偶像;祖灵附于神主牌位,神灵则化身于神像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祠堂会或是族房长的责任便不止于尊祖敬宗了,敬神迎会也是他们分内的职责。在每年的固定时间里,族人都要举行“祭神迎会”,由祠堂会依据房分户数划分出来的“福首”或祠堂会成员轮流担任的“会首”,来分别主持这两种仪式。可以说,民间宗教的信仰和仪式,使得人们的神圣交往领域扩展到了宗族之外,与外族、与国家、与历史以及物质与自然之间构成了多重交错的崇拜体系,进而将社会生命扩展到更为广阔和纵深的时空之中,成为极为混杂的多元的宇宙论系统。
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看,所有这些超大规模的仪式活动,都需要有超出祠堂制度之外的公共参与性组织来筹划实施。事实上,这一地区诸如“加会”或“把社”之类的自愿性团体,往往采取会员制,通过集款、竞标、配股等方式来盘活乡间资源,具有相当强大的集体动员和运行能力。或者说,从祭祖到敬神,从祠堂到庙宇,神圣仪式的扩展,不仅构建了从族内到族外来营造更为广布的神灵交通的世界,社会生命由此得到了更多的护佑,同时也刺激了宗族及其之外的社会参与和组织的范围。文化精神的领域总是与社会经济的领域互构和互为补充,宗教活动的外延,往往是宗族内生社会组织不断制度化和机制化的动力。
结语:作为社会的命运
《金翼》讲的只是福建某地农村的故事,但故事所展开的画卷,却是中国文明由古至今所塑造的普通人的社会生命历程。本文无意美化这样的生命方式,只是提醒今人,我们对此遗忘得过久了。林耀华曾说:“中国人最言实际,而尝把实际忽略。”在他的年代,所有人都追赶着新潮新风,他却在吴文藻等的教诲下,同费孝通等同辈学人一起扎根田野,深入普通人的实际。当所有人迷恋于技术方法,以为靠明证的科学就可探究到社会的真相时,他却主张用同情的、内省的、直觉的办法切入人性的深处,去把握社会生命的气息和脉动。中国人所要的社会科学,一定是基于体验的、反躬自省的、将心比心的科学,而不是所谓功能论、协调论或是均衡论这样的概念空壳。燕京学派从西方学到的,是返于自身、归于自身的自觉反省的认识。因为中国社会之生命本源,就来自于“人和人的心灵交通或精神接触”,就像东林依赖于他的土地、依恋于他的家族那样,任何世间的变故、命运的流转以及国破家亡的危险,都无法割掉他的生命之根。故事的结尾,年迈的东林依然奋力锄地,一架敌机从头顶掠过,孙儿们仇恨地仰视天空,而老人却平静地对他们说:“别忘了把种子埋入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