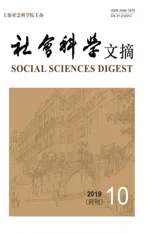“自然规律”概念的历史演进
2019-11-17樊姗姗刘大椿
文/樊姗姗 刘大椿
当下,科学家一般把他们在自然界中发现的可理解、可测量、可预测的规则(regularity)称为“自然规律”。毋庸置疑,近代意义上的“自然规律”概念,对于科学的兴起意义重大,它的含义也是现代科学的基本信条。现代科学所采用的“自然规律”概念并非一种神启,但是过往人们在论及其源起时语焉不详。本文致力于对“自然规律”概念进行语意考释,评析西方语境下关于“自然规律”概念起源的几种不同观点,探讨“自然规律”概念在近代中国何以确立,并试图说明这一概念的建构过程。
“自然规律”概念的考释
两千多年来,围绕自然规律概念而产生的疑惑和歧义,反映了这个词本身的含糊以及人们对它的不同理解。洛夫乔伊(A.O.Lovejoy)曾成功地区分了“nature”(自然)一词在古代至少66种用法,艾力克·沃尔夫(Erik Wolf)也曾列出“nature”的12种意义和“law”的10种意义,而将两者结合就具有了120种意义。所见诸多看法林林总总,莫衷一是,确也能说明“自然规律”这一概念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无疑带有不确定性、易混性和可塑造性。要弄清这一概念,需要做许多功课。在笔者看来,以下问题首先亟待解决:
其一,中文中的“自然规律”究竟是对应于英文中的“law(s) of nature”,还是“natural law(s)”?关于二者的区分,发生在文艺复兴之后。事实上,law(s) of nature中的nature(自然)是为实体,该词组强调的是“是什么”(如:万有引力定律、运动三定律等)。natural law(s)中的nature(自然)乃为性质,该词组强调的是“应当是什么”,如同“natural right”(自然权利),其中“natural”强调“天生的、生来的”。两者从翻译的角度来看,前者直译为“自然中的规律”或“自然规律、自然法则”,后者则为“‘自然的’规律”或“自然法”。值得注意的是,“自然法”并非“自然”(实体)的,而是理性的(自然理性、上帝理性以及人的理性),它有神圣的渊源,源自至高无上的立法者,也可称之为“道德法”或“法理法”。西方自然法学说在本质上是种正义论。简而言之:自然规律或是自然界固有的客观规律,或是人的认识为自然确立的规律。这样看来,本文讨论的“自然规律”应为“law(s) of nature”,而非“natural law(s)”。
其二,近代意义上的“law”源自哪里?是拉丁文“lex”,还是古希腊的“nomia”?“law”一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希腊文“nomia”,但在近代“nomia”一词更多指法律、法规等,直接对应的是“natural law(s)”。尽管西方文明起于古希腊,却并非直接承继古希腊。由于古典文本的失传,中世纪阿拉伯帝国曾经在古希腊罗马和近现代西方之间起到桥梁作用,它们开展过大规模、有组织的学术活动,将古希腊和东方科学文化典籍翻译成阿拉伯文,再经文艺复兴,又把那些翻译成阿拉伯文的文本从阿拉伯文重新译成拉丁文。可以合理推测,英文“law”是从拉丁文“lex”演变过来的。再则,在中世纪的欧洲,拉丁语是研究科学、哲学和神学所通行的语言;直到近代,通晓拉丁语也是研究人文和科学教育的前提条件。因此,讨论近代科学中的“自然规律”概念时,我们应当认真分析拉丁语中的“lex”和英语中的“law(s) of nature”的语义。
其三,英文中“regularity”、“rule”和“law”几个概念的意蕴,在中文的语境下应该如何理解?这三个单词在汉语语境下之所以极易混淆,除了英译汉过程中本身内涵被简化的原因外,还与三者在起源上的相互交织是密切关联的。尽管它们在使用中无法完全割裂,但是现代科学哲学对待三者是有差别的。当我们谈及“regularity”时,更多强调的是自然界现象存在的规则性。至于“rule”,则更多意为治理、实验过程中的“法则”、“规则”。近代科学意义上的“law”,乃是“规律”之意,较之颇为不同。
总之,科学哲学中谈及的“自然规律”一般对应于“law(s) of nature”,源于拉丁文。随着人们认识的加深,该词(“law”)与“regularity”、“rule”等词从初始混用到逐渐分离,最终具有了“实体的自然固有规律或人为之建构的规律”的内涵。尽管后来的实证论、约定论、实在论、建构论者对“law(s) of nature”的诠释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内涵可归结为两类:自然界固有的规律(客观规律),以及人的认识为自然确立的规律。换句话说,自然规律不只是对观察到的规则(regularity)的陈述,也是一种基本规律的形式化表述,也可用来解释或指称广泛的物理现象。科学哲学中各个派别对于自然规律的陈述,无外乎从这两类基本意义衍生而来,最终又将归入其中。无论其内涵如何变化、各学说之间论述的差异如何增大,自然规律始终是科学哲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也是科学认识的目的所在。
关于“自然规律”概念起源的四种观点
“自然规律”概念并非自来有之,对其起源的阐释有利于理解近代科学的兴起以及把握科学哲学的基本概念,因此,本文梳理了其中4种比较有特色的起源说法。
第一,“神的立法”说。就“自然规律”的起源问题,在西方学术界,19世纪到20世纪为近代“自然规律”做出解释的学者几乎都认为这一概念起源于“神的立法”(divine legislation或God's legislating for nature)隐喻。该观点代表性的学者如齐尔塞尔(Edgar Zilsel)、李约瑟(Joseph Needham)、奥克利(Francis Oakley)、弥尔顿(John R.Milton)和冯肯斯坦(Amos Funkenstein)等,他们都认为自然规律概念与神的立法相关。尽管这些学者都将源头指向“神的立法”,但在论述转变的原因时,陈述各不相同。一种观点认为,自然规律的概念转变是伴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资本主义的开端和王权专制的出现而进行的。而在笔者看来,“神的立法”不过为近代自然规律概念的出现提供了文字准备和隐喻。换句话说,“自然规律”与“神的立法”有一定的关联,西方近代以来所使用的“自然规律”术语,是借助于隐喻、模型和类比的途径,从中世纪“神的立法”观念中引申而来的。究其缘由,则愈抽象的概念,愈是要通过隐喻的方式来进行说明。可以说隐喻往往是新概念产生的前奏。
第二,“词源”演变说。即自然规律起源于学者们对拉丁语“regula”、“lex”的使用。“自然规律”并不是隐喻上帝法则,相反,它从一开始就意味着纯粹而简单的规律性(regularity)。在古罗马和中世纪,“lex”与“regula”常常交替使用。“regula”最初的意思是straightedge或ruler(直尺),罗马早期使用的第二种意义的“rule”,它是guideline or standard(指导方针与规范)的意思。同样地,“lex”不仅用于政府或管辖,也用于由当局制定的原则或为各学科实践而制定的原则。公元二世纪时,“lex”和“regula”在学科上意义几乎相同。之后,这两个术语的意义才逐渐变化。由此可见,“自然规律”从产生起就意味着一种秩序与规律性(regularity)。因此,“自然规律”的观念起源于秩序、规则性,起源于从一系列看似杂乱无章的事物、事件中寻找出有规可循的东西,而这种秩序与规则性的思维传统,在西方文明的早期就已经存在,并且为“自然规律”概念提供了思维准备。希腊哲学就是一种认为事物具有秩序的哲学。自然界秩序的原始表达即与那个大名鼎鼎的“逻各斯”有关。到了基督教时代,逻各斯又被引申为上帝造物的根源。近代以来,尤其是在文艺复兴期间,对于秩序、规则性、理性等的格外强调,最终促成了“自然规律”概念的转变和确立。
第三,数学启发说(或自然数学化说)。物理学与数学因其对象的不同,本是两门不同的学科。然而,在近代科学的产生过程中,除了实验方法的推广还有另外一种至关重要的方法,即自然的数学化(或数学化物理)。基于此,有学者认为“自然规律”起源于13世纪到15世纪对于数学知识的的运用。同时,数学定律后来被传递到自然哲学中,进而带来物理定律的产生。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的工作大抵属于这种情况。哥白尼频繁论述和谐与对称,开普勒更是用数学方式来表示行星运动定律。伽利略也没有说他提出了什么规律,而是使用“比例”(ratio)、“原理”(principium)等字眼,这无疑出于对数学—几何量度关系的重视和比附。更为重要的是,笛卡尔在1626年到1629年间发现折射定律时,他试图用网球穿过薄布来解释几何行为的原因,其中薄布代表了折射体的表面并且它会改变物体的折射速度。由此可见,这个过程不是把几何定律变成物理定律,而是寻求物理解释来说明几何理论。可见,自然的数学化推广,为“自然规律”概念的出现与转变提供了方法论准备。自然数学化意味着自然现象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可以用数学语言进行描述的,或者说自然本身的语言就是数学语言,自然数学化运动并非简单地将数学表达运用于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数学化”首先意味着一种全新的自然认识方式,这对于近代意义上“自然规律”概念的提出可以说起到了非常直接的方法论作用。
第四,笛卡尔自然本体说(或自然与上帝分离说)。近代第一个在科学意义上完整使用“自然规律”概念的是笛卡尔。笛卡尔之前,自然规律是对上帝的比喻,而在笛卡尔那里,才将自然规律与上帝分离,并将它外在于上帝。在笛卡尔看来,自然规律就是自然“据以发生变化的那些规律”,并且“神绝对不会在这个新世界里行任何奇迹”。笛卡尔之所以需要“自然规律”这一概念,是因为如果“自然规律”被看作是自然哲学的合理构成,那它就必须具有解释性而不仅仅是描述性的功能。笛卡尔若要建立新哲学体系,自然规律就必须是解释性规律,而不仅仅是数学规律。根据笛卡尔的方法和上帝在他思想中的位置,他很可能是通过神的立法思想和圣经中“物理规律(physical regularities)和定量操作规则(quantitative rules of operation)”的理念,重新创造了“自然规律”的概念。事实上,笛卡尔的自然规律是构成这个世界的机械规律。因此,近代意义上的“自然规律”通过笛卡尔的使用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并经过牛顿而被人们广泛使用。本文认为,与早些时候哥白尼所谓地球运动正是“遵循自然规律产生的效果”,与伽利略的“原理”(如惯性原理)、定量的“比例”关系等相比较,笛卡尔明确指出科学的目标是“自然规律”。笛卡尔的理念对于“自然规律”的起源如此至关重要,更在于他推动了牛顿对于这一概念的使用。
可见,源于拉丁文的“law(s) of nature”,经过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伴随着语言、思维、方法和人为的推动,最终导致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规律”概念得以确定,并成为近代科学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这一概念的起源是非常复杂的。“神的立法”从文字和隐喻角度为近代“自然规律”的出现提供了准备,避免这一科学概念空穴来风,有了易于人们理解和接受的对应物。西方文明早期就有的秩序与规则性思维,经过文艺复兴进一步被激发,人们迫切地希望从杂乱无章中寻求规则与理性,这无疑为“自然规律”提供了成长的思维土壤,使得这一观念被人们使用和认可成为可能。自然的数学化推广,让自然现象不再高高在上,而可以用数学语言的方式进行书写,这就从方法论上促成了“自然规律”概念的发展。笛卡尔引入的一个高度人为的概念,将“自然规律”与上帝分离,赋予它新的意义,并最终通过牛顿被人们广泛使用。可以合理认为,是这些不同起源说协力导致近代科学重要概念“自然规律”的出现。
“自然规律”概念在近代中国的确立
“自然规律”概念在西方文明土壤中是如何孕育出来的,已如上述。那么,它在中国近现代语境中,又是如何引进和确立的呢?过去国人在谈论中国“自然规律”概念的时候,往往有意无意将它限定到中国古代“固有”用法中,并将它看作是中国传统“天”、“理”、“法”、“道”概念的一部分,而对它的由来语焉不详。
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无“自然规律”这一概念,但有类似指称。受李约瑟的影响,许多西方的学者认为,“自然规律”这一术语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甚至认为,因为自身没有在“神的立法”隐喻下诞生近代自然规律概念,终致近代科学也未能诞生在中国。确实,“自然规律”一词在古代中国是没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相应的概念。西方意义上的“自然规律”,类似于中国古人的“道法自然”和“理法”、“天”、“格物穷理”、“道”等概念,中西方这些概念表达的都是一种宇宙观和秩序观。然而,“天”、“道”、“理法”等概念,不同于西方蕴含至高无上的立法者意蕴的“自然规律”概念。中国的“道法自然”概念中的“自然”,是自动、自发、不带人的痕迹、不含造物主的观念。
事实上,“自然规律”概念在清末作为科学概念为人所知,是从日本引进的。甲午战争之后,学习日本的热情高涨。这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学术界,使得“law of nature”经历了从中式译词“理法”到日式译词“自然”、“法则”的演变。通过留日学生和西学的传播,“自然规律”一词最终在中国学者笔下得以确立。
近代日本学者在翻译欧美术语时,会用古汉语固有字词去新造相应的意译词汇。西周在《尚白札记》中,提出将东方哲学中的“理法”对应于英文词汇中的“law of nature”。此外,现代汉语中的“自然”、“法则”、“规则”这几个词也都源自日本。此后,留日学者通过学习与传播西学,将日本的新学、新知等进行翻译,并在关键术语的使用上或保留或重组了日本学者们的译法。1906年,严复在《〈阳明先生集要三种〉序》中,主张人们要面向“自然”去求知,他使用的“自然”已非古代中国老子意义上的“自然”,而是从客体和对象实体意义上来谈论了。更重要的是,严复还使用了“自然规律”、“自然规则”、“自然律令”、“自然公例”等概念,这与他原先习惯于联系传统中国文化术语,从英语直接翻译、移植西文于汉语不同,而改用“自然规律”这一术语来代替先前所使用的“理法”、“天行”等译词了。
“自然规律”一词的出现,对近代中国科学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近代国人用“自然规律”代替词意生涩、复杂的“道”、“理”等概念,实有利于人们准确地把握科学概念,也有利于人们将科学知识与儒家伦理进行区分,便于西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
从古拉丁语“lex”到英语中的“law of nature”,再到日语中的“自然”、“法则”,之后汉语吸收日译术语,在近代西学传播的过程中将“自然规律”一词确定下来,最终成为世界性的科学研究的核心术语,这就是自然规律概念的历史演进概要。作为近现代科学基本概念的“自然规律”,其起源和演进不是一个突变过程,也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确有语言、思维、方法等方面的积累和准备。每个时代对于这一概念理解上的差异,都会激发对该概念的重新诠释与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