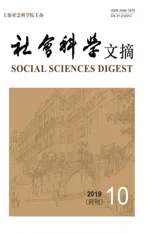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历史之维
2019-11-17郭台辉
文/郭台辉
在知识生产体制转型的大变革时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更加注重从本土历史经验出发,在自身历史及其他文明传统中汲取知识资源,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文明的宏观历史进程,探索中国历史、当下与未来的连续统一性,寻找中国国家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历史智慧。那么,社会科学如何与历史研究结合呢?这个方法论问题可以从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历史传统中获得启示与教训。
西方社会科学的三种方法论传统
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发韧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哲学家们开始把物理学和数学的成就,如方法、概念、命题与定律,应用到社会政治秩序的设计与想象,最终的目标是建立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但是,科学领域内部存在两大传统的分化:培根、牛顿和洛克开创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和笛卡尔奠定的法国理性主义传统。其中,英国的经验科学传统反对普遍的自然法则,认为道德哲学必定是实验科学,而政治学和法学及其相应的历史研究应以经济科学为基础,采用经验归纳与因果推论的方法,建立以政治经济学为主的社会科学。法国的理性科学传统则力图在社会政治和历史领域寻找普遍一致的理性法则,要求用统一的数学方法和概念来分析社会政治结构。人口、经济、国家、心灵与习惯等原属于讨论人性、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等抽象话题开始成为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到18世纪末,启蒙哲学家才开始把“社会”视为“第二自然”,主张在物理学与生物学主导的自然科学之下建立一门“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
孔德确立的实证主义传统综合英法两种启蒙哲学传统,整合物理学的静力学(秩序)与生物学的动力学(进步),调和经验科学与理性科学、保守派与激进派之间的争论,运用以社会观察为主的,以实验、比较、历史为辅的自然科学方法寻找支配社会现象的普遍法则和社会运转的因果规律。实证主义传统同时也是对19世纪法国大革命后浮现的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孔德深刻洞察到启蒙运动过度张扬个体自由而忽视更根本的社会整体秩序与进步,必然带来结构性震荡的社会政治危机。在孔德看来,个人行动服从于社会整体,社会发展规律服从于更稳定的自然法则,人类社会才能确保秩序与进步的统一。为此,必须以自然科学的知识、方法为基础,发展一个专门研究人类社会的学科,孔德将它命名为“社会学”。孔德的实证哲学体系不仅影响到同时代的欧洲知识界,比如密尔的逻辑哲学、斯宾塞的社会学以及“实证史学派”,而且通过涂尔干的扬弃与转换,对20世纪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科学产生巨大影响。
马克思与孔德都发展了圣西门关于整体重构社会新秩序的新设想,把政治纳入社会整体并进行科学考察。此外,马克思还批判地继承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传统及其两个原则,即总体性与矛盾性。但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唯心论,却坚持唯物论的总体性原则。唯物论的总体性原则表现有二。一是时间维度的历史总体性。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人类历史总体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和社会形态,而每种社会形态的社会关系都要历经诞生、展开、危机和自我扬弃的过程,从而逐渐过渡到新的阶段与形态。二是空间维度的社会关系总体性。马克思既考虑到“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的总体社会关系。总体性原则离不开矛盾性原则。辩证法强调批判性分析社会现象的内在矛盾,而矛盾的对立统一性让事物不断扬弃自身,以新的形式推动社会总体向高级阶段发展。这意味着科学研究不能停留在感性到理性、具体事实到抽象命题的实证逻辑过程,应该进一步运用抽象思维把握具体的社会实践。因此,马克思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原则包括,相对于多层多元社会关系的整体有机联系,相对于社会生活各部门与各领域的各种具体制度的总体规范,相对于阶段性历史存在的人类总体历史过程与发展规律,社会内部各领域的矛盾变动及其辩证运动构成了社会总体的历史变迁。
与孔德-涂尔干的实证方法论把社会视为统一同质的结构实体、马克思的辩证法把社会看作人与人之间关系汇集而成的动态总体不同,马克斯·韦伯提出个体实在论,把社会视为名义的存在,而参与社会行动的个体才是社会的真正实体。由此,韦伯开创了一种阐释学传统。韦伯与马克思一样,高度关注人在社会中的存在,但他理解的“人”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类的人”,不能结合成特定的“阶级”群体。韦伯主张独特的、具体的历史个体,其行动承载特定的文化价值与意义,是有目的性、非常规性的意图和动机,由此构成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特征体现为,“悬置”价值与文化层面的任何争论,权宜性地提炼并运用“理想类型”的特定概念,以“工具箱”的方式,理解与阐释个体行动“意图”中偶然多元的因果关系机制。
因此,孔德-涂尔干传统的“社会”是稳定秩序形态的“强结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在其中发挥不同的功能作用;马克思传统的“社会”是一个“动态过程”,由特定社会关系主导的“经济-社会”领域统摄;而韦伯传统的“社会”则是个体行动“意义之网”的“弱结构”,归属于“文化”的总体范畴。三种方法论传统作为“科学革命”的结果,都把“科学”视为一种理解与解释世界的思维方式,反对神学与形而上学,是超阶级、超利益、超价值的研究手段。它们充分运用经验、理性、客观的科学思维来理解人类社会的构成与运转,共同关注由法国大革命与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带来的现代性问题。
三种方法论的历史之维
社会科学对人类社会整体与部分及其间的联系进行全面考察,不仅要考虑空间维度,关注普遍世界与部分区域的具体表现及其间的关联性;还要重视时间维度,考察普遍历史与特殊阶段的形成过程及其变迁路径。19世纪奠定的三种方法论传统都认识到社会科学的时间维度,即方法论的历史之维。方法论的历史之维呈现三种形态,即孔德传统的“历史的社会科学化”、韦伯传统的“社会科学的历史化”与马克思传统的“历史科学”。
第一种形态是孔德传统的“历史的社会科学化”,它融合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两种启蒙传统。经验主义传统认为,科学知识的形成遵循归纳逻辑,这种研究逻辑同时适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历史研究,据此,培根把自然与社会的历史视为同一进程的整体,成为人类经验与知识的来源。此后,苏格兰的启蒙思想家,如吉朋、弗格森、亚当·斯密、休谟、马尔萨斯等人的历史著作都遵循经验主义的归纳研究传统。然而,法国笛卡尔开创的理性主义传统反对从感性到理性的知识探索逻辑,要求以数学的推导与演绎为基础,寻找绝对精确的理性知识。相应,历史研究必须有益当下时代,并以怀疑与批判的原则提供确凿真实可靠的史料。伏尔泰由此原则首创“历史哲学”概念,并结合英国的经验研究传统,为历史研究提供“理性之光”。此后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在专题史和普遍史中落实物理学与数学原则,旨在寻找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所以,实证社会科学把历史作为检验理性法则的“试验场”,历史研究则为之提供证据材料。
第二种形态是韦伯传统的“社会科学的历史化”。维柯的《新科学》抵制笛卡尔的唯理哲学,开创历史主义的哲学传统,严格区分普遍数学的“自然世界”与普遍历史的“社会世界”。前者是共同的、抽象的“物的科学”,而人类历史却是特殊的、个体的、具体的“人的科学”。后来,赫尔德、歌德、洪堡、兰克、黑格尔等德国历史哲学家们进一步完善历史主义传统,要求从具体的历史来看待宏观历史变迁的阶段性与规律性。此后,德国知识界出现了历史与哲学之争:兰克学派尝试对探讨具体性、独特性的历史学与追求普遍性、抽象性的哲学进行切割,在普遍历史下考察具体性和特殊性;新康德学派的狄尔泰等人主张历史阐释学的方法论,通过主观表意方法来理解和阐释历史个体在具体文化情境中的行动意义。韦伯开创阐释学的社会科学传统,就是为了调停德国历史主义传统中长期存在的历史与哲学、个体与整体之争。首先,社会科学作为一种逻辑的、客观的分析手段,用于发现社会行动的客观事实及其因果联系,从而更准确地理解特定行动在文化体系中的独特意义和价值。其次,作为倾向于经济史的历史学家,韦伯要求理论的自主性对历史学让步,社会科学的理论化、类型化与概念化只是阐释历史现象的权宜手段,在此过程中应始终保持价值中立。最后,在社会科学内部,社会学应该对经济学让步,因为社会并非实体,只是个体的“意义之网”,而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活动才具有社会属性。因此,社会学在文化、政治与经济之间丧失独立存在的理由,只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分析工具,历史才是本体。
第三种形态是马克思的“历史科学”。马克思扬弃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回到现实社会中的人及其物质劳动实践的生产关系。“社会”作为“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是理解现实历史发生过程的基础,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通过人的具体物质劳动过程,历史时间与社会空间成为一个完整的总体,而“历史科学”是“人在实践上的自我实现的产物”。自然因人的劳动而获得社会属性,人、自然、社会及其历史过程都统一到“历史科学”范畴。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与“辩证法”相一致,在逻辑上贯通了总体性和矛盾性原则。总体性原则体现为两个层次。在规范层次上,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黑格尔,认为历史在摆脱异化和否定阶段之后,“个人关系与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能够通向未来更高的完满阶段;在经验层次上,马克思不赞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利决定论和黑格尔的观念决定论,认为社会是个人社会关系的总体性。因此,总体的社会科学与总体的历史研究紧密结合。同样,“历史科学”在两方面运用矛盾性原则,让经验的总体历史贯通规范的总体未来。其一,经验上的生产关系形成阶级关系,并最终产生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是推动历史变迁的根本动力;其二,在规范上进一步挑战黑格尔的思辨认识论,认为知识不是黑格尔意义上那种抽象的形态,而是深入参与到人类的实践之中。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三种历史之维差异很大,但共同之处在于反思现代性问题的历史形成并探索化解之道。一方面,通过历史反思与批判,三种方法论传统充分肯定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思考“三大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与法国革命)改变(欧洲)人们生活世界的现代性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历史重建,他们把经验世界的过去、现在、未来融汇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尝试寻找当下与未来的确定性,在消除形而上学影响的经验世界里找到问题的根源与变革的力量。
方法论历史之维的迷失与复兴
19世纪的现代性问题是第一次以社会政治危机的方式“涌向”欧洲社会,从而激起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诸多相冲突的新兴思潮。这些新思潮与新意识通过新兴的世俗大学以及诸如涂尔干与韦伯等人的集体努力,到19世纪末都完成了学科建制化,并在民族国家建构与巩固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三种方法论传统在科学与社会政治领域的地位并不均衡。其中,实证主义得到资产阶级及其政权的欢迎而占主导地位,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这种“资产阶级哲学”的批判武器,而后起的韦伯阐释学则是一种权宜手段。实证主义之所以占主导地位,在于它不仅是一种科学方法论,还是一种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社会政治思潮,服务于现代国家与现代民族的双重建构。
在实证主义的主导下,社会科学与自由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存在本质性关联,反映现代国家建制对工具性知识的需求。社会科学内部的知识生产按照自由主义国家形态的原则进行功能划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分别对应研究市场、政治与社会生活三大领域,而人类学专门用以研究西方文明之外的国家与地区。相应,社会科学各学科按照不同的科学论假设与认识论逻辑分化发展,在不同领域落实个体论与整体论原则,从而消解二者的长期争论,各自为现代国家提供有条理的系统知识。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不再结合历史研究,专注于现时空间中的社会、经济或政治等局部事实,知识生产必然带有意识形态特征,并服务于特定国家的政权和党派组织。
从此,在实证主义(知识)与民族国家建构(政治)相互作用的影响下,社会科学与历史学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具体实践进行时空切割与研究分工。但两大学科范畴又不乏有共同之处,如追求价值中立,自认为追求严谨的科学研究,接受大学建制和国家财政的庇护,强化由上层社会精英主导的意识形态,主要是民族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与西方中心论。随着欧洲主要民族国家建制的完成,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不局限于科学研究,还致力于增强现代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合法化。
但是,实证主义无论作为一种方法论还是社会政治思潮,从19世纪前期的孔德开创到世纪末的涂尔干发展,依然坚持社会整体论的认识论传统,与历史研究依然存在方法与材料来源的关联。这与英国近代发展出来的个人主义观念传统无法完全相容,与20世纪之后摒弃历史而完全转向当下的主流社会科学也有距离。19、20世纪之交西方社会科学进入了历史转型期,这种转型受益于科学论内部的观念竞争与外部的文化历史传统两个因素的结合。
在科学论内部,个体论在世纪之交开始占上风。19世纪后半叶,在凯恩斯、帕累托等人的推动下,个体论为基础的经济学得到了长足发展。同时,生物医学和生理科学发展出心理学,不仅成为典型的实验科学,而且为个体行为的微观决定机制提供了科学的心理基础。实证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从宏观社会的群体与结构成功转向微观行为的个体,并彻底独立于抽象的道德哲学和纯粹的自然科学。
科学论的外部变化在于英美世界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新重镇”。其中,英国的社会科学领域以文化保守主义与社会进化论为基础,配合对内自由主义与对外帝国扩张这种悖谬结合的国家政策。美国作为没有历史的新大陆与新国家,使社会科学更注重当下社会的行为变化与政策调整。当时,欧洲大陆大量的知识精英逃离祖国,把他们所建构的各种抽象理论体系带到英美知识界,但后者却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碎片化的知识无法对社会进行总体的理解与解释。
显然,在个体论替代整体论的同时,英美知识界为实证主义方法论找到了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撑,并发展出以实用主义与逻辑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社会科学主流范式。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延续经验主义传统,强调经验观察、归纳与实用优先于理论。而以默顿为代表的逻辑经验论者吸收理性主义传统,要求社会科学追求不受时空条件限制与价值无涉的普遍科学知识,以此指导社会实践活动。帕森斯引入并改造韦伯的个体行动理论,主张一切社会生活源于有目的和意图的个体行动,但解除其历史与文化情境的约束。
从此,英美主导的西方社会科学摒弃历史意识,只顾具有时效性的当下问题,失去了对现代性问题的阐释与批判力,而确立个体及其行动为分析单位,又让社会科学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关联起来。
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与学术研究的重心转向缺乏历史感的美国,使美国社会科学倒转为欧洲及其他地区社会科学的蓝本,即定量化、精细化与技术化,进一步强化国际社会科学的去历史化趋势。同时,社会科学泾渭分明的学科建制及其个体-行动、结构-功能的系统整合与战后美国的政治发展高度吻合,把世界与历史纳入以美国为学术中心的解释体系,把“现代化”作为社会科学参与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目的是建构以美“新帝国”为中心的世界霸权体系。
然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美世界开始“涌现”新一轮现代性危机。这再次激发了社会科学的批判意识与历史意识,马克思的批判传统得以“回归”。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深受马克思的启发,认为社会科学应该是“探讨个人生活历程、历史和它们在社会结构中交织的问题”。欧陆兴起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社会理论也重启马克思主义传统,反思启蒙理性与资本主义体制。此外,逻辑经验论者把历史纳入分析哲学的普遍解释范畴,主张历史研究像自然科学一样发现人类发展规律,为主流的自由主义社会科学重新进入历史领域提供科学哲学依据。20世纪60年代末,一批社会科学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及布洛赫与埃利亚斯等欧陆史学传统,突破结构-功能主义藩篱,形成新的历史解释路径。
现代性危机再次把批判传统与历史意识带回西方社会科学,形成了几种“转向历史”,但这些转向都不重视“时间界限”,只是采用非经验、非方法论的非历史视角。由于缺乏共同的历史观念和统一的世界观与认识论基础,这段时期的“转向历史”仅仅停留在方法、概念与材料方面,不能真正复兴方法论传统的历史之维。相反,社会科学“转向历史”因沦为“社会学的历史想象力”而失去意义,导致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呈现相对化、碎片化与无意义化的趋势特征。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欧盟一体化、苏东剧变以及9·11事件后全球性的恐怖主义危机进一步冲击西方既定的民族国家体系,全球化时代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使西方社会科学正失去民族国家的制度基石,以自由民主为价值预设的实证主义传统也受到了批判。由于自由主义的社会科学无法直面从现代性问题到全球性问题的视域转换,一些社会科学家开始自我反思与重新探索。一方面,社会科学需要重新担纲现代性问题的批判角色,转变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及其时间观念;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必须摆脱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发展主义等意识形态的束缚,检讨现代社会科学的历史形成,重建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的结合方式。
余论
近代西方社会科学源于“科学革命”,但成型于19世纪确立的三种方法论传统。19世纪是后革命时代的社会危机、资本主义危机、精神信仰危机相交织的不确定时代,社会运动频繁、国际格局复杂与思想流派纷争,形成现代性的总问题域。社会科学的三种方法论传统均有历史维度,是顺应历史潮流,理解和解释现代性问题的历史形成,回应与化解时代危机,维护秩序与推动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但受不同历史观念传统的影响,历史研究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传统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形成不同的历史之维。历史研究在实证主义传统中作为“用”,在阐释学传统中却是“体”。在马克思辩证法指导下,超越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之间的“体”“用”之争,将二者融为一体。
西方社会科学的历史并不漫长,三种方法论传统及其历史之维也有清晰的变迁路径。但到19、20世纪之交,西方社会科学在晚清“西学东渐”的特殊历史时期传入中国知识界,造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长期以来的依赖性发展。历史时期的“特殊”体现主要在:其一,西方社会科学本身正在从近代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时刻,恰逢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建制基本完成,又遇美帝国与欧洲诸帝国的新旧交替;其二,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的各自内部以及之间进入高度分化、民族化与国家化的关键时期,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传统及其历史之维也正在分化,各学科受经济学与心理学以及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综合影响,走向无历史意识的个体行为研究,结果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始于各学科的分化建制,自发引入不同国家的学科门类形式,却屏蔽西方科学论领域的内在争论与变化;其三,引入西方社会科学的季清民初之际,中国社会恰逢内忧外患,从统一走向分裂,是传统向现代急剧转型的历史时刻,仓促舶来的社会科学知识不成体系,失去独立性与自主性,也无法与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实践需要结合。
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都是连续不断的历史统一体,而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又面临共时性的构建。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的结合必然同时具备中国性与世界性、时间性与空间性的二重特征,需要立足于当代科学研究的前沿,重视时空交织的社会整体及其知识属性,把社会与自然纳入同一历史整体和变迁进程来研究。因此,中国社会科学要重申马克思“历史科学”的方法论传统,而不是延续西方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的体用之争,进一步批判实证主义传统的无历史意识,抵制阐释学传统的知识碎片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