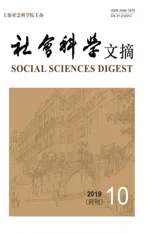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视阈下的“社会史”书写及其演变
2019-11-17李政君
文/李政君
近代中国史学史上的“社会史”书写,肇端于中国史学新旧更替之际,随着现代历史学理论在中国的逐步建构而演变;因国内政治形势变化而勃兴,又因之而顿挫。可以说,“社会史”书写的演变,不仅展现了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复杂历程,而且反映出政治对学术的深刻影响。
20世纪初的“新史学”与“社会进化史”
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人所倡导的“新史学”潮流,以批判中国“无史”和书写彰显人类进化之“公理公例”的新史为主要特征。中国的“社会史”研究即滥觞于此潮流中。
与“新史学”主体诉求相应的“社会史”是“社会进化史”,这也是较早被冠以“社会史”称号的。就理论诉求而言,此种“社会史”和“新史学”理念并无根本差别。如1907年《复报》发表一首七言律诗《读社会史》,就诗文内容看,其所说的“社会史”就是指人类社会的进化史。1916年范祎《社会史之创造》和1919年伦达如《社会进化之历史》,也都是试图突破政治史范畴,探寻整个社会“进化之历史”。
在史学实践方面,二者同样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如喜渥恩编译的《罗马社会史》,就是由帝政、民权、宗教等19个专题组合而成。这种看似囊括万有、稍显博杂的结构,正体现了“析之皆可成为一种别史,而合之则总名曰社会史”的认识。这一时期出现的新式历史著作,如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等,也表现了相同特点。这些学者并不是要排斥政治史,而是要增加政治史之外的其他门类,以补足社会的“整体”。
这种“社会史”与20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共享了相同的历史学理念,其历史观是进化论的,历史思维或历史哲学是实证主义的,他们要书写的都是“社会进化史”。
民史、民俗与“民众社会史”
20世纪前半期,不少学者曾努力发掘“下层”民众社会的历史。这些学者专业领域不同,研究内容涉及社会风俗、民众信仰、婚丧嫁娶等多方面,但他们表现出相同的取向,即均以梁启超“新史学”中所强调的“民史”为研究对象。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顾颉刚。
顾颉刚所说的“社会史”,主要以对传统学术纠偏为目的,以“下级社会”为研究对象。其见之行事的探索,主要集中在民歌、民间故事和民众信仰三方面,今天常被归于民俗学领域。但就其研究旨趣而言,则始终没有离开对民众社会历史的关注。顾颉刚对民歌价值的衡估,本就偏于民众社会之情状。在民间故事方面,也是试图透过故事的转变窥视整个历史文化迁流演变的脉络。在民众信仰方面,同样具有上述特点。顾颉刚关注民众历史的高峰,在1927年移席广州中山大学后。当时他倡导的“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等,与此前提及“社会史”时所说的“了解各种社会之情状,尤其注意于向来隐潜不彰之下级社会之情状”学术取向一般不二。
这一时期,有一大批学者与顾颉刚形成了呼应之势。1927年11月成立的“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学会”,成员就包括不少历史学者。由董作宾执笔,具有发刊词性质的《为〈民间文艺〉敬告读者》的旨趣,和顾颉刚“建设全民众的历史”的倡导,异曲同工。在这种思路引导下,由钟敬文、容肇祖等先后主编的《民俗周刊》,也曾经刊发了大量关于“民众历史”“民众文化”的文字。
除直接产生于民俗学活动中的大量作品外,当时史学界有些史家通过勾稽传统史料,也编撰出一些着眼于“下级社会”的著述。如1928年瞿宣颖《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以《汉书》材料为主,分社交、习俗、衣饰等16篇,考述西汉社会风俗制度。1933年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一书的编撰,同样缘于对汉代社会风俗问题的关注。
从整体上看,上述学者并非全都有“社会史”的概念自觉,但其大量成果,确实构成了近代中国史学史中“社会史”书写形态之一。从研究对象看,这种“社会史”和梁启超倡导的“民史”极为相似,但与梁启超批判“君史”“旧史”不能见社会进化之“公理公例”、不能提振民族精神而提倡书写“民史”“新史”相比,在这些学者的研究中,学术外的关怀相对弱得多。和20世纪上半期其他“社会史”研究者相比,这些学者既没有统一的方法工具,也没有整齐划一的理论规范,他们所具有的共性,主要是发掘被传统史学所忽视、掩盖甚至是歪曲的民众社会历史的真相。
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与“社会史”概念的多样化
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以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历史为主要特征,但它不是某一家一派的主张,没有形成某种固定的范式,甚至连“社会科学”是什么,不同史家也各说各话。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史”是什么,也愈益变得捉摸不定。
以往学界多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取向追溯至清末。不过,就整个史学界而言,此时的认知距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化还有一定距离。20世纪早期,受日本学者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浮田和民《史学通论》等著作影响,中国学者编译的“史学概论”“研究法”一类著述中,基本都出现了类似“史学之补助学科”或“辅助学科”的内容。但这些“辅助学科”,本身即与历史学关系密切,而且,这些学科的“辅助”功能,主要集中在史料或史事考订层面。这和20世纪20年代以后,借用社会科学理论来解释历史现象的取向,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别。
借助社会科学理论方法解释历史发展演变,真正形成一股思潮,大致出现在五四前后中国学者开始直接引介西方历史学理论的过程中。在当时学界形成较大影响的,当属美国学者鲁滨孙的“新史学”理念,其首要特征即强调历史学要与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新兴社会科学“结盟”,以解释“许多历史家所不能解释的历史上的现象”。
重视用社会科学理论来解释历史现象的观念在中国学界的广泛传播,对中国史学真正走上社会科学化道路,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中国学者编撰的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类著述,绝大多数都出现了类似“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内容,阐述“其他学科”对解释历史的助益,强调社会科学对历史解释的重要性。这说明,此时社会科学化已经演变为一股史学潮流。相比早前,这些学者所说“其他学科”对于历史学的价值与意义,逐渐从“补助”史料或史事考订提升到了历史解释层面。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也是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中的一次实质性的进展。
随着多种社会科学理论被纳入历史解释体系,当时学者对“社会史”概念的界定,也出现了多样甚至混乱的状况。择要列举如下。
第一类是从史学观念演变的系谱中对“社会史”作出的界定。如1921年陈训慈《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一文。他所说的“社会史”,是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以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风俗论》为代表,突破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的历史书写传统,主张历史学应记录人类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史学思潮。
第二类是按照社会科学的学科属性来界定的“社会史”。如1926年李璜在《历史科学与社会科学》一文中,将社会科学分为“单数的”和“多数的”:所谓“单数的”实即由孔德所创立的社会学学科;“多数的”实即社会科学的诸学科。他认为:社会学者“研究人类社会在历史上继续的活动”,“寻求社会的进化(progress)与他的公律”,是“社会史”;而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相对应的专门史,也是“社会史”。可见,李璜对“社会史”的界定是从社会科学的学科门类着眼的。
第三类更为特殊的“社会史”,是1930年张宗文翻译法国学者瑟诺博司《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一书的说法。该书所说的“社会科学”是专指“统计科学,其中包括人口统计学”“经济生活的科学”“经济学说史与经济设计史”;所谓“社会史”也只包括人口的历史、经济现象的历史和经济学说史。这种定义是作者基于西方社会科学发展历程的独特考量,尚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然而,当时何炳松以此说为基础,编成《通史新义》,却造成了“社会史”“社会科学”等概念不必要的混乱。该书在“通史”“社会史”等关键概念上,保留了当时学界较为通行的观念,但在具体界定“社会科学”和“社会史”两个概念时,却取自上述瑟诺博司《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中的特殊定义。所以,何炳松《通史新义》一书实际上杂糅了两套概念体系,即当时学界一般意义上的“通史”“社会史”“社会科学”等概念,和瑟诺博司《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一书中的特殊概念。这种作法不但造成《通史新义》本身颇多不通之处,而且造成学界对“社会史”概念理解的混乱。
第四类是我们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社会史”,以1924年李大钊《史学要论》为代表。从研究对象上看,李大钊所说的“社会史”仍是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历史,并无独特之处;其独特之处主要是,在他看来,要解释这种发展、进化现象,只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才是最科学的。
以上即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背景下出现的较具代表性的“社会史”概念。这些稍显多样甚至混乱的“社会史”,实际仍具有相同的大前提,即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特点。这一点,与20世纪初期“新史学”思潮中的“社会进化史”并无不同。其不同者,主要有两方面。第一,“社会进化史”所依托的理论,主要是社会进化论,而此时诸种“社会史”所立足的理论,则是多元的。这一变化所反映的,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近代中国史学界,从进化论一家独大,到日趋多元的传播特点。第二,“社会进化史”虽也是探求社会发展演变的规律、特点,但这种规律、特点,实际是既定的,即“进化”。也就是说,“社会进化史”多少有让中国历史去迎合“进化”规律倾向。而在上述诸种“社会史”中,这一特点虽也存在,但就整体而言,社会科学理论的方法工具属性得到增强,此时学者关注更多的,是如何用社会科学理论,去解释“许多历史家所不能解释的历史上的现象”。这一变化所反映的,是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中,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之间主客地位的渐变。不过,这一时期相关理论阐述虽然如花似锦,却并未结出相应果实。
中国社会史论战与唯物史观社会史的勃兴和分化
当一些史家在史学社会科学化潮流中龂龂于社会史理论之辨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社会史”,却在因中国国内政治局势转变而兴起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迅速崛起,并以作品数量的压倒性优势近乎统一了学界对“社会史”理论范式和书写内容的认知。这一时期的“社会史”,基本都成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社会性质、形态史的研究。不过,唯物史观社会史自身形象也因此被“拖累”,并使之最终走向分化。
当时学界对唯物史观社会史的积极反应,可以1930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反响为例。民国时期不少史家都肯定了该书的价值,其中较能说明问题的,是1932年张荫麟对该书的称赞,他将该书与顾颉刚《古史辨》(第2册)并举为1930年我国史学界最重要的两种出版物,并称该书“例示”了“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所以获得如此好评,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契合了当时史学发展的趋势。一方面,当时史学主流取向依然偏重史料考据,研究领域偏于上古史。在“古史辨”大刀阔斧地摧毁中国旧有古史体系后,人们迫切期待新古史体系的建立;随后殷墟考古的重大发现,又让人们把这种期待寄托在了考古新材料上。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不但以新的视角重新建构出一幅上古社会的演进图景,而且这一重建利用了当时关注度较高的甲骨金文材料。这是该书与当时“新考据派”的契合。另一方面,在社会史论战之前,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趋势已十分明显,但始终没有出现一部真正有影响力的著作。而利用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历史发展,正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特色。这是该书与史学社会科学化潮流的契合。因此我们说,1930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实际是恰逢其会地将近代中国史学上两股重要潮流结合在了一起,并有意识地将历史研究从“整理”转向了“解释”。这不仅是为古史研究,而且是为唯物史观社会史研究,“例示”了“一条大道”。
但是,由于当时人们急迫地要从中确定中国社会性质,为中国革命寻一条出路,造成唯物史观社会史研究日益走上了“公式化”道路,使其总体学术水准并未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基础上向前推进多少,反倒是让多数“学院派”史家产生了反感。论战高潮过后,唯物史观社会史研究开始重视夯实史料基础,逐渐转向学术立场,然而此时该研究取向也出现了分化。
唯物史观社会史研究转向的标志性事件,是1934年12月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将唯物史观社会史从“政治宣传”转向学术研究,特别重视史料搜集。陶希圣通过《食货半月刊》和高校任教,影响和培养了一批史学新秀。他们的社会史研究,明显偏向了经济社会层面,且在具体选题上呈现出多元化特点。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唯物史观影响,但在研究旨趣上弱化了对中国社会性质、形态、革命道路等问题的争辩,而主要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材料,发掘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变特点。社会史论战高潮过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论战中出现的问题也进行了反思与批评。不过,他们并没有因此削弱历史研究的革命性和阶级性。因此我们说,唯物史观社会史在中国社会史论战高潮过后,出现了“社会经济史”和“革命史”路向的分化。
从整体上看,唯物史观社会史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是较为深远的。首先,论战以其宏大的声势和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作品数量,近乎统一了人们对“社会史”的认知,使唯物史观社会史成了时人观念中最主要的“社会史”类型。其次,唯物史观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一批以考据见长的史家。复次,社会史论战影响了一大批学界新秀的学术取向。即便抛开政权鼎革影响,当史学界完成代际更迭后,中国史学面貌也会为之一变。这是唯物史观社会史影响近现代中国史学走向方面至关重要的一点。最后,唯物史观社会史在论战中虽曾出现“公式化”等弊病,一度使历史研究变成社会发展理论的附庸,但从另一方面看,论战中产生的大量作品,对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从理论诠释落实到研究实践,确实具有推动之功。而且,论战高潮过后,随着学界对“公式化”等问题的反思与纠正,在唯物史观社会史研究中,也确实逐渐调整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主客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