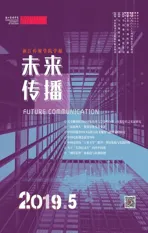社交媒体使用中印象管理与公众的自尊、自我监控之实证研究
2019-11-07刘翠红
牛 静 刘翠红
作为社交媒体的微信,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交流工具,用户在此平台上沟通感情、获取信息。根据腾讯2017年最新发布的数据,微信月活跃用户达到了8.8亿,平均每人有120个好友。[1]微信对于人际关系的维护效果显著,有助于建构人际之间的“强关系”,并在这种“强关系”中进行人际互动。当存在社会交往与人际互动时,不管个体所处的情境是虚拟的还是真实的,人们往往试图控制信息的呈现以影响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从而在他人心中树立一个符合自我期望的形象,这一行为过程就是印象管理。
社交媒体成为用户进行自我展示、印象管理的平台。研究发现用户在微信中的自我呈现与现实相比,伪装的成分更少;[2]在微信朋友圈中的信息以展现自己积极向上的生活为主。[3]现有研究较少去探讨影响用户印象管理过程的因素。本文以用户微信朋友圈的使用为研究对象,分析在印象管理的过程中,个人人格特质,如自尊和自我监控对印象动机、印象建构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
(一)印象管理的定义与发展
印象管理的研究由来已久,且研究视角各不相同。戈夫曼(Goffman)基于符号互动论的角度,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提出“印象管理就像戏剧表演”[4],任何人在社会中的交往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戏剧表演”,每一个人都是演员,并“总是尽量使自己的表演接近自己想要呈现给观众的那个角色”,从而塑造他人眼中的自我社会形象和身份。持该视角的研究者会认为,每个参与活动互动的人都必须尊重和维护其公共形象,甚至为了避免社会冲突和减少紧张,人们可能会不真实地表达自己,并不说出他们真正的想法或感受。[5]琼斯(Jones)将印象管理引入心理学领域,基于操作控制论的视角,认为印象管理还包括“人们会主动控制他人对自我的印象”。施伦克尔(Schlenker)认为印象管理是自我调节和认知的过程,[6]提出印象管理是“个体试图影响他人对自我认知的做法”以及“有意或无意试图控制在真实与想象的社会互动中所反映出的自我留给他人的印象”,[7]以此让自己在社会交往中获得想要的结果。
随着印象管理理论在商业领域的使用,学者们基于印象管理策略这一视角进行研究。艾坚(Arkin)认为印象管理是指“个体在与他人互动情景中,计划、采纳和执行一种传达自我形象的过程和方式”[8],他从个体印象管理的具体行为表现入手,区分了获得性自我表现和保护性自我表现。获得性自我表现是自我积极主动地采取行为活动进行印象管理,以此获得他人的赞许和建立一个被他人认可的社会角色;[9]而保护性自我表现是一种消极的管理策略,不是去创造好的形象而是竭力去避免不合适的自我形象,避免受到指责。[10]泰洛克(Tetlock)等将印象管理分为防御性印象管理和肯定性印象管理。防御性印象管理是对已有的社会形象进行保护,它被消极的情感状态所引动,感受到外界对自己形象的威胁并进行自我调节管理;肯定性印象管理是对个体的社会形象进行改善,被自我知觉动机所引导,对某些会构成被赞许印象的环境进行把握并采取行动。[11]
以上研究都是基于印象管理的定义、策略而进行的,1990年美国心理学教授利里(Leary)和科瓦尔斯基(Kowalski)提出了印象管理的两成分理论,认为印象管理的过程分为印象动机(Impression motivation)和印象建构(Impression construction)两部分。[12]
印象动机指控制或调控自我在他人心中印象的个人意愿程度,也可以理解为,在我们想要在他人心中创造一个好的印象之前,我们必须有动力去开始这个创造过程,这个动力就是印象动机。[5]动机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印象与目标间的关系,印象与个人目标相接近时,个人进行印象操控和管理的意愿就越强烈;二是目标的价值,越有价值,个人进行印象管理的动机也就越强烈;三是期望形象和已有形象间的差距,当他人心中的自我形象与目标形象差距较大时,进行印象管理的动机更强烈。[12]印象建构则是选择要创造的印象,并为这个印象的形成采取一些行为的过程。[12]社会交往中的一些因素会对公众的印象建构造成影响,其中自我概念、所期望的自我身份、个人角色的约束、目标的价值以及潜在的社会形象等是影响公众印象建构的因素。
基于印象管理的概念两成分理论,本研究认为印象管理是个人基于一定的印象动机而采取措施进行印象建构,从而塑造出自己所期望的个人形象的过程。在社交媒体上,公众使用微信朋友圈进行自我表露、自我展示,可以视为是基于一定印象动机进行印象建构的印象管理。
(二)印象管理与自尊
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自尊(self esteem)是影响个体印象管理的重要因素。自尊反映了一个人对自我价值的总体主观情感评价,包含自我的信心(如“我有能力”“我值得”),以及自我的情绪状况(如胜利、绝望、自豪和耻辱)。[13]史密斯(Smith)和麦凯(Mackie)认为“自尊是一种自我感受,是对自我积极或消极的评价”,自尊心强的人更愿意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为自己的信仰和目标挺身而出,愿意与他人接触,愿意承担风险。[14]
施伦克尔(Schlenker)认为受众自尊心高低的差异对印象管理具有预测作用,自尊心强的人,保护自我形象的动机更强烈。齐格勒(Zeigler)和梅尔斯(Myers)研究发现个体在形象塑造的过程中,可能会表现出比实际更强的自尊心,因为受众认为,高度自信的人更有利于获得社会福利。[15]舒茨(Schutz)的研究表明,高自尊者渴望形成令人满意的印象,而低自尊者更关注如何不产生消极的印象。[16]
在现实交往中,自尊与印象管理有一定的相关关系。本研究希望探讨在社交媒体上的人际交往中自尊与印象管理的关系,提出研究假设:
H1a:与低自尊者相比,在社交媒体上高自尊者具有更强的印象动机。
H1b:与低自尊者相比,在社交媒体上高自尊者具有更多的印象建构。
(三)印象管理与自我监控
在印象管理的过程中,有印象管理动机的个体往往基于对环境的评估进行印象建构。可以说,个体有调节行为以适应环境的能力,人们在交往中往往会密切观察他人的反应,对社交情境进行评估,以确保自我表现(印象管理)及时变化以符合他人的期望。斯奈德(Snyder)将这种个体对自我和环境的评估称为“自我监控(Self monitoring)”。[17]在现实人际交往中,高自我监控者具有高度务实性和灵活度,力求适应于各个场合,当进入一个社交场合,高自我监控者往往会辨别周围情况以决定如何表现自己,且呈现出自己的积极形象。[18]而当低自我监控者进入社会环境时,他们会仍然按照自己惯有的态度、信仰和感觉行事,继续自己一贯的形象,而不是努力成为适应环境的人。[19]
斯奈德(Snyder)等人认为高自我监控者:(1)更关注社会情境中他人的行为;(2)更愿意进入能够为行为提供清晰指导的情境中;(3)对具有公共行为性的职业更感兴趣,比如表演;(4)更善于阅读他人的面部表情;(5)比低自我监控者更善于沟通情绪。[20-22]因此,可以说高自我监控者与低自我监控者相比在进行印象管理方面更加有效。博利诺(Bolino)通过实验研究发现,相对于低自我监控者来说,高自我监控者知道并能够更好地进行印象管理。
而关于社交媒体上,是否存在着高自我监控者印象管理更有效的现象?研究者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美国心理学家巴克(Back)招募了236个使用社交网站的美国和德国学生,并对他们进行人格测试,发现在Facebook上高自我监控者更善于利用社交网络上的信息来表现自己外向和友好的性格特点。[23]相比之下,低自我监控者对Facebook上的社交信息并不敏感。[24]但是,荷兰的茱莉亚(Giulia)和埃勒(Elles)在对268名16岁至65岁的荷兰受访者进行调查研究后发现,自我监控对受访者在Facebook上的印象管理没有影响。[25]
社交网络上自我监控对印象管理的作用仍不确定,本研究根据现实交往中自我监控对印象管理的正向作用,提出了以下假设:
H2a:与低自我监控者相比,在社交媒体上高自我监控者具有更强的印象动机。
H2b:与低自我监控者相比,在社交媒体上高自我监控者具有更多的印象建构。
二、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择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利用问卷星以滚雪球的方式进行问卷发放,发放时间为2016年11月30日至2017年3月3日,共发放314份问卷,回收314份,剔除每一题项答案相同,自尊量表中正向计分题项和反向计分题项相矛盾的无效问卷共19份,保留有效问卷295份,问卷有效率为93.9%。
(二)测量方法
问卷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职业、学历,第二部分是自尊测量,第三部分是自我监控测量,第四部分是印象管理测量。
1.自尊量表
本研究采用罗森伯格自尊量表(Rosesberg self-esteem scale,RSES),[26]其中有5个正向计分题项:(1)我感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至少与其他人在同一水平上;(2)我感到我有许多好的品质;(3)我能像大多数人一样把事情做好;(4)我对自己持肯定态度;(5)总的来说,我对自己是满意的。还有5个反向计分的题项:(1)归根结底,我倾向于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2)我感到自己值得自豪的地方不多;(3)我希望我能为自己赢得更多尊重;(4)我确实时常感到毫无用处;(5)我时常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每一题项有四级评分,1表示非常符合,2表示符合,3表示不符合,4表示很不符合。总分范围是10—40分,分值越高,表示自尊心越强。
2.自我监控量表
斯奈德(Snyder)认为高自我监控者具有三个特征:关注行为的适宜性,对情境线索敏感,以情境线索作为行为调节的指南。在此基础上他编制出一份25个题项的自我监控量表(Self-monitoring scale,SMS),1986年斯奈德(Snyder)把25个题项精减成18个项目。[27]采用5点Likert计分,分为“非常不符合、不符合、不确定、符号、非常符合”五级。
本研究采用18个题项的SMS问卷进行公众自我监控的测量。为了检验问卷的适用性,本研究预先抽取120份问卷对量表进行检验与修正。项目分析发现题项“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的人,我常常有不同的行为表现,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和“我并不总是我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人”与整体自我监控问卷无显著相关性(P>0.05),所以将其去掉。同时题项“我会做出一些样子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或让人高兴”“我只能为自己已经相信的观点而辩护”“对于实际上不喜欢的人,我可能装得很友好”的皮尔逊(pearson)相关性指数小于0.3,表明这三个题项区分度不好,不能区分出不同被试者的反应程度,[28]因此将其删除,最终保留13个题项测量个人的自我监控程度。
这13个题项是:(1)我发现我模仿别人的行为很难;(2)在宴会或其他社交聚会中,我并不会按照别人的喜好说话做事;(3)我能够对几乎一无所知的问题作即席讲话;(4)我或许能够成为好演员;(5)在一群人中我很少成为注意的中心;(6)我不是特别善于让别人喜欢我;(7)我不会为了取悦他人而改变观点或行为方式;(8)我曾考虑当一名演员;(9)我从来不擅长玩即兴表演这类游戏活动;(10)我难以改变自己的行为去适合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场合;(11)在晚会上,说笑话讲故事一般都是别人的事;(12)与别人在一起我有点不知所措,不能自然地表现自己;(13)我能够面不改色地说假话(如果目的正当)。
3.印象管理量表
在利里(Leary)和科瓦尔斯基(Kowalski)的印象管理两成分理论之上,康罗伊(Conroy)、莫特尔(Motl)和哈勒(Hall)编制了自我呈现SPEQ量表(the Self-Presentation in Exercise Questionnaire)。本研究结合刘娟娟以及张立敏修订和检验的印象管理量表,[29]对SPEQ量表进行修订,编写出20个测量微信朋友圈中个人印象管理的题项,包括印象动机10个题、印象建构10个题,采用5点Likert计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2代表不同意,3代表不一定,4代表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分值越高,表示公众在微信朋友圈进行印象管理的强度越高。
因为本研究中的印象管理问卷是对SPEQ量表进行修订后建立的,需要检验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对抽选出来的120份问卷先进行“印象管理问卷高低组平均数差异检验”,发现题项“在发动态或者评论前,我会仔细斟酌用词用语是否合适”“我希望通过朋友圈信息能够给好友传达自己好的个人形象”“我希望通过朋友圈状态让大家看到我的优点”在高低组间不存在差异,即在印象管理问卷中没有区分力,所以将其删除。进一步采取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方差最大化旋转,以确保用来进行研究分析的题项信效度最佳,以载荷系数0.4为标准,结果又删除载荷系数低于0.4的4个题项:(1)我会尽量给所有的好友点赞或评论;(2)当好友对我的状态进行评论时我会立即回复;(3)我希望在朋友圈和好友形成更好的互动;(4)考虑到某些状态可能会让部分好友不快,我会进行好友屏蔽。
最后以13个题项来测量印象管理,其中测量印象动机的有7个题项:(1)当某一条状态被大家称赞时,我会积极发类似的状态;(2)我希望通过发布信息能够让大家更清楚地知道我的职业身份;(3)我想要将我的生活经历分享给大家;(4)通过朋友圈可以让大家看到我的能力;(5)我希望通过朋友圈的信息能够让大家认为我是工作/学习认真的人;(6)我希望通过一些朋友圈信息让大家进一步认可和尊重我;(7)我希望通过朋友圈状态能够控制好友对我的印象。测量印象建构的有6个题项:(1)我会有意无意关注并转载各类信息,使自己与时代同步;(2)我会经常发表(转载)一些与工作/学习相关的信息;(3)我尽量在朋友圈发一些好友感兴趣的信息;(4)我会经常发一些自己精神面貌很好的照片;(5)我更乐于在朋友圈发一些关心他人以及关爱大自然的信息;(6)我会根据之前朋友圈信息被点赞和评论情况选择发布的内容。
三、数据分析
(一)样本信息
本次调查男女比例较为平衡,295份问卷中男性占50%,女性占50%;年龄分布上19—26岁比例最大,占84%;以学生居多,占44%,其次是经管型,占16%;在教育程度方面,本科的比例最大,人数为181人,占61%,其次是硕士及以上占29%(见表1)。

表1 微信朋友圈中公众的印象管理调查问卷分布情况(N=295)
(二)信效度检验
自尊量表的信度为0.873,效度KMO值为0.881,自我监控量表信度为0.706,效度KMO值为0.766,说明修订后的自尊量表和自我监控量表信效度均较高,适用于本次研究。
利用克朗巴哈系数检验印象管理量表中的印象动机、印象建构以及整个印象管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结果显示克朗巴哈系数α分别为0.812、0.711、0.868,这说明所编制的印象管理量表信度好(α>0.7),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根据印象管理两成分理论,即“印象管理由印象动机和印象建构组成,人一旦产生印象动机后会进行印象建构”[12],在AMOS 20中对印象动机和印象建构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分析本研究所编制的印象管理量表是否符合印象管理两因子模型,模型如图1(图1中数字对应的是印象管理量表的题项),结果显示如表2。

模型CMINdfCMIN/dfRMSEAGFIAGFINFICFIIFI两因子模型110.826542.0520.0600.9460.9090.9200.9570.957
本特勒(Bentler)(1990)、伯恩(Byrne)等学者认为,CMIN/df<3表明该模型的整体效果良好,或者当RMSEA<0.08,GFI、AGFI、NFI、CFI、IFI的取值大于等于0.9时,模型的拟合程度亦可接受。[30-31]在本研究中,CMIN/df为2.052,RMSEA=0.060,GFI=0.946,AGFI=0.909,NFI=0.920,CFI=0.957,IFI=0.957,表明印象管理的两因子模型拟合很好,同时,结果显示印象动机对印象建构存在直接影响(印象动机→印象建构的直接效应为0.99,相关性P为***,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结果显示,本研究中的印象管理量表满足两成分模型且结构效度较好。
(三)自尊、自我监控与印象管理的关系分析
为了合理考查自尊、自我监控与印象动机、印象建构的相关关系,首先分析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皮尔逊(Pearson)相关系数见表3。
表3显示,印象管理的两个维度即印象动机与印象建构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750,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自尊与印象动机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51,与印象建构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56,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这说明自尊与印象动机、印象建构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自我监控与印象动机、印象建构之间相关不显著。但是自尊与自我监控间的相关系数为0.314,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自尊与自我监控之间有显著相关关系。

表3 自尊、自我监控与印象管理的相关关系表
前面已验证过印象动机和印象建构两成分模型结构效度良好,依据本文的研究假设,自尊、自我监控与印象管理存在相关关系,再结合已检验的自尊、自我监控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在AMOS中建立了“自尊、自我监控与印象管理的关系结构图”(图2),通过结构模型我们能够直接观察到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对模型进行拟合检验,发现模型拟合不是很理想,RMSEA为0.082,大于0.08,所以需要根据修正指数(模型运行后产生)和临界比率。进行模型修正后结果如表4所示,GFI、AGFI、NFI、CFI、IFI的取值均大于0.90(越接近1表示模型拟合越好),说明修正的模型拟合优度较好,RMSEA也达到标准。

表4 印象管理影响因素结构模型分析结果(N=295)
修正后的模型与假设模型(图2)相比,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分析过程中发现,无论是自我监控的测量方程部分还是结构方程部分,系数都是不显著的。所以,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表4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自我监控与印象动机、印象建构没有相关性,二是赫克(Hoek)最新的研究发现在Facebook上,自我监控不影响用户在Facebook上的印象管理。[25]笔者结合微信朋友圈私密化的特性,考虑到微信朋友圈存在自我监控不影响印象管理的可能,所以在模型修正过程中将自我监控剔除,最终模型如图3所示。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自尊对印象管理有影响,从模型系数估计结果来看(表5),由自尊到印象动机直接效应达到显著水平(P为***),直接效应为0.298,而自尊到印象建构P值为0.367,路径系数不显著。这表明,自尊对印象动机有正向预测作用,自尊心越高的受众在微信朋友圈的印象动机越强,自尊对印象建构没有预测作用,假设H1a成立,H1b不成立(见表5)。
通过结构模型的分析过程发现,在微信朋友圈中,用户的自我监控与其在微信朋友圈的印象管理行为无关,假设H2a、H2b被拒绝。

表5 印象管理影响因素结构模型系数估计结果
四、讨 论
本文探究了个人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其自尊、自我监控等与印象动机、印象建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自我监控与受众在微信朋友圈中的印象动机和印象建构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个人的自尊与社交媒体上的印象动机相关,但与印象建构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之一是自尊对印象管理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结构方程模型中得到了证明,自尊心高者具有更强的印象动机,因为自尊心强表示个体对自我的尊重与重视,自尊心越强的人越希望通过自我呈现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尊重和认可,满足对自我的认可。[32]自尊心的高低却不能直接预测受众在微信朋友圈进行印象建构的强弱,因为印象建构是需要付诸行动的,比如在朋友圈发内容时的遣词造句等,有较高的自尊心并不一定意味着有较高的行动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自尊对印象建构完全没有影响,因为印象建构是基于一定印象动机而采取的个人形象维护措施,在社交媒体上高自尊者具有更强的印象动机,更强的印象动机会激发个体进行更强的印象建构,可以说自尊对印象建构有间接影响。[12]
对于“自我监控与印象动机、印象建构的关系”,其研究结果并没有证实研究假设,相关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结果都否认了自我监控对受众微信朋友圈中的印象管理有正向预测作用。这一研究结果侧面表明,社交媒体上个人形象的印象管理与现实交往中个人形象的印象管理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因为过去的研究显示,在现实交往情境中,高自我监控者对社交情境更敏感,更善于表现自我,有较强的印象动机和印象建构。然而,在社交媒体上,高自我监控者与低自我监控者的印象管理并不存在着显著差别,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自我监控能力的高低是与一定的场景相联系的,自我监控能力高者可以依据场景而调整自己的行为,社交媒体中的人际交往所处的场景有别于现实社交中的场景。在现实社交中,有具体的现实场景(如“晚会”“面对不喜欢的人”“与别人在一起”等),交往时有面对面的互动,高自我监控者可以根据周围环境、他人的面部神态以及肢体语言动作等感知到自我表现是否合理,进而会即时作出言语和神态的调整以迎合他人,这有助于高自我监控者进行更有效的印象管理;但社交媒体中的场景信息比较简单,甚至是单一的,在微信朋友圈中公众无法估计环境,不能根据他人的言行举止进行自我表现,仅依靠自我感知来发布信息,即高自我监控者所获得的场景信息与低自我监控者所获得的场景信息基本相同,这促使其在印象管理方面的差异性并不显著。
其二,社交媒体具有的私密性、可控性使得高自我监控者与低自我监控者的印象管理并不存在差别。微信朋友圈是一个私密化的个人空间,同时还有各种隐私设置,如分组、屏蔽等,这样的设置,使得朋友圈成为一个被用户掌控的空间,或者说,公众通过各种设置而感觉自己是可以控制信息的传播途径和范围的。有了这样的感知,无论是对于现实中的高自我监控者还是低自我监控者,都会随心所欲地在社交媒体上进行表达。
自我监控与印象管理并不存在显著相关,这一研究发现具有一定的现实启发:其一,基于社交媒体的特性,公众在社交媒体上的表达会更为丰富;其二,公众在社交媒体上表达时,较少依据社交场景而进行适宜的话语调整,引人不快的、冒犯他人的、中伤他人的内容会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从而造成社交媒体上人际关系的尴尬或紧张;其三,在社交媒体使用中,高自我监控者有转向低自我监控者的风险。在社交媒体环境中,即使言语行为不当也不会受到责难,在此认识的影响下,可能会出现不顾及对方感受和个人形象而为所欲为的言语失控现象,高自我监控者有转向低自我监控者的可能。[33]
最后,本研究存在一定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主要是测量自尊、自我监控是否影响印象管理,没有考虑其他变量对印象管理的影响;其次,本研究仅依靠问卷和数据进行分析,缺乏更为深入的探讨。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量化、质化相结合等方法,详细了解用户在社交媒体中的自我监控认知和印象管理策略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