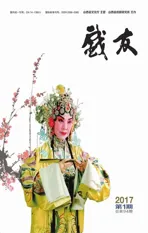正身守诚裴氏家风一脉传 声动梁尘一出好戏龙城绽
——观大型新编蒲剧历史剧《晋国公裴度》
2019-04-26朱天艺秦伟强
朱天艺 秦伟强
“春夏荣兹,我不竞于芳时,秋冬凄冽,我不改其素节。”声声如洪钟,句句似圭臬,这是一代名相的内心独白,也是六朝老臣的人格坚守。善美家风,宰相气度,由肖桂叶导演、白惠林与谢永峰编剧、张志勇作曲配器、闻喜县蒲剧团创作的大型新编蒲剧历史剧《晋国公裴度》近日于太原展演。在寒风阵阵的冬日,一出好戏如春风雨露般浸润心田、意蕴绵长。
晋国公裴度,一生经历六朝,五度拜相,一身正气、言以率幼,是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垂范者,他是闻喜历史文化名人,也是山西历史文化名人。在山西的历史上有狄仁杰、于成龙、傅山、裴度等,他们胸中有日月乾坤,心里存家国黎民,正是这样一个个灿若星辰的名字,深深印刻在山西文化的根脉上。山西不仅有大院文化、清官文化,还有家风文化,这是山西人的骄傲,这部剧是山西文化自信的又一力作。
一剪寒梅开,总有暗香来。一部好剧的诞生,离不开创排人员的坚守。演出当日,大幕拉开、鼓弦声起,我和爱人既紧张又兴奋,我们太知道这部剧创作的种种不易,看到现场座无虚席、听到观众叫好频频,再看到眼中有泪水、脸上有荣光的二位编剧老师,我们二人也如释重负、感慨万千。尤其对剧本的创作深表钦佩。编剧白惠林校长和谢永峰老师从初期买书籍、查史料,到实地采风、开研讨会,各个环节都是紧锣密鼓、精琢细磨。仅剧本打磨就将近一年时间,数易其稿。其间对人物关系梳理、剧情起承转合、角色的拿捏、行当戏份的关照、言语与身份的匹配、舞台调度与审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取舍与成全、文字与演出的契合度,都是反复斟酌。烛灯烁烁,是多少夜的坚守;掌声阵阵,是多少辛劳的回馈。剧本结构合理、选材巧妙、故事集中、枝节较少,是剧评界公认的评价,尤其对剧中文辞赞赏有加,用词厚重老练,玉粒珠玑、文采朗朗、韵对精妙、流畅雅致,读来满口生香。唯有时间见真知,韬光养晦方可一鸣惊人。最令我们感动的还有这部戏的导演肖桂叶老师,75岁高龄,谦逊随和,做事认真,亲赴闻喜,长期驻扎,从秋阳到冬日,导戏排戏,加班到凌晨,不喊累叫苦,雷厉风行又严谨持重的作风,对我们后辈是莫大的鞭策和鼓舞。人好,戏才好,德为先,艺才成,或许这就是这个团队乃至戏剧人踏实奋进的“艺路匠心”。
托声于言,树德载新。此剧的亮点在于主题的把握。有了好家风,才有好家教。注重家风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家风清则社风清,家风浊则社风浊。“推诚为应物之先,强学为立身之根,节俭为持家之基,清廉为做官之本”,正如裴度所说“让我裴氏家族,成了名扬天下的望族,凭的就是四个字——诚、学、俭、廉”。“裴氏家族”之所以声名显赫、历久不衰,除了特定的历史因素外,主要是和裴家严格的祖训家规有关。正值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面对快速发展的社会,人们的价值观更应向先贤看齐,以史为鉴,方知兴替。更应把这些宝贵的精神食粮,植根于心田。这部剧的推出,对弘扬裴氏文化、传承优良家风,对官员清正廉明、不徇私舞弊,不任人唯亲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笔者深感这是一出好戏,就谈谈观看这部戏之后的一些感受。
一、主题立意深远,选材巧妙。本剧以唐中期长庆元年科考案为背景,以科考成绩作废与否为主线,以裴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主动辞掉皇帝恩赐给儿子裴 的状元为切入点,以裴氏一族几千年不衰的祖训家规兜底,秉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家事影射国事,首次从家风家教角度,艺术化呈现一代名相可贵的人性闪光点,歌颂了其良好的家风家教。故事完整,台词厚重,节奏合理,从科举来入手,并没有铺开讲述裴度的一生,那样跨度太长,事绪繁杂,显然不易在两个小时的演剧时间里完全包含、面面俱到,而是把裴度的一生巧妙地在唱词里体现出来,以小见大、干净集中。这个戏是可以用裴度人生中一个片段来反映他的人格魅力、家承学源的。因此《晋国公裴度》的题目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设置的,大气准确且利于宣传,一叫就响,要是改成《裴度教子》,就略显单薄了。
其实,对于历史剧的创作有很多的局限,也有很多的可能,甚至可以更灵活些。史料是为艺术创作服务的,过于拘泥于历史真实,就不能叫“戏”了,俗话说“无巧不成书”,这个“巧”字正能体现作者构思巧妙之处。艺术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能动反映,是真与幻的统一,是生活的真实性与审美的真实感之统一。
二、人物饱满丰腴,形象生动可感。剧中行当较为齐全(文武老生、青衣、小生、小旦、须生、老生、二花脸、三花脸、花脸、娃娃生),戏份编排合理,不是裴度一人绝对主唱,裴夫人、裴 、书生赵群、皇帝都有大段精彩的唱词,能做到兼顾主次,形成“众星捧月”之势,除裴度的主角光环外,其他角色并没有黯然失色,也熠熠生辉,可圈可点,使人感觉这个县级剧团整体实力不容小觑。
剧中对几个人物印象深刻,一是裴度,是整部剧的绝对主角,演员功力深厚,力道拿捏准确,情绪调动积极,将一个有高度、有思想、有真情的名相演得较为到位。剧中的裴相目光如炬、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爱有怜,并没有把一个宰相级的人物塑造成“高大全”的形象,演成了“表彰会”,没有人情,不讲亲情,这也是剧本的可贵之处。剧中的裴度,宰相之尊,位高权重,科考成绩废与不废的两种声音,左右夹击,一面是科考律规、一面是亲生儿子,一面是官宦要臣、一面是寒门学子,他也有顾虑,也有选择,提起儿子也尽显心疼,面对儿子对他的质问,也有反思,打儿后又有自责,这样的人物形象就是真实可感的。他是人臣,就应身先士卒坚守清明;他是家父,也当教子明规德位相配。裴度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形象,而是一个懂情理,会自责的父亲,有人情,有温情,这样人物就立体丰满立得住了。再有就是一个小细节值得体味,裴度第二场戏的服装设计也是一个巧妙的亮点,左袖是文官的宽袍水袖,右袖是武将短打武生的袖口,这样就在服装上体现出裴相文武兼备,设计巧妙,非同一般。
二是张武、李文,虽为配角,但人物形象很突出、充满戏剧效果。二人是反面贪官又显得很可爱,二花脸三花脸的设置,使角色性格鲜明,再加上闻喜方言,嬉笑怒骂、诙谐狡猾,是添彩的一笔。
总体看来,这部剧没有绝对的反面人物,剧情也不是在斗争中剑拔弩张的冲突、难分高下的激辩、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展开,而是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从正面入手,激浊扬清,这样就避免了一些不必要场面的赘述。
三是老者的加入,如智者高人,点睛之笔,让人眼前一亮,出场三次,寥寥数言,道尽天机,犹如《红楼梦》中唱《好了歌》的跛足道人。可能,这一老者形象是另一个裴度,是裴度内心潜台词的外化,使得裴度人物更加完整,整部剧颇有深度。

三、导演、音乐、舞美尽显美学内蕴。清初黄周星说:“论曲之妙无他,不过三字尽之,曰‘能感人’而已。感人者,喜则欲歌、欲舞,悲则欲泣、欲诉,怒则欲杀、欲割;生趣勃勃,生气凛凛之谓也。”所说的就是在戏曲欣赏中,观众成为剧中的“这一个”,在戏曲舞台上,通过想像、移情和共鸣,把自己幻化成其中的角色。跟着剧情舞之蹈之,悲之泣之,或喜或悲、或愤或怒,在人们的主观世界里创造出一种意象化的艺术形态,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的再创作。肖导手法娴熟,群众场面、人物调度干净流畅,舞台节奏处理得当,确实是回归了戏曲对传统戏的把握。整部剧能够抓住观众的心,观剧过程中,很少有人走动,精彩处观众拍照、录音、鼓掌、叫好,可见导演深谙观众心理学。
音乐很有蒲剧特色,蒲剧唱腔高亢激昂,朴实奔放,长于表现慷慨激情、悲壮凄楚的英雄史剧,又善于刻画抒情剧的人物性格和情绪,这是蒲剧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基础。整部剧音乐与人物形象性格匹配度很高,主题音乐贯穿始终,既有大唐盛世、宰相气度的恢弘壮美,又有书生意气的慷慨激昂。演员驾驭唱词能力强,尤其是快节奏、在唱词排比与对偶对仗绵密、音乐的驱动下,唱起来连贯性很强,一气呵成。还有镲的运用恰到好处,像调节剂,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再有就是作为县级剧团,驱车六小时,带来乐队现场伴奏,难能可贵。
整部剧在艺术风格上回归戏曲本体,在出情、出戏的细节中浓墨重彩地刻画人物,音乐唱腔设计很有剧种本体特色,舞美设计大气恢弘,尤其是第四场,展现大唐盛世气象,突出舞台呈现的写意性和空灵感,给观众以美的享受,让人眼前一亮。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这部剧可以说编、导、音、舞、美、演浑然一体,是较为完整的一部戏。一出戏的推出和成功绝对不是某一方努力的结果,“一棵菜”“全盘棋”,百川汇海,才能蔚为壮观。只有各司其职,才能真正体现戏曲的本体,才能真实展现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晋国公裴度》堪称“起手在巅峰”,而怎样从“高原”到“高峰”,还得进一步的打磨,当然还有上升空间。譬如,“小莲”的设置,是否能更加突出,或是删减一部分;最后一场戏稍显仓促;舞美方面是否能再增加一些闻喜元素,能否地域性特点再强一些,长安和闻喜区分明显一下等等。此剧演出仅三场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已经很惊艳了,期待再接再厉,更完美的呈现。
肩扛重任不借史官之笔,百姓心中自有春秋大义。历史是一面镜子,是关照当下最好的教科书,艺术应当担起哺育思想的责任。裴度作为山西文化符号和文化代表,非常有必要挖掘他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晋国公裴度》从审美情感、自然情感、道德情感上都是值得称赞的好剧。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希望剧团能再精心打磨,把此剧做为保留剧目、乃至经典剧目、参赛剧目、展演剧目,让更多的人知道裴度,了解闻喜,了解山西文化根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