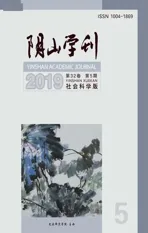中华本《廿二史札记校证》蒙古译语点校失误指正 *
2019-03-03胡云晖
胡 云 晖
(包头市政府办公室,内蒙古 包头 014060)
《廿二史札记》系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著读史笔记,其书采用以史证史方法,整体考察历代正史,尤其通过考异、辨误、纠谬等形式,进行周密辨析和订正,考据精详,资料宏富,与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并称清代三大史学名著。
《廿二史札记》共三十六卷,附补遗一卷。自行世之后,颇为治史者所重视,历代翻刻印行者甚夥,近代以来,更多有点校本出版。在补遗中,著者依据乾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将其中改译的辽金元人名、官名、地名,按照“旧名在前,今名在后”的方式,逐一录出,以利于读史者检阅。
笔者旧日尝翻阅诸书,发现其补遗部分之涉及蒙古译语者,多有刻印或点校错误,至今未见纠正,因此,深感有指出和考证之必要。今主要以中华书局出版、王树民先生所著《廿二史札记校证》为对象,仅就所知,拈出数则,予以考证,以求有所裨益于古籍整理。
“孛端叉儿,今改勃端察不”[1]858。
孛端叉儿,据史书记载,是蒙古孛儿只斤氏的始祖,成吉思汗的十世祖。〔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 “太祖本纪”:“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讳铁木真,姓奇渥温氏,蒙古部人。太祖其十世祖孛端叉儿,母曰阿兰果火,嫁脱奔咩哩犍,生二子,长曰博寒葛答黑,次曰博合睹撒里直。既而夫亡,阿兰寡居,夜寝帐中,梦白光自天窗中入,化为金色神人,来趋卧榻。阿兰惊觉,遂有娠,产一子,即孛端叉儿也。”[2]1
或译为勃端察儿。柯劭忞《新元史》卷一“序纪”:“有豁里秃马敦部长豁里剌儿台蔑儿干率所部至不儿罕山,都蛙锁豁儿见其女美,为弟朵奔蔑儿干娶之。是为阿兰豁阿哈屯,生二子,曰不古讷台,曰别勒古讷台。朵奔蔑儿干卒,阿兰豁阿嫠居有孕……既而,生三子,长曰不忽合塔吉,次曰不合秃撒勒只,次曰勃端察儿蒙合黑。”[5]
也译作孛端察儿。《元朝秘史》卷一:“朵奔篾儿干死了的后头,他的妻阿阑豁阿又生了三个孩儿:一个名不忽合塔吉,一个名不合秃撒勒只,一个名孛端察儿。”[6]10
上述勃端察尔、勃端察儿、孛端察儿等,均与孛端叉儿音同,并是一人,用字不同而已。而勃端察不,明显是勃端察尔之讹,因字形相近而致误。《廿二史札记校证》失校。
更有甚者,竟将孛端叉儿误为孛端义儿。如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黄寿成校点《廿二史剳记》卷二十九“元史”:“今案《金史·世纪》叙先世事至盈一卷,而《元史》叙孛端义儿以下十世不过千余字,可见国史院已无可征。”[7]校点本出现这样低级的错误,实在令人遗憾。
至于孛端叉儿之义,《钦定满洲源流考》卷十八“附金史国语解考”曰:“勃端察尔,胚胎之名。按蒙古语称始祖为勃端察尔,此云胚胎之名,义未当。第以汉语称鼻祖例之,意尚可通。《尔雅》亦以胎字祖字,皆训为始也。”[8]其是否为蒙古语胚胎之义,尚需存疑,聊备一说而已。
“跌甲温盘陀山,今改特里衮布达拉山”[1]859。
跌甲温盘陀山,当是跌里温盘陀山之讹,亦写作特哩衮布达拉。如《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九十:“按《元史》云:伊苏克依攻塔塔尔部,获其部长特穆津,还次特哩衮布达拉山而生子,因即以命名……特哩衮布达拉,旧作跌里温盘陀,今改,后仿此。”[3]12可证跌甲温盘陀山是因字形相近而误刻,《廿二史札记校证》失校。
跌里温盘陀山之名,在古籍中屡见。如〔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五“蒙古侵金”:“铁木真之先,有曰孛端叉儿,母曰阿兰果火,生二子而寡居。夜寝,屡有光明照其腹,又生三子,孛端叉儿其季也。其后子孙蕃衍,各自为部,居于乌桓之北,与畏罗、乃蛮、九姓回鹘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贡于辽、金,而总隶于鞑靼。至也速该,并吞诸部,势愈盛大。攻塔塔尔部,获其部长铁木真。还,次于跌里温盘陀山而生子,因以‘铁木真’名之。”[9]943
又作迭里温孛勒答黑山。如《元朝秘史》卷一:“与塔塔儿厮杀时,也速该把阿秃儿将他帖木真兀格、豁里不花等掳来。那时也速该把阿秃儿的妻诃额仑正怀孕,于斡难河边迭里温孛勒答黑山下,生了太祖。太祖生时,右手握着髀石般一块血,生了。因掳将帖木真兀格来时生,故就名帖木真。”[6]26
以上所述,均为同一事实,跌里温与迭里温音同,孛勒答黑与盘陀音近,则跌里温盘陀与迭里温孛勒答黑显然是一词异译,译音用字不同而已。
关于跌里温盘陀之义,〔清〕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一曰:“蒙兀谓源头曰迭里温,孤山曰孛勒荅黑,如云斡难河源头之孤山。”[10]但《华夷译语·身体门》曰:“脾,迭里温。”[11]〔明〕郭造卿《卢龙塞略》卷十九译部上卷“身体门”亦曰:“脾曰迭里温。”[12]则谓迭里温之义为脾,二说未知孰是。〔清〕李文田《元朝秘史注》则曰:“盘陀,译言山也。”[6]26与屠寄所谓孤山释义相近,但均未给出例证,不敢遽信。
而《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改跌里温盘陀为特哩衮布达拉,特哩衮是蒙古语为首之谓,布达拉是梵语,即汉语通常所谓普陀,合而言之,义即为首的普陀山。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也没有给出任何依据进行说明,而且将蒙古语和梵语混搭,不符合当时命名习惯,难以使人信服。
“宽佃,地名,今改库勒腾。木思海,亦地名,今改济苏哈雅”[1]860。
上述文字,可以说完全错误,不仅肢解和胡乱组合蒙古译语,而且擅改地名,同时也有刻写校对错误。
如前所述,《廿二史札记》中关于蒙古译语的改译,是照录自《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查《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九十二,有相关记载,其中有庞杂的夹注,亦照录如下:“蒙古击奇卜察克(西域国,《方舆纪要》:国在葱岭极西,旧作钦察,今改)诸部,破之(考《元史·苏布特传》太祖癸未苏布特请讨奇卜察克,许之,遂收其境。而《太祖本纪》不载其事。又《太宗本纪》,九年丁酉,莽赉扣征奇卜察克部,破之,擒其酋巴齐玛克。而《宪宗本纪》书其事而不详年月。盖奇卜察克在西域最远,叛服不常,太祖收其境,太宗复加征讨。《续纲目》于嘉定十八年书苏布特灭奇卜察克,于是年复书蒙古击奇卜察克。前既书灭,此复书击,体例未协。今节采《元史》纪传,并辑于此。按巴齐玛克,旧作八赤蛮,今改)。初蒙古太祖时,苏布特击奇卜察克(《续纲目》:奇卜察克去中国三万余里,夏夜极短,日暂没辄出,土产良马,富者以万计。所载与《唐书·郭喇洼传》略同,但郭喇洼地在翰海北,与日出处相近,故昼长夜短。此奇卜察克在葱岭极西,地当近日入处,昼夜何得与日出处相同?其言恐未足据,今不取),由库勒腾(旧作宽定,《续纲目》作宽田)济苏哈雅(旧作吉思海,今并改)至太和岭,凿石开道,与其酋伊勒吉(旧作玉里吉,今改)等遇,纵兵奋击,众溃悉降,遂收其境,与奈曼诸部千户通立一军。及蒙古主即位,既灭金,命诸王巴图(旧作拔都,今改)、莽赉扣等分讨西域诸部。至是莽赉扣击奇卜察克,至济苏哈雅。其酋巴齐玛克逃匿海岛,会大风刮海水,其浅可涉。遂进,屠其众,生擒巴齐玛克。”[3]38
其中蒙古译名,迥异于历代史书,但知其所记述者,是指速不台(即所谓苏布特)、蒙哥(即所谓莽赉扣)讨伐钦察(即所谓奇卜察克,亦译作钦叉)之事。关于这一史事,史书有明确记载。如《元史》卷一百二十一列传第八“速不台”:“癸未,速不台上奏,请讨钦察。许之。遂引兵绕宽定吉思海,展转至太和岭,凿石开道,出其不意。”[2]2976又《元史》卷六十三“地理志六·西北地附录”:“太宗甲午年,命诸王拔都征西域钦叉、阿速、斡罗思等国。岁乙未,亦命宪宗往焉。岁丁酉,师至宽田吉思海傍,钦叉酋长八赤蛮逃避海岛中,适值大风,吹海水去而干,生禽八赤蛮。”[2]1570
从上述记载可知,所谓宽定吉思海和宽田吉思海,是同一地名的不同译音。根据“师至宽田吉思海傍,钦叉酋长八赤蛮逃避海岛中,适值大风,吹海水去而干”等语,明白可知宽定吉思海或宽田吉思海,是一个很大的海(或湖泊),中间还有一个海岛,钦叉酋长八赤蛮逃避其中,因为大风将海水吹浅,蒙古军涉水攻入,八赤蛮才被生擒。很显然,宽定吉思海或宽田吉思海,是名叫“宽定吉思”或“宽田吉思”的海,海是个汉语词。将宽田吉思海分割成宽田和吉思海两部分,而且还为其译音为库勒腾和济苏哈雅,明显是错误可笑的。赵翼一代考据大家,原文照录,究竟是个人失察,还是装糊涂为君者讳,就不得而知了。
这一错误,在其后编纂《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时得到了纠正,并且给出了“宽田吉思”地名的蒙古语解释。《钦定元史语解》卷五:“衮腾吉斯,衮,深也;腾吉斯,湖也。卷五十作宽田吉思,海名。”[4]317明确指出宽田吉思是海名。宽田吉思或宽定吉思,与衮腾吉斯音近义同,只译音用字不同。
王树民先生在《廿二史札记校证·补遗校证》中说:“宽佃,地名,今改库勒腾。木思海,亦地名,今改济苏哈雅。按:此二条应为‘宽田吉思海’,即今里海。一名误分为二,又误‘吉’为‘木’,二本皆误。”[1]871所校甚是,但未指出该地名的蒙古语意义。
“唆大脱,今改苏固图”[1]860。
唆大脱改为苏固图,译音有明显差距。
查《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九十三,其原文(为便于叙述,删除其部分夹注)曰:“呼必赉以乌特哩哈达总诸军事,分三道以进。自临洮经行山谷二千余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栰以济,摩莎蛮主迎降。进薄大理城,大破其兵,虏其王段智兴。分兵取附都鄯善、乌爨等部。进入吐蕃,其酋苏固图(旧作唆火脱今改)惧,出降。”[3]8则唆大脱,当是唆火脱之讹。唆火脱为吐蕃酋长,又译为苏固图,其词恐是藏语,《廿二史札记》阑入蒙古语部分。《廿二史札记校证》失校。
“苦彻拔都儿,今改哲辰巴图噜”[1]860。
苦彻拔都儿改译为哲辰巴图噜,首字译音明显不符。
今查《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其卷九十三曰:“时蒙古围鄂州,都统张胜权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谕之曰:城已为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将台,可从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将退。会高达等引兵至,贾似道亦驻汉阳为援。蒙古乃复进攻,遣哲辰巴图噜(奇卜察克人,旧作苦彻拔都儿,今改)领兵同降人谕鄂州使降。抵城下,胜杀使者,出军袭哲辰巴图噜。”[3]30知所述事为忽必烈伐宋围鄂州事。
复查《元史》卷一百二十三列传第十一“苫彻拔都儿”:“苫彻拔都儿,钦察人。初事太宗,掌牧马……岁己未,世祖伐宋,募能先绝江者,苫彻拔都儿首应命,率众逼南岸。诏苫彻拔都儿与脱欢领兵百人。同宋使谕鄂州使降。抵城下,鄂守将杀使者以军来袭,苫彻拔都儿与之遇,奋击大破之。”[2]3031
又《宋史纪事本末》卷一百〇二“蒙古南侵”:“十一月,蒙古围鄂州,都统张胜权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谕之曰:‘城已为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将台,可从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将退。会高达等引兵至,贾似道亦驻汉阳为援,蒙古乃复进攻。遣苫彻拔都儿领兵同降人谕鄂州使降,抵城下,胜杀使者,以军出袭苫彻拔都儿,战败死。”[9]1112
则《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及《廿二史札记》之苦彻拔都儿,是苫彻拔都儿之讹,因字形相近而误,《廿二史札记校证》失校。
关于苫彻拔都儿之义,《钦定元史语解》卷二十曰:“彻辰巴图尔,彻辰,聪明也;巴图尔,勇也。卷一百二十三作苫彻拔都儿。”[4]506彻辰巴图尔与苫彻拔都儿音近义同,《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及《廿二史札记》改译为哲辰巴图噜,是译音用字不同。
“瓮古剌带,今改昂吉尔岱”[1]861。
瓮古剌带改为昂吉尔岱,译音明显不符,古当是吉字之误刻。
查《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九十五曰:“夏四月,以和尔果思为右丞相。初,昂吉尔岱(旧作瓮吉剌带,今改)为右丞相,至是降留守,以和尔果斯代之。”[3]45明白可证。
又《元史》卷十一“世祖本纪”:“十二月甲午,以瓮吉剌带为中书右丞相。”[2]236亦可证。
《钦定元史语解》卷九有关于瓮吉剌带的蒙古语释义:“昂吉尔岱,昂吉尔,黄野鸭也;岱,有也。卷一百七作瓮吉剌歹,系宗室诸王,卷九作瓮吉剌带。卷二十六作雍吉剌带,非一人,并改。”[4]359人名而叫作“有黄野鸭”,其释义令人生疑。
而《廿二史札记校证·补遗校证》曰:“瓮古剌带,今改昂吉尔岱。按:‘吉’字似为‘古’字之误。”[1]872观点既在疑似之间,又疏于考证,将古字视为正字,说明王树民先生并未熟读《元史》诸书。
“索罗,今改博罗”[1]861。
索罗而译改为博罗,首字译音明显不符,索罗当是孛罗之误刻。
查《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九十五曰:“阿哈玛特死,帝犹不深知其奸,及询枢密副使博啰(旧作孛罗,今改)乃尽得其罪状,始大怒曰:‘王著杀之诚是也。’命发冢剖其棺,戮尸于通元门外,纵犬食之,四民聚观称快。”[3]45知所述为元世祖时益都千户王著锤杀权臣阿合马(清译为阿哈玛特)事。《元史》卷二百〇五奸臣列传记其事曰:“阿合马死,世祖犹不深知其奸,令中书毋问其妻子。及询孛罗,乃尽得其罪恶,始大怒曰:‘王著杀之,诚是也。’乃命发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门外,纵犬啖其肉。百官士庶,聚观称快。”[2]4564可证参与其事者为孛罗, 《廿二史札记》误作索罗,《廿二史札记校证》失校。
“博达,今改拨绰”[1]862。
博达而译改为拨绰,尾字译音明显不符。
查《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九十六曰:“伊克图(睿宗世子博绰之孙。按伊克图,旧作牙忽都;博绰,旧作拨绰,今并改,后仿此。)”[3]69《元史》卷一百一十七列传第四“牙忽都”亦曰:“牙忽都,祖父拨绰,睿宗庶子也。拨绰之母曰马一实,乃马真氏。拨绰骁勇善骑射,宪宗命将大军,北征钦察有功,赐号拔都。”[2]2907均指拨绰为元睿宗拖雷之子,清代改译为博绰。而《廿二史札记》作“博达,今改为拨绰”,字既误植,又将新旧译名颠倒,《廿二史札记校证》失察未校,遂使错误一仍其旧。
“也先土于,蒙古人,今改额森托于”[1]867。
也先土于、额森托于,当是也先土干、额森托干之讹。
查《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一百〇二曰:“冬十月,帝至上庄堡(在宣化府万全县北)蒙古额森托干(旧作也先土干,今改,后仿此)来降,诏班师。大军至西阳河(即西洋河,在西安府淮安县西北,自西天镇县流入,经西阳河堡下流,与东洋河合,入桑干河),闻阿噜台为卫拉特所败,部落溃散,遂驻师,命陈懋为前锋,至宿嵬山(《方舆纪要》:在兴和北,亦曰宿嵬口,度漠处也),遇王子额森托干率所部来降,帝大喜,封为忠勇王,赐姓名金忠,赏赉甚厚,遂班师。”[3]48知所述为成祖亲征漠北时蒙古王子归降事。
其事凡叙明代史者屡有言及。如〔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百五十六列传第四十四:“金忠者,蒙古王子也先土干也。素桀黠,为阿鲁台所忌。永乐二十一年,成祖亲征漠北,至上庄堡,率妻子部属来降。时六师深入,寇已远遁。帝方耻无功,见其来归,大喜。赐姓名,封忠勇王,赐冠带织金袭衣,命坐列侯下,辍御前珍馐赐之,复赐金银宝器。”[13]4274
又〔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亲征漠北”:“冬十月,师次上庄堡,先锋陈懋知寇在饮马河北,为瓦刺所败,追至宿嵬山口,遇鞑靼王子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属来归。懋引入见,上喜,谓群臣曰:‘远人来归,宜有以旌异之。’乃封为忠勇王,赐姓名金忠,以其甥把罕台为都督,其部属察卜等七人皆为都指挥,赐冠带织金袭衣。”[14]
以上诸书俱言蒙古王子名也先土干,至清代译其名为额森托干。《廿二史札记》作也先土于、额森托于,明显失误。而《廿二史札记校证·补遗校证》于此条曰“原刻本‘托于’误作‘托子’。”[1]875既默认其失误,又疏于考证。
“辛爱,谙达子,今改锡林阿。桃松泰,鞑女,锡林阿之妾,今改托斯齐”[1]868。
桃松泰而译为托斯齐,尾字译音明显不符。
查《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一百〇九曰:“冬十一月,谙达子锡林阿(旧作辛爱,今改,后仿此)围大同、右卫。锡林阿有妾曰托斯齐(旧作桃松寨,今改正曰托斯齐也),私部目,惧罪来降,杨顺诩为奇功,致之京师。锡林阿来索不得,寇应朔二州,毁七十余堡,纵掠大同,围右卫数匝。”[3]56
则所述为谙达(即顺义王俺答)子辛爱黄台吉(清译为锡林阿)之妾桃松寨投降明军,黄台吉纵兵掳掠报复事。关于桃松寨投明事件,史书多有记载。如〔明〕王士性《广志绎》卷三:“又丁巳虏有逃妇桃松寨来归,总督杨顺纳之,上其状以为功,后俺答索之急,顺惧,上言虏情叵测,欲胁朝廷归之。未及决,俺答子黄台吉诈言以我叛人邱富易桃松寨,顺信之,予以松寨,而邱富竟不得。”[15]亦简称为松寨。
又《明史》卷三百二十七列传第二百一十五“鞑靼”:“冬,俺答子辛爱有妾曰桃松寨,私部目收令哥,惧诛来降。总督杨顺自诩为奇功,致之阙下。辛爱来索不得,乃纵掠大同诸墩堡,围右卫数匝。顺惧,乃诡言敌愿易我以赵全、丘富。本兵许论以为便,乃遣桃松寨夜逸出塞,绐之西走,阴告辛爱,辛爱执而戮之。”[13]8483
因此,辛爱黄台吉逃妾名为桃松寨是非常明确的,《廿二史札记》将桃松寨误作桃松泰,是刻写错误,而《廿二史札记校证》失校。
由于对蒙古人名字的不熟悉,还有更荒谬者。如〔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七“款议有所本”:“若嘉靖末,宣大总督杨顺之,纳淫妇桃松于寨,致虏大入。”[16]竟认桃松为人名,纳桃松寨,是纳桃松于寨,十分荒唐。点校者更将“宣大总督杨顺之纳淫妇桃松于寨”,断句为“宣大总督杨顺之,纳淫妇桃松于寨”,更复错误可笑。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廿二史札记》中蒙古译语方面的错误是比较多的,许多错讹,《廿二史札记校证》(包括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黄寿成校点之《廿二史剳记》)均未能予以纠正。究其原因,主要是著者欠缺蒙古语知识,面对明显失误时不能判别。另外,清代有肆意妄改蒙古译语的不良倾向,译名层见叠出,使人眼花缭乱,刻写和校对时往往容易造成失误。唯其如此,在点校整理类似古籍时,必须要谨小慎微,认真对待,才能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