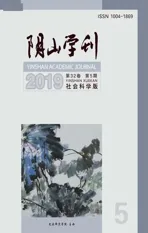《黄金时代》中的“成人仪式”原型分析 *
2019-03-03赵志强
赵 志 强
(内蒙古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王小波敏锐地察觉着生活的荒诞与人的异化,人的尊严、精神自由和主体性完整对他而言是人生及写作中最根本的问题,因此人与异化的对抗是他小说中一以贯之的主题。戴锦华在她的文章《智者戏谑——阅读王小波》中这样描述王小波小说的主题,“他所书写与戏仿的并非一段特定的历史;他所拒绝或颠覆的并非某种具体的权力、意识形态或话语系统,而是权力机器与‘历史’自身。”[1]27顺着这样的精神线索,可以看到《黄金时代》这部中篇小说集有着清晰的精神脉络,按照《革命时期的爱情》《黄金时代》《我的阴阳两界》和《三十而立》的顺序,小说描述了主人公王二从“大跃进运动”开始到80年代商业浪潮兴起的成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主人公年龄的增长,融入社会的程度加深,他所面对的异化力量也不断增强,每一篇小说就是对一种异化的抗争与克服。其中有着“主体性——异化——主体性——异化——”这样螺旋上升的结构。而这种抗争与克服的过程,可以看作是一次次的“成人仪式”。
“成人仪式”是人类学中的一个概念,描述了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一种仪式,一般包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成长到一定年纪的孩子要脱离自己所生活的环境,进入丛林或荒野准备接受考验;第二个阶段,孩子要在种种考验中挖掘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难;第三个阶段,具有了全新力量的孩子重新回到自己生活的社会。概括地说就是一个“死而复生”的过程。这种仪式不仅存在于大多数人类社会中,还普遍存在于人类的英雄故事里。美国学者约瑟夫·坎贝尔在研究了世界各地的神话和英雄故事后写了《千面英雄》,书中认为人类的英雄历险故事都有相同的核心,主要包括这样几个阶段:启程——放弃当前的处境,进入历险的领域;启蒙——获得某种以象征性方式表达出来的领悟;考验——陷入险境,与命运搏斗;归来——最后再度回到正常生活的场域。[2]52坎贝尔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这种现象,他认为这些英雄历险故事是人类潜意识的形象化,是人类的“白日梦”。故事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类潜意识的活动过程,在一次次的英雄历险中,人类不断调节着自己的潜意识,使之恢复和谐,并从中获得更多的力量。因此“成人仪式”才会出现在世界各处的人类社会中。
约瑟夫·坎贝尔对世界各地神话的分析与戴锦华对王小波小说的分析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他们都剥去故事中所描述的时代和故事,抽取出它们的内核。从这种意义上说,王小波的小说和坎贝尔所分析的那些神话都指向了人类永恒的困境。神话故事指向了人类的心灵结构,而王小波的小说则指向了人类历史永恒存在的权力关系,也就是学界所说的“元历史”。因此我们可以试着从神话研究的领域汲取智慧来解读王小波的作品。王二与异化的一次次抗争、对异化的一次次战胜就是“成人仪式”原型在文学中的重现。
一、自我意识觉醒
像他的中篇小说题目《我的阴阳两界》所显示的那样,王小波的小说里有着强烈的空间意识,一种是“阳”性的,即社会空间,其中交织着种种社会权力关系,是一个异化的空间;另一种是“阴”性的,比如《我的阴阳两界》中那个寂寞、黑暗而自由的地下室,《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王二为自己打造的无法攻破的“城堡”,《黄金时代》里王二和陈清扬逃向的云南的山野,这些是未被异化的、自由的空间。小说的主人公王二就穿梭于这两种空间中,在“阳”性的空间里遇到异化的力量,于是脱离他的生活,逃往“阴”性空间,在其中获得与异化抗争的力量,再重回“阳”性空间。就是在这一次次的“死而复生”中,王二不断地抗争着,捍卫着自己的主体性。
王二在《革命时期的爱情》里获得了最初的主体性。这篇小说有一部分写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武斗,当时王二还是一个十岁出头的孩子,饱受饥饿折磨,热衷发明,对古代的侠义精神充满热情。他欣喜、主动地加入了一个武斗组织,和他们一起占领了一座楼。但是他对外界的混乱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在见过一个人被长矛扎死的情景后,他受到触动,产生了脱离自己所处社会的冲动,“成人仪式”的第一个阶段开始了。王二把他们占领的楼改造成了有着很强象征意味的空间。这个所有的窗户都被堵上,所有的墙都用黑墨汁刷过一遍的黑暗空间,有着几条地道通向外面的集市,集市上可以买到维持生存的东西。他凭着本能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像子宫一样的空间。他主动地脱离了他所生活的社会,进入了“成人仪式”的第二个阶段。在这里,他的主体性得以成长。
首先觉醒的是生命意识,姓颜色的女大学生是王二最初接触到的女性,王二对她有着青春期懵懂的情欲。在他们相处的过程中,王二感受到了女性的美好,感受到了身体的存在。身体性的觉醒是他主体性确立的起点。其次,他在创造中体会到自我的价值。王二在改造楼房和发明武斗装备的过程中感悟到:人能吃饱饭,维持生存,就实现了最低的生命需要;能有行动的自由,不被束缚,是稍高的生命需要;而只有创造,人才算实现了人之为人的独特性。在改变外物的劳动中,人对自己的本质力量得到确认。王二发明了一个百发百中的投石机,小说对其进行了十分详细的描绘,在这里,投石机不再是一个杀人的机器,而是一件充满了创造力的发明,其中饱含着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小说里也写到,王二虽然和一派人在一起,却哪派也不是,他不是为了某种理念,也不是为了某种思想而发明投石机,只是为了自己。[3]301他只是为了对自己价值的确证和由此得来的乐趣而发明。最后,王二学会了抗争,在捍卫自己的城堡和发明的过程中王二得到了勇气和抗争精神,这在每一次与异化力量的斗争中都至关重要。
当王二对外界所发生的事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后,他意识到,自己建造的这个城堡也是疯狂、杀戮、荒谬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他放弃了这座城堡,重新回归了正常生活,这是“成人仪式”的第三个阶段。经历了第一次“成人仪式”后,王二获得了自我,他开始和外在世界拉开距离,学会了观察和判断。与没有经历过个体觉醒的同时代人相比,王二认识到了“人”的可贵,他知道生命才是最重要的,科学和智慧是美好的,而外界的“大跃进”、武斗、文革等等都是暴力而荒诞的。成人仪式让王二成长为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独立感受的,具有主体性的人,从而让他从时代的洪流中跳脱出来,冷眼旁观,书写集体主义下,人们失去判断力后的疯狂。
二、爱情唤醒生命
“文化大革命”发生时王二将近二十岁,在中篇小说《黄金时代》里,他被送往云南插队,成了一名知青。那是一个极权主义的时代,极权为了对这片土地上的每个人实施控制,不惜采用暴力。在云南的乡村,王二被以“军代表”为首的权力实施者改造着,被迫做很多体力劳动。社会对个体的控制是强制性的,是通过对个体人身自由的剥夺来实现的。就像他和陈清扬参加的那些批斗会,极权通过对肉体的惩罚来实现对异己的改造。在这次抗争中,王二除了沉默就只能逃走。他跑进了山里,开始了又一次的“成人仪式”。
充满原始气息的云南山野是一个自由的、野性的空间,这里不仅没有社会权力的控制,而且充满了生命力,王二在这样的环境中重新感觉到了生命的美好。傍晚,天上飘着懒懒的云彩,天空半明半暗,在这样的环境里,王二感到这是自己的黄金年代,“那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3]6。这样的时刻唤醒了在文革的斗争环境里逐渐麻木的心灵。随王二一起逃跑的还有小说的女主人公陈清扬,小说用诗意的语言描绘了他们逃跑到山里的情景,在原始的、充满生命力的空间里,他们的生命力蓬勃生长。陈清扬和王二一起逃亡,一起耕种,一起在一个“无性”的时代体验性的美好,一起在一个“无爱”的年代产生爱情。他们彼此治愈,在诗意的自然里重拾对美好人性的希望。他们相互依靠,成为彼此的勇气和希望之源。这是“成人仪式”的第二个阶段,他们获得了全新的力量。
之后他们又返回了农场,这是“成人仪式”的第三个阶段。他们之所以又回归社会,是因为小说里王二反复思考的关于存在的问题,当彻底逃离了社会以后,人虽然自由,但也会感到困惑,会对自己的存在感到迷茫。在一场极其荒诞的运动中,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于是个体无法在这样的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都在找着自己存在的证据。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他们返回农场。他们在自然中收获的一切都成了他们抵抗异化的武器。他们回到农场之后,面临着一次次的审讯,他们一遍遍写着交代材料。陈清扬在最后的交代材料里写,当王二因为担心她摔倒而生气,而打了她屁股之后,她就彻底爱上了王二,这是在乱世里唯一一个关心自己的人。在一个人和人之间只有斗争,人和人所有正常的关系都被颠覆的时代,他们对人性的希望、他们心中的爱,把他们从一个“发懵”的状态里唤醒,让他们能以一种黑色幽默的心态去直面现实,让他们不会被文革的洪流裹挟而去。
《我的阴阳两界》里,“文革”已经结束,王二面对的是一个“正常”的世界。但是就像王小波写的,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我们”,一种是“他们”,两种人生来就是为彼此制造灾难。[3]390“他们”对“我们”进行着异化,以一种放逐的方式。就像福柯在《疯癫与文明》里引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志健全。”[4]1王二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价值观单一,对主流价值观以外的所有思想都遮蔽压抑的时代,人们通过对异己的排斥来确保铁板一块的主流价值观不受威胁。这是一个刻板的时代,小说中一再描写的四四方方的丑陋建筑、灰色的城市和毫无人气的医院就是这个完全没有生命力、反智、无趣的社会的缩影,一切都被吞噬进灰色而压抑的社会文化里。王二从两件事中察觉到这个社会对人的异化。一是他与前妻之间的婚姻,其次是他作为医院的员工所需要过的生活。新婚之夜妻子履行责任的姿态让他意识到这是一个没有“性”,也没有生命力的社会,当生命力被种种社会制度和观念所束缚时,美好和爱情也就没有了。而作为医院员工,每天开不完的会和彼此为了分房子、评职称所进行的无穷争斗,让他意识到了这是一个智慧和趣味被消灭的社会。面对这些,王二开始了又一次“成人仪式”。
在这个时代,异化的力量是通过隔离的方式对异己进行规训的,对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个体避而远之。就像《疯癫与文明》里提到的那些疯人院和麻风村一样,把那些无法融入社会秩序的异己,辨别出来,并且加以隔离,以此来维护社会主体的有序运行。[4]8王二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以自我放逐的方式从自己的生活中脱离出来。他用疾病主动把自己变成一个另类,于是社会将他隔离,他住进了医院的地下室,开始了自己的精神之旅。
在这里,王二让自己对生命、智慧和美好的感受力变得更加敏锐。王二说地下室的寂寞是他自己的选择,“寂寞就是可以做一切事的自由”[3]405“自从我断绝了对女人的单恋,寂寞就真正归我所有。寂寞纯黑如夜,甜蜜如糖,醇香如酒”[3]405。在这里,他翻译自己喜爱的小说,并且一遍遍润色,把它打造成完美的艺术;他在深夜听着电台,旁观着纷纷扰扰世界上人们的生活;他一遍遍回忆着痴迷于西夏文的“李先生”,并且在回忆里,一点点荡涤尽自己的功利心。王二说“我们”就是一种不是因为一件事有用才去做的人,而是因为它是美好的。他说“世界上美的东西岂止是少,简直就是没有,所以一旦找到了,我情愿为之牺牲性命。”[3]397小孙是小说的女主人公,她和王二一起用游戏的态度嘲讽着楼上的世界。以看病的名义和王二结婚,骑在王二的脖子上穿过医院的大院,和食堂开王二玩笑的大厨打架,趴在床上以极其别扭的姿势算王二的生活费,和王二在寂静的夜里聊天,听王二讲李先生的故事,这一系列举动,让王二意识到小孙是“我们”,是这个灰色的世界里,一个鲜艳灿烂的人。
王二和小孙结婚后,从地下室搬了出来,成为一名骨干职工。这是“成人仪式”的第三个阶段,他获得了面对生活中的异化的力量。这一段的地下室生活,让他从功利社会的泥淖中挣脱。王二磨锐了自己的感受力,他还是那个愿意为了美好的事物而献出生命的鲜活的人。即使面对的是每天开不完的会,无数琐屑的事情,爱情也逐渐日常化,但是他能以一种黑色幽默的心态去面对,以一种游戏、调侃的方式去应对单一的社会价值观对生命力的压抑。在承担起自己社会责任、融入社会的同时,他找到了一种保持自我主体性、不被单一的功利化价值观同化的生存方式。这是成人仪式带给他的生存智慧。
三、构筑精神家园
《三十而立》的时间背景是1983年,商业化浪潮方兴未艾。王二是一名大学教师,在这篇小说里,王二面对的是一种无法反抗的异化力量。当社会的重心从阶级斗争变为经济建设的时候,社会变成了科层制社会。社会不可避免地变成一台非人格化的机器,让一切社会行动都以效率为目的,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这种社会模式使人们逐渐淡化了对价值理想的追求,剥夺了人的个体自由。异化的力量不再以对抗的形式出现,而是变成了一种吸纳一切,把社会中的每个“有用”的人网罗其中的力量,个体甚至失去了表达自己是异己的机会,因为它不关心精神,只在乎利用价值,工具理性精神在吞噬着人的自由和主体性。
这同样是一个无智、无趣的社会。在学校,没有人真正在乎王二所做的科研,他的科研成果只是为吕教授挣科研经费和奖金的项目,只是为吕教授敲开出国大门的敲门砖;他实验室的冰箱被厨房的胖三姑用来存放牛奶;他的学生们早早学会了勾心斗角、欺软怕硬和挑拨离间。还有器重王二、不计较他的胡闹、处处想着提拔他的校长,让王二必须“假正经”,必须去做很多他很厌恶却不得不做的事,比如照顾住院的老姚。在自己家,种种琐事让他狼狈不堪。在父母家,父亲是一个永远争第一的人,让他感到无趣和压抑。小说用不少的篇幅描述了王二与母亲的关系,她容忍王二逃学,和王二一起聊天,告诉王二不要成为他爸爸那样的人,告诉他不用去争头名,当个正直快乐的人就行。和母亲在一起,王二自由地成长,可是到了青春期,王二的主体意识萌发以后,他就渐渐躲着母亲了,因为她总是侵入他的私人空间,打探他的秘密。为了捍卫自己的隐私,他不写日记也不写诗了。这种不自由是一种甜蜜的束缚。王二说他爱他妈,甚至超过爱他的妻子,不过他一定要证明,他和母亲期待的不同。[3]103三十而立的王二感到深深的烦躁,一种个体自由和丰富性被科层制社会压榨时所产生的烦躁。可是这一切他都不能去抵抗,他的怒火无处发泄,他所抗争的每个人都情有可原,却也都是一种更大力量的实施者。这次当他想要逃离时,发现已经无处可逃,他不可能像年轻时那样逃到山野里去,社会也不会允许他躲进地下室。这是一个“成人仪式”无法开始的时代,王二无法去一个不被社会权力渗透的空间,无法在跳脱生活的过程中获得面对异化的力量,他感到的只是烦躁。
在王二不胜其烦、无处可逃的时候,他想到了小说的女主人公小转玲,不由自主地走到了小转玲的住处。他们回忆起在北京郊区插队时的日子。回忆就是王二最后的去处,是成人仪式第二阶段中他得以逃离社会获取智慧的场域,是一个社会权力关系永远无法抵达的空间,在那里,有诗意的自然,有纯净的爱情,有读不完的好书。他找到了自己的安身之所。那里落叶像一场黄金雨,那里大雪漫天,让人分不清天和地,“在一瞬间,我解脱了一切苦恼,回到了存在本身。”[3]71这同样是一个“有性,有智,有趣”的空间,回忆里,整个农场都是他和小转玲的。小说里多次提到了王二插队时写的一篇哲学论文《虚伪论》。社会按照一定的模式运行这本身是没有对错的,王二也知道这点,但是王二无法接受这套功利的、反理性的社会运行机制。他说人总有一死,这是常识,可是人们还是喊着皇帝万万岁。在理性的逻辑里,皇帝是人,所以皇帝也会死,在功利的社会里,人们为了利益就喊皇帝万万岁。他无法融入其中,他戏谑地写到,能自如地在这两种模式之间切换是一种进化,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条光荣的道路一点也不叫我动心。我想的是退化而返璞归真。”[3]78从小转玲那里出来,王二又回到了自己所处的社会,此次“成人仪式”的第二阶段虽然短暂,但是给予了他足够的成长、力量和智慧。
在这次与日常生活的短暂脱离里,王二再次确认了“有性,有智,有趣”的追求。在回忆里让自己的感受变得敏锐,让自己对生命、智慧和有趣的追求更加坚定。小说的最后,王二回归自己的生活,他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去医院给校职工陪床,在早晨从陪床的医院回到学校,昏昏沉沉地躺下时,他意识到,社会为他的成员所设置的目标,无非是让他们争取将死时的一个好病房,以及死后的体面葬礼。他觉得这和一心想住进粮仓的老鼠无异。他认识到了那个时代的运行逻辑,并且没有卷入其中。这场与异化的斗争,并没有取得轰轰烈烈的胜利,毕竟他只能在这个社会里活下去,承受着存在之烦。但是这次他的胜利是结实的,他在这个被社会权力所统治的世界里开辟出了自己的空间,他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其中他能诗意地栖居。而一个人精心建立起的精神家园,是外界力量无法摧毁的。
四、结 语
王小波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很独特的一位作家,他身上的标签有“特立独行”“自由主义”“幽默”和“智慧”等等。这些特质都意味着,他是一个有着独立个体,独特个性的人,同时,他对时代有着清醒的认识,却以一种看起来轻松幽默的方式去与时代相处。他的这些特征与他的这种精神成长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每当他的生命力直觉到异化的力量时,他就会选择暂时地跳脱生活,在一个社会关系无法触及的场域审视生活、审视内心,重新确立起自己的主体性,从而获得应对生活的智慧和力量。
王小波小说的主题是对人处境的关注和反思。《黄金时代》这部小说集就是王二这个人物的成长史,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所面对的处境和他的应对,可以看到他的自由精神在面对各种各样的异化力量时所做的抗争。我们会发现,王二通过一次次的“成人仪式”,让自己在“异化——自由”的结构里不断攀登。让自己从现实中抽离,在这种远离中让自己重新体会自由、获得对诗意的敏锐感受,以此来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和精神自由。在信息化、商业化、科层制的今天,在这个看似没有愤怒、没有抗争、没有压迫,只有一片享乐的时代,我们如何面对商业的无孔不入和科层制的无所不在,如何面对商业社会的价值观对个人主体性的抹杀和工具理性精神对人的异化,如何在这个被商业统治而渐渐没了诗意的时代“诗意地栖居”?通过对王小波这一系列小说的系统解读和分析,也许我们能得到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