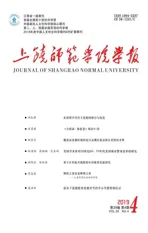辛弃疾送茂嘉弟二词作年考辨
2019-02-20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辛弃疾为族弟茂嘉共写过两首词,分别是《永遇乐·戏赋辛字送茂嘉十二弟赴调》与《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关于上述二词的讨论,虽然从古至今侧重各异,但却始终无法绕开作年问题“另起炉灶”。早期涉足辛词编年的学者,如辛启泰先生、梁启超先生等人认为此二词为辛弃疾在与族弟分别之际所创,作年较早;上世纪中期,邓广铭先生在《稼秆词编年笺注》中以刘过的《沁园春·送辛幼安弟赴桂林官》一词为参考,推断二词应产生于刘过入幕之后和辛弃疾起废之前,均属于辛弃疾隐居瓢泉期间(1194-1202)的作品;随后80年代罗荪先生发表论文,通过辛弃疾《贺新郎》与刘过《沁园春》之间的内容联系,将《贺新郎》之作年推定到了开禧元年(1205)的春夏之交,此时刘过恰在京口访晤辛弃疾,秋时辛弃疾方归隐铅山;直至本世纪初,辛更儒先生以新发现的辛氏族谱、墓志等资料重新修订编年,《永遇乐》与《贺新郎》的创作年份才得以真正分开。
本文即在上述研究背景与历史材料的基础上,挖掘方志、序文与词作内容等线索,以期进一步明确《永遇乐》与《贺新郎》的创作时间,从而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与体悟词作内涵。
一、《永遇乐·戏赋辛字送茂嘉十二弟赴调》作年考辨
依族谱来看[1]1575,茂嘉弟名为辛绩(勣),与辛词中常出现的“佑之弟”辛助属同辈,是济南辛氏一支中辛弃疾的族弟,题中既标为“十二弟”,可见辛绩排行应在第十二。“赴调”即前往临安听候吏部迁调,因而词中送别一事,应发生在辛茂嘉赴京调选之际。也就是说,此词与辛茂嘉的仕历行踪息息相关。
在《辛弃疾集编年笺注》中,辛更儒先生曾提供过一条珍贵史料,即《闽中金石略》卷七所载福建晋江县清源山一段宋人题名:“庐陵胡仲方,温陵林广叔、高密赵东武、莱阳辛茂嘉,庆元三年(1197)二月中休来游”[1]1576。“莱阳”位于今山东烟台西部。据朱熹的《济南辛氏宗图旧序》,莱州辛氏与辛弃疾家族属同宗关系,所以此处的“莱阳辛茂嘉”,应该就是辛弃疾的族弟辛绩。胡、林、赵、辛四人既然是“中休来游”,那么便极有可能为共事关系,工作闲暇同至清源山一带游历。四人中除辛茂嘉外,唯有胡仲方之行迹可考。胡仲方名榘,按《资政殿学士赠通奉大夫胡忠简公神道碑》所写,其在绍熙三年(1192)曾任“文林郎,监泉州市舶务”[1]1576,辛更儒先生推测:“胡仲方在绍熙三年所任的泉州市舶可能是待阙之职”[1]1576,这样胡仲方五年后与辛茂嘉一道中休,就可以解释通了。虽然这一设想目前尚无可证,不过由此段金石题名,我们至少可以确定辛茂嘉曾就任于福建南部一带,且庆元三年时仍在任上。
那么《永遇乐》题中的“赴调”入京一事,便应发生在辛茂嘉于福建地方任职期满之际。而通观《永遇乐》全词,不难发现这是首宣扬家风与勉励族弟的佳篇。
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得姓何年,细参辛字,一笑君听取。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
世间应有,芳甘浓美,不到吾家门户。比着儿曹,累累却有,金印光垂组。付君此事,从今直上,休忆对床风雨。但赢得,靴纹绉面,记余戏语。[1]1574
上阙以自己的姓氏为切入点,言辛家虽世代艰辛,却始终铭记忠肝义胆的初心,且风雨无悔。用笔恳切,掷地有声!下阙则以煊赫人家为比较,从反面立意来警戒族弟:切勿学那些腰缠金印的小辈们攀附权贵的行径。同时又以诙谐之语勉励其勇往直前,光耀门楣!对比以往书写送别的诗文词赋,辛弃疾此篇《永遇乐》的立意无疑显得严肃而又意味深长。那么为何他会在茂嘉弟即将赴京之际,谈到家谱、家训这类深刻的话题呢?
众所周知,族谱是记载血缘与世系繁衍的重要证明,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中都发挥着极大作用,所以修订族谱便成为维系家族血脉的大事,尤其在宋代取消官方修订族谱的传统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民间修谱风气的兴盛。在南宋国土分崩、家族离散的形势下,人们对于家族维系与宗谱修订愈加重视。作为南宋著名的爱国词人,辛弃疾自然也不例外。依民国修订的《铅山鹅南辛氏宗谱》和2006年发现的《菱湖辛氏宗谱》来看,朱熹曾在临终前月为辛弃疾手撰的《济南辛氏族谱》作序。在这篇序文中朱熹写到:“戊午,公(辛弃疾)复起就职,来主建宁武夷冲佑观,益相亲切。庚申之春,同游武夷山中”,随后在游览的过程中,朱熹由“水之源流”探讨到世系的支脉繁衍,辛弃疾感触颇深,于是邀请朱熹为自己新制的宗图作序。文末落款:“时宋庆元庚申二月戊午,新安朱熹题。”[2]根据宋史,庆元四年(1198)辛弃疾复职主管建宁冲佑观。而朱熹此时也正在建宁府建阳考亭附近居住,虽然宋代的奉祠之职按例不用亲往其地供职,但是辛弃疾此时的铅山住处与建阳地区相距仅二百来里,按古代车程也不过一天,两人间走动增多,关系日厚,自在情理之中。依照《旧序》,辛弃疾早在“庚申之春”,即庆元六年(1200)二月前就已经“窃制宗图”,并欲以此来“诏诰从人”,使其知源流、辨疏戚,“承传久远,以叙尊卑。”[2]
诏诰,多用于君臣、父子之间,此处当指对族中后辈的训诫与勉励,恰与《永遇乐》全词的思想内容相关照。据此,《永遇乐》便极可能是一篇诏诰之词,且就写在辛弃疾将家谱示与族弟的过程中。由此观之,词中的“千载家谱”便是实写,而“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则是辛弃疾面对刚正勇毅的宗族先辈所发出的由衷慨叹。“得姓何年”之语在词中本略显突兀,既不与勉励族弟的前后文意相通,又偏偏以问句形式出现,也不应答便另起“细参辛字”数语。从行文思路讲,这种写法未免过于跳跃,不似自问自答,倒更像是在询问旁人。如果此词创作于辛弃疾与族弟共览家谱之际,那这句兀自插入的“得姓何年”就可能真是辛弃疾对茂嘉弟的一番发问了。
而由《辛弃疾信州词与信州生活》[3]一书看,辛弃疾隐居瓢泉期间对于家族谱系的格外关心,与当地乡民的家族观念密不可分。如鹅湖山下的周氏家族,就曾因三世同堂而远近闻名,甚至得朝廷旌表,辛弃疾亦为此先后赋《最高楼·闻前冈周氏旌表有期》等多首诗词,以表钦羡。由此看,谪居瓢泉的岁月应该是辛弃疾修订家谱的黄金时期。而由前文所述,辛弃疾与朱熹早在庆元四年(1198)便已熟识,以朱子文章之造诣,倘若家谱在此前完成,那么辛弃疾直至庆元六年朱熹抱恙之际,方才邀其作序,便明显不合情理。所以从辛氏宗谱完成到庆元六年(1200)的武夷之游,前后应相隔不远。可惜陆九渊为辛氏族谱所作旧序目前尚不得观览,由现存与家谱相关之信息很难推断出其确切的完成时间,只能大致估算在庆元五年(1199)秋冬成稿。考虑到辛茂嘉此次入京赴调职务未定,兄弟二人再次相聚不知何年等实际情况,那么此次相聚无论家谱是否完成,辛弃疾应该都会将之示与族弟,以承家风。且从《永遇乐》中“千载家谱”之语看,此时家谱至少应是接近成稿的状态。由此,辛茂嘉的离任时间便成为考辨此词作年的关键。既然辛茂嘉是在庆元三年(1197)二月中休出游的,那么其上任时间最晚应不超过该年之春。按南宋基本“三年一易”[4]的传统进行约算,其离任时间最晚也该在庆元六年(1200)夏。所以《永遇乐》的作年便大体应在辛氏宗谱成稿到茂嘉弟最晚离任期间,即庆元五年(1199)秋至庆元六年(1200)夏这一时间段内。此时辛茂嘉刚好在福建一带仕任期满(约为三年),须按例入京,便特意于赴调途中前往铅山稼轩居处或武夷冲佑观附近,访晤族兄辛弃疾,随后赶往临安听从吏部调任。
二、《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作年考辨
辛弃疾写给茂嘉弟的另一首词,便是被陈廷焯称“沉郁苍凉,跳跃动荡,古今无此笔力”[5],被王国维赞“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6]的《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现将全词摘录于下: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1]1731
此词因笔法特异新奇,情感沉郁悲凉,而广为历代词评家所关注与称道。但也正由于其词风之悲、构思之妙,使得词意难明,以致历史上关于词作内容、用典意图等问题的探讨长久以来未曾停歇。其中一并被纳入讨论范围的,还有刘过的一首《沁园春·送辛幼安弟赴桂林官》:
天下稼轩,文章有弟,看来未迟。正三齐盗起,两河民散,势倾似土,国泛如杯。猛士云飞,狂胡灰灭,机会之来人共知。何为者,望桂林西去,一骑星驰。
离筵不用多悲,唤红袖佳人分藕丝。种黄柑千户,梅花万里,等闲游戏,毕竟男儿。入幕来南,筹边如北,翻覆手高来去棋。公馀且,画玉簪珠履,倩米元晖。[7]
因为这首词也是送别辛弃疾族弟之作,通观辛弃疾作品又只有送茂嘉族弟一篇语涉凄凉,与该词慨叹惋惜之意相符。遂而古今学者多将二词所述作为一事来看待,认为“茂嘉以得罪遣徙,故有是言”[8]。
罗荪先生也认为,从辛词引“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之典,和刘词“离筵不用多悲”之语来看,二词“当作于同一宴会”,且刘词写“送辛幼安弟”,“而不直称被送者之名”,可见刘过与辛茂嘉并不熟络,应是源于辛弃疾的关系,方才参与了此场离筵,并赋词相送[9]。关于辛、刘二人的交往情况,按邓广铭先生所考,应始于嘉泰三年(1203)刘过至辛弃疾幕下为官。随后开禧元年(1205)辛弃疾“在镇江守任”期间,刘过曾至“京口访晤”,约莫在“春夏之交”[10]90。那么送别茂嘉弟一事,定然发生在辛、刘相识到刘过逝世的时间段内,即嘉泰三年(1203)至开禧二年(1206)间。
而在此之前,北方在“金大定二十九年至明昌五年(1189-1194)连续发生旱灾”[11],百姓饥馑连年,金政府却仍横征暴敛,致使民生凋敝,起义不断,数十万饥民“流徙在唐、邓、颍、蔡、寿、亳间”[12],亦有许多不堪重赋的中原民众南渡入宋。开禧元年(1205),宋使李壁自金归朝后,更是直言“赤地千里,斗米万钱,与鞑为仇,自有内变”[13]。在此背景下,南宋以韩侂胄为首的主战派开始筹谋北伐事宜,辛弃疾也在嘉泰三年(1103) 被重新启用,并于次年正月得韩侂胄召见。
而今来看,这些史料与刘过《沁园春》[8]中的“正三齐盗起,两河民散……狂胡灰灭,机会之来人共知”数语,是基本吻合的。随后的“何为者,望桂林西去,一骑星驰”,则表达了刘过本人对于辛茂嘉贬谪桂林一事的痛心与惋惜。结合下阙中“入幕来南,筹边如北”之语,辛茂嘉在抗金过程中,应是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很可能便是辛弃疾原本“北伐”设想中的“左膀右臂”,可惜未及参与,就被调往桂林。“馀”即剩余之意,“且”即暂且,“公馀且”也就是劝慰辛茂嘉暂且放下未完之志,身在桂林不必牵挂北伐诸事。此处“画玉簪珠履”,应是借用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1]559中“玉簪螺髻”之写法,代指祖国的大好河山。而“倩米元晖”同样也是对《水龙吟》中的“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的仿写,“倩”可以解释为雇请,“元晖”则是北宋书画家米芾长子米友仁的字。米友仁世称“小米”,以书画造诣之深而备受高宗的赏识优待,甚至一度官至兵部侍郎等职,此处刘过很可能是想以米元晖绘画之妙,来标榜辛弃疾用兵之神,同时寄寓江山恢复指日可待的美好愿景。
思及开禧元年(1205)三月辛弃疾曾因“坐谬举”而被降两官,同年六月又“以言者论列,与宫观”[10]92,若茂嘉弟是在开禧元年(1205)春夏之交赴任桂林的,那么此时在京口访晤的刘过对于恢复之事的态度,应该远没有《沁园春》中这般热情高涨与意气昂扬。而据《咸淳临安志》[1]1576卷五十一中所记,辛绩曾在杭州仁和县出任县令,可惜离任时间与历任任期均已难详。由前文推测,仁和县令应是辛绩期满赴京后所得的调任,因而其出任时间大概在庆元六年(1200)。虽然直至宁宗嘉定九年(1216)方有“京官知县必以三年为任”[4]的硬性规定,但此前除特殊调动外,京官知县的仕任年限也基本都在二至四年之间。由此推之,辛茂嘉应是在嘉泰二年(1202)到嘉泰四年(1204)间被调往桂林的。既然辛、刘二人嘉泰三年(1203)才真正相识,那么茂嘉弟赴桂林任时,只有嘉泰三年当年符合刘过刚好在稼轩幕下,可能参与离筵的情况。又由《贺新郎》一词中“鹈”“鹧鸪”与“杜鹃”等暮春名物及“春归”一词来看,此次送别应在春夏之交。《离骚》中“恐鹈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14]句与辛弃疾题下自注,亦可为之佐证。综上,辛弃疾此篇《贺新郎》的创作时间当约在嘉泰三年(1203)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