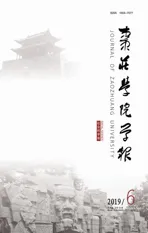略论贾科梅蒂作品中的自由、真实与存在
2019-01-29颜刚
颜刚
(枣庄学院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山东枣庄 277160)
瑞士雕塑家兼画家的阿尔伯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1901~1966)以其作品中瘦长的符号化的人物形象而著称于世,在20世纪西方现代美术领域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在作品中对于形象本身与周遭空间关系的处理以及其对形象抽丝剥茧般剥离出最本质内容的表达方式给予后现代主义艺术家们以启迪。纵观贾科梅蒂不同时期的作品,存在着共同的特质,即对艺术创作中对真实与绝对自由精神的向往与追求以及基于现实考量而对存在所作的淋漓尽致的诠释。
一、早期作品
在贾科梅蒂逐渐确立个人风格的历程中,其较为早期的探索即显现出了其对于自由与存在进行个体化思考的端倪。贾科梅蒂在定居巴黎的初期,受到了原始艺术、立体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在贾科梅蒂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无论受到哪种艺术风格的影响,其作品均呈现出共同的特质,即对隐蔽在物象表面特征之下的本质内涵的一种表述。这是一种体察方式的转变,贾科梅蒂由此开始将眼见的真实转化为内心的真实,而这种对于内心的真实的追求与表述,其背后深层意义上所要去彰显的正是对艺术中的绝对自由精神的向往。
(一)扁平风格作品
从贾科梅蒂作于1927年的《父亲头像》一作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表述方式的呈现。在这件作品中,贾科梅蒂并未按照眼见的方式去塑造一个头像,而是将现实的物象做了概念化的简化处理,他将形象的五官做了平面化的处理,集合于一个倒三角形的平面之上,运用刻画的方式进行表现,眼神的刻画简洁而又含蓄,将形象睿智的一面生动地表达了出来,面部至头部所共处的平面与呈现立体感的耳朵部位以及从作品侧面观察所呈现出来的整个头像所具备的体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表达方式在塑造方面的缺失实际上并未牺牲掉作品的表现力度,反而因为对物质的削减与浓缩,使得作品形象本身更凝聚了极具膨胀力的张力因素,这种对于面部物质的压缩所形成的头像整体扁平感以及由于压缩所形成的由内及外的扩张力在贾科梅蒂日后的作品中成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这种“扁平结构”在贾科梅蒂作于1927年的《扁平的母亲头像》一作中也得到了同样的体现,尽管在头部及面部五官体积的塑造方面,这件作品与《父亲头像》一作的表现方式有异,但是其整体头部所呈现出来的扁平状特征依然清晰可辨,尤其是形象右脸颊部位及头部区域的表现,按照正常的视觉经验来说,如果从形象正前方观察,这些部位会处于侧面位置,但是在贾科梅蒂的这件作品中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状态,这些部位像是被翻转了90度的角度而与形象面部五官共处同一平面,从而使得形象整体呈现出一种如同被挤压扁的扁平状态。贾科梅蒂曾就关于对其作品自我解读的相关问题时谈到:“如果我看着你的正脸,我就忘记了你的侧脸。如果我看着你的侧脸,我就忘记了你的正脸。”从上述这段文字分析,不难发现,贾科梅蒂在作品中关注的点并非局限于客观如实的再现,而是在与表现对象的对话中去把握真实的感受,而这种真实的感受与呈现则有力地彰显了其作品在表述方式上所具有自由精神。贾科梅蒂在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观察方式的转变或者说对客观视觉经验的反叛与其所处时代的艺术发展背景存在着必然的关联,“20世纪初在欧洲各国出现的现实主义思潮,普遍具有批判传统道德观念和美学观念的因素。”[1](P326)这些先锋艺术所普遍倡导的带有实验性质的自由精神为贾科梅蒂的创作思路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大茅屋学院的写实主义的创作方向已经不能够完全满足其精神世界的探索与追求,并对具象写实雕塑产生了逆反情绪。这种自由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其尽可能地摆脱了物的束缚,所以在艺术观念与观察方式上为贾科梅蒂提供了更深远的空间与更广阔的可能性,以至于其在后期的作品中得以进一步的发展并最终完全脱离物的束缚,从而形成了其符号化的火柴杆式的人物造型形式,将这种自由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二)超现实主义风格作品
如果说这一时期扁平风格的作品(包括贾科梅蒂受古埃及雕塑以及大洋洲土著雕刻影响而创作的作品)在对自由的表述上还停留在艺术观念与表达方式的层面,那么贾科梅蒂在受到超现实主义影响以后在其作品中所作的思考,则为其艺术形式注入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贾科梅蒂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创作具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比如作于1927年的《匙形女人》等),遂后成为超现实主义艺术圈的骨干,并与超现实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法国诗人和评论家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1896~1966)共同发起了超现实主义运动。在贾科梅蒂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充斥着欲望的情怀,性暗示与暴力因素成为作品中的主导因素,比如其作于1931年的《不满意的对象》,作品形象类似于一个被抽象化了的男性生殖器,在器物其中一端的表面排列着一些尖锐的刺状物,引导着观者对暴力因素的感官联想;再比如其作于1932年的《女人与其喉咙切割》,作品形象近似于一个呈平躺曲腿状的被切断头部的女性躯体,在其躯干部分横向平行排列着若干呈尖锐状的刺状物,隐喻了谋杀与强奸的意象。通过这些类似作品的表述,再比如其《令人不愉快的物体》中呈尖刺状的男性生殖器的意象,不难发现,贾科梅蒂在对性的表述上,并未停留在对性的愉悦的表述层面上,转而作了一种带有挑衅与攻击性的具有暴力色彩的表述。他的这种表述倾向的根源或许从其青少年时代的经历中可以找到线索与依据,贾科梅蒂曾经于1917年时患上了腮腺炎并且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此后其一直备受间接性阳痿的病痛折磨,这种青春期所遭受的巨大打击无疑会在其心理上留下深深的阴影与烙印,而这种影响又会反过来在潜意识中激发其创作灵感,成为其创作的动机。或许贾科梅蒂在其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性暴力的暗示与隐喻正是其基于身体的缺陷而在心理上通过作品所做的补偿。或许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贾科梅蒂在患有间歇性阳痿症以后时常混迹于妓院并在中年以后寻常情人的问题,如果说其在作品中的发泄可以视为单纯的心理上的补偿,那么其在生活中的行为则可视为通过生理行为完成心理补偿的双重补偿。此外,贾科梅蒂在其作品中所表现的女性形象无一例外的都是年轻形象,同时其在现实生活中所寻找的情人也都是年轻女性,这或许同样与其青春期的症结存在着密切的关联。由此,贾科梅蒂实现了其作品从形式到内涵的过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在超现实主义这一时期作品中所进行的思考与表述,也可以视为一种对真实与存在的诠释,即其作为一个个体而言,其存在的真实与意义。
二、二战时期及二战后作品
20世纪30年代中期,贾科梅蒂的创作观念发生转变并于1935年与超现实主义彻底决裂并脱离了该艺术团体,随后贾科梅蒂重新回到画室面对模特进行创作,回归到其20年代的创作方式并开始“重构头部”,这一回归对贾科梅蒂而言意义非同寻常,它直接开启了全新的贾科梅蒂艺术篇章。
(一)微小雕像作品
贾科梅蒂在此后直至二战结束以前的这一个时期所创作的作品在风格上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作品以体积微小的人像为主。贾科梅蒂在这一时期的创作灵感或许源自于其一次不成功的尝试,1937年他使用一个18英寸高的石膏对一个女人像进行雕刻,在雕刻的结果始终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情形之下,贾科梅蒂始终没有放弃继续雕刻,直至把石膏的体量缩减到了无法再小的地步,才不得不中止了雕刻;亦或是源自于其根植于骨子里的对真实的认知,传说在其小时候曾跟随其父亲对着一排梨进行写生,但是贾科梅蒂把梨画得越来越小,让其父不能理解的是这些梨在年幼的贾科梅蒂眼中的真实显现就是如此的微小。这其中的因果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客观上来说,在观察的视角这个问题上,贾科梅蒂的角度总是与其他艺术家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二)存在主义倾向的作品
纵观二战后贾科梅蒂直至离世前所创作的作品,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即对自由、真实与存在的表述,在这一表述的背后深刻地体现着其对人的存在这一严肃命题创作的一种艰涩而又深情的思考,这种思考决定了其作品深刻而又颇具哲学意味的内在品质,充分地展现了人在命运面前无力且抗拒的现实图景,将人的彷徨、无助、压抑、绝望等诸多情绪以及人为寻求存在价值所做的抗争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贾科梅蒂在这一时期的作品被普遍认为具有“存在主义”的倾向,“他的雕塑表现人的孤独无援和‘空无’的忧伤,反映经历残酷的二战之后人们心灵所遭受到的创伤以及他们追求自由的强烈愿望。他说:‘我作画与作雕刻,是为了攻击现实,是为了保护自我,是为了拒绝死亡,以争得所有可能的自由。’”[1](P339)萨特说贾科梅蒂的作品包含了两个基本要素:绝对的自由与存在的恐惧。[1](P339)“贾科梅蒂等人的作品曾参加1963年在西德达姆施塔特的题为‘焦虑在现代艺术中的表现’的展览,德国艺评家霍夫曼(W·Hofmann)说:‘这个展会所关心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安……我们必须将希望也包括进去,因为它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之一。’”[1](P339~340)在上述文字的论述中,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贾科梅蒂的言论以及萨特与霍夫曼对贾科梅蒂作品的评论,这三者共同揭示了贾科梅蒂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对自由、真实与存在所作的具有存在主义倾向的表述其发生的原因与表述的内涵。尽管贾科梅蒂并未实际上亲身经历二战,其于1940年回到瑞士的日内瓦避难并于1945年战争结束以后重返巴黎,但是战争残酷而血腥的极端暴力对世界与人的摧残力度是空前巨大的,即使战争已经结束,但战争投射到欧洲大陆的巨大阴霾不可遏止地弥散开来,整个欧洲大陆被不安的气氛所笼罩,在这种情形之下,到处充斥着悲观而绝望的情绪,人们在灾难过后面对周遭现实图景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普遍性的不安与焦虑,这就是上述霍夫曼所言“时代的不安”与“时代的焦虑”,贾科梅蒂置身其中,同样不可避免地陷入这种不安与焦虑之中,而这种不安与焦虑很自然地成为了其创作的源泉,加之贾科梅蒂天性之中对经由视觉层面“看到的”到心理层面“感到的”人最为真实的存在状态即“真实”的追寻,这种创作源泉与创作动机的产生也是顺理成章的。贾科梅蒂的交际圈甚广,作为战后风靡一时的“存在主义”学说创始人的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Pean Paul Sartre,1905~1980)也曾是其朋友圈的一员,他们曾共同讨论过有关人的存在的相关议题,此外,存在主义哲学由于其极大地对应了二战后西方社会的现状,因此其对当时那个时代西方社会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甚至成为了当时普遍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由此,可以推论,存在主义哲学对贾科梅蒂艺术观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贾科梅蒂本人并未公开宣称其对评论家对其这一时期作品存在主义性质界定的认可,但从其作品形象本身所折射出来的内涵特征来分析,其作品依旧具备存在主义哲学的某些特点与倾向。
考察贾科梅蒂在二战期间作品与二战后作品的区别,不难发现,其存在着下述几个方面的不同:
1.形体特征发生了变化
贾科梅蒂在二战后将其作品中的形体在原有作品形体的基础上进行了夸张与变形,形体变得更加瘦长,并发展出了其标志性的火柴杆式的作品形象,这种符号化的形成在贾科梅蒂的创作中一直延续到其生命的尽头。这些火柴杆式的形体如同被战火烧焦的人体,孤立无援地伫立着,如果说仅凭形象的外形特征无法完全论证贾科梅蒂对人的存在所作的具有存在主义倾向的表述的话,那么形体的表面特征或许可以加以佐证,在贾科梅蒂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形体表面变得更加斑驳,他同时放弃了对雕像表面的打磨使其凹凸不平、粗糙生涩的表面显露无疑,这种状态从感官上加剧了观者对战火烤灼的肉体模糊不清的视觉联想。此外,在贾科梅蒂火柴杆形式的雕像作品中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是个体雕像,另一种是群体雕像,如果说个体雕像依旧无法充分说明问题,那么贾科梅蒂在作品中对群体的表达或许另有深意,比如其作于1948年的《三个行走的人》,三个形体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同时又因各自行走方向不同而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如同三个形色匆匆的陌生人,彼此擦肩而过,彼此带着各自的茫然,呈现着一种疏离的气氛,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陌生与疏离恰当的对应了二战后普遍存在于人心理层面的焦虑与不安,人们身处彼时的情境之中已无暇顾及彼此,只能被动地深陷自身的焦虑与不安之中,而这也是当时欧洲那个时代的一种群体意识,即“时代的不安与焦虑”,这亦可视作佐证之一。这种群体意识即使是在其创作灵感来源于风景因素而制作的群体雕像作品中亦有所表现,比如其作于1959年的《森林》,尽管贾科梅蒂在作品中将女人与树、男人头像与石头作了象征性的表述,但是其个体之间亦呈现了彼此陌生与疏离的状态,形同陌路,彼此静默不语,如同现实之中的树与树之间、树与石头之间彼此独立的存在,这亦可视为同一语境下的群体意识。
此外,关于这种火柴杆式的人物形象方面,李建群在其《20世纪英国美术》一书中提到“贾科梅蒂细瘦而孤立的人物……男人的裸体,没有支撑物,孤立,没有任何神秘意义或叙事意味。但这些人物不是为了强调无力和孤立,而是用来集中力量,用贾科梅蒂的话来说是为了‘抑制能量’:这一生命的绝望和肯定之间的微妙的平衡保持在一个持续振荡的状态”。[2](P88)贾科梅蒂对形体的消减使得形体处于一个显现与消失的临界点,即上述文字中所提及的“持续振荡和状态”,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保持这种状态的目的,即上述文字中所提及的“这一生命的绝望和肯定之间的微妙平衡”,这种平衡恰当地对应了空间对形体的压迫以及形体为拒绝消亡而做的抗争,如同战争对人的摧残以及战后人的绝望与抗拒,这或许可视作贾科梅蒂战后作品对人的存在所作表述具有存在主义倾向的另一个佐证。
2.雕像大小发生了变化
贾科梅蒂在战后的作品中将形体体量放大,或与真人等大或者更大,联系其前期作品中对形体的微缩以及其对于“微小”的论述,这似乎成为了一种悖论,而这恰恰能够适当地诠释其对人的存在所作表述的存在主义倾向。贾科梅蒂或许是出于表现力度的需要而将形体放大,或许可以更准确地说,被放大的不单纯是形体本身,更是隐含于形体内部的焦虑与不安,贾科梅蒂似乎更要将人的绝望与压抑情绪通过形体的被放大藉由观者的视觉震撼而去作一种更为淋漓尽致的表达,这同样源自于其对真实的追寻,只是真实在此处的意义已发生了改变,经由原来的视觉真实转变成为情感真实,这种转变以牺牲其原有的“拒绝制造现实形象的对等物”的艺术观念作为代价,作为一种自身的悖论,或许相对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其要将人的这种现状活生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如此一来,贾科梅蒂在这一时期作品中对真实的表述就演变成了其情感层面对悲惨的、绝望的人的现状的关怀,同样源自于其对真实的追寻,只是出发点与角度不同,这或许可以成为其自身这种悖论的合理解释。
3.创作题材发生了变化
在贾科梅蒂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关于题材的选择有几个因素尤其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1)残缺的躯体因素
比如其作于1947年的《一只手》,在这件作品中,仅仅对一只单独的手臂进行了表现,贾科梅蒂对残缺肢体的表现在内涵的表述上或许有其深层意义,如果说单就一条手臂表现而言,尚不能足以表达贾科梅蒂对“视觉真实”的追寻,相对合理的解释或许是其试图藉由形体的残缺去再现战争因素对人的摧残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的“自我”的破碎,而这种“破碎”也恰当地对应了当时的历史情境下人深深的无奈、绝望以及“对抗”上的无力,只能被动的陷入一种“自我的沦丧”。
(2)战车因素
比如贾科梅蒂作于1950年的《双轮车》,尽管其在作品中对车轮性质的指示性尚不明确,但是结合站立于其上的雕像极易引发观者对“战车”的视觉联想,如果说单就“车轮”与“人体”这两种因素结合的表现而言,其并不存在太大的现实意义,或许贾科梅蒂在这两种看似不太相干的因素内所注入的正是“战争”与“人的存在”的本质内涵,通过这种方式去隐喻战争的残酷与人的极致绝望。
(3)笼状物因素
比如贾科梅蒂作于1947年的《鼻子》,这件作品或许可以视作其对于“人与环境之间的对抗” 所作的最为直接的诠释,在这件作品中由框架结构所构成的笼状物像是对密闭空间的隐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贾科梅蒂在作品中对形体的表现,其形象虽近似人形,但较之贾科梅蒂作品中普遍存在的形象,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肆意的变形上,在其巨大的呈现呐喊状态的口部之上,一个细瘦奇长的呈棍状的鼻子直挺挺地呈平行状横穿出笼状物的体外,强烈地呈现出一种颇具攻击性的态势,如此一来,给观者以强烈的视觉刺激,贾科梅蒂如此强烈的表达从其形象特征而言,视觉真实已然失去了必要的关联,其似乎是要试图去诠释当时西方的社会存在中人对环境的抗拒,这也使得笼状物在作为密闭空间的隐喻的同时象征了环境对人所施加的压迫。此外,其对形体这种肆意的变形,同时包含了人的异化因素,而躯干部分的残缺由于基座的消失使得其破碎感得以加剧,如此一来,使得其形体还包含了“破碎的自我”因素,而这种自我的沦丧与异化同时可以视作笼状物作为环境因素去做隐喻的合理解释。而在贾科梅蒂作于1950年的《笼子》中,形体伸展并附着于笼状物框架边缘所引发的人对环境加以抗拒时的无力感与挣脱感以及由于被置于笼状物偏下方部位的悬浮基座所引发的环境对人的压迫感,亦可视为这种合理解释的佐证之一。
此外,关于环境压迫与人的反抗因素,在贾科梅蒂战后的绘画作品中亦有所体现“贾科梅蒂……除雕塑外,还多画肖像,仍表达所谓‘空间敌意’主题。画中人物小,周遭空旷,暗示人类被环境压迫和困顿。画家为表现人类面对外在压力的敏感和恐惧,描绘人物使用迅捷锐利的线条,神经质般的颤栗笔法,借以体现人性的尊严和反抗。”[3](P77)除了上述论断以外,在贾科梅蒂绘画作品中,还有一种表现手法方面的因素值得我们注意,即在其作品中形象的存在介于显现与消失之间的状态,贾科梅蒂在此选取了一个临界点,比如其作于1954~1955年间的 《让·热内肖像》、作于1954年的《穿格子衬衫的蒂亚戈》、作于1948年的《迭戈坐像》等,在这些作品中,形象本身的色彩与背景相融,形象的显现主要依靠变幻多端的轮廓线的勾勒与亮部区域,闪动光斑的刻画而得以实现,由此形成了空间对形体的一种吞噬态势以及形象自身对消失的一种抗拒状态,而背景的平面化处理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又加剧了这种对抗。在贾科梅蒂其他的某些具备三维空间的场景画中,这种显现的方式同样存在,主要依靠在场景与形象的表现上其对于变幻多端的线条因素的统一运用而得以实现。通过对贾科梅蒂在绘画作品中对环境压迫与人的反抗因素的表述,反观其在雕塑作品中的表达,或许可以视作笼状物作为环境因素去做隐喻的另外一个佐证。
(4)动物因素
在贾科梅蒂这一时期系列作品中,除了较为普遍的人像雕塑以外,还有一类少见而特殊的题材,即其以动物为表现对象的作品,比如其作于1951年《狗》,如同贾科梅蒂作品中人的瘦长形象一样,其在作品中对狗的形体亦作了一种骨瘦嶙峋式的表达,纤细的四肢呈现疲惫无力的状态,从其低垂的头部似乎可以听到如同人的绝望一般的呜咽之声,形如丧家之犬,极易引发观者对战后废墟、流离失所等现实情境的视觉联想,这或许可以视作贾科梅蒂在其作品中对人的存在这一命题进行存在主义倾向表诉的另一种视角。
从上述三个方面对贾科梅蒂战前与战后作品的比对性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在战后的作品中无论是对形象特征与体量大小所做的改变,还是在题材选择上的多样性上,其这一时期的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特征无疑直接或间接的指涉了二战以后普遍存在于西方社会的绝望情绪以及人身陷困境之中所做的抗争,这与萨特存在主义学说的观点存在着一种本质上的契合。“存在主义一词的拉丁文Existentia,意为存在,生存,实存,存在主义哲学论述的不是抽象的意识、概念、本质的传统哲学,而是注重存在,注重人生,但也不是指人的现实存在,而是指精神的存在,把那种人的心理意识(往往是焦虑、绝望、恐惧等低沉的,病态的心理意识)同社会存在与个人现实存在对立起来,把它当做唯一的真实。”[4](P36)对此,我们或许可以从贾科梅蒂的某些言论中找寻到更为深刻的启示,贾科梅蒂曾在40年代对马尔罗说:“在布满创伤般的雕塑外表上,掩饰的是那种人类工业社会带来的深深的悲观及焦虑感”。1965年贾科梅蒂在其离世前一年的最后一次个人作品展上说:“当代艺术的一个最大文化特征,是它表明自身存在的‘现实’意义,它由大众的共同‘需要’为前提,这样‘当代艺术’才被抛入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由此,萨特笔下的“存在”经由贾科梅蒂的手完成了现实的视觉图解。
纵观贾科梅蒂毕生的作品,无不折射出其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所一贯秉持的绝对自由精神和基于现实考量而对所存在作品淋漓尽致的诠释以及其终其一生对真实的向往与追寻,他踏上的这条艺术之路,艰辛、生涩,但其满怀深情与深意苦心浇灌出来的艺术之花却于这生涩的土地上绽放出了生命的光彩,灿烂,夺目。
或许可以将贾科梅蒂视作“为自由与真实而存在的斗士”。在临终十分,他仍呐喊:“将一个头像制成如我所见,这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但总有一天,我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