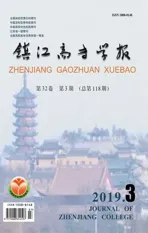《万寿寺》与《暗店街》“遗忘—寻找”主题表现差异的成因分析
2019-01-29段颖杰
段颖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英语语言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410520)
王小波的作品深受西方现代小说的影响。戴锦华认为其作品带有19世纪与20世纪欧洲文学及“道地的美国文学,诸如马克·吐温的印痕”[1]。张懿红在《王小波小说艺术的渊源与创化》一文中具体讨论了法国新小说派、杜拉斯和卡尔维诺对王小波的影响,分析了他作品中的互文、反讽、狂欢化和黑色幽默等后现代主义创作特点[2]。仵从巨另辟蹊径,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统计出王小波作品中“涉及西方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等各类人物共约173人,510次”[3]。
《万寿寺》与《暗店街》(Ruesdesboutiquesobscures)的比较研究出现于2014年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1945—)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小说主题层面,何鑫和高强指出《万寿寺》与《暗店街》有着共同的“遗忘—寻找”主题[4][5]。在叙事技巧层面,高强认为《万寿寺》借用了《暗店街》的复合文本和双重时空,不过前者更加复杂;江志全发现《万寿寺》和《暗店街》在景物描写上都“具有电影般的场景感和立体感”[6] 128。需要注意的是,王小波在创作时并非“简略地仿拟莫迪亚诺的叙事手法”[4],而是“以民族的文化意识和个人主体的想象力作出阐发和理解,然后予以创造性的发挥”[5]。具体而言,《万寿寺》中的王二沉迷于自己笔下的诗意世界,不愿重拾记忆、回到现实,《暗店街》中居伊·罗朗在苦觅无果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寻找自己的身份。那么,如何解释王小波和莫迪亚诺对“遗忘—寻找”主题的不同态度?这与两位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何关系?笔者试图解答这些问题。
1 共同的“遗忘—寻找”主题
《暗店街》对《万寿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从小说开头便可看出:
“莫迪阿诺在《暗店街》里写道:‘我的过去一片朦胧……’这本书就放在窗台上,是本小册子,黑黄两色的封面,纸很糙,清晨微红色的阳光正照在它身上。病房里住了许多病人……在这个拥挤、闭塞、气味很坏的地方,我迎来了黎明。我的过去一片朦胧……”[7] 1
王小波毫不避嫌地借用了《暗店街》中主人公失去记忆、寻找过往的叙事模式:“莫迪阿诺的主人公失去了记忆。毫无疑问,我现在就是失去了记忆”[7] 2。在《暗店街》中,主人公居伊·罗朗就是在开篇交代了自己失忆的事实,“Je ne suis rien”,即“我什么也不是”[8] 1。简单的一句话既设置了悬念,又为接下来的“寻找”之旅埋下了伏笔。
两部小说不仅有共同的“失忆”主人公,而且主人公在寻找自我身份的过程中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即“通过人证与物证(当事人、旁观者、电话簿、年鉴、档案材料、记事本、照片、信件、护照)等线索来再现和重构过去”[9]。白纸黑字的纸质材料无疑是记载过去的重要手段,斯特林堡的《半张纸》可谓个中典范,便条纸上的寥寥几个号码勾勒出两年的光阴。同样,《暗店街》中出现的各种纸质记录,犹如“阿里阿德涅线团的每一个头绪”,帮助主人公“搞清楚自己已完全被遗忘了的前半生的真相”[10] 359。另外,Akane Kawakami还指出,正是由于这些互相印证的、中立的材料记录,莫迪亚诺笔下的主人公显得更加真实[11] 72-73。居伊·罗朗的私家侦探身份让其更容易弄到各种资料,例如调查对象的信息、公使馆的名人录、过往的信件等。相比之下,王二运气就更好了,“我有张工作证,上面有工作单位的地址,循着这个线索,我来到了‘西郊万寿寺’的门前”[7] 2。王二的工作室在配殿的小房间里,里面的东西“带着熟悉的气息迎面而来——过去的我带着重重叠叠的身影,飘扬在空中”[7] 4。当居伊·罗朗长途跋涉在不同地点间来回调查的时候,王二只需“在万寿寺里努力回忆”[7] 16。
除了纸质的物证外,相关当事人和旁观者的口述回忆也帮助构建了这两位主人公的过去。他人的回忆可能不够真实,但是充满细节和想象,不少小说家都利用这一点来增添作品的文学性。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就曾说过:“我喜欢回忆,因为回忆是我们审视自己生活的过滤器。回忆模糊不清,就给自我欺骗提供了机会。作为一个作家,我更关心的是人们告诉自己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实际发生了什么。”[12] 241-242在《暗店街》中,居伊·罗朗总是通过与某个人的交谈得知另一个人的存在,然后颠簸在寻找自我的旅途中,逐渐接近自己身份的真相,整部小说充满各种对话。居伊·罗朗自己也承认他人言语的重要性:“怀尔德默前言不搭后语的话,那些姓名以及其他一些不可触知的细节,甚至包括怀尔德默沙哑的、几乎听不见的嗓音,引导我走出迷宫的正是所有这些东西。”[8] 188但是,在《万寿寺》中,王二的妻子白衣女人和他的表弟不请自来,主动谈论着他的过去种种。王二自己都不好意思地打趣道:“在《暗店街》里,主人公花了毕生的精力去寻找记忆,直到小说结束还没有找到,而我只用了一个星期,就把很多事情想了起来,这件事使我惭愧。”[7] 294
2 对“记忆”的不同看法
不难看出,王小波虽然借鉴了莫迪亚诺的“遗忘—寻找”这一文学主题,但是,他们对于“记忆”的看法不尽相同。正如小说主人公王二所说:“我和莫迪阿诺的见解很不一样。他把记忆当作正面的东西,让主人公苦苦追寻它;我把记忆当成可厌的东西,像服苦药一样接受着,我的记忆尚未完全恢复,但我已经觉得够够的,恨不得忘掉一些。”[7] 296所以,到了最后,当王二恢复记忆之时,他反而觉得“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7] 332。居伊·罗朗在得知唯一能证明自己身份的弗雷迪在海上失踪时,仍然满怀希望,“不,他肯定没有在海上消失,我终将找到他。另外,我必须作最后一次尝试:按我的旧地址,去罗马暗店街2号”[8] 225。
基于此,有学者表示,《暗店街》对王小波而言不过是个创作的“噱头”罢了[1]。这种说法未免有些草率。事实上,王小波和莫迪亚诺都意识到了“记忆”的重要性。王小波自己也借王二之口说出了这一事实:“但如你所知,我和他在一点上是相同的,那就是认为,丧失记忆是个重大的题目,而记忆本身,则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领域,是摆脱不了的。”[7] 296他们对于“记忆”的不同看法与他们不同的创作环境密切相关。
3 不同的创作背景
“莫迪亚诺以将小说背景设置在‘德占期’而闻名”[11] 69。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1939—1945),德国纳粹通过武力占领了包括法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这段历史成为老一辈法国人不愿提及的“黑暗岁月”。不少法国作家都将这段时期设为自己作品的背景,如《海的沉默》(LeSilencedelamer)的作者维尔高(Vercors)和《禁止的游戏》(Jeuxinterdits)的作者弗朗索瓦·布瓦耶(François Boyer),他们的小说都“真切反映了大战时期的生活”[10]361。
但是,莫迪亚诺生于1945年,此时二战已经结束,这就意味着,有关二战时期的法国,莫迪亚诺根本没有“任何直接的感受与第一手素材”[10] 361。那么,他为什么一再地选择这段时期作为小说的时间背景呢?莫迪亚诺曾在采访中作过解释:“我对那段历史本身不感兴趣。我只是将自己的焦虑移入其中。”换言之,莫迪亚诺无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摄取历史生活场景,他只满足于借用这个时期的名称与这个时期所意味的那种沉重的压力,这种压力直到战后很久还像噩梦一样压在法兰西民族的记忆里”[10] 361。美国认知心理学家尚克(Roger Schank)总结了历史故事(知识)来源的5种途径:官方的、编造的、直接经历的、间接获得的和文化共有的[13] 30。以集体记忆形式留存下来的法国“德占期”历史,不可避免会伴随着遗忘。如此看来,莫迪亚诺之所以着眼于二战时期的法国,是试图对抗“失忆症”。尽管莫迪亚诺不曾亲身体验过二战的痛苦,但那场灾难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影响之一便是现代人对身份的迷茫。莫迪亚诺显然觉察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笔下的主人公几乎都是“犹太人、无国籍者和飘零的流浪者”[10] 361,他们难以在现实生活中确认自己的身份。鉴于此,《暗店街》中居伊·罗朗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屡屡碰壁也就容易理解了,因为对记忆的追寻本质上就是对身份的构建。居伊·罗朗的苦觅无果,反映了战后法国人在二战的阴影和压力下、在自我确认的艰难中产生的“自我泯灭与自我消失”[10] 364。莫迪亚诺在小说中曾多次暗示了这一寓意:“或许我们最终将化为乌有。或者变成车窗上蒙着的水汽”[8] 196;“我们也是一道风景?我们的举动和我们的生命的回声,我觉得它被这棉絮一般的东西压低了”[8] 202;“我们的生命和这种孩子的悲伤一样迅速地消逝在夜色中”[8] 226。
柳鸣九认为莫迪亚诺在小说中探究了“寻找自我”这一“深邃的悲剧性的课题”[10] 364,确实有其道理。但笔者认为,莫迪亚诺的笔调是哀而不伤的。首先,他有勇气直面二战时期法国所经历的屈辱,并用隐喻的笔法揭露二战危及现代法国人的身份确认。其次,莫迪亚诺对于“寻找自我”并不是全然绝望的,《暗店街》中屡屡碰壁的居伊·罗朗到了最后也没放弃对自己身份的探寻。此情此景不由让人联想到法国作家加缪(Albert Camus)笔下的荒诞英雄西西弗。“只见他凭紧绷的身躯竭尽全力举起巨石,推滚巨石,支撑巨石沿坡向上滚,一次又一次重复攀登。这种努力,在空间上没有顶,在时间上没有底,……但西西弗眼睁睁望着石头在瞬间滚到山下,又得重新推上山巅。于是他再次下到平原。”[14] 128-129在笔者看来,居伊·罗朗对自己身份的努力探寻,不是悲剧性行为,而是充满悲壮的意味。《暗店街》不是一首悲叹往事的时代哀歌,而是一则警醒世人的现代寓言。
如果说莫迪亚诺的小说带有寓言性质,那么王小波的《万寿寺》则更接近童话。“他无视禁忌的顽童心,他的幽默反讽才能和想象奇趣,远远超出那个时代的某种文学理解力”[15]1。
《万寿寺》呈现了两个世界:王二所处的现实世界和王二笔下的虚构世界。在万寿寺的老旧办公室中,王二不得不成为一个学院派的历史研究员,按领导的要求琢磨一些无趣的课题。万寿寺厕所的化粪池堵住了,“喷涌出一股碗口粗细的黄水”,整个寺庙“弥漫着火山喷发似的恶臭”[7] 255-256。但是,面对自己的手稿,王二就成了一个现代派的小说家,自由驰骋着奇思妙想,穷尽小说艺术的无限可能。他笔下的世界也不似现实世界那般灰黄,而是充满色彩,“一处是长安城外金色的宝塔,另一处是湘西草木葱茏的凤凰寨”[7] 266。这样看来,王二不愿重拾记忆回到现实的态度就显得合情合理了。在文本的表象之下,隐藏着的是作家对文化媚俗的无奈。
王小波成长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一个“有浓郁的西方学科教育背景或生活经历、文理交叉、充满学习交流与民主气氛的知识分子大家庭”[4] 89。除此之外,学校教育和自主阅读也是王小波接触西方文学文化的重要途径,这里的学校教育指的是“文革”后他在人民大学求学和美国留学的经历。他的母亲宋华曾回忆道:“小波的确读了许多书,而且看书的速度很快”[15] 109;“他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他不仅有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对理工科如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都用心钻研过”[15] 111。仵从巨教授通过量化分析的方法统计出“王小波谈得较多的作家是:法国的杜拉斯、尤瑟纳尔,英国的萧伯纳、奥威尔,美国的马克·吐温,意大利的卡尔维诺,捷克的米兰·昆德拉”[3]。在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和融会过程中,王小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其精髓就在于“趣味性”和“想象力”。他曾在《小说的艺术》一文中表达了对小说创作的看法:“我自己也写小说,写得好时得到的乐趣,绝非任何其他的快乐可以替代。写小说需要深得虚构之美,也需要些无中生有的才能。”[16] 64-65不幸的是,王小波心中诗意的文学世界与他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1952年他出生时,其父在政治运动中蒙冤,他的成长经历颇为不顺。其姐姐王小芹曾在信件中写道:“小波也是我们五人中经历最为坎坷的一个。因我父遭不白之冤,我妈怀他时就常哭泣,致使他生下来就身体不好。……到上山下乡风潮哄起,他竟自愿报名到最远的西双版纳兵团。我妈费尽心机,将他调到安徽干校,后干校解散,他回京做无业人员,……万般无奈,又去山东老家插队,吃尽苦难。”[15] 116-117忍受着肉体上的痛苦的同时,王小波察觉到“文革”以来中国社会存在的文化媚俗,即“对时代话语霸权的无意识和麻木”[4] 124。他在20世纪90年代写的杂文里强烈批判了“国学热”“道德保守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思潮。王二对于记忆的抗拒,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王小波对于现实的抗拒。他在小说最后写道:“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7] 332此话好似谶语,《青铜时代》(包括《万寿寺》《红拂夜奔》《寻找无双》)出版的那年,王小波意外身亡,英年早逝,真的去了自己的诗意世界。作家刘心武曾如此缅怀:“是的,王小波怎么会没了呢?他只不过到仙界去了罢。那里一定会让他感到非常非常有趣。”[17] 258
4 结束语
同样是面对“记忆”这一主题,两位作家在各自的小说中讲述了不同的故事:《暗店街》中居伊·罗朗苦苦追寻记忆,《万寿寺》中的王二却不愿重拾记忆。这种差异与两位作者不同的创作背景息息相关:莫迪亚诺以“二战”法国德占时期为背景,指出了人类对抗遗忘、寻找自我的艰难;王小波则用一种荒诞不羁的手法暗讽了同时代人的精神匮乏与文化媚俗。其实,“遗忘—寻找”这一主题更常见于西方小说,毕竟这是西方小说的文学母题,希腊神话中就有俄底修斯(Odysseus)为了返乡在海上漂流十年的故事。王小波并没有生搬硬套这一主题,而是以“记忆”为切入点,阐发了自己对文学和社会的思考。
王小波甚至还在小说中对唐传奇进行了改写,这一点难能可贵。毕竟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基本上是以西方文学为参照而形成的。其实,不少中国作家都在作品中巧妙地结合了中国文学传统表现手法与西方的文学表现技巧,例如鲁迅的《故事新编》、王蒙的《布礼》、余华的《活着》、莫言的《生死疲劳》等等。他们无疑是在挑战和探究,如何用现代汉语借鉴西方资源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