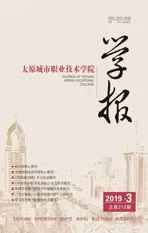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的保护
2019-01-21张洁
张 洁
(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一、问题的提出
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来临,从家居生活、自动驾驶汽车、服务业行业等领域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已悄然地进入到人类生活。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上,由人工智能创作的计算机程序、音乐作品、美术作品、诗集散文等创作物广泛存在。2014年5月29日,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STC)院研发了“微软小冰”,小冰在学习了519位风格不同的国内外诗人作品的基础上,创作出了《阳光失了玻璃窗》诗集。2017年7月5日,微软(亚洲)互联网研究院(MSRA)宣布放弃“小冰”所著诗歌版权。对于“小冰”所创作的诗集,有认为著作权人为“小冰”并依法享有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也有认为该诗集应当归属于研究院。2018年12月4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公开审理了北京律所状告百度侵权案件,该案因涉及著作权保护前沿问题而未当庭宣判。由此引发以下思考:人工智能创作物是否为作品?人工智能创作物作者应当如何认定?人工智能创作物应如何归属?
二、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理论争议
(一)人工智能创作物定性争议
1.人工智能创作物不是作品
依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著作权法上保护的作品应当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反映一定的思想或情感;第二,具有独创性;第三,具有可复制性。至少在现阶段,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只是应用某种算法、规则和模板的结果。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机器,不能同人类一般通过创作来反映思想或情感,且在算法、规则和模板设置的前提之下,人工智能对相同材料进行处理后所产生内容,重复性高且不具备独特性的特征。目前的人工智能尚处于运用“人类智慧”进行创作阶段,不能认定为著作权法上的作品。
2.人工智能创作物是作品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并未对独创性进行说明,也未规定独创性的判断标准。独创性从文字上看,需同时满足“独立性”与“创作性”,前者要求作品是由创作人独立完成,不存在抄袭剽窃行为,后者要求作品至少具有最低限度的思想或情感的表达。关于独创性认定标准,有认为是指作者个性与智慧的,也有认为是具备最低限度的创造性。人工智能除在已设定的算法、模板、程序等基础上完成创作行为之外,还可通过自主学习在没有前述设定情形下进行创作。
(二)人工智能创作物归属争议
在承认人工智能创作物可构成作品的前提下,对作品作者和著作权人的认定,有工具说、孳息说、意志代表说与创制者说。工具说认为人工智能与传统计算机一般,是人类进行创作使用的工具。孳息说是将民法上的孳息适用至人工智能的归属上,如同果树上掉落的果实归属于果树所有人,人工智能创作物也应当归属于所有人。意志代表说认为人工智能所创作的作品反映着人类的思想或情感,著作权应当归属于被反映之人。创制者说观点下,人工智能创作行为是在算法、数据、规则等设定下完成,其所依靠的设定是由人类提前设置好的,创作物实质是由人类创制而成。上述认定从工具主义、意志反映、创制人等角度出发,讨论了著作权人认定的规则。对于人工智能创作物归属存在以下观点:
1.设计者说。人工智能创作物最大的特征是由计算机在已设定的程序下完成,在创作过程中编程者投入了智力劳动,对创作物实际提供了贡献,著作权理应归属于设计者。设计者不限于自然人,也可以由法人或其他组织对人工智能创作物享有著作权。
2.使用者说。程序只是人工智能创作工具,编程者不具有通过人工智能创作的目的,相比之下使用者使用计算机在于创作作品,主观上具有创作意图。除此之外,在人工智能生成原始创作物上,使用者进行了修改、排版等行为,可以认为其是“二次创作物”的作者。
3.所有者说。该说认为人工智能的创作行为是所有者真实意志的实际表达,其生成物的权利归属可借鉴著作权法上法人作品制度规则,著作权由所有者享有。但现实中人工智能所有者与使用者分离的情况常见。
4.共同享有说。在此说基础上又存在两种观点:设计者对人工智能进行编程、规则、模板等预先设定,之后再由使用者操作后生成创作物,应当认为两者共同享有著作;有认为应当归属于人类与人工智能共有,但未明确具体享有著作权的权利主体,且在此共有情况下还需判断是否具有合作意图及均贡献了劳动。
除上述学说外,有学者主张“支配性侵权行为”可适用于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归属领域上,认为人工智能是人类进行创作的工具,创作物应当归属于人类。这一主张与工具说不谋而合。但需注意的是,人工智能与传统人类所利用纸笔、计算机、相机等工具进行创作的工具存在本质区别,人工智能可以自主学习、可以在设定的程序之上进行自主判断,与传统工具相比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三、人工智能创作物对现行著作权法的挑战
传统计算机需要在人类进行使用操作的基础上才能完成输出,该输出内容可以说完全是使用人意志的表现,该输出内容符合作品的条件下,著作权当然归属于使用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传统计算机相比,更具有自主性、学习性、智能性。人工智能创作的内容,与传统计算机与人类工作模式大不相同,人工智能只要有预先为其设置的算法、数据、模板与规则的背景下,即使在创作过程实际未有人类的参与,也可生成创作物。这一新型创作模式给传统著作权法带来了挑战。
(一)对传统法律主体的冲击
2017年10月26日,沙特阿拉伯授予机器人索菲亚公民身份。作为首个获得公民身份的机器人,索菲亚事件引发学界对于人工智能人格问题的讨论。在法人制度基础上,有学者主张人工智能可同法人一样拟制为法律主体。对此,应首先明确法人与人工智能的区别:在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上,法人的员工可以视为其手足,员工的创作可以视为法人的创作,在行为能力上可由员工具体实施,而人工智能则不具有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法人享有独立财产,可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并承担责任,相比之下人工智能不存在属于自己的财产,在发生侵权责任时的责任承担上尚在争议。据此,法人法律主体拟制不能同样适用于人工智能。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原则上作者只能是自然人,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视为作者。如上所述,人工智能不能拟制为法律主体,但在符合作者的情况下,可否参照视为作者制度将人工智能“视为作者”。
(二)人工智能运行机理下难以认定实际贡献人
人工智能的工作依赖于算法、数据、模板,在指令要求下完成输出内容。传统计算机下完成的创作,计算机仅是人类的辅助,其与手动完成相比更具有高效性,且是在使用人实际控制下进行创作工程。人工智能技术下,依据指令人工智能从现有数据库中寻找所需内容,自动生成内容。编程人与使用人为同一人时,无须对实际贡献人进行认定。当二者不一致时,对创作物的产生有实际贡献之人认定难度较大,编程者为人工智能设定的基础是工作的前提,但使用人对人工智能创作的后续操作也很难谓不存在实际贡献。
四、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保护模式
认为目前人工智能创作物在符合作品认定标准前提下,应对其著作权予以保护的学者存在多数。在人工智能时代下,对人工智能创作物予以保护,对于推进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人工智能人格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应当赋予其民事主体地位,还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具有有限人格。如上文所说,人工智能与法人在独立财产、权利享有、义务履行等方面的区别,因此人工智能人格化在目前的传统框架下尚不能得以突破。由当事人通过合同对著作权归属进行约定。易继明教授认为,对人工智能作品的著作权归属首先应该重视投资人的利益,需要重新重视人工智能设计者、所有者、使用者之间的合同安排,并且按照合同优先的原则确定权利、解决权属纠纷,如果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则应该建立以所有者为核心的权利归属制度。这一通过合同约定的保护模式,虽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解决了著作权归属的问题,但根据现有著作权法普遍规定,通过合同约定取得著作权不属于作品的原始取得,而是著作权的转让,且受制于传统著作权的约束,著作权中的人身权不得转让,上述问题是该模式下所存在的。
本文认为,应当借鉴“视为作者”制度认定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归属。美国和英国均有“视为作者”制度。美国版权保护强调作品财产权,在1909年创立“视为作者”制度。英国版权法认可创作者外的人可以成为“作者”,对事实作者和实际作者进行了区分。英国通过“法律拟制”手段解决了作者与著作权人不相一致的情况。可以大胆尝试采用法律拟制技术,参照美国版权法“视为作者”原则(“雇佣作品”原则)把没有实际参与创作的主体(人工智能的投资者、人工智能的管理者、人工智能的实际操控者等)视为人工智能作品的法律作者。
五、结语
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明确人工智能创作物是否为作品并对其在著作权法下予以保护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从“主客体统一认识论”和“人是目的”的角度来看,即使未来由弱人工智能时代到强人工智能时代转变,人工智能也只能看作是人类为达到一定目的所利用的客体,不能成为法律主体,作者必须是自然人以及被视为作者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在现有著作权法框架下,人工智能创作物作品应围绕“独创性”和“思想、情感的表达”的标准进行认定。著作权如何归属可参照“视为作者”制度,根据作品具体由设计者、使用者、所有者贡献了智力劳动,并通过人工智能的表达了创作意图,进而最终确定作者并享有著作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