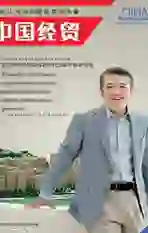中国经济学界的“十大馊点子”
2018-12-10李晓平
【摘 要】本文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开始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可能至少提供了“靓女先嫁”、“用卖掉好企业的钱改造破产企业”、“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某些腐败的存在,不是最好也属次优”、“‘下岗能治工人贵族病,能治政府腐败病”、“工资太高导致下岗增多”、“保8%要靠‘猛药、‘急药”、“加薪可刺激消费”、“经济增长不力的主要原因不是‘消费需求不足,而是因信贷萎缩导致的民间投资不足”、“中国经济增长只能主要靠投资拉动”这样“十大馊点子”。分析并批判这些“馊点子”,对于促进经济学的健康发展,应该会有帮助。
【关键词】“靓女先嫁”;腐败;下岗;“保8”;刺激消费
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经济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没有现成的理论或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在实践上常常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在理论上则是形成了形形色色学术观点的“百家争鸣”。其中一些学术观点,应该属于错误的观点,对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实践,可能是“馊点子”。分析并批判这样的“馊点子”,对于减轻这些“馊点子”对中国经济健康发展所可能会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克服中国经济学界可能存在的“轻浮草率”、“哗众取宠”的学风,促进经济学的健康发展,应该会有帮助。本文旨在对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改革中所曾出现过的一些“馊点子”进行选择、分析和批判,希望这一批判能对中国经济学界的进步发挥一点作用。
当然,错误的学术观点也不是毫无意义,在经济领域里提出“馊点子”的人对经济学的发展可能也会有实质性的帮助。这一点就像物理学里的牛顿力学,虽然本质上是一个错误的理论,但牛顿力学在物理学里的历史地位以及牛顿本人对物理学的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都是不可否认的。而人类的学术进步,也常常是通过对错误学术观点的批判来得以实现的。因此如同物理学里对牛顿力学的批判也应该被视为是对牛顿在物理学里所做贡献的致敬一样,本文的这些批判也不应被视为是对这些“馊点子”及其主要提出者们的“全盘否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应该被视为是对“馊点子”及其主要提出者们对经济学发展所做贡献的肯定。
中国人常常用“十大……”来归纳某类事物,因此本文对所选“馊点子”的數量也定为“十个”。另外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或“摆事实,讲道理”,因此有人可能会认为“实践”或“事实”应该是衡量“馊点子”的主要依据。但本文并不主要采用这种方式。因为由学术观点所派生出的政策主张在时间上可能会有“短期效应”或“长期效应”,在空间上可能会有“局部效应”或“整体效应”,因此选取不同时间范围内或不同空间范围内的“实践”或“事实”来“检验真理”,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所以本文主要是从“学理”即从该学术观点的逻辑基础上来分析该学术观点是否属于“馊点子”,而某些“实践”或“事实”只是有时会被用来作为判断某学术观点是否属于“馊点子”的补充依据。
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首先本文主要是根据一些媒体上的报道或报刊上的文章来选择“馊点子”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由于媒体上的报道或报刊上的文章有可能是对相关人士的真实观点的“误解”或“断章取义”,因此本文所列举的“馊点子”及其代表人物都只是“可能的”,未必符合真实情况;其次是某些“馊点子”的最早提出时间不太好考证,而且“馊点子”相互间“馊”的程度或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的大小也不太好比较,本文为行文方便,主要是根据所看到的相关媒体和报刊的出版时间来对这“十大馊点子”进行排名,因此这一排名不反映这些“馊点子”的“馊”的程度;最后是这些“馊点子”未必是“原创性学术观点”,而且相应的代表人物现在也有可能已转变看法,已不再持有其所对应的“馊点子”的观点,本文也不考证这些“馊点子”究竟是不是“原创性学术观点”以及这些“馊点子”的“原创性知识产权”分别应该属于谁,也不考虑相应的代表人物现在的观点如何,本文对一些“馊点子”注明出处或列出其“可能的”代表人物,只是想显示这一“馊点子”可能确实存在过。
本文认为,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改革开始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可能至少提供了这样“十大馊点子”。
一、“靓女先嫁”
“靓女先嫁”是指在在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中,应该对那些经济效益好的国有企业先进行私有化。“靓女先嫁”可能是首先出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中,因为“靓女易嫁,丑女难嫁”自然形成了“靓女先嫁”。“靓女先嫁”的“原创性知识产权”未必属于中国经济学界;或者在中国经济学界,是谁最先提出“靓女先嫁”的,现在也不是很容易就能考证出来。但“靓女先嫁”作为一种学术观点,在中国经济学界里确实存在过,这应该是毋庸质疑的事实。
“靓女先嫁”表面上的解释是:“靓女韶华易逝,等到成了丑女就会愁嫁,所以应该乘其还是靓女时赶紧先嫁出去”,隐含的意思则是“国有企业经营效益很难理想,乘着现在经营效益好赶紧转让出去,以后经营效益下来了再想转让出去就难了”。但这一观点的自身逻辑就有问题,如果“国有企业经营效益很难理想”,为何现在的这一国企会成为“靓女”?任何一个明智的个人或组织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一般都不会把自己“挣钱的买卖”先转让出去,不会“靓女先嫁”而更应该会争取“丑女先嫁”;从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对国企所有制改革试行“靓女先嫁”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国企所有制改革的“靓女先嫁”如果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行为可另当别论,但对国企所有制改革提倡“靓女先嫁”,绝对是一个“馊点子”。这一观点对因“优质国有资产被低价转让”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形成郎咸平所说的“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很可能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用卖掉好企业的钱改造破产企业”
这一观点的可能代表人物是原国家体改委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陆涌华。他认为“……大量差企业要获得中央投资和银行的贷款也很难”、“……拍卖好的国有企业,一个企业可卖得两个企业的钱,用这些钱,就可以改造四个濒临破产的企业,并将其改造成很好的企业,……又可以改造更多濒临破产的企业”、“广东就是用这个办法,仅用了两年半时间就使省内的不景气企业改造完成”。
这一观点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靓女先嫁”。其荒谬之处在于国有企业“差”的主要原因更可能是在于那些企业的经营方向和管理方式、管理水平等方面,而很可能主要不是因为“缺钱”的问题,否则“大量差(国有)企业”应该也不会难以获得融资;而且企业的规模也各不相同,因此如何能有“拍卖好的国有企业,一个企业可卖得两个企业的钱”?又如何能有“用这些钱,就可以改造四个濒临破产的企业”?这些话似乎很有“忽悠”的嫌疑。按照这种说法,一个好的国有企业的拍卖可以将四个濒临破产的国企改造成很好的企业,以及“广东……仅用了两年半时间就使省内的不景气企业改造完成”,这些话应该是说当时广东已没有了“不景气的国有企业”,而且“好的国有企业”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但当时广东省的实际情况显然不是那样的。
三、“某些腐败的存在,不是最好也属次优”
这一观点的可能代表性人物是北京大学的张维迎。张维迎认为,“如果腐败不能从体制上根治,那么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第二好的。所以反腐败力度要把握适当,如果力度把握得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张维迎这番话的问题:一是有“玩弄文字”之嫌,将“腐败”与“私人产品腐败”混淆在一起,为自己的这一观点可能需要的解释留有余地。二是轻率断言“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第二好的”,根据获得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决策学派代表人物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1916-2001)所提出的“有限理性学说”,人们在决策时常常找不到自己“最好的”决策,也找不到“次优、第二好的”决策,因此一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应该轻易不敢做出诸如“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第二好的”这样的断言,做出这样的断言往往是“不懂装懂”、“唬人”或“学术不严谨”的表现。第三也是因为“有限理性”,使得“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第二好的”这样的结论不具有“可否证性”,虽然可能是“错话”或“形同废话”,但别人也很难能明确证伪这一结论,只能对其无可奈何从而使其能长期“立于不败之地”发挥负面影响。第四“反腐败”应该也需要有一个摸索、学习的过程,应该很难一下子就“从体制上根治”或“力度要把握适当”,说“如果腐败不能从体制上根治,……,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可能会对“反腐败”产生威吓作用;或者按照张维迎的这一观点,是不是如果事先不能保证“腐败能从体制上根治”,或者“反腐败力度要把握适当”,那么对“腐败”就只能“听之任之”?张维迎的这番话客观上可能会对中国社会的“反腐败”产生负面影响。
四、“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
这一观点的可能代表人物是香港的张五常。张五常曾认为,“……国家要送资产给高干,或者说,以适当补偿他们因改革而受到的损失,‘诱导他们弃官从商,这样做,在道德上也许说不过去,但就经济效益而言,却是大为可取的。合乎经济原则的制度,是资产要有明确的权利界定,……”。
这一观点的荒谬性,一是张五常自己也已认识到的“在道德上也许说不过去”。二是对中国这样一个被认为民众有较强烈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心态的国度,这种做法会不会带来民众的强烈反对?会不会导致“民怨沸腾”、“官逼民反”?如果资产有了明确的权利界定就能“万事OK”,那么在过去长期实行私有制、“资产有明确界定”的中国,为何历史上会出现过多次对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的“农民起义”?三是如果真要实施,高干们“因改革而受到的损失”各自是多少?国家应该分别送多少资产给各位高干,才能“诱导”他们弃官从商?四是高干们得到资产补偿后是不是继续做官,那样他们会不会继续要求“以资产换特权”?或者这些高干们“弃官从商”后新的高干们会不会也要求“以资产换特权”?那样这种“以资产换特权”又何时是了?五是这些资产成为高干们的私人财产后被转移至境外,对中国又如何能“就经济效益而言,却是大为可取的”?
五、“工资太高导致下岗增多”
这一观点的可能代表人物是清华大学的胡鞍钢。胡鞍钢曾认为,“假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工资上升水平过快,吸纳就业能力就会下降,……,无法提高就业人口规模”。
胡鞍钢的这番话看上去似乎有道理,其实因为“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在现实世界中不成立,因此这番话反映的只是一种虚拟的情景,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中国社会“下岗增多”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政府对某些行业或企业的强制性“关停并转”,包括企业的经营方向与社会需求不匹配,包括企业领导层的“管理不善”,也包括员工自身的工作能力和工作表现等;但“工资太高”应该不是中国社会“下岗增多”的主要原因。如果确实是因为“工资太高导致下岗增多”,那么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平均工资相对更高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等是不是应该“下岗更多”?或者从企业界来看,平均薪酬更高的金融业、通讯业等是不是应该“下岗更多”?“工资太高导致下岗增多”的合理推论,就是“接受较低的工资就能上岗”,但现实生活中有些下岗人员连微薄收入的工作岗位都找不到。因此“工資太高导致下岗增多”不仅不符合实际情况,有损“下岗员工形象”,而且也不利于对这一问题的解决。
六、“‘下岗能治工人贵族病,能治政府腐败病”
这一观点的可能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学的周其仁,他曾认为,工人大规模下岗“这件事也有很多正面作用:一是能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二是能把几十年来所谓的城市工人贵族问题加以很好地解决”、“工人大规模下岗的第三个作用是:如果没有下岗职工的压力,政府也许对贪污、腐败等的治理不会像今天这样重视。”
根据中国人所熟悉的“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观点,任何事情都能找出“正反两个方面”,因此“下岗”也会是“有利有弊”的,像周其仁这样来为“工人大规模下岗”找“正面作用”也不是毫无道理。但问题是“辩证法的滥用”可以为任何荒谬透顶的观点都提供存在的理由;而决策要进行“利弊分析”,应该努力实现“利大于弊”,而不是“只要有正面作用,就可实行”。国有企业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多数社会成员都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以牺牲大量社会成员利益的“工人大规模下岗”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这种做法是否“利大于弊”?为什么差不多同时期进行“国有企业改革”,“俄罗斯、东欧各国都有相当比例的国有资产是通过职工持股形式私有化的”,而中国的大量下岗工人却只能是“今夜重又走进风雨”,只能用“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来进行阿Q式的自我安慰?另外就是罪犯也要根据犯罪的程度来适当量刑,某些工人可能会有“贵族病”,但是不是因为有了这种“贵族病”就应该“让工人大规模下岗”?至于说“‘下岗能治政府腐败病”,以实际情况来看,这种观点应该只是一种“凭空想象”。而且整个社会应该追求建立一种“不愿腐,不敢腐,不能腐”的“防腐败”机制,要尽力“将腐败扼杀在萌芽状态”,而不应满足于很可能会付出巨大社会成本的“腐败产生”之后的“反腐败”,用“工人大规模下岗”来治“政府腐败病”,即使有效,这种“反腐败”的社会成本又会不会太大?
七、“保8%要靠‘猛药、‘急药”
这一观点的可能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学的厉以宁。他曾认为,“今年只剩下7个月的时间了,要确保经济增长速度达到8%,必须找‘猛药、‘急药。”
厉以宁的此番话如果是由一位经济学初学者说出来,应该问题不大。但对于一位有声誉的经济学家而言,说此番话应该是非常“有失身份”的。用“猛药”、“急药”来拉动经济增长虽然在短时间内可能会有效,但副作用很大,从长期来看很可能是“饮鸩止渴”。真正有学识的经济学家更应该告诫政府对经济发展要慎用“猛药”、“急药”,而提倡用“猛药”、“急药”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一般都属于“目光短浅”之人。笔者认为,中国政府长时间连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在2008年时推出了可能会“贻笑万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与一些有声誉的经济学家倡导“保8%要靠‘猛药、‘急药”可能不无关系。
八、“经济增长不力的主要原因不是‘消费需求不足,而是因信贷萎缩导致的民间投资不足”
这一观点的可能代表人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樊纲。他曾认为,“……1998年经济增长仍不活跃的最主要原因,不是所谓的‘消费需求不足,而是因信贷萎缩导致的社会(民间)投资需求不足。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不增加,消费难以增加。”
这一观点的错误之处:一是收入只是影响消费的因素之一,但消费不是收入的函数,并不是收入增加了消费就一定会增加。二是从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来看,中国政府是在1998年由于当时出现的国际金融危机开始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下半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显著加快,全年增长19.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1%”,从这一点来看,说“1998年经济增长仍不活跃的最主要原因”是“社会(民间)投资需求不足”也难以让人信服。“消费不足”是近一二十年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久治不愈”的“顽疾”之一,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产品创新不够,现有产品给消费者所带来的边际效用较低;“刺激居民消费”的最有效手段是“科技”与“创新”。但在“科技”与“创新”这两个领域,经济学家基本都是“低能儿”,因此自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以来,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面对“消费疲软”时往往只会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或“积极的货币政策”之类的观点来彰显自身的存在价值。但在不改变商品总体生产状况(即不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或“放松信贷”,很可能只会导致“热钱泛滥”、多个产业产能过剩,无效供给(缺乏足够相应需求的供给)增多,大量商品滞销,而少数供给受“不可再生资源”所制约的商品如房地产、珠宝玉石、古玩、名人字画等的价格飞涨从而带动通货膨胀,整体经济呈现为“滞胀”的局面。
九、“加薪可刺激消费”
这一观点的可能代表人物是曾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综合规划局局长、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研究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的杨启先。他曾认为,“职工的工资提高了,就意味着城镇居民的购买能力增强了,不仅可以缓解现在产品普遍难卖的问题,而且可以拉动一些农产品以较高的价格出售,使农民的收入也得到增加”。
这一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没有认识到居民消费不仅受其购买力所影响,而且受其购买意愿所影响,“城镇居民的购买能力增强了”,不是一定能够“缓解现在产品普遍难卖的问题”,因为消费者对其“不想买”的商品,即使“有钱”也未必会购买。刺激居民消费的更有效手段,应该是全社会的大多数企业都能够积极利用“科技”和“创新”持续不断地生产出越来越多的有吸引力的商品,而不是“加薪”。在不改变商品总体状况的前提下“增加居民收入”,更可能会出现的是“一方面物价上涨,另一方面产品难卖”的“滞胀”的情况。
十、“中国经济增长只能主要靠投资拉动”
这一观点的可能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学的林毅夫。2013年4月27日,林毅夫在接受搜狐金融中心独家提问时认为,“……一旦舍弃投资转为消费,中国将很快陷入危机。当前中国基础设施方面仍有待完善,将成为下一个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主力”、“投資空间方面,……内城的交通中地铁拥挤、城市拥挤、道路拥挤,可改造的地方还有很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一是必须要靠技术创新,二是必须要把资源从低附加价值的产业不断转向更高附加值的产业。这两点都必须以投资作为载体。……财政政策的导向、想法相对比较能够掌控,而货币政策的流向很难掌控。在投资的带动下,工资水平将随着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自然会增长”。
林毅夫的此番话至少有这样一些问题:一是“一旦舍弃投资转为消费,中国将很快陷入危机”的依据何在?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要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人们生活质量提升的内容之一就是人们的消费增长,“多消费”才能“多生产”,才能拉动“投资”,没有“消费”或不对应于“消费”的“投资”就是浪费,也是很难持续的;试想如果人们都“不消费”或“少消费”,那样的“投资”还有实际意义吗?还能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吗?二是基础设施建设应该也不是“多多益善”,有媒体报道“从单条线路看,目前中国大陆除北京地铁4号线、北京地铁机场线、上海地铁1号线等个别线路外,几乎全部亏损;从路网整体看,所有城市的轨道交通网络都是亏损的”,因此这种连年亏损的基础设施建设会成为政府长期的财政负担,最终很可能逼迫政府通过“增发货币”从而以通货膨胀的方式将这些亏损分摊到民众头上,所以对一些基础设施是不是也要分析究竟是否值得投资建设?三是由政府掌控的财政政策如何一定能保证实现“把资源从低附加价值的产业不断转向更高附加值的产业”?林毅夫的这些观点有没有“高估了政府的德行”?四是如果是导致了“无效供给”的“无效投资”,又如何能实现“在投资的带动下,工资水平将随着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自然会增长”?
参考文献:
[1]1995年5月11日《上海证券报》.
[2]《财经》第一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40页.
[3]《中国经济大论战第二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第268-269页.
[4]1997年7月15日《山西发展导报》.
[5]1997年7月25日《经济学消息报》.
[6]金雁,秦晖.十年沧桑.东方出版社, 2012年8月第1版,第30页.
[7]1998年6月23日《工人日报》.
[8]樊纲.“克服信贷萎缩与银行体系改革——1998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1999年展望”,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9]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1999年3月5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199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1998年工作回顾”.
[10]李晓平.“关于消费问题的一点研究”.财贸研究, 1995年第1期.
[11]杨启先.“加薪可刺激消费”.领导决策信息, 999年第27期.
[12]http://business.sohu.com/20130428/n374379819.shtml.
[13]http://www.sohu.com/a/119943184_465518.
[14]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c9c1b610102wrxp.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