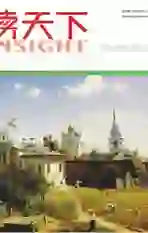托尼?莫里森小说中黑人女性与空间政治
2018-08-08宋健衡王禹
宋健衡 王禹
摘要:托尼·莫里森因其作品主题深刻,人物刻画丰富生动,语言优美感人,且饱含对黑人命运的关怀,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注意。进入20世纪,人们对空间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空间不再被视为单纯的故事背景和人类活动的“容器”,而是参与到小说内涵的构建中来。
关键词:空间政治;黑人女性;作品主题
目前国内评论者虽尝试从空间视角批评解读莫里森的小说,并在空间叙事研究和空间政治解读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在黑人女性与空间政治的关系方面的研究依然有所空缺。本文着力审视莫里森小说中的黑人女性在一定空间中的生存状况,进而探讨黑人女性身份构建与空间政治之间的关系。
一、 空间压制与女性的边缘化
亨利·列斐伏尔指出,空间不是简单的容器和人类活动的背景,而是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人类活动息息相关:人类活动生产出一定的空间,反过来,空间也会引导和限制人的行为活动,对人的个性、主体产生深远的影响。传统社会中,男性以成就事业为人生目标,谋求在社会上获取地位;与之相反,女性的角色是成为贤妻良母。因此,性别分工导致男性与女性空间形成二元对立。男性主要从事社会活动,占据社会空间,女性则受困于卧室、厨房、客厅这样狭窄、封闭的家庭私人空间。因此,在莫里森的小说中,房子对于男性和女性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对于黑人女性而言,房子不是避难所,而是禁锢她们的监狱和牢笼。她们生活在丈夫或父亲的掌控下,是他们的财产和女仆。她们在家庭空间中无权自由表达自己愿望,无权为自己的未来做出选择,她们是被边缘化的“他者”。莫里森小说中黑人女性的刻画向我们展现了空间政治中隐含的性别压迫。
《所罗门之歌》中奶娃的母亲露丝是一个典型的因家庭空间的压制束缚而失去自我的女性。童年的露丝自幼丧母,被父亲限制在家里的大房子里,接受着极其传统的教育。由于过着长期与外界隔绝的生活,露丝慢慢成长为一个温柔内向、逆来顺受的淑女。十六成年后,她依从父亲的安排,与商人麦肯结婚。但结婚对露丝来说,只不过是从一个牢笼走向另一个牢笼。麦肯家庭是典型的父权制社会的缩影:麦肯在家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掌管家庭大权,在家中说一不二,控制妻女的一切活动。他像露丝的父亲一样,把露丝控制在自己的大房子里,要求她操持家务、养育孩子,从不关心露丝的内心世界。对于这样的遭遇,露丝只会逆来顺受,被迫压抑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每日关心的依然是如何取悦自己的丈夫,如何引起他的注意。她的空间活动也主要局限在家庭中,在卧室里喂养孩子,在花园里种花、养金鱼,几乎与外界毫无交流。对于男性而言,宽敞的房子是其主权和成功的象征,但对女性而言,是压制天性、限制自由的监狱。就这样,露丝在男性空间的禁锢下,慢慢被异化成“他者”,失去了自我。
二、 空间重塑与身份构建
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人类活动能够改造空间,从而改变空间中隐含的思想意识形态,进而改变空间的影响,并在这个过程中寻求自我、构建自我。所以,女性可以通过破坏原有的压迫性空间来建构自己的空间,从而完成自己的身份构建。莫里森在不同小说中构建了多个女性空间——一个没有父亲、没有男人的家庭房屋。《秀拉》中,“木匠路七号”住着伊娃、汉娜、秀拉祖孙三代女性。伊娃婚后被丈夫抛弃,为抚养三个孩子,她以自残的方式获得赔偿。然后,她不断扩建房屋,指挥家人,招揽房客,成为自己房子空间的主人。通过扩建房屋,她招到更多房客,获得更多经济收入,进而稳固了自己在空间中的位置。她的空间实践拓展了生活空间,自己成为空间主宰。《宠儿》中的女性空间是由萨格斯、塞丝、丹芙和“宠儿”构成。萨格斯通过对房屋后门和厨房的改造,消除了屋内种族歧视的空间痕迹,改变女性的附属地位,帮助女性重塑自我。她的第一步是封闭房子的后门。种族歧视语境中,后门被赋予种族主义色彩,与正门形成高低贵贱式二元对立:前门专属于白人,是身份高贵的象征;后门属于黑人,是身份低贱的暗示。萨格斯堵上后门,所有黑人女性从正门出入,颠覆了种族主义社会里面的“黑白”二元对立,重构了黑人空间。她接着将厨房从室外移到室内,并对外开放,使厨房成为黑人聚集交流的地方。传统文化中,厨房是束缚压制女性的空间,在整个住宅中又总是偏于一隅,暗示着女性的附属地位。萨格斯改造厨房的空间位置,暗示对女性空间地位的提升,也暗含着对女性走出家庭、融入社会、获得社会地位的期许。不仅如此,萨格斯还在小镇外的一个密林深处创建一个布道空间——“林间空地”。在这个空间里,黑人女性们得到允许,可以自由哭泣、跳舞狂欢,她们被教育要热爱自己的肉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找回自我,拥有自我。但由于种族主义已经被部分黑人内化,萨格斯的空间实践以失败告终,萨格斯不得不在失望中悲愤交加离开人世。萨格斯、塞丝、丹芙和“宠儿”曾经居住的124号自此变成了一个冤魂肆虐的封闭空间,赛斯也被缠绕在种族主义创伤记忆中难以摆脱。最后,塞丝的女儿丹芙打破了这个封闭空间,她开始冲破封闭,向黑人社区寻求救助力量,最后,一些有所悔悟的黑人女性运用集体的力量驱赶走冤魂,使塞丝母女终于得到拯救。莫里森试图通过这个故事告诉读者,黑人女性可以通过自身的力量,或是借助社区的力量去改变空间政治,最后改变空间中隐含的政治话语,并最后获得女性的解放。
三、 结语
作为一名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莫里森小说一直致力于关心在种族主义和男权主义双重压迫下的黑人女性的生存状况。一方面,莫里森刻画了不少处于边缘化位置的黑人女性,她们受制于种族主义和男权思想的压迫,被围困在家庭这样狭窄有限的空间里,为白人主人提供劳役服务,或服从于自己生活范围内黑人男性的安排。另一方面,莫里森的小说也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女性屈服于种族主义和男权主义的压迫,种族主义空间和男权空间就会成为种族歧视和性别压迫的工具,但是如果黑人女性敢于積极改造家庭空间,创建新的社会空间,改变空间中隐含的政治意识形态,空间就能变成意识形态斗争和权利反抗的战场,黑人女性也可以在这个改造空间的过程中获得自我意识,重构自我身份。
参考文献:
[1]凯特·米利特,宋文伟,译.性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2]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宋健衡,王禹,安徽省安庆市,安庆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