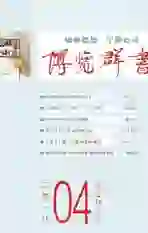评《宋家客厅》
2018-05-22徐可君
徐可君
《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
爱玲》(花城出版社2015 年版)是宋淇之子宋以朗围绕其父及其文人好友间生平交往的趣闻轶事,将信件作为史料,整理写成的一部传记体回忆录。身为中国早期现代戏剧理论家、藏书家宋春舫之子,作者宋以朗的父亲宋淇(笔名林以亮等)是个名副其实的文学“多面手”。宋淇笔耕不辍,涉猎甚广,一生致力于各种文艺事业,为人低调慷慨,他一生结交挚友无数,其中包括最耀眼的文坛巨擘,如钱锺书杨绛夫妇、傅雷一家、诗人吴兴华,以及不得不提的上海“天才”女作家张爱玲。
·壹·
《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一书呈现了特定时代背景下文人自身的选择,以及他们各自难以预测的命运走向,文字风格平淡而近自然,尽可能客观、公正地还原了上世纪30 年代至80 年代中国文坛一幅幅文人交往的生动画卷,时而博人一笑,时而引人唏嘘。与其说《宋家客厅》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传记,倒不如说它是一部颇具个人随笔性质的回忆录,颇有几分19 世纪享誉英国文坛的大散文家查尔斯·兰姆之“个人化散文”的韵味。然而,这部传记体回忆录却又不只是停留在个人随笔的层次上,此书探讨了诸多文学史上的谜团、公案,根据作者自身已掌握的资料,进行逻辑严谨的考据与大胆的猜测,因此深具学术价值。作者公开了许多钱、傅、吴、张与宋淇夫妇的信件,因此正如陈子善先生在序言里所写的:
以朗兄撰写《宋家客厅》,既充满感情,又不失客观公允。因而,不仅仅是张爱玲研究、钱锺书研究、傅雷研究、吴兴华研究,宋春舫、宋淇父子更不必说,乃至40 年代上海文学史以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这都会从这部引人入胜的《宋家客厅》中获益,而且我敢断言,不是一般的获益,而是深深的获益。
子善先生所言,精辟地概括了《宋家客厅》的价值。
宋淇之子宋以朗留学欧美,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又有较为年轻的心态,因此笔触不至于过于凝重稚拙,而是多了分恰到好处的含蓄与客观。宋以朗作为一个统计学博士,文学虽非其所长之终身志业,叙述人称虽为第一人称,却秉持“不随意评价,只公开资料,供读者判断的”的坚定立场。作者在该书中多次提到,宋淇与宋邝文美夫妇作为张爱玲下半生最要好的朋友,被张指定为其文学遗产的唯一继承人,而宋淇之子宋以朗在其父母逝世之后,则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张爱玲遗作的继承人和出版人。2009 年,宋以朗出版了张爱玲的遗作《小团圆》,立刻迎来轩然大波,网上的口诛笔伐、抗议出版接踵而至。这部被张爱玲生前嘱咐需“被销毁”的自传体小说却终于还是面世了。面对读者的负面回应,宋以朗的态度始终很明确,在该书的结尾他写道:
张爱玲在世时,出版商、朋友、经理人时常干预她的意愿,甚至替她做“不出版”的决定,以致有些作品到今天仍不见天日。我现在的责任就是把选择权归还读者,而不是给张爱玲的未刊文字做最后审判。
宋以朗的态度是无可挑剔的,出版作品并不意味着强迫读者阅读,但作为唯一拥有张爱玲遗作的继承人,如果不考虑读者的意见而私自销毁作品,无疑是更加不负责任的。作者的逻辑清晰、立场公正,不带个人偏见地澄清了许多误解,试图向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张爱玲”。
·贰·
作者自身与他笔下的人物之间的关系较为特殊,由于宋以朗与书中提到的文坛巨擘们并无直接的接触和来往,也非同时代人,使得作者能够以相对客观疏离,甚至可以说是以近乎學者的态度看待他父辈这一代的文人交往、文人逸事。作者撰写《宋家客厅》这部传记,主要的资料有三大来源:一是他自己的回忆,包括其父亲和亲戚告诉他的家庭往事。然而,这些回忆不免有真假掺杂的成分,就如同许多口述史一样。记忆的缝隙无处不在,个人历史建构的不可靠性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好在这些零星回忆并不占据书中大部分内容,而只是一笔带过。例如谈到作者对张爱玲本人的印象,他只用寥寥几百字作了个极为简短的叙述。第二个来源是已经刊行的文献,例如其父写宋淇的《毛姆与我的父亲》,提及他和张爱玲友谊的《私语张爱玲》等。这些文献虽然提供了许多细节,却只能表现笔下所写人物的一个侧面,不能窥得全貌,因此,宋以朗如何管中窥豹、整理资料、去伪存真,颇费一番周折,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考据功夫。最后一种来源,也是该书中最具研究价值、尚未受到学者充分重视的,则是宋家未刊行的手稿和书信。由于宋淇与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生前均为挚友,他们留下了上百封私人信件,仅张爱玲就有六百多封,而这些资料均在整理中,作者也会陆续斟酌刊发,颇值得期待。
传统的人物传记,几乎都套用人物从出生到死亡,一根线从头串到尾的直线形叙述模式,中间贯以诸多烦琐细节,读来难免沉闷。而宋以朗的这部传记,分开看都是一篇篇独立的散文,分开发表亦无大碍,具有其独立性与完整性。传记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应注重刻画人物性格、关注时代背景下的人物命运,而不是一味地堆砌史料,以“事件”为中心。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纪传史”的鼻祖,而太史公的长处亦在于对人物传神的描摹,第一次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表现出对“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重视。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史记》创造了一种“互见法。”所谓“互见法”的意思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 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所谓“为了使每部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就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
在这本史料无比丰富的《宋家客厅》中,宋以朗无疑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司马迁写《史记》的这种“人物互见法”。 书中涉及的活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人物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之间偶有交集,也曾互通有无,谈文论道,这些文坛人物之间,存在一个“看”与“互看”的问题,颇值得注意。文人的自我观照与文人间的相互观看,都构成了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史上一幅幅动人的画卷。该书的每一章节几乎都是围绕一个中心人物加以考察,由他展开叙述,例如开篇第一章写的是宋以朗的祖父宋春舫,中部分别分了三章分别写钱锺书、傅雷和吴兴华,最后卷下集中围绕张爱玲,这样以人物为中心的散文随笔文体,配之以报刊连载的形式,是非常引人入胜的。
在该书的第四章《钱锺书》中首次提到了宋淇与其周围文人朋友圈之间的交往缘起,这在之后写张爱玲的部分又从夏志清的角度复述了一遍。作者提到杨绛在《〈傅译传记五种〉代序》中这样写道:
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锺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
杨绛在2011 年百年诞辰时接受《文汇报》记者的采访,她回忆道:
我们身陷上海孤岛,心向抗战前线、大后方。当时凡是爱国的知识分子,都抱成团。如我们夫妇,陈西禾、傅雷、宋淇等,经常在生活书店或傅雷家相会,谈论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和前景。
(《坐在人生的边上——与杨绛的笔谈》)
在第七章《结识与交往》中,据夏志清回忆,从1942 年沪江大学毕业到赴台湾的三年里,“只参与过两个像样的文艺集会:1943 年秋天,我在宋淇兄嫂家里见到了钱锺书、杨绛夫妇和其他上海的文艺名流;1944 年夏天,我在沪江英文系低级班的同学家里见到了张爱玲”。可见,在当时,钱锺书、杨绛夫妇、傅雷一家、张爱玲之间都有过交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人圈”。那么,这些文人之间是如何“互看”的呢?
在第四章中,有这么一段关于钱锺书的文字,颇值得人咀嚼玩味:“钱锺书对张爱玲的看法如何?我们可以参考安迪的文章。作者提到了安迪去访问钱锺书时,问他对一些作家的看法,谈到了张爱玲,钱对她评价不高。但是1979 年钱锺书访美时,明明对学者水晶讲过,‘She is very good, 她非常好。为何对安迪又是另一套口吻呢?安迪当时也立刻质疑,钱锺书说他回答水晶的提问时的确曾夸过张爱玲,原因是‘不过是应酬,那人(指水晶)是捧张爱玲的,” 若我们细读这段文字,会发现作者寥寥数笔就写出了钱锺书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清高自傲,却又不失圆滑的性格特点。通过对这些细节的关注,宋以朗得出了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和其父亲宋淇不谋而合:“我起先有点担心,怕为钱惹祸,但钱如此出风头,即使有人怀恨,也不敢对他如何,何况钱表面上词锋犀利,内心颇工算计,颇知自保之道。”之后,当宋淇再次向钱锺书提起红学研究,提到张爱玲,甚至将她与余英时、杨绛的红学研究相提并论的时候,钱锺书不著一字,选择了视而不见的回避态度,也再没和宋淇讨论过红学研究的问题。宋以朗写至此处戛然而止,并未去费太多笔墨评价钱锺书的性格特点,而只是留给读者自行去判断。对于文人之间学术探讨的意见不同问题,宋以朗还是保持了客观中立的态度,仍然将选择权留给读者去判断,而并没有非常武断地下结论,但对于书中必须澄清的一些被歪曲的基本事实,该书也进行了多次澄清,这样以事实为依据的严谨态度让人感佩。
·叁·
该书不仅呈现出了中国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观照与互相观看,而且提供了一些观察中国文人难得的“西方视角”。1920 年,毛姆访问中国,他将自己在华的所见所闻写成58 篇短文,收录于游记《在中国屏风上》(On a Chinese Screen);其中有一篇是《一个戏剧工作者》(A Student of the Drama ),所讲的正是宋以朗的祖父宋春舫。习惯冷眼旁观的毛姆,对待东方文化的态度是比较不屑的。如果仔细阅读《一个戏剧工作者》這篇,会发现其中充斥着不少暗含挖苦性质的文字。例如文章开头,毛姆写道:“他显得有些腼腆。他说话的声音又高又尖,好像从来没有变过声,那些刺耳的声音给他的话语带来一种我也说不清的不真实的感情。”仅仅因为其“声音刺耳”,毛姆就武断地认为“他的话语有种不真实的感情”,这实在不能说不是一种偏见。毛姆笔下的宋春舫是个无趣、学识浅陋的人,他并不欣赏宋春舫的诚实和严谨。中国和西方的高级知识分子一个世纪以来互相之间的交流和观照,这其中必然产生许多的文化冲突,但西方对中国的理解与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厢情愿、主观色彩强烈的“西洋镜”,甚至带有明显的“傲慢与偏见”,归根结底,中西方文化仍然存在巨大的沟壑,这种隔膜的消除需要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努力。传记文学的真实性与虚构性究竟该如何把握?这个问题值得学者去深究。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发表于1966 年的《冷血》(In Cold Blood ) 可谓是美国非虚构小说的鼻祖,他开创了一种独特的纪实文学文体,将纪实与虚构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被公认是大众文化的里程碑。之后的西方传记文学作家尤其喜欢继承卡波特的非虚构小说体裁去撰写人物传记,例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库切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彼得堡的大师》,几乎可以说主要是作者的再创造,只是贯穿了人物的一些生平经历而已。宋以朗的这本《宋家客厅》本可以写得非常先锋,但作者并没有走得那么远,他没有一味跟随西方现当代文学“后现代主义”的时髦思潮,而是进行了大量的考据工作,对文献加以归类,这使得它成为了一本深具学术价值的严格意义上的传记文学作品,不失为一种成功。在该书的最后一章,宋以朗写道:(我)根本没什么第一手资料可说,只能自己花工夫查阅文献,再谨慎地陈述资料和对某些问题下判断。事实上,我连我祖父和外祖父也赶不上见一面。所以要用一句话概括整部书,最好就是蒙田的名言:“Que saisje ”(“我知道什么”)。由此可见,作者面对自己祖父辈的文人交往,已经没有多少直观的情感体验,必须通过严谨的考据、推断、猜测和论证,才能完成此书。美国历史学家贺萧(Gail. B.Hershatter)在其学术著作《危险的愉悦》(Dangerous Pleasures) 中提到历史学者的知识建构问题,她写道:“我们从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处学到的是关注一切范畴的不稳定性,关注语言的构造作用而不仅仅是其反映的功能。我已经对史料中无缝隙的叙述产生警惕,我本人更不会渴望创造出浑然一体、了无接缝的文章。我已经学会倾听历史记载中的静默无声,懂得了静默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失在。”事实上,文学领域的学者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处理记忆中的漏洞、史料中的缝隙,去伪存真,通过严密的考据和大胆的假设,耐心地拾起历史的碎片,将它们一片一片拼凑起来,还原出一幅相对真实,最好是鲜活动人的“文学画卷”?我想,宋以朗这本《宋家客厅》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极为成功的典范。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