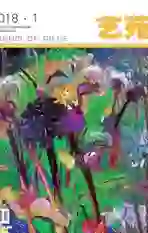朱宜剧作论
2018-04-20郭锦强
郭锦强

【摘要】 剧作家朱宜的《I Am A Moon》(《我是月亮》)、《Telemachus》(《特洛马克》)、《Holy Crab!》(《异乡记》)和《A deal》(《杂音》)主要从三个层面表达了剧作者对世界与人生的追问和思考:一、身体书写与欲望表达;二、移民文化身份的尴尬和冲突;三、个体确证存在意义时流露出的焦虑感。本文结合文本对这三个层面进行阐述,从而揭示朱宜剧作的独特内涵和价值。
【关键词】 朱宜;身体;移民;焦虑
[中图分类号]J82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剧作家朱宜的舞台剧作品《长生》、《I Am A Moon》(《我是月亮》)、《Telemachus》(《特洛马克》)、《Holy Crab!》(《异乡记》)和《A deal》(《杂音》)等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学者吕效平甚至对它们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它在中国话剧100多年的历史中是非常独特的,它让我在如此落后、如此闭塞、如此固步自封的中国大陆剧坛看到了未来剧本文体和戏剧思想变革的前景。”[1]83-84暂且不论这一评价是否言过其实,显而易见的是,朱宜剧作的观念、结构以及主题内涵都具有别样的风貌。
《我是月亮》《特洛马克》《异乡记》和《杂音》这几部剧作在一定程度记录了她在留学、工作和成长过程中一系列的辗转、成长与思索,它们通过一个个鲜活个体的际遇追问“我是谁”“我们为什么要去远方”这一类关乎人类生存本质的问题。可以看出,剧作的思考集中在“身体与欲望”“移民与文化身份”与“个体的存在价值”三个层面。具体而言,她在剧作中真实地展示纯粹的个体,以身体为中介言说欲望;在全球化语境中讲述移民的故事,折射社会中各种文化身份的冲突、尴尬与困境;同时,剧作蕴含个体确证存在意义过程中流露出的焦慮感。本文结合文本对这三个层面进行阐述,从而揭示朱宜剧作的独特内涵和价值。
一、身体:欲望的言说
面对“我是谁?”的疑问,朱宜的探寻从身体开始。她从身体引申到个体,赤裸裸地展示个体的情感、欲望和成长。
《我是月亮》中所有角色的性格,都是通过身体这一媒介展示的。剧作通过各种近乎病态的身体症候指证个体隐秘的欲望,刻画一个个拥有纯粹性格的角色。阿契尔指出:“性格描写是对人类本性的表现,是从一般对人类本性所共同认识、理解和接受的方面表现人类本性。”[2]314该剧通过塑造偏激和极端的性格表现人类的某些本性。它抛弃了传统的戏剧结构,由剧中角色的独白构筑起整部剧作。他们的共性在于对“身体”存有偏执乃至病态的感情:
亚裔男人出于对自己与异性身体的好奇,从12岁起就开始迷恋日本女优:“后来我看了其他的一些‘片子,深深叹服于这世界的千姿百态,以及身体和身体之间各种不可思议的差别,尤其在……柔韧性方面。”[3]90他无法真心爱上别的女孩,只能日复一日疯狂地以她为性幻想对象进行自慰,这种方式基于对异性身体的想象,最终又作用于自己的身体。
女大学生安吉拉则以另一种形式放纵肉体。她不加节制地进食,八岁时候开始发胖,变得比同龄人更矮更胖。小姨修长、美丽的身体使她感到羞辱。逛超市时,她敏感地注意到一个摔在地上有一个坑的苹果:“那只苹果就这么静静躺在那儿,我隐隐能听到它的尖叫。从那以后,它不再是一只完美的苹果了,伤口会加快它的腐烂,没有人会把它买回家,即使碰巧拿起来,看一眼,就会扔回去……它孤零零地埋在最底层的黑暗里继续腐烂,直到有一天没人能受得了它发出的恶臭。”[3]99在某种程度上,她的发胖与苹果的腐化相互指涉,苹果的腐烂象征身体的堕落与毁坏。
摇滚明星贾斯汀和同性恋人托尼热衷于在对方身体上留下吻痕:“他吻我的时候越来越失去控制。我的脖子,手臂上,肚子,胸前,大腿和脚……甚至脸上。你找不到一寸完好无痕的皮肤。”[3]101吻痕以伤害对方的身体为代价,代表存在和占有,恋人之间以这种狂热和极端的方式,宣泄彼间的破坏欲和占有欲。
女子梅的经历更是诡异。她受到大学教授性骚扰,打了对方几个耳光:“我发现手指沾上了他的鼻血。我盯着那血迹……那是温热的鲜红液体,就和我们所有人流的血一样。”[3]104体液作为教授身体的延伸作用于梅的身体,体液理论倾向于把体液过剩与性欲联系在一起,“过剩的热体液被扩大化时,人体自然产生愤怒情感或纵欲愿望。情欲就是血液过剩所致,是血液刺激内外感官而产生的反应”[4]7。教授的体液沾染到梅的手掌上,隐喻一种身体的占有,这对她的性格产生了难以言状的影响。
剧中其他角色也或多或少地存在顽疾:吉米体格健壮挺拔,但他从七岁开始就得了近视,身体的缺点使他无法既不摘眼镜又造型很酷地亲吻女孩。宇航员也声称自己从小戴上厚厚的眼镜被人嘲笑,同时,近视使他在赏月时看到某种幻象。
如果说《我是月亮》通过身体为中介描写性格,展示人类的某些本性。那么《特洛马克》以青年的身体为切入点,戏剧化地呈现个体成长过程中的特殊体验。这部以《奥德修》为母题进行改写的剧作从女性和儿童的视角出发,讲述奥德修之子特洛马克的寻父经历。副标题为“爸爸去哪儿了”,对子女而言,身体源自父母,小王子特洛马克的寻父之旅,正是对自己身体的求证。剧作一开场就有关于身体的隐喻:
求婚者 1: (扯下烤鸡的一根鸡腿,就着手吃了起来)童子鸡是我的最爱。什么都不用加,就那么好吃。真是鲜嫩,多汁……[5]114
在众多求婚者面前刚满20岁的特洛马克就像童子鸡,任由他们撕扯。于是,小王子毅然决定离家寻父,走进光怪陆离的成人世界。剧终,他带着自己刚出生的孩子回到家中,母亲毒死了众求婚者,他们不再承认载誉而归的父亲。
剧终的特洛马克与开场时童子鸡般柔弱、任人宰割的小王子判若两人。朱宜曾谈到:“一个青年的成长过程中会有一个既不属于孩童、也不属于成年人的阶段,这个阶段充满危险,还会有很多不正常的事情发生。特洛马克也是这样,他二十岁,既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没有能力保护家人、成为一家之主,但又也已经不能以再像一个儿童的身份一样韬光养晦养尊处优,他对求婚者已经构成了威胁,同时他自己也觉得再不长大是一种羞耻。”[6]143-144该剧以特洛马克独自出门远行的戏剧化形式描绘青年在成长过程体验的身体和心理的成长变化。
这两部剧中的角色一次又一次地观察、摆弄和放纵身体,以此宣泄极端的情感和欲望:同性或异性间性欲的宣泄、对食物的迷恋、情感的放纵、占有的满足感、对他者的逃避与恐惧、成长之中的荒诞体验……伊格尔顿将美学、身体与政治联系起来。他在《美学意识形态》申明:“对身体的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已经成为新近的激进思想所取得的最可宝贵的成就之一。”[7]7他通过美学这一中介将身体的观念与国家、阶级矛盾这些政治主题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看,身体的解放意味着个人的解放,剧作揭示出这些看似反常却可能实实在在地隐藏于人们内心的情感,将之赤裸裸地呈现在戏剧舞台上。
《我是月亮》中亚裔男人在大型企业工作、安吉拉是常春藤盟校数学系的研究生、贾斯汀是摇滚明星、梅是水果店老板,他们因为对身体的偏执,彼此产生奇妙的连接。朱宜通过病态的身体症候表现个体的隐秘情感和灵魂,书写真实的生命体验。《特洛马克》彻底颠覆了荷马史诗的叙事视角,从女性和儿童的视角出发,以荒诞的形式讲述青年的成长历程。有学者在评价《我是月亮》时指出:“现代以来,个体的身体及其感觉逐渐成为个体行为的重要依据,由之,身体性情的欠然和个体间的偶然遭遇成为真实的个体生活的重要部分,而戏剧也就开始重点关注个体身体性情的感觉、遭遇及其悖谬。”[8]65可以说,朱宜在戏剧中并没有直接回答“我是谁?”,但是正如剧名“我是月亮”,她通过身体书写和个体欲望的言说,关注个体身体性情的感觉,为观者展示人类本性的丰富性和可能性。《我是月亮》与《特洛马克》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们毫不掩饰地在舞台上展示人的欲望、灵魂和人的成长,也只有这类作品才能够真正地实现大陆戏剧最需要具有却又相当欠缺的品格,即董健先生坚持的“人在精神领域的对话和交流,以沟通人的生活体驗并帮助人养成健全的现代人格”[9]130。
二、移民:文化身份的尴尬
如果说《我是月亮》《特洛马克》询问的是“我是谁?”,那么《异乡记》和《杂音》将问题拓展到“我们为什么要去远方?”“我们为什么要回家?”这类关乎人的去处与归宿问题。
这两部剧作述说全球化进程中的移民故事。移民跨越国度,身为外来者与异乡人,需要面对不同国家和种族间意识形态、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的差异,这些对他们的身份认同产生冲击。全球化给社会和文化带来的变迁,在身份认同上体现为“人们在其中建构自己认同和理解其生活的民族构架已遭到严峻的挑战”[10]231。剧作者在全球化语境中描绘移民故事,记录了现实社会中各种文化身份的冲突、尴尬以及生存困境。
《异乡记》以荒诞的手法讲述中国女生怀抱无限憧憬踏入美国与哥哥团聚的故事,其中穿插各国移民的生活、诡异的历史场景、充满隐喻性质的物种入侵等戏剧性元素。剧作前言提问 “我们为什么要去远方?我们为什么要回家?”朱宜在采访中提及:“人类面对外界世界的向往,和对外来者的怀疑,这两种心态相撞,造成了历史上的无数次冲突,却也把我们在更深的层面连接在了一起。”[11]56因此,剧中不断地强调剧中角色之间身份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所带来的冲突,地域上:他们来自洪都拉斯、巴基斯坦、非洲、法国、北欧、俄国、中国以及美国本土;种族上:黑人、白人、黄种人。此外,剧中还有极具象征意味的角色——经过拟人化处理的来自世界各国的海产品:苏格兰三文鱼、挪威三文鱼、智利海鲈鱼、俄国鱼子酱、尼罗河鲈、孟加拉国明虾、中国大闸蟹。剧中写到大闸蟹作为“外来物种”入侵美国,给美国人带来了极大的恐慌,这种戏谑的表达方式极具象征意味。剧中有一段饱含诙谐与戏谑成分的对话:
徐夏 我不懂恐怖分子怎么会在时代广场放炸弹,会在这里的几乎都不是美国人啊。怎么会有人大老远跑来美国炸一群外国人?
道格(想了一下) 有道理。就像怎么会有中国人跑来美国来念中国史呢?
哈维(对小由) 一个法国人为什么要跑来美国扮另一个法国人?
游客一 墨西哥人为什么要跑来美国送墨西哥外卖?
……
游客二 一个巴基斯坦人为什么要跑来美国生下一个巴基斯坦人?
司机 不对,我们的孩子生下来会是美国人。”[12]95
到达美国后,此前建立的身份认同受到严峻挑战:怀抱对“美国梦”的向往,全球人民不约而同地以各种各样合法的或者非法的方式前往美国。他们试图寻求更深层次的心理认同,然而面对种族、文化、地域的差异,必须经历身份的尴尬和冲突,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说到底,之所以会产生冲突不断,主要还是在于这些角色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程度(identification),与他者对自我身份的肯认与否(recognition),彼此之间出现莫大的歧异。”[13]81自我身份包含着诸多因素,“在个人身份的形成过程中,多数个体也会获得团体的忠诚感和团体特征,比如宗教、性别、阶层、种族、性和民族性,这有助于使主体及其身份感具体化”[10]249。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造成移民们文化身份认同的错位。
这些错位的身份认同中,来自中国的兄妹徐林与徐夏的经历最具代表性。徐林根据中国人的葬礼习俗出售纸制“奢侈品”,这种在中国传统和普遍的习俗最终导致他锒铛入狱。徐林在美国延续中国传统的信仰、规范和价值观,这种在中国完全被接受和默认的行为却与美国的法律背道而驰。徐夏和美国本土白人道格相恋,对方却因为她没有拿到绿卡而心存芥蒂。道格对徐夏的感情建立在身份认同的基础之上,文化身份的差异也导致他们之间存在价值观分歧,这样的爱情无疑是脆弱的。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都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身份问题不仅仅困扰外来者,身为美国本土白人道格也一直不解自己从何处而来。他是一名机场海关警员,日常工作就是辨别他人的“身份”,荒诞之处在于他始终没有弄清楚自己的“身份”,他最后采取检测DNA的方式,却发现血缘组成成分极为复杂,甚至还有5%是的来源未知。从这个意义上,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成为全球化语境中所有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
《杂音》通过李先生和太太在美买房的经历牵扯出理想与信仰、意识形态与民族自尊心之间的碰撞与冲突,折射的问题依然是移民的身份认同带来的尴尬和困境。这对来自新兴中产阶级家庭的夫妇试图依靠一笔巨额拆迁款移民美国,却坚持不住在中国城:
李先生 不用了彼得。请带我们去看美国人住的地方。
彼得 刚才那里都是美国人。
李先生 我是说真正的美国人。
……
彼得 所以,你所谓真正的美国人是指多数族裔?(指向车外)你看!有个白人。看!那里还有一个!感觉好一点儿了吗?
李太太 那个是乞丐。[14]99
李先生是退休的国企高管,李太太曾是演员,他们的女儿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他们把自己定位在“精英阶层”。然而事实证明,他们在国内费尽心机、辛辛苦苦攒下的一百万美元,难以满足他们的特定需求。此外,一直引以为傲的女儿以欺骗的方式假扮成异见人士抹黑祖国,这令拥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夫妇尤其感到羞耻和痛心,最终与女儿断绝关系,凄凉地回国。
如果说,《我是月亮》中对个体的探索更多的是集中人类的情感方面,那么《异乡记》与《杂音》中,关注点转移到文化身份层面。“剧院就是一个民族当着它面前的群众思考问题的场所”[15]97,可以看出,朱宜剧本表现了全球化语境中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给移民们带来的巨大尴尬和困境,她也尝试展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个体在美国社会中各自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之间的碰撞与包容。
三、焦虑:存在价值的体认
问题并未止于此。无论是个体的欲望还是文化身份的尴尬,最终都指向个体的存在。朱宜剧作中贯穿着一种焦虑,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隐秘的理想,渴望确证自己的存在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看,剧作的精神内涵触及叩问人类生存意义的层面。
剧中角色的偏执和病态,实质上是个体确证存在意义过程中流露出的焦虑感。她试图让剧中角色超越意识形态和文化身份的掣肘,从内心出发探寻各自的存在价值。《我是月亮》中的宇航员幻想约会嫦娥,毅然决然地飞往月球,尽管其他人对他的这一想法不以为然:
宇航员的声音 在足足盯着那团黄色的光20分钟之后,我真的看到了月宫仙子的身影。[3]106
宇航员坚信自己看到了别人完全忽视的东西,前往月宫约会嫦娥成为自己的夙愿。他在剧终独白:
宇航员的声音 我没有在月亮上见到仙子,不过我的视力不太好,谁知道我错过了什么。不管怎样,等她看到我的宇宙飞船留下的这个坑洞,她会知道我曾经拜访过,她不是孤独的。这样我这一程便有了价值。[3]114
他强调“这样我这一程便有了价值”,这一程既意味他的月球之旅,又隐喻他的存在价值。奇妙之处在于所有人在此刻不约而同地产生一种奇怪的感应,他们同时抬起了头,侧耳聆听,仿佛有人在呼唤他们。这种感应正是建立在他们与宇航员的情感认同与共鸣上的,他们都像有伤痕的苹果、月球一样,时刻透露出一种焦虑,这使得在外人看起来他们古怪、偏执、病态,甚至是有一点疯癫。福柯《疯癫与文明》的启示在于:疯癫可能不是一种疾病,而只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些看似“疯癫”的个体是完全“正常”的,只是在不约而同地体认和践行自己的人生目标,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流露的焦虑而被人认为疯癫。
《异乡记》中每个角色也都有焦虑感。他们背井离乡不仅仅为了寻求美国公民身份,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践行心底不为人知的理想,这超越了政治与文化的范畴。徐氏兄妹们最后的告白令人动容:
徐夏 那时的家旁边就是铁轨,我每天晚上在那些绿皮火车的轰隆声中入睡。梦里总是遥远的世界……
徐林 不行。我属于这里,我的一切都在这里。家乡的人没法了解我的,他们不会懂我吃过的苦,做过的事。[12]122
他们渴望别人理解自己的梦想,正是不被理解导致了他们的痛苦和焦虑。《杂音》中的李苏同样为了实现自己的演员梦而不顾一切,她不愿意回国结婚生子成为“花瓶”,内心对舞台的爱是她的父母和著名编剧乔许都难以理解的:
李苏:可是一旦我上了台,一切都不一样了。我感到浑身炽热!好像死了很久,突然活过来了!就像是爱。如果你去想象爱,会觉得是挺好,但不值得用一切来交换。你以为你知道爱是什么感觉,因为之前也有爱过。但是你无法想象爱情。它每一次来,都好像能把你的心挖出来一样。这就是我对剧场的感觉。就是这种感觉每晚支撑我站在舞台上。[14]116
宇航员、徐氏兄妹、李苏等等,都不被外界所理解,表面的古怪源于发自内心对自由的向往和渴求。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西方荒诞派剧作家贝克特、尤奈斯库、热奈等人的剧作或多或少涉及人的孤独、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以种种怪异的形式表达出那些感到世界失去了中心解释和意义的个体心中的一种形而上的痛苦。马丁·艾思琳指出,这些戏剧表现“在一个由于宗教信仰崩溃而导致的人的确定性散失的世上人的处境本身的荒诞性”。[16]279如果说荒诞派戏剧中角色的体验代表了人生确定性的散失,那么朱宜剧作反映了寻求确定性过程中的焦虑。它们表明人的存在不仅仅是外部的受各种规训的存在,还是一种内向的、心灵的存在,外部的限制和内心的理想形成的冲突,使他们变得格外敏感,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在反抗焦虑,因此可能表现出离经叛道。然而,他们始终希望在这個世界中追寻真正属于自己的存在价值,这是对自由意志的肯定,是剧作者对生命意义的探求。
结 语
朱宜在她色彩斑斓的个人网站主页最显眼处留下一句话:“She Writes, in English, Chinese, and the language from her secret planet.”她的这些由英文写作又被翻译为中文的剧作展现出与众不同的风貌。她的剧作蕴含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男性与女性之间价值观的冲突与碰撞,在这种荒诞离奇的背后又不乏真实纯粹的生命体验:她从身体切入,对个体欲望进行大胆的言说,充分展示了人类本性的丰富性和可能性;她在全球化语境中思考移民面临的文化身份的尴尬、冲突与困境;此外,她的剧作中时时刻刻流露出的焦虑,是个体对自我存在价值的体认和对人类的生存意义追寻。可以肯定的是,她剧作所具有的别具一格的形式、理念和价值,为大陆戏剧创作提供了更多的方向和可能性。
参考文献:
[1]吕效平.我为什么爱《我是月亮》[J].戏剧与影视评论,2015(3).
[2](英)阿契尔.剧作法[M].吴钧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3]朱宜.我是月亮[J].戏剧与影视评论,2015(2).
[4]陶久胜.放血疗法与政体健康——体液理论中的莎士比亚罗马复仇剧[J].戏剧,2016 (6) .
[5]朱宜.特洛马克[J].花城,2017(4) .
[6]何平,朱宜.访谈:或许我们抄近道了[J].花城,2017(4) .
[7](英)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M].王杰,付德根,麦永雄,译.北京:中央编翻出版社,2013.
[8]杨鹏鑫.“我应该”式戏剧与“我是”式戏剧——从《我是月亮》的演出看中国当代主流戏剧的一个困境[J].戏剧艺术,2015(4) .
[9]胡星亮,江萌.在学术研究中坚守“五四”精神读三卷本《董健文集》有感[J].戏剧艺术,2017(3).
[10]周宪.文化研究关键词[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1]廖俊逞. Holy Crab! 异乡记:移民社会的异文化狂想[J].Par表演艺术杂志,2016.
[12]朱宜.异乡记 [J].戏剧与影视评论,2016(1).
[13]于善禄.一个关于美国移民历史、神话与寓言的剧本 ──读朱宜《异乡记》[J].戏剧与影视评论,2016(1).
[14]朱宜.杂音[J].戏剧与影视评论,2017(6).
[15](英)马丁·艾思林.戏剧剖析[M].罗婉华,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
[16](英)马丁·艾思林.荒诞派戏剧[M].华明,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