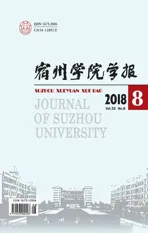尼 采 的 申 辩
2018-04-03刘一鸣何珺妍
刘一鸣,何珺妍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兰州,730030
20世纪,中国兴起了两次“尼采热”: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次是改革开放之后的80年代。这两个时期也被称为中国的两次启蒙。尼采对基督教的批评是众所周知的,五四新文化期间,知识分子就以“重估一切价值的”作为反对中国传统的口号,将尼采理解为鲁迅式的革命导师;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兴起,尼采又成为了自由派哲人的代表。现在看来,虽然中国的两次启蒙都与尼采有着紧密关联,但是国人对尼采的理解都是存在一定的问题[1]。随着新时期大批西方研究成果被引进中国,国内的尼采研究也日臻成熟,当中更是不乏从现象学、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角度解读尼采的卓有成效的努力[2]。然而,像尼采这样一位个性鲜明的哲人,争议与偏见似乎总是如影随形。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该如何重新认识尼采,笔者以为,第一步就是要剔除关于尼采的各种常识性偏见。
1 尼采的“等级制”
尼采的语言并不晦涩,然而总有语出惊人之效。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何为高尚”一章的开头开门见山地说道:“迄今为止,‘人’这个类型的每一次提高都是某个贵族社会的作品——而且永远都将如此:该社会信仰的人和人之间有一条等级顺序和价值差距的长长阶梯,并且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以奴隶制为必需。”[3]260诸如此类直接鼓吹“等级制”“奴隶制”的观点在尼采著作中屡见不鲜,应如何理解?尤其是在经过了启蒙以来民主、自由、平等思潮洗礼的今天,人们想要回到尼采的论域下重谈尼采就显得愈加困难。关于启蒙,很多自启蒙以来大力倡导、并为今人视为理所应当的观念在古典或者前现代时期往往并非如此。以启蒙推崇的“科学”概念为例,“科学”追求的是宇宙论意义上的确定无疑的知识,这与苏格拉底“自知自己无知”想要为知识确立一个界限的做法大相径庭,所以古典哲学家(以苏格拉底为例)往往追求过更好的生活,而并非现代科学那般试图宰治整个世界。
显然,尼采这里阐述的“等级顺序”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等级,而是侧重人有灵魂、人格上的差异等。尼采后期致力于“价值重估”的工作,《权力意志》的副标题就叫作“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而尼采强调的“等级制”正是“价值重估”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尼采眼中,整个西方现代文明都建立于基督教和柏拉图主义之上,理解了这一点,就自然而然地明白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就是要摆脱希伯来文明,重新返回到西方文明的源头,更确切地说,是返回到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古希腊文明中去。“价值重估”工作就是要把所有被基督教和柏拉图主义颠倒的价值重新颠倒回去,从而建立新的“等级制”。
伴随对尼采推崇等级制的批评,必然伴随尼采是一个“非道德主义者”的批评。然而,在尼采看来,西方的基督教道德传统是一种弱者规束强者的手段,哲人理应超拔于这种奴隶道德之上,这一点从尼采的另一部著作《善恶的彼岸》(又译作“超善恶”)的名称便不难看出。如果用奴隶道德规束强者,就是“对美德的滥用”[1]195。此类说法在中国古典著作中也有类似表述,比如,在庄子《天下篇》中就有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君子、百官、民七等次之分[4],“天人”“神人”“至人”“圣人”称“人”,“君子”“百官”“民”不称“人”,通常意义上的道德仅限于圣人以下的君子、百官、百姓的层次。如果用道德规束天人、神人、至人、圣人的话,就陷入尼采所说的“对美德的滥用”中。
尼采把基督教视为民众的柏拉图主义。尼采之所以称基督教为民众的柏拉图主义,是因为基督教中此岸与彼岸的对立恰恰是继承了柏拉图以降现象世界与超感性世界的对立,且认为超感性世界高于现象世界的传统。尼采因此对基督教乃至对柏拉图主义提出了诸多批评,并意图用“永恒轮回”的权力意志消弭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尽管如此,尼采却从未否定基督教作为“谎言”最基本的教化功能:民众得到心灵上的归宿和对于彼岸世界的崇拜(尼采本人当然拒斥所有在彼岸世界悬置一个“意义”的价值建构方式),哲人则践行着追求智慧的高尚生活方式而不必担心迫害,哲人与民众在基督教背景下并行不悖。然而,启蒙以来“现代理念”的发展彻底打破了柏拉图以降形成的形而上学传统,也打碎了民众的美梦。在“现代理念”统治下,思想的平等和自由颠覆了古希腊时期形成的高贵哲人传统,而这是尼采所最不愿看到的“末人”的时代。随着查拉图斯特拉下山时向人们宣称“上帝死了”,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已经来临,而这正是尼采“重估一切价值”、建立新的“等级制”的起点。当然,这里的“上帝”并非特指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一神论人格神,而是代表传统形而上学所追求的一切超感性或超验世界,无论理念、上帝还是本体;与此相对,“上帝死了”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自行废黜”[5]。
对于现代性最终只能走向虚无主义的反省,尼采分析的很准确,“真正与苦难相抵忤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苦难的无意义”[3]383。因此,“人类与其无所意愿,宁愿意愿虚无”[3]508。海德格尔那里称之为“形而上学之天命”的东西,在尼采这里则是指生命主体基于强力意志的主体性精神超出自身之外,成为查拉图斯特拉式的超人,以反抗柏拉图式的、基督教道德的世界解释及其所有或隐或现的虚无主义的变式[6]。
2 尼采眼中的女人
尼采对女性的贬低早已是老生常谈了,出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那句“你到女人那里去?别忘带你的鞭子”[7],更是成为尼采歧视女性的“铁证”。众所周知,尼采除了是一位哲人,还是一位语言大师。因此,在阅读尼采作品时,尤其是像《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样充斥着各色晦涩难解意象的作品,更应该区分尼采何时是在日常意义上表达,何时又是在假借意象进行言说。而那些试图将尼采对女性的“不友好”追溯至其个人品质的缺失,乃至恋爱经历的失败,就更显得无知可爱了!
以下将引用《善恶的彼岸》中的部分段落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女人想要自立,为此就开始了男人对‘自在女人’的启蒙,这属于欧洲普遍的丑陋化进程中最恶劣的步骤。”[3]214“幸运的是,迄今为止,启蒙都是男人的事情和男人的禀赋。”[3]215“我们男人的心愿是,女人不要再继续通过启蒙让自己出丑:这便是男人对女人的照顾,男人对女人的爱护。”[3]215这与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绝大部分的人(其中包括全部女性)都把步入成熟状态(启蒙)认为除了是非常艰辛而外并且还是非常危险的”[8]的论调如出一辙。在尼采看来,女性显然是不具备接受启蒙能力的,这恐怕会招致女权主义者的攻击,并引用历史上大批女性楷模进行反驳。但问题是,尼采这里是有意贬低女性吗?是的,尼采对女性的贬低显然是有意而为之,对此无须作过多辩解。对这一“偏见”的批判性工作就交给女权主义者们来做,不属于本篇文章的讨论范围。但问题是,尼采所言仅针对女性吗?或者进一步说,尼采只是为了贬低而贬低吗?尼采对女性的贬低在其哲学中有更深层次的根源吗?应该这样说,尼采对女性一贯的贬低态度是其“等级制”设计的一部分,正如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对奴隶道德(或称基督教道德、教士道德、群氓道德)与贵族道德的区分一样,女性对于男性权力的觊觎和试图取而代之的渴望在尼采看来无异于通过以“善”“恶”代替“好”“坏”标准所实现的弱者对强者的僭越。简言之,尼采对女性妄图接受启蒙的批评是与其政治哲学中高贵者与群氓的区分息息相关的。在尼采看来,所谓的男女平等,无异于粗糙地将形形色色的人一概而论,这是对强者最大的不公。在这样一个强调男女乃至众生皆平等的时代,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主义精神恐怕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偶尔见到了。
“错误地领会‘男人和女人’的基本问题,否认其中深不见底的对抗和一种永恒敌对的紧张的必然性,梦想在这里也许有相同的权利、相同的教育、相同的权利主张和义务:这些是头脑浅薄的典型标志。”[3]219-220
尼采连用三个“相同”修饰“权利”“教育”“权利主张和义务”,所针对的是所有力图弥合男女之间差别的“浅薄”行为。尼采继续说:“……上述所有这一切如果不是意味着女性本能的销蚀,一种去女性化,还能意味着什么呢……人们几乎到处都在用音乐中最病态和最危险的种类(我们德意志新音乐)来腐蚀她的神经,使她成天歇斯底里,而不能胜任她最初的天职——就是生育最强有力的孩子。”[3]222在尼采看来,女性的反抗,即所谓的“女性本能的销蚀”和“去女性化”,是一种受“有够白痴的女性之友和败坏女性者”和“性别为男的博学的驴子”蛊惑的结果。因为让女性承担了本不属于女性职责范围内的职责,才是对女性最大的不敬,所以并非一味贬低女性,尼采侧重强调的是男女之间的各司其职,同时对女性在启蒙时代中所处的尴尬境地表示了同情。如此看来,尼采既不是那个疯言疯语、随意谩骂诋毁女性的疯子哲学家,也不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女性视为城邦公有财产那样冷漠无情,在这里,他对现代女性的关照和体贴反倒使人们看到尼采人文关怀的另一面。
尼采对女性的“贬低”并非针对女性本身,而是针对那些藏在女性背后鼓吹男女平等之现代理念的阴谋家。尼采之所以对“平等”概念如此深恶痛绝,是基于其生命哲学(意志哲学)的根本目标,那就是:生命意志的丰富、提高和强化。由此目标出发形成的对高贵生命的强调,使他反对一切弱化生命的道德化倾向,从而走向启蒙运动的对立面[9]。
3 尼采与“反犹主义者”
尼采无法预见到在自己死后仅仅几十年的时间里,德意志政坛将有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将自己与他联系起来,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一个自以为继承了尼采式理想的政治狂人。这位政治狂人从尼采的只言片语中汲取着养分,并且毫不避讳地在公开场合表达对尼采的崇拜。从这个意义上讲,施特劳斯将尼采作为第三次现代性浪潮的开端,并且说“第三次浪潮的政治含义已经被证实为法西斯主义”[10]167是合乎事实的。
“金发的雅利安人”对“犹太式价值重构”等言论在尼采文本中比比皆是。人们不禁要问,尼采抑或是在修辞上与纳粹种族主义、反犹主义主张极为接近的尼采哲学是否要为纳粹运动这一现代性事件负责?这一问题的答案可以参见近年来争议颇多的海德格尔《黑皮书》事件。《黑皮书》(又名《深思》)三卷本自出版以来,关于其中出现的海德格尔的反犹言论就一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关于海德格尔反犹主张的批评始终未能盖棺定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部分人坚持海德格尔所说与“反犹”无关,他主要谈论的是种族问题。如果说海德格尔对犹太人和种族原则有所批判的话,那这种批判也弱于对纳粹、种族原则的无限运用、种族思维的绝对化、“去种族化”或种族主义等的批判[11]。关于对尼采的类似批判,亦可作上述理解。即是说,海德格尔文本中的语言只有置于形而上学语境下思考才有价值,一味追问政治立场或以善恶之名对其进行谴责是没有出路的。经历了纳粹事件并直接参与其中的海德格尔尚且如此,尼采就能够为纳粹运动负责了吗?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关于尼采“反犹”的讨论主要是出自《权力意志》,然而此书的编排顺序和结构都是尼采的妹妹确定的。她有意将尼采批评犹太人和犹太教的言论集中起来,以便人们误以为尼采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反犹主义者。然而,在《敌基督》中,尼采更是直接批评了反犹主义者的无知和浅薄。
诚然,尼采文字的张力对于政治狂飙运动中的领袖再合适不过了。希特勒或许读过尼采的文本(或许根本没有),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可以肯定的是,希特勒既不懂哲学也不懂尼采。他所做的工作只是将尼采哲学中的个别概念或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地作为支撑自己政治实践的理论工具,以“六经注我”的方式使尼采思想为己所用,在将尼采塑造为时代先知和德意志精神导师的同时,也将自己塑造为德意志复兴的希望。关于希特勒对尼采自作多情式的滥用,施特劳斯的观点倒十分中肯:“从某种意义上看,对尼采的任何政治利用都是对其教诲的滥用。不过,他所说的还是被政治人解读了,并带给他们灵感。他对法西斯主义所负责任之少,正如卢梭之于雅各宾主义。然而这也意味着,他要对法西斯主义负责,其分量之多,一如卢梭之于雅各宾主义。”[10]166-167
讽刺的是,希特勒以尼采哲学中高贵道德的继承者自居,但他的政治实践和个人的精神气质无时无刻不在践行着奴隶道德之要求,即从仇恨本能出发,将一切异己者赶尽杀绝。在这个意义上,希特勒并非尼采哲学意义上的“超人”或继承尼采衣钵的政治实践家,而是深谙教士伦理并将之发扬光大的阴谋者。尼采确实没有准确预见到纳粹运动的出现,但是对于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希特勒式人物,尼采比任何一位思想家都理解得更为深刻。
4 结语
通过上述对尼采文本的梳理,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味追问尼采言辞中细枝末节的部分,并对其有违“常识”的部分横加指责,对人们走进尼采思想本身非但没有帮助反而徒增障碍。与康德环环相扣的概念逻辑推演表现出的严密准确和黑格尔构建出的哲学体系的宏大完整不同,尼采本人拒斥哲学日益学科化、分工化、精细化的趋势。接受过严格古典学训练的尼采,在完成《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更是直言这是一部为所有人而又不为任何人的著作,由此能够看出尼采对于自身的写作风格是颇为得意的。然而,尼采的这种风格恰恰为偏见提供了可能,许多人正是利用这一点,对尼采口诛笔伐,殊不知尼采这样做恰恰是要将这些人拒之门外。对尼采而言,哲学活动是一种自我表达,哲人因此适宜以个体身份立于舞台中央,为万众所瞩目,而并非柏拉图所认为的哲学到来的智慧不仅仅属于特定时空的某个个体。尼采选择将自己超乎常人的洞见以别具一格的写作方式隐遁起来,只有少数被选择的人才能理解。人们应该尊重和原谅尼采的这种选择,因为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哲学总只是极个别人的直接事务。”[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