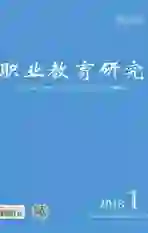学生主体与高职校企合作稳定性的关系研究
2018-01-27吴冰
摘要:以专用技能人力资本为视角,探讨了学生作为主体在高职校企合作中的作用影响。基于800份问卷调查的回归分析发现,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可在不同程度上提高学生个体专用技能人力资本水平,但个体专用技能的提高未必能为企业换回稳定的雇佣(稳定就业或稳定实习);建立学生个体、企业与院校三方可信的契约承诺与违约机制可以避免专用技能人力资本形成后个体技能所有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要保障校企合作稳定性,要将学生个体纳入校企合作签约主体,建立学生主体、合作院校、合作企业三方的可信契约承诺与违约机制。
关键词:学生个体;高职院校;校企合作;专用技能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8)01-0075-07
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一个热点。但该领域的国内研究大多就院校与企业两个合作主体进行分析。而在现实的校企合作过程中,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很多顶岗实习生并未在院校签约的合作企业中稳定实习;企业与高职院校签约培养的订单合作生也并未都到合作企业就业,或即便被合作企业聘用因离职率高而最终导致校企合作失败的案例也屡见不鲜。那么,如何解释在控制住学校、企业和专业因素的前提下,学生个体在校企合作中的作用?本文拟从专用人力资本的视角来讨论学生个体因素对校企合作的影响。
高职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涉及多个环节和多种合作行为,但目前对我国高职院校学生而言,其个体能够作为主体直接参与的校企合作主要体现在(合作企业)顶岗实习、(合作企业)订单培养、(合作企业)就业三方面。因此,本研究将聚焦于学生个体作为主体参与合作实习、合作订单培养与合作就业环节中的作用影响。
一、理论分析框架
国内研究发现,职业院校学生毕业后形成的是专用人力资本,所谓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其实质是企业投资于人力资本从而实现人力资本专用化的过程[1]。而人力资本区别于物质资本的最大特征在于其个体依附性和个体产权私有,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往往具有滞后性和风险性。人力资本领域的研究发现,企业在对个体技能进行投资前,首先要考虑的是人力资本的可雇佣性以及雇佣的稳定性。本研究基于如下逻辑起点:如将企业与高职院校的合作看作企业对技能人力资本的投资,当学生个体能成为校企合作参与主体的时候,学生个体人力资本特征中的“可雇佣性”和“雇佣稳定性”对校企合作有何影响。
(一)个体“可雇佣性”与校企合作
由于通用技能人力资本往往可以从人才市场中购得,企业与高职院校的合作动力主要来自专用技能人力资本的需求,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的实质是企业对学生个体“技能人力资本专用化”投资的过程[2]。凝结于个体的专用人力资本一般包括职业专用、企业专用和行业专用人力资本。由于学生个体在校企合作活动中所形成的技能人力资本专用性程度不同,其所获取的(职业、企业、行业)人力资本专用性程度越强,个体的“可雇佣性”也就越强,也就越容易与企业形成“锁定关系”。
(二)个体“雇佣稳定性”与校企合作
根据本领域既有研究,高职与企业间的合作可以看作企业与院校在相互独立条件下,基于技能人力资本的契约关系。一个完整的(含有订单培养和顶岗实习等环节)校企合作关系一般至少持续如下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事前阶段),校企双方签订合作合约后形成了所谓不完全的“或有雇佣契约”(时期0);随后,企业对交易对象——订单培养学生和所在院校进行师资、教学设备等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时期1);在第二个阶段(事后阶段),学生接受在校理论学习后(合作双方的专用化投资)参加合作企业的顶岗实习(时期2);如期毕业之后,学生个体与企业双方进行正式谈判、正式雇佣并稳定工作(时期3),其时序模型如图1所示[3]。
显然,作为单边的交易行为,企业与学校合作存在如下投资风险。
1.不对称信息造成签约前的机会主义行为
由于校方往往比企业(未来的雇主)更了解学生的自身能力。而个体技能的代理方——院校为了提高校企合作水平、增加学生就业率可能对潜在的雇主说假话——夸大对学生个体的控制力,从而产生逆向选择。
2.不对称信息和专用性投资造成签约后的机会主义行为
企业一旦签订与院校的合作培养协议,通过对院校师资、设备、技术等形式的投入,从而将原本技术不熟练的在校生训练为具有专用技能的熟练工人。但在没有强有力的外部监管和惩罚违约行为机制的情况下,任何一方——企业、学校、学生都无法确认对方会始终履行合同。在没有违约机制的情况下,学生在顶岗实习中可能退化为企业剥削廉价劳动力的工具;而在没有赔偿机制的情况下,那些从企业专用投资中受益的订单培养学生则可能竭力摆脱束缚,以期进入劳动力市场,从而凭借他们在企业中获得的专用技能获取更高的工资。
所以,企业唯有与学生个体(作为第三方)达成某种“可信承诺关系”提高其“雇佣稳定性”,才能避免企业投资风险,维护校企合作稳定性[4]。
二、研究假设与设计
(一)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设
根据前述分析,本文构建出学生个体人力资本(可雇佣性)、可信承诺(雇佣稳定性)与校企合作三者之间的关系:校企合作能提高学生个体專用人力资本(学生个体的可雇佣性),学生个体的可雇佣性与雇佣稳定性又可进一步促进校企合作稳定性(见图2)。
在上述理论框架下,笔者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H1):校企合作可提高学生个体的专用技能人力资本水平;研究假设2(H2):在校企合作中所形成的个体专用技能人力资本有助于锁定与企业的关系,从而提高校企合作稳定性;研究假设3(H3):学生个体的可信承诺(可雇佣性)有助于校企合作稳定性。
(二)变量设计与测量
根据上述假设,本研究就涉及的主要变量做如下处理。endprint
1.职业人力资本专用程度的测量
国外学者曾通过对学生顶岗实习生的测量来衡量校企合作成效;国内学者范凯凯将专业对口变量作为“技能人力资本专用性的重要指标”[5];米勒和沃尔克、埃若伯什巴尼、钟宇平也发现“学用对口”与收入密切相关。以上述研究为基础,本研究用“顶岗实习与专业匹配程度”(即学用对口程度)来衡量学生顶岗实习岗位的职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特征变量。
2.企业人力资本专用程度的测量
国内外研究发现,员工掌握企业专用知识、技能所需时间越长,其企业人力资本专用程度越大;而企业专用人力资本程度与员工流动性(转换工作的概率)呈负相关。所以,本研究以实习生熟悉专用知识所需时间和实习岗位流动率来衡量实习生所获的企业专用人力资本。
3.行业人力资本专用程度的测量
由于同一专业的合作企业往往同属相同或相近行业。根据既有研究,行业人力资本专用程度的测量用(合作实习企业)“是否制造业”和“是否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两个指标来衡量所在行业人力资本专用程度。
4.学生个体可信承诺的测量
学生个体的“可信承诺”主要是指具有法律约束意义的契约[6],本研究采用学生“是否为合作签约方”来作为衡量该变量的指标。
5.校企合作稳定性的测量
本研究采用稳定就业(在合作企业签订就业协议)和稳定实习(稳定的实习时间与收入)两个指标来衡量校企合作稳定性。
在上述变量处理的基礎上,将本研究假设与指标汇总见表1。
(三)样本数据来源
本研究总计发放实习生调查问卷1 000份,回收的800份有效问卷中,总计涉及30个高职院校、106个专业和728个合作实习企业。
三、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校企合作对个体技能人力资本专用性的影响
本节首先验证假设1,就合作企业在顶岗实习环节对学生个体人力资本专用性的影响进行分析。之所以选择顶岗实习环节进行分析,是因为学生在校理论学习期间接受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各环节中尽管也获取了某种专用人力资本,但(在同一专业或班级中)不同学生个体获得的专用人力资本差异较小。而在顶岗实习阶段,不同学生在不同的合作企业顶岗实习,有的实习学生要更换多个实习企业和岗位直至稳定就业。因此,本研究首先引入校企合作企业特征变量,建立如下实证模型,试图先找到不同企业对于学生个体技能专用人力资本的影响。
模型1:
Y1= α+βX1+δX+ε(式1)
模型2:
Y2= α+βX1+δX+ε(式2)
两个模型中的因变量都是衡量学生个体掌握技能人力资本专用性程度的变量。其中,式1中的Y1为学生职业人力资本专用性变量(用“实习岗位和所学专业间的匹配度”来衡量);在式2中,Y2为学生企业人力资本专用性变量(用“掌握企业专用技能所需的实习时间”来衡量)。式1与式2中的X1为“是否在校企合作企业实习”的虚拟变量(“是”取1值;“否”取0值);X为如下一组变量:校企合作企业实习时间和校企合作企业特征变量,如企业行业门类“是否制造业”的虚拟变量(“是”取1值;“否”取0值)、企业规模(分为“大型、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历史长短的虚拟变量(“5年及5年以上”取1值;“5年以下”取0值)。
式1与式2的回归结果(见下页表2)发现,(是否)在校企合作企业中顶岗实习对学生职业专用人力资本的形成效果显著;而在校企合作企业实习时间长短对企业人力资本专用性指标作用显著,即实习时间越长,所获取的企业专用人力资本知识越多;在企业特征变量中,新建企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或制造业企业对于(职业和企业)专用人力资本形成更为有利。因此,在校企合作企业中实习能不同程度提高学生个体人力资本专用性,但个体所获取技能专用性的程度和企业本身人力资本存量(如企业所属行业、企业历史等特征)密切相关。这一回归结果和前期初步调研结果相吻合:学生到合作企业顶岗实习后总体上认为“能够学到东西”,但不同实习生在不同企业、不同岗位的顶岗实习收获差异明显。
以上研究验证了假设1A、1B,即以顶岗实习为例,校企合作可以显著提高学生个体的专用技能人力资本。随之引发的一个问题是,学生个体在校企合作中所获取的职业专用人力资本能否用实习收入来衡量(假设1C)?学生个体在校企合作活动中所获取的企业专用人力资本大小能否用(实习)岗位流动性来衡量(假设1D)?
本研究将学生个体的“顶岗实习收入”作为因变量建立模型3,试图找到个体专用人力资本对于学生实习收入的影响:
模型3:
Y3=α+βX1+δX+ε(式3)
式3中的Y3为顶岗实习生实习收入变量(月工资取对数);X1为“是否在校企合作企业实习”的虚拟变量;X为一组反映实习生个体人力资本特征变量,具体包括了反映职业人力资本专用性指标(用“实习岗位与所学专业匹配度”衡量)和企业人力资本专用性程度的指标(用“掌握企业专用知识技能所需时间”衡量);同时,将通用人力资本(实习生入学时的高考分数)作为参照比较。
然后建立模型4,试图找到企业(岗位)专用人力资本对实习岗位流动性的影响:
Y4=α+βX1+δX+ε(式4)
式4中的Y4为(实习)岗位流动性因变量;X1为“是否在校企合作企业实习”的虚拟变量;X为一组个体专用人力资本特征变量,包括反映个体掌握职业专用人力资本和企业专用人力资本程度的指标(岗位/专业匹配度和企业专用技能熟悉时间)。
从个体专用人力资本对学生实习收入的回归结果发现(见表3),和通用人力资本相比较,学生个体在校企合作企业中所获取的(职业和企业)专用人力资本对其实习收入都不显著;学生在合作企业中实习反而比通过个人、家庭等其他渠道找到的实习岗位收入低。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校企合作企业顶岗实习的学生实习工资是校企之间的“集体协议工资”,这一工资低于学生通过家庭或市场渠道获取的实习岗位工资。所以,表3回归结果未能验证假设1C。endprint
而从学生个体专用人力资本对实习岗位流动率的回归结果发现(见表4),个体掌握的企业专用人力资本、职业专用人力资本对实习岗位流动率指标的影响都呈现显著负相关(假设1~D得以成立);但与学生和家庭自行寻找的实习单位相对照,校企合作企业的实习岗位流动性显著偏高。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至少从调查样本来看,大部分在合作企业顶岗实习的学生从事着人力资本专用性程度较低的工作。
本节研究分别验证了假设1A、1B和1D,证明了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能提高學生个体的专用人力资本;同时也发现,高职院校相当数量的实习生所从事的是专用性人力资本存量较低、岗位流动性较高的岗位;而且校企合作过程中所获取的专用人力资本未必能给学生带来更高的收入。
(二)学生个体人力资本专用性对校企合作稳定性的影响
上节的研究部分验证了假设1,即校企合作能提升学生个体的专用人力资本,但这种“可雇佣性”的提升未必能给学生换回更高的“收益”。本节研究重点转到学生个体专用人力资本对校企合作的影响。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企业与高职院校的合作主要是基于“稳定而专用的”技能人力资本。根据假设2——学生个体所增加专用人力资本有助于校企活动稳定性,本研究采用“稳定就业”和“稳定实习”这两个指标作为衡量校企合作稳定性的因变量,分析校企合作形成的学生个体专用技能人力资本对校企合作稳定性的影响。
1.个体人力资本专用性对稳定就业的影响
本小节研究首先将实习生“是否已与顶岗实习企业签订就业协议”作为稳定就业的因变量,建立实证模型5,试图找到学生个体人力资本专用性对于学生实习后稳定就业的影响。
模型5:
Y5=α+βX1+δX+ε(式5)
在式5中,Y5为学生“是否在顶岗实习企业中就业”的虚拟变量(“是”取1值;“否”取0值);X1为“是否是合作企业顶岗实习”虚拟变量(“是”取1值;“否”取0值);X为一组反映学生个体人力资本的特征变量,具体包括职业人力资本专用性(岗位与专业匹配度)、企业人力资本专用性(顶岗实习岗位流动率、企业专用技能熟悉时间)和通用人力资本(入学高考分数)。
表5的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学生个体(专用和通用)技能人力资本大小对其(是否)在顶岗实习企业稳定就业的作用都不显著;学生个体(是否)在校企合作企业中顶岗实习与最终是否在合作企业中稳定就业的关系也不显著。
综上所述,实习生在合作企业获取的专用人力资本大小对其能否在该企业稳定就业无关,假设2A未能成立。
2.个体人力资本专用性对稳定实习的影响
既然学生个体人力资本专用性与其在合作企业稳定就业关系无关,那么学生个体所增加的人力资本专用性对其在合作企业稳定实习有无影响呢?在前述分析基础上,本节提出模型7和模型8,试图发现学生个体专用人力资本对其稳定实习的影响。
模型7:
Y7=α+βX1+δX+ε(式7)
模型8:
Y8=α+βX1+δX+ε(式8)
在式7和式8中,Y7和Y8分别代表学生在校企合作企业顶岗实习的时间和更换实习单位数量;X1为“是否在校企合作企业顶岗实习”的虚拟变量;X为一组代表学生个体通用和专用性人力资本特征变量,包括学生入学高考分(通用人力资本)、实习岗位员工流动率(职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岗位与专业匹配程度(职业专用性人力资本)、企业专用人力资本(企业专用技能熟悉时间)。同时,还将可能影响学生实习稳定的实习工资收入指标作为自变量对照检验。
回归结果(见下页表6)发现:学生(是否)在校企合作企业实习与其稳定的实习时间关系不显著,但与学生更换实习企业数量呈负相关;学生稳定的实习时间与企业人力资本专用性(专用技能熟悉时间)和实习收入相关,而和职业人力资本专用性无关。换句话来说,从实习生个体的角度,最初在合作企业顶岗实习的学生可以降低未来更换实习企业的频率,但最终在合作企业稳定实习时间长短不仅取决于(学生个体)所获企业专用知识收益大小,还取决于企业实习收入收益高低。因此,假设2B和2C未能成立。
综上所述,本小节未能验证假设2——即学生在合作企业实习所获取的个体专用人力资本未能换回校企合作稳定性(稳定就业和稳定实习)。也就是说,学生个体在校企合作中所提高的“可雇佣性”与校企合作稳定性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三)学生个体“雇佣稳定性”对校企合作稳定性的影响
本部分研究转向假设3:学生个体雇佣稳定性对校企合作稳定性的影响。对企业来说,学生个体雇佣稳定性主要体现为学生作为主体与企业之间的契约,在实践中主要体现为学生参与签约的顶岗实习、订单培养(双方或三方)协议。
1.学生个体契约与顶岗实习稳定性
将学生“本人是否与顶岗实习企业签订实习协议”作为自变量,建立如下实证模型,试图找到个体签约对于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稳定性的影响。
模型9:
Y9=α+βX1+δX2+ε(式9)
模型10:
Y10=α+βX1+δX2+ε(式10)
在式9和式10中,Y9为学生在企业稳定的顶岗实习时间(月);Y10为学生实习工资的连续变量。X1为“本人是否与顶岗实习企业签订正式实习协议”的虚拟变量;X2为“所在院校是否与顶岗实习工作单位签订正式的实习协议”的虚拟变量;
回归结果表明(见表7),相对于校企之间的合作契约,学生本人“是否与顶岗实习工作单位签约”对其稳定的实习时间和实习工资收入的影响都呈正相关。
2.学生个体契约对订单培养稳定性的影响
从收到的针对订单培养的240份有效问卷中发现,学生在回答订单培养协议中是否有“违约责任条款”中,将近60%的订单培养学生回答“没有签订”;而在未来“计划毕业后到订单培养单位工作年限”的回答中,回答“5年以上”的不到15%。在上述描述统计的基础上,本研究建立如下实证模型:endprint
模型11:
Y11=α+δX+ε(式11)
将Y11作为订单培养学生“毕业后预计到订单培养单位工作年限”,X则是校企合作订单培养中“学生个人与合作企业是否签约”与“订单培养协议中是否含有违约责任”这两项作为一组虚拟变量。
回归检验结果(見表8)发现,学生个人与校企合作企业之间“是否签订书面协议”和“订单培养协议中是否有违约责任”这两项自变量对于订单培养学生在未来在合作企业预期工作年限呈显著正相关。
所以,学生个体的契约承诺提高了雇佣稳定性从而有助于校企合作稳定性(假设3成立)。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研究发现,学生个体在高职校企合作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校企合作能提高学生个体的专用人力资本。但以顶岗实习环节为例,不同行业、企业学生所获取的专用人力资本程度迥异。
第二,校企合作尽管可提高学生个体的专用技能人力资本水平,但所增加的专用人力资本未必能给学生带来更高的实习收入,也未能给企业换回稳定的雇佣。即学生个体通过校企合作获取的专用人力资本大小与校企合作稳定性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第三,学生个体与企业间的契约承诺,可以减少双方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保障校企合作稳定性。就学生个体而言,通过校企合作会形成不同程度的、凝结于个体的专用技能人力资本,但在实习阶段由于无法同时兼顾学生“收获大”“收入高”和“能就业”利益诉求,在没有雇佣保障或个体约束的情况下,学生、技能所有者和企业及技能使用者都容易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在人力资本专用性较大的企业中,缺乏经验的实习生可能会充当“旁观者”;而在人力资本专用性较小的企业中,如果监管缺失,企业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包括提供低技能岗位、通过“协议工资”让实习生充当廉价劳动力等);学生作为第三方与校企双方签订契约有将助于学生个体与企业之间的可信承诺从而提高校企合作的稳定性。
(二)政策建议
第一,为保障校企合作长期稳定,避免学生个体的机会主义行为,要将学生作为校企合作参与主体之一,将学生个体承诺作为校企合作稳定性的保障。以顶岗实习与订单培养为例,要在每期顶岗实习之前制订一个三方短期合同:企业保障给学生高质量的顶岗实习;作为交换,实习生必须保证能够在一段时期内在合作企业中稳定实习并接受低工资。与此同时,订单培养学生如获得了企业实质性的雇佣承诺,则必须接受培养合同中低于市场价格的实习工资并保证毕业后在合作企业内稳定的工作年限。
第二,要在整个社会和高职院校中提倡尊重技术工人和注重技能长期积累的观念(“工匠精神”),避免学生个体(和家庭)的短期行为。
第三,要改变政府对高职教育机构的财政资助方式。政府今后对高职院校财政支持除了对特定院校的专项财政扶持,还可以考虑对“校企合作订单培养项目”的财政补贴,受益对象从过去的特定院校适度转向基于专业——项目的“校企合作订单培养学生”。
参考文献:
[1]耿洁,黄尧.技能型人力资本专用化:工学结合中一个新的概念[J].中国高教研究,2010 (7):74-75.
[2]耿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体制机制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11.
[3]刘志民,吴冰.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培养人才的机理研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J].高教探索,2013(5):27-32.
[4]范皑皑.高校毕业生的学历与岗位匹配——基于全国高校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教育与经济,2013(2):18-24.
[5]吴冰,刘志民.人力资本专用性对高职校企合作的影响[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6(6):27-34.
(责任编辑:王璐)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