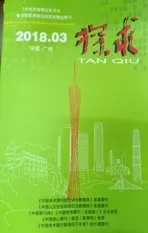不是风幡正是心,岭外别传挹清芬
——评李舜臣《岭外别传:清初岭南诗僧群研究》
2018-01-27姚蓉王天觉
□ 姚蓉 王天觉
一、历史、地域、群体相结合的视角
首先,《岭外别传》(以下简称该书)对明末清初史事的论述颇为到位。该书的研究范围是明末清初,而明末清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天崩地坼”的时期,朝代鼎革引起的社会动荡,促使大批士人遁入山林、寺院,岭南一带由于反清复明活动的持久存在,故而此风尤炽。世道人心的转变、诗人身份的转换,都使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文学呈现出复杂、多样的景观,尤具看点,也尤具难度。不同于有些著作的面面俱到、笼统论之,该书紧扣“清初”这一要点,又始终结合“岭南”和“诗僧群”阐发清初的历史、文化内涵。这就较同类著作更显得有的放矢和收放自如。如在论述清初岭南诗僧群崛起的政治文化背景时,作者分别从“‘应劫而生’的诗僧群”“明中后期‘儒释会同’的学术背景与诗人禅悦之风”“丰厚的禅文化土壤”“诗文化的蓬勃”四方面立论,直面要害问题,剥离复杂现象,并总结言简意赅的结论。例如,作者把明末昏暗的政局总结为文士逃禅、长年战乱、武夫跋扈这三点,又如,在论述岭南士人的禅悦之风时既详细梳理了明中后期以来的学术背景,又有针对性地重点阐发陈献章、憨山德清这两位代表人物的儒学和禅学实践,论证一目了然。还有些总结性话语一针见血,如说“遗民们在头发上的‘用心’之苦,实际也透显出他们在面临‘文化之劫’时,似消极实积极的抗争态度”[1](P33)、“诗、文、词中,澹归词的艺术价值最高”[1](P253)等。此外,全文的《结语》更是画龙点睛之笔,作者写道:“首先,从规模看,清初岭南诗僧是中国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诗僧群体。”“其次,从诗歌表现的情感看,清初岭南诗僧之诗也较此前的诗僧更为丰富。”“再次,从审美情趣和诗歌风貌看,清初岭南诗僧的诗歌也出现了新变。”“最后,从人格看,清初岭南诗僧不但是诗人与僧人的结合体,而且还带有极为鲜明的遗民色彩。”[1(]P295-296)
其次,该书对广东一地的文化解读甚为精微。书的题目有“岭南”二字,根据作者在“绪论”中的概念界定,该书研究的地域实为广东一省。就此而言,这又是一本地域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专著。为了投身此一课题的研究,作者不但细读文献、多方讨教,而且积极与佛教中人交往,参与佛寺活动,甚至到粤北寺庙中挂单修行。因此,在行文立论时,作者能重点抉发清初岭南佛教的特点,而非清初佛教的特点,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性。如言及“佛教在岭南有着十分深厚的根基,自六朝以来,一直就是中国佛教的重镇”这一观点时,作者给出了三个分论点,“其一,岭南历代高僧辈出。”“其二,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许多重要节点均与岭南休戚相关。”“其三,岭南寺院林立,佛教渗透社会的方方面面。”[1](P40-41)无一不是岭南特色的反映。
再次,该书大大推进了清代文学群体的研究。在21世纪初,作者选择诗僧群体为研究对象之时,古代文学研究界内的文学群体研究正在兴起,诗僧群体因为处于文学史的边缘地带,尚未受到重视,明清诗僧群体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清初岭南一代到底有多少位诗僧?他们的生平状况又是如何?而此书作者经过统计分析指明清初岭南这一时段、这一地域的能诗僧人共有154人,并将他们的基本履历、诗歌存佚情况制成了《清初岭南诗僧总目表》。而因是群体研究,故须发掘群体的共性。这种共性当然是相对的:相对于这154位中的每一位是共性,而相对于从古至今的诗僧群体,这无疑又是个性了。作者先把这154位僧人根据宗门世系关系以类相从,划分为五个亚群体:“阵容庞大的天然系诗僧群”“‘戒律精严’的鼎湖山系”“一枝独秀的大汕长寿系”“光孝寺诗僧群”“以外籍僧人为主的曹溪诗僧群”,然后探究他们“充满着法缘与俗缘纠葛的生活形态”。这些论述共同建构了第二章“群体之构成与生活形态”的内容。第三章研究的则是“清初岭南诗僧的结社活动”。从第四章“清初岭南诗僧的诗心”到第五章“诗学旨趣与诗歌风貌”又是纯粹的文学研究,从内容、艺术到风格,作者提要钩玄、旁搜远绍,确实把握住了清初岭南诗僧群的文学特点。
二、僧传、佛学、诗学相勾连的考辨
该书作者以学者的身份探究禅诗的魅力,既不满足于胡适先生在20世纪所倡导的禅学研究的历史的、科学的道路,也不偏执于铃木大拙先生主张的超越历史时空的感悟性研究,而是将两者结合起来。
就历史的、科学的一面而言,该书体现出了难得的考辩精神。如在论述清初岭南诗僧的“务实媚俗之态”时,作者通过详细举证表达了与陈垣先生不同的观点:“对于清初岭南诗僧诗歌中呈现出的奉承、媚俗的倾向,不能简单予以否定,而应当深入彼时的历史情境,充分考虑到他们作为僧人的特殊身份,这样方能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若仅从‘遗民’的角度观之,自然就会得出像陈垣先生那样‘恶劣’的印象。”[1](P166)与之相类的是对金堡澹归的历史评价问题。金堡本为南明诤臣,直言敢谏,人称永历“五虎”之“虎牙”,出家后却为新朝权贵歌功颂德,替平南王尚可喜编次年谱。邵廷采、陈垣先生对金堡澹归颇多微词,而作者不苟合邵、陈之见,能跳出狭隘的遗民观,从而真正做到了知人论世。可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研究对象的身份变化及时调整研究思路和方法,是作者成功考辩“僧传”的一大法门。其诀窍在于就僧言僧,既看到僧人身上的士风印记,又充分抉发其为僧人的身份认同。
除了人物评价不随人短长外,史事辩驳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其发力点主要集中在“诗学”和“佛学”上。作者善于捋清基本的诗歌史事。例如,东北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诗社是“冰天诗社”,可关于其成员的认定学界积压了不少误判,作者辩驳道:“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后世不少学者皆误将这几人归入冰天诗社。其实,李呈祥于顺治九年(1652年),陈心简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季开生于顺治十五年(1659年),方抵辽东,根本不可能参加冰天诗社于顺治七年所举行两次诗社,因而,他们决不在‘三十二’位诗社成员之列。”[1](P120)再如,清人李呈祥,字吉津,号浣木斋主。有学者在论文中不慎将其弄错,作者则在注释中点出一笔:“曹汛《剩人和尚<金塔铃>诗集考述》(载《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1期)一文中以为‘北里先生’系指李呈祥,实误。”[1](P120)
相对于“诗学”的考辩,该书更多的是对“佛学”的考辩,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深厚的佛学修养。遇到“豆腐渣材料”难免一番辩驳,如宋人姚勉云:“汉僧译,晋僧讲,梁魏至初唐,僧始禅,犹未诗。唐晚禅大盛,诗亦大盛。”这段材料较为常见,引用者往往不予细究,舜臣则补充道:“姚勉所说未必尽合事实,因为僧人做诗之始实可溯自东晋,但‘唐晚禅大盛,诗亦大盛’云云,确为的论。据《全唐诗》所载115名氏家诗人中,可确考生活于中唐之后者90余人。”[1](P40)不但梳理佛史,且用数据说话,很有说服力。
再如有学者依据《海外纪事》中的文字,断定“大汕对佛学只懂一点皮毛知识,并无多少学问。他在越南贩卖的是儒、佛、道合一的理论。”[1](P87-88)作者认为这种判断与事实不符。证据有三:一是《海外纪事》属于记录闻见的笔记,其目的并非为了阐释精深的佛学义理;二是大汕面对并不了解禅宗的安南信众,首先要做的是“普法”工作,而非阐释深奥难懂的佛理;三是大汕崇尚的是活泼任运的生活禅,而非死参经义的“文字禅”。因此,切不可以《海外纪事》而否定大汕的禅学修养。这三点,分别从材料本身的性质、僧人普法的目的和僧人推崇的佛法立论,自然比盲从原始材料者高出一筹。
可以说,书中的辩正之处俯拾皆是。这当然与清初岭南文学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有关,故对史料的发掘和辨析还须众人拾薪,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则是作者具有很高的识见。唐代史学家刘知己认为治史者须同时具备史才、史学、史识,清代学者叶燮也认为学者须同时具备才、胆、识、力。因有过人的识见,往往能在习以为常的材料中发现人所不见之处。书中的第六章“论金堡澹归”,第七章“论石濂大汕”即充分体现了作者的识见,故辩正发覆之处也最为详细。关于澹归,前已举出事例,兹不再赘。这里就大汕再补充说明一二:石濂大汕是清初岭南诗僧中最值得重视的人物之一,精通佛法、天文、地理、兵农、礼乐、术数、书画、琴棋、剑戟、百工之艺,可谓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还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应越南国王阮福周之邀,抵达安南传法,度弟子上千,次年返粤,并带回大量珍宝重建长寿寺,其建构之富丽、耗奢,为当代罕见,俨然是一位“实干家”,但他却“常画素女秘戏图庄,以媚诸贵人,益昵近之”,因此被屈大均、王士禛、潘耒等人讥为“花怪”“妖僧”“狂僧”,最后被潘耒刻《救狂砭语》一书攻击,为朝廷驱逐致死。大汕在当时即有正反两面评价,且针锋相对。清以后学者,言及大汕,仍“非此即彼”,落于前人窠臼。姜伯勤先生的《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以40余万字的篇幅研究此一人物,可谓一网打尽、尘埃落定。就此看来,对大汕的评价已经可以止步于姜伯勤先生“同情式”的理解和饶宗颐先生在《<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序》中所持有的中肯评价了。再往前推进一步,似乎都难上加难,不可企及。面对先贤的成果,作者并没有低眉敛手,而是在占有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从文化学的角度对其展开研究,旨在说明大汕乃“在欲行禅”,并将其置于禅宗史的链条上审视,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与慧可、仲殊、慧洪等僧人一样,也是中国佛禅文化中一位典型的‘在欲行禅’的僧人,是佛教日渐世俗化的集中体现。”[1](P292)这就完全跳出了前人的思维定势,而将这一问题大大的、精彩的推进了。它如,对诗僧们写颂圣诗、祝祷文的考辩,指出颂圣文学历来真假参半,诗僧们写作颂祝诗文时的普遍心态是既苦于作此等诗文,又不得不为之,这些作品并非出自诗僧们的真心。[1](P165)也颇能体贴古人之心,令人读了耳目一新!
总之,僧传、佛学、诗学相勾连的考辨是本书值得称道的又一特点。如果说僧传的考辩体现了以人为本,或曰以僧为本,那么佛学和诗学的考辩就直指僧人安身立命之所在。从人出发,抵达佛和诗,这种研究思路本身就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
三、会通、专精、感悟相交融的批评
李清照说:“慧则通,通即无所不达;专则精,精即无所不妙。”(《<打马图经>序》)[2](P340)今人治学,主张会通与专精并举。会通是面上的融会贯通,专精是点上的深挖细刨。该书即体现出了会通与专精相结合的特点,全书第一章至第五章,纵论清初岭南诗僧群体的政治背景、文化背景、群体构成、生活形态、结社活动、诗心、诗风、诗艺、诗学等,无不大处着眼,宏观着手。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岭南诗僧群体虽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居于一隅,但走进这个领域,亦五光十色、别有洞天,作者有能力带领读者领略这个小范围中的大世界。从第六章至第七章,又从面入点,选取众僧中最具代表的两位:金堡澹归和石濂大汕做个案分析,俨然又是仰观星河、手摘日月了。除了整本书的框架体现出会通与专精的特点外,每一章的撰写也多是点面结合、由表及内。
作为一本文学研究专著,回归文学本位至关重要。岭南诗僧群体的诗心、诗风、诗艺、诗论是什么?这恐怕是很多文学研究者首先关心的问题。作者敏锐地看到,自宋元以降,僧人的思维方式、情感生活已逼近俗世常人,岭南诗僧又多为“有托而逃”的文人志士,故其思想也半为俗人半为僧次。“因此,我们在研究诗僧以及僧诗时,既不能忽视他们的特性,亦不能过于拉大他们与一般文士的距离而置于玄渺之境,只有同样以世间法和出世间法观之,或可获得更多的会通契机。”[1](P134)正是在这种“会通契机”的原则下,作者将清初岭南诗僧的诗心概括为“苦难的悲吟”、“故国的挽歌”、“尘劳的解脱”、“禅悦之风致”、“友谊之求”、“媚俗之态”等方面。这几点有与前代诗僧相同的地方,亦有与前代诗僧相异的地方。相异的地方自不必说,仅就相同之处而言,作者亦能匠心独运地提炼出彼时僧诗的“异量之美”,虽在措辞上偶有因循——这其实是无法避免,也不必避免的——在内涵上则迥然有异。如“禅悦之风致”可谓是历代诗僧共有的特点,作者也承认“与前代诗僧的禅诗相比,清初岭南诗僧的禅境诗、禅理诗并不显得很突出”[1](P151),但他并不因此对其置而不论,因为这些诗不但体现的是诗僧的身份意识,而且“仔细品味,仍禅意盎然,禅理精辟。”[1](P151)在结论部分,作者说:“作为最能体现诗僧特色的禅境诗与禅理诗,清初岭南诗僧的确创作了一些佳制,但若将此类诗作与王梵志、寒山、皎然、齐己、惠洪等唐宋诗僧相比,似乎又逊色不少。”[1](P157)可见,至始至终,横亘在作者心中的都是历代诗僧群像图,作者要做的就是在千年诗僧的长廊里,找到清初岭南诗僧的合适地位。这一过程虽不乏对诗僧诗心的琐碎言说,其结论则早已打通了千年僧诗的研究。
“人皆讥造次,我独赏专精”(《学诸进士作精卫衔石填海》)[3](P770)将韩愈的这两句诗用在作者身上并不过誉。如果说上文对第四章“清初岭南诗僧的诗心”的介绍旨在说明作者深具会通的视野,那么下来对第五章“诗学旨趣与诗歌风貌”的介绍,就侧重于说明作者如何在会通之外,将专精的研究发挥到酣畅淋漓的境地。当然,在论述诗学取向和诗歌风貌时,作者也还时时顾盼禅宗诗史的发展脉络。但一落实到对僧诗特质的分析,对“蔬笋气”和“酸馅气”的讨论,作者马上就摆出穷根究底的姿态。第五章伊始,作者先抛出三个问题引人思考:“蔬笋气”和“酸馅气”的内涵究竟为何?它们又是怎样成为评鉴僧诗的重要术语?清初岭南诗僧在观念上是否承续了此种创作模式,他们的诗歌风貌是否也具有此等特质?众所周知,对“蔬笋气”和“酸馅气”最有发言权的是周裕锴先生,作者本可将周先生的观点拿过来直接使用,但鉴于对这两个术语的阐发还有可兹探讨的空间,于是干脆采铜于山、另起炉灶,重新论断一番。这番功夫毕竟不白费,正如书中所说“因为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实际的创作中,清初岭南诗僧们多能突破此等习气,表现出与前代僧诗迥然相异的审美情趣与艺术表征。”[1](P183)这样,就把清初岭南诗僧的特质水到渠成地引出来了。
作者对禅诗往往别有会心。例如,面对万余首僧诗,其整体风貌如何描述?诗僧山水诗的自然意象过于丰富,又如何把握?事实上,这些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固定、标准、唯一的答案,也正是在这些地方作者发挥了自己的感受能力。其中对大汕诗“日出锄白云”的心解,[1](P281)对大汕诗好用“隔”字的揭示,[1](P282-284)皆发前人所未发,大有禅宗祖师以心传心,教外别传的风范。平心而论,感悟性的诗歌批评在书中并不占有很大比例,作者总归是把重点放在了史事的梳理和理论的阐发上,但这偶一寓目的吉光片羽已足以使人“破颜微笑”了。
面上的会通,点上的专精,加上点面结合之上的心灵感悟,融为一体,共同搭建了一个三维立体式的批评空间,其对僧诗的阐释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不但理论功底扎实,而且文笔优美,书中时有珠玉之语跳入眼前,令人心醉。如说“屠夫本性,暴露无遗。他们将战马牵入城内,使‘城内外三十里所有庐舍坟墓,悉令官军筑厩养马’,‘羊城’居然变成了‘马城’!”[1](P28)“这些高僧大多道法精深,提持祖道又能苦口婆心,悲智双遣。明季清初的很多文士,皆因久慕他们的德容风范而趋皈浮图。”[1](P44)“衲子呕出心肝,磨破蒲团,苦吟冥搜,虽远文人习气,却也含带酸味。”[1](P182)无不彰显出老练的文字功夫。
概言之,清初岭南诗僧是中国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诗僧群体。在清初风云变幻的时代里,这些僧人腾挪活跃,为清廷忌惮,文集惨遭禁毁,乃至造成了对这段历史描写的缺位,今天看来殊为可惜。随着时下学术研究的蓬勃繁荣,学者们逐渐对这一诗僧群体展开零星研究,但既不具体,也不充分,且偶有偏执之论。该书论述全面而成熟,能从历史、禅学、文学等层面深耕细作、爬罗剔抉,可谓有俾于学术之功大矣。
[1] 李舜臣.岭外别传:清初岭南诗僧群研究[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7.
[2] (宋)李清照.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 (唐)韩愈.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