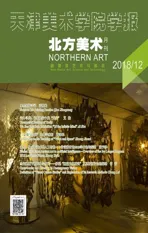当代视域下的跨界与多元
——界说“视觉文化研究”及其研究方法的探绎
2018-01-25常雷
常 雷
引言
长期以来传统艺术史多数解读的是“高雅、精英文化”下的视觉图像,随着时下图像外延的扩大以及学科间交叉影响的增强,传统艺术史面对当代“流行、大众文化”下的图像范畴,往往显得力不从心,研究方法也相应自闭与滞后,局限性自不待言。但是,20世纪60年代“视觉文化研究”的诞生,为视觉图像研究开拓出新的局面。然而,关于“视觉文化研究”的界说及其研究方法却始终语焉不详。欲明正道,须先正名,名正才能言顺。本文尝试爬梳理清“视觉文化研究”界说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视觉文化研究诸种方法做进一步的探绎,以期更有效地开展对当代视域下视觉图像的研究。
一、视觉文化研究(Visual Culture Studies)界说
1.“视觉文化”一词的提出
“视觉文化”一词在文本中首次被提出,外文资料中多以美国艺术史学者斯维特拉娜•阿尔珀斯(Svetlana Alpers)所著的《描绘的艺术:十七世纪荷兰艺术》(The Art of Describing: Dutch Ar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一书中所提及的“视觉文化”一词为正式出处。在《描绘的艺术》这本书中,阿尔珀斯借其师兄迈克尔•巴克森德尔(Michael Baxandall)1972年出版的《十五世纪意大利绘画与经验》(Painting and Experienc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Italy)中“时代之眼”的定义,明确指出:“我(阿尔珀斯)意图研究的不是荷兰‘艺术的历史’,而是荷兰‘视觉文化’——一个归功于巴克森德尔的术语。”西方艺术史学者之所以没有将“视觉文化”一词的产生归功于巴克森德尔,是因为巴克森德尔提出“视觉文化”一词时,在其书中上下文并非具有主导性作用,只是作为巴氏艺术社会史研究的辅助依据。因此,在此种意义上把阿尔珀斯称为“视觉文化”一词的缔造者亦不为过。
虽然阿尔珀斯明确提出了“视觉文化”一词,但《描绘的艺术》中,皆是通过研究荷兰十七世纪天文学、画像手艺、地图志来展开对画家创作时社会环境的重新构造,因而实际上,她使用的还是像巴克森德尔等人所用的社会学研究艺术史的方法。
2.“视觉文化研究”之名
“视觉文化研究”,顾名思义,是一种针对“观看”的视觉性(Visuality)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
“观看先于言语。儿童先观看,后辨认,再说话。”[1]这是英国当代艺评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其代表作《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正文第一页中写下的第一句话。这句似是常识又富有哲学意味的开头,重新确立了“观看”对于人之存在的重要性。面对日益图像化的现代社会,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形容当下为“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Spectacle),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则比喻为“拟象”(Simulation) 时代,这些名词均包含着一个共性:视觉性的在场。这里所谓的“视觉性”的概念,不是指视觉对象本身的物质性或可见性,而是指观看的行为。关于“视觉性”的研究,就是研究如何看与怎样看,即看与被看的关系。我们从中可以得出,视觉文化研究的对象不限于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下的艺术,也不限于文化下的非艺术形象,而是扩展到了整个看与被看的日常实践。[2]343
正如上述所指,视觉文化研究是针对视觉性的文化研究,那么将其归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顺理成章。“文化研究”发轫于英国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设立“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文化研究成为一门显学。由于文化研究是一门交叉学科,故与文学、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稍不留意往往容易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混淆。“文学研究”在我国教学学制内被称之为“文艺学”,由于“文艺学”中的“艺”字迄今没有显现出来,若究其本位,“文艺学”应称为“文学理论”,文学理论才是文学研究的内容所在。
视觉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共享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论。但是,文化研究对于视觉文化的研究较为单一,主题多为阶级、种族与性别,较少关注视觉性本身。相比之下,视觉文化研究较少政治说教,马克思主义色彩大为淡化,更多的是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式的符号学、拉康(Lacan)式的精神分析、福柯(Foucault)式的后结构主义、德里达(Derrida)式的解构主义、鲍德里亚式的后现代主义等方法入手。引用约翰•A.沃克(John A.Walker)和萨拉•查普林(Sarah Chaplin)的话说:“视觉文化研究就是艺术史的争论与扩展、‘艺术社会学’的更新、‘新艺术史’的出现、电影多媒体研究的迅猛扩展以及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相互交融的结果……”[3]一言以蔽之,视觉文化研究是“跨学科”的,即各学科之间交叉对话的场所。
二、视觉文化的研究方法
英国艺术史家恩斯特•贡布里希爵士(Sir E.H.Gombrich)曾将有关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形容为:“要想敲钉进墙就得使用钉锤,要想拧动螺丝就得使用螺丝刀。”[4]一层意思是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另一层含义是研究不应拘囿于单一方法,应清楚并熟练多种研究方法,以期应付不同的研究状况。随着图像研究范畴的延伸与拓展,传统艺术史研究方法如图像学、形式分析,显得陈旧和不合时宜,而视觉文化研究因具备了与生俱来的“跨界”属性,其研究方法更加开放与多元,除共享文化研究和传统艺术史的方法之外,较为流行的研究方法还有符号学、艺术社会史、精神分析,等等。因文章篇幅有限,无法详尽展开,只能述要常用的几种研究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并不相互排斥,常常也会交叉使用。
1.符号学分析(Semiology)
现代符号学源于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美国哲学家查尔斯•S.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索绪尔研究的主要理论为结构主义符号学,在其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他提出了符号由两个要素构成:“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要比索绪尔复杂些,他将符号分为三部分:象征(Symbol)、图像(Icon)、索引(Index)。以皮尔斯的理论为基础,会发现理论上符号可以被无限解读。但实际上,符号的意义是要受到所处社会及文化的影响与制约的。
法国学者罗兰•巴特对符号学发展的贡献,主要在于他超越了索绪尔等人的语言学局限而进入到文化研究领域。在其著名论文集《神话》(Mythologies,1972年)里,巴特认为“神话”是一个二级符号体系(或称为“次生符号系统”),索绪尔符号学中的“能指”和“所指”创造了符号(第一级层次),而由“能指”和“所指”创造的“第一个层次”又继续成为其他事物的“能指”,于是便有了“第二个层次”。巴特通过符号学方法对法国杂志《前进-巴黎》(Paris-Match, June-July 1995)封面的图像进行了“视觉文化”分析。封面照片里的人物是一位身着戎装向法国国旗敬军礼的黑人士兵,他目视远方,沉着而又坚定。在巴特看来,这个人物形象充满了符号学上的意义:法兰西是伟大的帝国……在法兰西帝国没有任何的种族歧视现象,她(法兰西帝国)的孩子们都在她的旗帜下效忠保卫祖国……这样一来,巴特就通过符号学,将隐蔽的图像意义——一个掩盖法兰西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历史真相的神话解读出来。符号学同样也是训练设计师的有益工具,它曾一度成为德国乌尔姆(Ulm)设计学院的主要课程之一。
图像学(Iconology)和形式主义(Formalism)这两种传统美术史研究方法论在相互分离的条件下各自发展,但两者却有一共同点,即绘画作为符号的存在均被强行忽视了。美国艺术史家梅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是艺术史界第一位使用符号学来分析艺术作品的学者,但真正系统使用符号学进行艺术分析的当属英国“新艺术史”(New Art History)的代表——诺曼•布列逊(Norman Bryson)。布列逊是英国剑桥大学文学批评及语言学专业出身,攻读博士期间还在伦敦大学考陶尔德学院(The 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 University of London)学习艺术鉴赏等课程。在艺术史学习过程中,布列逊发现“近三十年来,在文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相对于艺术史学科来说,却依旧是死水一潭的平静。在这种平静状态中,当然,艺术史的职业继续存在,各种专论也在平静中写出,越来越多的目录也编制出来;然而,艺术史却是产生于人文学科中人迹罕至的区域,或者说产生于智力生活的闲适区域”[5]。他尤其针对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和贡布里希的理论,提出传统艺术史的研究多采用科学实证主义和知觉经验主义。科学实证主义即遵循科学研究的方法,首先像科学家一样提出问题,其次寻找相关的论据,再次反复论证,最后得出结论并衍生出新的问题。它被认为是艺术家为了更加真实地描绘世界而进行的一种试错过程(a trial-and-error process)。
自布列逊的著作陆续被翻译引介到中国以来,国人因布列逊熟练地运用符号学来重新阐释历史经典艺术作品而印象深刻。文学批评出身的布列逊就这样带着符号学武器从艺术史外部进行干预,吸收和引入了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方法,尝试将艺术史从“实证主义”和“知觉主义”中摆脱出来。其本质是打破从瓦萨里和温克尔曼的生物学循环模式、黑格尔的螺旋式进化模式、里格尔的线性进化模式、沃尔夫林的形式分析以及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等以来的艺术发展自律性“内向观”,试图从外部寻找艺术发展变化的他律性因素。
布列逊反对贡布里希的“知觉主义”。布列逊在其主编的《视觉理论:绘画与阐释》(Visual Theory: Painting and Interpretation)一文《符号学与视觉阐释》(Semiology and Visual Interpretation)中提出贡布里希在《艺术与错觉》(Art and Illusion)中过分强调“知觉主义”(Perceptivism)在艺术作品创作中的作用是个明显错误,布列逊提出用符号学代替知觉主义:“绘画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贡布里希给予的回答是:它是一种知觉的记录。我要肯定的是,这个答案在根本上是错误的。……读者将会看到,那种被绘画是一种知觉记录的解释所掩盖的,正是图像的社会性及其作为符号的现实。”[6]不过,布列逊的符号学方法也并非表现得无懈可击。假设真是如此,导致的后果将是观者面对艺术作品,考虑的只是作品本身的意义,而却不再接受作品所带来的“移情”之感。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作品,必须具备理解与欣赏的完整性。
2.艺术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Art)
艺术社会史起源并脱胎于马克思(Karl Marx)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理论,其特点在于通过艺术与经济、政治、社会的关系来解释艺术现象。因马克思生前并没有对艺术做过系统完备的论述,故一些西方学者从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变通来解释艺术现象。
传统艺术社会史方法的学者当推美籍匈牙利裔艺术史家阿诺德•豪泽尔(Arnold Hauser)。豪泽尔在其两卷本鸿篇巨制《艺术与文学的社会史》(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 and Literature)中提出艺术与社会应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是辩证唯物的关系。其主旨思想是:历史产生的成就皆是由人所为,但人总是处于特定的时间、地点等因素之中,故人所做出的成就是个人的才能天赋加社会环境两者共同的结果。同样,人为的艺术也就与社会亲密联系于一起,不过,艺术虽受社会影响,但它不是社会的直接产物。艺术的产生与发展,一部分是由艺术发展的内部自律性决定,另一部分则由外部相关因素决定。豪泽尔还进一步解释了外部的相关因素有艺术家的个性与社会环境两个方面。以外在的视角来审视艺术内部,这样有助于认清和克服“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性。由此可见,豪泽尔的艺术社会史范式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艺术),另一方面上层建筑(文化艺术)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不过,豪泽尔在书中讨论艺术风格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时,武断地认为“阶级决定艺术风格”,此观点存在着生硬、机械的决定论倾向,因此受到不少现代学者的质疑与非难。
当代“艺术社会史”的主将是英国艺术史家T.J.克拉克(Timothy James Clark)。克拉克的理论亦来自马克思主义,他在《泰晤士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1974)中提出:艺术史应该是唯物史观的艺术史,而不是唯心史观的,艺术史的实践不能脱离历史、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但是,以克拉克为代表的艺术社会史学家对将艺术看成为简单、机械的“决定论”的反映采取了批判态度,克拉克在其著作《现代生活的画像:马奈及其追随者艺术中的巴黎》(The Painting of Modern Life: Paris in the Art of Manet and his Followers)中写道:“正如我早已说过的那样,我也许厌恶那样一种艺术的社会史版本;它总是将图像当作它们简单地加以反映的知识的记号。”[7]22
克拉克的艺术社会史与豪泽尔的历史唯物主义艺术史观的区别在于:(1)克拉克没有像传统艺术社会史学家那样预设一个简单、机械的“决定论”(如“阶级决定风格”),而是将艺术社会史纳入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中,开始关注艺术品、艺术家的独特性和艺术生产的复杂状况和环境;(2)对传统艺术社会史研究方法进行了范式更新:从原有的绘画(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直接反映经济基础或社会现实演变成了一套周密的理论模型,即绘画(不同于意识形态)、经济基础(社会现实)以及绘画传统(绘画惯例)三者之间的关系。[7]483
3.图像转向:当代图像学(Pictorial Turn:Contemporary Iconology)
传统“图像学”是由德裔美籍美术史家欧文•潘诺夫斯基创立。潘氏图像学是为研究文艺复兴艺术图像的意义而生,潘氏将其创造的这种读图方法分为三个步骤:(1)前图像志(Pre-Iconography)描述,即对艺术作品的外部特征进行描述;(2)图像志(Iconography)分析,对艺术作品的内容进行解读;(3)图像学(Iconology)阐释,对具备内容与形式的艺术作品整体把握,解读文化语境下艺术作品的引申之意。潘氏认为“圣像”(icon)这类图像并非模仿之物,而是特定时期下历史文化的象征形式。因此,要胜任图像学研究的工作,须得具备丰厚的人文历史学识,包括宗教、哲学、历史、文学、心理学等。总之,潘氏的图像学是一种为阐释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跨学科研究范式和方法。
尽管潘氏开辟了这种新的艺术史研究方法,但只是在视觉艺术这样一个有限领域内展开研究。如果用传统图像学解读多彩缤纷的当代图像则会力不从心。因此,20世纪80年代末,芝加哥大学文学系及美术史系教授米歇尔(W.J.Thomas Mitchell)针对美国当下的视觉图像文化,在其著作《图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Iconology: Image,Text, Ideology)中提出了当代“图像学”[8]的概念。米歇尔主张在潘氏基础上建立起当代“图像学”,其主旨并非延续潘氏架构的传统图像学方法,而是要发展潘氏在艺术史视域下开拓出的跨学科研究视野。
米歇尔在杂志《艺术论坛》(ARTFORUMin 1992)上以“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为口号,根据视觉文化研究自身的“非学科性”(Indiscipline),即解构学科,让视觉文化从艺术史、美学等解脱出来,去研究那些非艺术、非美学或日常生活所见的具备“视觉性”的图像[2]343,使得米歇尔的当代“图像学”研究远远超出了传统图像学的艺术史研究范畴,跨越了心理学、传播学、美学及社会学等广大领域,具备了研究当代图像(包括数码影像、生活照片、艺术展览等)的优先权。
结语
综上所述,视觉文化研究是将图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进行研究,不仅综合了传统艺术史、文化研究的研究范畴和方法,而且还将符号学、艺术社会史、当代图像学等纳入其中。可以说,视觉文化研究是在跨学科语境下传统艺术史方法与文化研究的有益补充与拓展。
纵然传统艺术史研究受跨学科的视觉文化研究冲击在所难免,但是传统艺术史不会就此而消亡,亦不可能消亡,它有着自身的优势和存在理由,视觉文化研究只会使艺术史的形状更加丰富多彩。与此同时,视觉文化研究和传统艺术史研究又互为依赖,既能看出自身的不足,也能发现新的机会,使得艺术史研究在不断反省的同时内部相互协调,愈加趋向和接近图像的真相。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理论方法的使用都是一把双刃剑,它的有效性和局限性如影随形。由于“视觉文化”研究的是可见之物,所以有读者或许认为研究眼睛所能及的东西是相对容易的,但是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教授詹姆斯•埃尔金斯(James Elkins)看出了此种倾向的危险性,在其著作《视觉研究:一种怀疑性的导论》(Visual Studies:A Skeptical Introduction)中指出在视觉符号充斥的今天,一般性的视觉符号通俗易懂,但并不意味着看到这些视觉符号的观者的反应会保持一致。因此,我们在使用符号学、艺术社会史、当代图像学等诸多研究方法的同时,需要保持一种审慎而严格的分析。[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