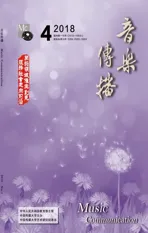当代中国音乐纪录片中的民歌传播模式
2018-01-24陈律薇
■陈律薇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杭州,310053)
近年来,音乐纪录片在学界和业界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从音乐纪录片在国内萌芽到发展至今的20多年间,正值我国经济腾飞、社会文化随之不断迁替嬗变的时期,若能从时空场域的角度对音乐纪录片进行观察与分析,或将开辟音乐纪录片创作和传播研究的新视角。而从音乐纪录片的主题和内容来看,国内的音乐纪录片虽然涉及了许多不同体裁的音乐,诸如流行音乐、古典音乐等,但其中最具有中国本土民族文化特质的体裁则是中国民歌。
音乐纪录片是如何在保持自身非虚构性和客观真实的特质的同时,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以及中国传统艺术审美观念融合与互渗的?带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笔者拟将以中国民歌及与其相关的事象(歌手、乐器或音乐事件等)为主题的音乐纪录片作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这一语境中加以考量,探析中国民歌在音乐纪录片中的运用与传播模式,及以其为拍摄主体的音乐纪录片历经20多年的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变化,以期为中国民歌在音乐纪录片中的传播研究增添一些新的内容。
一、对相关概念的解释与说明
首先,笔者将先对本文中所用的“民歌”概念作一解释,并对研究采样范围等进行必要的说明。
(一)对“民歌”在本文语境中的阐释
中国民歌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各民族各地区的民歌也各具特色、绚丽多彩,共同为我国音乐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①参见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词典》编辑部编《中国音乐词典》,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版,第269页。面对当代社会经济文化变迁和现代媒介传播介入的纷繁复杂的文化格局,中国民歌的内涵与外延均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进程中,因此,有必要先对“中国民歌”这一概念进行厘清和阐述。
关于“民歌”这一概念的权威性阐释,可考《中国音乐词典》之“民歌”条:“民歌,即民间歌曲。是劳动人民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集体创作的一种艺术形式,源于人民生活,又对人民生活起广泛深入的作用。在人民口头的代代相传中,不断得到加工。音乐语言简明洗练,音乐形象鲜明生动,表现手法丰富多样。有多种体裁和形式,主要为劳动号子、山歌、小调、长歌和多声部歌曲。”②《中国音乐词典》,第268页。在上述定义内容的基础上,再结合音乐人类学、音乐传播学等学科的观点,可归纳“民歌”在创作和传播方式上的特征:源于生活艺术③“生活艺术”是相对于“职业艺术”而存在的概念。参见何晓兵著《从中心到相对——电视音乐传播价值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页。、口耳相传的传播模式、集体创作方式④因此,借用民歌的元素创作而成的由音乐家或词曲作者个人署名的民歌样式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中。。
本文涉及的“民歌”概念,是广义上的概念。除了具备上述本体特征的民歌之外,还包括了与其相关的歌手、乐器、音乐事件以及音乐风格、音乐文化等。笔者对“民歌”的阐释在对其进行内涵特征研究的基础上关注其外延界定,且将其纳入生态学的研究视域中。本文涉及的“民歌”概念的外延的核心内容与21世纪初在学术界和大众传播领域兴起的“原生态民歌”⑤“原生态民歌”是21世纪初音乐学、传播学、文化人类学、广播电视学以及大众传媒领域都高度关注的学术概念。对在“民歌”前加入“原生态”这一定语,音乐学界有着不同的理解与争议,具体可考乔建中《“原生态民歌”琐议》(载《人民音乐》2006年第1期)、查子明《中国原生态民歌生存发展之我见》(载《音乐探索》2006年第1期)、杨民康《“原形态”与“原生态”民歌音乐的辨析——兼谈为音乐文化遗产的变迁过程跟踪立档》(载《音乐研究》2006年第1期)、王可《原生态民歌电视传播价值》(中国传媒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等文章中关于“原生态民歌”概念的界定,以及词典相关词条。概念在生态环境的认知和理解层面有重合部分——“原生态民歌”提出者认为“民歌”的歌唱环境须保持其原本的“状态”,本文在此观点的基础上,重视对民歌创作与演唱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探析,也对社会文化变迁、媒介生态变迁给民歌带来的内涵及外延上的变化予以关注。比如音乐纪录片《黄河尕谣》讲述了一个担心失去“农村味儿”的“80后”西北歌手张尕怂如何用自己热爱的民歌在现代化都市闯荡的故事。其中,张尕怂向民间老艺人学唱原生态民歌,但他在经历了现代化城市的文化冲击后,歌唱风格和词曲内容都会呈现出不同于他所学得的民歌母体的嬗变。因此,笔者也将此类由于原生环境变迁而产生变化的民歌纳入研究视野。
(二)对“音乐纪录片”的研究采样范围
音乐纪录片作为一种影像语言、媒介,其在认知音乐、诠释音乐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它对音乐文本、音乐事象、音乐文化的阐释和呈现,亦是一种传播载体。
研究以中国民歌为主题的音乐纪录片,不能避讳提及另一个名词“音乐民族志电影”。笔者认为,近年来学术领域出现的“音乐民族志电影”等学术名词,与“音乐纪录片”不是同一个概念。两者有相似之处,比如它们都运用影像语言对音乐及其相关的事象进行非虚构的记录与捕捉,以民歌为主题的音乐纪录片在拍摄和制作时,也会运用民族学的“田野工作”的方法。而若要区分两者的差别,可从音乐的定位、传播目的和受众分析等方面来作比较。
音乐民族志电影以音乐事象为核心关注对象,音乐及其相关事象在影片中是绝对的主体;在音画关系上,视觉语言是一种手段和方式,是为了音乐而服务的。音乐民族志电影具有文化人类学的资料属性,其用于学术与研究的目的是首要的,⑥庄孔韶著《文化与灵性》,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页。一般由人类学者拍摄或主持拍摄,遵循人类学的专业原则,因此一般归入影视人类学的范畴,其受众也大多为具有民族学或人类学学科背景的专业人士。
音乐纪录片虽然是以音乐及其相关的事象为拍摄主体,但是影像语言在音乐纪录片中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其与音乐是以“双主体”的状态、互为表里的方式并存于音乐纪录片中的。纪录片作为一种影像表达的方式,不仅可以捕捉到绚丽多彩的音乐本身,还可以用视觉语言讲述音乐故事,记录音乐事件,挖掘音乐人的人生感悟和心路历程,记载音乐流派的兴衰荣枯,关注音乐背后的文化变迁。音乐纪录片的大众传播属性决定了其在受众层面与音乐民族志电影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因此,本文中涉及的中国民歌的音乐纪录片研究未包括音乐民族志电影的样本。
此外,本文中的“音乐纪录片”是不同传播媒介的纪实影像的统称,研究与采样所涉及的音乐纪录片,既包含由主流媒体创作与传播的电视纪录片,也包含纪录电影。
(三)研究模式
音乐民族学家蒂莫西·赖斯(Timothy Rice)①蒂莫西·赖斯(Timothy Rice):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教授,著有《愿它充满你的心灵:体验保加利亚音 乐》(May it Fill Your Soul:Experiencing Bulgarian Music,1994)、《保加利亚音乐:音乐体验、文化的表达》(Music in Bulgaria:Experiencing Music,Experiencing Culture,2004)等著作。他曾任《民族音乐学》期刊编辑(1981—1984)、民族音乐学学会(SEM)主席(2003—2005)、传统音乐学学会(ICTM)执委会委员(2007—2013)、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与建筑学院副院长(2005—2006)、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赫伯埃尔伯特音乐学院院长(2007—2013)。曾提出通过对“时间”(time)、“地点”(location)、“隐喻”(metaphor)②见蒂莫西·赖斯(Timothy Rice)著《民族音乐学建模》(Modeling Ethnomusicology),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年版,第91页。这三个维度的考量来将音乐与其所处的场域进行联结,以此进行音乐的主体定位研究。笔者欲将此研究模式引申至本文的研究焦点,以中国民歌及与其相关的事象(歌手、乐器或音乐事件等)为主题的音乐纪录片作为研究对象,分析20多年来的社会文化变迁对其发展的影响。
二、民歌走进音乐纪录片(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
以民歌为拍摄主体的音乐纪录片最早可追溯到1998年北京电视台制播的电视系列纪录片《民歌魂》,它当时还被作为我国国家领导人赠送外国元首的国务礼品——这被认为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国内文化(音乐)价值取向调整的一次表态”。③何晓兵著《从中心到相对——电视音乐传播价值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7页。而其背后深层次的动因则与当时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在社会文化背景的助推下,中国人获得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契机,并进而重新确立文化自尊和自信。曾被边缘化的民歌登上了主流媒体的舞台,音乐纪录片也将其作为主体内容开始了创作和传播历程,这标志着中国民歌的音乐纪录片传播的发端。
从这一时期中国民歌的音乐纪录片传播在内容层面上的呈现来看,其不仅具有纪录片创作的时代背景特征,也展现了电视纪录片创作者对于民歌的关注,以及对民歌与中国传统文化之的关联的认知。这较显著地体现在以下这些方面:
一方面,绘制民歌的全景式地域版图,关注环境、民歌与人的关系。以《民歌魂》为例,它根据民歌的地域文化特征与传播特点,以“黄土地交响曲”、“江南吴歌”、“白山黑水”等不同地域的民歌意象为组成部分绘制起中国民歌图景。它通过对民歌的挖掘和表达,将人们的内心情感和生存状态展现出来,比如在其第二集《黄土地的交响》中谈及民歌《走西口》时,通过解说词和采访阐述了歌曲的传唱背景,呈现了当时农民内心的疾苦和生活的艰难。
另一方面,注重解说词的文学性和知识传递功能。在《民歌魂》中,解说词不仅起到了叙事的作用,也承担背景信息补充的功能,因此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例如,当《黄土地的交响》这一集中《赶牲灵》这首陕北民歌响起时,解说词便开始了叙述和信息补充,形成了一个以解说词内容为“前景”,民歌演唱为“背景”的听觉语言表意方式。由此,《民歌魂》对环境、人文信息和音乐知识的阐释非常依赖解说词,旨在通过解说词向电视受众进行音乐文化事象相关知识的传播。
另外,《民歌魂》中除了采访之外,较少运用到同期声。在技术层面,以民歌的录音棚录制方式取代拍摄现场拾音,并通过后期剪辑,使民歌与画面中拍摄的当地风土人情、当地人的生活生存状态共同构成了一个视听语言系统,展现了民歌生长的土壤,挖掘了民歌与人、环境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国产音乐纪录片的创作也刚刚起步,因此民歌走进音乐纪录片,不仅标志着民歌从“乡野”走上了“殿堂”,而且探寻到了音乐纪录片在民歌阐释和传播上的价值与优势,展现了音乐纪录片创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交汇和碰撞,开启了民歌电视传播的新篇章。
三、主流媒体“民歌热”构建了音乐纪录片的传播格局(2000—2013)
21世纪初,为了配合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的综艺栏目《魅力12》开播,以纪录片的手法追溯中国各地的民族民间音乐的源起与发展脉络,展示音乐在传播传承过程中呈现出的内容和形态上的变化,并通过讲述民歌背后的故事,折射出西部不同民族和地区的人文特质。民歌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的主要符号之一,在21世纪初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呈现出由衰微转为复苏的态势与表征——而这一历史时期,最受社会各界关注和热议的就是“原生态民歌”。2004年,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民歌·中国》栏目的开播,进一步确立了原生态民歌类电视节目的形态及其在中国媒介文化生态格局中的地位。①关于《魅力12》与《民歌·中国》等栏目在展示与传播原生态民歌方面的情况,还可参见朱智忠、通拉嘎《原生态民歌在电视节目中的走势》,载《今日中国论坛》2005年第12期,第42-45页。该栏目在每周二播出的子板块《民歌·寻访》,围绕着民歌、歌手、乐曲、乐器及音乐事件等内容,以纪录片的方式拍摄和记录了民歌及其现实生存状态。除了中央电视台对民歌力推之外,许多地方台如上海东方电视台音乐频道的栏目《海上回音》、内蒙古卫视的栏目《音乐部落》、广西南宁电视台的节目《温飘贝哲》等,都将创作的内容和拍摄的主体对准了民歌资源。2012年,湖北卫视制作播出的14集电视系列纪录片《天籁——寻找中国最美乡野歌声》,以“民歌的文化功能”为出发点,在拍摄所得的民歌素材的基础上,提炼出与中国民歌事象相关的主题,每个主题形成一集音乐纪录片,以民歌的求偶仪式、文化认同、人际关系调谐等多个功能维度架构起中国民歌的全景视听图景。
在这一时期,音乐纪录片在创作和传播上都呈现出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的特征。叙事上的变化使得音乐纪录片在呈现主题时,将民歌及与其相关的事象(歌手、乐器或音乐事件等)纳入全景式的生态环境中来考量,从民族志式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度解读。
以《民歌·中国》2005年播出的电视纪录片《民歌·寻访——李怀秀》为例。节目编导在叙事上构架了两条线索。一是原生态民歌的展示部分,以李怀秀、李怀福姐弟在故乡的田间地头弹起月琴唱起海菜腔为视听内容,并利用景深镜头凸显了歌手与原生环境之间的关系。此外,节目编导和摄像通过主观系统的安排,跟拍李怀秀回乡等一系列事件,捕捉到了李怀秀、李怀福与父亲李云发等家人的相处点滴;拍摄了云南省红河州石屏县彝族的特色民族民间歌舞——烟盒舞;记录了年长的彝族老人(曾经教李怀秀唱山歌的老师)唱民歌——以民族志式的探索方法和电视的影像语言呈现了原生态民歌特有的传承特点。
视听同步化以及对同期声的重视与广泛应用是这一时期音乐纪录片所反映出的重要特征。这与实践领域对同期声在观念层面的认知、对事件的记录和跟拍在表达层面的应用、对声音捕捉和处理在技术层面的提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解说词在纪录片中所占比重较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有明显下降,其在传播知识和承担叙事的同时,抒情性逐步弱化。在纪录片的拍摄中,民歌的演唱部分基本是由话筒进行现场同期声采集的。
这一时期,中国民歌的音乐纪录片传播主要是由电视媒体人和学者发起的,其主要目的一方面是展示、传递知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是对民歌(原生态民歌)面临的严峻的保护与传承形势进行的反思和抢救式的挖掘、整理、收集、传播。而以民歌为主题的音乐纪录片恰好吻合当时的传播需求。与演播室录制民歌这一节目形态相比,音乐纪录片能从田野调查出发,在关注民歌及与其相关事象的同时了解和展现其母体文化、文化生态环境,能巧妙地运用多维度的信息和多元化的视角,解读和传播民歌的核心文化基因。在当时的以城市为中心且由城市向农村辐射的“单向”文化传播模式环境中,音乐传播领域也正经历以流行音乐为中心的传播态势,而主流媒体在电视传播领域掀起的“民歌热”,使得民歌的传播拥有了更大的平台和更高的关注度,从而构建起中国民歌的音乐纪录片传播的格局。
自《民歌·中国》于2011、2012年间改版后,关于音乐纪录片的节目制作和播出量大幅度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带有观众互动的小型演唱会类节目。而且传播内容也发生了转变——原先的主体内容“原生态民歌”被有歌手演唱的“新民歌”代替。
四、媒介生态变迁下民歌的音乐纪录片传播中的文化觉醒(2013年至今)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践行,更加推进了我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基本战略。中国纪录片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开启了国际化传播征程,在2013年至今的发展阶段中获得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并在增强中国文化自信、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②秦瑜明、周欢《纪实观念重构与中华文化传播图景重绘——“联合会杯”中国青年影像创意大赛及高峰论坛综述》,载《南方电视学刊》2018年第1期,第77-78页。此外,“互联网+”理念的提出使得“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迅速融合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急剧改变着中国的媒介生态环境,并且为纪录片在语体、内容、媒介形态等方面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为纪录片注入互联网的基因。在政治、经济、科技等多方因素的合力影响下,纪录片业态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其在创作、(国际化)传播与市场化进程中的突破创新和重新定位也为中国民歌在音乐纪录片中的运用和传播打开了新的篇章。
在此期间,音乐纪录片的创作与传播受到了文化观念迁替的影响。“民歌热”时期,主流媒体对于民歌的传播是认知、展示与保护,其在观念层面多少带着“应该”的设定,但此设定在2013年之后的纪录片创作发展过程中逐渐被更广泛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醒所取代。这种自觉与自醒,建立在厚积薄发的,与国家发展状况吻合的,具备社会、大众基础的,并能与受众产生共鸣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之上。而纪录片的产业化转型与国际化发展,也进一步助推了纪录片在创作思维、思路、主体定位、表现形态和传播媒介、传播受众等方面的探索。若从社会文化背景和媒介生态变迁的场域视角来了解和认知民歌的音乐纪录片传播,则必须重点考量场域的变化所引发的纪录片创作主体、传播的主体与客体在价值观念、思考模式和视角上的变化是如何集中反映在关于民歌的音乐纪录片的创作和传播上的。
比如关于黄河的“母亲河”意象,就作为孕育华夏文明的文化象征符号多次出现在该时期的音乐纪录片中。如2017年6月亮相上海电影节的《大河唱》、2018年在多个国际纪录片节上获得好评的《黄河尕谣》等院线作品,以黄河两岸的民歌作为视听语言的主体,承载了当代中国人关于“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里去?”的哲学思考。而对民歌的生存状态及其折射关联的社会文化变迁的思考,成了创作者通过拍摄音乐纪录片追溯文化根源、思考文化身份的出口。在影像体系中导入中国人的宇宙观和视角是这一时期的以民歌为主题的音乐纪录片在创作和传播上的文化和价值诉求。以音乐纪录片《黄河尕谣》为例,它以“80后”西北歌手张尕怂的个人经历为切入点,展现一个主动学习民歌、传播民歌的青年歌手,于社会文化变迁大背景下在思想、价值观以及歌唱上发生的变化。影片通过民歌、歌手及音乐活动,联结起更广泛的社会、地域甚至生命哲学的议题。
随着媒介生态的变迁,依托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传播的新媒体纪录片的出现及其与民族民间音乐的融合,在国外的纪录片实践领域已有尝试和成果。①采访时间:2018年1月9日下午;采访地点:汕头市龙湖区大南山路3号长江公寓蔡树航家中。例如,法国导演贝利尔·科尔茨(Beryl Koltz)于2015年制播的《声音猎手》(Sound Hunters)是一个以声音(人声、音乐、音响)记录、传播和创作为灵感来源的交互纪录片(interactive documentary),由网站、手机APP和纪录短片交织而成。其中,纪录短片有4则,以4个不同地域为切入点,以人物的故事为线索,讲述了发生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德国柏林、巴西圣保罗、美国纽约等地方的人与声音的故事,其中涉及民族民间音乐的运用与传播。若能把中国民歌的音乐纪录片传播研究置于社会文化变迁、媒介生态变迁的背景下,从音乐学、广播电视学、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等多维视角更进一步对其进行分析与考量,将会为该课题的理论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