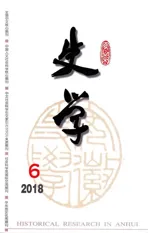宋明儒者的礼教思想及其礼治实践:以宗族思想为中心
2018-01-23周兴
周 兴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400715)
学术界对儒家礼治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对宋代以降出现的宗族研究也成果斐然。但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则较少关注,如陈瑞探讨了徽州宗族依据朱熹《家礼》实践儒家以礼治族等问题[注]陈瑞:《朱熹〈家礼〉与明清徽州宗族以礼治族的实践》,《史学月刊》2007年第3期。,陈支平讨论了朱熹及其后学在宗族建设中的贡献[注]陈支平:《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考察》,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林鹄从宗法、丧服和庙制等外在制度方面探讨了先秦儒家和宋儒的宗族观,认为宗族制度基于儒家伦理思想[注]林鹄:《宗法、丧服与庙制:儒家早期经典与宋儒的宗族理论》,《社会》2015年第1期。,但都没有将宗族建设放到宋明儒者以礼治国的层面来探索。本文将研究重点集中于宋明理学家与心学家指导的宗族建设中对礼教的侧重点不同,进而揭示儒家内部对礼治有何不同的理解。浅薄之见,俟教于方家。
一、宋儒推行宗法的礼制建构
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提出道德政治原则:“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6页。孔子的理想社会是道德价值与礼制融为一体的,又是通过推行礼教实现的。孔子提出这种道德政治原则的依据是西周的宗法社会。宋儒改造唐末五代以来长期遭受战争破坏的社会,所利用的正是西周宗法。
宗法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尊崇共同祖先,在族内区分尊卑长幼秩序,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法则。典型的宗法存在于西周,但“宗法”这一名称却是宋儒提出来的。先秦时期的宗法有其实而无其名,隐藏在周礼之中,通过礼制来表现。[注]晁福林:《周代宗法制问题研究展望》,《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3期。宋儒对宗法的理解来源于经书,与现代学者利用经书与考古资料互证而得出的宗法制有一定差异,本文只据经书简述宋儒所理解的宗法制。宋儒将古老的制度冠以“宗法”之名,表明他们对宗法的现实需要。宗法需要依托一套礼制才能运作,核心是祭礼,嫡长子继承制和宗法的等级名分主要由祭礼来维持。宗法的核心精神是尊祖,而尊祖通过祭祖来表现,宗庙作为祭祖的场所就成为宗法运作的核心设施。庙制有严格的规定,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注]王梦鸥注译:《礼记今注今译》第五《王制》,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241—242、244页。庙制的等级性决定了宗法与分封制融为一体。祭祀需要一定经济基础,即“大夫士宗庙之祭,有田则祭,无田则荐”[注]王梦鸥注译:《礼记今注今译》第五《王制》,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241—242、244页。,这又与井田制直接关联。祭礼的贵族性决定了“礼不下庶人”[注]王梦鸥注译:《礼记今注今译》第一《曲礼上》,第44页。的原则。这一套礼制又与孝道为核心的道德价值发生联系:“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注]王梦鸥注译:《礼记今注今译》第三十《坊记》,第907页。
在汉至唐的千余年里,贵族依赖世官制尚能维持宗法礼制。然而,经过唐末五代以来战争的破坏,贵族制不复存在,宋代实行宗法的社会基础已经被摧毁。宋儒在新的时代环境中推行礼教以改造社会,就意味着如果向庶民阶层推行宗法礼制,就不能不对西周宗法进行改造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因此,如何突破上古“礼不下庶人”的礼教原则并制定出适合于庶人的礼制规范,是宋儒所面对的最大难题。
北宋时期,首先组建宗族的是范仲淹、欧阳修和苏洵等人,苏洵对宗法的认识最为深刻。他在《苏氏族谱》中讲:“观吾之谱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注]苏洵:《嘉佑集》卷14《苏氏族谱》,《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48页。他视族谱为“孝悌之心”产生的根据,关注的是宗法的道德价值。另一方面,他又讨论了宗法的制度问题,在《族谱后录上篇》中讨论了小宗[注]苏洵:《嘉佑集》卷14《族谱后录上篇》,第950—952页。,由于“《苏氏族谱》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未及大宗也”[注]苏洵:《嘉佑集》卷14《大宗谱法》,第954页。,又作《大宗谱法》,意图提供振兴宗法的途径。苏洵所论的大、小宗法只是大宗与小宗的区分原则,没有谈及改造礼制的问题。他提出了复兴宗法以改造社会的图景,但没有认识到祭礼与宗法的深层联系,也没有提到改革礼制的问题。
张载、程颐等理学家推进了对宗法的认识。张载提出组建宗族的原则:“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注]张载:《经学理窟·宗法篇》,《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58、259、259—260页。张载对宗法的秩序和价值两个层面之间联系的认识已经很深刻了,依其逻辑,道德价值奠基于道德秩序,“管摄天下人心”是从道德价值的层面讲,“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是从道德秩序的层面讲。改造宗法制实质是革新上古礼制,张载认识清晰:“言宗子者,谓宗主祭祀”[注]张载:《经学理窟·宗法篇》,《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58、259、259—260页。,因此改造祭礼就成为关键。上古宗子主祭难以行于后世,张载主张加以变通:“宗之相承固理也,及旁支昌大,则须是却为宗主。……至如人有数子,长者至微贱不立,其间一子仕宦,则更不问长少,须是士人承祭祀。”[注]张载:《经学理窟·宗法篇》,《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58、259、259—260页。在张载看来,礼教的推行与宗族建设是一体的:“祭接鬼神,合宗族,施德惠,行教化,其为备须是豫,故至时受福也。”[注]张载:《经学理窟·祭祀篇》,《张载集》,第293页。
程颐继承了张载的宗法思想,又在张载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祭礼的制度问题,提出:“自天子至于庶人,五服未尝有异,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须如是。其疏数之节,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注]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15《伊川先生语一》,《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63页。程颐明确提出了要将祭礼推行于庶民阶层,且庶民应当享有与天子同等的祭祀权。他用以突破礼教贵族制原则的是理学,这为宗法推向庶民阶层实现了理论上的突破。他又明确指出:“时祭之外,更有三条: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祢。他则不祭。”[注]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18《伊川先生语四》,《二程集》,第240页。程颐提出祭始祖、先祖,这是大宗祭祖之法,为庶民组建大宗提供了礼制上的支持。
朱熹的《家礼》在制礼实践上打破了礼教的贵族制原则,突出表现在祠堂制度。朱熹的祠堂制度遵循小宗,可能是当时形势不允许立大宗:“大宗法既立不得,亦当立小宗法。”[注]黎靖德:《朱子语类》卷90,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308页。但是其目的是大宗,他在理论上也为立大宗留下了空间。[注]常建华认为朱熹《家礼》为大宗提供了方案,井上彻也认为朱熹在礼制上意在复兴大宗。参见常建华:《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1页;[日]井上彻著、钱杭译:《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从宗法主义角度所作的分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99页。他还对制定祠堂制度的意义作了深入阐述:“此章本合在《祭礼》篇,今以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守,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后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相背之曲折,亦有所据以考焉。然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注]朱熹:《家礼》卷1《通礼》,《朱子全书》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875页。朱熹认为设立祠堂是宗族礼制“先立乎其大者”。他明确指出祠堂是承上古庙制而来,而之所以命名为祠堂,不仅因为“古之庙制不见于经”,还因为“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礼不下庶人”的原则依赖于庙制而存在,朱熹避免使用“庙”这一名称,暗示祠堂通用于士庶,在礼制上突破了“礼不下庶人”的局限。通过在祠堂举行冠婚丧祭等礼仪,宗子在族内的统率地位显示出来,宗法原则得以贯彻,故而,在《家礼》中宗法的运行依托于祠堂的礼制。因此,朱熹设计的祠堂制度标志着宗法礼制重构基本完成。
应指出的是,程、朱等理学家在理论上重视宗法的外在秩序。程颐说:“只有一个尊卑上下之分,然后顺从而不乱也。若无法以联属之,安可?立宗子法,亦是天理。”[注]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18《伊川先生语四》,《二程集》,第242页。倾向于以等级秩序为天理。他又在解释《易》履卦时说:“礼,人之所履也。为卦,天上泽下。天而在上,泽而处下,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当也,礼之本也,常履之道也,故为履。”[注]程颢、程颐:《周易程氏传》卷1《周易上经上》,《二程集》,第749页。认为“上下之分,尊卑之义”是“礼之本”,说明他重视礼的等级秩序。朱熹也同样如此,他解释“齐之以礼”:“齐之以礼者,是使之知其冠婚丧祭之仪,尊卑小大之别,教人知所趋。”[注]朱熹:《朱子语类》卷23,第549页。将礼理解成等级制度。正如陈来所论,朱熹强调伦理关系作为外在规范对人的制约作用。[注]陈来:《朱熹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1页。《家礼》的礼制设计中完全贯彻了朱熹的理论主张。
在宋代,从苏洵等人提出复兴宗法开始,程颐在理论上以理学思想突破了宗法的贵族制原则,而朱熹在礼制实践中新创祠堂制度彻底打破了这一原则,最终完成了对宗法的礼制改造,使之能推行于庶民阶层。
二、宋、元、明理学家的礼治实践
在朱熹之后,儒者着重于推动儒学思想的文化转型,实现儒家道德价值的社会功能[注]何俊、范立舟:《南宋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页。,致力于推行宗法、组建宗族是他们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朱熹就已经开始了推行宗法的社会实践。据常建华考证,今存《唐桂州刺史封开国公谥忠义皇公祠堂记》当属朱熹轶文。[注]常建华:《宋以后宗族的形成及地域比较》,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朱熹认为:“创之者尔祖也,后之人可无念尔祖乎?然念之者无他,祖庙修,朔望参,时食荐,辰忌祭,云礽千亿,敦睦相传于不朽云。”[注]朱熹:《唐桂州刺史封开国公谥忠义皇公祠堂记》,转引自常建华:《宋以后宗族的形成及地域比较》,第33页。这里“念尔祖”即是尊祖,尊祖是宗法的基本原则,尊祖才能收族。朱熹认为尊祖收族是通过推行祭礼来实现的。
至元代,儒者在政治上仕进的机会较少,更加重视基层社会的宗族建设。理学家吴澄精于礼学,他对祠堂与上古家庙的关系颇有考究:
爵之为公侯伯子男,官之为卿大夫士皆有庙,以奉其先,古制然也。……秦汉而下,惟宋儒知道。河南程子始修《礼略》,谓家必有庙,必有主。而新安朱子损益司马氏《书仪》,撰《家祭礼》,以家庙非有赐不得立,乃名之曰“祠堂”。古者庶人荐而不祭,士无田亦然,盖度其力之有不足故尔。遵朱子《家礼》而行,亦惟荐礼而已,视古祭礼为简。然古之卿大夫士祭不设主,庶士之庙一,适士之庙二,卿大夫亦止一昭一穆,与太祖而三。今也下达于庶人,通享四代,又有神主,斯二者与古诸侯无异,其礼不为不隆。[注]吴澄:《吴文正集》卷46《豫章甘氏祠堂后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482—483、483页。
吴澄明确地指出古庙制与朱熹所定祠堂制度的区别,祠堂祭礼的仪文较古祭礼甚简,只相当于上古荐礼而已。然而,祠堂之制下达庶人,而可祭四代并设神主,其规格之隆“与古诸侯无异”。对于这样简且隆的礼制,吴澄是持支持态度的:“予谓奉先之礼,孝子慈孙之所当自尽者,奚以人之言为哉?虽然,礼久废之余,而君之好礼甚非其质之得于天者厚而然与?非其识之超于人者远而然与?”[注]吴澄:《吴文正集》卷46《豫章甘氏祠堂后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第482—483、483页。可见,他对于朱熹改造上古祭礼是认同的。可以说,吴澄对朱熹《家礼》改造礼制的看法基本代表了多数儒者的态度。
从总体上说,宋元儒者对宗族外在秩序的要求没有后世那么严格,理学对宗族的渗透也没有后世那么深。[注]常建华:《宋以后宗族的形成及地域比较》,第88页。明初,统治者将程朱理学确定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儒者推行礼教的实践也基本依据程朱理学是不争的事实。朱鸿林注意到,士人致力于《大学》八条目之一的“齐家”是明代前期的一种学术趋势[注]朱鸿林:《儒者思想与出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55、59页。,他认为这“显示越来越多士人将理学的价值和观念,贯彻到地方社会组织的努力”。[注]朱鸿林:《儒者思想与出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55、59页。理学家贯彻的是理学的何种价值和观念?
明初,宋濂是重视宗族建设的学者。他明确提出宗法的等级制度是孝悌等道德价值的来源:“故宗法立,则名分正;尊卑序,则孝悌生焉。”[注]宋濂:《金华施氏宗谱序》,龚剑锋等:《宋濂诗文拾遗(一)》,《文献》1993年第1期。宋濂还直接参与了推行宗法的实践,帮助浦江郑氏修订了《郑氏规范》,将宗法的制度规范贯彻于郑氏宗族成员的日常生活。如规定宗子管理祠堂:“祠堂所以报本,宗子当严洒扫扃钥之事。”[注]费成康主编:《中国的家法族规》附录《浦江郑氏义门规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69页。宗子对宗族的责任是:“宗子上奉祖考,下壹宗族。”[注]费成康主编:《中国的家法族规》附录《浦江郑氏义门规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69页。这些规定明确宗子主祭权,以凸显其在宗族内部的地位。
《郑氏规范》在明代影响非常大,理学家曹端撰写《家规辑略》,就参照了《郑氏规范》。他对义门郑氏评价非常高:“自今观之,江南第一家义门郑氏,合千余口而一家,历千余岁而一日,以其贤祖宗立法之严、贤子孙守法之谨而致然也。”[注]曹端:《曹端集》卷4《家规辑略序》,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81页。他从《郑氏规范》的168条中择取94条,并根据自家实际情况增加52条,分为祠堂、家长、宗子、诸子、诸妇、男女、旦朔、劝惩、习学、冠筓、婚姻、丧礼、推仁、治蚕等14篇,将祠堂置于首要位置。在《家规辑略》中,宗法的尊卑秩序强化了。
宋濂弟子方孝孺也非常重视宗族建设。侯外庐注意到,方孝孺将“齐家”置于治国的根本,并认为“这在理学家讲内修外用当中是一个古怪的思想”。[注]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下),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方孝孺作《宗仪九首》,其中尊祖、重谱、睦族三首讨论了宗族组织。祠堂祭祖放在尊祖篇中,他主张立大宗:“立祠祀始迁祖,月吉必谒拜,岁以立春祀。”[注]方孝孺:《逊志斋集》卷1《宗仪九首·尊祖》,宁波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方孝孺也重视宗法的人伦秩序:“盖闻谱者,姓名之经纬,昭穆之纲纪,导一宗之根源,提九族之总统。人伦根蒂,君子贵之。”[注]方孝孺:《逊志斋集》卷13《族谱序》,第426页。
明初政治家杨士奇也非常重视宗族建设。在他看来,族谱是宗法遗法的载体:“天下之治本于亲亲,故先王之世特重宗法。后世宗法废,士君子笃意于谱牒,盖亦先王之遗法而敦本之道也。谱牒明,然后源本不昧,疏戚不紊,而孝友慈睦出于仁爱之良心者,自不容于己矣。”[注]杨士奇:《东里续集》卷13《丰城李氏族谱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第527页。杨士奇强调,编撰族谱的功能在于明确宗族的秩序:“族谱之作,所以明世次,别疏戚,著其所自出,而表先烈、启后昆之意亦具乎其中。”[注]杨士奇:《东里续集》卷12《玉山李氏重修宗谱序》,第521页。
宋、曹、方、杨等人作为明初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强调宗法的等级制度,体现了明初宗族建设中强化外在秩序的趋势。明代前期,由于社会动乱因素的增加,儒者更加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这表现在他们对宗族建设的理论指导中对宗法等级秩序的僵化。在明代前期的重要学者中,王直撰写的族谱序跋达50多篇,绝大多数都强调宗法秩序,如:“夫谱,所以明昭穆、辨尊卑,使亲睦而无间,惇序而不紊也。”[注]王直:《抑菴文集》卷5《竹山陈氏族谱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6册,第99页。理学家薛瑄也强调宗法秩序:“故士君子有志于复古者必修其族谱,纪世次,序疏戚,使其为子若孙者得有所考据,而知所自来,虽五服之渐穷,亦不忘水木本源之义,而亲有未尽者益敦其孝敬慈爱之心,此族谱之作,亦古宗子之遗法而有关于家道人伦为甚重也。”[注]薛瑄:《敬轩文集》卷17《廖氏族谱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3册,第300页。邵宝企图借族谱造就稳定的社会秩序,并将其提升到关乎天下之治的“王道”层面:“凡谱为家作也,其要在辨族姓、序昭穆、明冢介嫡庶而家政行焉。故天下之家,各谱其谱而王道成。谱之于世,其亦可谓重矣。”[注]邵宝:《容春堂前集》卷13《林氏族谱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8册,第143页。
明前期,对于宗法的总体看法可以举丘濬为例。丘濬撰写的《家礼仪节》宗法思想非常有代表性,在明代“几成为与朱子《家礼》并行的新经典”。[注]赵克生:《明代国家礼制与社会生活》,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00页。在上呈给明孝宗的《大学衍义补》中,他花了5卷叙述《家乡之礼》,核心是讨论宗法制的可行性方案。他说:“古者设官以奠系世,唐以前皆属于官,宋以后则人家自为之。……然朝廷无一定之制,人家兴废不常,合散不一。或有作者于前,而无继者于后。请为之制,除贫下之家外,凡有仕宦及世称为士大夫者,不分同居异籍,但系原是同宗,皆俾其推族属最尊者一人为宗子,明立谱牒,付之掌管。”[注]丘濬:《大学衍义补》卷52《家乡之礼》,《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2册,第626—627、623、629页。他指出了当时宗族建设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即私家修谱难以为继,建议朝廷为私家修谱确立一定的制度,使宗族通行于天下。丘濬曾言:
若夫见任文臣及仕宦人家子孙与夫乡里称为大族巨姓自谓为士大夫者,朝廷宜立定制,俾其家各为谱系,孰为始迁于此者,孰为始有封爵者,推其正嫡一人以为大宗。又就其中分别某与某同高祖,推其一人最长者为继高祖小宗。某与某同曾祖,推其一人为继曾祖小宗。某与某同祖,某与某同祢,各推最长者一人以为小宗。其分析疏远者,虽不能合于一处,然其所以聚会于一处,缀列于谱牒者,则粲然而明白也。若夫军官袭替故事,明具宗支图,亦俾其明白开具如五宗之法。若其正支绝嗣,而以旁支入继者既袭之后,即将其名系于所后正支之下,以承大宗,而以其次弟承所生父母以为小宗。[注]丘濬:《大学衍义补》卷52《家乡之礼》,《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2册,第626—627、623、629页。
丘濬改造宗法制度,优先实行大宗,并根据情况可以实行四种小宗,为“五宗之法”。这种宗法制度如灵活运用,只要是共同祖先的族人聚居,不论同多少世祖都可以成宗。另外,如果人口迁徙,只要“聚会于一处”,也可修谱立宗收族。丘濬的宗法方案还考虑了人口迁移的因素,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丘濬著《大学衍义补》是为明王朝提供可行的治国方略,就其宗法方案看,切实可行,确是整治社会的良策。
丘濬作为实学家,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整治社会秩序。从“家乡之礼”的内容看,强调族内的等级名分是主调。他制定的宗族礼制非常全面,连族人称谓都花大量篇幅介绍,并强调:“人家亲属称呼乃人伦之大纲,名正然后言顺,言顺然后上下相安,而可以致肃雝之化,非细故也。”[注]丘濬:《大学衍义补》卷52《家乡之礼》,《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2册,第626—627、623、629页。这是将程颐“名分正则天下定”[注]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21《伊川先生语七》,《二程集》,第276页。理论运用于整治社会的方案。张学智指出:“在礼乐的诸功能中,丘濬最重视的是礼的别尊卑贵贱,定人之伦序,从而使整个社会和谐有序这一点。”[注]张学智:《中国儒学史·明代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76页。就丘濬的政治地位及其书产生的影响而言,其宗法主张必然影响深远,由此可见,儒者在明代前期推行礼教强化等级秩序的努力是空前的。
全面考察明代前期的族谱序跋,不难发现昭穆、尊卑、长幼等得到反复强调,表明宗法等级秩序的贯彻是强有力的,礼教的推行偏向于道德秩序,而道德价值却遭到忽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程朱理学的理论倾向所致。理学家的礼教实践侧重于发挥儒家道德政治原则“齐之以礼”的一面,他们将天下太平主要寄托于稳定的社会秩序。冯尔康等学者认为明代宗族对族人的外在制约更加严格,族谱也明显带有政治化的倾向。[注]冯尔康等著:《中国宗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5—249页。如果撇开心学不论,此点是可以成立的,这是理学家追求礼制秩序社会运用的结果。
三、明代心学家的礼治实践
明代理学士大夫推行的礼教渐渐走向僵化了,正如葛兆光所论:“经过长时期意识形态的制度化过程,理学已经失去了当初那种拯救心灵、批判权力和建设秩序的意义,成了空洞的道德律令和苍白的教条文本,应当有一种活泼泼的思想来更新这个时代。”[注]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5页。这里所说“活泼泼的思想”就是心学。那么,心学是如何指导宗族建设的,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明代心学家对于宗族建设大多较为踊跃,他们推行宗族建设的礼制文本仍然基于朱熹的《家礼》。如陈献章就称赞新会县知县丁积“参之文公冠婚丧祭之仪,节为《仪节》一书,使民有所据守。”[注]陈献章:《陈献章集》卷1《丁知县行状》,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2页。王阳明也明确表示:“承示《谕俗礼要》,大抵一宗文公《家礼》而简约之,切近人情,甚善甚善!……故今人为人上而欲导民于礼者,非详且备之为难,惟简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为贵耳。”[注]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6《寄邹谦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1页。可见,明代心学家对《家礼》是基本认可的,只是要依据时代变化而进行修改以便于推行而已。然而,心学家所认为的礼的内涵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礼教的理论导向也随之而变,进而影响到其宗法理论。
陈献章阐发了祠堂祭祖的重要意义:“古圣贤以民德归厚,必曰‘追远’……庙始迁之,祖而祭之,古之制不可考已。君子随时变易,以不犯其分而得其心。盖人情出于天理之不容己者,夫何嫌欤?”[注]陈献章:《陈献章集》卷1《增城刘氏祠堂记》,第43页。他认为,上古祭礼“不可考”,但礼制可以“随时变易”,重要的是“得其心”。因此祠堂祭祖的目的是整合人心,“贫贱不薄于骨肉,富贵不加于父兄,宗族者谁乎?故曰:收合人心,必原于庙。”[注]陈献章:《陈献章集》卷1《增城刘氏祠堂记》,第43页。陈献章将宗族建设的理论指导转向了整合人心,为明代宗族建设指出了新方向。
陈献章弟子湛若水则更为明确:“王者之风衰而封建废,封建废而宗法亡,宗法亡而后谱作。故谱者存宗法以教仁孝于天下也。今夫人惟不知身之所自出,则不知敬其父以及其祖,而孝道几乎息矣。人惟不知身之所同出,则不知爱其兄弟以及其同气于祖者,而仁道或几乎息矣。是故夫谱者,以明仁孝之道者也。”[注]湛若水:《甘泉先生文集内篇》卷8《南海梁氏族谱序》,《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83册,黄山书社2015年版,第299页。他将族谱的功能定位在“存宗法以教仁孝于天下”,认为宗法的外在制度虽然不存在了,但其所蕴涵的仁道可以凭借族谱而推行于天下。如果说陈献章所谓“收合人心”显得较为笼统的话,那么湛若水要求“明仁孝之道”就将仁道具体化了。
明代心学中,阳明后学是宗族建设的重要力量。张艺曦探讨了王学与宗族的关系,对江西吉安府的王学兴盛与宗族进行了微观考察,发现依靠宗族关系网络比利用书院讲学的方式更成功地实现了王学的草根化;另一方面,王学对宗族提建设供理论指导,这种理论是“一体说”的学术思想。[注]张艺曦:《阳明学的乡里实践: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1—217页。最早提出“一体说”理论的儒家思想家是程颢,“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注]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2上,《二程集》,第16页。王守仁对此进行了充分阐释:“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注]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26《大学问》,第1066页。由此可见,“一体说”实际是儒家仁道的另一种表述。因此,王守仁与湛若水指导宗族建设的理论在根本精神上是一致的。张艺曦主要考察了王门学者如何通过修谱联宗和解决族内的具体事务。[注]张艺曦:《阳明学的乡里实践: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第211—217页。但是,心学家如何利用“一体说”指导宗族建设?与理学家的理论指导相比,有何根本差异?已有的研究尚未论及,下文将讨论这一问题。
王守仁作为明代心学的领军人物,对宗族的看法具有指向性。他阐述族谱的功能道:“谱之作也,明千万人本于一人,则千万人之心当以一人之心为心。”[注]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32《新安吴氏族谱序》,第1321页。所谓“明千万人本于一人”是以“一体说”对宗族的理论解释。他又讲:“子孝父,弟敬兄,少顺长,而为父兄长者亦爱其子弟。”[注]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32《新安吴氏族谱序》,第1321页。朱熹认为收族是通过祭礼实现的;而王守仁则认为收族是通过族人对孝悌等道德价值的践履实现的。在此,王守仁对宗族提出了心学的理论解释。然而“一体说”如何落实,他并没有提出具体途径。而王门后学在此问题上有所讨论,如王畿讲:
按凡例,修国史者必知《春秋》之义,然后可以明王道而正国体;修家乘者亦当知《春秋》之义,然后可以明人伦而正风俗,可谓得其意矣。予谓欲明《春秋》之义,莫先于辨是非,究明一体之学。良知者,是非之公,自圣以至于塗人皆所同具。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良知者,天地之灵气,原与万物同体,手足痿痹则为不仁,灵气有所不贯也。……今夫聚族而居,父子、伯叔、兄弟咸在,出入则同吉凶,庆吊则同序,事则同堂,会食则同席,由是而及其所自始一体相授,俨然如将见之,以其谱之存也。[注]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卷13《太平杜氏重修家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98册,齐鲁出版社1997年版,第513页。
王畿将修谱比作修国史,要求修谱者“知《春秋》之义”。而蕴含于族谱中的“《春秋》之义”就是“一体之学”。引文前半段是对“一体之学”内涵的解释,后半段要求族人“出入则同吉凶,庆吊则同序,事则同堂,会食则同席”,则是“一体之学”落实到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途径。王守仁的“一体说”还落在抽象的观念层面,王畿明确要求落实到族人具体的日常生活层面。
王门后学的许多学者有将仁道落实到日常生活的要求,其中江右王学最有深度。欧阳德对宗法有着深刻的认识,“夫谱之为教,兴孝以缵祖,兴让以睦族,振德励行,引宗人于道,此其大致也。”[注]欧阳德:《欧阳德集》卷20《永丰聂氏族谱序》,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526页。明确提出族谱是要“引宗人于道”。他又说:“其法不知何所始?意古者九职之民皆联于比闾族党,使之困穷相赒,患难相救,善相劝,过相规,恶相纠,相生相养,相亲相睦,以美其俗。公卿之族,下不列于齐民,上不可以无所统。故联之以大宗、小宗,以行其赒、救、劝、纠之义,以成其生养亲睦之仁。”[注]欧阳德:《欧阳德集》卷23《董氏立宗子记》,第597页。欧阳德虽然也讨论宗法问题,但对宗法的礼制毫无兴趣。他认为宗法的目的是达成儒家的仁义之道,所谓“引宗人于道”就是要将仁义之道推行到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来。
聂豹赋予族谱以“人道之典籍”的地位:“夫谓征而传者,谱特人道之典籍耳。……惟人道为能永世。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而仁义之实,莫大乎君亲。”[注]聂豹:《聂豹集》卷3《恩江张氏重修族谱序》,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页。他提出族谱的功能在于“立人之道”,即确立仁义之道。他还讲:“天地不仁,则乾坤毁;人不仁,则族散宗离。是故谱学所以继宗法之亡也。……仁以结之,礼以维之,疾痛痾痒,皆切于吾身,于是贫穷者有养,患难者有恤,鳏寡茕独者有所归。”[注]聂豹:《聂豹集》卷3《上濠汤氏族谱序》,第68页。他提出族谱要继承宗法所蕴涵的道德价值,具体是使仁义之道真正落实到民众的现实生活之中。他所谓“立人之道”,指向的是有道德关怀的现实生活。
明代心学家很少专文讨论宗法问题,而罗洪先撰写了三篇论宗法的文章,从中可以一窥心学家对宗法的看法。罗洪先否定了宗法的现实可行性:“盖言宗法为公族卿大夫设也。诸侯之始封也,有人民、社稷之寄,有朝觐、聘享、祭祀、省助之政,势不能自领其宗,而公族无统,国人不可得而治也。诸侯绝宗,大夫不可得而祖也。”[注]罗洪先:《罗洪先集》卷2《宗论》,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37页。他认为宗法建立在分封制之上,只为贵族而设立,庶民不可行宗法:“宗法尽于此,则知庶人以下无宗法,又可知矣。”[注]罗洪先:《罗洪先集》卷2《宗论》,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37页。所以他对宗法的现实可行性持否定态度:“宗法不可行于今者有三:封建不可复举,学校不复修,井田不复制。其不可行者,势也。”[注]罗洪先:《罗洪先集》卷2《宗论》,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37页。
既然罗洪先认为宗法不可行,那么他在理论上如何指导宗族建设?他讲:“封建废,卿大夫无世家矣。无世家,则宗法不可得而复;于不可复之时,而存什一于千百,岂不难哉!取其意稍可行于今,惟族谱近之。”[注]罗洪先:《罗洪先集》卷12《安成华秀彭氏族谱序》,第523页。他认为宗法虽然不可复兴,但修谱可以“取其意稍可行于今”。他所谓宗法之“意”指什么?他论述道:“惟昔圣人教家,既为之鼓舞其辞矣,然大要自其少时习为长幼、礼容、俎豆、诵说之节,以淑其性行;俟其既长,使之出而治民,以行其所知;及倦而归,则训于里门以溥利于乡党。其材能下者,躬耕孝养,而出其赢以佐人之急。……盖立人之道,莫大于此。”[注]罗洪先:《罗洪先集》卷12《乐安湖平王氏族谱序》,第533页。在他看来,宗法之“意”是指“人之道”,即以仁道原则为基础的现实生活,宗族建设的目标是在现实社会中“立人之道”;而宗法的外在制度不过是没有实质意义的虚套。
不难看到,罗洪先意在抛开宗法的制度外壳,而取宗法内在的道德价值并推行于社会。他将宗族建设定位于“立人之道”,而所谓“人之道”是将儒家的仁道原则贯彻于族人的日常生活。王守仁曾讲:“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注]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2《答顾东桥书》,第51页。罗洪先的“人之道”体现了王学“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的学术要求。从这个角度讲,“立人之道”是良知学说的社会建设实践。
可以说,王门后学的诸多重要学者不满足于仁义仅流于抽象的观念层面,而有将儒家仁道贯彻于现实生活的要求,体现了罗洪先“立人之道”的目标。王守仁并非不重视宗法的等级秩序:“察统系之异同,辨家承之久近,叙戚疏,定尊卑,收涣散,敦亲穆,胥于谱焉列之。”[注]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32《重修宋儒黄文肃公榦家谱序》,第1324页。宗族内部的尊卑等级仍然很重要,但王门后学很少提及了。在他们看来,宗法外在的礼仪制度对于民众来说没有实质意义,而民众在现实生活中切实受惠于仁道才是宗法根本精神的体现,也是其指导宗族建设的总体目标。
如果说理学家在礼教实践中侧重于礼制秩序的建设,那么心学家则突出道德价值体系在社会的真正落实。与理学家倾向于“齐之以礼”相比,心学家则倾向于“道之以德”的一面,他们将国家的长治久安主要奠定在牢固的社会价值体系基础上。
余 论
《大学》作为四书之一,高尊地位是宋儒奠定的。《大学》的八条目中,齐家是关键一环。《大学》构建八条目的历史根据是西周家国同构的国家形态,侯外庐指出,上古国与家是结合的,家族保留在邦国里面。[注]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宋明儒者赋予“齐家”新的内涵,并借此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标。那么,宋明儒学所谓“齐家”新的内涵何在?
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注]张载:《拾遗·近思录拾遗》,《张载集》,第376页。用现代语言可理解为:“为社会重建道德价值,为民众确立生命意义,为前圣继承已绝之学统,为万世开拓太平之基业。”[注]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32页。横渠四句是理学家和心学家担当社会责任的共同追求。与功利主义儒学注重富国强兵的短期效应有别,理学和心学都企图建立起天下万世太平之基业。其途径都是在基层社会推行礼教,建立社会礼教体系。宋明儒者改造和利用上古宗法来组建宗族,使宗族作为国家稳定的根基,也成为落实礼教的承载者,从而达到整治社会的目的,这是“齐家”的新内涵,以礼治国也在“齐家”的过程中得到贯彻。
如上文所述,理学侧重于“齐之以礼”的一面,心学突出“道之以德”的一面,这种差异根源于二者学术理论上的分歧。孟子讲:“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注]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1页。孟子认为实施仁政最重要的是孝悌等道德价值的奠立。与理学相比,心学的宗族思想显然更接近孟子的仁政。
理学和心学的礼教实践都产生了一定流弊。明代理学家的礼教实践逐渐失去活力,社会生活中等级名分的过度强调导致了严重后果。清代学者戴震批判:“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天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之同欲达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者之罪,人人不胜指数。”[注]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页。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是程朱理学重视尊卑秩序的理论倾向使然。心学家的社会礼教实践也有弊病。钱穆指出,王畿等人的讲学,一面是讲各自的良知,反身即得,一面是讲万物一体,当下即圣人,听者多且杂,讲得又简易,遂有所谓伪良知。[注]钱穆:《宋明理学概述》,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92页。这样的弊病在宗族建设中亦难以避免。心学家宣扬高昂的道德精神却缺乏相应的规范来保证,最终流于伪善是难免的。宋明儒者在推行社会礼教时,都难以取得道德价值与道德秩序之间的平衡。这一课题在当今文化建设中依然有着重大价值,值得我们继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