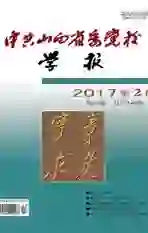同一性与多样性:理解政治的一种新方式
2017-10-20韩毅
韩毅
〔摘要〕 自然科学式的研究方法以及二元对立的政体观是现代人对政治理解面临的两大困境。自然科学式的研究方法存在三个问题,即研究对象的适宜性较差、价值判断不可避免以及较易产生价值偏见,而二元对立的政体观则会将人带入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激进结构。解决这些困境可以借用同一性与多样性理论,即对亚里士多德的混合政体与现代的二元分类方式进行融合,并以此从相对平和、平等的立场看待不同的政体模式。就其根本而言,同一性与多样性的政体都具合法性,不应有所偏颇。
〔关键词〕 同一性与多样性;政治;二元对立;政体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17)02-0023-10
现代人对政治的理解面临两大困境,即自然科学式的研究方法以及二元对立的政体观。在这种困境的作用下,一些人将西方自由民主制奉为不容有任何质疑的政治正确,从而难以公正客观地看待西方自由民主制以外的其他政治体制。面对这种咄咄逼人且颇为偏颇的局面,我们不仅要对自然科学式的政治学以及二元对立的政体观进行批判,还应该从同一性与多样性的角度对亚里士多德式的古代政治学进行一定程度的综合分析。如此一来,现代人或许能够战胜激进和偏见,从而汲取古代人的智慧,避免在政治领域走极端。
一、自然科学式的政治
自然科学在现代社会的蓬勃发展,使人类开始迷信于人的力量,历史进步论、进化论和人定胜天等论调成为现代人的时代主题。当人类意识到自身理性可以把握、发挥甚至改造自然界以为我所用时,对神圣性的崇拜就面临危机。人既然可以制天,又何须敬神?那些建立在神圣基础上的道德和价值大厦迅速松动。对现代人而言,“子曰”或“耶稣曰”不再具有自明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先哲和神明的规诫都需要被后人以自然科学的方法证明。由此,现代人展开了在人文领域追赶自然科学的尝试。这种尝试的核心是把那些原本交错繁杂的关于人的学问分门别类,逐一自然科学化。这一历史背景不仅促使各种冠以科学后缀学问的产生,还为人文社科领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人文社科这个大框架内,本文主要从政治学视角进行探讨,这既是因为政治学是“最权威的科学或最大的技艺的对象……制定着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法律,它的目的就包含着其他学科的目的” 〔1 〕5-6,也是因为现代与古代研究方法的对立在政治学中最为明显。
古代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是政治哲学,其精神可以由价值判断来表达。海伍德认为:“这涉及人们对伦理、规定性和规范问题的关注,显示出关心‘应然、‘必然或‘必须的命题,而不是‘实然命题……尽管此类分析可能是审慎和严谨的,但在任何科学意义上都是不客观的,因为它们所处理的是规范性问题。” 〔2 〕15-16
现代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是政治科学,其内在精神是价值无涉。政治哲学的式微与政治科学的崛起都与自然科学方法被推崇为揭示真理的唯一可靠途径密不可分。政治科学探索“实然”层面的问题,并且希望在政治领域找到可以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定理和规律。海伍德观察到,人们对政治成为科学的热忱,到20世纪50-60年代达至巅峰,当时,尤其是美国,出现了一种相当倚重行为主义的政治分析方法;行为主义提供了此前所欠缺的东西——验证假设的客观且量化资料,政治第一次有了可靠的科学性证明 〔2 〕17。
政治科学虽然逐渐取代了政治哲学,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方法,但是这种自然科学式的理解习惯存在三个问题:
首先,研究对象的适宜性较差。自然科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截然不同,前者主要研究自然界可以观测、量化和实验的事物,后者顾名思义是为了研究人及其政治生活。人的内心无从窥测,行为也不能做重复性的实验。此外,人与人之间的诸多联系、互动和反应则更具随意性。所以,我们对人及其政治活动的理解无法做到全面、深入和客观。我们可以对人的政治活动有一百种不同的假設,却很难获得可靠准确的资料来支持其中任何一种。如果一定要在不牺牲科学方法的前提下研究政治的话,人们只能专注于那些类似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政治事务,比如投票。如此一来,政治研究的视野就会被方法限制,无法摆脱削足适履的嫌疑,从而沦为一种关乎细枝末节的学问。然而,人们一旦对自然科学方法的坚持有所动摇,现代意义的政治科学就会回归到古代的政治哲学。毕竟政治哲学从未与自然科学的方法全然对立,但政治科学却与一切非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决裂。
其次,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如果说政治哲学模糊了事实与价值,那政治科学就是坚持对二者进行切割。但是,政治领域中的事实与价值往往紧密相联,比如自由民主制就既有事实也包含价值。而且,政治研究者的所有行为和观点无不受其预设立场的影响。这种立场有多种多样的来源:意识形态、家庭教育、人生阅历、社会地位及个人偏见无不蕴含其中。由于偏见和预设立场在人的价值判断中无所不在,所以人们常常不能自知,反而觉得稀松平常。正如孔子所言:“人莫不飲食也,鲜能知味也。” 〔3 〕19换言之,绝对的价值无涉和科学客观在政治学中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或许正是由于古代人对人类理性能否认识绝对客观的真理有所保留,所以孔子和苏格拉底才会强调无知之知,即“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3 〕58,“我是智过此人,我与他同是一无所知,可是他以不知为知,我以不知为不知” 〔4 〕。现代人之所以胜过古代人,并不是现代人在实质上克服了人类固有的偏见和价值判断,而是现代人能在形式上对价值判断的存在予以否认和忽略,从而将自身的偏见和价值变为唯一正确可靠的真理。
再次,较易产生价值偏见。现代人强调绝对客观、价值无涉及价值中立,并且否认价值判断在科学方法中的存在——这些观点无疑是价值判断最武断的形式。在关乎人的领域内,价值判断几乎不可避免。现代人虽然旨在规避古代人缺乏客观性之失,却因否认自己同样有主观判断的可能,而与其孜孜以求的科学精神失之交臂。现代人反而是在借科学和客观之名,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包装成唯一的绝对真理。这种形式的价值判断,具有成为意识形态和宗教的标准:“简洁明了,逻辑性强;有很强的排他性和进攻性;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及可信的实现手段。” 〔5 〕事实上,现代人的价值判断往往是在二元对立角度上展开的:一切与现代价值相左的事物都被冠以价值判断、主观、感性、落后、古代、非科学、专制等字眼,一切现代价值认同的事物都被称为价值无涉、客观、理性、进步、现代、科学、民主。与古代人不同,现代人精致的价值判断以科学方法和价值无涉为其左膀右臂。一方面,他人无法在既有框架内提出任何有关价值和规范的问题,因为科学方法否认价值和规范在其体系内的存在。另一方面,一旦以超出科学方法的框架来审视价值问题,就会成为反科学、反客观和反理性的众矢之的。这样的双保险使科学方法自带默认现状和现有价值的内在基因。
实际上,科学方法在政治研究中的一大用途就是拥护民主的制度和价值。投票普选式的民主在科学方法的支持下,一跃成为人们普遍遵从的价值并且不接受任何其他价值的挑战。民主与科学之所以能够紧密结合,在于二者的内在气息和操作手段具有相通性。民主与科学同样追求客观性、透明性、可计量性和规律性;与此相反,非民主和非科学则更具有主观性、神秘性、不计量性和随意性。在科学与民主的逻辑下,任何挑战其现状并与之相反的政治状态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落后和专制。任何有意对科学民主进行反思的人都会陷入两难的困境:一方面,价值无涉使得人们无法在科学民主体制内部进行价值和规范层面的反思;另一方面,自然科学取得的客观成果以及民主意识形态的强势统治,使得任何体制外的反思都面临被冠以开放社会的敌人、专制主义的鼓吹手、无视客观事实等恶名的危险。然而,究竟何为民主?何为专制?二者的内涵又是什么?就其最小的元素形式而言,包含民主的统治形态是否一定胜过包含专制的形态?这些看似无需解决的问题,其实迫切需要得到审视。
二、二元对立的政体观
有关民主和专制的范畴,其实就是政治学最古老的政体问题。作为政治学的鼻祖,亚里士多德认为研究政体就是为了让人“较好地理解何种政体是好的,每种政体在各种政体的优劣排序中的位置,以及它有着何种法律与风俗” 〔1 〕318。通过对158个希腊城邦的考察,亚里士多德为政体分类提供了影响至今的范式。亚里士多德从统治人数和获益人群两个方面分出了三组政体类型:一人统治、所有人受益的政体是君主政体,一人统治、统治者受益的政体是僭主政体;少数人统治、所有人受益的政体是贵族政体,相反是寡头政体;多数人统治、所有人受益是共和政体,相反是平民(民主)政体①。君主政体在所有政体中最好,但其堕落形式即僭主政体却最坏,共和政体的堕落形式平民(民主)政体则最不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上述六种政体都过分理想化和纯粹化。现实中真正可取和可能的形式是混合政体。后世如《国家论六卷》(布丹)、《利维坦》(霍布斯)、《政府论》(洛克)、《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等论著,在政体分类问题上大多没有超出亚里士多德的范式,仅仅是根据自己时代的需要和特点有所剪裁和发展。
(一)古代政体分类方式的显著特点
第一,正反两面。政体如硬币,两面并不相同。一般而言,任何统治形态总是一面好,一面坏。比如,一人统治,好的一面是君主政体,坏的一面是僭主政体。人们既不能因君主政体就认为一人统治好,亦不能因僭主政体而认为一人统治坏,因为一人统治兼有好坏、可好可坏。人们只能就事论事地去分析每个政体,不能因某种具体的实践就对统治形态作总体上或好或坏的评价。然而,这样明显的道理却常常被现代人所忽略。如有些国家的民主虽好,却不能说明多数人统治在任何条件下都好;有些国家的民主虽坏,却不能说明多数人统治在任何情况下都坏。值得现代人学习的是亚里士多德借政体分类所表达的审慎态度即顾此而不失彼以及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第二,物极必反。亚里士多德通过把最坏的政体孕育于最好的政体,最不坏的政体孕育于最不好的政体,表明了物极必反的道理。越是崇高、奇特的政治,越有可能变得罪恶、恐怖;越是平庸、寻常的政治,越有可能变得美好、温和。人们应该警惕那些看似救世主般神圣的统治者,也应该重视那些仿佛邻家老人般平常的政治人物。前者往往不仅无法拯救苍生,反而会带来无休止的痛苦;后者却能时常为人民带来真正的幸福。对见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现代人而言,这无疑是极其重要的规劝。一旦放弃庸常去寻求奇迹,人们得到的有可能不是激动人心的善和利,而是地狱般的恶和害。
第三,混合政体。在列举六种不同的政体后,亚里士多德提出唯有混合政体才是实际可能的状态。这一立场的价值主要在理论而非现实层面。在现实层面,只要一经实践就会马上发现纯粹政体无法实现的事实。然而,如果没有在理论层面明确指出纯粹政体的局限性,人们很可能会认为某种纯而又纯的政体(尤其是当其有着新颖的外观时)有现实的可能性,从而着手实践。直到在实践过程中屡次碰壁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人们才会意识到混合政体的意义。原本可以在理论层面得到劝阻的悲剧,何必等到实际发生后才能明白其为悲剧。任何理论构建者或乌托邦思想家都应尤其注意混合政体的理论价值。
亚里士多德政体分类的这三个特点会不约而同地将人引向其道德德性——适度。所谓适度,“第一,它是两种恶即过度与不及的中间;第二,它以选取感情与实践中的那个适度为目的” 〔1 〕55。由于统治形态兼有好坏、政体会物极必反、混合政体现实可行,所以人们在政治问题面前不能走极端,而应采取审慎和适度(中道)的态度,毕竟过犹不及。
(二)二元对立政体观的起源
古代人意识到政体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强调中道与权量,然而现代人却抛开了古代人的慎重或含混,变得愈发自信、简洁。现代人政体分类的方法主要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在现代人眼中,不同政体固然可以有不同技术性或学术性的定义,但天下所有政体究其根本而言,无不符合善与恶、对与错、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理性与非理性、自由民主与极权专制等二元结构。如此一来,混合政体在现代人简洁的理论(而非现实)中无法立足。试问在这样黑白分明的世界观下,善怎么能混合恶,进步怎么能混合落后,自由民主怎么能混合极权专制?现代理论的结果,必然是一方压倒另一方,善对恶的全面勝利。任何置于善与恶之间的政体,并不具有合法性,只是有待进一步加工转化的半成品。
现代人黑白分明的政体观,同其独特的经历尤其是殖民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息息相关。殖民主义使现代人将西方等同文明、非西方等同野蛮,所以西方的民主政体代表了先进,而其对立面即诸多其他政体形式只是落后。15世纪末以来,西方世界尤其是英国依靠航海技术、武器装备、工具创新等一系列高超的军事、社会、经济组织手段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崛起。隨着坚船利炮敲开世界不同角落的大门,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也得到了印证。西方同世界其他文明的关系不再对等,而是先进对落后、文明对野蛮。对西方列强而言,“他们不满足于剥削其他民族,还要教化他们。当地人民也许不再受掠夺了,但是他们的文化——那些被认为迷信、落后、异教徒的东西——却受到了侵蚀” 〔6 〕。从某种意义来说,文化歧视的最高表现就是政体(制度)歧视。殖民主义浪潮所到之处,无不见证了模仿西式民主不同程度的政体改革。欧洲的权威和统治逐渐渗透到思想意识层面。不少非西方的仁人志士亦坚信西方政体象征着科学、进步和文明,应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及。福泽谕吉曾在《文明论概略》中写道:“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世界的通论,不仅西洋各国人民自诩为文明,就是那些半开化和野蛮的人民也不以这种说法为侮辱。” 〔7 〕9在西方乃至世界其他文明眼中,殖民主义并非全然不可接受,有时甚至与开化同义。各国应该正视自己的落后和野蛮,积极推进西化:“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文明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一切事物的利害得失。” 〔7 〕11在西化过程中,政体改革居于枢纽地位,因为政体是人类获得文明的重要手段。福泽谕吉提出:“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 〔7 〕14。简言之,学习西方形而上的精神和政体比获得坚船利炮等形而下之器更为重要。如此一来,欧洲殖民主义逐渐在现代人的脑海中培育出了黑白分明的世界观,即西方为白,非西方为黑:欧洲之胜不仅在于坚船利炮和奇技淫巧,更在于精神和政体的文明;所有落后民族都是相对意义上的野蛮民族,终将被文明征服和改造。任何除西方之外的政体和文明都不具有合法性,至多只是过渡阶段。可以说,西方的挑战是文明体制对野蛮体制、先进生产方式对落后生产方式、现代对古代的全面战争。在这二元对立的零和状态下,一旦落败就只能臣服于人:“此新文明之势力,方挟风鼓浪,蔽天而来,叩吾关而窥吾室,以吾数千年之旧文明当之,乃如败叶之遇疾风,无往而不败衄……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 〔8 〕
现代人另一个独特经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与轴心国你死我活的战争,进一步塑造并加深了现代人二元对立的政体观。如果说欧洲的殖民主义使政体有了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之分,那二战则人为地在政体间划分了善恶敌我的阵营。当时轴心国阵营有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而同盟国的主要参与者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中国以及苏联。在今人的理解中,轴心国与同盟国之战是残暴、独裁、极权、邪恶的法西斯与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人类卫士之间的战争——一场邪恶与正义的较量。巧合的是,邪恶阵营中的三大政体有着较高的相似性:独裁主义、极权主义和军国主义。随着同盟国阵营的最终胜利,軸心国及其政体形式都被牢牢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架上。直至今日,任何带有独裁、极权、军国色彩的政体,都会饱受世人非议。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人跳出了古代人的范式。须知在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人那里,任何统治形态都兼有好坏,所以即便坏如独裁主义、极权主义和军国主义亦不过是某种好的政体的变异形式。现代人无疑抛弃了这种观点,纯以非善即恶的角度视之。现代人会如此决绝地对待轴心国的政体形式主要是因为痛恨其所作所为:轴心国率先发起侵略战争,并对无辜人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轴心国固然罪不可赦,但是如果人们仅因具体实践的罪恶而不假思索地全面反对与之相关的一切,就无法真正反思二战的悲剧。轴心国犯下的滔天罪过成了一堵厚厚的墙,使人难以跳出善恶褒贬的结构,心平气和地对理论和机理层面的问题予以研究。这样一来,轴心国的后裔只知败而不知为何必败,无法真正认罪知罪;同盟国的后裔亦只知胜而不知胜敌益强,无法从轴心国的体系中汲取有益人类文明发展的教训 ②。因此,对现代人来说较为紧迫的任务是剥开独裁与民主、极权与自由、军国与和平等善恶评价之茧,从政体的元素形式重新进行亚里士多德式的考察。
冷战是现代人面临的又一独特经历。冷战亦以善恶划分敌我阵营。 值得指出的是,拿善恶划分敌我早已是西方的传统。在1656年,英国的奥利弗·克伦威尔就在议会上指出:“世界其他地方存在邪恶轴心……他们憎恨我们,因为他们憎恨上帝和世界上美好的一切。” 〔9 〕23自此300多年后,美国总统里根同样认为自由世界与邪恶帝国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而苏联则是“现代世界的邪恶核心” 〔9 〕24。因此,反思冷战与反思二战有着相似的际遇,即无法跳出善恶褒贬的价值观评价。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固然出了问题,但不能将其过度简化为善恶概念;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政体亦是如此。除去善恶,冷战引出了另一组划分阵营的标准即对(可行)与错(不可行)。虽然苏联阵营与美国阵营之间一直持续竞争,但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苏联的解体并非所谓的“光明”战胜“黑暗”。因此,对错这组标准就变得十分重要。简言之,苏联的解体不仅在于“恶”更在于“错”,即政体僵化、缺乏人性基础和经济萧条等一系列失败。在轴心国与同盟国的划分中,对错概念并不适用,因为即便轴心国的体制对(可行)也无法挽回其初衷和目的上的恶,即便同盟国的体制错(不可行)也无碍于其善。由此,冷战的经历丰富了现代人二元对立政体观的内容。一些并不十分落后野蛮也没有在善恶问题上犯下滔天大罪的政体,仍可以在对错的标准上相对立。
冷战以后,二元对立的政体分类方法变得越来越不敷现实之需。几乎与苏联解体同步,美国学者福山适时地提出了历史终结的理论,即“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 ……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不能再改良了” 〔10 〕1。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可谓现代人二元对立政体观的全胜形式。虽然文明、善和对与野蛮、恶和错的实质(实践)斗争还未完全结束,但是文明、善和对的政体形式(自由民主)已经在人们的意识领域赢得了胜利。换言之,人们无不承认自由民主是最好的政体,并认为:“真正的重大问题都已解决,形成历史基础的原理与制度,遂不再进步与发展。” 〔10 〕3人类只剩下零零散散和无足轻重的“官子阶段”,即在现实中逐渐让其他政体形式向自由民主制过渡。二元对立的政体观,似乎进入了一元独霸的时代。然而,历史的终结和一元独霸都不过是冷战昙花一现的残留物。这种观念的立足点无疑是建立在西方中心论和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即西方发展模式的优越性和普世性。但是,历史终结和一元独霸无法解释后冷战时代西方国家同伊斯兰国家的冲突以及东亚国家的崛起,二元对立的政体观在如此复杂多元的现实情况下显得捉襟见肘。
现实情况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自由民主政体的崛起、大量混合政体的产生两方面。第一,世界自冷战以来见证了许多非自由民主国家的崛起,这些国家(如中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的政体既不野蛮、邪恶,也有较高的可行性。因此,人们很难将其框入二元对立的结构中。毕竟它们并不与西方世界相对立,亦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阵营,只是以分散、个别、多极的形式挑战现代人二元对立的观念。第二,世界现存的政体基本都是混合政体。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由民主制),早已融入了一些社会主义(苏联阵营)的素材,成为了福利国家。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借鉴了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其他国家亦少有纯而又纯的政体形态。在多种多样政体的现实面前,二元对立的政体观只是一种过度的描摹和简化。
(三)二元对立政体观与基督教思维
基督教的教义涵盖着二元对立的结构即世界在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上帝与撒旦恒定的冲突之中。善与恶不斷作斗争,每当善获得胜利之后,又会有新的恶产生。最终,善与恶的斗争会有一个螺旋的终点,那就是善的绝对胜利即历史的终结。这种二元结构可谓打开基督教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钥匙。随着西方文明对世界的征服,基督教的二元结构亦改造了现代人(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思维模式。启蒙运动虽然以提倡理性和反对宗教为其主旨,但只是反对了某个上帝、某种教义、某些教会。基督教赖以生存的基础即创造上帝和撒旦的二元结构,不仅完好无损,而且渗入了启蒙运动的体系当中。自然科学成了新宗教,人成了新上帝,而大学成了新教会。以前是上帝为善,撒旦为恶,现在是理性(科学)为善,非理性(非科学)为恶。随后的民主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无不进一步发展并反映了二元结构。在民主运动中,民主为善,非民主为恶,民主的胜利即历史的终结。如果说二元对立的弊病在政体、宗教、科学或文明的层面还不足以显示的话,那么二战中纳粹德国的行为则深刻揭示了这种结构的危害。二元对立只是中性结构,可以承载任何事物。一旦纳粹德国将种族放置其中,就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屠杀。在纳粹的眼中,日耳曼民族为善,犹太民族为恶,日耳曼民族应该彻底消灭犹太民族。
对今天的现代人而言,二元对立结构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而且会制造问题。现代人正在深渊的边缘徘徊。如果一定要将某个世界中个别势力的挑战框入二元对立的结构中,那么人类将会面临另一场持久、残酷的战争(甚至大屠杀)。如果将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非西方自由民主式的崛起框入二元对立的结构中,就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于今而言,二元对立不仅无益于人类的和平、文明与发展,而且会加深人与人之间的分裂、斗争和毁灭。
在殖民主义、二战以及冷战的时代,二元结构虽有不少问题,但仍能自圆其说。然而,世界日趋多元复杂的现实使二元结構愈显不足。目前,二元结构面临两个显著困境即虚无主义和一元独霸。冷战以来大量混合政体的存在,突破了二元对立结构的简化,营造出了一种政体多元化的氛围。一旦发现政体多元化才是事实,二元结构只是虚构,现代人原本泾渭分明的政体观会瞬间坍塌,从而走向政体虚无主义,即从根本上否认政体问题存在善恶的标准。任何政体只要存在就有其合法性,并且政体间只在相对的意义上存在善恶和对错,因此没有一种政体有号令、纠正或改变其他政体的道德权威(而非实力)。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二元对立政体观的破产就是政体虚无主义产生的基础。在这种虚无主义的观念下,西式民主政体并不比非洲独裁者的制度更具有道德优势。非洲独裁者能在那一方水土存在必有其原因和意义,西式民主政体亦只在少数地区适用。政体问题只能因人而异、因地制宜,毫无普遍性可言。
与政体虚无主义相对,现代人需要同时应对政体一元独霸即任何政体形式都必须向自由民主制过渡的问题。在一元独霸观念的支配下,政体的合法性不在于治理的实际成果而在于同自由民主制的相似程度,失败的民主犹胜于成功的非民主。一元独霸政体观的兴起同20世纪人类经历的几场极权主义的灾难性事件密不可分。由于极权主义在历史上带来了悲剧和罪恶,人类因此将极权主义彻底打入另册。任何同极权主义沾边的政权形式,都被视为邪恶轴心。任何具有些许类似极权主义特征的政治思想,都被视为极权主义的鼓吹手和开放社会的敌人——“企图毁灭文明、重返部落主义的反动运动” 〔11 〕。在二元对立的框架内,一旦极权主义被公认为恶,自由民主必然成为善。更何况,极权国家的实践印证了自身的恶,并最终被民主国家击败。因此,自由民主制理应成为唯一的善即一元独霸的政体形态。尽管民主并非全然正确和完备,人们却因极权主义是更大的恶而无法在二元对立或一元独霸的框架内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批判民主就等于支持极权主义,民主不能有错,否则极权主义亦可以对。如此一来,包含民主特征的政体形态就走入神坛,成为无人能够抨击、无人敢于抨击的信仰。包含极权主义特征的统治形态同时走向地狱,成为无人能够借鉴、无人敢于借鉴的罪恶。时至今日,极权主义、专制、独裁等描述某种特定政体形态的概念无不包含贬义、残暴、屠杀、反人类、黑暗、邪恶和恐怖等因子。与此相反,自由民主则令人联想到褒义、人权、尊重、平等、博爱、光明、正义和安全等理念。极权专制与自由民主已成为具有价值判断与道德褒贬的词汇,无法捕捉这两种统治形态的机理与原则。鉴于此,政治学应该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观性,不能沦为意识形态、宗教或者战争的工具。
(四)汲取古代政治学范式的智慧
现代人的当务之急是反思二元对立结构并汲取亚里士多德式古代政治学范式的智慧。现代人必须向古代人学习的一点是,人类不能走极端,尤其是不能在政治问题上走极端,更不能使政体分歧宗教化和道德化。虽然非黑即白的价值观易于理解、宣传和斗争,但却无力应对复杂的现实局面,甚至会无故挑起事端。毕竟如何跳出二元对立才是政治最原初的意义和智慧,因此,汲取古代政体分类范式的智慧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但是,这种汲取不能建立在一味复古的基础上。正如商鞅所言:“治世不一道,变国不法古。” 〔12 〕古代范式虽然可以给今人提供借鉴和思考的框架,但是古代的时代背景、实际情况及适用情形都与后世有很大区别。否则,亚里士多德式的范式也不会被基督教的二元结构所取代。
汲取其智慧就要综合现代人的二元思维结构与古代人的分类范式。二元不对立最能体现这种综合,即把从古代正反两面、物极必反以及混合政体中提炼出的适度、中道、和谐融入现代二元结构。宋代哲学家张载准确表达了二元不对立的逻辑,即“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13 〕10,所谓和是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3 〕147。简而言之,有民主必然有其反面,二者相反必然产生矛盾,但是矛盾的解决不应是一方压倒另一方、善良战胜邪恶这类非黑即白的极端方式,而是和而不同的共存状态。任何政体都一定有对立面,即便消灭了现今的对立面,新的对立面也会随即产生。因此,你死我活式的斗争、胜利和终结只能是人类的幻想。矛盾永远无法彻底解决,一种稳妥且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承认对立面和矛盾存在的合理性,从而与之共存于一个整体。虽然和平共存,但是原则问题从未妥协。“象与对”在这不妥协的共存中相互此消彼长、取长补短,从最初水火不容的尖锐对立行至水乳交融、难分你我的和谐状态。二元不对立即和而不同的境界:此始终是此,彼依然是彼,但是无需强调彼此对立。统治形态不能偏向任何一方,而要兼具正反两方面,由此就需引出同一性与多样性的概念。
三、同一性与多样性
同一性與多样性既是分、殊、偏,又不会使人产生偏见。单言统治形态则显得混沌不分,难以理解。如果将统治形态分为自由民主和专制极权,会使人们联想到诸多历史事件,从而形成或隐或显的偏见。没有人欣赏专制极权,厌恶自由民主,但是这并不代表包含专制极权特征的统治形态毫不可取,包含自由民主的统治形态完美无瑕。因此,从同一性与多样性这两个角度来考察,不仅避免了不分的含糊,也克服了分的偏见。同一性与多样性可谓统治形态的元素和基础形式,便于人们认识机理、原则和价值层面的问题。
(一)同一性与多样性政体的倾向
同一性与多样性政体在具体制度层面有着不同的倾向性。一般来说,同一性的政体倾向于一个意志掌握最高权力、单一的社会思想、指令式的经济政策以及中央集权式的中央地方关系;多样性的政体则倾向于多个意志掌握最高权力、多元的社会思想、市场竞争式的经济政策以及地方分权式的中央地方关系。具体制度层面的倾向只能说明不同政体与某些具体制度安排在内涵上更加契合,并不意味现实中一定如此,也无法揭示两种政体的实质区别。
同一性的政体与多样性的政体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二者在统治意志与统治目的这两个方面按照不同的原则进行安排。就统治意志而言,同一性的政体要求掌握最高权力的意志为一,多样性的政体则要求多于一。此处的统治意志不能单从人数的角度进行计算。当然,人数与意志在最理想的状态下应该相符,即同一性的政体只有一个统治者,而多样性的政体则有多个统治者。然而,统治人数的多寡在现实中往往无法决定统治意志,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在人数与意志的张力下,大致会产生四种情况,即“似一实一”、“似一实多”、“似多实多”和“似多实一”。“似一实一”是指看似只有一個统治者,实际也只有一个统治者;“似一实多”是指看似只有一个统治者在前,但实际有多个意志在背后操纵和博弈;“似多实多”是指看似有多个统治者,实际也有多个统治者;“似多实一”是指看似有多个统治者,但实际都听命于一个意志。亚里士多德曾按统治人数的多寡分出了共和制(民主制)、贵族制(寡头制)以及君主制(僭主制)三种政体及其变异形式。然而,从统治意志的角度来看,共和制、贵族制以及君主制都既可能是同一性也可能是多样性的政体,因为政体之为同一性或多样性取决于统治意志而非人数的多寡。如今自由民主与极权专制的分野同样是建立在人数和教条而非统治意志的基础上,因此表面现象并不能完全反映实际情况。比如一些国家有投票制度和议会制度,但实权却在一个意志手中掌握;另一些国家虽没有投票和议会,但实权却为不同意志共享。前者看似民主,实际并不民主;后者看似专制,实际并不专制。
就统治目的而言,同一性的目的在于共同体本身,多样性的目的则在于共同体利益的多数。柏拉图曾在《理想国》中充分阐述了同一性的目的:“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 〔14 〕所谓共同体(全体)只能从整体论的角度去理解,因为将一个复杂的系统拆散成无数组成部分的总和或分离的元素不仅繁琐而且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因此,共同体绝非所有人之和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或系统。假设一个共同体由100人组成,其中99人富贵,1人贫贱。同一性的政体不会牺牲少且贫贱的1人来成全多且富贵的99人,因为如此则不是共同体而是多数人或强者的利益。同一性的目的是让共同体作为整体获得利益,不会迁就人数众多或势力强大的团体。简而言之,同一性的原则是苟利共同体,虽一人亦保全,虽众人亦废除,虽权贵亦驳斥,虽贫民亦扶持。与此相反,多样性的逻辑是从还原论的角度看待共同体,即“共同体的利益是道德术语中所能有的最笼统的用语之一,因而它往往失去意义。在它确有意义时,其意义可以表述为:共同体是个虚构体,由那些被认为可以说构成其成员的个人组成。那么,共同体的利益是什么?是组成共同体成员的利益总和。不理解什么是个人利益,谈论共同体的利益便毫无意义” 〔15 〕58。边沁试图为如何计算共同体成员的利益总和提供可依循的步骤:一是从利益最直接受某行動影响的人当中,挑出一个来估算;二是估算该行动最初造成的每项可辨认的快乐与痛苦的值;三是估算随后造成的每项快乐与痛苦的值,这构成最初快乐与痛苦的丰度及不纯度;四是把所有快乐的值相加,同时把所有痛苦的值相加,如果快乐的值更大则表示该行动有利于个人利益,如果痛苦的值更大则相反;五是按上述程序对每一个利益相关人士的值都进行估算;六是将快乐值更大的所有人相加,将痛苦值更大的所有人相加,如果快乐值更大的人数更多则表明该行动有益于共同体的利益,如果痛苦值更大的人数更多则相反 〔15 〕88。姑且不论边沁的方法是否准确、恰当和适用,单因其繁琐、复杂就无法运用于人口众多的共同体。尽管如此,边沁的尝试依然指出了运用多样性逻辑测量共同体(全体)利益的两个重要标准,即人数和强度。以人数而言,共同体的利益即保障或增进尽可能多的人的利益。假设另一个仍由100人组成的共同体,其中90人富贵,10人贫困。共同体的利益是找到最多人能够受益的比例:能使90个富人加2个穷人受益的政体要优于80个富人加10个穷人受益的政体,因为前者的受益人群为92人,后者只是90人。此外,共同体仍需考虑利益与损害的强度。在前一个例子里,如果90个富人加2个穷人获利的强度为每人10即920的总利益,8个穷人受害的强度为每人100即800的总损害,那么共同体的净利益为120。在后一个例子中,如果80个富人加10个穷人受益的强度为每人10即900的总利益,10个富人受害的强度为每人5即50的总损害,那么共同体的净利益为850。从人数和强度之积的角度来说,后者远胜于前者。简而言之,同一性的目的在于使作为整体的共同体获利,多样性的目的则是让共同体中获利群体的人数和强度之积超过受害群体的人数和强度之积。
(二)同一性与多样性的分类方法
在阐述了同一性与多样性政体本质上即统治意志与统治目的的区别之后,还需在表1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和表2现代二元对立政体分类的对照下进一步揭示同一性与多样性理论的内涵。
表1中亚里士多德按照一人、少数人和多数人统治来划分政体的方法不再适用于现代社会,多数人的统治即直接民主无法适应当今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状况。在古代雅典人看来,民主意味着全体成年公民③ 的统治即直接民主。雅典人之所以能够实行直接民主主要在于其小国寡民的现实:全部成年男子的总人数大约仅在25 000至40 000之间 〔16 〕。然而,雅典的民主根本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地广人多的状况。密尔曾说:“能够充分满足社会所有要求的唯一政府是全体人民参加的政府……但是既然在面积和人口超过一个小市镇的社会里除公共事务的某些极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亲自参加公共事务是不可能的,从而就可得出结论说,一个完善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了。” 〔17 〕现代民主制最理想和完善的状态只能是间接民主,多数人根本无法统治,权力终归只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现代民主的本质是精英政治即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贵族制和寡头制。罗伯特·米歇尔斯曾提出寡头政治的铁律:现代民主制的权力最终必然为一个寡头核心控制,人民始终无法自己作主,仅有选择不同统治集团或寡头核心的权利 〔18 〕。亚里士多德时代多数人与少数人统治的区别现今已不存在,所有统治都不是多数人的统治。因此,多样性比共和政体、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寡头政体更能如实反映现代社会的情况。
同一性与多样性理论的另一个贡献是不再对政体作性质层面的区分。比如,亚里士多德曾从统治者财富的角度区分政体,他认为:“凡以自由人执掌治权者为平民政体而以富人执掌治权者为寡头(财阀)政体……多数自由人的为平民政体,其特征在于出身自由而不在于为数之多,少数富人的为寡头政体,其特征在于财富而不在于为数之少。” 〔19 〕然而,统治者财富的多寡不足以作为政体分类的标准。对现代人而言,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有自由的出身,统治集团成员或贫或富的经济背景不应影响政体的性质。如果共同体的利益得到保障,即便统治成员为富人亦可谓同一性或多样性政体的善的形式。如果共同体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即便统治成员为穷人也只是同一性或多样性政体的恶的形式。简言之,政体性质全由统治的目的和结果而非统治集团的私人背景决定。在同一性与多样性的理论中,表述统治目的和结果的标准是善、恶。值得指出的是,同一性的善、恶与多样性的善、恶有所区别。同一性的善是指一个统治意志为了整体的利益进行统治,中国古代的尧、舜、禹以及《理想国》中的哲学王即属此类;同一性的恶是指一个意志为了自身的利益进行统治,比如桀、纣和希特勒等独裁暴君。多样性的善是指多个意志的统治使共同体中获利的人数和强度之积大于受害群体之积,比如美国的民主;多样性的恶是指多个意志的统治使共同体中获利的人数和强度之积小于受害群体之积,比如伊拉克的民主。
通过表3对同一性与多样性内涵的罗列,同一性与多样性理论基本克服了现代二元对立方法过度简化的弊端。在现代二元对立的视野中,政体只分为自由民主和专制独裁及其他一切非民主政体,其中自由民主为善,专制独裁为恶。同一性与多样性理论虽然继承了现代人以善、恶划分政体的思想,但是无疑丰富了这种思想资源。在对同一性与多样性政体进行考察之后,可以发现二者兼有善恶:现代专制独裁为同一性政体的一种恶的形式,但亦有与其对应的善的形式;现代自由民主为多样性政体的一种善的形式,但亦有与其对应的恶的形式。由此可见,同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绝非你死我活、非此即彼、善恶相异的二元对立,而是一种辩证关系。同一性与多样性只是两种不同且中性的统治形态,各有优劣,并不是天然对立形态。所以,人们不能单纯地因多样性而否定同一性,或者站在同一性的立场上排斥多样性,更不能因同一性之恶就以偏概全地反对同一性本身,亦不可因多样性之善就无条件认同多样性的一切。然而,现代人往往从自由民主与专制极权二元对立的角度看待同一性与多样性:因自由民主的善就肯定多样性,因专制极权的恶就否定同一性。多样性包括但不仅限于自由民主,专制极权亦至多只是同一性的一种形态而已。现代二元对立视野的简化和盲点无疑在表3的两处空白中得到了体现。拿多样性之善与同一性之恶相比,只能说明多样性这一具体的善胜于同一性这个具体的恶,决不能说明多样性本身一定胜于同一性。与此相反,人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多样性与同一性。同一性与多样性都有善恶,但其原则、手段以及标准仍有较大的区别:一个按同一性的方法进行组织,另一个按多样性的方法进行安排。因此,二者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同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是全方位的立体关系。同一性之善可以拿来修正同一性和多样性之恶,也可以对多样性之善有所裨益;多样性也是如此。人们尤其应该习惯拿同一性的原则改进多样性,拿多样性的原则修复同一性。但是,这种相互砥砺的起点在于承认二者的平等地位。正如《大学》所言:“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着,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 〔3 〕8简言之,人们应该见多样性之善而思其恶,见同一性之恶而思其善,从而做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三)反思多样性的独尊
对于今天的现代人来说,除了要破除自然科学式的政治学和二元对立的政体观之外,还要对多样性的独尊进行审视。同一性与多样性本是辩证关系,应该互通有无和相互促进,不可偏舉。但是,人类在20世纪见证了诸多同一性的恶的事件,因此走向了抑一扶多的立场。在现代人眼中,同一性乏善可陈:同一性的善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或者即便能够成为现实也不足以抵消其恶,同一性的恶却是众所周知、人神共愤的现实。因此,多样性的政体形态及其原则成为了现代政治正确的标准。任何对多样性进行批判的人都会或多或少犯了现代人的忌讳,成为开放社会的敌人;任何对同一性予以中肯评价的人也会被当作专制极权的支持者而被现代社会所排斥。至于那些自認为是自由民主(多样性)的朋友而非其谄媚者的人亦难畅所欲言,只能行隐微教义。这样一来,多样性就处于独霸的地位,现代人因此尤为缺乏拿同一性修正多样性的视野。代议制虽好,但开明的一人统治也不乏可借鉴之处。现代人唯有深刻反思多样性独霸的缺陷,才能不偏不倚地从同一性与多样性的原则中都吸取经验教训,并且恢复二者的辩证关系。
在现实中,任何政体都不可能单纯地按多样性或同一性的原则进行安排,实践层面的政体一定是同一性和多样性的混合制。所以,反思和借鉴的意义更多是在理论层面。理论层面的第一个贡献是解决知行不一的问题。很多现代人往往想一套做一套,知行之间不仅没有统一有时还张力十足。比如,现代人认为政体应该是自由民主(多样性),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发现如果权力不集中、没有一个权威往往很难取得任何成果。然而即便在实践中采用了同一性的原则,仍要在思想和口头上对其口诛笔伐。理论层面的第二个贡献是解决合法性的问题。由于现代人在思想理论层面对多样性俯首称臣,所以那些实际有效的同一性的方法都不具备合法性,任何人都可以冠冕堂皇地从多样性的角度予以驳斥。如此一来,稳定性和安全性就难以保全,容易犯朝令夕改、卸磨杀驴的错误。理论层面的最后一个贡献是为改革留下空间。一旦人们发现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运用同一性来改良多样性时,就会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会惹来为极权主义招魂的骂名,另一方面可能因蹉跎不前而积重难返。
四、余论与思考
现代人对政治事物的理解面临两大困境,即自然科学式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以及二元对立的政体观,这二者与现代自由民主互为表里、紧密结合。自然科学的方法支持具有较多可量化和观测性质的自由民主制,二元对立的政体观为自由民主筑牢了非此即彼的激进结构。在这种交互作用下,自由民主不容任何异议和挑战,成为了唯一科学、善且正确的政体和价值。所有与之相反者都被视为迷信和恶。面对如此咄咄逼人的局面,人们最好的应对方法是对亚里士多德式的古代政治学进行某种程度的综合和回归。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说明自然科学式的政治学无法摆脱价值判断,只是拿自身的价值取代了其他一切价值;二是揭示二元对立的政体观是近乎宗教狂热的过度简化;三是从同一性与多样性的角度沟通古代范式和现代理解。绝对的价值无涉、客观科学和善良正确并不存在于客观世界中,一切事物的发展只能在相对的意义上取得进步,现代人既要大方承认也要试图克服这种相对性。辩证和适度而非科学和激进,可谓处理事物相对性问题的良方。归根究底,古代范式不断强调但现代人却遗忘了的智慧是人不能尤其是不能在政治领域走极端。
〔注 释〕
①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3卷、第4卷。
②战后同盟国从轴心国那里得到的科技和军工层面的收获远大于政治和文化层面。
③女性、外邦人以及奴隶被排除在外。
〔参 考 文 献〕
〔1〕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 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 〔M〕. 张立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朱 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柏拉图. 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 〔M〕. 严 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56.
〔5〕許振洲. 浅论意识形态及其在当下中国的困境〔J〕.国际政治研究,2011(4):60-75.
〔6〕尼尔·弗格森.帝国 〔M〕. 雨 珂,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99.
〔7〕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 〔M〕. 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8〕胡 适.胡适文集:第9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65-666.
〔9〕沃尔特·拉塞尔·米德.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M〕. 涂怡超,羅怡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10〕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 〔M〕. 本书翻译组,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
〔11〕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M〕. 郑一明,李惠斌,陆 俊,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6.
〔12〕蒋礼鸿.商君书锥指〔M〕.北京:中华书局,1986:5.
〔13〕张 载.张载集 〔M〕. 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
〔14〕柏拉图.理想国 〔M〕. 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33.
〔15〕边 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 〔M〕. 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6〕黄 洋.古代与现代的民主政治〔J〕.史 林,2007(3):129 -140.
〔17〕J.S.密尔.代议制民主 〔M〕. 汪 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55.
〔18〕Robert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M〕.Kitchener: Batoche Books, 2001: 224-235.
〔1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M〕. 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84.
责任编辑 周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