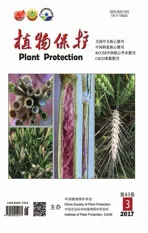防治药用植物土传病害的芽胞杆菌制剂开发的制约因素分析
2017-06-05秦雪梅雷振宏
高 芬, 郝 锐, 秦雪梅, 雷振宏
(1. 山西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 太原 030006; 2. 山西大学生物技术研究所, 太原 030006; 3. 山西大学中医药现代研究中心, 太原 030006; 4. 山西振东道地药材开发有限公司, 长治 047100)
防治药用植物土传病害的芽胞杆菌制剂开发的制约因素分析
高 芬1*, 郝 锐2, 秦雪梅3, 雷振宏4
(1. 山西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 太原 030006; 2. 山西大学生物技术研究所, 太原 030006; 3. 山西大学中医药现代研究中心, 太原 030006; 4. 山西振东道地药材开发有限公司, 长治 047100)
芽胞杆菌是土传病害生防制剂开发中最具应用潜力的微生物之一,但目前针对药用植物土传病害,市场上可供选择和使用的,以其为生防因子的产品和数量较少,远远不能满足生产实际需要。本文从菌株的筛选获得、定殖与生态适应性、安全性评价等方面概述了影响其开发的制约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展望,以期为促进芽胞杆菌制剂在防控药用植物土传病害中的应用提供参考。
芽胞杆菌; 制剂开发; 药用植物土传病害; 制约因素
药用植物的药用部位70%为根和根茎[1],而土传病害的严重发生直接降低了药材产量和品质,给药材生产造成了重大损失[2]。药用植物土传病害种类繁多,发生最普遍的有根腐病、黑腐病、锈腐病等真菌引起的病害[3]。目前该类病害的防治主要依赖于化学农药,但化学农药存在毒性高、残留大、污染重、且病原菌易产生耐药性甚至抗药性等缺陷。土传病害发生环境相对稳定,相对适合微生物的定殖和存活,适宜开展生物防治[4]。利用植株上附生的或根际土壤中的拮抗细菌或其代谢产物调控根围有害微生物的平衡以达到控病保产的目的是土传病害防治的重要途径。
芽胞杆菌是土壤和植物微生态区系的优势生物种群,具有很强的环境适应性和友好性,能通过分泌抗生物质,调节微生物区系,促进植物生长以及竞争作用等方式发挥多种有益作用[5],在土传病害的防治中显示出了巨大潜力,国内外已有不少制剂产品报道,且新的拮抗芽胞杆菌也不断被筛选出来,针对药用植物土传病害,科研工作者也开展了相关工作(表1),但与针对大田作物病害进行的菌株筛选和产品研发相比,其产品数量仍较少,且缺乏作用机制方面的研究。同时,由于次生代谢产物含量较高的药用植物会引起根际土壤理化性质的改变,导致根际微生物及根际土壤酶活性也发生变化[6],从而使得药用植物根际的生理生态状况与农作物有一定差异。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未见相关报道。

表1 土传病害拮抗芽胞杆菌的筛选及其制剂
从2012年的调查来看,我国登记的农药有效成分总数600多个,生物源农药登记品种112个,而微生物农药仅30个[15],且近一半的生物源农药品种虽然处于登记状态,但并未生产。2014年对全国主要生物农药企业的问卷调查也发现,在已登记的生物农药产品中,约20%处于未生产状态,34%为生物农药与化学农药的混配制剂[16]。目前,自1982年我国实行农药登记制度以来,获得登记的130多种生物农药[17]中,仅有1种芽胞杆菌制剂(登记证号:LS2001821),登记用于三七根腐病的防治。由此看出,针对药用植物土传病害开发的微生物农药,特别是以芽胞杆菌为目标因子开发的、在市场上可供选择和使用的生物农药产品和数量很少,远远不能满足生产实际需要。
生物源农药的发展与国家政策、研发水平、农业生产方式、市场需求等密切相关,其自身特性、登记管理政策以及用药成本等因素是制约生物源农药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16]。芽胞杆菌制剂作为生物源农药的重要组成部分,阻碍其发展的制约因素有与其他生物源农药共性的地方,也有因其自身特性导致的差异。本文从拮抗菌筛选获得、定殖与生态适应性和安全性等3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为避免盲目筛选所导致的后续问题,促进药用植物土传病害芽胞杆菌制剂的开发提供参考。
1 拮抗芽胞杆菌的筛选获得
1.1 菌株来源
对于获得具有生防潜力的拮抗芽胞杆菌而言,其来源是首要考虑的因素。分离位点优先选择高病害压力下植物不发病或少发病的区域。抑病型土壤为选择天然存在的土传病害生防制剂提供了一个逻辑位点[18],如Mendes等发现种植于抑病型土壤的甜菜其根际优势群落普遍为与拮抗病原菌相关的微生物,如放线菌门、β变形菌门、γ变形菌门等[19]。其次,药用植物根际微生物中细菌具有较高的类群多样性,其中芽胞杆菌属Bacillus、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细菌最常见[6],也是获得拮抗菌的良好来源,且因其“土著”性而更容易适应当地生态环境。另外,植物内生菌是防治植物病害的重要微生物资源[20],芽胞杆菌是其中的常见类群。如李勇等[21]从人参根部分离出了具有理想抑菌活性的枯草芽胞杆菌B.subtilisge25。
1.2 分离方法
土壤中芽胞杆菌的分离主要采用先加热杀死非芽胞细菌,再进行分离的方法[22],但这种方式是针对土壤中能够培养的微生物进行的。目前发现土壤中超过99%的微生物不能被传统的技术所分离培养[23],这大大阻碍了拮抗菌的获得。分子技术克服了传统培养方法的弊端[24],如宏基因组学技术是完全不依赖于人工分离培养直接获得环境中理论上所有微生物基因组信息的一种有效手段[25],但单凭分子生物学方法也存在不能得到纯培养物的缺陷[24]。纯培养物的获得不仅能够提供生理学、遗传学、病理学等研究的对象,也可获得能够应用于工业生产的新菌株[26],所以将传统方法与分子方法相结合,二者互为补充,用分子技术指导分离培养的方向,是我们当前应着重考虑使用的。例如:近年来兴起的基于PCR 技术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方法RAPD、AFLP、RFLP、SSCP、DGGE 等,能分析或鉴定出大部分土壤微生物,且精度高[24]。据此,我们可以根据分离需求,先选择适宜的分子技术对土壤或植物等分离源进行分析,确定其所含微生物种的丰富度和优势种群,进而选择特定的适合待分离菌生长的培养基进行分离,以提高目标微生物的分离率,更迅速地得到所需的菌种。为了克服纯培养物获得过程中环境因素的影响,还可通过培养基的重新设计和优化,准确模拟微生物栖息地的化学条件;也可通过选择透性滤膜直接进行天然环境原位培养,减少非生物因素对土壤微生物生长的影响[26]。如龚国淑等[22]先将土壤悬液热处理后,再采用麦芽汁牛肉膏蛋白胨琼脂培养基分离土壤中的芽胞杆菌,程序简单,鉴定的类群也多。
1.3 筛选策略和方法
筛选高效稳定的拮抗菌株是生防菌剂成功研发并保证生物防治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5]。筛选策略和方法直接决定了获得菌株的类型。以预防为目的,遵循基本生态学方法的筛选策略主要是基于诱导或提高抑病型土壤的活性,达到对植物较为长期的保护作用;而治疗性的策略则将微生物作为生物农药,以期在有限的时间内控制病害,这在某些方面和化学农药类似[18]。但这两种策略在实际的筛选过程中由于拮抗菌株多样化的作用机制,并不能完全割裂开来。
筛选方法中以平板法筛选产生各种酶类(如溶菌酶、几丁质酶、葡聚糖酶等)和抗生素、抗菌肽等物质的拮抗芽胞杆菌主要倾向于治疗性的策略。以简便的平板法进行产酶拮抗微生物的筛选可以先于拮抗菌与病原菌和/或植物的互作进行,但作为拮抗菌攻击的靶标,真菌细胞壁的复杂性要求拮抗菌能迅速产生多种的胞外酶来消解细胞壁组分达到生防效果[18],这就使以单一的酶作为指标筛选获得的菌株生防效果不能尽如人意。而以芽胞杆菌产生抗生素、抗菌肽等拮抗物质为出发点,通过活体外平板上“抑菌圈”的产生进行筛选已成为评价拮抗菌—靶标菌互作的经典方法。也有研究表明:活体外抗生素的产生和活体内是不相关的[27]。尽管平板法筛选忽略了菌株对植物的诱导抗性,但从获得能产生高性能抗菌物质菌株的角度来说,依然最为简单有效。
土传病害拮抗菌的筛选,除了考虑对病原菌的直接作用外,还将对土壤的调控作用、营养竞争、促生长和诱导抗性作为指标,这类筛选在考虑对病原菌抑制作用的同时,更多地遵循了基本的生态学策略,利于获得更为高效的菌株。如利用特殊培养基筛选产嗜铁素的细菌,可获得对尖孢镰刀菌Fusariumoxysporum,稻瘟病菌Pyriculariaoryzae和小菌核属菌Sclerotiumsp. 等土传病害病原菌具有拮抗作用的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芽胞杆菌属Bacillus等属细菌[28]。
传统平板对峙筛选主要测试供试微生物产生抗生物质的能力,难以明确或预测所选菌株的根际定殖能力[29],也排除了寄主与病原菌敌对关系之间的关联因子,常使筛选出的菌株性能较差[18]。可见,拮抗菌的有效性不能仅以室内抑菌率来判断,必须经过大田验证。然而,活体内试验获得的拮抗菌株也有局限性。某些菌株的生化途径是诱导性的,有的功能在某一环境下可以表达,但改变条件后不再表达;而另一些具有抗菌能力的细菌在传代过程中所产生的特异性转化酶容易使其发生“相位变异”,导致在试验条件下有效的拮抗菌株,在根际条件下却丧失了作用[30]。
另外,由于药用植物土传病害一般由多种病原菌混合侵染引起[2],致病机理多样,且不同生长期和生长地优势病原菌差异明显,而针对单一靶标筛选的拮抗菌不一定对其他病菌有良好的抑制效果,因此筛选方法的选择应基于菌株呈现复杂性的水平而定,避免因靶标单一造成效果降低。
2 拮抗芽胞杆菌的定殖与生态适应性
2.1 拮抗菌的定殖
拮抗菌稳定的定殖能力是其发挥生防、促生作用的关键因素[31],其在土壤及药用植物根部的生长状况、定殖时间的长短及定殖数量的变化直观地反映了菌株定殖能力强弱[32]。以根部入药的药用植物多具多年生特性,使得拮抗菌必须在土壤中具有增殖存活更长时间的能力才能产生好的生防效果。首先,由于药用植物根际微生物有着丰富的类群多样性和数量多样性[6],因而作为外来生物的拮抗芽胞杆菌,对土著微生物菌群需具有更强的竞争力,才能在根际竞争中占得有利位置;其次,药用植物产生的次生代谢产物中的一些小分子物质在栽培生长过程中很容易释放到环境中,从而改变根际土壤理化性质,进而影响土壤环境的微生物群落结构[33-34],这就要求拮抗芽胞杆菌必须对因根际分泌物积累引起的微生物群落变化有更好的适应性。第三,药用植物根际分泌物随着时间的变化对已经引入的生防菌株数量和群落结构也可能产生影响。
另外,有些拮抗菌可以通过产生次生代谢产物来增强其在寄主植物根围的竞争力,从而在定殖过程中占据优势[35],如:嗜铁素、抗生素、水解酶等,所以在拮抗菌的筛选和遗传改造中,可以将上述能力作为筛选指标和改造靶点,以期获得定殖力较强的菌株。
芽胞杆菌通常以生物膜的形式定殖于植物根际,表现出较好的定殖能力[36-37]。生物膜不仅可以提高生防菌的生存竞争力,帮助其抵抗抗生素等环境压力,还能维持其在植物根部的定殖数量,从而提高细菌分泌的胞外酶和抗生素的浓度,保证生防和促生作用的正常发挥[36]。因此,对拮抗芽胞杆菌产生生物膜能力的测定可先于土壤测定来评价其可能的定殖情况。另外,有益的植物内生细菌往往能在植物体内定殖传导,长期发挥生防作用[38]。
2.2 对环境的适应性
拮抗菌能否适应其被引入的生态环境,充分发挥自身的抑菌机制,与相应病原物有效竞争,决定着生物防治的成败。拮抗菌在田间环境中的定殖、生长很容易受到紫外光、温度、化学农药、水分、pH和营养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对于多年生药用植物,环境因子可通过对其次生代谢物和根际分泌物的影响改变根际微环境,进而影响拮抗菌的生长环境。如:养分胁迫可导致药用植物生理代谢的异常变化和根系原生质膜透性的增加,促进分泌物的大量分泌,进而引起植物自毒作用,改变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土壤pH值,引起土壤物理化学性质的改变[1]。由于大多数实验室条件下筛选出来的拮抗菌,筛选环境与田间条件有很大区别,因此针对药用植物土传病害筛选获得的目标生防菌,在应用于根际时,除了需要适应自然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还要适应由于其生理变化导致的土壤微环境的变化。
此外,芽胞杆菌制剂多为活菌制剂,田间应用时常受到温度、湿度、土壤、pH值等外界因素的影响,导致防效不稳。要使其在田间施用时可以较长时间地发挥抑菌作用,维护其产生的抗菌物质的稳定性对于确保生防效果非常重要,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很欠缺[5]。
3 拮抗芽胞杆菌的安全性分析
3.1 对药用植物活性成分的影响
药用植物由于其生产和用途的特殊性,病害防治中使用的农药必须符合《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AP)的要求,既要有效防控病害,又不能影响药材品质。据报道,芽胞杆菌制剂可直接作用于植物,促进生长,增加产量,提高有效成分的含量[39]。在药用植物上也有一些相关报道,如:Sharaf-Eldin等[40]发现枯草芽胞杆菌可提高番红花苦苷、番红花酸和藏红花醛的含量;Karthikeyan等[41]报道,芽胞杆菌可以提高长春花抗癌有效成分生物碱的含量。但上述报道只是针对药用植物中单一或几种成分进行研究,没有考虑活性成分的整体变化。近年来,利用以组群指标分析为基础的植物代谢组学技术来分析植物在非生物或生物胁迫下的应答机制已取得了很大进展[42-44],因此,若将其应用于研究芽胞杆菌对药用植物活性成分的影响,更利于从整体变化的层面来进行安全性评价。
另外,芽胞杆菌应用后,药用植物中某一成分含量的显著升高或降低是否会对其他成分的效果有负面作用,以及芽胞杆菌是否会对药用植物中的非药效成分,特别是一些毒性成分产生影响也需引起高度重视。
3.2 对土壤微生物群落及结构的影响
虽然大多数生防菌来自于土壤或植物内生菌,与土壤及植物具有较好的相容性,但将其大量集中释放到土壤中也可能破坏部分土壤原有微生物的群落结构和功能,并对其构成威胁,从而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有害作用[45-46]。其中,最大的潜在影响是引入微生物对土壤小生境中原有微生物的取代,导致土壤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机能下降[47]。生防芽胞杆菌的引入对土壤微生物的类群存在重要影响,例如:连玲丽等[48]报道:枯草芽胞杆菌EN5处理使根际土壤中细菌、真菌和放线菌的数量明显高于对照土壤,同时,还改善了根际土壤中细菌群体的多样性;余贤美等[49]报道,施用枯草芽胞杆菌Bs-15 后土壤中细菌的数量变化不明显,放线菌的数量在第3天和第7天显著低于对照,第14天以后恢复到对照水平;而真菌种群数量于第7天开始显著下降。另外,芽胞杆菌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也会因作物的不同而不同,陈雪丽等[50]报道:多黏类芽胞杆菌Paenibacilluspolymyxa和枯草芽胞杆菌B.subtilis对不同时期黄瓜和番茄根际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有不同的影响。向土壤中引入生防菌也可能对群落中原有的非致病真菌产生非目标效应[47],尤其经过基因改良的生防菌,由于它们的某些能力通常被特别加强而更需加以注意。
3.3 对人及有益生物的安全性
相对于化学农药来说,大多数芽胞杆菌对人畜有益,具有较高的安全性,但进入市场开发的芽胞杆菌必须经过安全测试,对其毒理学、非靶标环境影响、环境繁衍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才可生产使用。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专门的微生物农药安全性评价技术与相关试验导则[49],对于微生物农药的环境安全性评价和药效评价等均是参照化学农药的准则,缺乏对其特殊性的考虑,因而尽快建立适合微生物农药的生态毒理学评价标准、风险评估程序以及药效试验准则非常重要[52]。
生防芽胞杆菌除了在土壤中定殖外,还可进入植物体内,特别是来源于植物的内生芽胞杆菌。这些菌进入药用植物体内后,保留于药材成品中,在加工及煎煮过程中,定殖的数量和变化尚属未知。进一步研究这些菌的自身毒性、在植物体内的定殖情况以及在药材加工过程中的变化,对保障安全用药至关重要。
4 展望
研究和实践证明,芽胞杆菌类制剂对土传病害经济有效,是仅次于假单胞菌被广泛研究和商业化的菌种。因此,尽量避免开发过程中的各种制约因素,对于促进芽胞杆菌制剂快速发展,有效防控药用植物土传病害非常重要。今后的发展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考虑:
(1) 借鉴医药源微生物资源开发的新技术,优选生防微生物发掘的生态环境,扩大筛选范围和信息获取量,加强生防微生物新颖性的科学评价,建立新的高效菌株筛选体系,增加新菌株发现的几率。
(2) 芽胞杆菌在稳定性、与化学农药的相容性等方面明显优于非芽胞杆菌和真菌生防菌剂[53],因此将其与化学农药或植物源杀菌剂复配使用,可使芽胞杆菌形成优势种群,同时发挥化学药剂抑菌迅速、防效稳定的优势,达到优势互补的目的。
(3) 根据与其他拮抗微生物协同互作,功能互补的原理,将互融的两种以上的拮抗微生物混用,达到对植物不同空间部位的全面占领,实现多种病害兼防、作用持久的协同控病效果[54]。
(4) 芽胞杆菌可以产生多种重要的酶和抗菌物质,利用生物技术手段生产代谢物产品,也是一条值得探索的途径。
[1] 郭兰萍, 黄璐琦, 蒋有绪, 等.药用植物栽培种植中的土壤环境恶化及防治策略[J].中国中药杂志,2006,31(9):714-717.
[2] 高芬, 任小霞, 王梦亮, 等. 中草药根腐病及其微生物防治研究进展[J]. 中国中药杂志, 2015, 40(21):7-11.
[3] 姜竹, 李晶. 中药材土传病害生物防治研究进展[J]. 现代农业科技, 2009(24): 152-156.
[4] 李世东, 缪作清, 高卫东. 我国农林园艺作物土传病害发生和防治现状及对策分析[J]. 中国生物防治学报, 2011, 27(4): 433-440.
[5] 陈志谊. 芽孢杆菌类生物杀菌剂的研发与应用[J]. 中国生物防治学报, 2015, 31(5): 723-732.
[6] 肖艳红, 李菁, 刘祝祥, 等. 药用植物根际微生物研究进展[J]. 中草药, 2013, 44(4): 497-504.
[7] Yu Xianmei, Ai Chengxiang, Xin Li, et al. The siderophore-production bacterium,BacillussubtilisCAS15, has a biocontrol effect on Fusarium wilt and promotes the growth of pepper [J]. European Journal of Soil Biology,2011,47(2):138-145.
[8] Szczech M, Shoda M. The influence ofBacillussubtilisRB14-C on the development ofRhizoctoniasolaniand indigenous microorganisms in the soil [J]. Canadian Journal of Microbiology, 2005, 51(5): 405-411.
[9] 张红骥, Xue A G, Zhang Jinxiu, 等. 尖镰孢菌和禾谷镰孢菌引起的大豆根腐病生物防治研究[J].大豆科学,2011,30(1):113-118.
[10]陈刘军, 俞仪阳, 王超, 等. 蜡质芽孢杆菌AR156防治水稻纹枯病机理初探[J]. 中国生物防治学报, 2014, 30(1): 107-112.
[11]关一鸣, 潘晓曦, 王莹, 等. 哈茨木霉菌、枯草芽孢杆菌对人参灰霉病和根腐病病原菌的拮抗作用[J]. 江苏农业科学, 2014, 42(5): 123-125.
[12]高琳娜, 曹克强, 段英姿, 等. 拮抗细菌Bs-0728对板蓝根根腐病的防治作用[J]. 植物保护, 2011, 37(5): 97-100.
[13]辛中尧, 徐红霞, 陈秀蓉. 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subtilis)B1、B2菌株对当归、黄芪的防病促进生长效果[J]. 植物保护, 2008, 34(6): 142-144.
[14]傅俊范, 史会岩, 周如军, 等. 人参锈腐病生防细菌的分离筛选与鉴定[J]. 吉林农业大学学报, 2010, 32(2): 136-139.
[15]杨峻, 林荣华, 袁善奎, 等. 我国生物源农药产业现状调研及分析[J]. 中国生物防治学报, 2014, 30(4): 441-445.
[16]袁善奎, 王以燕, 农向群, 等. 我国生物农药发展的新契机[J]. 农药, 2015, 54(8): 547-550.
[17]唐韵.我国生物农药登记品种及其使用技术[J].农药市场信息,2013(6):43-44.
[18]Pliego C, Ramos C, de Vicente A, et al. Screening for candidate bacterial biocontrol agents against soilborne fungal plant pathogens [J]. Plant and Soil, 2011, 340(1): 505-520.
[19]Mendes R, Kruijt M, de Bruijn I, et al. Deciphering the rhizosphere microbiome for disease-suppressive bacteria[J]. Science, 2011, 332(6033): 1097-1100.
[20]严婉荣, 赵廷昌, 肖彤斌, 等. 生防细菌在植物病害防治中的应用[J]. 基因组学与应用生物学, 2013, 32(4): 533-539.
[21]李勇, 赵东岳, 丁万隆, 等. 人参内生细菌的分离及拮抗菌株的筛选[J]. 中国中药杂志, 2012, 37(11): 1532-1535.
[22]龚国淑, 张世熔, 唐志燕, 等. 土壤芽孢杆菌分离方法的比较—以成都郊区土壤为例[J]. 中国农业科学, 2008, 41(11): 3685-3690.
[23]Pham V H, Kim J. Cultivation of unculturable soil bacteria[J]. Trends in Biotechnology, 2012, 30(9): 475-484.
[24]许文涛, 郭星, 罗云波, 等. 微生物菌群多样性分析方法的研究进展[J]. 食品科学, 2009,30(7): 258-265.
[25]芦晓飞, 罗坤, 谢丙炎,等. 宏基因组学及其在植物病害生物防治中的应用[J]. 中国生物防治,2010, 26(S1): 106-112.
[26]袁志辉, 王健, 杨文蛟, 等. 土壤微生物分离新技术的研究进展[J]. 土壤学报, 2014, 51(6): 1184-1191.
[27]Renwick A, Campbell R, Coe S. Assessment ofinvivoscreening systems for potential biocontrol agents ofGaeumannomycesgraminis[J]. Plant Pathology, 1991, 40(4): 524-532.
[28]Chaiharn M, Chunhaleuchanon S, Lumyong S. Screening siderophore producing bacteria as potential biological control agent for fungal rice pathogens in Thailand [J]. World Journal of Microbiology Biotechnology, 2009, 25(11): 1919-1928.
[29]郭荣君, 李世东, 张晶, 等. 基于营养竞争原理的大豆根腐病生防芽孢杆菌的筛选及其特性研究[J]. 植物病理学报, 2010, 40(3): 307-314.
[30]van der Woude M W. Re-examining the role and random nature of phase variation [J]. FEMS Microbiology Letters, 2006,254(2): 190-197.
[31]Fan B, Borriss R, Bleiss W, et al. Gram-positive rhizobacteriumBacillusamyloliquefaciensFZB42 colonizes three types of plants in different patterns [J]. The Journal of Microbiology, 2012, 50(1): 38-44.
[32]孙卓, 杨利民. 人参病原菌拮抗细菌的分离筛选与鉴定[J]. 植物保护学报, 2015, 42(1):79-86.
[33]张重义, 林文雄. 药用植物的化感自毒作用与连作障碍[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2009, 17(1): 189-196.
[34]陈慧, 郝慧荣, 熊君, 等. 地黄连作对根际微生物区系及土壤酶活性的影响[J]. 应用生态学报, 2007,18(12): 2755-2759.
[35]杨威, 刘苏闵, 郭坚华. 细菌定殖能力与其生物防治功能相关性研究进展[J]. 中国生物防治, 2010, 26(S1):90-94.
[36]乔俊卿, 陈志谊, 梁雪杰. 枯草芽孢杆菌Bs916在番茄根部的定殖[J]. 江苏农业学报, 2015, 31(6): 1278-1283.
[37]Abbasi M K, Sharif S, Kazmi M, et al. Isolation of plant growth promoting rhizobacteria from wheat rhizosphere and their effect on improving growth,yield and nutrient uptake of plants [J]. Plant Biosystems, 2011, 145: 159-168.
[38]刘慧芹, 韩巨才, 赵廷昌, 等. 果树内生拮抗细菌的筛选鉴定及其生防作用研究[J]. 园艺学报, 2014, 41(2): 335-342.
[39]张智慧, 赵振玲, 金航, 等. 根际促生菌研究进展及其在药用植物上的应用[J]. 云南中医学院学报, 2012, 35(6): 63-67.
[40]Sharaf-Eldin M, Elkholy S, Fernández J A, et al.BacillussubtilisFZB24affects flower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saffron(CrocussativusL.)[J]. Planta Medica, 2008, 74(10): 1316-1320.
[41]Karthikeyan B, Joe M, Jaleel C A, et al. Effect of root inoculation with plant growth promoting rhizobacteria (PGPR) on plant growth alkaloid content and nutrient control ofCatharanthusroseus(L.) G. Don.[J]. Natura Croatica, 2010, 19(1): 205-212.
[42]滕中秋, 付卉青, 贾少华, 等. 植物应答非生物胁迫的代谢组学研究进展[J]. 植物生态学报, 2011, 35(1): 110-118.
[43]张凡忠, 刘小红, 章初龙, 等. 植物响应病原真菌的代谢组学研究进展[J].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报, 2016,38(4): 434-440.
[44]Walker V, Bertrand C, Bellvert F, et al. Host plant secondary metabolite profiling shows a complex, strain-dependent response of maize to plant growth-promoting rhizobacteria of the genusAzospirillum[J]. New Phytologist, 2011, 189(2): 494-506.
[45]Brimner T A, Boland G J. A review of the non-target effects of fungi used to biologically control plant disease[J]. Agriculture, Ecosystems and Environment, 2003, 100(1):3-16.
[46]Abdo Z, Schuette U M E, Bent S J, et al.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characterizing diversity of microbial communities by analysis of ternial 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s of 16S rRNA genes[J].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2006,8(5): 929-938.
[47]蒋志强, 郭坚华. 生防菌对土壤微生态影响的风险评估[J]. 微生物学杂志, 2006,26(1): 85-88.
[48]连玲丽,谢荔岩,陈锦明,等.生防菌EN5的定殖能力及其对根际土壤微生物类群的影响[J].植物保护,2011,37(2):31-35.
[49]余贤美, 侯长明, 王海荣, 等. 枯草芽孢杆菌Bs-15在枣树体内和土壤中的定殖及其对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影响[J]. 中国生物防治学报, 2014, 30(4): 497-502.
[50]陈雪丽,王光华,金剑,等.两株芽孢杆菌对黄瓜和番茄根际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影响[J].生态学杂志,2008,27(11):1895-1900.
[51]陈源,卜元卿,单正军, 等. 微生物农药研发进展及各国管理现状[J]. 农药, 2012, 51(2): 83-89.
[52]袁善奎, 王以燕. 我国微生物农药标准制定现状[J]. 农药, 2013, 52(8): 612-614.
[53]Elliott M L, Des Jardin E A, Batson W E, et al. Viability and stability of biological control agents on cotton and snap bean seeds [J]. Pest Management Science, 2001, 57(8): 695-706.
[54]陈志谊, 刘邮洲, 刘永锋, 等. 拮抗细菌菌株之间的互作关系及其对生物防治效果的影响[J]. 植物病理学报, 2005, 35(6): 539-544.
(责任编辑:杨明丽)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Bacillusspp. agents againstsoil-borne diseases in medicinal plants
Gao Fen1, Hao Rui2, Qin Xuemei3, Lei Zhenhong4
(1. Institute of Applied Chemistry,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China; 2. Institute ofBiotechnolog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3. Modern Research Center for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4. ShanxiZhendong Geo-herbals Development Co., Ltd., Changzhi 047100, China)
Bacillusspp. is one of the microorganisms with great application potential in controlling soil-borne diseases, but the few bio-control agents developed from it on the market cannot meet the growing demands for medicinal plants. This article presented a review on the restricting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tagonisticBacillus, including screening, colonization, ecological adaptability and safety evaluation and proposed some measures concerning future research in hope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Bacillusbio-control agents against soil-borne diseases in medicinal plants.
Bacillusspp.; agent development; soil-borne disease in medicinal plant; restricting factor
2016-07-08
2016-09-22
山西省中药现代化关键技术研究振东专项(2014ZD0501-2)
S 436.3
A
10.3969/j.issn.0529-1542.2017.03.004
* 通信作者 E-mail:gaofen@sx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