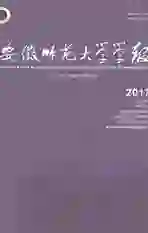“贫民窟”概念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
2017-05-20张波
张波
关键词: 贫民窟;贫穷;城市化;社会保障
摘要:
“贫民窟”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失衡而形成的城市空间极化现象。任何现代国家与地区都应当谨防贫民窟现象的发生。基于上海城市发展的考察分析,本研究认为,贫民窟现象确实存在于中国城市的历史记忆中,但因国家政府对贫民窟的精心治理,目前中国城市的贫民窟濒临绝迹,这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是现代化国家城市发展的“巨大奇迹”。但随着城市化的深度发展,城市的边缘生存空间频现于城市不同角落,这亟需国家政府通过缩小城乡差距、减少城市贫困、共谋区域改造等方面努力,尽量回避城市贫民窟现象,从而实现城市化的有序健康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7)02022907
Key words: slum; poverty; urbanization; social security
Abstract:
“Slum” is the urban spatial polarization phenomenon caused by the imbalance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Any modern countries and regions should guard against the occurrence of slums.From the analysis of Shanghai urban development,suggest that slum phenomenon does exist in China's urban memory,but because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careful management of the slums,currently China's urban slums has been on the verge of extinction,which reflects the ability and level of the government to manage the socialist state and is a “great mirac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ities.However,With the deep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marginal living space frequently appear in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city,which requires government to narrow the gap between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side,reduce poverty and achieve common region reconstruction to avoid urban slums and realize the orderly health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一、問题提出
“贫民窟”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城市社会现象。目前广泛存在于诸如印度、巴西、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据联合国人居署估计,2001年,世界上有924亿(即316%)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窟,在未来30年中,贫民窟居民数量将达20亿,世界也将成为“贫民窟星球”。这些被称之为“城市灾难的根源”“城市的毒瘤”的贫民窟,开始逐渐“包围”城市,城市社会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1]22就中国而言,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快速化发展。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超过50%(5127%)后,2015年底,中国城市化率增长至561%,农民工总数也达到约28亿人。探究现代化国家共同存在的贫民窟问题,对于中国有序、健康、协调推进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不少学者关注底层社会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底层的居住领域,学者们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城中村”“城郊结合部”“棚户区”“工厂宿舍”等方面,较少使用“贫民窟”这一概念。而对于“中国是否存在贫民窟”问题,目前学术界主要存在虚无论、相似论与实在论三种观点。虚无论者认为,因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与严格有效的城市管理,目前中国城市并没有出现贫民窟,但是,随着中国城市化的继续推进,贫民窟是迟早的问题,谨防贫民窟的出现是政府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相似论者指出,中国城市目前出现了类似于国外社会的贫民窟,比如北京的浙江村、安徽村,广州的冼村、瑶台村、三元里村等城中村与城乡结合部,改造“类贫民窟”是目前面临的艰巨任务。实在论认为,中国城市的贫民窟有两种形式,一是城市角落,主要包括内城遗忘区、城中村、厂中村等在城市开发建设中由于各种原因被遗忘的角落;另一种是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民进城后搭建工棚居住而形成的棚户区。上述三种观点背后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诸如城中村、城郊结合部、棚户区是否是贫民窟,并逐渐形成了对城市的这些边缘空间进行彻底改造、适当宽容和顺其自然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在政府看来,“贫民窟”是拉美陷进“大城市病”的标志,其相伴而生的是犯罪、吸毒、卖淫等罪恶行为,这也与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理念背道而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要加大棚户区改造力度,2015-2017年要改造城市危房、城中村在内的各类棚户区住房1800万套。这是保障城市低收入群体住房保障的重大社会政策。但事实上,据潘毅、任焰调查,我国城市中的外来人口大多数都居住在诸如城中村、城郊结合部、工厂宿舍等边缘空间。[2]这些空间在降低城市发展成本、加速城市化进程、农民工市民化等均扮演着重要功能,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阶梯”。[3][4]那问题在于,随着乡城人口迁移的加速推进与城中村、城郊结合部的加速改造,这一部分外来人口将居住何处?尽管有学者提出把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作为替代方案,但由于城市有限的公共资源、强势利益主体的态度、政策落实的差异等现实因素,这一替代方案仍然任重而道远。而产生这一系列矛盾的根源就在于,“贫民窟”这个词语没有得到公正的认识。“贫民窟”到底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意识形态问题,中国是否存在“贫民窟”,或者说“贫民窟”是否适用于中国社会?这正是本文尝试探讨的问题。
二、“贫民窟”概念溯源
19世纪80年代,英国伦敦的角落出现了最早的“贫民窟”,其意指“最差质量和最没有卫生条件的住房,是边缘行为(包括犯罪、恶性和毒品)的避难所”。[5]103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书面文字都是“黑色贫民窟”,贫民窟指的是“一个街道、小路、庭院,坐落在一个城市或城镇里,居住着许多低收入或非常贫困的人,他们的住房和生活条件是肮脏和不幸的……城市到处是肮脏的街道,充满了贫困、肮脏、堕落和品行不端的人口,如威斯敏斯特的贫民窟里充满盗贼”[6]。到20世纪末,这个词的含义更加精确和严格,如租住房屋、租住区和恶化的社区。截止目前,贫民窟并没有一个严格统一的定义,在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与地区,贫民窟具有不同的衡量标准。与之相应的是,“贫民窟”使用词语上都有所不同。在英语词源中,贫民窟译为“Slum”,其定义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住房”。巴西使用“favela”,指临时性的、不符合国家法定标准以及没有合法手续的简易建筑,有人干脆译为“危房”,与中国的“违章建筑”相似。在卡拉奇,地方用语为Katchi abadi(非永久性住所),如英语里“非正规的小块土地”。阿根廷用Villa miseria,法国用Bidonvilles,其代表住所是由铁和锡做成的。在发展中国家,“贫民窟”一词带有蔑视性,指低质量或非正规的住房。实际上,贫民窟并非含义丰富的概念,之所以造成歧义,其主要是建立在不同的经济水平与生活水平之上的。简单地讲,“贫民窟”是指“城市地区的高密度人口住房,其特点是房屋达不到标准”[7]。其最基本的特点是高密度、房屋的低标准与贫穷。在衡量是否为贫民窟时,高密度、低标准与贫穷如何衡量本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在汉语中讲,“贫民窟”是“贫民”与“窟”的合成词,其本意就是贫民的居所,而“窟”强调低标准。“贫民”是一个相对概念,它的内涵与贫困、贫穷相似。按照这样来理解,只要存在贫困的地方,贫民窟就会存在;当然,这或许按照其他国家的标准,不能算作“贫民窟”。2002年联合国专家组会议提出了一个可操作性定义,将贫民窟定义为:不充足的饮用水;不充足的卫生和基础设施;房屋质量结构差;过度拥挤;不安全的卫生状况。这个定义对于贫民窟具有很大的说服力,但是不足的是,描述性定义具有很大的操作性与灵活性。对此,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肯定有不同类型的贫民窟。从功能主义角度来说,没有贫民窟才是社会值得堪忧的现象。当然,贫民窟的形成是一个城市经济的不均等而造成的居住空间的分离与集聚的过程,单一的贫民住所并不能组成贫民窟。它是一个社区或一种社区关系。这种社区形成需要有经济、政治、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在多重原因的相互交织下构成此种社区或社区关系。贫民窟也是一个人口增长的过程,当住宅供应与人口增长出现失衡状态时,贫民窟极有可能产生。因此,在快速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墨西哥等,贫民窟成为必然的城市社会现象。
总体来看,贫民窟是在城市人口急剧增多——因乡城人口迁移、人口自然增长、战争等——与人们收入极度不均衡条件下,城市空间的分离与集聚的过程。它是快速城市化所产生的城市住宅不均衡所造成的必然现象,是人们走向城市的“阶梯”。贫民窟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1999年,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人居署认为,贫民窟应符合以下基本特点:基本公共服务缺乏、建筑结构不符合法定标准、人口密度大、生活条件安全性差、居民贫困、居住面积小等。[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中国城市内,城中村、城郊结合部与棚户区具有“贫民窟”特征,或可称之为“类贫民窟”。
三、我国城市变迁中的“类贫民窟”
与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同步,贫民窟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城市记忆里,贫民窟的历史是一部贫民窟改造的历史,特别是解放后,贫民窟在经历了徘徊阶段后,急剧下降,接近消失。从上海城市发展来看,随着外国资本的侵入,在黄浦江畔出现了以移民为主的贫民窟,随之遍布全市。但在城市再造过程中,贫民窟进入了快速改造阶段,且濒临绝迹。
(一)稳步扩建时期(1949年之前)
中国近代城市不是在民族工业的带动下内生发展起来的,而是外国资本强力作用的结果。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在各通商口岸、租界大量投资,生产了中国近代一批工厂、城市,上海就是这一工业化的结果。然而,上海并非一国的租界,而是英、美、法、日、德等多个资本主义国家租界共同所在地。在群雄割据的土地上,上海获得了自由快速的发展。随着各国资本的大量侵入,很多周边地区农民成为工厂工人,居住在苏州河两岸、黄浦江畔、工业区周围,这使得上海贫民窟初具规模。而随着战争的持续推进,周边地区的难民则成为贫民窟主力军,并在全市范围内迅猛发展。[9]18根据有关部门统计,到上海解放,全市200户以上的贫民窟达到322处,累计达20多万户家庭,居民总数近百万。[10]7上海贫民窟主要是由周边农民(经济移民)、战争移民共同组成的,他们大都居住在租界范围外,但又紧靠租界的码头、车站、铁路、工厂附近。
上海贫民窟前期居民大多来自农村,这些从农村逃亡来沪谋生的老居民,经历了艰难困苦,最终寻求到居所。大体上来说,他们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船户阶段。这些农民摇着小船经由运河来到上海,那时的苏州河上,密密麻麻的挤着這些由苇席做蓬的小船。贫穷的船主长年生活在河上,往往一住就是几年,直到船破底漏,才把破船搬上岸来。这些就是早期贫民窟的雏形,也是初来上海人的“家”。(2)滚地龙阶段。当小船过于陈旧后,主人便把破船推上岸,住在破船上或利用船篷材料搭个“滚地龙”——仅用几张苇席弯成半圆形搭成的十分淡薄、矮小的窝棚——栖身。(3)棚户阶段。大多数上海原始居民经历了几年的苦苦积蓄后,才买些毛竹、稻草和着泥土搭建起草棚,以此定居下来。[11]110111随着“一·二八”“八·三一”战争的爆发,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战区经历了严重破坏,某些近郊的市镇成了一片废墟。受到租界保护的租界边缘成为难民们的逃亡地,原来留下的一些空地,马上盖满了“滚地龙”。随着人数的增多,这些贫民窟发展到后期,草棚占据多数,其中比较高大、有玻璃窗、不破不漏的只是极少数,而这些都是流氓住的,其他普通人住不起也住不安逸。[10]23这些棚屋都是用几根毛竹做柱子,竹笆上摸泥做墙,用破木板或草帘、破布做门,地面是高低不平而又很潮湿的泥土,在破墙开个小洞算做窗子。这些简陋的棚屋经不起风雨的侵袭,建好几年后就会东倒西歪、破败不堪。许多棚屋全靠相互支撑,才能勉强站立。它们都十几间、几十间连成一片,而且大都是七高八低、大小不等、密集而又凌乱。
随着外国资本的侵入,苏州河两岸密集而又零乱的大小工厂群里,有许多纺织厂、化工厂、机器厂以及砖瓦厂等。林立的工厂烟囱,时时刻刻散发出大量的烟尘和有害气体;黑色的煤灰无声无息地倾泻在河里;大量的工业废水排入河中,河水又脏又臭,遇到大水,河水上窜,流到贫民窟居民的家中。人们吸不到新鲜空气,还要吃苏州河上的臭水,饮水、洗菜、洗衣等都在其中,因为外面高昂的水价是他们不能支付的。在这里,没有垃圾箱、没有厕所,藏垃垢污,无所不有。这些杂乱而密集的房屋之间,仅留下狭窄、弯曲的过道。根据解放初期统计,在15岁以上的成年居民中,产业工人只占392%,其余大部分从事人力车、三轮车与小商贩等。然而,随着上海外资与工厂数量的增多,上海周边城市的移民不断转移到这里,他们成了贫民窟的“新居民”。在解放前,虽然也存在贫民窟改造计划,如民国时期上海特别市政府采取实施的“平民住宅建设计划”,但由于政局混乱,屡遭战火,损害严重,加之用来改建的税收较少,贫民窟并没有得到改观,并呈现递增趋势。
(二)徘徊时期(1949-1978年)
上海解放后,贫民窟成为了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基地,贫民窟的住宅、就业、医疗以及生活条件都得到了极大提高。解放初期的上海,生产停顿,物价瞬息万变,不少劳动者生计断绝,贫民窟居民民不聊生。为此,人民政府开展了全面的救助措施:克服种种困难,恢复工厂生产;稳定物价;实施贫民救助。据有关部门估计,自1952年起的7年内,政府发放的贫民救济——包括现金、寒衣等——共计1400余万元,490余万人次,另有医药补助850余万元,110余万人次。[10]53在实施计划经济后,大批的贫民窟居民都参加了就业,失业人数迅速下降。在社会主义改造下,贫民窟房屋经历了各种类型的改建:
(1)自我翻修型。解放后的贫民窟,人和房子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滚地龙”被改成了草棚,原先破败不堪的草棚,经反复修葺,加高加固,甚至重新翻造;还有些家庭把草棚改建成瓦顶平房甚至是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在“一五”期间,这种分散、个别翻修改建的房屋,为数不少,“滚地龙”近乎绝迹。据估计,药水弄一地段原231间草棚,到1960年,经过翻修或改建的达80%以上。这些房屋一般都是青砖墙的楼房、明净的玻璃窗、整齐的门户以及新鲜的空气,并安装有电灯,部分还铺着地板。然而,由于土地限制,这种住房空间都不是很大,并缺乏卫生设施、用水设施,居民们的日常生活还是不太方便。
(2)政府改造型。为了改善居民的卫生条件,增加游息场所,在市政建设中,有些棚户区被改造成公园和绿地,而棚户区的居民被安置在一片片瓦顶平房中。这种所谓的“简屋”一般由政府贴款修理,布局合理,密度适当,房屋面积也适当增大。1959年后,一部分棚户居民在建筑部门的帮助下,成片地把草棚翻造成简屋或二三层的楼房。这些房屋一部分材料是由政府供应,另一部分是居民们自行购买或旧有材料充分利用而成,调动了人们改造房屋的积极性。
(3)新工房型。還有一部分棚屋变成了新工房,在拆除一批草棚和陈旧房屋的基础上,盖起了新的职工住宅,也翻造了一部分旧式弄房。经过几年的改造,原来草棚密集的贫民窟,面貌大变。截止1969年,草棚面积急剧下降,“滚地龙”房屋所剩无几。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贫民窟经过了整修、改建,但是作为上海市域的贫民窟面积并未明显改变,可能较解放前还有所增加。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解放后,上海经济迅速复苏,行政区划业进入大调整时期,原本郊区邻县所在的贫民窟划入了上海区域内,使得贫民窟内居民人数有增无减;二是十年动乱使得区域行政工作陷入停滞,贫民窟居民更加混乱不堪,[12]245这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到了根本性改观。
(三)快速改造时期(1978年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国家住房体制的改革,使得上海贫民窟面积迅速减少。为解决户籍居民的住房困难,上海市住房工作会议(1980)制定了“住宅与城市建设相结合,新区建设与旧城改造相结合,新建住宅与改善修葺旧房相结合”的住房改革方案。对旧区改造,实施了“相对集中,成片改造”的原则。在具体操作中,主要形成了四种改建方案:(1)集资组建,就是政府委托房地产投资公司,筹集各方面的资金改建旧区棚户区住宅,修建的房屋一部分用于安置原住居民,另一部分则归开发商所有,如果住房得房率不足4%,则由所在区县政府用补贴土地建设的房源进行补充。(2)联建公助,就是开发商主要投资修建、居民自愿出资参建的形式,建成的住宅作为有限产权卖给动迁居民,另一部分房屋则属开发公司所有。(3)民建公助,就是在城区政府部门主导下,由居民、职工、企事业单位、政府等多个主体出资,在棚户区区域进行修建住房,解决居民的居住问题。(4)商品房经营,就是房地产开放商征用棚户区,在城市外围修建住宅安置居民,而棚户区区位与城市外围之间的级差地租用以补贴开发商建设住宅的资金。[13]7981大概来说,棚户区的前期改造是以集资组建为主,但随着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后期的安置措施则主要为商品房经营。根据统计,“七五”期间,划给各区的补偿土地共2733公顷,可建筑面积240万平方米,其中直接用于旧区改建补贴的117万平方米,约占总量的50%。地方财政投资42亿元,新建住宅84万平方米,占市区住宅面积1/5。[14]160161自1982年,全市棚户简屋面积从400余万平方米降至291万平方米,首次低于解放初期水平。此后每年均有加大幅度的下降,到2003年,仅剩下最后的43万平方米。[12]370
可以说,具有空间景观意义的贫民窟在我国一段时间内近乎绝迹,中国“无贫民窟”话语呼之即出。然而,快速的城市发展、乡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无贫民窟”的美梦消逝殆尽。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往往也把乡村贫困以城市化的方式转移到城市,产生了庞大的城市贫困阶层,其聚居区的形成,实际上是把从乡村转移过来的贫困再进一步集中与“嵌入”到了特定的城市地域空间中。[15]同时,我国经历了国有企业改制,中国城镇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突发性、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失业洪水,《2000年社会蓝皮书》调查显示,1998年底,我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610万人,失业人口为580万人。[16]164失业的城市居民、乡城迁移人口共同构成了“城市新贫困群体”。这一部分人由于经济或制度买不起或不能买城市商品房,他们只能被安置在被人们遗忘的城中村、城郊结合部以及未改造的零星棚户简屋中。《北京城市角落调查报告》指出,这些边缘空间“常常环境脏乱差,周围各类机构少,市政基础设施不足,危旧平房集中,居民整体文化素质不高,居民总体收入偏低,实际居住人口老化,流动人口相对聚集,特殊群体聚居(如外地求学者、上访者、发廊女等)”[17]。
四、“贫民窟”的本土化阐释
在南亚、拉美,具有空间景观与社会结构双重意义的贫民窟非常普遍,但在中国,近乎绝迹的贫民窟成为了一个久违的话题。在过去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城市管理者运用国家力量有效的控制了贫民窟的再度出现与蔓延。[18]但这并不是说贫民窟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城市现象。很多批评家把贫民窟理解为资本主义罪恶的证据、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恶果,并把拉丁美洲、巴西、印度等作为反面教材予以警示。客观来讲,这不是事实。19世纪,马克思主义者就曾严厉批评过这种资本主义造就贫民窟的观点。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就指出:“穷人一般总是住在恶劣的、拥挤的、不卫生的住宅中”,“这并不是现代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它甚至也不是现代无产阶级遭受的一种和以前一切被压迫阶级所痛苦不同的特有的痛苦;相反,它几乎是同等地被伤害到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19]223贫民窟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现象。[20]从拉美地区发展历史来看,过度城市化、城市贫困化和收入分配不公平是产生贫民窟的主要原因。[3]就上海城市而言,解放前的棚户区就是典型的“原生态贫民窟”,那里破败不堪、东倒西歪、密集而脏乱的居住环境。解放后的棚户区改造并没有把贫民窟消弭于无形,而是长久存续在城市中。但到改革开放后,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例如上海实施的365危棚改造计划,中国城市大面积的棚户区基本消失殆尽。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不存在贫民窟,而是国家精心对贫民窟进行了有效的治理,从而形成了体现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巨大奇迹”。
事实上,大规模的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并不能避免贫民窟的产生。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没有完全的把握保障大量迁移人口和城市贫困人口的居住权利。[21]在早期工业化国家,恩格斯论著中的伦敦工人、狄更斯小说中描述的伯明翰和曼彻斯特、芝加哥学派调查的芝加哥城、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笔下的底层阶级都是如此。后工业化国家如印度、巴西、拉美等地自不待言。故可说贫民窟是任何工业化、城市化国家和地区的“噩梦”。贫民窟的根源就在于城市化和工业化,三者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因此有学者强调,防范城市出现贫民窟的根本出路在于创造就业速度,只有创造就业速度与农民进城速度实现均衡,贫民窟现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22]中国城市真的避免了贫民窟“噩梦”,这恐怕会引起争议。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乡城迁移人口急剧增加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城市外来居民的住宅需求与有效供给出现紧张,即政府为满足流动人口需要的、带有公共福利性质的廉租屋供给机制严重滞后、外来居民对于市场领域的商品住房有效需求不足。在社会的自适应机制下,外来居民的居住供给出路被推到了城市非正式市场领域。城中村、城郊结合部等边缘区域成为“收容”城市外来人口的空间,并进而自我演化为具有暂时实现多方共赢功能的自平衡体系。
与西方、拉美等地区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并不是农民自身所有,而是实行国家全民所有制和村集体所有制。《宪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在城市,未经国家允许修建的住房都是违法违规的,城市的管理者有权予以制止。在农村和城市郊区,村集体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事实上掌握着家庭所承包土地的实际控制权,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农村土地成为农民生存保障的重要基础。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但仍然把土地作为最后的生活保障。这种双向的流动机制,使得流动人口对城市生活并无过高要求,他们居住在环境较差的城郊结合部、城中村,只求能够挣钱。居住在城中村、城郊结合部的根本原因也大多是经济的理性使然。在这里,最大障碍就在新生代农民工。据国家统计局监测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4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68亿人,其中16-40岁的占565%。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农业生活的经历、对农民身份的认同度不高,致使“回不去”农村,但因经济、制度等方面限制又不能落户到务工城市。值得称赞的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逐渐放开了城镇户籍制度,为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城市人祛除制度障碍,这必然会带来更快速的城镇化进程。而相对的是,工业化的速度、创造就业岗位的速度就成为应对新一轮快速城镇化的巨大挑战。这是因为,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的同步协调发展很大程度上能够回避贫民窟问题。
讨论至此,我们都是从负面角度去思考贫民窟问题,强调贫民窟是不好的、不人道的,是城市罪恶的源泉。不得不承认,贫民窟确实有碍于人们提升自身的生活品质,但它并没有很多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罪恶。国际一些研究證据显示,贫民窟中居住的居民绝大部分都是勤劳守法的外来移民,一些还是农村中具有闯劲的开拓人物;社区居民之间相互帮助、相互扶持,当社区中成员失业或遇到生计问题时,一般都从亲戚朋友那里得到帮助。事实上,贫民窟并不是与暴力犯罪直接相关,暴力犯罪更容易发生在那些稀缺资源分配不均与相对剥脱感强烈的地方。[23]就上海棚户区而言,政府管理部门、新闻媒介、精英阶层等都把棚户区污名化,忽略了棚户区作为城市居住形态以及棚户区群体作为城市社会群体生态正常的组成部分。把棚户区历史放在上海整个历史来看,原先居住在棚户区的居民逐渐形成了拥有自我认同的“上海人”,而这种转变却很少被主流文化所观察和塑造,或者他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棚户区与上海城市空间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把棚户区污名化定格在历史记忆中,并成为权力阶层和主流文化继续污名城中村、城郊结合部的合理证据。[24]。在目前城市普遍存在的城中村、城郊结合部等公共空间,它们不仅给与了流动人口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增加了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而且还给农村迁移居民成为城市居民提供了过渡空间。[3]
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历程都表明,贫民窟是城市化进程中绕不开的问题,只要农村、周边中小城市大量居民流向大城市,贫民窟问题就难以避免。这不是说,我们对贫民窟就无能为力、任其发展。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发展来看,中国政府就很好地回应了城市化进程中的贫民窟现象。但随着户籍制度的逐渐放开,城市化进程中的贫民窟问题仍然需要警惕。对此,笔者认为,第一,以缩小城乡经济为目标,大力发展乡镇经济和县域经济。“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过程是由迁出地的推力或迁入地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大量农村、周边中小城市居民向大城市迁移,根本原因就在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发展乡镇和县域经济,这不仅能够减缓人口向大城市聚集的速度,而且在很大程度能够缓解在县、镇买房居住的农村居民的就业困难。第二,保障居民享有平等的社会权利,从根本上减少城市贫困现象。城市贫困与贫民窟就如孪生兄弟相伴相生的。当然,引起贫困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物资条件不足、社会权利不足、自身能力不足、脱贫动力不足等等,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权利不足。政府应从制度上赋予公民同等的权利,对社会弱势群体、底层阶级给予更多地政策关怀,保障他们作为公民的应有权利。第三,鼓励城中村、城郊结合部等边缘社区居民、租房客共同参与改造工程。国际上许多研究发现,对于贫民窟的治理,扶持比对抗更有利于减少负面影响。例如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做法是“自助式原住区提升改造”,就是鼓励土地所有者与居民共同参与进居住区的改造工程中。目前中国边缘社区改造逐渐考虑到原住户籍居民的利益,但是社区的整体规划、搬迁等改造工程还更多地是政府决策,公民参与还是有限;而对于居住于社区内的租房客基本不予考虑,极大地损害了房客的利益。当然,贫民窟的产生、改造和治理等本就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复杂课题,需要政府管理部门、专家学者、民间组织和广大民众共同出谋划策。
参考文献:
[1]迈克·戴维斯.布满贫民窟的星球[M].潘纯琳,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
[2]任焰,潘毅.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J].社会学研究,2006,(4):2133.
[3]陈友华.迁徙自由、城市化与贫民窟[J].江苏社会科学,2010(3):9398.
[4]罗峰.“过渡性市民化空间”的理论分析与现实思考[J].学习与实践,2015(12):8995.
[5]沈莹.西安市城中村居住形态更新改造模式研究[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1.
[6]James Murray.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Second edition[M].Oxford:Charendon Press,1989.
[7]MerriamWebster.The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M].Springfield:MerriamWebster Inc,1994.
[8]Karishma Busgeeth,etc.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Remote Sensing in Monitoring Informal Settlemen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here Complimentary Data Dos not Exist[C].Johannesburg:Planning Africa Conference,2008.
[9]孟眉軍.上海市棚户区空间变迁研究:1927年—至今[D].华东师范大学,2006:18.
[10]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棚户区的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11]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的上海[M].段炼,吴敏,子羽,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2]熊月之.上海通史:当代社会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3]刘勇.旧住宅区更新改造中居民意愿研究[D].同济大学,2005.
[14]徐明前.城市的文脉:上海中心城旧住区发展方式新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15]蓝宇蕴.我国“类贫民窟”的形成逻辑——关于城中村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5):147153.
[16]汝信,陆学艺,等.2000年社会蓝皮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7]赵依黛.“城中村”负外部性分析及其治理机制的探讨[J].北方经贸,2011(11):3334.
[18]漆畅青,何帆.城市化与贫民窟问题[J].开放导报,2005(6):2427.
[19]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0]秦晖.城市化:容忍贫民窟与贫民权利[J].中国市场,2008(24):1012.
[21]吕新雨.新乡土主义,还是城市贫民窟[J].开放时代,2010(4): 115135.
[22]茅于轼.防范贫民窟现象[J].上海经济,2006(1):45.
[23]Janet Gie.Crime in Cape Town 20012008:A brief analysis of reported Violent,Property and Drugrelated Crime in Cape Town[R].Cape Town:Strategic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and GIS Department,Strategic Information Branch,2009.
[24]吴俊范.上海棚户区污名的构建与传递:一个历史记忆的视角[J].社会科学,2014(8): 6777.
责任编辑:汪效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