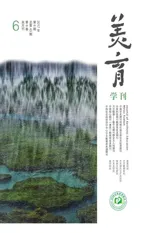论魏晋音乐的本体论建构
——“五声有自然”
2017-03-25洪永稳
洪永稳
(黄山学院 文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论魏晋音乐的本体论建构
——“五声有自然”
洪永稳
(黄山学院 文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魏晋的音乐美学理论继承了先秦以来道家“以乐论道”的历史资源,在玄学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在哲学本体论精神的关照下,形成了音乐艺术的“乐道”观思想,强调音乐的本体之道,“五声有自然”。在音乐的功能上表现为审美,与传统儒家的教化论迥然有别。在音乐的特征上表现为“平和”,和传统儒家的音乐之“和”也有区别。这一新的“乐道”观理论表征着中国音乐艺术本体论建构的形成,对于开启艺术的独立和审美的自觉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后世的中国艺术理论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价值。
乐道观;五声有自然;声无哀乐;玄学;文化语境
魏晋的音乐美学思想在中国美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出现了嵇康、阮籍等引人瞩目的音乐美学家,产生了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琴赋》和阮籍的《乐论》等重要的音乐美学专论。历来研究音乐艺术理论的学者大多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这一阶段。纵观诸多研究,或是研究某个理论家的音乐美学思想,或是阐释某篇专论的审美价值,或是讨论其音乐理论的时代背景等,旨在揭示它们对于中国的“艺术觉醒”时代主题的贡献,突出艺术独立、审美自觉的时代特征。然而,对于这个时代音乐艺术如何独立的哲学根据只是点到为止,也就是说对魏晋音乐的哲学研究关注不够。本文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在以道家为主流的玄学思潮的文化语境中,探索魏晋音乐理论中关于音乐的本体论问题,即“乐道”观思想,分析其理论形成的历史源头和产生的文化语境,阐释其“乐道”观的具体表现,揭示其理论的时代价值和影响,以进一步探究中国古代艺术本体论如何建构的课题。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当下艺术学理论的建构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魏晋音乐本体论建构的历史资源
所谓“乐道”观,就是指音乐艺术与哲学本体之“道”关系的理论,讨论音乐艺术何以独立的本体问题,在魏晋时期中国的音乐思想中出现了这一命题。魏晋“乐道”观理论的形成,有其先秦道家音乐观念的历史资源。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说:“理解甚至根本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主体性的行为,而要被认为是一种置自身于传统过程中的行动。”[1]就是说,一切认识都是从历史地在先给定的东西开始的,这种在先给定的东西是一切主观见解和主观态度的基础。艺术理论的演进也是这样,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发展的。因此,我们对魏晋“乐道观”理论的探讨,必先溯源与其密切相关的先秦道家“以乐论道”的历史传统。
徐复观先生说:“老庄所建立的最高概念是‘道’……他们所说的‘道’,若通过思辨去加以展开,以建立由宇宙落向人生的系统,它固然是理论的、形上学的意义(此在老子,即偏重在这一方面),但若通过工夫在现实人生中加以体认,则将发现他们之所谓道,实际是一种最高的艺术精神。”[2]这就是说,道家的最高范畴“道”与艺术是密切关联的。道家的开创者老子建构了以“道”为核心的哲学本体论,认为“道”是世界万物得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本依据,何为“道”?《老子·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131-134在老子看来,“道”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万物的本源,先天地生,可为天下母,万物皆生于“道”,宇宙的生成过程则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3]217其二是指宇宙变化的总规律,它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为人类遵循的自然法则,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这样的哲学本体论出发,老子对人类的音乐艺术提出了自然主义的本体论音乐观,这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大音希声”的音乐美学范畴上。《老子·四十一章》说:“……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3]211-213老子在此处说明“道”的存在方式和特征时,提出“大音希声”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意义重大:它经过魏晋玄学化以后对中国后世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以无声之乐对无以名状之‘道’的描述,同时又是以‘道’的自然本色对完美至上音乐的一种追求与界定,是崇尚自然纯朴的表现,具有重要的审美意义”。[4]后世的文学艺术正是追求这种无上之境,从而形成了中国艺术深邃灵动的独特风格,绘画中的“空白”、音乐中的“休止符”、书法中的“寓动于静”、诗歌中的“象外之象”等都是这一理论的延伸和发展,中国艺术追求的“无声胜有声”的艺术境界都无不与此相关。老子这里的“大音”就是指合乎“道”的自然规律的音乐,也就是“道之音”,这是一种哲学的抽象,不是指具体的音乐,老子把“道”也称为“大”,前文所说的“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因此,“大音”“大象”等都是在本体的层面上来说的“道”;就特征上来说,“大音”是听之不闻的,即“希声”,所谓“希声”就是指无声,老子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3]67,“大音希声”的命题就是认为最高的、最完美的音乐是“无声”,是“无”即“道”。“大音”虽然无声,但它是有声的根源,它蕴含着永恒的、至高无上的音乐精神,它朴素自然,虚静无为,至善至美,超越一切的人为的“五音”。而日常生活中的“五音”则是“大音”的表现形式,是“道之音”在现实中的具体呈现。这如同“道”的运动变化衍化世间万事万物而本身不能用感官来把握一样,“大音”衍化成世间一切美妙的音乐而自身却是无声,所以,道家学派的继承人文子在《通玄经·卷八自然》中说“故肃者,形之君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道家学派的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了以“道”为核心的本体论哲学体系,在音乐观念上,同样推崇与“道”同在的音乐。他说:“夫道,渊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无以鸣。故金石有声,不考不鸣。……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5]庄子认为,音乐之美妙在于“道”,金石因有“道”才鸣响为乐,有道之乐能在无声中听到“和声”(“独闻和焉”)。这里,庄子看到了音乐的“中和”特征,和老子所说的“声音相和”是一致的,但庄子进一步指出这种和声来自于自然,他说:“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6]庄子认为音乐之和是合乎自然的,音乐遵循人事,顺应天理,合乎自然,庄子用了“太和万物”“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清一浊”“阴阳调和”“能柔能刚”等一连串词语,旨在说明音乐与自然同在,音乐的变化与自然界的变化毫无二致,音乐的本质就是自然,自然就是“道”本身。自然是有规律的变动不居的,音乐的运动也是“变化齐一,不主故常”的。因此,能体现这种自然境界的音乐,庄子称之为“天籁”之声,与人为无涉,纯出天然,它是音乐美的最高境界。这样老庄从其本体论哲学精神的关照下对音乐的本质论和特征论作了精彩的论述,可惜,先秦不是个艺术自觉的时代,只有到魏晋,经过玄学家的提倡和改造,才会影响中国的音乐艺术理论,但先秦道家的“以乐论道”作为伽达默尔所说的传统的“先见”,为后来魏晋玄学背景中的“乐道”论思想提供了理论上的资源。它是魏晋时期的音乐理论家嵇康和阮籍的音乐理论思想的重要源头。
二、魏晋音乐本体论建构的现实文化语境
魏晋“乐道”观理论是在一定的文化时空中形成的,一定的现实文化语境是其生长的阳光雨露和土壤。这种文化语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的勃兴,由此而掀起的儒道合流的玄学思潮;其二是现实政治的黑暗导致人性的觉醒以及艺术的觉醒。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作用、互相交错、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构成了魏晋“乐道”观理论生成的二维现实文化语境。
首先,就道家哲学的勃兴而形成的玄学思潮来说,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给社会带来了重大的灾难,政权动荡,政治腐败,时局混乱,民不聊生,正如曹操《蒿里行》中所言“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时至魏晋,政治黑暗,天下才俊之士不满现实,深感人生理想的破灭,再加上汉代以来经学的支离与琐碎,士人对儒家思想的信仰产生了动摇,面对残酷的政治现实,他们不再尊尚节义,只求苟全性命,他们深感,人生如朝露,行乐需及时,人生理想的失落导致思想风气的转变,士风逐渐趋向放浪旷达的一途,以追求心灵的精神自由,道家哲学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以阮籍、嵇康、山涛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就是当时士人的典型代表,他们饮酒弹琴,蔑视礼义,好言老庄,崇尚清谈,于是,玄学风起,谈玄论道、操琴饮酒成了他们精神的寄托,“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就是这种“魏晋风流”的诗性表达。道家学说日益成为时代的主潮,《老子》《庄子》《周易》合称为“三玄”,成为士人研究的对象,中国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折,由汉代以来“独尊儒术”的经学时代转向了儒道合流的玄学时代。玄学是以老庄思想为基本构架而兼蓄儒道的哲学思潮,玄学讨论的主要问题有:本末有无之辨、自然名教之辨、言意之辨、才性之辨等。最高的主题是关于形上本体而对个体人生价值意义的思考。玄学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实现从宇宙发生论向哲学本体论转变的同时,进一步鲜明地体现了追求理想境界的理性自觉,从本体和境界两个向度推进了中国哲学和美学的发展,同时也促使了中国艺术本体论的建构;其二,实现了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的融合汇通,魏晋玄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将儒家的基本价值系统和道家的基本价值系统整合在同一个哲学命题中,提出“名教即自然”的概念。把儒家的名教纳入老庄的“自然”范畴里,正如《文心雕龙·论说篇》所言:“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7]360以老庄学说解读儒家经典成为时尚,如哲学家王弼以老庄注《周易》、何晏以老庄注《论语》等,从而形成了儒家经典的玄学化;另一方面,关于老庄本身的研究也成为一种热潮,一时涌现出许多老庄的注释和解读著作,如钟繇的《老子训》、张揖的《老子注》、阮籍的《道德论》、向秀的《庄子注》、郭象的《庄子注》、李颐的《庄子集解》、张湛的《列子注》等。道家哲学的勃兴而形成的玄学思潮深刻地影响了魏晋的文学、艺术的观念的演变和发展。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先秦以来音乐美学理论的观念和价值取向,玄道思想的盛行为魏晋音乐的“乐道”观理论奠定了哲学的基础,同时也规定了理论的向度。
其次,就人性的觉醒以及艺术的觉醒来说,魏晋时期由于现实政治的黑暗与混乱,士人对政治的失望,转而回归自身,追求自我精神的自由和解放,寻求心灵的安慰,促使了追求理想境界的理性自觉,形成了思辨、玄虚、深邃、空灵的思想风格,玄学的滋养,对于形塑中华民族的生命存在形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魏晋玄风的推动下,老庄道家以“任自然”为核心的价值观念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态度,铸造了魏晋士人玄、远、清、虚的生命境界和生活情趣,从而催动了中华民族人性的觉醒,这就是美学家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所说的“人的觉醒”。随着“人的觉醒”,人对自身生命存在的价值的洞察与反思,直接导致人的主体性的强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审美的觉醒”和“艺术的觉醒”。鲁迅先生说,魏晋是个“文学自觉”的时代,就是强调这个时代对文学审美价值的重视,对于艺术同样是觉醒的时代,艺术审美成为时尚,中国的艺术文化和艺术精神开始兴起和盛行,所以宗白华先生称之为最有“艺术精神”的时代。同时,玄学谈玄析理的特点和人生价值论的思考,又为中国的艺术文化增添了理性的色彩,使中国的文学和艺术开始走上了理性自觉的道路,在众多的艺术领域不仅有许多杰出的艺术作品诞生,还有各种艺术理论的著作出现,如在绘画上,中国的绘画艺术开始形成,人物画、山水画以及以敦煌为代表的宗教壁画在中国绘画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出现了王廙、戴逵、顾恺之等著名的画家,画学理论逐渐走向成熟,有顾恺之的“形神论”、宗炳的“以形媚道”论等;在书法上,产生了代表“魏晋风度”的“二王”书法,形成了代表民族特色的书学理论,强调“意在笔先”“以意论书”的书学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已经触及“艺术本体论”的建构问题,时代提供了“艺术本体论”建构何以可能的契机,而以“重神理而遗形骸”“重自然而轻雕饰”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美学观念,对于形成富有中国艺术特色的艺术精神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音乐的本体论建构则是这股艺术独立思潮中的时代的主题之一。
三、魏晋音乐艺术的本体论建构
音乐是中国最早受到重视的艺术,原因是它和“礼”构成了中国主流文化儒家的“礼乐文化”。音乐的审美属性早在汉代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如蔡邕的“琴操”说、马融的“通灵”说等,都触及音乐艺术的审美功能,但真正的音乐审美的独立是在魏晋,魏晋时期的主要音乐理论代表有嵇康和阮籍。嵇康从玄学的哲学本体论出发,反对儒家的音乐情感论,主张自然,反对名教,提出了自然主义(艺术独立)的音乐美学思想,明确地表达了音乐艺术与玄学之道的关系;阮籍从儒家音乐理论的内部入手批判了儒家音乐的情感本源论,阐释了音乐的本体以及音乐的特征和“道”的关系。两者的切入点不同,但都表达了音乐艺术与玄学之“道”相关联的时代主题,代表了时代的最强音,表明了魏晋时期中国学人探索艺术本体论建构的自觉。
在音乐的本体问题上,传统儒家音乐观认为音乐是来自人的内心情感,是情感的表达。《礼记·乐记》说:“凡音者生人心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8]就是说,音乐是“本在人心之感于物”的结果,这就是古代儒家关于音乐的“物感说”。魏晋的音乐理论家们针对儒家的这种观点进行大胆地颠覆。嵇康旗帜鲜明地提出音乐的本体是“自然”,它的产生是一种自然现象。在魏晋玄学中“自然”一词与“道”同义,如晋人张湛说:“自然者,道也”[9]41。嵇康从自然本体论的哲学出发,认为宇宙万物本源于自然,音乐也本于自然,他说:
夫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为五色,发为五声。声音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浊乱,其体自若,而无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变哉?……
夫五色有好丑,五声有善恶,此物之自然也。
这就是说,天地万物皆产生于自然之道,包括四季交替,五行以成,五色、五声等,音乐的本体就是自然(道),它的产生是自然而然的现象,不因为人的感情爱憎、哀乐而改变性质,即与人的情感的哀乐并无关系。这一观点对于传统的儒家可谓骇世惊闻,在这里,当今的国内也有些学者对此质疑,甚至反对嵇康否定音乐与情感的关系。其实,嵇康并不是否定音乐与情感的关系(后面关于音乐的审美论将会谈到),而是就音乐的本体问题来说的,嵇康继承道家“以乐论道”的传统,认为自然(道)生万物,音乐是万物之一种形式,也应该来源于自然之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音乐本身的产生与人的情感爱憎、哀乐没有关系,即“声无哀乐”。嵇康从两个方面论证了“声无哀乐”的命题:其一,就发生学来说,音乐的发生是独立于情感的,音有天出,情由心生,音乐是自然发生的,“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哀心藏于苦心内,遇到和声而后发”,就是说,音乐好坏,是音乐旋律、音色、音高等自身的事情,与哀乐之情无关,而音乐的哀乐之情是人的内心哀乐借助音乐之后的表达。其二,就其二者的关系来说,“和声无象”“音声无常”。嵇康认为,音乐不表达任何具体的对象,音乐的发生是自然而然的,与人心哀乐不相关,他说:“声之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声音和情感之间的联系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二者之间并无一定的必然联系。这就从音乐的产生和情感的关系方面否定了儒家音乐的情感本体论,发展了道家“以乐论道”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乐道”观思想。
无独有偶,主张这种观点的还有魏晋的另一位音乐理论家阮籍,阮籍的音乐理论思想集中地表现在《乐论》一文中。阮籍的《乐论》与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相比,两者的立论角度不同,但异途同归,阮籍是穿着儒家的外衣反对儒家的音乐本体论,他提出音乐的本源在于“道”而不在“心”,他说:
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性,体万物之生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阴阳八风之声。均黄钟中和之律,开群生万物之情气。故律吕协则阴阳和,音声适而万物类。
故八音有本体,五声有自然,其同物者,以大小相君。有自然,故不可乱,大小相君,故可得而平也。
阮籍认为,音乐是合天地之体,得万物之性,是天地八方之音、阴阳八风之声的中和之律合成的。“和”是音乐的本质特征,这和儒家《礼记·乐记》的“乐者,天地之和也”的观点是一致的,看似是坚持儒家的立场,但阮籍认为,这种“和”是合自然之道,顺天地之性,体万物之生,协阴阳之和,适万物之类。这就是说音乐之“和”是与天地万物之性为一体的,也就是合自然之道。所以他提出:“八音有本体,五声有自然”,这里的“自然”就是“道”,这就明确地表明音乐的本体是“自然”即“道”。这与儒家的音乐本体论大相径庭。儒家的经典《礼记·乐记》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8]196《礼记·乐记》认为,音乐的本源是生于人心,人心之动,物使之然,感物而动,形于声,声相应,谓之音,比音而乐,谓之乐,音乐最终的根由是人心感物而成。这就清楚地看出了阮籍的音乐本体论与儒家的音乐本体论的根本区别,而与老庄的音乐本体论是一致的,正如前面所说的,老子提倡“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论,认为最高的音乐是无声之声,是“无”即“道”,这就暗含着音乐本于“道”,庄子则提倡“天籁”之音,所谓“天籁”是天地之间自然天成之音。阮籍继承了老庄的乐道论,并明确地提出音乐“八音有本体,五声有自然”的自然主义音乐本体论。这是魏晋音乐艺术“乐道”观理论的明确表达。
综上所言,阮籍和嵇康的音乐本体论思想代表了魏晋中国音乐理论的最高成就。同时,我们也看到,阮籍和嵇康的“乐道”观与他们的哲学观“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道家思想是紧密相关的,他们反对先秦两汉以来的儒家正统思想,也不满于王弼把“名教”和“自然”统一在一个体系里,面对现实政治的黑暗,清醒地认识到儒家的“名教”对人性的戕害,继承老庄的对现实批判和怀疑的哲学精神,站在人性解放和自由的立场上,否定儒家音乐艺术本源论,强调了音乐与自然之道的关系,主张艺术独立,这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祈求精神自由、呼唤人性解放和艺术审美独立的强烈呼声。
四、魏晋音乐本体论视域下的功能、特征和意义
音乐本体论的建构也关联着音乐的功能、特征和意义。在音乐的功能上,魏晋继承汉代以来的音乐审美观,并作了进一步的强化,使之定型,这是建立在艺术本体论的基础上,嵇康和阮籍便是这种观念的代表。儒家的音乐功能观强调音乐与政治的关系,《礼记·乐记》说:“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也。”[8]204由于看重音乐与政治的关系,故儒家强调“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8]204。这就是说,音乐是政教治乱的工具,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并不是作为艺术的审美对象而存在,而是作为政治的附庸、工具而存在,这也是儒家艺术的“工具论”在音乐理论上的表现。嵇康针对儒家这种艺术“工具论”进行了猛烈的反叛。他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强调了音乐的感染效果,他说:
然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劳者歌其事,乐者舞其功。夫内有悲痛之心,则激切哀言。言比成诗,声比成音。杂而咏之,聚而听之,心动于和声,情感于苦言。嗟叹未绝,而泣涕流涟矣。夫哀心藏于苦心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无象之和声,其所觉悟,唯哀而已。
嵇康强调,音乐有很强的感人力量,人们可以借助它表达自己的感情世界,辛劳的人用音乐表达自己的劳动艰辛,快乐的人用歌舞表达自己的快乐,内心悲痛的人借音乐表达自己的悲情。音乐有表达内心情感的功能,这被当代学者陈望衡先生称之为“因借论”。所谓“因借论”就是审美主体凭借音乐艺术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怒哀乐的情感。嵇康还认为音乐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聚而听之,心动于和声,情感于苦言。嗟叹未绝,而泣涕流涟矣。”也就是说,音乐能够感发心志,激发起本来就藏在人内心的情感。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嵇康这里所说的音乐和情感的关系是就审美功能来说的,与儒家的音乐情感本源论是不同的。在嵇康看来,音乐的感染力来自于“有主之哀心”在“无象之和声”的引发下而产生的结果,这被陈望衡先生称之为“感发论”,不论是音乐的“因借论”还是“感发论”都是在“自然之道”的前提下运行的,即所谓“五声有善恶,此物之自然也”。“因借论”和“感发论”都是强调音乐的审美功能,与儒家的政治功能不同。这是中国音乐艺术史上第一次在理论上明确地定位音乐艺术的审美功能,对中国古代艺术的觉醒和独立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音乐特征上,魏晋的音乐理论强调音乐之“和”,这与传统儒家的音乐本质特征论是一致的。但魏晋人所谈的音乐之“和”又有其独特的含义,这从阮籍的相关论述中可以看出。《礼记·乐记》云:“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8]200这就是说,音乐的本质特征是“和谐”,这是一种天地之间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雷霆鼓动,风雨滋润,四时交替,日月照耀,万物化生的和谐,与天地同谐,合生气之和,这种“和谐”类似于天地万物之“和”,有上升到本体论高度的意味。阮籍接受儒家的音乐之“和”的特征论,认为音乐之和是“合天地之体,顺万物之性”,是天地之和的体现,圣人就是按照这种天地之和的原则作乐的。但同时他又吸取了老庄的自然精神,认为音乐之和更是一种“平和”,他说:“圣人立调适之音,建平和之声”,“歌咏诗曲,将以宣平和、著不逮也”,“至于乐声,平和自若”,“乐者,使人精神平和”,等等,这种“平和”与老庄的自然无为的精神是相通的。“平和”是一种简易不烦、平和淡静、与物勿扰的境界。阮籍说:“乾坤易简,故雅乐不烦;道德平淡,故五声无味。不烦则阴阳自通,无味则百物自乐,日迁善成化而不自知,风俗移易而同于是乐,此自然之道,乐之所始也。”显然,阮籍认为美妙的音乐就是一种简易不烦、平淡无味的平和之作,使人无欲,心平气定,与阴阳自通,与百物自乐,改过向善而不自知,移风易俗也是这样自然而然,这就是自然之道。阮籍的音乐特征论仍然从“自然之道”的立场进行立论,把事物的特征和事物的本体连在一起,具有理论的合理性。从“道”的高度讨论音乐之“和”的特征,这是魏晋音乐“乐道观”理论的深入和扩展。
魏晋音乐艺术的“乐道”观思想,从本体论上论述了音乐与“道”的关系,在批判儒家的音乐政治伦理功用观时,进一步强化音乐的审美功能;在音乐的特征论上,强调了音乐的自然平和的特征,把道家的思想引入其中,从而把中国人对艺术审美特征的认识推到了一个新高度,对后世的音乐理论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五声有自然”和“声无哀乐”的思想为人称道,南朝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称赞嵇康说:“叔夜之《辨声》……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人伦之英也”[7]361,《南齐书·王僧虔传》也说:“《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南齐书》,湖南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第378页。,可见深受后世的推崇。唐太宗李世民的音乐观也受其影响,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李世民和大臣讨论音乐时提出“夫音声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欢者闻之则悦,忧者听之则悲,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何有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当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10]李世民认为,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这与嵇康的“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的观点是相同的。但他认为音乐有哀乐之情,只是不能使悦者生悲,至于政治的兴亡、国家的盛衰与音乐本身没有什么关系,这种主张音乐的独立性,突破儒家“乐教”论的思想和魏晋“乐道”观的精神如出一辙。这种影响也扩撒在其他的艺术领域里,如绘画上对“神”的关注,讲究“以形媚道”,诗歌中追求“自然清新”,书法上讲究“意在笔先”等都与魏晋音乐美学的“乐道”观——“五声有自然”的思想分不开。
总之,魏晋对艺术的审美特征的重视,对艺术本体论的探究,开创了中国审美文化的新时代,在今天中国面临着艺术理论建构的重任,魏晋音乐的“乐道”观思想建构艺术的本体,强调艺术的独立,重视艺术的审美作用无疑有其重要的启示价值。
[1]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8.
[2]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9.
[3] 刘坤生.老子解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31-134.
[4] 朱黎光.老子音乐观述论[J].四川戏剧,2009(5):113-114.
[5]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299-300.
[6] 李薇.庄子[M].长春:延边人民出版社,2006:220.
[7] 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360.
[8] 礼记·乐记:四书五经本[M].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1987:196.
[9] 列子[M].张湛,注.上海:上海书店,1986:41.
[10] 旧唐书音乐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41.
(责任编辑:紫 嫣)
OntheOntologicalConstructionofMusicinWeiandJinDynasties: "TheFiveSoundsSpringfromNature"
HONG Yong-wen
(College of Literature, Huangshan Institute, Huangshan 245041, China)
The theory of music aesthetic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inherited the historical resources of Taoism since the pre-Qin dynasties. In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metaphysics 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hilosophical ontology, the idea of "Daoism through music" was proposed and the ontological nature of music was emphasized to the point of claiming that "the five sounds spring from nature." The aesthetic function of music is highlighted at the expense of the didactic Confucian aesthetics and its characteristic of "peace" also differs from the Confucian term of "harmony". This idea of "Daoism through music" represent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nt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usic art. It is therefo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autonomy of art and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and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and value for subsequent Chinese art theory.
Daoism through music; the five sounds spring from nature; music knows neither happiness nor sorrow; metaphysics; cultural context
2017-06-17
洪永稳(1962—),男,安徽舒城人,文艺学博士,黄山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西美学、文论和艺术学研究。
B83-0
A
2095-0012(2017)06-005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