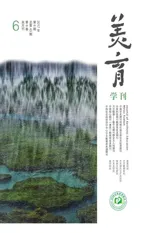论弗朗索瓦·于连对中国美学“淡”之诠释
2017-03-25叶默玄
萧 湛,叶默玄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论弗朗索瓦·于连对中国美学“淡”之诠释
萧 湛,叶默玄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法国当代汉学家于连自觉摆脱西方传统哲学视角,以“迂回”的策略揭示中国思想的迥异面貌。“淡”的美学在西方历来无人问津,但在中国传统中却持续在场。于连借助对“淡”的诠释来考察中国思想与美学,进而从外部他者视角反思西方传统,解构欧洲中心论和逻各斯主义,为重新发现中国及建立中西之间的崭新对话提供了有益的尝试。
淡;迂回与进入;中国古典美学;逻各斯中心主义
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以其深厚的汉学修养及其西方哲学背景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中国美学中“淡”这一范畴引起于连非同寻常的关注,他惊觉中西方对“淡”之认识与态度有着强烈反差,正如他所举过的鲜明例子——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不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1]Matthew 5:19这是西方人眼里的“淡”。再看中国的传统:“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2]87“君子之道,淡而不厌。”[3]40——前者认为“淡”不足取,后者视“淡”为极致。如何看待二者间的巨大差异?作为一个外来者,于连选择了认识中国的独特路径:迂回—进入,迂回乃是为了更深刻地进入。
一、何谓迂回?何谓进入?
(一)西方人的“理性”
西方世界自苏格拉底以来的主要思维方法之一是归纳法,一向把探求公理和本质作为思维目的:从个例寻求共性,从特殊过渡到普遍。逻各斯(logos)原意为“道说”,进而过渡到“说出物的本质(ousia)”——从词源衍生出的主要含义有说明、谈论、公理、理性等。德里达认为,以此为基础构成了整个西方哲学的根本思维导向,继而搭建起了西方的形而上学大厦: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e)[4]。于连认为下定义的便捷背后埋藏着隐患:如果将一切重大价值问题都抽象化地并入一个个概念和一条条公理中,必将导致认识的片面化——这并非优点,而是懒惰。中国远在西方理性主义框架之外,如果试图用西方固化思维方法强行拆解之,必是方凿圆枘,导致哲学家们为了迎合己身偏见而贬斥与己异质的中国文化与思想。
出于对逻各斯的执着,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直接把中国道家的“道”曲解为西方人的“理性”[5]126,认为中国人的思想停滞不前,缺少对这一理性本体更高更有意义的认识:中国人不仅停留在感性的或象征的阶段,我们必须注意——他们也达到了对于纯粹思想的意识,但并不深入,只停留在最浅显的思想里面。因此在这一套具体原则中,找不到对于自然力量或精神力量有意义的认识。[5]120-121
此外,同样秉持逻各斯中心主义标准,黑格尔对孔子的评价尤其不堪:
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西塞罗留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书的内容丰富,而且更好。[5]119-120
(二)于连的“迂回”之策
黑格尔从孔子的平淡言语中轻率地推论出中国思想的落后与赤贫。与之相反,于连却从这里开始反思,摸索进入中国的差异门径。他避免用生硬的西方哲学概念去考量中国,而是提出“迂回—进入”的全新方法。
何谓“迂回”?法文中的“迂回”即détour,有两层基本含意:走路时绕行/偏离主题。学者吴兴明指出在于连的语境里,“迂回”有两重含义:一指一种思想探索方法;二指一种文化取向策略。前者亦称作为方法的迂回,后者则是作为示意的迂回。[6]56两者受到于连同等重视。 从第一层含义看,“迂回”发生在中国思想内部,即不以精确下定义的方式直言。例如,作为基本范畴的儒家之“仁”,孔子却从未曾明确定义之;老子更是直指“道”完全不可经由概念(名言)来定义:道可道,非常道。[2]87第二层含义指的是中西方跨文明对话的一种努力,即经由中国这一他者视角来反观希腊。
综上,“迂回”即回避单刀直入,而是反复地逼近和体味,仿佛游离于主题之外,却始终暗自关切着主题。
(三)迂回—进入
迂回是为了更好地进入(l′accès)。从字面意义言,进入,就是从外面进到里面。于连强调文化土壤间具有绝对异质性(L′altérité),先有外在才会有所谓的由外而进入。对西方人而言,中国是最典型的“外在”(dehors)——即使同在东方的印度,在语言上也同属印欧语系(l′indo-européenne),具有根源上的家族相似性,唯有中文在血缘上彻底隔绝在他方。另一方面,“进入”暗示移位(se déplacer)、离开(quitter),所以要抛下己方固有的预设和成见,接受对方立场并从其视角看待事物。[7]4于连的“进入”,类似于柏格森的“理智同情”,是“灵魂的敞开”并完全融入对象生命之中,使认识主体的意识与对象完全同一:“这样一种理智的同情,我们通过这种共鸣置身于一个对象之内,以便与这个对象所独有而不可言传的东西相契合。”[8]
二、“淡”的进入——从一幅山水画说起
中国的“淡”何以值得称颂?在《淡之颂》中,于连分析了元末画家倪瓒的《容膝斋图》。此画大致可分近景和远景两部分,前景是稀松几棵纤树,远处则是轻勾淡抹的小丘。画卷中平淡至极的呈现方式让于连惊诧,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观看方式让他看到差异所在,成为他分析的切入口:借着画作的比照,他窥探到中西美学的根本分歧。
(一)“象”与“境”
要说明这个引发西人错愕的分歧,还得从“象”与“境”这两个范畴说起。
“象”与“境”的区分在中国美学史上是一个关键飞跃。早在老子处就提及“象”,虽已作为万物之本的“道”之客观化,但往往只指涉有形的、具象的、可视的物象,还在“滞留于物”的层面。晋-唐美学家则认为“境”更深入地表现了宇宙的本体和生命,更充分地表现了“道”——“境”比“象”走得更远,是对有限的“象”的突破。如南朝谢赫的“气韵生动”命题,提出有形之物象必须生动表现无形之气韵的美学新规定,体现出对“象外之境”的推崇,逐渐成为中国美学最高准则;唐代司空图则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命题,是对“境”的认同与扩充。如叶朗先生所言,“象”与“境”的区别在于“象”是某种孤立的、有限的物象,而“境”则是大自然或人生的整幅图景。境不仅包括“象”,而且包括“象”外的虚空。“境”不仅是一草一木一花一果,更是虚空中元气流动的整个造化自然。[9]270这就让艺术呈现从凝滞的、孤立的单一物象中解放出来,不是简单地再现生活场景,而是突破有限追寻无限,直接向生命本源作探求,去表现宇宙奥秘。
(二)透视法及其局限
为何中国绘画中从未执迷透视法(perspective)?于连认为,那是因为透视原则的追求与中国古典美学的追求迥异其趣、相背而行。
第一,中国画的境界要求“以物观物”,而透视法总是“以人观物”。如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所提命题“身即山川而取之”[10]35,直面山水的审美观照,必须具备林泉之心(超个人功利性的审美心胸),即所谓的“以玄对山水”或“以物观物”。这种主观心理状态是艺术创造和欣赏的必要前提——这个世代间普遍有效的审美规定性,体现出作为文化-审美共同体的中国人长期养成的默契,这种默契——传统对画者或观者都作出更高要求——此即于连所言“默契的基础”[11]379,这种基础排斥透视画法之唯我论“我执”。
第二,中国画讲求“气韵生动”,透视法却与此相悖。如宗白华所分析,《易经》的宇宙观是阴阳两极化生万物,生生不息的阴阳二气织成一种有节奏的生命。[12]108与之相应,山水画的空间立场永远是游移幻化,避免笔滞于物:中国画家俯瞰自然,在画境里不易寻得画者的立场,似是无人自足的境界。[12]110
第三,透视法难以完成“意境重造”的过程。透视法基于几何原理,有一个固定观察者,从其观测点统率一切目光;画要符合光学规律,所以对色彩、明暗、光源的处理就必须严格,在时空上要求定时定点。而一幅中国画却是多重视角的叠加,郭熙说得很透彻:
山,近看如此,远数里看又如此,远十数里看又如此,每远每异,所谓山形步步移也。山,正面如此,侧面又如此,背面又如此,每看每异,所谓山形面面看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数十百山之形状,可得不悉乎?山,春夏看如此,秋冬看又如此,所谓四时之景不同也。山,朝看如此,暮看如此,阴晴看如此,所谓朝暮之变态不同也。[10]39
远近、四季、朝夕、阴晴的观测变化力求表现在一幅画卷上,因此观测点不能凝固在一人/一个确切位置,而是随着景致变换的需要而流动不拘,即叶维廉所说的“观者仿佛可以跟着画中所提供的多重透视回环游视”[13]18,是以完成“意境重造”。
如宗白华所言,中国画跳出了主客观二分的视野,这从画中对远景的重视可以窥见——从世外鸟瞰的立场观照全整的律动的大自然,他的空间立场是在时间中徘徊移动,游目周览,集合数层与多方的视点谱成一幅超象虚灵的诗情画境。所以它的境界偏向远景。[12]109
(三)为什么是“远”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近”暗喻着西方的人体画,那么“远”则呼应了中国的山水画。在中西绘画比较的论著《本质或裸体》中,于连指出西方艺术倾向以人体作为表现对象,而中国艺术则青睐山水,“裸体”(le nu)在中国古典绘画中无立足之地:“中国对裸体的抗拒已到断绝可能性的地步。”[14]51何出此言?
于连认为,“裸体”反映了西方人痴迷于对人的本质下定义——它在纷繁各异的个人中寻求共性,不论时代和条件如何变化,艺术家总是忠实贯彻柏拉图的理想,寻求共通的人之“理念”。因此,“裸体”旨在将“人”(l′homme)抽象化和概念化,这种精确的呈现是西方形而上学统摄之下的呈现,它是“所有时代的亚当”[14]64。而中国则在迂回中逐步认识事物,永无止歇,并永远将目光投向远方。那么为什么说“远”就是山水画的意境?如前文所说,意境要超出有限的“象”而趋向于无限(infini),这就必然和“远”(loin*法文“loin”的其中一层释义为“从可直感的有限维度内抽身而出”(au-delà d′une limite raisonnable ou acceptable)。)的观念相联系。“意境”的美学本质是表现“道”,而“远”就在追寻道、通向道,因而也必然追求“远”。《庄子·逍遥游》所谓“游无穷”[15]16,“游乎四海之外”[15]23,“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15]33都是将“远”与“道”二者相系。西方油画用近观人体来界定本质,中国山水画则以远视追寻其本质难言的“意境”。西方将人奉为万物灵长从而让人体凌驾于自然之物,中国则将人与自然等而视之。所以这里的空间之远不是物理概念,它暗喻“道”之超出人类把握能力以外的无穷无限。
(四)为什么是“淡”
还可追问一步,为什么在于连那里,“淡”就是山水画的意境?
首先,“淡”之特性使其绝无强制性的感官霸权,而西画中,画家和观者都受制于固定观测下的紧张凝视。看一幅山水画,是不强调、不刻意、不沉溺的观测与感受,这便很自然地过渡到以平淡来表达。这一原则落实到取景上则为寂寥高远的山水,用色上则是绝少浓墨重彩。再者,“淡”的独特功效还表现在它能建立一种最适度的均衡,而这一均衡直达中国哲学范畴里最深远的“道”。于连举《老子》为例:
“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2]87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2]87
自老子发端,唐代司空图,宋代梅尧臣、苏轼等在创作或理论中继承和发展这种思想,在司空图《诗品》中,有些范畴直接谈及“淡”,如“冲淡”“洗练”“自然”“含蓄”“清奇”“飘逸”,而其中又以“冲淡”里的讨论最为集中:
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犹之惠风,荏苒在衣。阅音修篁,美曰载归。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脱有形似,握手已违。[16]5-6
司空图首先指明了这一体验的主观条件和情境:素处以默。主体在此情境下,才能领会宇宙最高的微妙——那样一种境界,像和风微拂衣裳,若有若无,在可感与不可感之间。而当我们刻意捕捉它,却只能失落:它“稀寂不可窥寻”[16]6。中国批评家认识到“道”之难寻,但并不坠入虚无主义,而是采取迂回的方式来认识“道”。“冲淡”一品就是对“道”的一种探索和呈现:引入“淡”的范畴,用鲜活生动的诗化语言来描述、重构作为第一人称(the first-person)的“我”在周遭自然环境里活生生的身体性具体-直接经验(concrete-immediate experience),以象构境(有我/无我之境),以诗解诗,而非用抽象的概念语言来涵括它。郭绍虞评注道:“冲淡本不可言说,这样一路说来,亦就活跃于纸上矣。”[16]7
若从总体上理解二十四诗品,将二十四范畴视作有机体的一部分,则会看到“淡”之精神弥漫《诗品》全篇。于连认为二十四个范畴出现的先后位置乃是精心布置的,每一品类都是对上一个的补充与调和,如第一品是“雄浑”,紧接着第二品乃是“冲淡”,冲淡以后,则是“纤秾”,而后是“沉着”:总在稍要逾越本分的时候制止住冲动,在过分讲求一种品性时,又渗入对应的补充与弥合,以达到于连所谓的“持续再造平衡”(rééquilibrage continu)[17]——“淡”与其说是一种刻板概念,不如说是一种平衡状态:随时在过渡,随时受威胁,却随时应变,正是“浓尽必枯,淡者屡深”[16]18。
(五)从“味”到“淡”的美学演变
在《淡之颂·淡在文学中转变符号》里,于连认为“淡”在中国美学史中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动态转化的,逐步上升为备受推崇的美学范畴:“淡乃是渐此成为评价诗歌优劣的标准。”[18]72在此历史流变中,“淡”又和“味”有密切关系。
最早把“味”引入美学理论的要算陆机。陆机在《文赋》中提出,文学要够“艳”,要有“味”。他把“淡”作为“味”的匮乏而加以贬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19]如于连所言,在彼时,文章中的平淡无味显然是一种瑕疵。[18]72沿此主张,刘勰继续讨论“味”,但他开始提“余味”“遗味”的概念,并站在褒扬的立场。张少康指出《文心雕龙》里多处谈及“遗味”或“余味”:如《宗经》里“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20]22,《隐秀》里“深文隐尉,余味曲包”[20]633。“余味”美学是对《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2]113的继承,于连在《淡之颂》中讨论音乐的部分认为,西方音乐早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就已经奠定下道德层面二元对立的优劣划分:一边是颓废的靡靡之音,一边是载道的雅重之乐。这种对立虽在中国亦曾出现,却不像西方那样将音乐理论建立在形而上学层面;中国传统对“余音”的推崇,更重视音乐内在性而非关社会影响。[18]52于连进一步说,如果人们喜欢余音和它的延长胜于喜欢强烈音效,那是因为前者还未被固定下来,仍然有开展的空间,藏有某种潜在的东西,所以扣人心弦。在“味”的方面的经验也是一样。[18]49
刘勰的“味”不同于陆机的味,他注重对“味”的间接、迂回的呈现,其美学可说是从“味”到“淡”的一个过渡态。如张少康所指出,刘勰强调文艺上的“隐秀”,只有具备“隐秀”特点的诗歌,才能做到“情在词外”“状溢目前”,方能有味。[21]319南朝钟嵘则更自觉更明确地把“味”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21]320在他那里,凡是概念化的思辨,都是没“滋味”可言的,文学作品应该让读者回味不尽。于连对此总结说:当诗人不再将其直观直接地透露在已变得陈腔滥调的玄学写作中,而是借有一个充满个人感动的情境去表达时,诗就被用来以可见的事物捕捉不可见的事物,以形象召唤虚无。平淡无味不再是一种令人感到枯燥乏味的抽象意义。[18]73
到唐代司空图处,用于连的话说,“淡”这个词已深入评论用语当中,且明显具有正面价值(司空图上文已论及,从略)。对平淡的偏爱,苏轼可谓司空图后继者:“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21]372“外枯”和“中膏”分别指形式的平淡质朴与意境的遗味无穷。又言:“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22]——“味外之味”已经从陆机那里的“阙大羹之遗味”反转为正面推崇,并成为最高美学律则,艺术的创造不靠华丽的辞藻、浓厚的色彩,而是借助质朴的平淡,从其中提炼出纯净的美感。“淡”既是反抽象思辨的,又是反概念言说的,亦即,“淡”是反逻各斯的。
严羽反逻各斯的倾向更坚定明晰——《沧浪诗话·诗辨》中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23]26,又说“诗有别趣,非关理也”[23]26。前者指认识要靠妙悟而非通常意义上的学识积累,这是对认识的“迂回”之策的肯定;后者认为“兴趣”不靠推论说理得来:“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者,上也”。[23]26《沧浪诗话》所标举的审美旨趣在于讲究语言的绕道迂回、艺术手法的隐而不显、认识路线的通会妙悟,故曰:“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23]26严羽不直接强调“味”与“淡”,却用“别趣”“兴趣”“妙悟”等范畴间接参与了对上面各家关于“味”和“淡”的讨论,所以他在这一美学脉络中,并未偏题。至此,严羽在对概念/意象(比量/现量)、推理/妙悟、间接/直接、质实/空灵、纤秾/冲淡等范畴的对照、分析与选择中,已基本奠定了中国诗学的本体论、方法论、内质论与目的论,也奠定了“淡”在其间的中心地位。
三、淡之颂:撬动西方“逻各斯中心”
于连可算是逻各斯主义反思序列中的突出后继者,他并未简单复述前辈的逻辑链条,而是借助不同工具,立足于差异视角来解构逻各斯权威:通过“淡”的诠释而进入中国思想;借用中国思想的成就来解构形而上学。下面重点列举来自逻各斯主义对中国思想的非难,并借着于连的策略作出回应。
(一)中国语言发展不成熟,是思维的障碍?
黑格尔认为中国思想“没有概念化”,意即中国人不擅长抽象思考,滞留在感官经验的粗浅辨识上。在一些西方人看来,这种差别也表现在语言方面:中文没有西方语言那样“精确的”文法规范,如时态、名词单复数、动词随人称和时态的相应变位,以及人称的变格等等。由此,对“言说”(logos)格外重视的西方人常质疑中国人的语言。
于连将他讨论“淡”的专著命名为“淡之颂”,在序言里模拟西人提出疑问:人人都会以为这是个悖论,因为颂赞平淡,欣赏淡而无味而不欣赏有味,这简直和人们的审美习性与价值标准背道而驰。[18]2“淡之颂”这一立论被看作悖论(paradoxe),是因为西人预设了中文“淡”的内涵等同于法文fadeur:法文fadeur或英文blandness*英译本通常把“淡”译作blandness,“淡之颂”即in praise of blandness。常见释义之一是“呆板”“无趣”“缺乏吸引力”,由此很自然派生出另一义项,即“不值得称颂的”。于连认为,想要理解中国的“淡”,就必须把fadeur或blandness在西文中的单纯意指转换为中文里的“淡”,包括它所蕴含的全部美学内涵:“如果一开始就用我们欧洲的语汇去简化中国思想,你就没移动,没离开,不会有任何发现。”[7]5显然,《淡之颂》开宗明义其讨论和探索的对象是“淡”,而不是“fadeur”。
汉语为何没有发展出印欧语言的语法?那是因为汉语追求平淡的表达,从这种平淡和简约中获得艺术家(或诗人)的自由与观者(或读者)的自由。中西语言的差异,叶维廉在《中国古典诗中的传释活动》中做过比较,他以周策纵的回文诗《绝妙世界》为例,把“舟 绕 乱 沙 白 岸 晴 芳 树 椰 幽 岛 艳 华 月 淡 星 慌 渡 斜”一列排开,再首尾相连组成一圆环,我们无论从哪个字哪个方向开始,都能成句成诗。[13]15而西方语言由于谓语的变化形式同主语密不可分且词性固定,因此绝无回文的可能。叶氏想凸显的并非中国语言能在某些场合耍小聪明、变戏法,而是欲借此揭示其高度灵活性。这种灵活性规避了逻各斯式的思维冲动——如“潮平两岸阔”,逻各斯式的释义倾向是“潮水涨起来后与两岸平齐,故而显得更开阔了”;但在中国的审美里,则直感“潮平”与“两岸阔”两个并立为和谐整体的意象——逻各斯主导下的认识方式把立体的感受捏成线性的,“都是以‘思’代‘感’,或先‘思’后‘感’的解读方式,与原句的视觉活动有违。”[13]21
就像中国山水画,视角游移,不定时定位——中国的语言不决定人称,使得情境开放,主客自由换位,任凭我们参与创造。没有时态变化,使原是作者过去的经验得以常新的面貌在我们眼前铺展开——山水艺术常提醒我们,意象的美感远非逻辑概念所能把握。显然,黑格尔没能“进入”中国,他将“道”直接译作“理性”(Rationalit?t),也就封锁了进入中国美学的可能门径,他的中国研究只不过是在臆想一个早期的西方。中国的语言不是发展迟缓,而是思考方式根本不同,于连认为一旦西方人认识到这一点,便可从外部来消解(déconstruction du dehors)逻各斯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的固执狭隘。
(二)中国美学缺乏对大自然有意义的认识?
另一个来自黑格尔的批评:中国缺乏对大自然有意义的认识。于连的回应是,中国人认识宇宙自然,总是从整体把握,不把它理解为实体的存在者,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西方传统用逻各斯严格区分虚与实、可视与可感、个别与共相、有限与无限。中国则是力图在过程中将对立消解,使之统一。于连在《本质或裸体》中说:中国画家不以模仿来再现(représente)自然,他是要再制(reproduit)自然不断进行的过程——画家画的就是宇宙。[14]62
西方人痴迷于几何所勾勒出的世界(毕达哥拉斯主义),对人体对万物有着精确度量的追求。于连认为,正是解剖、几何和逻各斯在表面上的可信任,导致了认识的片面:解剖学的思维总需要分别解剖、各自求证;而中国人和大自然的关系则更亲密。当西方的裸体以形式或量感将人体独立而出时,中国绘画则偏好描绘人物与周遭世界的亲密关系。[14]7希腊世界里的自然形式固定且绝对,是一种霸权的形式;而中国艺术中的自然则是一个生生而条理的生命过程,于连富于创见地观察到中国人画竹子画岩石的兴趣丝毫不亚于画人物,将这种自然解释学归结于中国独特的生命哲学:“人与岩石,奇特的对比,我们真的能将其比较吗?中国的评论家以为可行,因为它们出于同一原则。画岩石与画人体所需要的条件是相同的。并非他们认为人体是僵直的,而是他们认为岩石是活生生的。”[14]83逻各斯主义、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e)都最重视在场(présent),突出、固定和绝对乃是对在场的竭力强调,而隐晦、持续和清淡则是对不在场的肯定——中国采取的态度是将注意力放在隐晦且持续的事物之上。[14]81
西洋画不论流派风格怎样发展更迭,主流方式仍是以画家的眼睛瞄准所画对象,注重实景写生,比如画竹子也必须是坐在竹林前现场细摹;而中国画家却讲究“身与竹化”(苏轼语)[9]284,它要求画家进入自然山水的生命内部以体悟其生命节奏,并在空间上对其作多角度关照,超脱于固定时间与空间。
对自然力量的领悟微妙如斯,怎会缺乏有意义的认识?因此,于连的“淡”之美学对逻各斯中心论构成了有力的冲击。
(三)中国思想只有道德教训,乃是哲学的童年?
要摆脱黑格尔并非易事[24]72,黑格尔认为古代中国思想只有零星的道德训诫,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不足为观。结合上述于连观点再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黑格尔的谬误是显见的。
于连认为,孔子提供的不是居高临下式的道德教训,而是指示。在《圣人无意》中,他将孔子称作“圣人/智者”(sage),认为中国圣人的言谈风格看似平淡至极,却最少有偏见,不追求论辩意味上的压倒性胜利,是谓圣人之“无意”(sans idée)。而西方哲人们总是抱持顽固的先验立场来发号施令。于连说,“不管是对经验的某些方面,还是对他人的思想,(西方的)哲学家一开始总是要视而不见。”因为第一支点必须建立起来,即使以怀疑为出发点,落脚之处却总是确定无疑的公理定义(如笛卡尔),为了开创所谓的第一公理,忽视了在先验预设中包藏的独断性和片面性。于连大胆断言:“我们甚至可以说:哲学家在开始时视而不见的程度越大,就越天才:柏拉图、康德是伟大的哲人,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很多。”[24]11
中国的孔孟重视伦理,古罗马演说家西塞罗同样重视伦理。但相比孔子的朴素平淡,西塞罗那份长者式的说教架势要浓重得多。作为希腊文化的优秀继承人,西塞罗坚信作为万物尺度的“自然法”的存在,也就肯定了人的行为背后有恒定标准,亦即坚定了对形而上预设的信念(同柏拉图)。西塞罗说:“对任何问题的每一个阐发都应当从下定义开始。”[25]由此原则出发,他给伦理问题下了一连串定义: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友谊,什么是神性,等等。孔子怎么做的呢?他不给出僵化的定义,而是因人制宜和因时制宜地提供启示,用语简洁平淡。同样是问什么是“孝”,当鲁大夫来问时,孔子择要地回答:“无违”,因为孔子看出他有僭越君主的意图——这种春秋笔法正是于连说的“迂回”。当该大夫之子也问该问题,孔子则说:“父母唯其疾之忧”,真诚地站在为人子女的角度,提出中肯建议。轮到学生子游来问孝,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3]55对素来有孝敬心的子游提出更高的期许。这是道德相对主义吗(relativisme moral)?显然不是。孔子没有给“孝”下定义,但也绝不是说“可孝,可不孝”。他的三次回答,是以三条迂回之路殊途同归地通向“孝”,其间的启示是无穷深远的,如程颐的评注:“圣人之语,因人而变化,虽若有浅近者,而其包含无所不尽。”[3]141孔子说“疾固”[3]158,即讨厌僵化,回避下定义正是一种“疾固”的表现,因此他总是离逻各斯很远。
儒家眼中的理想人格与西塞罗不同,后者主张严格践行“自然法”,律令鲜明;前者则以平淡简素为典范,认为一个君子要秉持平淡温和的性格,在此基础上才能通达事理,明察秋毫,进而更好地实践伦理上的德性,即是《中庸》里说的:“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知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3]40可见,中国思想也有普遍性,却是彻底相异于西方哲人所提供的那种普遍性。于连认为,中国人是自愿放弃了求助定义的便利,转而进入更艰难的探索——“或者人们注定要去走那不可能真有尽头的弯路,中国思想随孔子踏上这无休止的迂回之路。”[11]232-233在此,于连以十足肯定的口吻高声颂扬了中国的思想与美学,中国思想的普遍性超越了道德训诫,中国哲学也不是哲学的童年阶段,亦不是“哲学之下者”(sous-philosophe)。[24]1
四、结语:于连的洞见与盲视
对于“淡”的美学,中国自古就不乏论述,但西人于连的阐释,不能算作对前人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洞见与补充,即使也有盲视与不足。
洞见方面:一是于连关注中西方美学研究方法上的不同。在《间距与之间》中,他用“间距”(l′altérité)一词绕过“差异”(différence):“间距不像差异那般紧抓着认同,差异既假设认同还以之为其目标。”[26]可以说,传统西方哲学的眼光总在求同,而于连的“之间”(l′entre)则在寻异,即承认两个认识对象的迥然不同,但又不是从单一的基准(西方的,或中国的)来审视,从而让双方迸发活力、俱放光彩。在对“淡”的美学阐释中,如果咬紧“差异”的比较框架不放,就会陷入认识的僵局,从早期的黑格尔到近期的罗兰·巴特无不是遭遇这种困境的体现,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仅止步于“平淡寡味”。[18]3于连的“迂回”“间距”等的提出和运用,正是对此困境的突围。二是于连借中国的“淡”来反思西方哲学,既是对“淡”作新的阐发,又是对西方作新的反思。于连眼中的“淡”,既是认识对象,又是认识手段——是攻克西方逻各斯的他山之石。于连把西方人对“淡”的惊异,联系到人类思想在遭逢苏格拉底之前的样貌,承接海德格尔的“未思”(impensée)和福柯的“异托邦”(hétérotopie)中的发问,继续探寻:拉开间距相互对视,从外部去解构(déconstruction du dehors)逻各斯-理性主义,既不把西方哲学作为基准,而把中国仅视做自身的粗陋镜像,又是在克服“文化相对主义”的取巧和懒惰。
盲视与不足之处则体现在论述上的瑕疵:于连谈论作为美学范畴的“淡”,却常将此范畴与日常语境下的“淡”混淆。《淡之颂》第三章谈倪瓒的画与道家哲学,于连说“凡味道都使人垂涎,同时又令人失望;它只诱导过客停步,引诱它,但没有满足他。”[18]19第七章谈音乐的“遗音”:“和‘遗音’一样,‘遗味’具有一种用之不尽的潜在性,它未被尝,因为叫人更想尝。”[18]50不难看出,此论说缺乏说服力,且易造成误解。当真是未被尝过的东西才最让人想尝吗?那为什么人们会以“回味无穷”来赞美已被尝过的东西?说倪瓒的画之所以杰出是因为它最不引诱人,是极不充分的理由,也是对“淡”的穿凿附会。那么“淡”若非此意,又作何解?叶维廉在《严羽与宋人诗论》中谈到诗的“无言”,说“禅宗的无言之境是真的无言,诗是语言的产物,无法真正无言。”[13]104严羽诗论追求“不落言筌”,但并不是根本地否认文字,而是希望透过学识积累兼空灵妙悟,化解语言文字的缺陷,达到似是无言的状态。这话放到“淡”的“无味”也是同理。在《淡之颂》第三章于连又说:“我们不应该在味道里寻找味道。因为味道基本上都是相对的,一旦被隔离出来就无法辨认了。”[18]20这个立论,不论是从日常经验还是科学报告都显得尤为奇怪。很明显,用这种日常化语言解释美学范畴是把“淡”的两个层面的含义混为一谈。
总的说来,《淡之颂》单独作为一部论著,结构松散,例证常显得孤立,论述缺乏严谨。但这种瑕疵又在本书与于连其他著作所形成的互文性中得到弥补:如果结合他在《迂回与进入》中对“迂回”策略的阐发、《本质或裸体》中较为系统的画论主张、《间距与之间》和《经由中国》中对“外部解构”(déconstruction du dehors)的欧洲反思路径的介绍,以及其他著作的相关论述,那么这位汉学家的“淡”之诠释,还是有章可循且有所补益的。
[1] International Bible Society.The Holy Bible: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M].Thzondervan Press,1973.
[2] 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
[3]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 豪威尔斯.德里达[M].张颖,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5]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6] 吴兴明.迂回与对视[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7).
[7] 朱立安.进入思想之门:思维的多元性[M].卓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8] 罗素.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M].陈启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7.
[9] 杨伯.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0] 郭思,杨伯.林泉高致[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1] 于连.迂回与进入[M].杜小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12] 宗白华.宗白华选集[M].叶朗,彭锋,编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13] 叶维廉.中国诗学[M].合肥: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6.
[14] 于连.本质或裸体[M].林志明,张婉真,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15] 刘文典.庄子补正[M].赵峰,诸伟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
[16] 司空图.诗品集解[M].郭绍虞,集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17] JULLIEN F. Eloge de La Fadeur:à partir de la pensée et de l′esthétique de la Chine[M]. Paris: Philippe Picquier,1991:89.
[18] 余莲.淡之颂:论中国思想与美学[M].卓立,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
[19] 陆机.陆机集[M].金涛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4.
[20] 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21] 张少康.古典文艺美学论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2] 苏轼.苏轼全集[M].傅成,穆俦,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133.
[23] 严羽.沧浪诗话校释[M].郭绍虞,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4] 于连.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M].闫素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5] 西塞罗.论老年,论友谊,论责任[M].徐奕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92.
[26] 朱利安.间距与之间:论中国与欧洲思想之间的哲学策略[M].卓立,林志明,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39.
(责任编辑:紫 嫣)
OnFrançoisJullien′sInterpretationof"Blandness"inChineseAesthetics
XIAO Zhan, YE Mo-xuan
(School of Humanit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François Jullien, a contemporary French sinologist, stands in the background of western philosophy with a unique vision to look at China and finds Chinese thought and aesthetics to b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stereotype named logo-centrism. Here is a new way to reveal the uniqueness of Chinese thought, a strategy he calls "bypass". Juliien′s idea and method not only transcend many western sinologists, but also provid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indigenous Chinese scholars. Not a category in western aesthetics, "blandness" has never been absent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Revealing the mystery of "blandness" may furnish an opportunity for communication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 and a new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François Jullien; blandness; bypass; logo-centrism; Chinese classical aesthetics
2017-07-09
萧湛(1975—),男,湖南邵阳人,美学博士,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西美学史研究;叶默玄(1994—),男,福建南平人,厦门大学中文系硕士生,主要从事中法比较诗学研究。
B83-09
A
2095-0012(2017)06-004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