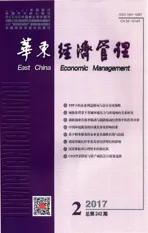敌意归因风格在组织管理中的影响研究
2017-02-23徐志超吴启涛陈思竹
李 辉,徐志超,吴启涛,陈思竹
敌意归因风格在组织管理中的影响研究
李 辉1,徐志超2,3,吴启涛4,陈思竹3
(1.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北京100038;2.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海南海口570228;3.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天津300072;4.青岛大学商学院,山东青岛266071)
文章以敌意归因风格的视角,探讨“为什么一些员工对组织的情感承诺水平总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这一现实问题。通过对四家企业的468名员工的问卷调查,构建并验证了敌意归因风格对组织情感承诺的影响模型。结果表明:敌意归因风格对员工的组织情感承诺有消极的影响;领导—下属交换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起着中介的作用;心理授权和组织支持感在领导—下属交换关系对情感承诺的影响过程中分别起着部分的中介作用。文章最后探讨了研究结果对管理实践的启示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敌意归因风格;情感承诺;领导—下属交换关系;组织支持感;心理授权
一、引言
《三国演义》中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诸葛亮刚去世,魏延马上造反,不料被身后的马岱一刀砍于马下。原来诸葛亮生前就料到魏延必反,特意提前做了安排。其实魏延的反叛早有前科,先弃刘表,又弃韩玄,最后才投了刘备。以至于诸葛亮见到魏延就要斩他,说他长有“反骨”。当然这只是文学作品中的故事。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些人经常变换工作,对组织的忠诚度不高。那么,这只是偶然现象,还是客观原因使然,或者真的是因为有些人具有背叛组织的特质?人真的有“反骨”吗?它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呢?这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虽然所谓的“反骨”只是文学作品中的词汇,但是笔者仍然倾向于认为某些特质确实能够导致员工对组织的承诺度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下面将从敌意归因风格(Hostile Attributional Style)的视角,对此问题进行解构。归因理论认为人都是“天生的心理学家”,因为人们具有自然地寻找并试图理解与其相关事件发生的原因的内在倾向[1](Heider,1958)。不过,不同人在进行归因时具有不同的倾向性,这就是所谓的“归因风格(Attributional styles)”。Selige⁃ man[2](1979)认为归因风格是一种习惯性的思考方式,在童年期或青少年期就已经养成了。敌意归因是归因风格中独特的一种,它是指人们在试图寻找事件发生的原因时,总是以一种特殊的、充满敌意的方式去思考。在这种情况下的归因结果往往是不客观的,会使人感到更多的愤怒和不满,导致更多的挫折感和进攻性[3],从而会影响员工对组织的态度。
先前的敌意归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儿童或青少年心理研究领域[3]。国外学者Hubbard等(2001)研究发现反应性攻击儿童的敌意归因同其与对方关系质量的不同而密切相关,比如对待同他们关系不好的儿童会产生更多的敌意归因[4]。国内学者寇彧等(2005)在比较攻击性儿童与亲社会儿童在社会信息加工的特点时发现,攻击性儿童具有敌意的归因倾向等特点[5]。周广东、冯丽姝(2014)发现反应性攻击儿童有较多的敌意归因偏差和负性情绪[6]。近些年,一些管理学研究者开始将其引入组织研究领域[7-8],探讨敌意归因对员工心理带来的消极影响,如刘军等(2013)认为由于员工的敌意归因倾向影响了其对上级主管行为的理解以及自身的心理认知,使得敌意归因倾向在辱虐管理行为引起员工的反抗行为过程中起重要的调节作用[9]。Liu,Liao和Loi将归因引入到辱虐管理的研究领域中,研究发现:员工的归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领导辱虐管理对于员工创造力的影响[10]。李澄锋等(2013)发现敌意归因偏差对结构高原和辱虐管理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显著,高敌意归因偏差的领导者的责他性认知思维更易于诱发辱虐下属的行为[11]。
虽然在组织管理领域,归因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远远不够。一方面,现有研究大多侧重于对员工个体层面的心理感受和行为的探讨,尚未涉及员工与他人的人际互动过程,没有考虑个体的敌意归因对整个组织环境的影响。实际上,个体的敌意归因风格会使信息传达不准确,影响员工与其他成员的有效沟通,长期如此,可能会造成个体的组织归属感和认同感低下,以及团队绩效不佳,甚至会产生高离职率等一系列消极的后果。另一方面,很少有研究探讨“敌意归因风格影响对组织态度”背后的影响机制。敌意归因风格背后影响机制的探究不仅在现有的组织成员关系中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后续的其他相关研究也具有潜在的积极作用。基于此,本研究将以“敌意归因风格”为出发点,从领导与下属交换关系的视角,探讨“为什么一些员工对组织有较低的承诺度”,并试图构建影响机制模型。
二、理论发展与研究假设
(一)敌意归因风格与情感承诺
归因理论认为人们天生就具有寻找和识别与自己相关事件发生原因的内在愿望[12]。Heider[1](1958)将原因分为内在原因(个人因素,如性格、动机、情绪、能力等)和外在原因(环境因素,如运气、他人、外在的阻力等)。Weiner[12](1985)则把归因分为三个维度:内外性(内在原因还是外在原因)、可控性(原因是否可以被人为地控制)以及稳定性(造成结果的因素是否稳定存在)。Seligeman[2](1979)的分类与Weiner[12](1985)略有不同,他提出普遍性维度(原因是普遍存在的,还是具有独特性)。归因风格作为一种认知性的人格特质,是个体在对于某一积极或消极事件进行归因过程中所具有的内在趋向[13]。依据上述的归因维度,可以将归因风格分为两类:积极归因风格和消极归因风格。积极归因风格是指人们倾向于将积极事件归因于内在的、可控的、稳定的因素,将消极事件归因于外在的、不可控的和不稳定的因素。
敌意归因风格是一种比较独特的归因方式,它指人们将消极结果归因于外控的、稳定的、普遍的因素(如不当监督、不公平的公司政策等)的趋势[7]。从认知角度来讲,当消极事件发生后,敌意归因风格的员工经常会将失误归咎于他人或组织;从情感角度来说,敌意归因往往会导致个体感到绝望和愤怒[7]。因此,上述两点都会影响具有敌意归因风格的个体与其他员工和领导的人际关系,进一步影响其对组织的认同。其中,与领导的关系尤为关键,因为对于员工来说领导往往是组织的代言人[28],直接代表着组织的形象[13]。尤其是在中国,领导在组织中承担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如果员工与领导没有良好的沟通和交换关系甚至产生冲突,会极大地影响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度和承诺度。另外,消极归因会导致员工将失败迁怒于组织[14]。敌意归因倾向的员工往往会认为自己本来可以成功,是因为组织的制度和政策的不合理才导致失败。长此以往,员工会感到习得无助[2],对工作和组织产生绝望感。比如,当他们没能按时完成任务或绩效过低时,会认为是由于组织的绩效指标过高,或者组织提供的信息和资源不够造成的,靠个人的努力是无法改变的。因此,如果员工常常将失败归结于组织的原因,必然会破坏其对组织的感情,降低其对组织的承诺。
实证研究也证明敌意归因风格的破坏性影响。Harvey[8]等2008年的研究表明:敌意归因风格可以通过降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提高员工的离职倾向。Douglas和Martinko[7]的研究表明:具有敌意归因风格的员工表现出更多的工作场所的侵犯行为(aggres⁃sion)。Robert和Daniel[16]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个结论,他们发现:敌意归因对于模糊情境下的侵犯行为具有良好的预测效果;而对于明确情景下的侵犯行为也具有一定的预测效应。Chiu和Peng(2008)[15]通过对台湾企业的233名员工及其下属的调查发现:敌意归因风格不仅与心理契约违背(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人际间异常行为(Interpersonal devi⁃ance)和组织异常行为(Organizational deviance)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且敌意归因风格可以调节心理契约违背的影响。
综上,笔者推断具有敌意归因风格的员工会倾向于责备组织,从而对组织有较低的情感承诺。因此,提出假设1。
H1:敌意归因风格与员工对组织的情感承诺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二)LMX与敌意归因
领导—下属交换(Leader-Member Exchange Rela⁃tionship,LMX)理论认为:由于资源与时间是有限的,领导者只能针对组织中的少部分成员建立相对特殊的关系[18]。敌意归因风格会对这个过程产生消极的阻碍作用。因为敌意归因会使员工在认知上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领导,从情绪上又经常表现出愤怒和气愤的特点,这些都会影响与领导有效的社会交换。具体而言,敌意归因至少会从以下三个方面破坏与领导的交换关系:
(1)消极的情绪表现会损害与领导的有效互动。根据Weiner的归因动机理论[12],外部不可控的归因会产生愤怒和无助的情绪。尤其是当员工认为失败是由领导原因造成的时候,对领导的态度会更加冷漠,甚至具有侵略性。这样的情绪加之于领导,必然会损坏与领导间的情感交换。在中国,对领导消极情绪的宣泄会让领导觉得“丢面子”,而在中国的社会规范中,下属是应该给领导“留面子”[20]的。因此,领导从情感上会不喜欢甚至会厌烦这样的员工。
(2)敌意归因的认知方式会增加与领导冲突的可能性。员工对领导和组织的埋怨和责备,大部分情况下不会得到领导的认同,可能会造成认知上的冲突。比如,敌意归因的员工会将工作绩效归结于领导的支持不够,或者领导安排不当,而领导则可能认为是由于员工没有努力或者不重视。认知冲突进一步发展则会引发人际冲突。华人的组织中,领导总是希望获得下属的认同、尊重甚至是感激[19],因此,会强调“立威”的过程。而敌意归因的员工经常与领导的意见相左,甚至将责任归咎于领导,显然很难获得领导的青睐,成为“圈内人”。
(3)对于失败的外部归因,会降低员工的信心,进而削弱员工的工作动机和激情。这又会进一步加剧与领导关系的恶化。一方面,领导会认为这样的员工不努力工作,甚至会认为是在故意跟自己作对。另一方面,从领导自身的绩效考虑,他们也会更喜欢工作动机强、有能力、能为团队做出积极贡献的下属。多维度的LMX中至少有两个维度的交换内容都涉及这一点(贡献与专业技能)[21]。
总之,敌意归因风格对LMX所包含的情感、贡献、专业技能和忠实四个维度的交换内容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而LMX水平的降低,又会对员工的组织承诺有破坏性的作用。如前所述,在下属的心目中,领导往往代表着组织。对于员工来说,领导不仅是组织的愿景、目标以及规章制度的传达者,更是组织具象化的体现[22]。而领导也在组织的框架内掌握着升职、加薪、辞退以及任务分配等生杀大权。因此,与领导的交换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员工对组织的承诺度。这一点在先前的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了支持。比如:Major等的研究表明领导下属交换关系与离职负相关,与组织承诺有正向关系[23]。Gerstner和Day分析同样证明了LMX与组织承诺的正相关关系[24]。综上所述,提出假设2。
H2:领导—下属交换关系(LMX)在敌意归因风格对员工的情感承诺的影响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
(三)组织支持感和心理授权的中介作用
在LMX影响情感承诺过程中至少有两种机制,一个是基本的保障,一个是充分的给予。前者表现为对其工作的支持,后者则表现为充分的授权。下面将分别讨论这两个过程。
组织支持与LMX都以社会交换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点,但两者又是完全不同的概念[28-29]。前者强调员工与组织的交换,而后者则关注员工与领导的交换。组织支持感(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POS)是指员工对组织如何看待其贡献以及是否关注其幸福感受的综合感知[30]。组织给予员工的资源和支持往往是通过领导完成的,所以员工所感知到的组织对其的支持也往往直接来源于领导。Levin⁃son[22]的组织拟人化的思想认为领导是拟人化组织的化身,员工会把领导的行为理解为组织的意图。Rhoades和Eisenberger[27]研究证明领导的支持会提高员工的组织支持感。Wayne,Shore和Liden[26](1997)也认为,在管理实践中领导与下属的交换关系直接影响着员工对组织支持的知觉。根据社会交换理论[32],如果员工感受到组织的支持,他们会以同样的态度和行为来回报组织。组织的关注满足了员工的尊重、认同、归属等社会情感需要,从而也增进员工对组织的感情,提升了对组织的情感依附和承诺。组织支持感的研究表明:组织对员工的支持可以激发同等程度的组织承诺[25]。Randall[31]等则更直接地表明:情感承诺与组织支持感显著相关。
因此,领导与下属良好的交换关系可以通过提升下属对组织支持的感知,来增进下属对组织的情感承诺,因此提出假设3。
H3:组织支持感在LMX对情感承诺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员工所感受到的组织授权,同样可以来自于和直接上司良好的社会交换。领导—下属交换理论认为:领导对与其保持良好关系的“圈内人”,会给予更多物质资源和精神鼓励[17-18]。他们会拥有更多工作的决策权,在工作中的错误也更容易被领导所包容。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组织或团队中,能够感受到更多的自由和授权的氛围。因此,与领导良好的交换关系能够提升员工对授权的感知。而心理授权的研究表明:心理授权能够促进员工对组织的承诺[32]。被授权的员工会感到自己更有能力,更能够决定工作中的方向,同时认为自己的工作更有意义,对组织的影响力更大。因此,他们更愿意留在组织中继续发展,对组织也更有感情。Chan[33]研究发现,员工在工作中感受到的心理授权与其对组织的情感承诺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整个过程来看,与领导良好的社会交换促进了员工对被授予权力的感知,而当员工感受自己在组织中拥有足够的自由,并且对组织的发展有着自己独特影响力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会把自己看成组织的一部分,产生对组织的依附感。通过这个过程,心理授权将员工与领导的个人关系,转化成了对组织的情感。因此,提出假设4。
H4:心理授权在LMX对情感承诺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4家企业的问卷调查,这4家企业分别属于电力、化工、制造、教育行业。发放问卷500份,收回468份(93.6%),有效问卷423份(90.4%)。其中,女性占41.4%,男性占58.6%;10.1%的被试为25岁以下,46.4%的被试为26岁~35岁,43.7%的被试为36岁~45岁,9.8%的被试为45岁以;5%的被试是初中及以下学历,51.4%的为高中及中专学历,43.6%的被试为大学及以上学历。
(二)研究工具
敌意归因风格:参照潘静洲等[34]编制的中国职业归因风格问卷(COASQ)的消极事件分问卷,包括5个消极事件,每个事件下面对应着三个选择题。这三个问题分别从控制点、稳定性和普遍性三个维度设计。敌意归因风格操作化为:对消极事件作外部、稳定、普遍性的归因倾向。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6。
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参考王辉等[35]修订LMXMDM的问卷,包括4个维度,共16题。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1。
组织情感承诺:采用Allen和Meyer[36]的情感承诺子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04。
组织支持感:采用Rhoades,Eisenberger和Arme⁃li[30]的组织支持感量表,包括8个项目。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40。
心理授权:采用S李超平等[38]等修订的心理授权问卷,包括工作意义、自我效能、自主性和工作影响4个维度,共12道题。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5。
以上所有量表均采用Likert 7级量表(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进行测量。
(三)数据分析
首先,分析考察了所使用问卷的信度;其次,检验了本研究的同一方法偏差;最后,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LMX、组织支持感、心理授权和情感承诺之间的关系。考虑到本次研究涉及的变量比较多,样本相对变量来说较少,根据Kishton[39]等的建议先对数据进行了打包(Parceling)处理。
四、实证分析
(一)同一方法偏差的检验
Harman单因子检验(Harman’s One-factor Test)结果显示:在主成分分析中,共有12个因子的特征根值大于1,而且最大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也只达到23.209%,未超过一般的标准40%。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同源偏差(same source bias)问题。
(二)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敌意归因风格、LMX、情感承诺、心理授权、组织支持感的平均数、标准差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见表1。各变量间有中等程度的相关,且p<0.001。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Pearson相关系数(N=423)
(三)敌意归因对员工态度的影响
首先,运用结构方程对该假设模型A1(见图1)进行检验,结果显示:c2/df=2.763,GFI=0.921,NFI= 0.903,IFI=0.936,TLI=0.920,CFI=0.936,RMSEA= 0.065。结构拟合较好(见表2所列),所有路径均显著。然后,参考已有的研究[40],构建了路径比较全面的备择模型A2,如图2所示。结构方程拟合的结果发现,A2模型部分路径并不显著,而且各拟合指数比假设模型A1略差。因此,选择拟合指数较好而且模型较简单的A1。

图1 修正模型(A1)路径

图2 假设模型(A2)路径

表2 假设模型和修正模型结构方程分析的拟合指数
从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测量模型的非标准化参数估计和标准化参数估计均比较理想,说明观察变量和潜变量有良好的对应关系,T检验均显著(p< 0.001)。因此,本研究的测量模型是有效的。

表3 测量模型的参数估计(N=423)
从表4的结果可以看到员工对消极事件的外部、稳定、普遍性的归因(敌意归因)会对领导—下属交换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47。良好的领导—下属关系会增加对员工对组织的情感承诺,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28。而这种影响还会通过心理授权和组织支持感的部分中介作用来实现。LMX对心理授权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681,心理授权对情感承诺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447。LMX对组织支持感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617,组织支持感对情感承诺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44。LMX对情感承诺的间接效应为0.476。员工敌意归因风格也会影响心理授权和组织支持感,但这种影响完全是通过LMX的完全中介作用来实现的。敌意归因对心理授权的间接效应为-0.168,对组织支持感的间接效应为-0.152。敌意归因也会对员工的情感承诺产生消极影响,但它本身并不直接影响情感承诺,而是通过上述一系列的中介作用来影响的,它对情感承诺的间接效应为-0.174。从模型A2删除的路径可以看到,敌意归因风格并不直接影响心理授权和组织支持感,而是完全通过LMX来影响的。心理授权对情感承诺的影响不需要通过组织支持感的中介作用,而是直接影响。

表4 外源变量与内源变量的效应分析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与理论贡献
本研究表明:敌意归因风格通过影响员工与领导的关系影响心理授权和组织支持感,进而影响员工对组织的情感承诺。具有敌意归因风格的员工更易于将消极结果看成是外部的、不可控制的、稳定不变的因素造成的,更重要的是他会将问题归咎于他人或者组织。这正是产生后面一系列消极后果的根源。而归因风格作为个性特征或者认知方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短时间内不会有大的波动。因此,具有敌意归因风格的员工与其他人相比,对组织有更低的承诺度,更易于背叛组织。这也是对文章开头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而这中间的影响过程则是通过与领导的交换关系来完成的。由于这样消极的归因方式所带来的认知偏差和情绪体验往往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与领导的社会交换,从而使这样的员工成为领导的“圈外人”。正像《三国演义》里的魏延与诸葛亮关系一直不好,也无法进入“刘关张”的核心圈子。在中国社会,领导往往被当成组织的化身[22],被领导边缘化就很难感受到组织的授权与支持,从而将与领导低质量的个人关系转化为较低的组织承诺。这个模型就是对开头第二个问题的回答。通过与备择模型的比较,确认敌意归因风格并不直接影响心理授权、组织支持感和情感承诺,而必须通过与领导的交换关系的中介作用才能完成。可见,与领导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确实起着桥梁般的关键作用。
在理论上,本研究扩展了归因研究尤其是工作归因风格研究的范围,将归因风格与领导—成员关系以及组织态度结合起来,以归因风格的角度解释了组织领域中的现象。另一方面,本研究丰富了领导—下属交换关系的研究,揭示了员工自身的认知风格对领导—下属交换关系的重要作用。
(二)对实践的启示
除了在内容上的理论贡献外,本研究还对管理实践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首先,在招聘过程中可以增加对敌意归因风格的考察。本研究表明敌意归因风格会带来一系列影响组织发展的消极后果。因此,企业在进行招聘时可以从源头上控制,减少具有强烈敌意归因风格员工的加入,以避免敌意归因的员工入职后所带来的额外成本。在实践过程中,既可以通过问卷法来测量员工的职业归因风格,也可以通过设置虚拟的情景对归因风格进行观察。
其次,加强积极归因倾向的培训。敌意归因风格不可能成为企业招聘的唯一标准,这就意味着难免会有一些具有这样认知风格的人进入组织。因此,对员工归因倾向的积极引导,则可以成为企业培训的重要环节。这也是本研究结果对实践的重要启示之一。虽然本文提到归因风格是比较稳定认知方式,但是研究表明个体的归因风格可以经过长时间积极的归因训练加以改变[41]。Proudfoot[41]等(2009)对166名金融销售人员经过认知行为训练,之后的4个月半内员工的离职率有明显的降低。
最后,领导在与下属互动过程中,应该留意敌意归因的影响。尽管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敌意归因会损害领导与下属的交换关系,但是作为领导在认清敌意归因这个引起冲突的潜在根源之后,在实践工作中要注意避免其消极影响。出现问题后,要主动沟通,引导他们从客观和积极的角度去认识问题,并寻找一些切实有效的方法去激励这样的员工。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结合本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未来潜在的研究方向:
第一,未来研究可从领导—员工双视角来探讨此问题。一方面,只从员工单方面收集数据,存在着同源偏差的潜在风险(尽管统计检验表明同源偏差并不严重)。另一方面,单方面的数据只能反映员工的心理状态,缺乏对领导特征的关注。未来的研究可以从领导和员工两方面收集数据,探讨领导—下属归因风格的异同对LMX以及组织态度的影响。
第二,未来研究可以构建客观测量指标。本研究着眼于员工认知方式和心理状态,侧重于内在的影响机制研究。因此,所有变量都具有主观性特点,特别是可能存在潜在的同源偏差。未来研究可以收集客观数据,从更客观的角度来反映现实状况,比如:测量真实的离职率、出勤率以及工作绩效等。
第三,未来研究可以采用纵向的研究设计。使用横截面数据来研究影响机制是具有局限性的,因为它难以客观地反映事物的发展变化。未来研究可以尝试通过追踪研究来更深入地揭示潜在的因果关系。
第四,未来研究可以将敌意归因风格扩展到其他研究领域。组织领域中的敌意归因研究主要是集中于对组织忠诚问题的探讨[7-8,18]。而实际上,敌意归因倾向所产生的认知偏差和消极的情感体验,会影响员工的工作动机[13],从而可能对工作绩效、组织公民行为、创新行为等一系列结果变量产生消极作用。总之,本研究从敌意归因的视角,探讨了“为什么某些员工对组织的情感承诺会保持在较低的水平”的问题。从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敌意归因这样的认知方式对于组织和个人的重要意义。然而,在现实工作中,员工潜在的归因风格往往被组织和管理者们所忽视。因此,企业的管理者们对此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同时,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去挖掘并揭示其在组织中的作用和影响。
参考文献:
[1]Heider F.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M]. New York:Wiley,1958.
[2]Seligman M,Schulman P.Explanatory Style as a Predictor of Productivity and Quitting among Life Insurance Sales Agent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6,50:832-830.
[3]De Castro B O,Veerman J W,Koops W,et al.Hostile At⁃tribution of Intent and Aggressive Behavior:A Meta-Analy⁃sis[J].Child Development,2002,73:1467–1486.
[4]Hubbard J A,Dodge K A,Cillessen A H,et al.The dyad⁃ic nature of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boys’reactive and proactive aggression[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1,80(2):268-280.
[5]寇彧,谭晨,马艳.攻击性儿童与亲社会儿童社会信息加工特点比较及研究展望[J].心理科学进展,2005,13(1):59-65.
[6]周广东,冯丽姝.区分两类攻击行为:反应性与主动性攻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4,30(1):105-111.
[7]Douglas S C,Martinko M J.Exploring the Role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Prediction of Workplace Aggression[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1,86:547-559.
[8]Harvey P,Harris K J,Martinko M J.The Mediated Influ⁃ence of Hostile Attributional Style on Turnover Intentions[J].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2008,22(4):333-343.
[9]刘军,王未,吴维库.关于恶意归因倾向与组织自尊作用机制的研究[J].管理学报,2013,10(2):199-205.
[10]Liu D,Liao H,Loi R.the Dark Side of Leadership:A Three-level Investigation of the Cascading Effect of Abu⁃sive Supervision on Employee Creativity[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2,55(5):1187-1212.
[11]李澄锋,田也壮,葛晶晶,等.领导者结构高原对辱虐管理的诱发研究:领导者特征与组织政治氛围的调节效应[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13,15(1):45-51.
[12]Weiner B.An Attributional Theory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Emotion[J].Psychological Review,1985,92:548-573.
[13]Peterson C.The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of Explanatory Style[J].Psychological Inquiry,1991(2):1-10.
[14]潘静洲,周晓雪,周文霞.领导—成员关系、组织支持感、心理授权与情感承诺的关系研究[J].应用心理学,2010,16(2):167-172.
[15]Chiu S F,Peng J C.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 and Employee Deviance:The Moder⁃ating Role of Hostile Attributional Style[J].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2008,73:426-433.
[16]Robert J H,Daniel B K.Hostile Attribution in Perceived Justification of Workplace Aggression[J].Psychological Reports,2003,92(1):185-194.
[17]Graen G B,Uhl-Bien M.Relationship-Based Approach to Leadership:Development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LMX)Theory of Leadership over 25 Years:Applying a Multi-level Multi-domain Perspective[J].Leadership Quarterly,1995,6(2):219−247.
[18]Graen G B,Novak M A,Sommerkamp P.The Effects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 and Job Design on Productivity and Job Satisfaction:Testing a Dual Attachment Model[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1982,30:109-131.
[19]Cheng B S,Chou L F,Farh J L.A Triad Model of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The Constructs and Measurement[J].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2000,14:3-64.
[20]Hwang K.Face and Favor:The Chinese Power Gam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7,92:944-974.
[21]Dienesch R M,Liden R C.Leader-Member Exchange Model of Leadership:A Critique and Further Development[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6,11:618-634.
[22]Levison H,Reciprocation:The 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Organization[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65,9:370-390.
[23]Major D A,Kozlomski S W J,Chao G T,et al.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of Newcomer Expectations,Early So⁃cialization Outcomes,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Role Development Factors[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95,80:418-431.
[24]Gerstner C R,Day D V.Meta-Analytic Review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 Theory:Correlates and Construct Issues[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97,82(6):827-844.
[25]Bishop J W,Scott D K,Goldsby M G.A Construct Validi⁃ty Study of Commitment and Perceived Support Variables:A Multifocal Approach across Different Team Environments[J].Group&Organization Management,2005,30(2):153-180.
[26]Wayne S J,Shore L M,Bommer W H,et al.The Role of Fair Treatment and Rewards in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Leader-Member Exchange[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2,87:590-598.
[27]Rhoades L,Eisenberger R.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2,87:698-714.
[28]Chen Z X,Tsui A S,Farh J.Loyalty to Supervisor versus OrganizationalCommitment:RelationshipstoEmployee Performance in China[J].Journal of Occupational&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2002,75:339-356.
[29]Blau P M.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J].New York:Wiley,1964,19(2):36-15.
[30]Rhoades L,Eisenberger R,Armeli S.Affective Commit⁃ment to the Organization:The Contribution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1,86(5):825-836.
[31]Randall D M,Mike P O.Affective versus Calculative Com⁃mitment:Human Resource Implications[J].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997,137(5):606-618.
[32]Janssen O.The Barrier Effect of Conflict with Superior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 Empowerment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J].Work&Stress,2004,18(1):56-65.
[33]Chan Y H.An Ontological Network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Antecedents,Moderator,Mediators and Outcomes of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J].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Section A: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2004,64(10/A):37-49.
[34]潘静洲,韩仁生,周文霞.把脉员工行为背后的原因:工作归因风格问卷的开发[J].经济管理,2012(1):104-113.
[35]王辉,牛雄鹰.领导—部属交换的多维结构及对工作绩效和情境绩效的影响[J].心理学报,2004,36(2):179-185.
[36]Allen N J,Meyer J P.The Measurement and Antecedents of Affective,Continuance and Normative Commitment to the Organization[J].Journal of Occupational Psychology,1990,63:1-18.
[37]Spreitzer G M.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in the Work⁃place:Dimensions,Measurement,and Validat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5,38(4):1442-1465.
[38]李超平,李晓轩,时勘,等.授权的测量及其与员工工作态度的关系[J].心理学报,2006,38(1):99-106.
[39]Kishton J M,Widaman K F.Unidimensional Versus Do⁃main Representative Parceling of Questionnaire Items:An Empirical Example[J].Educational&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1994,54(3):757-765.
[40]Jöreskog K G,Sörbom D.Lisrel 8:User’s Reference Guide[R].Chicago:Scientific Software International,1993.
[41]Proudfoot J G,Corr P J,Guest D E,et al.Cognitive-Be⁃havioural Training to Change Attributional Style Improves Employee Well-being,Job satisfaction,Productivity,and Turnover[J].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09,46(2):147-153.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Hostile Attributional Style on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LI Hui1,XU Zhi-chao2,3,WU Qi-tao4,CHE N Si-zhu3
(1.School of Police Administration,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38,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28,China; 3.College of Management&Economics,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China; 4.School of Business,Qingdao University,Qingdao 266071,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ostile attributional style,this study explores to answer the practical question:“Why are some em⁃ployees more likely to keep a relatively low level of affective commitment to the organizations?”.We investigate 468 employees from 4 en⁃terprises in China,build and validate the influence model of hostile attributional style on organizational affective commitment.The find⁃ings show that:The hostile attributional style has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employees’affective commitment;The leader-member exchange relationship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process;The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have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leader-member exchange relationship’s influence on affective commitment respectively.Finally,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for management practice and prospects for future research.
hostile attributional style;affective commitment;leader-member exchange relationship;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F272.9
A
1007-5097(2017)02-0143-08
[责任编辑:欧世平]
10.3969/j.issn.1007-5097.2017.02.019
2016-09-11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71402117;71402067);天津市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计划项目(S15113140)
李辉(1984-),男,山东菏泽人,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理论;
徐志超(1996-),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研究方向:公司金融,人力资源管理;
吴启涛(1973-),男,山东莱芜人,讲师,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管理;
陈思竹(1996-),女,河北青县人,工商管理专业学生,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