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与何叔衡的革命情谊
2017-02-06
谢觉哉和何叔衡都是湖南宁乡人,他俩与王凌波、姜梦周4人,号称大革命时期的“宁乡四髯”。他们4人于1904年结为盟兄弟,志同道合,五四运动后都来长沙参加革命活动,并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谢觉哉和何叔衡的友谊尤为深厚。他们两人的经历很相似,从小同乡、同学,是至好的朋友,20多岁时先后中秀才。何叔衡是谢觉哉的入党介绍人。参加革命后,他们是亲密战友。他们之间共同的理想、坚定的信念、不屈的斗争精神和深厚的友谊,被传为佳话。
两个秀才走上一条革命路
谢觉哉和何叔衡考中秀才,这对两家来说,都是祖上没有过的大喜事。按照封建礼教,两人由此就属于士绅阶级,高人一等了。左右乡邻、亲戚朋友,都以此为荣。谢觉哉和何叔衡却以此为辱。谢觉哉曾经说过:如果“不是父母在,决不干这事”。当他们在宁乡县的云山书院讲学时,曾对教育方法有所改革,反对八股文,提倡应用文、白话文,并为此而遭到官府和守旧分子的责难,被称为“学匪”。然而,谢觉哉和何叔衡都泰然处之,与之针锋相对,在社会上造成了较大的影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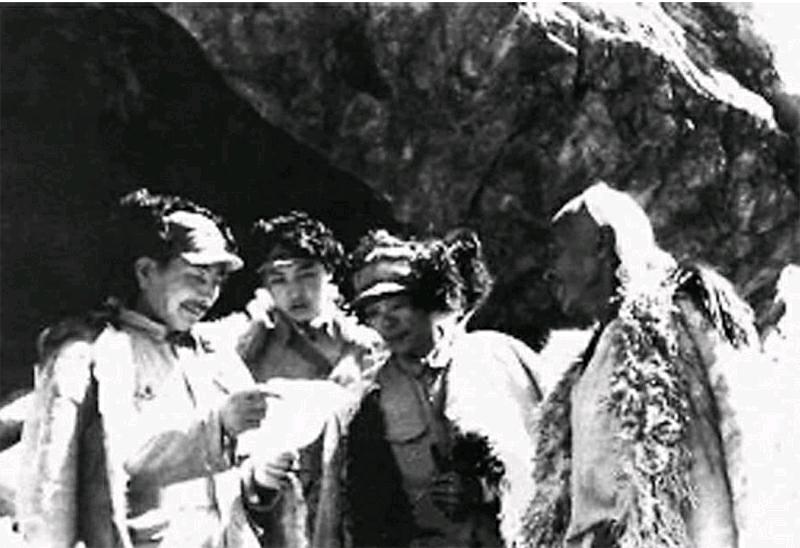
1912年,何叔衡放弃在云山书院的任教,进入湖南一师讲习科学习。1913年,谢觉哉进入湖南商校深造。何叔衡首先认识了毛泽东等青年,他与毛泽东在一块讨论个人和社会的进步问题,所得的见识,每每不忘告诉谢觉哉,阅读过的进步书刊也要推荐给谢觉哉看。他还多次对谢觉哉说“毛润之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使谢觉哉与毛泽东尚未谋面就对他有了很深的印象。何叔衡和谢觉哉就这样由同乡、同学、朋友逐步变成了坚定的志同道合者。有一年,谢觉哉的一个堂弟去世,谢觉哉的挽联是这样写的:“性命等于小埃尘,频年苦里愁中,剩下皮囊归昊土;世界若无大改革,自此生而死去,有何趣味在人间。”在这副挽联中,谢觉哉大声疾呼:“社会如不进行彻底改革,就是活着的人也没有多少趣味在人间。”
1917年冬,毛泽东、蔡和森和何叔衡发起组织新民学会。谢觉哉是由毛泽东和何叔衡介绍最早参加的会员之一。1925年,谢觉哉经何叔衡和姜梦周介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谢觉哉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十分感慨地说过:“我想我们两个秀才,不为革命者打倒的对象,而自己成为革命者,算是人生幸事。”谢觉哉和何叔衡都是老秀才,饱读诗书,但他们没有被旧学问束缚住思想,这主要是他们千方百计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正如林伯渠所说:“旧学问一经和革命学间相结合,即和最新的学问——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蔚然发出奇光。正是这道奇光,把他们引上了革命的路。”
办报纸,一个当馆长,一个当总编
1920年6月,毛泽东、何叔衡发起湖南驱张运动。军阀张敬尧被赶走后,省教育委员会派何叔衡任省通俗教育馆馆长。该馆主办有《湖南通俗报》,这张报纸以前一直被用来粉饰省政府门面,没有明确的目的和方针,每天除登载政府的一些文告和空洞无物的讲演、评论外,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引人注目的地方。
何叔衡接任馆长后,决心把报纸办好,使其成为宣传新思潮的有力工具。为此,他在选择办报人时,首先是请谢觉哉担任总编辑,同时邀请了熊瑾玎、周世钊几位老同事分别担任经理和编辑。谢觉哉的工作最辛苦。他曾在信中写道:“我在这里每天的事也不少。早晨6点多钟起床,洗面呀,做八段锦呀……差不多要7点多钟。8点钟时吃早饭,吃饭之后就要做报,要到11点才完工,最后看10分钟报吃中饭。吃中饭之后,或者要到学校里去上课,或者在屋里看书,或者看外面来的信,或者自己写信,下午算是闲一点。点灯后要预备明天的稿子,或者自己做点文章,大约要几十分钟。”
谢觉哉等人孜孜不倦的工作,使《湖南通俗报》很快有了起色。该报在劳工神圣、妇女解放、文学革命、民众联合、反对吃人的封建礼教、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军阀等方面大声疾呼,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特别爱读的,是谢觉哉在该报“小批评”“随感录”专版中发表的那些揭露社会上怪相丑态的讽刺短文。这些文章,说话不多,搔到痒处,击中要害,读者大呼过瘾,争相传阅。《湖南通俗报》的发行量也大大增加,由几百份销行到六七千份。有些中小学还把它作为课外必读之物,工人和市民读者也一天天增多,连没有读报习惯的农民也有订报的。对此,毛泽东极为称赞。而湖南当局则感到恐慌不安,惊呼《湖南通俗报》宣传了“过激主义”,说“政府自己办的报纸专门骂政府,真是岂有此理”。
在这样的呼声下,1921年5月,湖南赵恒惕当局撤了何叔衡的馆长职务,谢觉哉也被停止了总编辑的工作。但《湖南通俗报》所宣传的革命道理是封锁不了的。在毛泽东的帮助下,谢觉哉等和何叔衡密切合作,对于推动湖南早期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谢觉哉为何叔衡蒙冤仗义执言
1927年“马日事变”以后,何叔衡和谢觉哉被迫离开长沙到上海等地进行革命活动。1931年11月,他们又先后秘密进入中央苏区,参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何叔衡任工农检察部长、最高法院院长和内务部长。谢觉哉最初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后任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
在中央苏区,有一个时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坚持实事求是路线、拥护毛泽东领导的何叔衡受到排挤,被撤销了领导职务。谢觉哉对此很不理解。他与何叔衡患难与共,生死相交,彼此最熟悉。他知道何叔衡从认识毛泽东起,就是毛泽东革命活动的直接参加者和坚决支持者。1920年前后,新民学会在讨论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改造中国与世界时,何叔衡就和毛泽东一样,坚决主张采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
毛泽东信任何叔衡,对他办事的果断极为赞赏,常向人说:“叔翁做事,可当大局。”谢觉哉不理解,像何叔衡这样一位耿直诚恳、危急关头决断有方的人,为什么要受到留党察看和撤职的处分呢?为此,谢觉哉3次向毛泽东请示。第一次去,毛泽东没有吭声。谢觉哉了解毛泽东平日是有问必答的,便没有再问。过不久,谢觉哉又去请示,毛泽东还是沉默不语。第三次,谢觉哉直接问:“主席,中央为什么要整何老头?何老头有么子错?”谢觉哉把干部群众的意见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当时满心期望能得到毛泽东的答复,可是毛泽东听后仍然一言不发,慢慢地走开了。
谢觉哉感到很奇怪,后来才知道这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为了排挤毛泽东,便选择了打击毛泽东的坚定拥护者何叔衡。毛泽东有苦难言,只好沉默。
怀表和小钢刀见证两人革命友谊
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以后,党中央决定将何叔衡和其他一些同志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谢觉哉则随军参加长征。9月的一天,何叔衡在一间破旧的房子里,想方设法弄了点猪肉和一条鱼,还有他自种的蔬菜,要为谢觉哉饯行。俩人虽然过惯了患难中分手又重逢、相聚又离别的生活,但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面对生死未卜的将来,两人都默默不语。吃过饭,何叔衡送谢觉哉回到住处。分手时,他又把自己使用过的一块怀表和一把小钢刀,作为礼物送给谢觉哉。在那艰难岁月里,何叔衡为党的事业东奔西走,到处筹款,还理过财,而他自己长期过的是极为俭朴的生活。这块怀表,是何叔衡在1931年冬化装成商人从上海去中央苏区穿过敌人封锁线时使用过的。
1935年4月22日,何叔衡在福建水口遭敌袭击,壮烈牺牲。谢觉哉想不到一年前的那次饯行,竟成了他们相处几十年的最后一面,悲恸不已。1940年,何叔衡之女何实嗣在延安见到了谢觉哉。谢觉哉对何叔衡的牺牲极为悲痛,当即把那块珍贵的怀表转交给何实嗣,动情地说:“你父亲生前有句话,就是‘我要为苏维埃流下最后一滴血!今天看来,他果然为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流尽了他的最后一滴血。临别前他给了我这块怀表和一把小钢刀。小钢刀现在已经不在了,这块怀表我应该转交给你们,你们去留作纪念吧!”1945年6月13日,在何叔衡诞辰70周年之际,谢觉哉又想起了这件事,便深情地写了一首题为《旧历五月五日为何叔衡同志七十生日》的怀念诗:“怀沙屈子千秋烈,焚券婴齐一世豪。十二年前生死别,临行珍赠小钢刀。”
在诗中,谢觉哉以屈原仗节死义不易其行,自投汨罗江而身亡的比喻,歌颂何叔衡临难不屈的壮烈牺牲;又以历史上传说的齐国的冯瑗为孟尝君收债于薛,矫命以债赐诸民,因烧其券的故事作喻,赞扬何叔衡在中央苏区领导土地革命时的丰功伟绩。同时,还追忆了他珍赠怀表和小钢刀的往事。
谢觉哉对何叔衡家属的关怀
1957年3月,谢觉哉回到了阔别30年的故乡湖南宁乡县。下车伊始,他就想去看望相距数公里的何叔衡的遗孀何老太太。他知道,何叔衡自1927年被迫离家后,何老太太没有过一天的安宁生活。为躲避反动派的追捕,她不得不常常独身逃进深山密林,历尽了无数艰辛。当时,谢觉哉身边工作人员考虑到他已经74岁高龄,又坐了长途汽车,身体吃不消,就劝他第二天上午再去。谢觉哉同意了。
但事情不巧,何老太太当天深夜不幸逝世。第二天,谢觉哉刚准备出发,却传来了何老太太逝世的噩耗。谢觉哉极为悲痛,十分感叹地说:“事情这么凑巧,我为什么不能和她再见一面啊!”他决心亲自去送葬。但是天不遂人愿,这天大雨滂沱。何老太太居住的村子没修公路,虽然相距何家只有几公里,但小道又窄又滑,对于70多岁的谢觉哉实在是难以行走。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挥泪写下挽联和悼词,以此寄托哀思:
何老太太千古!
我与叔衡少同学,壮同事,同做共产党员。可惜他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了!
我这次回乡,拟来看您,而今天您又逝世了。生死永诀,不得一面,万分遗憾。何叔衡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当然您也是光荣的。您安息吧”!
谢觉哉的秘书吉世霖将挽联和悼词抱在怀中,撑着雨伞,作为谢觉哉的代表,由宁乡县的一位副县长陪同,亲手把它送到何老太太的灵前。在灵堂一侧的墙壁上,贴着何叔衡的遗书。吉世霖致哀完毕后,便一笔笔一字字,将遗书抄写下来,带回给谢觉哉看。谢觉哉双手捧着遗书,念着,哭着。
几十年来,谢觉哉对何叔衡的两个女儿何实山、何实嗣,如同亲生女儿一样看待,在政治上关怀,工作上指导,生活上爱护。1929年3月,何实嗣在上海结婚。那时何叔衡去苏联学习未回,谢觉哉得知后代表何叔衡赶来祝贺,并对何实嗣说:“你和延庆结婚,父亲又不在,我没有什么礼物,这里只有6块大洋,你去买件衣服作个纪念吧。希望你们今后更好地为党工作。”在那艰苦的年代里,党的干部是没有多少生活费的,这6块大洋是谢觉哉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何实嗣激动地接过礼物,不禁掉下眼泪。
1938年1月,何实山和丈夫陈刚跟毛泽民等一道去新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路过兰州。谢觉哉当时正担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代表,他向全体去新疆的同志介绍情况后,又单独接见了何实山和陈刚,语重心长地告诫说:“你们要看到去新疆工作的艰苦性,那里是沙漠地区。你们长期生活在内地,生活习惯可能不适应,这不要紧,慢慢会适应的。更重要的是,那里是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去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情况可能更复杂一些,要把困难想多一点,这样对开展工作有利。”
1940年5月,何实嗣从重庆来到延安。在何实嗣即将去参加征粮团出发之际,谢觉哉把她叫到身边叮嘱说:“你刚从大城市来到延安,又是从南方敌占区到陕甘宁边区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你要好好地向边区人民学习,要好好地为党工作,特别要准备吃苦,要接受党对你的新考验。”他还说:“要联系群众,要学会做群众工作。”他还特别嘱咐何实嗣“要坚决执行边区政府制定的政策,用政策去发动群众,这样才能完成任务”。临别时,谢觉哉还风趣地对她说:“如果回来带了一身蚤子,就说明你的工作做好了。”征粮工作结束后,何实嗣回到延安。谢觉哉听人说何实嗣在工作中干得不错,感到很高兴,见面第一句话就是问:“实嗣,带蚤子回么?”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何实山和何实嗣经常去看望谢觉哉。每次去,谢觉哉总是问长问短,从工作到家庭都要嘱咐。1963年后,谢觉哉患病,行动不便,但仍要夫人王定国搀扶着,一直把她们送出大门口。“文化大革命”中,何实嗣和杜延庆、何实山和陈刚夫妇都受了审查。谢觉哉虽然身患重病,但对此非常关心。有一次,何实嗣去看他,谢觉哉一见面就关切地问:“实嗣,你‘解放了吗?你姐姐‘解放了吗?”何实嗣回答说:“都‘解放了。”其实,那时谁也没有“解放”,而且陈刚已经被迫害致死了。可为了安慰重病中的谢觉哉,何实嗣没有讲真话。不过,谢觉哉从何实嗣低沉的口气中,似乎也感觉到了事情的真相,心情非常沉重。
1970年冬,何实山从四川来到北京,与何实嗣一起去看望谢觉哉。当王定国告诉谢觉哉“实山、实嗣来了”时,他显得非常高兴,在病床上艰难地睁开双眼看了她们一眼,流下了眼泪。1971年6月,谢觉哉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何实山和何实嗣再次去看他时,他已不能言语,眼神也已无光。王定国贴近谢觉哉大声喊:“谢老,实山、实嗣看你来了。”谢觉哉吃力地“嗯”了一声,微微地点了点头。何实山和何实嗣再也忍耐不住内心的悲痛,眼泪不停地往外流。她俩知道,此时此刻谢觉哉该有多少话儿要嘱咐她们啊!但他只能积压在心中,已经永远无法表达了。
(责任编辑:徐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