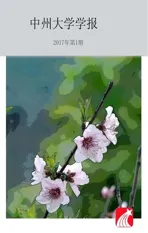市政建设中群体性冲突的心理诱因及其疏导
——基于河南J市水利市政工程建设中村民纠纷的考察
2017-01-12马润凡路旭东
马润凡,路旭东
(郑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郑州 450001)
市政建设中群体性冲突的心理诱因及其疏导
——基于河南J市水利市政工程建设中村民纠纷的考察
马润凡,路旭东
(郑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郑州 450001)
在市政建设中,村民、村干部、基层政府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与纠纷时常发生。这一群体性冲突的发生动因很多,其中,村民的“相对剥夺感”和焦虑心态、村干部的“内心委屈”等心理症结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利益取向性的偏差、宗族行动力量的过度依赖以及村域分利集团的张力,是促发上述心理的关键因素。因此,建立利益表达的双向传导解压机制,规范宗族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构建村域利益群体关系的平衡机制,是疏导和化解市政建设中村民群体性冲突的关键路径。
群体性冲突;政治心理;疏导机制
市政建设是我国城市化建设有效推进的关键环节,在繁荣城市经济、便利市民生产生活环境、促进城市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市政建设实践中,村民、村干部、基层政府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与纠纷时常发生,成为阻碍市政建设发展的痹症。其中,河南J市水利市政工程建设中的占地村村民群体性冲突更为典型。为改建扩建该市濮水河相关河道,解决多年来城区西部防汛除涝问题,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深入5个占地村向村民明确了以租期15年,每年每亩补偿1800元的标准补偿占地村民的用地政策及赔偿标准和支付办法。绝大多数村民同意以上方案。次年3月,J市新出台了调整国家建设征地的补偿标准,每年每亩补偿2600元,用地范围内附着物按有关政策规定据实清点补偿。上述工程占地村部分村民强烈要求按新征地补偿政策执行。但按规定,用地及附着物赔偿标准应按原政策执行,否则,类似工程参照此工程索赔,财政无力承担。在政策认知和执行的分歧中,一方面J市市政工程执意推进,另一方面部分村民强行阻工,甚至走上上访之路,并且抱怨村干部的态度倾向,而村干部在上级施压和村民抱怨的“夹缝”中更是尴尬无奈。这一群体性冲突的发生动因很多,本文尝试通过对河南J市水利市政工程建设冲突的个案分析,来揭示诱发村民群体性冲突的心理症结,以期提出化解冲突和增进村民市政建设认同的心理机制。
一、“被剥夺”的焦虑、夹缝中的“委屈”、认知的偏差:市政建设中群体性冲突的三大心理诱因
在河南J市水利市政工程建设中,主管部门就土地使用政策与被占地村村民产生了分歧,J市市政工程执意推进。部分村民也坚守自己立场,抱怨村干部并强行阻工,甚至上访。而村干部在上级施压和村民抱怨的“夹缝”中更是尴尬无奈。在此冲突中,村民的“被剥夺”的焦虑心态和处于夹缝中的村干部的“委屈”心理更为凸显。
村民利益“被剥夺”的焦虑是引发群体性冲突的关键心理诱因。根据土地使用补偿标准,J市按照每年每亩补偿1800元的标准补偿占地村村民的用地政策及赔偿标准和支付办法,之后J市出台了调整国家建设征地的补偿标准,每年每亩补偿2600元,用地范围内附着物按有关政策规定据实清点补偿。面对此标准,部分村民强烈不满,陷入自己利益“被剥夺”的焦虑中。在此焦虑中,在“闹大有理有利”的心理驱使下,村民群体性冲突多次发生。当工程进度到达被占地村土地并按计划施工时,被占地“当事人”就集合所在家族强行阻工闹事。一方面,家族中的老人分为两拨:年迈的妇女负责蹲坐在施工工地上和施工机械上哭天抹泪,破口大骂当地政府胡乱作为,一旦出现现场公务人员劝阻、搀扶等肢体接触,便瘫躺在工地与施工机械上,高声大呼“政府打人啦!”,以博取旁观者的同情;年迈的家族男性与家族“能人”则负责在现场与公务人员激烈交涉,依据自己对我国现有法律与制度的理解为自己家族利益辩护,对自己不利的政策和制度一概不谈。另一方面,家族的中青年作为表达不满的中坚力量,被分为留守妇女、留守家中务农的男性和外出务工或经营的家族青年等三类,并各有分工:留守务农的男性负责接应蹲坐在现场的年迈老人,一旦家族中的老人遭到劝阻或现场事态对本家族不利,便时刻准备以保护家长的名义诉诸暴力行为;留守妇女负责对闻讯赶来的村民旁观者进行动员,激发旁观者对当事人的同情,唤起围观村民也是潜在受害者的“被剥夺”的焦虑;一部分外出务工或经营的家族青年因具备一定经济条件和法律意识,负责在现场利用图文和视频影像的形式,通过传统媒体曝光和新媒体平台快速交互传播现场事态发展,以期在大众网络化的环境下引发社会舆论,还有一部分外出务工或经营的家族青年专门组织人员到国土资源部、省、市上访,致使工程严重延期。
在基层政府“责备”和村民抱怨的“夹缝”中,“内心委屈”的村干部执行力弱化。在村民心目中,被选举出作为村民利益代表的村领导班子,本应是维护村民利益的主体,是协调村域内多元利益阶层矛盾、实现乡土社会资源分配均衡的“仲裁者”。但是,夹在村民和乡镇干部之间的村干部更是尴尬无奈,更是充满“委屈”。当占地村领导班子代表上级基层政府维护乡土社会公共安全,召开村委会化解村民因占地补偿而引起的纠纷时,被占地“当事人”所在的家族的“能人”威胁道:“咱村450亩耕地被占用,假如咱们力争按新政策每年每亩2600元补偿,咱村被占地的农户每年可多得36万元的收入。地面附着物若按最高标准争取,每年可多争取赔偿800多万元。咱村的干部就要为咱村谋利,不能胳膊肘往外拐!给咱村带不来效益的村干部要他干啥?不如趁早换个当家人!”而关心工程进展的基层政府则也不断施压和责备村干部的工作不力。在“委屈”心理的趋势下,村干部与村民之间、村干部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极易产生。
基层政府对处理方式的认知偏差也是诱发村民群体性冲突的因素之一。村民群体性冲突往往伴随着多重不同性质的矛盾交杂,合理要求与无理要求交织。问题错综复杂,一旦处理不当,极易激化矛盾,引起事态升级。当村民群体性冲突发生,群众情绪激动时,基层政府往往采用“拿钱买稳定”“更换村领导班子”“处理干部”等权宜性手段,甚至违规迂回处理。这在基层干部的心理上形成了“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无事就是本事,妥协就是和谐”[1]的偏差认识。基层政府权宜性的处理农民群体性冲突的方法,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闹事者”的利益需求,但客观上也带来了负面的示范效应,致使“闹大有理有利”的心理不断强化。
二、市政建设中群体性冲突心理诱因的生发根源
1.直接利益与非直接利益的并存与交互影响
作为经济性直接利益冲突的主体,村民群体性冲突的“当事人”在与基层政府的多次博弈中,得不到预期的价值补偿,其“相对剥夺感”的焦虑不断强化。作为村民群体性冲突的旁观者,虽然与该博弈的特定利益客体和利益博弈双方并无直接利益冲突,也无明确的或直接的利益诉求,但由于冲突引发的乡土社会治安事件的频发和少数利益受损村民“代表”的社会动员,旁观的村民感受到自身也是潜在受害者。在此感受下,其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和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被点燃,引发了对群体性冲突“当事人”的情感共鸣。在情感共鸣的发酵下,“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主动参与到村民群体性冲突之中,借机发泄不满情绪。群体越是在现实的问题(即可达到的物质性目标)上发生争端,他们就越有可能寻求实现自己利益的折中方案,因此冲突的激烈性就越小。群体越是在不现实的问题上发生冲突,在冲突中激起的情感与介入的程度就越强,因此冲突就越为激烈。[2]
2.村民对宗族行动力量的非理性认同和过度依赖的制约
宗族因其地位和行动力量在村域内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直接影响和塑造着村民的心理倾向和行动能力。宗族集体行动是借助农村正式组织或非正式组织而在成员之间达成正式或非正式的契约,进而为实现潜在利益而采取的行动。宗族集体行动的有效交涉力量及其低廉的纠纷解决成本激发了村民政治参与的效能感和消极的政治行为,由此也形成了村民对宗族行动力量的非理性认同和过度依赖。但是,对内奉行狭隘私利主义,对外采取排他主义和实力优先的丛林法则,追求本宗族利益最大化,是各宗族集体行动的主导取向。因此,在村民群体性冲突中,各宗族都是集全族之力进行集体交涉,有的甚至采取暴力化方式。在频繁的宗族集体行动与无序纠纷冲突过程中,宗族“精英们”的交涉能力不断增强,推动宗族集体行动由“有动员无组织”向“强动员有组织”方向发展。在这种强大的宗族集体行动交涉力量下,基层政府只能采取延缓或妥协的权宜方法处理,而村民并没有花费较大的交涉成本就获得了宗族的私利。由此,这种“成功”的无序政治参与模式的效应不断扩大,农村宗族在解决官民纠纷问题上表现出强大的集体行动力量再次强化了村民在群体性冲突中对宗族的心理依赖。
3.利益分化加剧所引发的“争抢瓷器”现象的强化
随着乡土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不断加剧,农民阶层进一步细化,形成了占有不同农村社会资源、处于不同社会地位、具有不同集体意识和代表不同利益诉求的微观层面上的阶层群体,引发了乡土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伴随着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村域内权力格局的分配也向占有更多社会资源的利益集团或强大宗族势力倾斜。在社会公共产品供给匮乏的农村,因基层政府动员能力趋势上的弱化,农民法律契约精神和有序政治参与能力的缺失,村域内各利益集团为了私利的最大化,强力干预基层民主,在村领导班子选举中选出代表自己利益阶层或家族的代表,以求占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支配权。于是,就产生了竞相获取更大分配份额的“争抢瓷器”现象。村域基层民主选举受到农村分利集团的强性动员,选举出不同的农村分利集团的代表担任村领导班子的成员,以实现竞选成功后分享收益的格局。村民的利益意识日益觉醒并不断强化,他们在寻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实现途径。村庄内小姓宗族与占有较少社会资源的分利集团,在集体行动困境的制约下,产生了“搭便车”的心理,由群体性冲突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由“观望者”变成“支持者”。然而,由于村民支持率的下降和未能完成上级基层政府公共治理的任务,村干部在这次博弈中落败,取而代之的是代表被占地“当事人”利益的宗族精英代表。在“争抢瓷器”的竞争中,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向“村庄权贵”倾斜。村域内的利益博弈,并未因某一宗族集团单次博弈的失败而告终,反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增强了村民群体冲突的效能,必将诱发更为严重的村民群体性冲突。
三、建立心理调适机制,有效化解市政建设中村民群体性冲突
1.建立利益表达的双向传导解压机制
缓解村民“边缘化情绪”和提高村民政治参与效能感,可使村民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放松。通畅的沟通系统可以让村民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及时地宣泄不满情绪,防止和减少不满情绪的积聚。这等于在政府与村民之间安装了一个意见表达双向传导的“调压阀”,化解社会矛盾,缓解社会冲突。[3]一方面,基层政府应采取符合村民需要和特点的方式,将主导的政治价值倾向和行为模式有效传递到乡村,并引导村民认知、认可进而自觉认同主流政治信息,提升自身的利益表达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改善村干部的录用,扩大基层民主范围,提高政治体系整合村庄多元利益的能力。同时,不断强化以村委会为枢纽的基层政治沟通机制的优势,拓展村民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及时满足村民内在诉求,缓解和消除其焦虑心理。
2.规范宗族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
一是有限度地承认宗族在农村社会及乡政村治中的社会政治地位,限定宗族发展的合理边界,划定宗族等非正式组织在农村自治权力的负面清单,实现宗族在发挥社会自治功能上的权责对等,并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确立下来。二是加强农村产业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实现农村社区城镇化。实现农村社会化生产的变迁,使宗族的内部结构逐渐松散分化,同时也为宗族的可控性健康发展提供物质保障。三是以乡政村治为制度载体,大力倡导精神文明,引导乡土社会政治价值倾向,实现农民对政策和基层组织的情感认同。四是创新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建立村域内宗族参与村务协商制度和宗族与村委会交流反馈机制,强化宗族制度化参与和村委会精细化调节能力。
3.构建村域利益关系的平衡机制
村民心理的合理调适有赖于村域内利益关系的平衡。因此,建立一个平衡各阶层利益关系的均衡政治结构,调节农村各种政治力量和政治关系的制度安排,实现农村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是有效化解村民群体性冲突的前提和基础。一方面,通过建立以竞争机制、价格导向、利润导向为基础的市场机制来构建“平衡阀”,发掘乡村社会潜在的社会资本优势,实现资源有效分配。另一方面,建立群体利益非市场化的分配制度设计,运用政府财政手段这只“有形的手”,“张扬农村中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共同利益,缩小高低端收入间、贫富间的利益量差,” 在农村各阶层利益中寻找平衡点,把利益差距限制在农民承受心理可控范围内,有效防止和矫正农村社会资本向占有多数社会资源的利益集团集聚的“贫者更贫、富者更富”的现象,从而实现各利益主体间利益关系的和谐,有效消除市政建设中的村民群体性冲突。
[1]刘中起.转型期群体性社会冲突:特性、动因及其“安全阀”机制研究[J].城市观察,2011(5).
[2]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M].孙立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5-50.
[3]向德平,陈琦.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03(4).
[4]葛贤平.当代中国群体利益心理问题与政府协调机制的构建[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5).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he Psychological Inducement and its Solution of Group Conflict in Municipal Construction——Based on Villagers Dispute Investig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 J City of Henan
MA Run-fan, LU Xu-do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In the municipal construction, the conflict and disputes between the villagers, the village cadres,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and other stakeholders often occur.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is group conflict. Among them,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anxiety of the villagers and the inner grievances of the village cadres are one of the factors that can not be neglected. The bias of interest orientation, the over-reliance of clan action force and the tension of villagers’ profit distributing groups are the key factors to promote the above-mentioned psychology. Therefore, it is the key way to ease and dissolve the conflict of the villagers in the municipal construction by establishing the mechanism of bidirectional transmission and decompression of interest expression, regulating the path of clan participation in the rural governance, and building the balance mechanism of the village interest groups.
group conflict; political psychology; dredging mechanism
2016-11-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ZZ007)
马润凡(1976—),女,河南平顶山人,博士,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07
D630.8
A
1008-3715(2017)01-003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