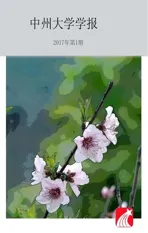国民人格的变形镜像
——谈贾平凹的《老生》
2017-01-12梁艳丹
梁艳丹
(郑州大学 文学院,郑州 450001)
国民人格的变形镜像
——谈贾平凹的《老生》
梁艳丹
(郑州大学 文学院,郑州 450001)
贾平凹的长篇新作《老生》自出版后备受关注,这是一部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小说,其批判的矛头所向就是“国民性”。《老生》并非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而是运用了夸张、变形、戏谑、意象性等叙事手法,所呈现的是一种关于书写对象的变形镜像。
《老生》;批判意识;国民性;变形镜像
《老生》[1]是贾平凹2014年推出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出现在了多个好书榜单上。从整体水准上看,也许不能说它高出了此前的《秦腔》《古炉》《带灯》等作品,但从主题到表现形式都还显示出了某些新的特质。本文围绕小说的思想主旨、叙事视角、结构特征等要素谈一下有关看法。
一
首先,这部小说在思想主旨上,与贾平凹之前的作品有着某种内在的差异。我们知道,贾平凹小说的“典型环境”就是他的商州故土,“典型人物”就是那片土地上的农民。对于他的描写对象,贾平凹的情感态度呈现出了这样一个路线图:他最初的“商州系列”作品,多是对这个地方和生活在这里的人民进行歌颂。写完《废都》,由城市重返乡土后,“视角不一样了”,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出于一种朴素的感情了”,而是“基本上都在说商州不好的东西”[2]。或者说,其文学世界,在内在精神上体现出了这样一种转变:从对心中乡土的歌颂情怀到对现实的乡土人性的理性批判意识。同样的地域文化,同样的场景及人物,但他的作品开始真正学会了“向整体说话”。一个作家,当他真正学会了“向整体说话”,对于他的描述对象能真正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他的文学世界才算是抵达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或许意味着一场隐秘的精神逃亡:由乡土家园梦的破灭,及对都市生态的不适应感(《废都》),深深地逃进写作本身那“叙述的密林”中去疗伤。《老生》基本上延续了作家自《秦腔》以来的创作精神,在作品的基调上,如果说《秦腔》还是作家为逝去的风土人情所唱的一曲挽歌的话,《老生》则是一部颇具批判色彩的变文。《老生》的叙事浸润有“清白和温暖”,但更多地是“混乱和凄苦”,是“残酷,血腥,丑恶,荒唐”。这样的题材本身也许很难给创作主体带来精神上的抚慰,但狂欢化的叙述想必会成功地补上这一功能。
《老生》独特的地方在于,它沿两个似乎有些相悖的维度,把贾平凹的小说叙事推向了一个更高的表现层次:一方面,其叙事空间伸向了更为宽广的历史场域;另一方面,人物则更加由具象走向抽象。活动在这些具体历史时空中的一个个人物,虽然也都是活生生的生存个体,但总让人觉得更像是一些符号化了的人。之所以如此,也许是因作者要触及更为深刻的内容:勾勒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基本面相,大时空跨度地漫画国民人格的现代演绎。
首先,作品描写的场景发生在秦岭里的一些村镇上。作者以“蒙太奇”的手法,在四个大的历史场域——革命战争时期、土改时期、农业合作化时期及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剪辑了一些人物故事,浮光掠影地叙述了祖辈父辈及我辈的生生死死。这里,众多人物的行动被置入不同的历史场域,但总好像有同一根神髓在连接着、主宰着各种历史环境中的人——我们不妨仍以国民性命名之。这里,看似具体的历史人物,实乃全体中国农民的一些缩影;看似在进行一种关于“大历史”的叙事,其实是在描写历史语境下琐屑人性的脸谱化表现;看似某种地域性的人性演绎,其实折射了整个国民性的现代镜像。小说所铺陈的基本事实脉络就是,历史戏剧的荒诞性与自私、蒙昧、缺乏理性和良知的人性状态,互为表里地创造着真实而又奇特的中国历史。
放眼中国新文学史可以发现,鲁迅的小说以其深入国民灵魂的力度,把国民性这一现代文学的表现主题推至顶峰。后来,赵树理、高晓声、韩少功等作家接续这一文学表现主题,都曾做出过不小的贡献。贾平凹《废都》之后的作品,尤其是这部《老生》,在新的历史视野下,与这一现代文学脉系遥相呼应。在《废都》之前,贾平凹着力描写的主要是商州这一特定地域的人与事,到《秦腔》以来的几部作品,他思考得更多的是整个中国的命运,虽然表面上看写的仍是一些特定地域的人与事。贾平凹在谈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古炉》时,说的一段话,就他这一时期的创作而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我的意思里,古炉就是中国的内涵在里头。中国这个英语词,以前在外国人眼里叫做瓷,与其说写这个古炉的村子,实际上想的是中国的事情,写中国的事情,因为瓷暗示的就是中国。而且把那个山叫做中山,也都是从中国这个角度整体出发进行思考的。写的是古炉,其实想的都是整个中国的情况。”(《古炉》封底)而《老生》,不但延续了这种思想主旨,而且提交了一种全景式的书写,堪称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底层社会和人性的一面镜子。
在这片土地上,人们没有先进的思想,没有现代意识,没有理性眼光,只是本能般地忙着生,忙着死。但不管是生还是死,都给人以某种难以尽述其味的“轻”的感觉。在第一个历史场域,老黑、匡三、三海等祖辈们,起初参加革命,就是为了能吃饱饭,能够依靠枪杆子抢财主家的粮食,能把财主的家财据为己有。游击队员们所抱的革命目的,有“消灭反动派”,有“建立秦岭苏维埃”,还有另一条:“打出秦岭进省城,一人领个女学生!”由此可见,社会各阶层人的境界也都不尽人意。他们可以随意草菅人命,可以随意像丢一袋垃圾似地丢掉自己的性命。他们做事表现出很多令人诧异的“去底线性”:缺乏对生命起码的尊重,完全无视生命本身的尊严,个体生命在“阶级敌人”的语境中经常极受其辱……在第二个历史场域,随着土改运动的开展,富户们非常恐惧地意识到“天变了”,因为“定出了成分就划分了阶级,地主富农属于反动的,是敌人”;破坏土改不但吃枪子,而且“枪子还得他家里掏钱买”。穷户们却也都惴惴不安地闹着土地和财产的分配,谁都怕分配的结果不尽自己的意。老城村忙着分地时,唱师(即作品中那个亲历了所有历史阶段的专事“唱丧”的“老生”)可真够忙的,“因为这一个乡23个村寨里不停地死人,除了正常的死亡,更多的是一些想不通事理一口气上不来死掉的地主,还有在分地过程中因分配不公斗殴打架死去的贫农”。在第三个历史场域,也即合作化运动中,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活动开展得可谓彻底。因为每个村都分摊有坏分子指标,所以大家都莫名其妙地互相检举揭发,无中生有,结果冤死的冤死,气死的气死。在对“坏分子”的惩罚和体罚上,“心红气壮”者的手法中还经常融入了某种“超绝的想象力的智慧”。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段描写:“几个人在给送来的那三个坏分子下马威,蘸了水的麻绳捆住往紧里勒,三个坏分子一个不吭声一个只吸气一个杀猪一样叫,叫着叫着就没气了。有人说:叫呀!没气了?没气了就补些气!便拿了给架子车用的充气筒,皮管子塞到肛门,嗤嗤地往里打气。”在第四个历史场域,也即改革开放后,人们的表现又如何呢?小说告诉我们,此时的人们继续发挥着“农民式的狡猾”。他们“巧妙”地利用政策,通过各种各样的弄虚作假的伎俩发家致富。在作为“主人公”之一的戏生身上,我们似乎仍能清晰地目击到阿Q、二诸葛、陈奂生们的影子。可以说,虽然历史变迁了,社会更替了,时光推移了,江山旧貌换新颜了,也改革开放了,但唯一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的就是那顽固的国民性。在它的混沌却又强势的“光线”氛围中,依然看不到人性的光辉,依然看不到高贵的人生境界。不管是“头顶上的星空”,还是“内心深处的神圣感”,在它那里引起的,好像永远都只是千百年来一成不变的漠然。
二
无需赘言,《老生》也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应该说,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始终有着现实主义的底色,呈现“国情、世情、民情”永远都是其创作的基本思想追求。不过,他显然越来越意识到,一个当代作家,必须要不断汲取文学史上各种创作手法的优长并加以革新,必须要不断转换其叙事模式——这一点与自我“风格”的纯熟以及一个作家创作的最高境界之间其实并不矛盾。要想增强作品的影响力和感染力,作家在处理人人熟知的题材时,必须在叙事技巧上尽量给读者带来某种“陌生”感。贾平凹在《老生》的后记中谈到:“写起了《老生》,我只说一切都会得心应手,没料到却异常滞涩,曾三次中断,难以为继。苦恼的仍是历史如何归于文学,叙述又如何在文字间布满空隙,让它有弹性和散发气味。”通常来看,中国作家有一种现实主义惯性,但我们也不要简单地认为这就是一种缺陷。其实,现实主义作品才是最难写的作品。某些现代主义式的随意书写,有时还能遮掩一下作者的创作水平;而现实主义的书写,则最直接地检验了作家的创作水平,使其无以遮掩——写好了,就是大手笔;写不好,就会味同嚼蜡。
自《秦腔》开始,贾平凹其实就在有意地尝试着多种叙事技巧。不难发现,贾平凹在《废都》之后的显著变化之一,是在其叙事氛围中“出现了一些意象的东西”,这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互补互渗的结果。《废都》之前的作品,如获得较多赞誉的《浮躁》,“是老小说的写法,也就是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小说写法”,或者说“严格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写法”[2]。《废都》之后,贾平凹逐渐探索出一些新的写法,其基本表现是:中国本土味及其浓厚的历史文化语境、题材内容、语言形式与人类意识、现代意识及某些现代主义的叙事技巧,有机地结合为一体。
意象性叙事氛围的成功营造固然受到了绘画中的意象主义及文学上的意识流手法的影响(贾平凹亦从事美术创作,且从美术作品中汲取了不少东西),但贾平凹在借鉴它们时,没有照搬照抄,而是不显山不露水地化用了它们,以致于读者在阅读他的小说时,既能明显感知到其中融入的现代主义表现手法,又能发觉其原创性之所在。新的叙事策略使贾平凹的小说延续了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底色,又使其美感氛围得到了强化。
贾平凹对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技巧的化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他所采取的一些独特的叙事视角。在这方面,《秦腔》和《老生》两部作品最具代表性。《秦腔》叙事情节的“非情节性”或者说写意性特征,是作家钦定的叙述者引生(一个善良、朴实、秉有生命情怀和审美情怀的“疯子”)的独特叙述口吻所引发的;《老生》叙事情节的漂移性及夸张、变形、狂欢化的话语色彩,则与作家所写的又一个特殊的叙述者——冷眼看尽人生世事的唱师——处在奄奄一息之际的那种谵妄般的叙述语气有着内在逻辑上的关联。故事中,奄奄一息的唱师像是一个游走于阴阳两界的幽魂。历史是怎么演绎的,历史中每个人的命运是怎么展开的,他好像都知道,他于冥冥之中不断道说着从他飘忽的记忆中大块掠过的历史戏剧。
也许,正是《老生》这一独特叙事视角所导致的话语氛围,使得这部现实主义长篇所反映的国民性发生了变形,使得这面反射国民性的镜子成了一面夸张的大哈哈镜,有些叙述甚至具有了某种魔幻色彩。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发生,与小说中的叙述者有关,作者本人则“狡黠”地脱身了。这部小说所采取的这一独特的叙事视角,颇为隐秘地使小说的另一叙事特征得以彰显,即叙述语言的狂欢化。其实,也正是这一点,为作家的这样一种诉求——如何使叙述“在文字间布满空隙,让它有弹性和散发气味”——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保证。俄国批评家巴赫金曾言:“小说性就是一种杂语狂欢性,其主题精神可能是悲剧性的,但其语言却“完全是欢快的,无所畏惧的,洒脱不羁和坦率直白的。”[3]187毋宁说,一代代小说家都在努力创造着这一话语事实。
显然,《老生》的叙事也具有这样的特色。其民间原生态的、不拘形迹、欢快诙谐、富于动感以及实写与想象性的描写间杂的叙述话语,确立了小说的狂欢化叙事风格。不管是在描写喜剧性的场景还是悲剧性的场景,都能给人带来阅读的快感。尤其是那众多的悲剧性场景的描写,让人为那人性的野蛮、蒙昧的表演感到寒栗的同时,快感神经也会不时为作品幽默、诙谐、生动的语气和恣意狂想性的叙述所刺激。另外,小说中还有很多描述,则属于小说独特的叙事视角自身逻辑的产物,它们带来的是另一种性质的话语狂欢,如:“唱着唱着,我感觉到了不远处的草丛里来了不吭声的豹子,也来了野猪,蹲在那里不动,还来了长尾巴的狐狸和穿了花衣服的蛇。它们没有伤害我的意思,我也不停唱,没有逃跑。唱完了,我起身要走,它们也起身各自分散,山坳里就刮开了风,草丛里开着拳大的白花,一瞬间 ,在风里全飞了,像一群鸽子。”
三
这部小说结构上的铺陈也带来了某种“陌生化”效果。这主要表现在其显在结构上的双重线索性。主线索是唱师过电影一般呓语四个历史场域的故事;次线索是放羊娃在唱师临终的床榻前听父亲从镇上请来的老师讲解《山海经》。写作因人而异,各有各的路数,而且,同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往往也是路数各有不同。那么,贾平凹为什么会想起来在这部小说里安排这样一种结构呢?笔者认为,这两重故事线索的并置并非一种偶然幻想的结果。
这固然是作家追求“陌生化”阅读效果的一次特殊的叙事路数。在后记里他谈到,《山海经》是他近几年喜欢读的一本书。“它写尽着地理,一座山一座山地写,一条水一条水地写,写各方山水里的飞禽走兽树木花草,却写出了整个中国。”也许是作家从《山海经》那种空间感很强的叙述结构中得到了某种灵感吧,“《山海经》是一座山一条水地写,《老生》是一个村一个时代地写”。于是,“只写人事”的《老生》与“只写山水”的《山海经》就有了某种神不似而形似的同构性。一方面,这种同构性增强了整个文本设置的空间感;另一方面,小说叙事的大时空感与《山海经》叙事的强烈空间感,由此形成了一种巧妙的互为特殊镜像的关系,这使得两者之间有了某种映射性。
两个有着如此历史距离的文本之间,除在叙事的空间转换方面的互相映射外,还有没有内涵上的一些延续性呢?或许有之。渗透在《山海经》中的观感、认知事物的方式,如对周围事物认知上的直感方式及巫术迷信色彩的处理方式等,到了今天,也仍有不少被延续下来。两个文本的叙事在内在质地上,都有着令现代理性无法解释的混沌性。《老生》中,不管是社会哪个阶层人物的活动,都有谶纬色彩顽固相伴,这使得作品的整个叙事场都弥漫着传统的阴森氛围。当然,也正是这一点,恰恰给唱师施展自身绝技提供了广阔的历史时空。
作家让这双重线索发生关联的方式相当独特:两个故事板块之间总是在上下文间发生着叙述上的牵连。老者每读一段《山海经》,就由小孩问问题,老者作答。老者的解答中,还不时拿今天的人生世事举例子去说明古人所表达的意思。而唱师的叙述往往接着那一老一小的问答进入状态。思绪处于谵妄状态的唱师的叙述,其叙述的开始又总是由上文“问答”中的语言符码而来。这样一来,作家为这部小说钦定的叙述者,那位奄奄一息的唱师,就像是一直处于梦与醒之间的梦游状态,而一老一小的对话又不期然地成了梦游者的提示音,引起其自由联想,及对自己过往经历的模糊追忆。而小说的叙述语体,则充分表现了叙述者当下的存在情状,具体表现为——对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的叙述与谵妄般的幻听幻视情节随意地交织在一起。
或许作家还有另外一些更深的思考,就是《山海经》的叙事看上去怪诞不经,但“或许那都是真实发生的事”;而“现在我们的故事”,在后代看来可能也是怪诞不经的事,但这的确又是真实的故事。对作家贾平凹来说,此举很可能还隐藏着这样一种意思:他在尽可能使自己的叙述“陌生化”的同时,也在提醒读者以及他自己,要充分警惕从元叙事的视角去看待文学作品的历史叙事;文学叙事,哪怕是充满了异常想象的,其背后也折射着外在的或内在的真实。
[1]贾平凹.老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2]贾平凹,王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汉语写作[J].当代作家评论,2002(6).
[3]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M].李兆林,夏忠宪,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刘海燕)
Deformed Mirror Image of National Personality——On Jia Pingwa’s Laosheng
LIANG Yan-dan
(College of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Jia Pingwa’s new novelLaoshengis so much concerned since its publication. It is a critical novel with its target, “national personality”.Laoshengis not a traditional realism work. It applies such narrative methods as exaggeration, distortion, banter, and imagism, which make it a deformed mirror image of the object.
Laosheng; critical consciousness; national personality; deformed mirror image
2016-11-20
梁艳丹(1991—),女,河南西华人,郑州大学文学院2014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05
I206
A
1008-3715(2017)01-002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