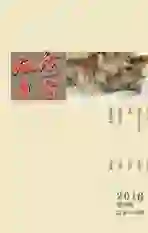老腔
2017-01-09陈绍龙
陈绍龙
耒 歌
一片雨烟。一片朦胧。
耒歌响起的时候我还在梦里。耒歌是耕田人耕田时唱的歌。秋李郢人叫它“嘞嘞”,或叫“打嘞嘞”。耕田人是报时鸟,秋李郢人说他们都是属“鸡”的,差不多鸡叫过之后他们就起身了。耒歌为秋李郢报时。童年时,我去过一次上海,还未醒,听到钟响,音乐起。是海滩钟楼的声音。上海人听惯了这样的晨曲。秋里郢人也听惯了耒歌。只是这耒歌要早。起先,耒歌被淹没在夜色里,一声,一声,仿佛那娇嫩的鸟喙始终还没有啄开壳儿。忽然,歌如闪电,裂帛声出,这只壳终于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咿呀”一声,晨,破壳而出。
耕田要早。野地里,听到鸡鸣,耕田人也会仰着脖子“喔、喔、喔”的,学着鸡叫,玩。他们这样“喔”的时候就把耒歌停下了,鸡不叫的当儿,他们照样唱他们的耒歌。唱给牛听,唱给田野听,唱给自己听。
牛听了有精神。牛不说话,只在默默地耕田,在水田里拉犁,垄笔直,夜还黑着呢。“牯子——”,每句词前面都加“牯子”,“牯子,哥哥想你到五更哟,牯子”,好像耒歌就是唱给牛听的。牯子能听明白吗?真是。牯子是牛。天没亮的时候,耒歌唱的都是掏心掏肺的句子。秋老二还会唱《姐是一枝花》的情歌。有人听过。天亮的时候,秋老二就不唱了。有人不断地怂恿:“来一段吗。来一段吗。”
“谁是你姐呀?”
“一枝花是谁呀。”
秋老二没有接话,始终不抬头,像是做过见不得人的事似的。这会,他如见光的合欢,叶子蔫了。秋老二五十多岁了,单身。对牛谈情,耒歌真是这样的。
田野原本是黑的,在梦里,没醒,渐渐地,泛白,见亮,睁开惺忪的眼睛,似被耒歌唤醒。
鞭催花发,押着水韵。鞭子打在歌间,歌不断;鞭子打在牛背上,牛背上不见一丝鞭痕。伸直臂膀,秋老二把鞭子抡圆,在空中画个圆圈,然后猛地一抽,像是在空中写了一个“中”字,只是那一竖特别长,几乎近地。“叭”的一个响点,牛会猛地一触,一个机灵,向前一步。夜色顿时活泼了许多。
“打伴儿”。问急了秋老二说了实话。耒歌唱给自己听,给自己打伴儿。黑夜寂寥,唱歌,跟牛说话,跟自己说话,一个人在心里,一个人在嘴上。
秋老二耕田的时候喜欢带他的黑黑。黑黑是条狗。黑黑的叫声夹杂在耒歌里。黑黑叫,隐约地,村庄也便传来狗的叫声。耒歌是秋里郢的晨曲。黑黑的叫声有点沙哑,像这支曲子里的锣,或是铙。远处的狗叫声成了低音部的和弦。
黑黑一身黑,没杂毛。黑黑有劲,个大,有小半人高,也能吃。早年,粮食金贵,一条狗的饭量能顶一个人呢。好些人劝他:“勒了吧,多肥。”秋老二不吱声。过年的时候,又会有好些人到他家晃悠:“勒了吧,喝酒。”
“滚”!
他们是冲着那条狗的,想吃狗肉,喝狗血汤。狗血汤没喝到,一个个却被骂得狗血淋头。
秋老二多心疼黑黑呀。没有人理解。那会,秋李郢人家家都有二亩自留地。自留地得请人耕田呀。秋老二是耕田的好手,请他的人多。队里的牛,队里的犁。用犁无妨,用牛得把牛喂饱。饿牛不耕田。这是铁律。给哪家耕田了,哪家得把牛喂饱,也还要做份早茶或者晚茶给耕田人的。早茶、晚茶也是尽村民家之所有。秋李郢人不怠慢耕田人。有人发现,吃晚茶或是早茶的时候,秋老二会偷偷用手帕包一块饼或者一块鸡肉揣在怀里。动作之快,像是魔术。人们知道了,那是带给黑黑吃的。秋老二不想让人说闲话,狗哪能吃饼,吃肉。
他对黑黑那么好?
那天有人晚茶用酒招待他,他喝大了。他哭了。黑黑早有人觊觎,那天他的黑黑给偷了,真的叫人给勒了。地上一大撮狗毛。
“打伴儿……”
从秋老二断断续续的话语中,人们拼凑出了这样的一个事实:
有一天早起,天黑。毛毛雨。秋老二耕田没归。“斜风细雨不须归”,雨如风,如阳光,庄稼人都喜欢,没有归的。秋老二只顾在雨地里唱他的耒歌了。黑黑的嘶咬声他没听到。天亮时他发现,黑黑嘴角流血,一只耳朵耷拉到了嘴边,血肉模糊。再一看,田头一只狼眼放绿光,另两只狼夹着尾巴跑了。“放绿光”的那只狼见状小坐之后也跑了。
黑黑救了秋老二一命。
秋李郢人说,“五狼神”,狼喜结群,五只狼就是神了,无人能敌。
原来如此。秋李郢似乎理解了这个“伴儿”更深的内容。
秋老二把那撮狗毛给埋了,边上竖了块木板。
好些年,我早上听到秋李郢上空有耒歌响的时候,都仿佛能听到里面有黑黑的叫声。仿佛看到,黑黑端坐在田头,端坐在雨地里,看着秋老二,看着田野。
田野,一抹雨烟。
新 声
犁铧的声响簇新,还泛着亮色。
犁铧如舌,尝泥土的气息。它埋在泥里,叫牛拉着,翻地。翻过的地成行、成垄、成浪。犁铧是冲浪者脚下的踏板。一路向前,如镞、如矢。矢志不渝,耕耘是它的使命。犁铧的坚毅和执着让它来不及生锈。与泥土摩挲、交好,遇着石块,它也只是一带而过,小有磕碰,算是打个招呼,也并不理会;没有缠绵,草茎、树根们纵有万缕情思,它也会挥剑斩断,决绝得连头也不回。
哪知,这块铁石心肠的“闷葫芦”,却天天在树下发出悦耳的响声。
这是半块犁铧。
凹下,有弧度,像瓦,尖已秃,仍是锃亮。犁铧差不多也是老了,或许是力道不济,或许是锋利不再,要么是遇着一块大的石头,遇到过不去的坎了,几次角力,无果,在泥土深处发出了一声生猛的脆响之后,生命从此夭折。寻着那半块犁铧,当!当!当!有人发现它还有如此洪亮的喉舌。当!当!当!有人突发奇想,把它当作了钟。
钟是铃。那半块犁铧就挂在秋李郢小学的那棵歪脖子榆树上。
山如黛,眉如峰。薄雾笼罩,或是散去,晴日里,村民们会执着地去看东方的那抹亮色,去看太阳。早晨,秋李郢人的脸庞都成了向日葵。他们会依照太阳的高度来判别早晨的时间,以竹竿的长度为计量单位。一竹竿高,或者是半竹竿高。在一个个刻度间,为孩子穿衣、烧早饭、喂猪。这半块犁铧的出现似乎一下子改变了他们的认知习惯。他们不再早早地起来,甚至都无需出门。他们去听学校的铃响,去听那半块犁铧发出的声音。当—当当!当当!或是当!当!还有,连续性的“当—当—当!”其意表述为:预备、上课、下课、放学。村民们会依据铃响行事,他们会说,学校都打预备铃了,都是上午第二节课了,或者说,下午都放学了。铃响是另一种时间的刻度。铃声没有阴天。
我是新时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师范毕业生。我在秋李郢小学教过书。学校建在山脚下。这里过去是公房,秋李郢人设想要在这里办造纸厂,没成;又有人想在这里养蚕,只养了一季,也放弃了。考虑到周边有好些孩子失学,用这几间房子办学校,成了。教室是村民自己用石头砌的。教室石头缝漏风。遇雪,再刮风,会有雪花从墙缝里吹进来。冬季,我们常在室内看雪。学校的简陋今天难以想像。什么都缺,包括那半块犁铧。
“勤工俭学”不只关乎学生自己,更关乎学校,关乎学校的生存。记得那时学生没有课桌。我便想着自己动手,造课桌。山上不缺石头,村民们搬来石头。我和孩子们一起在两头搭成墩,中间用学生从家里带来葵花杆或是竹竿密密地码好,上面用和好的带草茎的泥巴糊好,再在泥巴上糊一层报纸。泥巴收干,课桌便成了。我的创意成了经验,受到公社的表扬,并且在全公社推广,还得到了我工作以来的第一件奖品,一盏马灯。
那会儿我常想,怎么会有这样的奖品。
学校没有食堂,我就到学生家里代饭,就是挨家吃,吃百家饭。说好了是给钱的,可家长不收,算是“白吃”。好在学生多,一家吃过一顿,没有第二回,差不多一个学期也就结束了,并没给学生家增添多少负担。这让我多少有些安慰。早年家贫,村民家不富裕,有豆腐吃也算不错的了。起先,我不明白,学校那棵歪脖子的榆树,怎么就不见新长的嫩叶呢。当地的一位民办老师告诉我,嫩绿的榆树叶能吃。
吃过百家饭之后,我似乎跟秋李郢所有的人都熟了。他们常来看我。隔着窗户向教室里张望。他们把锄头扛在肩上。锄头亦如那片犁铧,与阳光窃窃私语,甚或有一团光映照到教室的墙上。这团光像是搞笑的表情。他们在窗外看我拿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看我拿小铁锤去敲那半块犁铧,所有的东西都让他们觉得新奇;然后向我笑,跟学生一样没缘由地走到我面前,道一声“陈老师好!”他们知道我是“新时期”以来第一个到学校教书的大学生。这成了一件很励志的事。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过来。孩子要读书。
铃声清脆,一如这板结的土地上播下的光明种子,这串晶莹的露珠,使得每个早晨和黄昏都变得激越起来,为山乡增色。
日子在走。
山里的孩子我没有要求他们来上晚自习,可是,家长都愿意把孩子送到学校里来。家长们就聚集在教室的外面等。直到那半块犁铧敲响,晚自习结束,他们才领着各自的孩子回家。家长们把灯点亮。我才发现,每个家长手里都拎着一盏马灯。我也似乎明白了那项奖品的寓意。
站立窗前,马灯把夜色磕出一个个亮点。亮点在山梁上蜿蜒。当!当—当!一如一串串清亮的铃声,山乡古老的节律里,让人听到了新声。
秧 歌
秧歌响起的时候,春天已是一片青枝绿叶。
春天是一张素签,是一张写意的素签。秧苗在这张素签上落笔。一行。一行。田字格里涂满了绿色。有燕在田字格上低飞,一个个墨点,空灵而律动。秧歌其实就是田野上的题句,是竖着写的一行行诗。
三月是一幅画。
田野是一幅画。
秋里郢是淮河边上的一个小村。淮河从桐柏山下来,一泻千里。从秋里郢边上流过,流进洪泽湖,再入海。洪泽湖成了淮河最大的驿站,大海,是淮河最后的家。和着河水、湖水和海浪的声音,秋里郢的秧歌成了淮河的绝唱。
流连复流连,徘徊复徘徊。无语凝噎。我没听过其他地方的秧歌,听过也不记得,自然不会唱;我也不知道其他地方的秧歌唱词是怎么写的,写了些什么。秋李郢的秧歌很特别。有调,没词。其内容极简。有词,是字,除了“我”之外,是“咯、咚、呔”。一唱三叹,平仄相间,循环往复。
“咯、咚、呔——咯咚呔”
“——我呔哩咯咚呔!”
“——我呔哩咯咚呔!”
一人起头,唱。众人和。
简单不是没有内容。听锣听音。听话听声。我在“咯、咚、呔”里听到了水的声音。“咯、咚、呔”有对插秧时水的声音的摹拟,有秧苗刚入水时的声音,有秧苗入水时空气与水的碰撞,有插完秧苗时的回响。“呔、呔、呔”似京剧舞台上铙儿不断敲打的声音。有人要走台,有人要出场。歌门不断,音乐不停。
有人说,秧歌是稻田里的《诗经》,是《诗经》里的“风”。秋李郢的秧歌莫不是古老瓷盆上的那尾鱼,是龟甲上烧开的裂痕,文字之外,音乐之外,或许,它也是一块珍贵的“化石”。
因为歌词极简,韵律上口,有水韵,秋李郢大人小孩,张口就唱,三月里,仿一句旧话,凡有秧田处皆有秧歌。
“农家三样苦,栽秧,垒墙,磨豆腐”。秋李郢人说“三样苦”就有栽秧。
垒墙是见得着的,将和熟的泥一叉叉地送上墙头,像燕子泥窝似的,“与人不睦,劝人盖屋”,盖房自然劳神,哪能不苦。磨豆腐我还真没见过,据说磨豆腐人都是半夜起,要泡豆、磨浆、点卤。
说栽秧苦,那倒也是。栽秧是面朝水田背朝天。背在天上,一天下来,天就像是压在背上一样,是把天背在背上。沉呀。说腰酸背痛都有点轻描淡写。唱歌吧,唱秧歌解乏。
左手分秧,右手栽秧,刀起面落,跟山西大师傅削刀削面一样。手起秧出,分苗栽秧,快得水连成了线。始终保持这横“7”字状的姿势插在秧田里,我哪里受得了。我是要“拄拐”的了。“拄拐”就是将左手弯搁在左膝盖上栽秧,让膀弯分点力,舒服些。这样栽秧姿势一定难看。“拄拐”影响速度,也惹人讥笑。讥笑倒是不怕,男人吗,栽秧不是强项,何况我那时只是个孩子,问题是“拄拐”时间长了会“掉秧趟”里的。
米丫说我是“老先进”。米丫是我儿时的伙伴。米丫是个女孩。
她在笑我。栽秧一人一垅。每垅大约六七行,倒着走,插秧是以退为进。“先进”自然就是落后。秋李郢人不说落后,叫“掉秧趟”。米丫救我。她挨在我旁边,“救”就是帮我多栽几行,有时,我只要栽两三行就行,速度自然快,很快便能和米丫齐头并进了。
这让我轻松了起来。远处秧歌响:“咯咚呔咯咚呔,我呔哩咯咚呔,我呔哩咯咚呔”。
我来了精神,也跟着唱“咯咚呔”起来。
一田响:“咯咚呔咯咚呔,我呔哩咯咚呔,我呔哩咯咚呔”。
米丫没唱。她挺会唱秧歌的呀。她看我得意了,便故意留出五六行给我,有时是七八行,出我丑。看你得意!我便不言语了,埋头栽秧便是。一时秧歌蔫了,米丫看我又“掉秧趟”里,她自然开始“救”我了。
米丫不唱秧歌。她要跟我说话。
“你唱呀。”她在反讽我。
唱什么?秧歌对于情窦初开的男女,该是一部什么样的《诗经》呢?
天 籁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那是另一个晚间版本。
柴门响,“咯吱”一声,新的一天被打开了。
其实,我最先听到的声音是门闩响。门闩是早晨的机关,家的机关,日子的机关。门闩响“咔咔”的,精神抖擞,鲜活生动,清脆愉悦。木头不是“木头”。门闩早已叫手摩得光滑锃亮。我妈只是用左脚尖轻顶门缝,左手朝门上一抵,右手轻拉闩头,“咔咔”,门便开了。她手脚并用且配合默契,像是一个老驾驶员完成了整套挂挡起步的动作,“咔咔”一声响。油门也是门。新的一天上路了。
狗也叫,是“哼哼叽叽”地摇头摆尾。这样子像在撒娇。它第一个冲到我妈面前。犬吠那是对生人的,夜里叫。现在是早晨,它在乞食。它把鼻子埋在我妈的裤脚处,围着我妈转,嗅来嗅去的,然后,又把前腿伸出,作站立状。它哪里站得稳,只是坚持了几秒钟的样子,两前腿又合拢慢慢落下,作揖似的,我求你了。我妈并不看它,她嘴角的笑意逃不过一缕阳光,有时,也会“噗嗤”笑出声的。好哭的孩子有奶吃。狗如此乖巧不吃亏。狗好像也是我妈的孩子。我妈会从厨房端出狗食放地上,或是把一块骨头,故意地扔出很远。狗撒腿便追。双“手”抓住骨头,转过身来,嘴不离骨,眼还盯着我妈,歪着脑袋。这里面有感激的成分。我妈早已心领神会。我妈是怕它黏,缠人。这会,我妈站在门前,借着最新鲜的亮色,也歪着头,嘴里衔着扎头的皮筋,梳头。阳光是最好的面霜。两个脑袋都这么歪着。我妈心里还是喜滋滋的。
哪里安神,鸡在笼里早已待不住了,它们在“咯咯咯”地骚动。窝里下蛋的母鸡最闹腾了,“个个大”猛叫。我妈得表示表示吧,随手从土瓮里抓一把稻子撒地上,算是犒劳。其他的鸡也跟着沾光,一起围了过来,低头啄食。刚一吃完,鸡们便飞也似的跑出家门,到野外觅食,撒野,寻欢。“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公鸡三个庄”。领头的是公鸡。秋里郢人说一只公鸡能统领三个村庄的母鸡,也就是说,三个村庄的母鸡都是它的后宫。“喔喔喔”,引吭高歌,公鸡是值得骄傲。公鸡在跟随它的母鸡面前左右腾挪。公鸡真幸福。
与狗和鸡相比,“哼哼”的猪低音要低调得多,在晨曲这个和声部中,猪的“哼哼”声类中提琴,凑场子,起个哄。引不起关注,猪会用嘴去拱猪圈的门。圈门多是竖扎的木栅。木栅已被猪拱得圆光溜滑。猪不停地哼哼,拱已罢了,问题是主人并没理会,它依旧还是这么哼哼,把嘴和脑袋朝栅栏里钻,以为能钻过栅栏,一刻也不消停。这多少让人发急。猪脑袋。
槐树,杨树,枣树,还有楝树,想想也有石榴、腊梅、桂花什么的。树是秋李郢人多年生的庄稼,是散养在院内院外的家畜。所有的叶都为这支晨曲音乐会鼓掌,所有的叶都是观众们的眼。树记得。树心里有数。站在枝头的喜鹊、斑鸠、白头翁也会一块来帮腔,声音同样鲜活,一如一颗颗晶莹的挂在叶片下、草尖上的露滴,亮闪闪的。声音年轮唱响的磁盘,好像是树们在为每一个新鲜的日子播放晨曲。
音乐齐鸣,太阳放出大亮。夜幕完全被拉开。满光,我妈的身影在强光中一边与天色融为一体,一边已镶入大地。
我沉浸在天籁之中。“哐、哐、哐”关门的声响把我的思绪打乱。就此收笔。抬眼,看窗,天已亮。保存文档,关闭电脑。“咚、咚、咚”是下楼的脚步声。
“哐、哐、哐”,一家关门。
“哐、哐、哐”,又一家关门。
“咚、咚、咚”,有人下楼。
“咚、咚、咚”,又有人下楼。
我写作已毫无思绪。隔着门缝,我好奇。哪家关门。谁下楼。
门缝很窄。钻过门缝的只是目光。我这么傻站着,不觉哑然。我想到了那只努力钻出栅外的猪。
我们被圈养在一个叫城市的地方。“哐、哐、哐”,“咚、咚、咚”,还有鸣笛声,还有轰鸣的马达声,记忆中晨起家的声音,还有天籁,业已成了老腔。
唱 喜
在秋李郢,每块土疙瘩都是带响的风铃。
情不自禁,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嗟叹之不足歌咏之。且足之蹈之。《诗》有言。想唱就唱。有喜就要唱出来。这叫“唱喜”。
秋李郢有三大喜事总有人来唱喜:娶媳妇、上大梁、剃红头。
秋后,日子殷实了许多,也渐闲,娶媳妇带新娘子也多半在这时节。一家迎亲,全村热闹。焦点就在于闹新娘子。小孩子一刻也不消停,叽叽喳喳,窜来窜去,抢着去偷枕头和金桶里的糖果。“金桶”也就是木制手拎的马桶,是娘家的陪嫁,新的,自然也干净。大人看在眼里,这些糖果就是让小孩子们去偷的,图的就是热闹。那年,李老三结婚,我对新娘房窗花后面那盏晕红的灯好奇。有大人怂恿:去看看。我蹑手蹑脚地来到窗下,由于个头小,根本就够不着窗台,怂恿我的大人也蹑手蹑脚地来到我的身边,把我抱起,让我用手抓住窗棂。窗子极简,几根竖起的窗棂,里罩千格篾窗,篾上糊一层簇新的红纸。隔着纸只看到里面有晃动的身影。我自恃聪明,手指蘸唾液,贴在红纸上,想把红纸湿出个洞来。手刚触到红纸,有了动静。“谁!”我一惊,一撒手,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噗!”有人把灯吹灭,还在待我“哎哟”喊疼,我身后的大人也发出一阵阵的狂笑。
其实,我们小孩子闹新娘子都只是个铺垫,高潮处在于大人的唱喜。
唱喜要道具,婆婆脖上挂的是蜡瓶。喻意自明。公公脖上挂的类似猪八戒扛的耙子,“耙”与“爬灰”的“爬”谐音。全副“武装”的公婆被带到儿媳妇的床前。唱喜的是主唱,还有一配角叫“道‘好的”。“道好”就是主唱唱过一句之后,要道一声“好”。其实,往往在场的人都跟着道“好”的。起哄呗。唱喜的要公公拨开盖头,这时唱声响起:手拿红纸链,照照新娘面……还不待“好”字出口,闹新房的人也将公公推到儿媳妇的床前。喧闹不绝于耳。其实,道喜的唱词只是开了一个头,便叫闹喜的众人搅了局。我似乎只知晓“手拿红纸链,照照新娘面”这两名唱词,便没了下文。
盖屋是大事,也是喜事。要闹。要唱。节点就选在上梁那天。看好日子,风和日丽。房屋三架梁,也有五架梁、七架梁的。其他梁单上无妨,上中梁就有讲究了。中梁是“大梁”。这天,家主知道有人争喜,便早早地备了烟、茶食和红包放在匾里。放在匾里的还有小馒头或是糖果。唱喜人手捧匾,其他盖房的茅匠(过去乡下草房多,盖草房的人叫“茅匠”,盖瓦房的人叫“瓦匠”)把中梁一点一点地向上挪,每挪一点,唱喜的就唱一句。屋高,人闹,道“好”声响,我哪里听他唱什么。我们低头在抢糖果和小馒头呢。唱喜的也够坏,屋里有人,屋外有人,四周都有人,唱喜的手抓糖果和馒头,一会儿撒在东面,一会儿撒在西面,有时,明明看他像是要向东面撒的,可是,手一扬,东西却落在了西面。我们疲于奔跑,累瘫了。
村上的秋三是茅匠,喉咙大,待房子四檐齐的时候,家里人就准备上大梁了。那天,大根家带儿媳妇盖新房,请秋三唱喜,大根把蒸好的小馒头、糖果什么的放在小笆头里给秋三递过去。秋三一面唱喜,一面朝地上撒东西给人抢。
“正是吉庆日——好!”
“华堂娶儿媳——好!”
“来年生子时——好!”
“孩叫大根爹——好!”
抢东西的一片叫“好”,听不清什么词。站在一边的大根起先还跟着道“好”呢,看到屋顶上的茅匠们个个笑得前仰后合,知道秋三在“涮”自己了,骂秋三是“讨债鬼”,便径自离开;大根的儿媳也听明白了,面红耳赤,回屋后就没有出来。
剃红头就是给娇宠的男孩剃头。男孩生下来的时候,胎毛总是要留一撮的,这一撮胎毛动不得,要到孩子六岁的时候才能剃。这就叫“剃红头”。剃头着一“红”字,也无非是添喜罢了。孩子六岁生日那天,家里人给孩子买来新衣服。唱喜的是理发师。理发师将孩子四周的头发剪去,把那撮头发用梳子梳来梳去的,就这么磨蹭着。过了一会儿,理发师捋直几根头发,大声唱:“青云直上——好!”;接着,他又放下剃刀,将一条糕用红布包着垫在孩子的脚下:“步步高升——好!”听到理发师的高声唱喜,一旁站着的人要跟着大声叫“好”。就那几根头发,理发师是不会轻易就剃去的,他会一边唱喜,一边争喜钱。其实,孩子的舅早就准备好了。只是我至今没明白,那红纸包里包着的到底有多少钱呢。
吆 喝
有吆喝的村子有生气,也有味。
“香—蕉—冰棒!”
“香”字拖的老长,“蕉”声轻,且短,“冰棒”迅即从唇上滑过,土声土语,清脆洪亮。满嘴的香蕉味。满耳的香蕉味。一声过后,香蕉冰棒的味道便像在整个村子里迅速弥散开来。
闻声而动,村四周便会跑出孩子,向“香—蕉—冰棒”聚拢。听到吆喝,我便去摸我奶奶腰间的荷包。我近乎伏在我奶奶的怀里,左右摇晃,撒娇。我知道,只要我一撒娇,我奶奶一定会依允我的。荷包里有钱。我奶奶把荷包系在腰带上的。荷包里有一些毛票子,也有一些硬币。接过一枚5分硬币,我撒腿就跑。其实,也不用这么急的,卖冰棒的人自行车就架在村口,并不走,他在这里差不多要喊上近半个小时呢。
秋公社奶奶没给他钱。他从家里的鸡窝里摸了只鸡蛋。“摸”也就是偷。一只鸡蛋也能换一支冰棒。哪知秋公社没有把鸡蛋拿在手里,他把鸡蛋装进了书包里。他自然不敢明目张胆的样子。家人以为他背书包上学的呢。离开家门,看到我飞奔,他也跟着跑呢。哪知打开书包一看,鸡蛋破了,蛋黄蛋液流了出来,把书都糊住了。我们几个小孩子围了过去,差点笑晕。笨蛋,书包里有鸡蛋哪能跑呢。
其实,从村口围过来的孩子有好些只是来看热闹的。他们一个个把食指放在小嘴里,发呆。有些家长会看不过去,不忍心看孩子馋相,似乎是一咬牙,才从身上掏出5分钱来。只是在拿到冰棒之后,会拎着孩子的耳朵回家的。孩子一边歪着头,一边把冰棒放在嘴里滋滋啦啦跟着小跑。
卖冰棒的小伙子自行车后面绑只木箱,戴副墨镜,穿条喇叭裤,酷。“香—蕉—冰—棒—!”我觉得这个吆喝声好听,好些年之后我们还会跟着学。自小我以为,“香蕉冰棒”的吆喝声是最体面的。家里大人只舍得花5分钱买一支吃完,冰棒中间的小木棒也并不立即扔掉,仍放在嘴里,想,我要是天天有冰棒吃就好了。
吆喝声最响的是那只铁皮“喇叭”,发号施令全仗它了。它是队里的喉舌。乡场是队里的“政治中心”、“生产中心”。队长站定乡场,左手叉腰,右手拿着喇叭的把儿,部队司号员一样,憋足了劲:“农年挑把——妇年割麦——嘞——”“农年”就是男人,“妇年”当然就是女人了。队长“指挥生产”,也像是调度。听到队长吆喝声,村民们便磨磨蹭蹭拿着镰刀或是扁担从家里出来了。要是听到“抢—场—喽—”的吆喝声,全村就没有人再懒洋洋的了。他们会拿上家里的篮或是笆斗去乡场上抢收晒在地上的谷物。事急也,雨将至。后来有了电喇叭了,队长就轻松多了。不过,吆喝声的韵味也就没有了。电喇叭哇里哇啦的,让人烦。
遛乡手艺人的吆喝是南腔北调,这些不是小村本土的吆喝声,有好些猛一听你不知他在吆喝什么。“磨剪—子嘞—戗—菜—刀—!”电影《红灯记》里那是演员演的。遛乡的手艺人才不会那么中规中矩地吆喝,他们用的是乡音,是方言。这些手艺人多半是外乡人。方言一时难以听懂。“麻—绳儿”,是收麻绳的,也收牙膏皮、旧报纸什么的。“补锅呐!”“补锅”的多是河南、山东那边过来的,吆喝便能听懂。他们除了补锅之外,也能补缸。南方人吆喝我就听不懂了。那年,我家新买了一台14吋电视机,家里人无比珍视,想把它做个套子罩起来。恰巧有遛乡手艺人经过,专门卖电视机套。套子做得讲究,好看,价钱也不贵,家里人便买了一只。付完钱,起身吆喝,浙江那位卖电视机布套人的吆喝我是怎么也听不懂的。
听不懂的多呢。
有时我好奇,听到吆喝声,我跟在手艺人后面,看他究竟是干什么的。别说,还真的叫我看出了一些门道。
“打—箍儿”,听到吆喝,你要是只以为他打扁担箍就错了,“打箍儿”的工匠担子上还挂有好些牛皮筋和棕麻。这些东西是给人家修绷子床的。后来我明白了,打扁担箍是小活,断扁担的人不多,有好些扁担断了也失去了修复的意义,便扔了。活不够,这些手艺人采用这“混搭”的方式,耧草打兔子,一工带两件,外带修床。只是在吆喝声里没有“说”明白。不过,秋李郢人知道,家里的棕绷床要是坏了,会让家人留心,听着村口“打箍儿”是不是来了的。
现如今,冰棒倒是天天能吃得上了,也不再稀罕,可原汁原味的乡间吆喝声倒是少有听到。好些手艺和行业都已消失。那天我看一则新闻写的竟是上海好些市民家的剪子刀没人磨了,疾呼:让手艺人进城。
“香烟—洋火—桂花糖—”、“修洋伞嘞—”,其实,有吆喝的城市,也有味。我只在老电影里听过这走街串巷的吆喝声。现在乡间手艺人再进大都市吆喝会是什么样子呢?想象不出来。只是我不免担心起来,上海是车水马龙,市声鼎沸,这吆喝声哪里还听得到?除非这些手艺人也做个过去队长用的铁皮喇叭。那喇叭的口径该有多大呀。
眠 歌
“月儿明,风儿静,树叶儿遮窗棂……”
孩子有“三闹”:“下床气”、“磨饭碗”、“闹觉”。就是说,小孩子在刚睡醒之后,吃饭之前,要睡觉的时候,都哭闹。“下床气”和“闹觉”要哄,不能跟孩子拧。据说,治“磨饭碗”就不一样了,不能依允孩子。孩子哭闹,家人只拿一只畚箕,将哭闹孩子摁在畚箕里,端着扔到外面的垃圾堆上。大人不要看,决绝毅然,转身离开,无论孩子如何哭闹,不回头,不理会,回家,一甩门便可。仅此一回,保证奏效。想象一下:孩子大哭,泪流满面,一脸泥垢,看大人离开,迅即从垃圾边上爬起,一路踉跄,倒在关闭的门前,再哭。“仅此一回”,估计孩子之后真不敢“磨饭碗”了。只是,这招狠了点吧。
还是唱《摇篮曲》好。
《摇篮曲》是电影里的版本。秋李郢大人们唱的版本很多,词不同,调子也不一样。
我奶奶唱的最多的就是:“小乖乖,听听话;乖乖睡,到天亮。”
“小乖乖,听听话;乖乖睡,到天亮。”
听多了也无趣,无新奇的地方,乏味;或许,我当时心想,老声老调的,听它干嘛?不如睡觉算了。
我奶奶在唱眠歌的时候,拥我在怀,用一只手在我背上轻摸或是轻拍。抚着拍着,我极放松,眠歌唱不了几句,我也便躺在我奶奶怀里睡着了。
现在才知道,这眠歌和“摸拍”的效力有多大。那天看中央电视台的一档电视节目。节目亮绝活。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能让鸡、兔子、青蛙、狗、蜥蜴、蛇等六七种小动物在几分钟内都睡着。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多有不信。小女孩把这些小动物摊放在台上,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地唱着“眠歌”,一边用手轻轻地抚摸和拍打着它们。奇迹出现了,所有的小动物们在台上睡着了!
有一回,我奶奶兴许觉得眠歌真的太老了,没新意,自作主张,想增加新的内容,将眠歌的歌词给改了:“小乖乖,听听话;乖乖睡,有糖吃。”
我那会儿被“摸拍”得迷迷糊糊,依稀听到“有糖吃”的时候,一下子来了精神,骨碌从我奶奶怀里挣脱出来:“糖呢!”
“乖乖,睡吧,明天奶奶去买。”
我哪里依允,嚷着要糖吃,不再睡觉。听我奶奶说,她把我抱起,直到半夜时分,我的眼泪差不多哭干了,是真累了,才入睡的。
我奶奶之后再不敢乱改词了,好些年听到的都是那几句老掉牙的眠歌了。
也有孩子真不乖的,夜啼,闹觉不止。这回,村上人便去找秋大先生写“符”,将“符”贴在电线杆子上,或是贴在树上。“符”是一张纸。秋大先生是队里的记工员,识字,会写毛笔字。他戴副眼镜,像个旧时的账户先生,又因为他在家排行老大,秋李郢人都唤他“秋大先生”。
“符”曰:“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先生念七遍,一觉睡到大天亮。”
看到有“符”,秋李郢人都会凑上前去,好些人并不识字,这不影响“过路先生”“念七遍”的,因为,“符”上的词,个个会背。
我不相信“符”的魔力。但是我相信秋李郢人对孩子的呵护。相信家人对自己的爱。眠歌也许已是老腔,但是这种爱是永恒的。
责任编辑:邓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