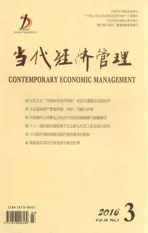社会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的衍生逻辑及实践启示
2016-12-31徐俊峰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江苏南京210093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1701
徐俊峰(1.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江苏南京210093;2. 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1701)
社会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的衍生逻辑及实践启示
徐俊峰1,2
(1.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江苏南京210093;2. 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1701)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论突破,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的衍生。社会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渊源于马克思的“无市场”、“近市场”、“亲市场”等理论学说,生成了“反市场——近市场——亲市场”逻辑路径,历经了政府模拟市场、政府联姻市场、市场主导型、市场决定型等模式演进,积累了诸多经验教训,启示我们必须兼顾社会主义与市场的二维创新与博弈层次;探索政府与市场互补结构;整合市场因素与非市场因素合力,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逻辑溯源;实践启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论突破,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的衍生,预示了“市场决定性作用论”实践的长期性、复杂性、挑战性。因此,回溯社会主义探索“市场决定性作用”的理论渊源、循环逻辑、模式形态、借鉴启示等,对我们探索“市场决定性作用论”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社会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衍生的理论渊源
社会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渊源于马克思的“无市场、近市场、“亲市场”等理论学说,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近市场、亲市场、无市场”的属性论述,是社会主义与市场博弈的逻辑渊源。
(一)社会主义“近市场”的本源属性
马克思“市场起源论”认为,社会主义拥有“近市场”的本源属性,同时又具有“近市场”的制度属性,是客观性与本源性的统一。
1.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天然互补性
社会主义与市场天然互补属性蕴含在马克思市场起源的理论判断中。马克思坚持市场起源于社会组织的“市场社会论”观点,反对西方古典经济学家的市场起源于人类交换倾向的“市场人性论”观点。马克思认为,最初的商品交换“不是在原始公社内部出现的,而是在它的尽头,在它的边界上,在它和其它公社接触的少数地点出现的”。[1]即市场起源于社会制度的本源属性,而不是由人的自然属性产生并自然满足社会发展的基本观点,蕴含了市场可以与任何社会制度或社会组织进行结合的可能,自然也预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结合的本源属性。同时马克思也指明了市场与社会分工相互促进的积极作用。马克思认为,“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独立生产者的劳动最终“发展成一个多支的体系,发展成社会分工”,进而不断推动市场范围的扩大;[2]肯定了市场与社会双向互动功能。暗示了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只要存在社会分工与剩余产品,市场交换生成的逻辑前提就存在;在社会分工存在并不断拓展的情况下,产品交换的领域不断扩大,交换的类型也不断复杂化、精细化,只要市场对社会的促进属性存在,其依附于社会的本源属性就不会丧失。因此,具有先进制度属性的社会主义同样脱离不了社会分工的存在,自然拥有与市场结合的互补性。
2.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客观相容性
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客观相容性是由社会主义制度属性所决定的。一方面,社会主义既具有一切社会制度的共同属性,即必须建构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同时又满足人诉求的政治文化社会有机体,必然与市场促进社会有机体属性具有相容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又具有独特的制度属性。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基础之上,又在精神追求、社会公正、文化繁荣等方面超越资本主义的新型制度,在经济层面与道义层面均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其核心价值目标是给人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和丰足的精神财富,让人类享有自然权利和社会权利的高度统一,最终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决定其必然需要借助于一切能够满足其发展需求的机制,市场机制的优势属性能确保社会主义获取未来发展的物质条件与精神追求,而其自身固有的优越属性也为限制市场劣根性提供了屏障。因此,社会主义仍然拥有利用市场的客观必然性,同时也拥有促进市场优化的天然优越性。
总之,马克思关于市场起源与社会主义制度属性的基本判断表明,社会主义与市场具有本源的相容性,构成了社会主义探索“市场决定性作用”问题的逻辑源头。
(二)社会主义“亲市场”的内质属性
1.未来社会“无市场”的理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制度“无市场”的制度设计是共产主义社会,而这种共产主义社会是直接针对物质条件、精神财富高度发达的“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并非是“各方面尚未成熟”的共产主义低级阶段。
马克思在客观分析市场起源、市场要素、市场机制、市场功能、市场分类等的基础上,明确肯定了市场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优势功能;同时也对市场蕴含了劣势属性功能进行了深入的批判。马克思继承发展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市场批判思想,透视市场与私有制结合等产生的社会不公、拜物教现象、不当竞争、市场失灵、市场滞后性等问题,揭示了市场与私有制、个人主义等客观兼容性,看到了市场产生的人性异化、优胜劣汰、两极分化、极端趋利性等,预测了未来社会是“无市场”的社会制度;但根据马克思后来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可知,在其尚未实现高阶段共产主义之前,社会主义必然不可避免带有其原有社会的特征,甚至可以包括商品货币、银行的、利息、利润等。由此可知,“无市场”的未来制度必然是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
2.社会主义“亲市场”的必然性
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社会主义“亲市场”的属性是暂时的,是其过渡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必然会通过“去市场”的途径实现“无市场”的未来社会制度。因为马克思的设计要求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精神基础、政治文明、社会素养等综合的实践条件。当社会主义社会具备了实现共产主义需求的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素养等,市场也就无需再发挥职能,或许会转化为另外一种形态,市场就自然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主义自然过渡到“无市场”的共产主义社会。当然,如果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具备“无市场”的制度条件,就应该保留其实践中的市场制度属性以不断提升社会主义制度的综合条件,为其向未来社会的过渡与发展创造条件。因此,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制度又具有“亲市场”的应然属性,否则就不能实现“无市场”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
由此可知,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既蕴含了社会主义“去市场”的应然性,又蕴含了社会主义“亲市场”的必然性,只有等条件成熟的时候才能实现未来社会主义的“无市场”性。
二、社会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衍生的逻辑路径
社会主义探索“市场决定性作用”问题历经逻辑起点、逻辑展开、逻辑升华等阶段,完成了“反市场——近市场——亲市场”的逻辑循环,建构了社会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的理论实践。
(一)社会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生成的逻辑起点
指早期社会主义的反市场实践与市场理论矛盾徘徊,孕育了社会主义市场本位探索建构的实践先兆。主要包括苏联及早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构计划经济主导以排斥市场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
早期苏东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未来社会制度“无市场”目标设定的误解,忽视了社会主义“去市场”条件,混淆了共产主义“废市场”与社会主义“去市场”的根本区别,把“去市场”理论等同于“废市场”理论,走向了“反市场”的社会实践,衍生了社会主义排斥市场的通行模式。在实践中主要以排斥市场为核心手段,建构了绝对公有制所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试图建构替代市场经济的实践超越,进而衍生了与计划经济呼应的政治、文化社会体制等。但事实上该模式却是在计划经济主导下的市场矛盾状态。一方面,政府试图运用行政手段取消市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运营机制,在理论意义上建构了排斥市场的形态,如列宁曾设想在“世界几个大城市”的主要街道“用黄金修建公用厕所”的绝对反市场设计。[3]另一方面,在经济实践中又不得已采取保留部分市场的制度形态,如货币、经济核算、价格信息、价值规律等,试图借助货币实现“经济计量的尺度、所得的分配和企业结账的手段”、“支付个人及家庭生活费用,获得消费资料及服务”等;尤其是在国际中必然借“黄金和美元”等国际货币在世界市场中进行“贸易交换和贸易结算”等,凸显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实践不可分割性。[4]
因此,早期社会主义反市场的实践范式验证了马克思“去市场”的正确性,为社会主义“近市场”属性埋下了伏笔,预示了“市场决定性作用论”建构的理论起点。
(二)社会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生成的逻辑主体
主要是指20世纪50年代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辟的“近市场”实践探索,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解构联姻的理论突破,以南斯拉夫、匈牙利等为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率先揭开了探索与市场联姻的兼容之路。
东欧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试图回归市场在社会主义应有的地位,但由于当时社会主义矛盾尚未充分实践以及世界格局的制约影响,大多是设想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中植入市场经济的成分,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的结构联姻,大大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如南斯拉夫、匈牙利的实践探索,东欧其他国家的理论探索等,曾被西方国家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其重要的理论实践奠基时期。
但由于其大多是在传统社会主义框架内植入市场经济的内核,但社会主义仍然是主导地位,恢复了社会主义“近市场”的自然属性;但其未能真正调整市场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市场经济在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激化了市场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如政府与市场的矛盾、企业与市场的矛盾、社会与市场的矛盾等问题凸显,这些矛盾表面看是改革带来的矛盾,实际却是市场主体地位未能复归衍生的必然矛盾,再加上苏联的强力压迫等因素,这种探索并未真正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实践探索由此而中断。
(三)社会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生成的逻辑升华
主要是指20世纪90年代苏东社会主义解体以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左翼作家的探索设计;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实践,尤其“市场在社会主义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提出,完成了社会主义与市场博弈的逻辑循环。
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社会主义近市场的路径中断之后,社会主义市场本位问题的建构任务被欧美当代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承担。当代市场社会主义主要以英美国家为主导,把市场作为主导机制引入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作为实现发展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他们既坚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又坚持市场作为主导经济手段的理论设想,借用市场经济的微观机制,建构了工人自治型、经济民主型、经理经营型等社会主义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历经市场与计划共存、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等的路径变迁,建构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模式,标志着社会主义探索“市场决定性作用”问题的逻辑升华。
三、社会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的模式演进
社会主义市场本位理论建构的探索起始于西方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大辩论,产生了政府模拟市场、政府与市场分权、市场主导型、市场决定型等模式形态。
(一)政府模拟市场的竞争社会主义模式
该模式是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终结西方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大辩论而设计的模式,是市场本位社会主义建构问题探索的初始形态。其核心理念针对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社会主义无市场、无经济核算、无信息等争论焦点,“比照竞争市场上的均衡决定条件,通过“政府模拟市场”的设想,利用“试验错误的方法”来解决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实现资源合理配置。
具体说来,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由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局模拟市场功能,通过价格制定来调整供需关系和收入分配等;企业必须按照政府制定的价格体系,以消费者的偏好确定生产问题,而不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消费者个人根据自己的偏好自由选择职业等,实现政府、企业、个人利益关系协调的实践机制。兰格认为,尽管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实际的市场,但政府可以根据历史价格随机抽取价格设定价格体系,通过不断试验错误的方法确定合理的价格体系以实现供需平衡,确保资源合理配置;同时政府严格按照政府偏好与消费者偏好统一的理念,借助计划性和行政性手段以保证合理的分配和积累,实现社会均等化,满足社会主义的实践诉求,以政府模拟市场为中心的资源配置、生产消费、分配积累、个人需求等的合理化的社会形态形成。
总之,兰格的政府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模式尽管没有在实践中实施,同时也存在诸多不合理性,如企业的市场性、政府的行政性等问题,但却为社会主义探索“市场决定性作用”理论建构揭开了序幕。
(二)政府联姻市场的分权社会主义模式
该模式是指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提高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效率而嫁接市场的实践理论模式探索。其核心理念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内植入市场机制。包括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等实践模式;布鲁斯的“含有受控制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奥塔·锡克的“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分配计划”模式,科尔奈的“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模式等,理论界称之为传统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该模式具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政府与市场联姻;二是政府与市场分权。
所谓政府与市场联姻主要是指传统社会主义普遍利用市场机制作为提升经济效率的手段,但并未关注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内生性问题。如南斯拉夫与匈牙利的实践模式中,都主张运用市场经济,在价格机制、收入分配、企业生产、对外贸易等相关领域依靠市场调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同时把市场经济局限在产品市场,而在“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方面并没有突破,这种“没有资本市场的折中方案”,并不会带来“人们期望发生的从行政协调到市场调节的变化”,更不能给“社会主义经济效率低下问题提供”合理的答案。[5]
所谓政府与市场分权,主要是指政府行政权利与市场自由权利的“二元并存”关系,并没关注政府与市场的交融共生,二者处于共存剥离现象。如奥塔锡克设计的政府宏观计划与企业微观决策在生产、分配、信息、市场透明度等分权形态;科尔奈设计的行政协调与市场协调处理企业软预算约束和社会保障等。尽管都从不同的视角看透了传统社会主义面临的问题,但由于分权嫁接的形态致使企业在“从属行政和从属市场”的“双重从属”纠葛不清,不能从根本上破除传统企业存在软预算约束、企业经理人机制不完善、社会人责任心不足等问题。
总之,尽管政府联姻市场实践并未彻底理清政府与市场的职能边界等问题,但却实践了社会主义探索“市场决定性作用”问题的理论,从理论与实践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三)市场主导型社会主义模式
该模式主要是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市场本位社会主义失败解体后,西方欧美国家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兼容的理论设计,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坚守者,也有西方左翼理论家的探索。其核心理念是借助市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试图利用“某些资本主义成功微观机制,设计出与发达资本义经济一样运行得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机制来”。[6]主要包括工人自治型市场社会主义、经理经营型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型市场社会主义等,理论界称之为当代市场社会主义。
首先,该模式确立了市场的绝对主导地位,设想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微观市场机制建构新型的社会主义模式。如罗默的证券市场社会主义就是借助“股票”对初始财产进行平均分配,并借用“股票”参与利润分红,甚至死亡上交“股票”来平抑代际不公等设想,建构以“平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模式。而巴德汉的银行中心市场社会主义则试图借助主银行、企业、分银行等互相监督、互相管理等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其次,该模式借用了新自由主义的外壳。尽管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宣称坚守社会主义的目标,但其实质是试图借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运用“凯恩斯主义式的管理”,通过“更加间接的宏观的”市场因素调控办法,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及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4]最后,该模式关注了“非市场”因素的作用。为了确保市场充分发挥作用,该模式普遍借助了“非市场”因素的助推作用。如米勒的工人自治型市场社会主义等就非常关注工人的“自由、民主、一人一票”等权利,通过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等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等。而经理经营型市场社会主义则普遍关注职业经理人治理结构,通过对职业经理人的监督管理及物质刺激等手段,确保职业经理人不贪腐、发挥最大能动性等,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斯韦卡特、罗默等人则非常关注法治在市场经济的保障作用,通过法治的手段监督企业、监督投资、甚至向民众保证公平公开等手段,以确保市场经济的导向性作用。
总之,尽管市场主导型社会主义具有一定的乌托邦特性,但却设计了早期“市场主导性作用”的模式。
(四)市场决定型社会主义模式
主要是指新常态下当代中国政府致力打造的市场本位社会主义的新形态。核心理念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最佳效应,建构政府、市场、社会等一体化的最优运行状态。
首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决定型社会主义是中国在原有的计划经济架构基础上,历经社会主义与市场二元共存、三位一体、四位一体、五位一体的实践建构,逐步恢复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定位。因此,市场决定型社会主义必须优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次,政府在市场调控中具有导向作用。市场决定性不代表“自由化”、“私有化”、“无序化”等,市场配置资源必须在政府宏观调控的导向作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政府宏观导向下实现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处理好市场与企业、市场与政府、市场与社会等的核心关系,发挥政府在制定市场法规、市场监管、市场服务、市场协调等方面的导向功能等。再次,市场因素与非市场因素整合运行机制。市场决定性作用并不意味着市场唯一性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同时,建构了融核心价值、法制保障、文化软实力、社会公正等一体化的整合优势功能,为市场决定型社会主义提供了良好的“合力机制”,回归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和马克思市场本位的逻辑本源。
总之,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探索市场决定性作用方面上尚面临诸多困惑,但市场决定性方向的提出却具有重大的创新作用。
四、社会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探索的借鉴启示
尽管社会主义市场本位理论探索经历了曲折,但其积累的实践经验以及教训的总结必然能够为新常态下市场本位探索问题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一)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本体创新
社会主义是调控市场的重要制度载体;市场是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重要手段。只有优先坚持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不变,市场才能具有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这就要求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市场机制等的双重创新,实现马克思所指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创新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真正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强势互补功能。社会主义探索市场本位的经验教训足以说明实现两种载体创新的价值。
国外社会主义在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实践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一是没有正确认识和评价马克思所示的社会主义的市场属性内涵,忽视了马克思市场本位思想的价值,在不符合实践的条件下片面采取了废除市场的极端举动,背离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实践道路;但在实践矛盾中退却回溯的背景下又忽视了市场机制的实践创新,限制了市场机制的优势属性发挥,窒息了社会主义与市场融合生成的力量。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在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逐步探索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的“二元并存”、“联姻兼容”、“市场基础型”、“市场决定型”等实践,在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市场机制的实践属性,建构了市场决定性社会主义新常态,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本质回归,恢复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市场本源定位。
总之,尽管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新常态下仍然面临更加艰巨的任务。因此,必须坚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双重优化,使社会主义与市场逐步回归本质性属性。
(二)理清社会主义与市场博弈的逻辑层次
社会主义市场本位问题的实践必须围绕社会与市场、政府与市场、企业与市场等三重逻辑维度,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深层次融合,这是社会主义与市场博弈实践得出的正确结论。
首先,关于社会与市场关系。社会与市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与市场博弈探索的宏观层次,也是社会主义市场实践中应该优先关注的问题。这要求社会主义在实践市场时应该考虑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实现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等与市场的宏观融合。早期苏东社会主义因过分强调社会公平公正问题,避免市场交换机制衍生的收入和财产的不平等性,建构了以绝对公有制为基础,以集权化的政治形态、文化形态等排斥市场的社会形态。但由于没有摆正社会公平与市场的关系,导致了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层次的错位与缺失,在效率低下的物质基础上建构了“平均主义”倾向的社会形态。传统市场社会主义却又忽视了社会主义制度属性与市场的融合,片面关注经济机制的价值发挥,没有看到社会组织、社会人、社会制度架构等对市场机制的同化影响作用,阻碍了市场与社会主义双重优越性的发挥。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在重视市场的同时却又忽视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性,建构在理想状态的理论设计必然是乌托邦等。
其次,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是社会主义与市场博弈的中观层面内容,也是社会主义与市场融合的关键。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市场机制优势的发挥、市场因素与非市场因素的整合、企业及职工积极性发挥等均依赖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早期苏东社会主义为了坚守社会主义价值目标选择了排除市场的政府集权式模式,过分夸大政府的力量,限制了市场机制的发挥而最终促使社会主义效率低下问题。传统市场社会主义为了克服社会主义与市场逻辑层次缺失错位的实践困境,努力探寻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结合。在坚持传统的社会公平的宏观导向下,着力于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为突破,建构了政府与市场联姻分权的实践形态。但由于未能理清政府职能边界与市场功能边界问题,使企业陷入了处理行政协调与市场协调双重制约的窘境,最终未能摆脱窒息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功能的困境。如南斯拉夫废除国家经济职能的“无政府”状态的企业自治形态;而匈牙利新经济体制强势政府造成的企业软预算约束、管理人员缺乏活力等同样导致政府管理失控与企业市场弱化等问题,造成了社会主义解体的根源。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则选择了坚持市场机制的背景下弱化政府宏观调控或者试图借助资本主义政府建构社会主义的梦想,必然陷入不切实际的幻想。
再次,关于企业与市场关系的微观模型。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与市场融合的最终落脚点,是正确处理二者关系的微观层次,也是最终检验社会主义与市场融合成效的关键点。早期社会主义因政府排斥市场而限制了企业与市场的运营机制,导致了传统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平均主义、效率低下、工人积极性不高等弊端;传统市场社会主义则因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难以摆正,并没从根本上破除国有企业存在的弊端,企业也不能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参与竞争,最终难以摆脱破产的历史宿命。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在深刻批判资本主义严重社会不公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探索市场本位问题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以市场为核心,着力建构市场与企业关系为重点的转型突破。如工人自治型市场社会主义借助“合作社”的市场载体,建构工人管理、市场机制、民主自由一体化的社会主义;经理经营型市场社会主义则重点通过“经理经营”,利用银行、利率、股票等市场机制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兼顾社会主义效率与公平。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则综合上述两种模式的优势,试图实现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完美结合等。但他们过分关注企业市场的关系而忽视社会与市场、政府与市场关系等的处理,致使这种模式陷入了乌托邦的嫌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探索市场本位的过程中同样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恢复了马克思市场本位社会主义思想传统。但同样也遭遇到关于社会主义市场关系逻辑层次混淆问题的困惑。
总之,社会主义在不断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博弈的进程中,理清了二者博弈的逻辑层次,为我们新常态下建构新型社会主义提供诸多启示。
(三)重视政府与市场的互补结构
政府与市场关系是辩证的统一体,不仅具有互相排斥、互相矛盾的对立关系,同时也存在优势功能互补结构。社会主义市场本位问题的探索充分证实了政府与市场互补结构的重要性。
首先,强势政府与弱势市场的结合。东欧传统市场社会主义就混淆忽视了政府与市场的互补结构,一直纠结于政府与市场孰重孰轻问题,最终在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方面选取了强势政府弱势市场的逻辑范式;片面把市场经济的机制植入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框架,但却忽视了政府蕴含的政治文化社会等制度功能对市场的反制约作用,未能及时发现政府蕴含因素对市场发展的优势作用,最终导致了二者的不可兼容性。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时,只关心政府与企业的权力边界,而忽视了政府的其他功能结构属性,比如社会与市场、人与市场的关系等,结果最终阻碍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兼容。
其次,强势市场与弱势政府的兼容。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则同样没有避免这个问题,他们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没有关注二者的互补结构,他们则采取了强市场与弱政府兼容的模式,把重点转移到关注企业与市场的关系,致力于微观企业模型的建构,试图通过企业模型利润提升在资本主义国家体制中实现社会主义。但对于政府蕴含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等的逻辑结构功能故意回避或者不甚重视,不仅忽视政府与市场的宏观导向作用,更缺乏对政府内在结构的思考,没考虑到资本主义的政府外壳能否自动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这种设计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乌托邦或改良变异的逻辑本质,也注定了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质疑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探索与市场兼容的改革中取得了系列成果,但同时也经历着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的矛盾纠葛。因此,在新常态背景下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政府与市场的互补结构,摆脱政府与市场的“强势、弱势”之怪圈,整合发挥政府的宏观导向与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四)发挥市场因素与非市场因素的合力
市场优势功能的发挥不仅依靠市场机制的优化,同样离不开其依附制度属性的熏陶,只有整合市场因素与非市场因素的合力机制,才能真正建构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市场本位结构。
首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理念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具有双重属性,一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一是优化市场经济的机制属性。其制度属性能够确保社会主义有机体的科学性;其机制属性能够优化市场经济的劣根性,确保市场有机体的属性优化。社会主义市场本位问题探索的事实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不管是苏东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抑或是市场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在探索市场本位问题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导向。为了坚守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目标,苏东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不惜牺牲市场利益而滑向“平均主义”倾向;传统市场社会主义则嫁接市场以提升效率促公平的实践模式;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引入市场主导的平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试图恢复市场决定型模式践行公平效率目标等。尽管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本位的实践中出现了或多或少的误区,但社会主义公平公正的核心价值目标并未改变,并在此目标导向作用下,设计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公正的实践模式。
其次,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与法治规范结构。法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保障,是调节政府与市场职能关系,规范企业运行、社会人市场活动等的基本约束体系。社会主义探索市场本位的实践经验教训暗示了法治的重要价值。
传统市场社会主义在实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嫁接时,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传统社会主义的人治体系,忽视了法治作用对市场本位的重要价值。南斯拉夫市场社会主义解体根源于其民族分裂问题,而其民族分裂问题又渊源于国家职能的消失,在国家的经济职能丧失的同时,其政治职能、文化职能、社会职能等同时也随之消失;最终完全丧失运用法治对市场的控制权与主导权,以“劳动组织”自治的社会主义陷入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而步入穷途末路。当代市场社会主义非常关注这种这种实践的教训,其在模式设计的时候都充分考虑到法治的力量,一是借助资本主义的法制体系管控经济与社会;二是依靠法治的手段管理企业与职工。米勒、罗默、斯韦卡特等都明确地提出运用法治监控银行企业的方法和手段;其他市场社会主义者则明确制定了工人政治生活、民主生活的经济管理化形式则,规定了工人参与管理、分配、收益、投资等的具体规章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提出“市场决定性配置资源”之后,虽然提出“依法治国”的重大法治导向,以确保市场经济的规范性发展,破解市场经济带来的腐败、政府职能模糊、市场规则不健全、经济人职能错乱等问题,但完善市场与法治规范结构的任务势在必行。
最后,实现“经济人”与“社会人”融合。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不仅要在“道德上优越于资本主义”,同时要在“经济上优越于资本主义”,二者是“比肩而立、相互补充”的。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人将会替代经济人是不对的”,未来社会必将是“二者融为一体”。社会主义市场本位问题探索的实践基本秉承了马克思的设想。
传统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是建构在“社会人”导向较强的社会体系中,人们的物质意识、竞争意识、权利意识、规则意识、民主意识等大多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缺乏成熟的市场经济需要的价值观念、价值导向、市场心态、交往规则等,处于政府行政管控与市场治理的行政领导、职业经理、普通职工等很难做出正确的决策,最终直接反映在企业生产、销售、分配等各个领域,从深层次制约限制市场经济的完善与发展,严重影响了东欧传统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如南斯拉夫设想把国家职能交由“劳动组织”等所谓的群众自我管理机构,让民众实现自由民主地管理国家生活,以避免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带来的分配、交换、腐败、利益纠葛等问题,但结果是原有政府存在的矛盾直接被转移到了“劳动组织”内部,与传统国家的矛盾并无差异。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则借鉴了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在理论设计中充分考虑到了经济人与社会人的融合问题。如工人自治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直接提出通过工人的一人一票制来决定企业的重大事项,参与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而经理经营型社会主义则聚焦于经理的经济人社会人属性,既通过各种法律、监督等手段制约其经济人属性,又通过激励机制等促进其社会人属性的发挥,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面临经济人与社会人的属性融合问题,公民的法制意识观念淡薄、民主意识扭曲、规则意识不强、市场心态脆弱等新问题,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整合经济人与社会人属性的融合,破解新常态社会主义市场本位问题建构的薄弱环节。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问题是马克思市场批判理论的重大理论预示,也是社会主义百年实践的艰辛探索之结晶。其蕴含的实践经验与失败教训必然能够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实践提供理论启示与实践借鉴,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
[2]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6.
[3]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4.
[4]伊藤诚.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M].尚晶晶,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34-35.
[5] W.布鲁斯,K.拉斯基.从马克思到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索[M].银温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39.
[6] Roemer John,Can There Be Socialism After Communism? [M]// Market Socialism:The Current Debate,Pranab Bardan,John Roemer,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责任编辑:张积慧)
The Derivative Logic and Practice Enlighten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Decisive Role Theory"
Xu Junfeng1,2
(1.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2.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1701,China)
Abstract:A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it is propos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market should be well handled,and market should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allocating resources",which is considered as a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The "socialist market decisive role theory" is originated from Marxist theory of "no market","near market" and "pro-market" and a logical route of "anti-market——near-market——pro-market" formed thereafter. The model of it experienced several rounds of evolution,including government simulating market,government allying with market,market dominating and market deciding,and many lessons and experiences have been accumulated during the process. All these reveal that we should that we must take the bi-dimensional innovation and game level of both socialism and market into account;explore the complementary structure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integrate force of mar
ket factors and non-market factors;enrich and perfect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socialism;market decisive role theory;logic traceability;practice enlightenment
DOI:10.13253/j.cnki.ddjjgl.2016.03.002
[中图分类号]F04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03-0001-07
作者简介:徐俊峰(1971-),男,河南杞县人,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与发展。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马克思市场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14YJA710033)中期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5-10-05
网络出版网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356.f.20160202.2118.002.html网络出版时间:2016-2-2 21:1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