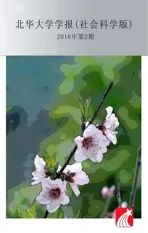论张爱玲小说的生命意识
2016-12-17龚永标
龚永标
□ 文学研究
论张爱玲小说的生命意识
龚永标
[摘要]尽管张爱玲曾在上海一夜成名,其作品也多为在大陆时所作,但国内对张爱玲的研究在几十年的现代文学研究中一直是一片空白。直到近些年,特别是张女士在洛杉矶去世后,国内才重新掀起了“张热”。人们从不同的视角,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探索张爱玲小说世界的奥秘,取得了许多可观的成果。本文试试从张爱玲小说生命意象的荒凉来阐述张爱玲小说的成就与特色。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生命意象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不论社会革命抑或传统文学,均融于狂飙突进的时代长河。尤其是在文学领域,一方面追求现代化,另一方面不断探求民族精神底蕴,并且在二者的张力中发展、变化,而在其中表现得较为突出的,非张爱玲莫属。
一、生命意识的表征是荒凉
张爱玲的荒凉意象是在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矛盾张力中发展的,她以自己的笔触,从女性角度,阐述社会的人、事、物,描摹出一个个荒凉意象,构筑出一个个荒凉的意境,很好地诠释出自己的文学观与创作观。
西方作家往往喜欢用一个主要意象和几个次要意象来模拟和深化题旨,因此有所谓“主模题”和“副模题”之分。如《包利法夫人》中的主、副模题就是大海和蓝色;海明威的小说里,遍布着“牡牛头”和“鲟鱼”等意象,颇似图腾。
张爱玲在大陆重新“出土”之后,很多评论文章都提到了她的四个使用最频繁的基本意象:“太阳”“月亮”“镜子和电车”。在它们之上,还有一个统摄全局的主模题:荒凉。类似的意念还有:“陷下去”“坠着”“向下浇”,等等。在张爱玲的小说里,荒凉不仅是一个抽象的主题,也是一个使用频率颇高的具体意象。荒凉,是这个世界的一种普遍失望,是生活理想的逐一破灭。正如她写的诗歌:
谯楼初鼓定天下,
安民心,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
沉到底……
中国,到底。
张爱玲虽然不是一个诗人,但她小说中的许多情境都是相当诗化的。这里面写的,是她对中国现实生活的诗意感受,比小说更诚实地表露了她的文学世界观。它提供了《传奇》故事一种共同的诗性氛围。在“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里“下沉”就是张爱玲小说所有人物的共同命运。小说《花调》里,有一句话可以概括她笔下主要人物的心理感受:
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
这是张爱玲小说同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区别所在。她不是以超然的态度客观地观察和摹写现实,而是以她荒凉的主体意识以及自身的悲剧气质感受生活。她是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抒写“内心的现实”的。因此,她对人性中自私、冷漠和残酷等特点的揭示,虽有她自己生活经历的现实基础,但这个现实是经过她“主观放大”后的“现实”,有别人达不到的人性深度,[1]42-43也有不可避免的偏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来谈荒凉这个主题。
二、淡然的笔触流泻的是生命情感的缺失
既然张爱玲认为世界根本没希望,而这绝望的荒凉状况又正是人自己造成的,人性和文明都是靠不住的,朝不保夕的,这就使人类只能走向无边的黑暗。在这样一种荒凉的大悲之下,张爱玲对人性及文明作了最彻底的否定。具体到作品中,也就是否定了人类的两种基本情感:“亲情和爱情”。
张爱玲在散文里认为母爱这一大主题,像一切大主题一样,被做了太多的滥调文章……其实有些感情是:如果把它戏剧化,就只剩下蚕豆病,母爱尤其是。张爱玲对伟大的母爱之类的题目一向反感甚深,固然有她童年时母女感情冷漠生疏造成的心理上的创结,但主要还是出于一种对人性的普遍失望。她所做的,果然不是滥调文章。
最明显的是《金锁记》。曹七巧是一个因金钱欲而出卖青春和自由的女人,长期的生活煎熬使她心理变态,她像毒蛇一样凶狠地守着她卖掉一生得来的钱。她的贪欲膨胀到这种地步,她要完全占有自己的儿女。于是她一个个逼死自己的儿媳妇,让儿女抽上鸦片,又剥夺女儿唯一一次婚姻的机会……到最后,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30年来她载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深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上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透了她……这一段对亲情冷静而又令人悚然的描述,在现代文学史上就算不是绝无仅有的,也是相当罕见的了。七巧的家庭,是封建家庭制没落延续,七巧同她代表的那种生活一起荒凉了。
然而曹七巧还是她小说里唯一一个彻底的人物。但一样的是,亲子关系的生疏和冷漠。纵观张爱玲一生的小说,母子情、父子情、兄弟之情全是不可信、不可靠的。即使是她受到解放初政治环境的影响,写出的唯一一部具有光明结局的小说《十八春》里,亲情依然被写得令人沮丧:漫璐出于欲望作祟捕杀自己的妹妹;曼桢的母亲出于名誉上的考虑,实际上是放弃了被坑害的女儿……由此可见张爱玲对亲情的绝望是何等彻底,任何情况下她都不放弃这一观念。在一切都绝望,一切都荒凉的大主题下,亲情没有被肯定的可能,相反,只能是这样一种丑恶人性的侧面。
在同一主题下,爱情也岌岌可危。
《倾城之恋》里,白流苏是一个年近30岁的单身女人,成了全家的拖累。为了利用剩下的最后一缕青春,她同范柳株“谈恋爱”了——为获得丰足的物质生活,并保证她的淑女身份。而柳原则是一个留过洋又自暴自弃的风流子弟,他只是在流苏身上欣赏她传统的中国女人的美感。“他要她,可是他不愿意娶她。”流苏的目的是结婚,柳原的目的是“谈恋爱”。他们的恋爱,倒更像一场勾心斗角的战争。最终流苏面对的,仍是不明不白、不尴不尬的绝望生活。
同样的,《金锁记》里姜季泽利用七巧对他的爱去骗她的钱。《心经》里是父女的乱伦之爱。《沉香屑——第一炉香》里,薇友被迫把婚姻当成“长期的卖淫”。《红玫瑰与白玫瑰》里,佟振保因为担心舆论会影响他的前途,把与他相爱的女人果断地牺牲掉了。
我们看到,爱情也好,亲情也好,一旦同人的私利发生冲突,立即化为乌有。在这种伦理的沦丧,真情的沦丧之中,人性的世界荒凉了。
其次,荒凉这一主题消解了小说人物所有抗争的意义。既然这是一个没有希望,没有出路的世界,挣扎有什么用?既然这个世界不可挽回地荒凉到黑暗中去,又何必争取什么呢?于是似乎只剩下一条路,闭上眼睛,跟这世界一起往下沉。
张爱玲自己说:“……我小说里的人物的那种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1]42-43她小说里许多人物都挣扎过,但最后都选择了“失面子的屈服”。
小说《留情》里,郭凤是米先生的姨太太,两人相差20多岁,已完全没有什么感情。夫妻关系相当疏远、冷漠、不和谐。照郭凤的说法她“是完全为了生活”。这样的婚姻是令人窒息的。然而郭凤并没有摆脱米先生的念头,相反,倒出现了这样的场面:
郭凤站在那里,呆住了。回眼看到阳台上,看到米先生的背影,半秃的后脑勺与胖大的颈项连成一片,隔着个米先生,淡蓝的天上现出一段残虹,短而直,红,黄,紫,橙红……
对于郭凤而言,米先生是谁并不重要,生活本身已把米先生同她绝望的理想牢牢地拴在一起,米先生已经取代了她的理想。她已经不再需要理想。
而米先生则“仰脸看着虹……对于这世界,他的家不是爱而是疼惜”。
“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然而郭凤与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着。”尽管“相爱”两人字多少有点讽刺,可到底无可奈何。这两个人,在烦冤的人声中沉下去了。
小说《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有一个意象含义是颇深的。做佣人的阿小看过一部电影:一个女人在大风雨的街头歪歪斜斜地奔波,无论她跑到哪里,头上总有一盆水对准她浇下来。阿小也感到“一盆水对准她浇下来”,然而,“她在雨中睡着了。”流苏、薇龙、振保、娇蕊、郭凤、小寒、长安……所有这些人物,最后全在“雨”中睡着了。闹归闹,闹完了,终归要活下去;疯狂了一阵,他们还是安静了,麻木了,妥协了,沉下去了。“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
更为重要的是,张爱玲不仅对她笔下苟活下去的人物不作什么道德评判,而且还彻底否定了旧道德的评判标准。也就是说,在否定了人性之后,她又否定了人类文明的成果。这同样是在荒凉的大主题中达到的认识。在她意识里,她深刻地认识到,正是旧道德对人生的忽视的虚伪态度,日积月累导致了人性与人类文明的没落和毁灭。
在记录香港战事的散文《烬余录》里,张爱玲同她的许多同学一起,到“大学堂临时医院”去当看护。有个病人得了烂蚀症,痛得受不了,为了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他整日整夜地大声呻吟,召唤护士。张爱玲没有同情唯有厌恶。那个病人同护士之间,形成的其实是一种敌对关系。后来那病人终于死,她用平静的语气记录了她与同伴的反应:
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快天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小炉面包,味道颇像中国的酒酿饼。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
尖刻的讽刺后面是压抑了的悲哀。在这里,她自己和同伴的态度向她证明了人的孤独和自私,但她的冷嘲并无多少自责之意——她一直无意于道德上的判断。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自私的,人生来就是孤独的,自责又有何用?对张爱玲而言,问题的关键不是对道德原则的重申,而是人性真相的必须接受。在《烬余录》的结尾,她道出了这一真相:
“……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和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在张爱玲的视野里,现代人是各自悬浮在真空之中的。由于人性中的自私和愚蠢是不可克服的,所以每个人都是别人的敌人,每个人同这世界,也是敌对。在这个意义上,张爱玲对个性,对人类文明的把握,逼近了现代意义上西方文化对“存在”、对终极意义的理解。只是在张爱玲这里,这种“理解”更彻底地表现为怀疑和否定,因此她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也不需要希望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唯一命运,就是在绝望中荒凉下去。
三、生命意象的交错共鸣
荒凉主题并不仅仅提供一种抽象的整体意义上的“氛围”,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也呈现出“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妙不可言的状态。
《红玫瑰与白玫瑰》里,振保在巴黎街上看见的是一个“落日”的景象:
街灯已经亮了,可是太阳还在头上,一点一点往下掉,掉到那方形的水门汀建筑的房顶下,再往下掉!房顶上仿佛雪白地蚀去了一块。
在这里,太阳的落下,象征着欲望的堕落。振保终于狠下心,跟一个有狐臭的下等妓女进了旅馆。他一生情欲的堕落,就从这次巴黎的落日开始。
而在《倾城之恋》里,荒凉意象的使用就更为关键。前面已经提到过发生在流苏和柳原之间的这场“战争”,柳原后来渐渐占了上风,流苏一步步走向被动,最后只好朝姨太太的路上走。然而这时,香港沦陷了,两人在战火中相依为命,疲于逃窜。最后,柳原终于决定同流苏结婚。在进城结婚的半路上:
走到一个峰回路转的地方,马路突然下泻,眼前只是一片空灵——淡墨色的,潮湿的天。小铺门口挑出一洋磁招牌,写的是:‘赵祥庆牙医。’风吹得招牌上的铁钩子吱吱响,招牌背后只是那空灵的天。
在一场长期的、沉闷的、令人沮丧的拉锯战之后,突然出现了这样萧疏而开阔的境界。然而,柳原马上感到了那“丰谈中的恐怖”。在这里,人性急转直下,去掉了一切的浮华,所要的无非是一点踏实感,因为再也掩饰不了那种“迷路的文明人”刻骨的孤独。
“马路下泻”不仅是一个心灵契机,流苏命运的转折点,也是整个故事情节发展到顶峰的急转直下。如果我们注意到马路不是“上升”而是“下泻”;马路之上不仅是一块空灵的天,还有一块突兀而有工笔画风格的牙医招牌,我们就可以模糊地猜到人生的真相,并掉到流苏命运的未来。“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人生是这样充满苦难、没有希望,流苏也没有理由例外。两人结婚以后,柳原是“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尽管流苏还可以用“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这种念头来欺骗她自己,但她仍摆脱不了“一寸一寸陷下去”的命运,她只是和别人一样“在雨中睡着了”。
在张爱玲其他小说里——
那月亮,“低一点,低一点,大一点,像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金锁记》)
那雨,“还在哗哗下,一盆水对准了她浇了下来。”(《桂花蒸 阿小悲秋》)
在《年轻的时候》里,“只有年轻人是自由的,年纪大了,便一寸一寸陷进习惯的泥沼里。”
七巧是“一颗心直往下沉坠”。(《金锁记》)
范柳原是“不由自主往下溜”。(《倾城之恋》)
言丹朱是“那斗篷浮在空中仿佛柄偌大的降落伞,伞底下飘飘荡荡坠着她莹白的身躯。”(《茉莉香片》)
……
这种逐渐向下坠落、沉陷的空间感觉,几乎在每一篇小说中都可以找到,那一个个对外封闭的世界,夹带着鬼气、烟枪,不会走的时钟,咿咿呀呀的胡琴全部都沉了下去。那些在封闭的世界中活着的人,也都闭起眼睛随它往下沉。
四、小说生命意识的内在机理
(一)从荒凉这一主题,我们还可探讨张爱玲跟西方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复杂关系。
如果以一次世界大战为界,把西方文学划分为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那么我们大多数新文学作家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实质上是他们与西方古典文学的关系。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建立在对人的理性、对科学、对社会和文明进步的肯定信念上。因此其作品的基调本质上必然是理想主义的、乐观的,其作品的一切冲突最后几乎都归结到人与业已腐朽的旧制度的对立上。
而张爱玲则不同,西方文学中真正影响她的是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西方作家。她在文章里多次提到过的毛姆、赫胥黎、威尔斯、奥尼尔等,都是活跃于战后英、美文坛的小说家、戏剧家。他们创作的共同背景是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普遍感受到的精神危机。当时弗洛伊德学说也已产生了广泛影响,很多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强调了非理性的一面。张爱玲显然受到这些作家的影响。她多次提到的“思想背影里惘惘的威胁”;时代“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跳出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看来是如此。”这些同上述作家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同时她自觉地以情欲,以非理情解释悲剧,解释人的行为动机,解释人性的肮脏和不可理喻。悲剧扎根于人性。因此它是人的普遍永恒的处境。“张爱玲的作品中弥漫着对人生的非个人的大悲”。尽管这种“大悲”仍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但也确实使她达到了别人难以企及的人性深度。[2]
由于张爱玲自觉形成了荒凉这一悲剧性主题,以至于她能整体地接受内在的关于人的本性的解释,从而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关于存在的意识,并能得心应手地在作品里表达出来,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同现代文学史上其他女性相比,如那吟唱着凄然将捉在手里的灯蛾放到窗外去了的冰心,张爱玲几乎是狞厉的。
但是她与西方现代文学的瓜葛也仅止于此。她对西方现代文学的阅读也就只局限于上述几个人。很明显,传统文学对她的影响要大于外国文学。
首先,为她的创作直接提供养料的,是传统的章回白话小说。再进一步说,就是旧小说的言情传统。这个“情”,既指“男女之情”,也指“世情”。鲁迅评说《金瓶梅》: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揭写世情,尽其情伪。而脂砚斋评《红楼梦》也说:冷暖世情,比比如画,世态人情隐跃其间。但是在这些平凡琐碎的世态人情之上,有着作者对人生的一种绵绵不绝的经过审美化了的忧患意识和挽歌情调。由于张爱玲本身具有的悲观气质,她与这一传统一拍即合。对此,她自己在《中国人的宗教》一文中作了最好的阐释: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拽向虚无。[3]
在这里,张爱玲清楚地说出了她对世情小说传统的解释,由于对生命意义的彻底绝望,因而人们形而下地追求琐碎的生活细节,追求无意义的意义。张爱玲对旧小说的这种解读,也指导了她自己的创作。所谓荒凉其实正是对一切都怀疑,永远悲观。很多人认为她后期作品才气枯竭,索然无味,其实她是严格地贯彻了自己的创作观念。作为作家,她一年比一年成熟,但也一步步走上了同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一样的绝路。
于是在张爱玲的作品里,我们看到,现代人的存在意识,对时代的恐慌,对现代文化的失望,与这种古老的东方式的悲哀融为一片。在荒凉这个大主题下面,它们相互渗透在一块;于是我们看到的,不再是西方现代作家笔下惨淡的决裂,而是以审美的、诗意的哀感来中和现实苦难。《传奇》里所有的人物,最后都在“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中荒凉到平庸琐碎的生活底层去了,可他们在人生中还不断找到小小的暂时的欢乐,不断地感到小小的满足。
哪怕仅仅在这一点上——在对中西文学有机的结合上,张爱玲也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二)童年生活的“创结”。张爱玲生长在一个满清遗老遗少的家庭。父亲具有一切纨绔子弟所有的劣性:“抽鸦片、娶姨太太。”父母在她年幼时就离了婚。后母虐待她,而父亲在毒打她之后,把她囚禁在一间小屋达一年之久。她在囚禁间得了痢疾,几乎死去。后来逃至生母处,新派的母亲对她又没有多少感情,失落于家庭,失落于人群,她对这世界可以说有一种“基本敌对”的情绪。她的前期作品,都可以说是对这些窒息过她的人与事的全面清算。
(三)香港战事经历。沦陷时她正在那里念大学。战争摧毁了文明的成果,人性失去了所有的依托和矫饰,赤裸裸地显现出来。在散文《烬余录》中,张爱玲记录了战祸中人类情感异类反应的种种深刻表现。而这里的“异常”,其实也正是一种返回原始、返回动物性的真实。“人类的文明努力要跳出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吗?看来是如此。”她的人生观很大程度上利益于这个时期阅历;她曾经称小说集《传奇》是写给上海人看的香港传奇,就是基于这个原因。
(四)所处时代。1943—1945年是她文学生涯中最辉煌的两年。当时的上海沦陷于日寇,处于“孤岛”,是“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以张爱玲的近乎病态的敏感,对这样的气氛不可能没有感觉,所以她多次说:“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人们只是感觉日常一切都有点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像影子似的荒凉下去。”然而,这种“惘惘的威胁”却是最适宜她创作的后气氛,最契合她荒凉的主体心态。柯灵对此有精彩的论述:“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她机会。”事实证明,离开上海后,她再也没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她文学生命的起点,也是她的顶点。由此便可以这么说:揭示“在不可避免的时代沉落中,人的生存状态”,是张爱玲以《十八春》为界的前期作品的基本主题。
从近代西方小说中吸取运用象征和意象的手法,从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红楼梦》中获得丰富的艺术营养,中西两种艺术传统在她的小说中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和谐。小说作心理分析,既不采用冗长的独白,又不作繁琐枯燥的解剖,而是利用暗示,把动作、语言和心理三者打成一片。巧设譬喻,形象入画,新旧意境交错,新旧文字揉和,构成了独特鲜明的艺术风格。
张爱玲经常强调自己最常用的字是“荒凉”。确实,这“荒凉”二字是张爱玲的生命特征的写照,是她的心态的描绘,也是她创作的基调。正是基于此,张爱玲小说生命意象特征集中表现于生命的荒凉,并进而奠定了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尤其呈现出女性文学的璀璨。
参考文献:
[1] 周魏.论张爱玲小说的艺术创作[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42-43.
[2] 黄修己.20世纪中国文学史[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212-214.
[3] 颜雄.简明中国现代文学史[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260-263.
【责任编辑李开拓】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01(2016)02-0121-05
[收稿日期]2016-02-24
[作者简介]龚永标,湖南环境生物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写作教育研究。(衡阳421001)
On the Life Consciousness of Zhang Ailing ’s Novels
Gong Yongbiao
(DepartmentofPublicCourses,HunanInstituteofEnvironmentalBiology,Hengyang421001,China)
Abstract:Although Zhang Ailing ever became well-known overnight in Shanghai,most of her works were written in China ’s mainland,the research of Zhang Ailing’s in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as been a blank.Until recent years,especially after the death of Ms.Zhang in Los Angeles,it once again set off a “hot” in China.From different angles of view,people took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 to explore the mysteries of the world in Zhang Ailing’s novels and achieved many significant results.The author tries to explain the achievem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Zhang Ailing’s novels from the desolation of life consciousness in Zhang Ailing novels.
Key words:Zhang Ailing;Novel;Life conscious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