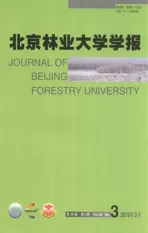一次未能付诸实践的太平洋科学会议
2016-12-15刘亮
刘 亮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一次未能付诸实践的太平洋科学会议
刘 亮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太平洋科学会议是20世纪上半叶在太平洋地区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综合性国际学术会议。民国时期该会召开过7次,但作为太平洋科学协会会员国和太平洋沿岸大国之一的中华民国,竟然没有举办过一次。事实上,当时以竺可桢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对举办该会早有设想,并随着时局的变化对设想的具体内容不断作出相应的调整。但由于当时中国政局不稳,科学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政府投入有限,而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及太平洋局势不断升级后,太平洋科学会议自身也陷于停滞的局面,这些都造成了在中国举办会议这一设想化为泡影。
太平洋科学会议;竺可桢;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
创办于1920年的太平洋科学会议,原名泛太平洋学术会议。最初由美国学术研究评议会的太平洋研究会发起,召集新西兰、澳洲、爪哇、中国、日本、加拿大、美国、檀香山、菲律宾等太平洋沿岸国家和地区代表举行会议,旨在促进太平洋地区的地方科学研究,增进科学家之间的感情。后于1926年东京会议时成立永久组织——太平洋科学协会,凡沿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及其属地均有资格加入,并以该国国家科学研究院或与之相当的学术团体为代表。由于当时英法等国在太平洋地区有大片的殖民地,因此也成为成员国。这样,当时世界上科学发展走在前列的几乎所有国家及其在太平洋地区殖民地的科学家,每隔3年定期聚集在一起进行学术交流。由于当时中国内乱频仍,政府无暇顾及,学界亦馁于从事,以致前两次会议均无中国学者参加。1926年东京第三次会议,中国开始派团参加。这是民国时期中国学者首次组团赴海外参加综合性国际学术会议。此后一直到1939年第六次会议,中国均有代表参加。
由于会议举办地实行轮流制,在夏威夷、澳大利亚、日本分别举办了前3次会议,而第四次、第五次已确定分别在爪哇和加拿大举办的前提下,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1890—1974)及地质学家翁文灏(1889—1971)于东京会议后就提出了将来由中国主办一次会议的设想。那么这个设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最终为何没有实现?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展现中国科学事业在20世纪上半叶艰难的发展状况,并为认识今天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太平洋区域合作机制的渊源提供更深刻的历史背景。
目前学界关于太平洋科学会议历史的研究很少,如周雷鸣的《凌道扬与太平洋科学会议》一文,而其《凌道扬参加第五次太平洋科学会议及其主持太平洋沿岸国家森林资源调查史料》则是对相关档案资料的整理。由于主要围绕林学家凌道扬展开,因此对太平洋科学会议的历史及关于中国举办会议的设想等内容论述较少。其他则散见于各种论述民国时期科学体制化历程的专著中,但仅在有关中央研究院成立的背景时提到东京会议上的风波,并不涉及具体内容。
一、设想的框架
1925年8月,在中国科学社第十次年会书记报告中,竺可桢首次建议对于由中国举办太平洋科学会议应有所准备。“既曰联太平洋科学会,则各国均有尽地主之义务,我国科学界似应于相当时机得政府之资助召集会议。顾目前国内蜩螗,科学事业均未发轫,只能暂作缓图也。”[1]当时第三次太平洋科学会议举办在即,但中国学者还从未参加过。竺可桢在谈及和外国科学团体联络问题的时候,提到这件事情,可见由中国主办会议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意义。在参加了第三次东京会议,对太平洋科学会议有更深入的了解后,1927年2月,他对于由中国主办会议的设想就明显具体化,计划1941年在长江流域举行会议。当时的考虑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第五次会议地点已确定在加拿大,而第六次举办权很可能会给越南。而按照3年一届的周期,1941年为第八届会议的举办年,当时尚未确定举办地。另外,“据天文学上之推算,民国三十年九月二十一日,长江流域将见日全蚀。日全蚀为稀有之现象,天文学物理学上有若干问题,均待日全蚀时数分钟之时间为解决,是以科学家往往不惮数万里之跋涉,以得瞻览此一瞬即逝之现象为快。而阳历九月,在我国长江流域一带,秋高气爽。其天气与观测日全蚀又极相宜。是以,若于民国三十年九月杪或十月初,在我国开大会,实可谓一举两得。”[2]
可以看出,这一设想兼顾了会期与日蚀观测,应该说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个方案。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有所变化,他又适时地对这一设想做了调整。1931年9月17日,第五次太平洋科学会议筹备委员会在南京召开会议,会上通过六项决议,第六项即请中央研究院呈请国民政府于加拿大开会时,准由我国出席代表提出邀请第七届太平洋科学会议于民国27年(1938)在中国举行[1]。这些决议是由时任太平洋科学会议筹备委员会主席的竺可桢亲自草拟的,主要是考虑到按照3年一届的会期,1938年应举办第七次会议。但由于种种原因,本应于1932年在加拿大举行的第五次会议延迟至1933年。这样事实上,第七次会议也无法在1938年如期举行了。在第五次会议上,关于下届地点,代表们看好中国、俄国及越南。越南因为经济困难,取消了在爪哇会议上的邀请。俄国因政治关系,无人出席会议。可以说这是中国发出邀请的大好时机,但是由于当时政府并未做出任何回应,因此中国代表未敢贸然邀请。下届开会地点悬而未决,为历来所未有之事,其意似专待中国之邀请也[1]。1937年5月2日,在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上,竺可桢考虑到当时美国邀请于1938年在洛杉矶举行第六次会议,因此建议邀请于1941年9月21日在中国开第七次会议,并决定请行政院拨给40万元作为招待费,这一建议获得了院务会议的通过[3]。
翁文灏对此也有类似的设想,他在参加1929年第四次爪哇会议后,考虑到各国轮流举办会议,而第五、六次会议举办地已基本确定为加拿大和越南,第七次会议(1939—1941)则由新邀请国筹备。这样提出邀请后,约有6~10年筹备时间。他认为“中国学术事业虽尚幼稚,然二十年来亦已稍有进步,倘能确定经费,用心筹备,亦未始不可举行一次国际会议。且以中国地大物博,气候适宜,各国学者来者必多,专家切磋其所能指导发明以引起吾国学者之观感,而促进吾国学术之进步者,为效必极宏大,中国学者中亦颇多责望吾辈赴外出席者早为轮作主人之计。……中国倘欲邀请,亦必须审慎从事切实筹备方可。目前似尚在内部建设,自身努力时期,会须直起急进,迎头做去,庶十年以后或有实在成绩可于天下共见也”[4]。
可以说,这与竺可桢的设想不谋而合。他们都认为在1940年前后中国可以举办一次会议。当然,竺可桢之所以能作出更加具体的设想,与他当时在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所做的工作,在中国科学界的地位以及他一直关心国家科学发展是分不开的。1915年竺可桢成为中国科学社第一批社员;1916—1918年,他连任中国科学社董事;1919年成为科学社永久社员;192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社理事会书记。1926年11月21日,在中国科学社理事会上,竺可桢向大会传达了商务印书馆已应允承担招待出席第三次泛太平洋学术会议各国代表转道来华游历者的费用这一消息。1927年9月在中国科学社第12次年会上,被推为参加太平洋科学会议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后又在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会及各专门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被推为观象台(包括天文台、气象、地震、地磁)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同年12月在中国科学社理事会议上当选为社长。1928年5月12日,竺可桢提“关于太平洋科学会议应急进行案”,经中国科学社理事会议决从速筹备。同年5月22日,在中国科学社邀请各学术团体讨论出席太平洋科学会议事宜的宴会上,竺可桢报告了太平洋科学会议有关情况。同年8月18—22日在中国科学社第13次年会上,报告筹备参加太平洋科学会议经过。同年8月19日,主持中国天文学会第六届评议会第三次会议,讨论参加太平洋科学会议代表等事宜[5]。太平洋科学会议主办方发来的相关通知、日程、论文规则等均由竺可桢接收并转发中央研究院办事处[1]。
在哈佛留学的5年,竺可桢深受哈佛大学校长罗慧耳、前任校长伊里阿特、地理学教授台维斯等人的影响[6]。而台维斯正是推动举行太平洋科学会议的关键人物之一。
二、设想提出的背景
上述设想的提出,绝非偶然。东京会议上,中国几乎丧失会员资格,中国学者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而在亲眼目睹东京会议之成功与日本科学发展取得的成就后,思想上亦受到强烈的冲击。他们从日本科学发展隐约看到了中国科学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急欲通过举办太平洋科学会议唤醒政府和社会各界对科学事业的重视,并以此作为向国际同行展示中国的平台。正如竺可桢所说的那样,“此等会议,于各方虽均有益,而以开会地点所在国关系为尤大,盖各国代表不远千里而至异邦,对于所在国之风俗人情、文化学术多属茫然,全赖所在国当局之指导与宣传。如得其道,则可以引起各国人民之爱敬,增进国际之地位”[2]。
(一)中国争取到太平洋科学会议行政委员会成员资格
作为太平洋沿岸的大国之一,中华民国理应成为当时太平洋科学会议行政委员会(Pacific Science Council)的成员。但由于澳洲会议中国无代表参加,因此该会议所推定之学术会议章程起草委员中,包括了美、澳、加、法、英、夏威夷、日、荷、荷属印度、新西兰、菲律宾等11国,并没有中国。可以看出,这些国家要么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要么是其殖民地或属地。东京会议时,中华民国和苏联同被邀请。但在闭幕开全体会议时,中国代表团才被告知由于中国没有能够代表国家的学术机构,因此落选。当时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所谓缺乏国家学术机构,只是推托,并非全部的原因,因为已经获得会员资格的国家或地区中,夏威夷以一博物馆(Bishop Museum)为代表机关,荷属印度以太平洋委员会为代表机关,这都与国家学术机构的性质不相符合[2]。显然,当时中国“科学程度幼稚,国际学术地位衰微”[7]才是真正的原因。
后中国代表提出书面抗议,暂以中国科学社为代表机关,要求加入委员会,请大会公决。幸赖美国学者祁天锡(N.Gist Gee)动议,终于得到通过,从而获得应有的地位。
由于中国科学社无法真正代表国家,竺可桢、任鸿隽等学者在东京会议后呼吁国家学术机构急应设立。当时著名学者张云(1896—1958)在向国内介绍如何加入国际学术研究会议(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这一组织时,也呼吁及早成立国家学术会议。因为欲加入国际学术研究会议,须有一负责的团体担任缴纳会金等。这种团体分为3种,一是以政府名义,二是国家学术研究会议(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三是科学院或皇家学会。他认为当时政府“基础未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因此以政府名义加入不适宜,最好的方法还是国家学术机关。但当时,中国的学术团体多由私人组建,“分门别类,自树一帜,对内既与政府不发生关系,对外亦不能为国家学术团体的代表……所以乘此对内提倡科学,对外增进国家学术地位的时候,理宜立即组织此项国家学术团体,以担此巨责”[8]。在各方的努力下,中央研究院于1928年成立。可以说东京会议上的风波直接促成了这一国家学术研究机构的成立。此后从第四次爪哇会议开始,中国即以中央研究院作为代表机关。
“我国既在太平洋科学会议之行政委员会中占得一席,则我国下届开大会时即有直接派遣代表之权利。但大会地点由各国轮流邀请,将来必有一日,我国应尽地主之义务。则未雨绸缪,今其时矣。”[2]这是设想在中国举办会议的先决条件。
(二)东京会议的巨大成功及日本科学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东京会议是太平洋科学会议创办以来,中国学者首次组团参加,同时也是民国时期中国学者首次参加综合性国际学术会议。中国的亚洲近邻在科学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迅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高度注意。
首先,此次会议本身办得非常成功,会议规模为前三届之最,第一次夏威夷会议到会50人,第二次澳洲会议与会90人。而此次会议,仅日本本国代表就有413人,其他各国代表共计150人[9]。更重要的是,“其设备之完美,招待之周到,莫不驾澳洲大会而上之”[2]。日本政府对此次会议也非常重视,日本朝野出其全力至诚招待外国代表[10]。此次学术会议日期,虽仅两星期,但日本政府招待之期限,达一月之久。会后游历名胜5次,计20组。北自北海道,南至四国九州,包括日本全国名胜及科学机关[2]。各国对主办方的工作都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竺可桢曾说,“此次东京大会,日本政府招待之周,宣传之力,可谓至矣尽矣,蔑以加矣。而所得印象亦极为良好,美国澳洲各国代表莫不交口称誉,我国到会代表亦众口一词,以日本科学上之设备布置足为中国之借鉴。美国某代表告著者,谓东京会议得益以日本为独多良有以也”[2]。任鸿隽也曾说,“我们但凡到日本的人,看见日本人招待的殷勤,注意的周到,以及客人啧啧称赞,感谢不尽的神气,无不说日本人的联络感情,是大大成功的。拿我们中国到会的人来说,我们对于上面所举的两种情形,当然也有一致的感觉”[11]。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会议是日本在克服极大困难的背景下如期举办的。在澳洲会议闭幕前两天,即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发生大地震与大火灾。在此之前,日本代表已邀请下届大会于1926年在东京举行。虽然日本代表知道震灾严重,但以顾信义,重然诺,不愿取消前议。而东京会议办得如此成功,尤为各国代表所称道,也是令各国代表印象深刻的一件事。“东京丁此烬余,全城几夷为平地,三年之间竟尔楼阁连云,车水马龙,举凡近代大都市所有之各种建筑及便利交通之具罔不咸备。与会者均可享有之。此则各国到会之代表无不交口赞美者也。日人办事之敏捷,与其毅力热心,有可惊已。”[2]
同时,日本在科学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引人瞩目。与会中国学者竺可桢、薛德焴、胡先骕曾分别撰文《日本气象学发达之概况》《日本动物学进步之经历》《参观日本植物森林研究机关小纪》等,向国内学者介绍日本在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竺可桢曾感慨,“返观吾国,则科学界情形,尚在日本维新初年时期。西洋文化之被于东亚各国,虽在同时,而日本科学之发达,乃早我三四十年,虽多半由于政府之乏提倡,然学术界自身亦不得辞其咎”[12]。亦有新西兰代表在会后曾撰文介绍日本科学发展盛况[13]。
任鸿隽认为,“日本人的科学程度究竟如何,我们不敢妄下断语,但他们地方的科学,已经发展到了充分的程度,那是我们所赞赏不置的”[11]。而竺可桢则从中看到了中国科学家努力的方向。“日本为东洋科学先进之国,然其筹备上届大会,尚费全国数百学者之心力,经二年余之时间,始克臻此盛况。则我国若不欲相形见绌,可不警惕自励,即日倾全力以从事于搜集调查讨论研究哉?况太平洋科学会议,本以地方科学为限,而我国之地质矿产动物植物气候人种,为国家开发利源计,为人民增进幸福计,即无大会,亦有调查研究之必要也。”[2]
东京会议的巨大成功及日本科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深深地刺激到了中国学者,毕竟中日作为亚洲近邻,“日本学术研究发起殆与中国同时,而进步早于我国相去殆数十年,各学术中心亦皆能基础巩固,进行不断,始终无间,然自近年以来始有召集国际会议之举,一九二六年举行太平洋学术会议,本年又召集世界工业会议,其筹备之周至谨慎不遗余力,一经提出邀请,虽遭意外大变如东京地震等亦不变计划,维持信用,故各国专门人士亦共相钦佩,为其国增加名誉不浅”[4]。既然日本已经成功举办了太平洋会议,作为太平洋沿岸大国之一的中国,自然不能落在后面。
(三)申办机制
早期会议并非轮流举办,甚至也没有形成定制。在首次檀香山会议后,因无人敢邀请下次会议,与会学者们对于该会是否能继续办下去都不得而知。而自澳洲邀请并成功举办第二次会议,并形成每三年一届的惯例后,每次会议上都在邀请举办下届会议的国家中作出选择。如在澳洲会议上,仅有日本发出邀请,因此决定1926年在东京举办第三次会议。而在东京会议闭幕前,邀请下届会议的有爪哇与加拿大,最终决定由爪哇主办[2]。第四次会议上,对于第五次会议之地点,计有加拿大及越南二国提出邀请,以加拿大提出在先,故决定第五次会议往加拿大举行,第六次或可往越南。议定加拿大筹备期间为3年,越南或可为4年[4]。
当时太平洋科学会议理事会实际上有英、法、美、日、荷、苏联及我国7国而已,其余均属属地。考虑到前4次会议的主办国及加拿大、越南已提出邀请,只有苏联和我国尚未举办。苏联虽名义上在委员会内,实际上因为尚未恢复外交关系,其他会员国也不愿其参加,而苏联亦自甘放弃,第四次会议竟未派代表,故所余者唯我国。按惯例,我国也必须做好主办会议的准备[14]。
在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业已成立,中国科学家对举办太平洋科学会议怀有极大热情,而第六次举办国已基本确定的背景下,第七次会议是中国举办的最好时机。
三、设想的落空及其原因
由于种种原因,太平洋科学会议从第五届开始已无法按照三年一届的周期举办。原本应于1932年在加拿大召开的第五次会议,最终推迟了一年开会。而本应在越南召开的第六次会议迟至1939年才在美国举办,距离上届会议已有6年之久。从此,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太平洋科学会议中断长达10年,直到1949年复会,在新西兰召开第七次会议。会议举办时间的混乱是一方面原因,而随着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国民政府迁都至重庆,各学术团体、研究机构相继内迁,在战争的环境下,中国无力举办太平洋科学会议。
中国科学家关于举办太平洋科学会议设想的落空,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既有当时中国自身的原因,也受到了国际局势的影响。
有学者当时就对面临的困难作出了分析:“时局不定,各学术机关基础不固,政府及社会上对于已有成绩之学术机关是否有始终维持之决心,尚无明确保证。虽新立团体间见风起于一时,而旧有基础或被弃置于不顾。覆辙可循,前车为戒,在如此不安定状态中,殊恐无人敢为十年以后之担保。即各国人士对于中国学术一时之成绩是否能继续勿坠,亦往往不无疑虑,见之言辞。”[4]
但这些仅仅是表面的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当时中国科学事业尚处起步阶段,无论政府还是社会,对发展科学的重视和投入都远远不够。1919年协约国代表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成立了国际学术会议(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下设8个科学联合会,如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国际测地和地文物理联合会、国际纯粹和实用化学联合会、国际数学联合会、国际科学的放射电报联合会、国际纯粹和实用物理联合会、国际生物学联合会、国际地理学联合会等。当时除德奥同盟诸国外,有24个国家加入了该组织。而中华民国与阿根廷、智利、摩纳哥虽符合条件,却并未加入。事实上,该会议成立之初,曾请我国加入,将请帖送往驻伦敦中国公使处,但中国没有加入。而其下属的各学术联合会,“每当开会时,均有信寄我国教育部,请中国派人加入开会,以襄盛举,但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数年以来,不特无代表派出,而且向例不覆只字。”有学者就曾针对当时的这一状况一阵见血地指出,“我国当此科学程度幼稚,国际学术地位衰微时,对内故要发奋,实行向发展科学途上做工夫,对外亦应同时有所表示,方不至常落人后。”[8]而政府对科学事业的态度从中国参加历次太平洋科学会议的实际情况中也可见一斑。
“无如我国政府社会,对于各种国际集会向来漠然视之。泛太平洋学术会议第一次开会时,仅驻檀香山之领事与会。第二次在澳洲大会,则阒焉无人。第三次会议则在民国十四年春间,日本政府即以正式通知我国教育部,邀请与会。而我国教育部当局竟束之高阁,视等虚文。至十五年秋间,由少数学会之发动与督促,始有派代表赴会之举,但离开会之期已不及两阅月。故此次中国代表所提出之论文,以数目而论,仅仅七篇,与日本方面所提出一百八十余篇,固不可同日而语,即较之美国澳洲菲律宾以人数为比例,亦有逊色也。至于赴会经费,则完全由各学会与文化基金委员会担任,国务会议虽通过一万元之经费,但口惠而实不至也。”[2]经费问题导致几乎每次会议都有部分中国学者无法按原计划参会。
1924年7月2日,在中国科学社理事会书记报告中,竺可桢提到太平洋科学联合会邀请中国科学社出席同年7月31日至8月13日在檀香山举办的泛太平洋食物会议,并愿意担负一半的旅费。但中国科学社因为经费紧张,并未指派代表列席,仅由任鸿隽发函通知国内各学术团体及实业团体,而秉志和竺可桢向大会邮寄了论文[1]。
1925年4月14日,竺可桢在致丁文江关于中国科学社年会及经费函中说,“弟已两度往见省长,均口惠而实不至,社中职员势难枵腹从公。……生物研究所论文印刷业已积极进行。惟经费一层宁沪两方均已垫付巨款,难乎为继,望吾兄在津京各方设法”[1]。
1925年8月24日,竺可桢在中国科学社第十次年会书记报告中,对于上一年因经费无从筹措,未能参加泛太平洋食物会议,认为这是“坐失国际联络之时机”。若要避免前车之鉴,欲在国际科学团体中占有地位,必须未雨绸缪。进而以泛太平洋科学会议为例,“历届开会,日、美、澳固无论矣,暹罗尚派代表,独我国阒焉无闻,立国于太平洋之滨,而自外若此,殊足为中国科学社之羞”[1]。
1926年第三次会议前,中国政府已排定秦汾为代表,并经阁议通过,支给参加旅费一万元。驻京日使馆以会期迫近,欢迎中国各学校各学术团体届时多派代表与会,以共切磋。特派西田参赞到外部口头声述,并称希中国方面若能以文范村、翁文灏等为代表,尤为欢迎。如经费不足,愿赠送旅费二千五百元。教育部函复外部称参加第三次太平洋会议经费,早已筹有的欸。对于日方补助旅费则予以谢却。当时计划参会的代表包括秦汾、翁文灏等14人[15]。当时政府虽拨款一万元作为会议代表旅费,但实际上并未兑现。最终由各学会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担负,一些学者因此未能成行。
在1931年10月30日竺可桢致蔡元培的函中,对于黎国昌拟参加第五次太平洋科学会议作出回复。“此次代表原定十人,而要请提出论文者已逾此数,黎君意固甚善,终以额满无能为力,且远赴北美,旅费浩大,殆将倍蓰于南洋,届时政府果能否按数发给亦未可知也。”倍蓰于南洋,说的是此次赴加拿大参会旅费将数倍于上届爪哇会议。从这段话中可以想见,当时参会人员在获得旅费方面是何等艰难[1]。
1932年5月6日,胡先骕致函中央研究院,答复关于参加第五次太平洋科学会议各代表机关垫付旅费,云“因敝所无法筹垫,只有暂不出席,好在尚有其他代表出席,人数不妨略减”[16]。
事实上,因为经费而无法出席五次太平洋科学会议的不止胡先骕一人,当时中国有10位学者均获得了参会资格,但最终仅有竺可桢、李顺卿、凌道扬、沈宗瀚4位成行,而钱崇澍、胡先骕、李济、秉志、蒋丙然、翁文灏6人因经费问题遗憾未能出席会议[17]。
1933年3月2日,竺可桢致函凌道扬,告知加拿大五次太平洋会议出席代表暂定10人,旅费已由国府命令财政拨给。惟财部是否照拨,尚是问题[1]。1933年4月21日,在致蔡元培函中,竺可桢特别提到“出席旅费美金一万元虽经国府通过,命财政部照拨,迄今尚未下发。因会期迫促,可否通融办理,请各代表服务机关垫发,俟日后国库发款再行拨还”[1]。
1933年4月28日,竺可桢在致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函中,建议对于金陵大学教授沈宗瀚、青岛市观象台台长蒋丙然参加第五次太平洋科学会议的手续问题,拟请用中央研究院名义,“分别用公函通知金陵大学,请准沈代表请假出国;用电报通知青岛市政府,说明服务机关代垫旅费原委,请予即日拨款交蒋代表具领,以便早日成行,实感公谊”[1]。像这样由代表服务机关垫付旅费的情况,在当时屡见不鲜,这也是造成很多学者无法依照计划参加太平洋科学会议的直接原因。
从以上当时中国学者在参加太平洋科学会议时面临的经费困难问题,不难想见当时中国科学发展的境况是何等艰难。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经费缺乏和国内外时局动荡是制约民国时期科学发展和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因素”[18]。
四、错失良机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
表面上看,未能主办一次综合性国际学术会议,不外乎错失了向各国展示中国当时国家建设尤其是科学发展水平的良机。但如果仔细分析会议的主旨及长期从事的工作,就不难发现未能成功举办会议给中国科学发展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
首先,在当时急需振奋精神、奋发图强的时刻,如能由国家给予支持,由中央研究院来实际负责具体事宜,联络各界,成功举办一次太平洋科学会议,对于凝聚人心、提振科学界信心都大有裨益。中国科学家对这一点,已从当时参加日本举办的1926年会议的亲身经历中获得深刻体会。错过这样一次可能对中国科学界产生空前激励作用的大好机会,无疑令人惋惜。这是精神层面的影响。
再者,主办会议,必然要在国家建设、科学研究、资源调查和保护等方面提早进行准备,诸如地质、地理、生物、森林资源调查等地方性科学比其他科学更易在短时间内取得成绩,以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非常适合优先进行这些工作。如果当时中国成功获得举办权,将使方方面面的调查得以大为提前并集中开展,这是其他的举措无法代替的效应。以森林资源的调查和保护为例,这是会议的宗旨之一,而中国幅员辽阔、森林资源丰富多样,在林业研究方面具有一定优势。著名林学家凌道扬(1888—1993)曾被推为太平洋科学协会林业组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太平洋沿岸各国林业调查与研究。关于中国林业调查,也曾有一份计划,但最终并未完成[19]。试想,如果在20世纪30年代初甚至更早中国已获举办权,至少对太平洋科学会议给予足够的关注度和参与度,那么或许以此为契机,对于东北地区的森林资源调查能够及早开展,上述关于中国林业调查的计划也能继续开展下去,并进而为林学研究和国家经济建设服务。后来在日本占领东三省,而中国又错失了20世纪30年代的机会,尤其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对东部地区森林资源的调查已无从谈起。这是就科学发展具体层面上而言。
五、结 语
太平洋科学会议是民国时期在太平洋地区乃至全世界范围内都有重要影响力的综合性学术会议,当时世界上主要的国家均相当重视。它的兴起反映了当时科学发展的重心正向太平洋地区转移的趋势。但是作为太平洋地区的大国之一,中华民国迟至1926年第三次东京会议才正式派出学者参加,并因未成立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而几乎丧失会员资格。在亲见日本会议的巨大成功及其科学发展取得的成就后,中国学者及时地提出了将来由中国主办一次会议的设想,并随着形势的发展对设想的具体内容不断作出调整。但由于当时中国科学事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基础薄弱,社会和政府的投入都远远不够,学者赴海外参会尚且难以保证。举办综合性学术会议这样的大事在缺少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下,更是难以付诸实践。尤其是在错过了1933年第五次会议上提出邀请的大好时机后,太平洋科学会议自身已无法如期举办。此后随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以及太平洋地区局势的不断升级,该会议长期陷入停办。这也反映了科学发展必然要受到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虽然中国学者已经对举办会议的困难有清醒的认识,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由中国主办太平洋科学会议的设想竟然在半个多世纪后才得以实现。1995年,第18届太平洋科学会议是中国首次举办该会议,而台湾地区将在2016年举办第23届会议,其中走过的漫长历程不禁令人感慨。
[1]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22卷[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1:108,128,142,353,358,362,365,367,375,375,379,387,389,390,396,398,458,530,534,541,559,562,576.
[2] 竺可桢.泛太平洋学术会议之过去与将来[J].科学,1927(4):465-480.
[3]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294-295.
[4] 翁文灏.第四次太平洋科学会议纪略[J].科学,1930(4): 615-639.
[5] 李玉海.1890—1974年竺可桢年谱简编[M].北京:气象出版社,2010:5-22.
[6]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4卷[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1:89.
[7] 翁文灏.太平洋科学会议之历史[J].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1929(1):138-147.
[8] 张云.国际学术研究会议和中国科学的发展[J].科学,1926(9):1341-1402.
[9] 杂俎.第三次泛太平洋学术会议纪略[J].科学,1926(9): 1455-1457.
[10] 魏喦寿.第三届泛太平洋学术会议[J].科学,1927(4):544-549.
[11] 任鸿隽.泛太平洋学术会议的回顾[J].科学,1927(4): 455-464.
[12] 竺可桢.日本气象学发达之概况[J].科学,1926(9):481-495.
[13] COLERIDGE F C.Science in Japan[J].Nature,1927(2993): 407-410.
[14] 竺可桢.第四次太平洋科学会议概况[J].科学,1930(5): 640-645.
[15] 杂讯.泛太平洋会议中国代表之决定[J].教育杂志,1926(11):5.
[16] 胡宗刚.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174.
[17]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1)[C].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34:111-112.
[18] 周雷鸣.凌道扬与太平洋科学会议[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3):28-33.
[19] 沈岚,周雷鸣,朱林林.凌道扬参加第五次太平洋科学会议及其主持太平洋沿岸国家森林资源调查史料[J].民国档案,2014(2):15-26.
(责任编辑 何晓琦)
The Plan of Hosting the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 Once in China Never Put into Practice
LIU Liang
(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Natural Science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100190,P.R.China)
The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 was a comprehensiv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gress,which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cience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Pacific area and even around the world.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congresswas held seven times,however,the Republic of China didn't hold once,even as one of the members of the Pacific Science Association and one of the powers in the Pacific area.In fact,at that time,the Chinese scholarswith Zhu Kezhen as a representative,had the plan that China held the congress once,and continuously made corresponding adjustments to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the plan while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changed. However,due to the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was still in its initial stage,and the limited investment from government;moreover,in 1937,Japan launched an all-outwar of invasion to China,and the situations in the Pacific area continuously were escalating,thus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 itself stalled,and finally all these resulted in the plan of the congress held in China once vanished.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Zhu Kezhen;Science Society of China;Academia Sinica
K332
A
1671-6116(2016)-03-0078-07
10.13931/j.cnki.bjfuss.2016026
2016-01-20
中国科学院科技史青年人才研教项目“近代来华西方人对中国环境变化的关注及影响”(Y522021013)。
刘亮,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水土保持学史、中西交流史。电话:010-57552578 Email:liuliang@ihns.ac.cn 地址:100190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55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