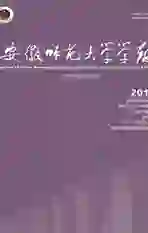略论新文化运动的法兰西风格
2016-12-14高毅
高毅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启蒙运动;法兰西风格
摘要: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性和法国启蒙运动的激进性密切相关。中国启蒙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法国迷”,这是当时中国盛行的一种“法国崇拜”的结果,而这种“法国崇拜”其实就是对法国大革命产生的那种激进革命文化的崇拜。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性源自法国启蒙的激进性,其根本缘由是法兰西民族对“平等”价值的强烈偏好。中法两个民族都勇敢地选择了激进革命来摧毁不平等的制度,都愿意坦然面对由此产生的一切负面效应。法国革命后的政治文化革新工程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法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6)03-0265-04
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家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这是一场面向现代的中国启蒙运动,其特点是特别激进,主要表现为它有鼓吹全盘西化的倾向。听起来难听,但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鲁迅要青年人“少读或不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李大钊主张要实现中国的“再生”,必须“取由来之历史,一举而摧焚之,取从前之文明,一举而沦葬之”;陈独秀也说:“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类似言论不胜枚举。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新文化运动大师们之所以有这些言论,并非出于一时的愤激,而是由于他们痛感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前现代的、封建专制糟粕的根深蒂固,是救国大业的严重障碍,必须下猛药才能根除之。也就是说他们认定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采取这种激进的方式,不过正不足以矫枉。但这种激进主义策略究竟该不该,好不好?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之前,有关的评价是一边倒的肯定,都说好得很。只是改革开放后,在80年代,才出现了一些否定的意见,不少人猛烈诟病之,说这是20世纪中国激进主义极左思潮泛滥的根源。这种意见主要来自思想解放后出现的“右翼”思想阵营,一般称之为自由主义思潮。然而我们也看到,即使是自由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不同意见的,比如中山大学著名的袁伟时先生就很反对这种说法,说那这种说法不恰当地否定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现代性、正义性。袁先生尖锐地嘲讽说,那种认为提倡反传统就是灾难的观点,实际上是在主张“中国人应该永远匍匐在圣人和尊长的脚下:同时设置思想警察,拘禁一切超越标杆的‘过激思想。”
很有意思的是,袁先生还专门批评了那种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法国启蒙的孽子”的说法,顺便还批评了一下哈耶克关于“启蒙”有英法两个传统、只有法国启蒙才是激进主义根源的看法,说这种看法忽视了两国思想相互交融的一面:“法国和英国两个传统是互相交叉的,法国有过很多很极端的东西,英国则有掘地派、平等派,那些主张同样是空想的”,而且由于英国早在16世纪就有过托马斯·莫尔本质上是主张恐怖统治的乌托邦思想,英国革命事实上比法国革命更加血腥恐怖——因为英国革命中死了20万,而法国革命雅各宾专政只处死了4万人。
袁先生认为英法两国的启蒙思想都有激进与温和这两个面相的看法,无疑是合乎历史实际的。但说到英国革命比法国革命还血腥恐怖,恐怕就没有多少人能苟同了。毕竟法国革命中的那种“恐怖统治”,在英国革命中从未实际出现过。而且如果说英国革命中死了20万人,那一定与内战的战争伤亡有关,而如果一定要算上战争伤亡,法国革命导致的死亡人数肯定得以百万计(仅滑铁卢一役就死了5万人)。所以,关于革命恐怖的账,是不能那样算的。
不仅如此,由于另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英国或苏格兰启蒙是“革命后的启蒙”,其任务是建设,而法国启蒙是“革命前的启蒙”,其第一要务是破坏,即摧毁旧制度——所以,尽管都有激进与温和这两个面相,两相比较起来法国启蒙还是不免要显得激进一些甚至激进得多,而且法国大革命那种特殊的激进性,其实也是与激进的法国启蒙正相关的:关于这一点,学界从埃德蒙·伯克起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异议。
我们当然也不能同意“中国新文化运动是法国启蒙的孽子”这一说法,因为这种说法是以否定法国启蒙乃至法国大革命甚至一切激进革命运动的历史正当性为前提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历史修正主义思潮曾一度在世界范围内甚嚣尘上,只是令人欣慰的是,它终究得不到任何注重实际的严肃历史学者和明白事理的人们的认同,毕竟这里涉及的实际上是应不应该“反抗压迫”这样一个基本人权问题。
可是在阐明了这一点之后,有几个重要问题就立即需要我们来好好考虑一下了。
首先,中国新文化运动虽然不能被看做法国启蒙的“孽子”,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性和法国启蒙的激进性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我个人认为,这种关系还是有的——不仅有,而且还特别紧密。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知识界的一种带启蒙性质的普遍思潮,公认是从陈独秀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第二期起更名为《新青年》)开始的,陈独秀也因此充当了这场中国启蒙运动的旗手。而当时的陈独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法国迷”。不信?大家看看他办的这个杂志的封面,自始至终,都在极醒目的位置上赫然印着一行法文的杂志名:LA JEUNESSE。为什么不用英文,也不用俄文(要知道1905年推翻了帝制的俄国,本来应该自然成为陈独秀这位早期中国革命者的榜样)?当然是因为法国文明在陈独秀心目中地位特别崇高的缘故。在杂志的创刊号上,陈就写了一篇文章“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极力讴歌法国文明的伟大,说当代三大文明——人权说、进化论、和社会主义——皆是法国人的贡献,称“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新文化运动期间发生的那场规模浩大影响深远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自然也可作为法国启蒙对新文化运动这场中国启蒙有特殊影响的明证。特别是,后来人们还发现,18世纪的法国启蒙实际上还深深地受到过西传的中华文化的影响,自由平等博爱三大理念的奠立都与中华文化的影响有密切的关联(以至于阎宗临、朱谦之等人甚至断言没有中华文化的西传就没有法国启蒙因而也没有法国大革命——话说得过头了些,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而且法国启蒙(也是整个欧洲启蒙)的旗手伏尔泰本人,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中国迷”。所以,发动中国启蒙的“法国迷”陈独秀,实际上是在不自觉地投桃报李。
第二,陈独秀能成为“法国迷”,也不是偶然的,是当时中国盛行的一种“法国崇拜”的结果。而这种崇拜,实际上是一种“革命崇拜”,更确切地说是对法国出产的那种特别激进的革命文化的崇拜。这崇拜的始作俑者,是戊戌变法时期的谭嗣同,因为他最早对法国大革命发出这样的赞美:“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日‘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夫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唱民主之义,未为奇也。”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中国革命者在1901年开办《国民报》为中国革命造舆论,其第一、第二期就连续发文宣传法国大革命,并公开鼓吹在中国实施法国式革命,中国舆论界由此刮起“法国风”。后来一有批评法国革命的言论出笼,就会立即招来潮水般的围攻。湖南省因其“法国风”刮得最盛且最早发生反清暴动而获得“小法兰西”雅号,湖南人为之骄傲,陈家鼎(同盟会著名湖南籍会员及孙中山心腹之一)更是豪迈地提出,仅湖南成为中国的法兰西还不够,还应将中国变成“亚洲之法兰西”才可。看来,湖南这地方,后来能走出黄兴、宋教仁、毛泽东、刘少奇等等许多大革命家,绝非偶然,那显然也是跟20世纪早期湖南盛行的这种特殊强劲的法国崇拜有关的。
第三,法国启蒙之所以激进,是因为其崇尚平等的左翼势力特别强大,其代表人物有魁奈、马布利,但主要是卢梭。卢梭出身贫寒,但文采过人,而且由于近民众、接地气,他那支笔了不得,连以善辩著称的达朗贝尔都不敢跟他打笔仗。卢梭在启蒙时代备受伏尔泰等主流文人压抑,但随着大革命临近却迅速升温走红,终于成为法国大革命中人人崇拜的精神导师。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性很大程度上就是他的思想影响的结果。卢梭思想中有很强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因素。当今欧洲盛行的社会主义,也与他的影响息息相关。而中国20世纪初期兴起的革命崇拜,乃至新文化运动对法国文化的崇拜,主要也是对卢梭的崇拜。邹容《革命军》疾呼,“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旖,以招展于我神州土”。陈天华的《狮子吼》指出,法国能通过暴力革命而成为民主国,全是拜卢梭《民约论》一书所赐。当今法国大汉学家巴斯蒂发现,当时中国知识界读得最多的西哲是卢梭。报刊上的政论作者多以“卢骚之徒”“卢梭魂”“亚卢(亚洲卢梭)”“平等阁主人”“竞平”“民友”“人权”等等为笔名。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号也以卢梭肖像为扉页。在此基础上兴起的崇尚法国革命文化的新文化运动,自然也被打上了深刻的卢梭崇拜的烙印。
由此看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确实是法国启蒙的产儿,而这也就在相当程度上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激进基调。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便是: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新文化运动和中国革命的这种激进性?
我们承认新文化运动是法国启蒙的产儿,但不认为这个产儿是一个“孽子”。因为,首先,我们认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整个中国革命,跟法国启蒙和法国大革命一样,作为一种争取个人自由和民族解放的“反抗压迫”的斗争,具有不容置疑的正义性;其次,这些运动和革命之所以都特别激进,最后都闹出了血腥恐怖、血流成河的后果,那是由两国相似的一些历史社会条件造成的,具体说来是因为两国的历史都特别悠久,积累的问题都特别多,传统的包袱都特别重,反动保守势力都特别大等等的缘故。总之,既然中法两个民族都有不甘受压迫奴役的血性,因而蒙受血雨腥风的革命,就的确是他们“在劫难逃”命运。那么,我们能因此而断言这种激进的启蒙和革命都不该搞、都没有正当性吗?应该说很多人都会认为,当然不能。因为怕流血牺牲而放弃思想解放、放弃革命、放弃反抗压迫的权利,那是懦弱,是猥琐,是奴性,是丢人。所以,在这个问题面前,具有强烈的文化自尊的中法两个民族给出了一致的回答,那就是勇敢地选择激进革命,并坦然面对由此产生的一切负面效应。
只是与此同时,为了避免盲动冒险和赢取革命的最后胜利,对于这种激进革命的种种负面效应,我们即使不能做出事先的预测,也应及时做出事后的反思,不断总结经验,以利再战。诚如许多人所看到的,激进革命的直接后果,往往会导致某种专制政治。这种专制政治在某个特殊时期也许是必不可少的,但它终究会给争取政治民主这一时代任务的完成构筑一些新的障碍。应该承认,这的确是一切激进革命都难以避免的后遗症。而且,法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事情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在激进革命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过于崇尚平等的政治文化。法国大革命作为一种史无前例的激进革命,它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实施大规模的民众动员,而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所带来的,必然是民粹主义的萌生,是平等主义的泛滥,是自由主义的被打入冷宫。但吊诡的是,这种崇尚平等的政治文化远没有给法国人民带来解放和幸福,反而给他们带来了拿破仑的军事独裁,让他们成了一个共同的主子之下普遍平等的奴隶。这当然不是大革命的预想目标。于是,为了完成大革命的民主主义初衷,法国革命者们只好再一次从文化上来下功夫,即对那种崇尚平等而贬抑自由的政治文化实施改造:一方面适当削减其大众平等的偏好,一方面适当申扬法国启蒙中的精英自由取向——说白了,就是要在自由与平等这两大价值之间玩平衡。这件事在革命后的法国,做起来很难,因为这需要说服法国人放下架子去学习英国人的政治文化——那是一种颇善于在自由平等之间玩平衡的政治文化,两党制、内阁制和两院制议会等政治机制就是这种政治文化的创造物,其最大的优点就在于能较好地保障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在自由平等作为一般原则或发展方向已基本确定的前提下,终究是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的。法国大革命开始时,革命者们对英国人的那一套是看不惯也看不起的,说那太保守,也不合法国国情。但在经历了激进革命负面效应的种种磨难之后,我们看到,从18世纪末的西哀耶斯、贡斯当、斯塔尔夫人,到19世纪的基佐、托克维尔,再到20世纪的雷蒙·阿隆、孚雷等等,法国代代都有人在努力放弃这一思维定势。他们感悟到了英国那一套政治制度的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并随之产生了学习和借鉴的兴趣。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法国人并没有就此放弃文化自尊,这个从来就不乏创造性的民族绝不会盲目照搬别人的经验,他们对盎格鲁一撒克逊政治文化的借鉴自然也是批判性的,说到底他们只是要吸收其中的一些合理要素,以期改良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大革命之后的100来年,法国人其实就是在这种政治文化的革新试验中度过的,现在的第五共和体制——一种典型的法国式民主,便是这种试验的一个比较成功的阶段性结果。
法国的这一历史经验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我以为,既然中国新文化运动是法国启蒙的产儿,而中国革命也是学着法国革命来的,那么法国革命后的政治文化革新工程自然也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不必跟在法国人后面亦步亦趋,但法国人在政治革新、民主试验方面的历史首创精神,终究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不必事事处处照搬法国的历史经验,但由于中法文化关系的特殊性,法国的经验往往对于我们有很重要的直接参考价值。总之,我们100年前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尽管历史功勋卓著,如今终究已经过时。现在我们需要的可能是一场“新新文化运动”,即继续本着法兰西的精神和经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进行全面梳理,超越左右翼之间的尖锐对抗,努力建立平等主义和自由主义各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唯其如此,中国革命才有望取得真正的成功。
责任编辑:汪效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