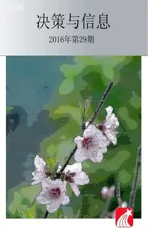市场场域中的族群与族群性
——以中国少数民族的市场参与为例
2016-11-26陈祥
陈 祥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研究所 江苏南京 210023
市场场域中的族群与族群性
——以中国少数民族的市场参与为例
陈 祥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研究所 江苏南京 210023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水平非常高且还在不断发展的今天,过去囿居于山地农村等相对隔绝地带的中国少数民族也不可避免地被席卷入了市场当中。不管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还是在经济发达的汉族聚居区,少数民族都采取了各种方式参与到了市场经济的过程当中,这在极大程度上为他们自身的族群认同构造出了依托,当然这也加强了他们的族群认同。如果说民族识别作为一个进行族别划分的国家手段并没有划分出带有严格意义上“族群”属性的群体的话,这些群体参与市场经济的这个动态过程,却为他们在其所冠有的少数民族名号之下发展、创造或复兴出了“族群性”,少数民族名号之下的“族群”正在形成。
少数民族;市场参与;族群;族群性;族群认同
一、族群、族群性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
族群(ethnic)源于希腊文ethnos的形容词形式ethnikos,据说ethnic是在 14世纪中期才成为英语的(潘蛟,2003:55)。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的所指是“非基督教的”,“ 非犹太教的”,或“异教的”(heathen,paganor Gentile)。19世纪,随着科学主义兴起,宗教式微,“异教徒”一词在西方用语中被“ 种族”(race)一词替代,ethnic几乎成了与“种族”同义的赘词,被一度闲置(Connor,1984:379-388,转引自潘蛟,2003)。当然,现在使用的族群概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与种族概念分离了出来,后者被用于人的体质差异对比中去,而前者则注重的是人们直接的社会文化差异(Banton,1987)。
最早的族群理论是“文化共同说”,根据巴特的概括,这一理论把一个族群看成是一种社会文化承载和区分的单位。但巴特发展出的“族界理论”却否定了这一说法,他认为族群是一种社会组织,是一种人们自己或别人根据他们的出生和背景来推定的归属范畴,是人们在交往互动中生成和维系的一个排斥和包容性的社会组织。在这一理论假定之下,族群认同就生成于具有不同内在文化价值取向的人群之间的社会互动中,其作用在于组织这些互动并使它们结构化。此外,族群理论当中最有名的两个理论范式是“原生论”与“工具论”(或称“场景论”)。原生论的提出是旨在解释为何族群意识难以消解,于是它倾向于认为族群认同是亲属认同的一种延伸或隐喻,它是人性中某种非理性原生情感的外化,或某种植根于自私基因中的生物学理性的表现。由于原生论过于强调族群的原生维度而忽略了族群认同的灵活性与工具性,于是强调族群认同的另一个特质——族群的情境性与工具性——的工具论(或称“场景论”)应运而生。工具论有助于解释族群意识的兴衰,由于族群意识具有场景性和工具性,故其兴衰是由具体的政治、经济场景交换来决定的。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对族群的界定既要注意它在社会层面的工具性与场景性,也不能忽略其构建的文化原则,正如Charles Keyes所说,任何一种完整的族群理论不仅要考虑族籍在追逐社会利益方面的功能,还应考虑那些构建族群的文化原则(Keyes,1976:205)。本文便是在这种调和的理论背景之下,试图通过中国少数民族群体在市场场域中对族籍的利用及其与其他群体的参与和互动,来探讨民族识别后中国少数民族在其“名号”之下的群体是如何产生族群性并“再造”(remake)族群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文所采纳的“族群”概念所指的就是人们在交往互动和参照对比过程中自认为或被认为具有共同的起源或世
系,从而具有某些共同文化特征的人群范畴(庄孔韶,2003:79)。这种说法强调人的主观认同与建构,而由此说来,中国由国家自上而下所划分出来的少数民族大多最初并不具有“族群”的这一特质。一个少数民族当中可能是一个“族群”,但更多的可能是包含了好几个互斥的“族群”,比如纳西族中还包括了摩梭人等,但是它们在国家层面的语境中打着同样的“旗号”。那么,按照这一理论,这些“旗号”下的少数民族群体何以成为一个族群呢?这就需要人们在交往互动和参照对比过程中构建出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将他们联系起来,这就涉及到了族群性的问题。
族群性(ethnicity)这一概念与“族群”相生相依又有所不同。如果说族群是在实体层面上指向特定的一群人的话,那么族群性则指的是特定人群在与“他者”相遇之后对自己所属人群的一种归属与认同意识。某个特定族群可以独立生活而不产生族群性的问题,但一旦他们开始接触“他者”,他们便需要表达“他我之别”,这时族群性便出现了。究其根本,族群性其实也就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问题(范可,2015:53)。中国少数民族的族群性表达与认同也基本遵循这一进路。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中国市场化改革在户籍制度松动之后发起了一场大型的移民运动,这场移民运动将1953年民族识别(ethnic identification project)后相对独立生活的少数民族个体迁移到了汉族聚居的沿海城市和大都市中去。当然,这只是一方面,汉族群体也相应随着政策与资源攫取的需要迁移到了少数民族聚居区。
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充分接触,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场合的较量,使得少数民族的族群性问题凸显了出来。于是,接下来,笔者将对少数民族族群性问题凸显的背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及其历史进程进行简要概述。
毫无疑问,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甚至在2010年首次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成就无疑都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及其与之相伴随的市场化改革。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所走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济发展道路,这一时期由政府政策指导的中央分配制度决定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在1949年建国到1978年这段时期内,经济活动似乎成了政治活动的附属,公平成为计划经济的首要目标,地区、城乡与工农之间的经济差异并没有过于显著的区别,少数民族都各自在所划定的区域范围内从事农牧业或者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并且,当时的户籍制度把人口牢牢地栓在了特定区域生活与活动。但是到了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尝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便逐渐地从政治中剥离了出来,效率成为经济所关注的重要方面。于是,从那时起,中国的市场像是获得重生一样迅速发展起来,政府政策对经济的推动更使得市场经济发展得更加蓬勃。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的开放、基础设施建设、税收补贴以及外资和私人股份的扩大,使得工农差异、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异、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越来越凸显(JIAPING WU,2014:971)。最初人们还普遍相信“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口号,但是随着市场的逐步开放与发展,这似乎变得难以控制了,走出谎言的贫困农民和少数民族人们开始不满于这种贫富差距与不平衡而开始主动地参与到了市场及其竞争当中。再加上户籍制度的松动,少数民族和汉族人们开始互相流动,并在市场当中频繁接触与竞争。这就是本文论述话题的制度背景。
二、中国少数民族的市场参与与族群再造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水平非常高且还在不断发展的今天,过去囿居于山地农村等相对隔绝地带的中国少数民族也不可避免地被席卷入了市场。正是在这个无孔不入的市场当中,最初划定时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族群”的一个个少数民族群体在其“民族籍别”的称号下开始逐渐形成了族群性和族群认同,于是他们参与市场的过程也就相应地成为了他们再造族群的过程。
埃里克森(Thomas Hylland)曾以格陵兰的因纽特人过去四五十年里的族群形成过程为例概括出了族群形成的阶段,他还认为由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新兴的文化自我意识刺激了强调文化特殊性的族群身份的形成。简要来讲,埃里克森的族群形成理论主要有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几乎涉及了三代人,例如以某个因纽特人来说:他的祖父母可能对于他们所具有的文化毫无知觉,并就此活着;而他的父母则沉浸在族群同化和现代化对他们文化的污名和耻辱所造成的苦痛中,他们拼命想逃离这种文化;但是到了他这一代,他则奋力去做任何能够复兴他们习俗和传统的事情来保住他们的文化,这种文化如前所讲,在他祖父母那毫无知觉而在他父母那拼命想摆脱(Eriksen,1993:129)。
毫无疑问,埃里克森从个人心理的层面展示了族群形成的过程,他的阐述很具有启发性,而且显然,他也认为复兴习俗和传统对于族群形成来说非常关键。但是,在什么境况之下作为少数群体的他们会复兴习俗和传统呢?他们又是在什么场域中通过什么手段来复兴习俗和传统呢?这些问题埃里克森并没有详细深入地再作探索,而这些恰恰又成了本文论述的关键。
个体的族群认同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原生论),当这些文化基础因素被应用到特定场景中去的时候(工具论),这些应用反过来又能够加强群体的认同。放到中国少数民族的语境中去就是,民族识别后把一个特定的称谓如“彝族”划分到特定的一群人身上的时候,他们其实更多地是无意识的(第一阶段);当他们初初参与市场时,市场中占控制甚至垄断地位的汉族人对他们排斥的时候,他们想要拼命甩去这一特定名称所带来的“包袱”(第二阶段);但当他们在市场中发现某些特殊的习俗、传统或礼仪具有经济价值的时候,他们便会利用这些习俗、传统或礼仪作为救命稻草参与到市场当中,这种参与同时也使得那些作为民族标签的习俗、礼仪或传统在某个特定名称的少数民族群体中推广开来(即便以前它们可能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习俗或传统),这种复兴与推广不仅创造出了它们族群认同的依托,而且还加强了这种认同,族群性也由此产生(第三阶段)。如果说民族识别只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族别划分”的话,那么如上论述的这个过程就是“族群再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族群得以产生。也许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并不一定是历时的发展状态,它们也有可能是一种共时的理想类型。在中国少数民族族群性形成的过程当中,第二阶段跟第三阶段更多的就是一个共时的状态。下文将根据少数民族的市场参与状况并举出一些实例来主要对第二和第三个阶段作出阐述。
(一)少数民族身份对于他们参与市场所造成的阻碍
首先,汉族人对于一些少数民族“好斗”的刻板印象使得用人单位对少数民族劳动者心存畏惧。譬如,发生于2009年7月5日的新疆“7·5事件”就有很多人把原因归于同年6月25日发生在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的事件。当时“该厂的一位实习女工误入新疆籍男员工宿舍,遭到几位新疆籍男员工的挑逗戏弄,至6月26日凌晨引发群体斗殴,造成两名维吾尔族男青年死亡和一百多人受伤,其中有八十多名为新疆籍人。”①至于“7·5事件”的起因究竟是不是旭日玩具厂事件我们尚不可知,但是关于大部分汉族人对于维吾尔族人好斗的刻板印象我们却能管窥一二。此外,对于藏族、蒙古族、彝族等这些民族的野蛮好斗和原始蛮荒的刻板形象导致很多汉族为主导的用人单位谈少数民族而色变,以致很多这些少数民族的人在市场经济的参与过程中经常会受到阻碍。
其次,很多少数民族的群体虽然参与到了一些工厂企业的市场运转中去了,但是他们的少数民族身份致使他们只能以“临时工”的身份参与,以致报酬和职业前景并不光明。例如,彝人在珠三角地区的劳动用工模式是“领工制”,即已经进入工厂或企业
的工头们充当“中间人”,把他们老家的劳动力带出来并从中赚取劳动力差价(刘东旭,2013:204)。这种参与方式使得他们大多只能以“临时工”的身份参与到市场经济过程中去。“临时工”身份无疑既不稳定,也没法参与到固定的工资或职业晋升系统中去,在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方面自然也缺乏有效的支持。
如上讲的两种阻碍少数民族参与市场经济的模式虽然对少数民族较有不利,但是这却促进了在外务工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共同的“民族身份”使得这些群体团结在了一起去面对外面世界的危险和不利。所以,这种消极的阻碍越多、越严重,族群认同与“族群再造”或“族群复兴”的进程也就越快。譬如,刘东旭就研究过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凉山彝人如何在外地利用“领工制”的模式参与市场经济并进行“家支再造”的(刘东旭,2013:203),这种“家支再造”的模式无疑也就是“族群再造”或“族群复兴”的一种表现形式。
(二)少数民族身份作为他们参与市场的资本
少数民族身份之所以能够成为他们参与市场的资本,是因为他们民族内某些特殊的习俗、传统或礼仪具有可供大众消费的经济价值。这种经济价值来自于广大汉族人民的猎奇心理,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奇风异俗和所谓民族美食、以及他们生存的自然环境的浪漫追求心理。当少数民族们在市场中发现某些特殊的习俗、传统或礼仪具有经济价值的时候,他们便会利用这些习俗、传统或礼仪作为救命稻草参与到市场当中,这种参与同时也使得那些作为民族标签的习俗、礼仪或传统在某个特定名称的少数民族群体中推广开来(即便以前它们可能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习俗或传统)。当然,这种参与也主要分为两种:民族旅游的开发和民族特色的“外送”。
首先,民族旅游的开发无疑成了少数民族参与市场经济的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方式。这种方式大多都会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发可供游人观玩的人文和自然景观,满足游客对奇风异俗的猎奇心理。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就是“侗族大歌”作为少数民族的资本并成为民族旅游开发的重点的过程。“侗族大歌”原本只是侗族地区一个小村庄的歌唱传统,它只在非常有限的地域内流传(JIAPING WU,2014:976)。但是如今它已在维也纳、纽约、巴黎和上海世博会等这些国际性的都市和国际性的重要场合中表演过,并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侗族人民的“金色标签”。在侗族当地的侗寨“体验经济”(experience economy)的发展过程中,“侗族大歌”成了王牌栏目,以致于外来人都认为“侗族大歌”是所有侗族人民的歌唱传统。此外,苗族的“苗银”、蒙古族的“呼麦”、土家族的“酱香饼”等等都成为了一些类似的传统文化符号。这些符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他们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推广,同时,这种复兴与推广不仅创造出了它们族群认同的依托,而且还加强了这种认同,族群性也由此得到了强调。
其次,在民族聚居区以外的其它大中城市或地区,所谓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美食和奇风异俗等还提供了“外送”服务。来到经济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大多喜欢从事小型的“个体工商”行业,他们可能会在这些地区开一些大型或中小型的民族餐馆、民族服饰店等,也可能就是摆摊兜售民族特色食品或饰品等等。例如,随处可见的“新疆羊肉串”、“土家酱香饼”、“傣妹”、“苗银”等等招牌大多都是少数民族在经济发达地区参与市场经济的方式。这些方式不但为少数民族群体在经济发达地区提供了生计,而且还为他们自己的传统与文化“打了广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促进他们民族聚居地内的旅游业的发展。
三、结论
总之,不管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还是在经济发达的汉族聚居区,少数民族利用他们民族传统文化来对市场经济的参与,在极大程度上给他们自身的族群认同创造出了文化依托,当然这也加强了他们的族群认同。如果说在市场经济发展以前的民族识别并没有对他们自身造成什么影响的话,那么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他们对市场经济的参与却是促进了他们族群性的形成或复兴。所以,如果说民族识别作为一个进行族别划分的国家手段并没有划分出带有严格意义上“族群”属性的群体的话,这些群体参与市场经济的这个动态过程却是在他们所冠有的少数民族名号之下发展、创造或复兴出了“族群性”,这个名号之下的“族群”正在形成。
注释
①引自南方网新闻网页:http://wenku.baidu.com/link?url=fO Pdlh3Q8nvX U2menlL7HatZ6ZH5WBnstSsK3Tc7r46jGOYzzWC Lr_nym27UUywLX Fxt1Lbo93L1wELuHtwhVLgu94HKI1NklQ MLtAU7lS
[1]范可.2015,《论多民族国家语境里的族别问题》,《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
[2]范可.2015,《略论族群认同与族别认同之异同》,《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4期.
[3]郝瑞.2002,《再谈“民族”与“族群”——回应李绍明教授》,《民族研究》第6期.
[4]刘东旭.2013,《流变的传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彝人家支再造》,《开放时代》第2期.
[5]潘蛟.2003,《“族群”及其相关概念在西方的流变》,《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5期.
[6]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2004,《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7]张九霞,2001,《珠江三角洲外来企业中的族群与族群关系(下)——以深圳中成文具厂为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
[8]庄孔韶,2003,《人类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9]Banton,Michael,1987,R acial T heo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C onnor,Walker,1984,T he National Q uestion in Marxist- Leninist T heory andStrategy,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1]Eriksen,Thomas H.,1993,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London:PlutoPress.
[12]JIAPING W U,2014,T he R ise of Ethnicity under China’s Market R efor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R egional R esearch, Vol. 38.3.
[13]Keyes, Charles, 1976, Toward a New Formulation of the Concept of Ethnic Group, Ethnicity, Vol.3:202-13.
[14]R avenstein, E.G., 1885, The Law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48, No.2.
陈祥(1990—),男,汉族,湖南郴州人,目前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研究所就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社会与文化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