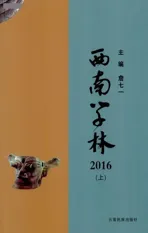文化地理:木霁弘茶马古道研究的意义
2016-11-14叶向东
叶向东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茶马古道”一词最早出现在木霁弘、陈保亚、李旭、徐涌涛、王晓松、李林等人著,1992年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滇藏川 “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中,这是第一次在文本里对茶马古道进行考证、命名和学术定位。1990年7月至9月,木霁弘等人对滇藏川交界的广大区域进行了徒步考察,行程两千多千米,收集了有关茶马古道的几百万字的第一手材料,可以说木霁弘的茶马古道研究是其在西南大地上走出来的,文化是其研究的逻辑起点。“我们用 ‘茶马古道’的名称,是因为贴近大西南古道的特点:用马帮输送云南的茶叶。”茶是茶叶,马是驮东西的马,茶马古道是古代马帮运输茶叶所形成的道路。这条古道所带来的不仅有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而且有文化的融合与进步。茶马古道的历史很久远,大约在四五千年前,云南就和印度、中亚和西亚有交往,到了公元前四五世纪,这种交往在史书上有了明确的记载。有人称这条连接中国西南和印度、中亚和西亚的通道为 “南方丝绸之路”。这实际上是模仿 “北方丝绸之路”的一种提法。“北方丝绸之路”是德国人李希霍芬提出来的,话语权属于西方人。中国西南通往印度的这条通道,经过木霁弘等人的实地考察后,最终将其命名为茶马古道,这是中国人用自己的文化视野来观照这条古道,并说出了自己的话语。
一
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茶文化。云南是茶的原产地之一,由于民族众多,地域多样,故云南的茶文化就具有了多样性与丰富性。云南由于自然条件的优越,古人类很早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在人类早期的发展过程中,采集业的发展,刺激了人的文化思维,而这种思维的发展,必然引导人们去选择一些较好的植物进行定向栽培,而这种思想的孕育,标志着农业社会的诞生。云南的先民把茶作为定向培育的植物,开了把茶作为饮料的先河。早在先秦的时候,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就已饮用茶并创造着属于自己的茶文化。德昂族在其长诗 《达古达楞格莱标》中就讲述了其祖先是由茶叶变来的故事:“很古很古的时候,大地一片浑浊,天上美丽无比,到处都是茂盛的茶树,茶叶是万物的阿祖。天上的日月星辰,都是茶叶的精灵化出……”。木霁弘认为云南少数民族早在汉代就开始栽培茶树了,“茶”字到唐代就见于正式文献了。“茶树原产地为中国的云南,而云南也是 ‘茶文化’的发源地,它是最早培植茶树并使用茶的地方。在云南西双版纳、思茅、临沧等地至今仍有千年的老茶树,而四五百年的茶树则是成片、成林。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云南省除稻作文化外,贡献给世界最重要的 ‘文化’之一。”云南的先民把茶作为定向培育的植物,开始了世界饮茶文化的先河。樊绰 《云南志》卷七载 “茶出银生城界诸山”,“银生”指的就是现今景东、景谷及其以南地区。大叶子普洱茶,早在唐天宝年间就在澜沧江两岸大量种植。滇茶最初由马帮运入四川,并向西、向北扩展。宋代在今普洱市境内就已有茶马交易市场,檀萃的 《滇海虞衡志》记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16世纪,茶传入欧洲,各国纷纷进口中国的茶叶,托尔斯泰的 《战争与和平》中就有关于中国普洱茶的细致描写。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就是因茶引起的,这就是世界近代史上有名的波士顿茶叶事件。19世纪末,法国、英国先后在思茅设立海关,增加了普洱茶的出口外销。
茶本来具有实用功能,但这种实用功能逐渐在转化,在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中产生了变异。它同各个民族不同的性格、情感和审美情趣相结合,并融于众多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和习俗之中。茶的魅力,在于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不断地在茶马古道上流动和积淀,这样一来,它就能反映许多民族的理想,并渗透于人们的情感世界之中,西南地区的各个民族至今仍被笼罩在它浓烈的文化馨香氛围之中。“从现在的很多考证来看,云南是茶的原生地,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外延再扩大,包括现在四川一带,贵州一带,湖南一带,广西一带都可以说是茶文化的酝酿和孕育之地,是从这一地方逐渐向世界各地扩展。从正史 《唐国史补》上来看,唐代之后茶叶进入吐蕃。藏族一接触到这个茶就离不开它了。藏族是游牧民族,大量地食用乳制品,后来藏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一个观念,一个民族的发展必须有茶——我们今天科学地说是要有维生素,要有蔬菜这些东西。所以它把茶叶的茶汁和它的乳制品合在一起打成酥油,酥油茶。藏族有一句谚语,说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那地方的人喝的茶都是砖茶,这也是当时为方便运输而留下来的习惯,将茶制作成茶饼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运输的成本。”(第36页)由于国内、国外市场的大量需要,使来自云南的茶在长年累月的运输和商贸过程中,被多次不规则地发酵,出现了茶叶工艺史上的一次革命,茶的自然发酵,普洱茶就是其代表。普洱茶现已成为世界物质文化中的一个符号,正造福于全人类。云南独特的地理和自然环境,为茶文化的滋长创造了条件。在云南的很多地方都有茶会,它是男女青年的一种集体社交活动。茶会时,由男方或女方邀请其他村寨的客人到本村赴会,主人备茶,客人吃茶。唱歌、对歌是茶会的主体,茶会同时也是一个歌会。在这种社交场合中,可以谈情说爱,可以用歌声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可以用歌声寻求到自己的知己和伴侣。茶调有颂茶调、约会调、赞垫调、欢聚调、情谊调、鸡鸣调、分别调、伤心调等等,这些茶调,有的欢快,有的哀怨,有的激昂,有的深沉,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茶会的习俗在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中都有,这种习俗以茶为支点,由此引发出一种群体社会活动,茶文化巧妙地和云南少数民族本身的民族习俗相融合了。
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木霁弘,他是在考察方言的时候发现了茶马古道的。他从语言的角度展开对于茶马古道的研究。“茶”这个词在古藏文中读 “dza”,是一个浊声母词,与汉语里的 “茶”的古音 “dea”非常相似,现在藏语的 “tcha”的音是从古藏文 “dza”演化而来的。
“古藏语中也有 ‘茶’这个词,‘茶’作为藏族人民生活的 ‘主食’品,很难想象不产茶的地方,茶那样深深地渗透到藏族人民生活中去。”(第27页)木霁弘认为茶马互市起于唐,而兴于宋。“《滴露漫录》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国家之大经。’这里茶已同国家的政治大事联系起来了。宋统治者用茶马贸易来同少数民族搞好关系。”经过对 《太平寰宇记》《岭外代答》《桂海虞衡志》《云南志》《滇略》《长物志》《考磐余事》等文献中有关茶的研究和考证,木霁弘对茶有了自己的独特认识:“‘茶’这个 ‘新文化源’由于自己的‘积淀要素’的影响,不断 ‘汲取’另外一个社会的 ‘文化’进行 ‘融合’,因而得到传播。‘茶’文化的 ‘要素’首先被发源地的社会所吸收,接着沿 ‘茶马古道’逐渐向北方延伸开去。”
木霁弘通过对饮茶方式的分析发掘茶文化的丰富内涵。云南傣族地区是把茶晾干后在锅上用火烤得略焦,饮用时用开水冲泡即可饮之,味道是茶的本味。这种饮茶方式多在低海拔地区,并为茶产地居民的基本喝茶方法。云南凤庆是 “滇红”茶的发源地,历史上曾有每年一度的 “春茶会”,明代的徐霞客所品的 “太华茶”便是凤庆所产。凤庆茶随一年四季的变化配制风味不同的茶,四季茶名曰:清明春尖尖,云雾玉露,金秋谷花,银霜太华。茶便显示出了艺术性。这里的茶多经细炒加工,不配其他料,用开水冲沏,头道滑,二开三开味道溢出,醇厚苦中带甜。大理白族用茶独特,“三道茶”为其代表。用云南绿茶精品,分别配以核桃、乳扇、蜂蜜、生姜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原料进行特殊加工而成,头道苦,二道甜,三道则回甜,味道清香爽口,高雅舒心,体现了较高的审美情趣。“三道茶”的饮法,大约在唐宋的南诏大理国时就已开始于上层社会,随后进入寻常百姓家。进入滇西北藏区和西藏后,藏族用茶则又有其独特的风采。“酥油茶”是藏族人民离不开的主要饮料。这是因为他们居住在高海拔地区,多食肉和乳制品,而茶具有清胃健脾的独特功效,同时酥油茶能产生高热量,能抵御严寒气候。在茶马古道经过的地区,藏族比其他民族更爱茶,依恋茶。酥油茶、茶桶、木碗、木盆以及与茶有关的歌谣、民间故事,无不渗透于藏民族的茶文化之中。藏族婚姻中以茶作为定亲之物,婚礼中还必须演唱茶调。因茶衍生出来的“茶会”“茶歌”等都是茶文化的具体表现。藏民族不仅品出了茶的真正味道,而且将茶文化上升到意识形态上来加以延传、深化,这是藏民族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印度的饮茶习俗是从中国西藏传入的,茶的读音与藏语基本相同。印度人多饮红茶,他们把茶放入壶里煮,加入牛奶、白糖,使茶水成粥状,味无苦而香甜,具有提神醒脑的功能。“‘茶’不但是人的物质需要,也成了人的精神所求。‘茶文化’因饮法的不同变化,显示了各民族文化分离与之连接的文化特性,同时也体现了 ‘茶文化’传播的特殊性。”
二
“茶马古道”这一概念,揭示了这些通过马来驮运茶叶的古道的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
由于茶马古道是流动的,其跨越的地区非常多,与不同民族的交往构成了它文化的特殊性。茶马古道贯穿了不同的区域,各个民族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如果没有这些文化的差异,那么茶马古道文化也就失去了它的博大性和特殊性,同时其价值和意义也就消失了。茶马古道文化本身就是各民族各地区进行交流和影响并相互渗透形成的,正因为如此,同化、取代、融合、碰撞,各民族各地区在更高的层次上有表现出自己的独特个性和特质,并形成各民族之间文化的新的差异。茶马文化是以云南的本土文化精神与西藏、四川、印度、尼泊尔、中原腹地的文化交往中,在众多民族文化的接触中逐步完善和在更高层次确立了自己的文化个性特征的典型。木霁弘的实地调查不仅证实了茶马文化的博大,同时也发现了茶马古道文化的特性。“拿小中甸村来说,村民平常恪守藏族习俗,通用藏语交际。但现今老一辈的人还能说纳西语。在我们调查过的一些藏族村寨,‘烧猪毛 (杀猪后不烫毛)’,上门女婿另起 ‘喜名’的白族旧俗。乡城、盐井的藏族说他们开梯田,打渠引水,烧砖瓦的技术最初是从纳西族那儿学来的,在乡城,还能见到纳西族的城堡遗址及现在的纳西式房屋。‘茶马古道’上的一些藏族的丧葬就包括天葬、水葬、火葬、土葬等等。中甸县、德钦县等地的许多借词多来自汉语云南方言,这就说明了 ‘茶马古道’文化 ‘是一种流动的文明文化’。”(第26页)语言是思维、交际不可缺少的工具,同时它也是民族文化最有力的体现者。茶马古道上的民族语言变化、融合,非常复杂,从这些变化、融合的语言上,可以看出这条古道是各民族交流迁徙的路线。“试对 ‘茶马古道’上的一些纳西族聚居地的语言进行比较,他们主要分布在昌都的察雅,甘孜的乡城,迪庆的大、小中甸。这些纳西村民都会说纳西语。由于他们被包围在藏族村寨中,他们大多也会说藏语。根据我们的调查,中甸县的小中甸村和德钦县的巴美纳西族所说的纳西话和丽江县的纳西话基本相同,而且相互间能比较自由地对话,基本词汇的对应也比较严格。”(第29页)
木霁弘认为,佛教作为一种文化,就是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中国西南地区的。由于茶的价值,其交易可以获得高额利润,佛教也就伴着茶马古道而流布,寺庙也就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兴盛起来,僧众的地位也就伴随着经济的繁荣而显赫起来。云南境内的茶马古道兴于汉、晋并以佛教汇合点大理为中心,辐射成众多的道,它可达丽江、中甸、福贡,跨金沙江、澜沧江、怒江进入我国西藏、尼泊尔、印度。从佛教传播的路线来看,许多和茶马古道是重合的,大理的崇圣寺,剑川石宝山石窟,宾川鸡足山,中甸归化寺,德钦东竹林寺,西藏碧土寺、左贡寺、田妥寺、向巴林寺、类乌齐噶玛丹萨寺等等,这些寺都是沿着茶马古道修建而成的。滇西北地区藏族信仰的宗教是由自身的原始宗教和由印度传来的大乘佛教融合而成的。大乘佛教是大众的,以普度众生为其终极目的,将释迦的存在超历史化、超人格化,而且使释迦的人格、精神具体化,为芸芸众生提供了各种手段来实现成佛的目的,人人具有佛性,人人都能成佛。“大乘教传入滇域,正是‘茶马古道’繁盛的时期,它远传到云南的丽江、大理、楚雄一带。在纳西族的东巴经典中有大量的大乘教借词,而且可以明显地看出藏语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如 ‘丁巴什罗’‘东巴’‘能科’以及 ‘参禅’‘金刚杵’‘天尊’等等。从这里面可以看到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纳西东巴教三者通过 ‘茶马古道’所进行的 ‘融合’。”(第27页)所以,茶马古道也是一条宗教传播线路。茶马古道是汉族和藏族等各民族人民亲密合建的道路,使各民族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关系,使西南地区和祖国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木霁弘特别强调了茶马古道和西藏的关系。“茶马古道形成的历史,大约有两千多年了。西藏作为中华一体的成员,茶马古道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茶’文化由于历史的原因,藏族人民很难离得开它。”(第29页)
三
滇藏川地区山高水急的自然环境,带来了交通的不便,道路的艰险,只适于马帮的运输,马帮和古道构成了与外面世界沟通的生命大动脉,东接中原,北达西域,西邻印度,南经印度支那半岛通往印度洋,因而得以构成独具一格的地理单元,这种自然形成的生态格局,给民族和文化的发展融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印度文化、中原文化、西北氏羌文化、东南沿海的百越文化、中南地区的百濮文化等多种文化的冲击影响,使该地区形成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宝库,它所形成茶叶、马帮、古道文化对世界有过较大的影响。一般认为中国对外交流的路线有四条:海上之道,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青藏 “麝香丝绸”之路。木霁弘认为滇藏川 “茶马古道”是东西方交流的第五条文化古道,它应当和其他四条文化线路并列。从云南进入西藏的通道,这就是他和其他研究者徒步考察的茶马古道。茶马古道其实并不是一条单一的古道,而是一个网状结构。“随着我们不断地对云南、四川、西藏的很多地方和广西、贵州的考察,发现滇藏线和川藏线这个茶马古道是一个狭义的茶马古道概念。广义的茶马古道应该范围更广,云南、贵州、广西、四川、西藏是这个茶马古道的核心区域。”(第40页)木霁弘认为,茶马古道并不是某一条或几条道路,而是由雪域古道、贡茶古道、买马道、滇缅印古道、滇越古道、滇老东南亚古道、采茶古道等形成的一个交通网络。这个交通网络以云南为中心,涵盖整个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地区,从文化的意义上可以说,茶马古道就是以云南为中心的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各地共同的历史文化现象和社会经济现象。由于青藏高原海拔处于三四千米的高度,地形地貌非常特殊,再加上民族迁移频繁,因而形成了独特的雪域文化。雪域文化的精髓体现在其独特的饮食结构、社会层次、婚姻家庭、心理素养、宗教巫术、人格特点、风俗习惯等方面。“这次考察使我们对茶马古道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比如说茶马古道从第一台阶的喜马拉雅下来,到了云南,就是第二台阶,第二个台阶再向下,就逐渐地平缓了。这是一条伟大的线路,以云南为例,如果我们从梅里雪山算起,梅里雪山海拔6740米,那是一片雪域的高原,在雪域生活的藏族是畜牧民族,其生活方式是喝酥油茶、吃牛肉、吃糌粑等等;到了第二台阶,就到了丽江,这个区域主要是畜牧业和栽种高山农作物,如麦子、玉米等等,生活方式介于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从丽江下到大理,就开始有大量的稻作文化,彝族和白族生活在那儿;继续再往下,就全部是稻作文化,傣族、壮族生活在那里,这些稻作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整个茶马古道是一条贯穿民族文化的大走廊。”
木霁弘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了藏族人民非常独特的物质观。藏语 “物质”这个概念是 “生来具有变性者”的意思。它把 “物质”的东西分为三类:一是意识现象;二是没有意识的触觉物体 (如石头、水等);三是除了意识和无意识的触觉物体之外的一切生来具有变形者 (如人、牛等)。藏族有意识是物质、物质不等于意识的观念,因而不会产生 “物质”与意识孰先孰后的问题。“‘茶马古道’在雪域文化圈内,既体现出其文化的收敛性,也表现了它作为张力性的象征,正因为雪域文化包含着自主生长的基因,同时又有再生的吸收,这样一来,茶马古道作为催化剂,使得雪域文化具有生成功能。”(第11页)木霁弘认为,茶马古道是唐宋以来汉藏等民族之间进行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它主要穿行于藏、川、滇横断山脉地区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域,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式的一条古代商道。马帮是云南地区特有的一种民间商贸组织,两千年来,商人们通过马背把货物从一个地方驮运到另一个地方,当时马帮驮运的东西以茶叶为主。茶与马在历史中的相遇,使木霁弘开始了对于茶马古道文化内涵的深刻探索。茶马古道是中国藏区连接祖国内地,并外延至南亚、东南亚的重要纽带,是中国西南各民族自古以来相互交往、融合的走廊,是一条中国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和文明传播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古老驿道。茶马古道沿线是中国民族文化最富集的地区之一,是藏、汉等各族劳动人民智慧的共同结晶,是中国西南各民族和睦相处、同生共存的历史见证,是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铁证。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最险峻的驿道,是目前世界上仍在部分运行的古道。茶马古道沿线是世界上地势差异最复杂的区域,拥有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气候复杂多变,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东亚植物区的核心地带,植物区系特有成分十分突出。茶马古道以茶文化为其独特的个性在亚洲文明的传播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它扎根在亚洲板块最险峻的横断山脉,它维系着两个内聚力最强的藏文化和汉文化集团,它分布在民族种类最多最复杂的滇、川、藏及东南亚和印度文化圈上,它是在亚洲板块上和北方丝绸之路、北方唐蕃古道并列的一条古代文化传播要道,它在文化史上的意义不亚于其他任何一条古道。木霁弘把茶马古道研究的逻辑起点定位在文化上,显示了其研究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茶马古道是一个庞大的网络,造成各个民族的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一种叠置性文化。
木霁弘的茶马古道研究对藏川滇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探索 ‘茶马古道’文化的目标就是要建筑一个新的 ‘人文生态’系统,为 ‘脆弱’文化类型提供一个新的生存模式,尽可能地推动大西南少数民族自觉继承并弘扬文化传统的进程,并为这一地域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通过对大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为这一地区人民在新的经济发展中积累充足的文化资源。同时也为该区域利用非经济因素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模式。人们最终将在此创造一个文化多样性、生物多样性的共生地域,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持续性社会发展模式。”(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