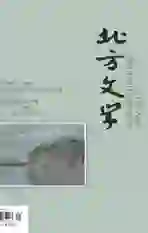浅析史部分类释例
2016-11-10周洁
周洁
摘要:史部分类是在史源学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分类,编纂成专门目录,史部类目的形成同样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本文以《四库全书总目汇订》史部分类为例,并结合《直斋书录解题》,就其在编纂过程中的分类原则作出如下探讨,以及阐述追溯史源在整个编纂过程中的意义。
关键词:史源;史部分类;《四库全书总目汇订》;编纂
一、史料来源
清代学者崔述在《考信录》提要中云:“故今为考信录,不敢以载于战国秦汉之书者悉信以为实事。不敢以东汉魏晋诸儒之所注释者悉信以为实言。务皆究其本末,辨其异同,分别其事之虚实而去取之。虽不为古人之书讳其误,亦不至为古人之书增其误也。”
可见,早在清代就有学者注意到史料来源的问题。即在读书做学问时,必定对所引用的古文,考证其来源,辨别真伪,以判定史料价值,由此决定采用何种文献。
在对搜集到的史料进行鉴别真伪,鉴赏价值后,根据收录原则和成书标准,按照一定的分类系统,分门别类,编纂成一部专门的书目。目录学类的书,在今天看来更多的是作为工具书性质的书。因为中国古籍浩如烟海,真假难辨,若没一个系统,不知有何书,更不知从何查找,无疑为读书做学问带来不便。这就要求在编纂目录时,考证书目的最早来源,以达到类例分明的目的。一般做学问的人可以通过目录书扩充知识,获得更多的文献来源。于研究者而言,则不失为一种考证门径。所以整理和编纂,在本质上与史源学的观点是相通的,运用到了层位的、系统的观点。而史部分类更是在史源学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分类,编纂成目录书,史部类目的形成同样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二、史部分类原则
郑樵《校雠略》尝曰:“以今之书校古之书,百无一存,其故何哉?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又云“欲明天者在于明推步,欲明地者在于明远迩,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因他重视类例,才能分门别类,疏通伦类,以考其得失之故。
(一)主次分明,类目相属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史部总叙言“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祥。莫简于《春秋》,莫祥于《左传》。鲁史所录,具载一事之始末。圣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定以一字之褒贬,此作史之资考证也;丘明录以为《传》,后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贬,此读史之资考证也。”由此可见,对于史料的编纂,不仅需要语言凝练,繁简得当,还应当按照尊重史实,还原历史面貌的原则进行史料编纂工作。
史部类目的形成同样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下简称《直斋》)将史部分为:正史类、别史、编年、起居注、诏令、伪史、杂史、典故、职官礼注、时令、传记、法令、谱牒、目录、地理。《四库全书总目汇订》(以下简称《四库》)中将史部分类设置为十五类。“然则古来著录,于正史之外兼收博采,列目分编,其必有故矣。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旧有谱牒一门,然自唐以后,谱学殆绝。”
对比两书可看出,史家对于史部分类是在总结前代分类法的基础上设置的。除了沿用以往史官分类标准外,因朝代不同,根据重要程度以及存世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可以从中窥见其在编排目录时的成书思想。《四库》的史部分类与《直斋》互有不同。除了相同类目的排序发生了变化,还有一些补充,包括史抄、载记、政书、史评。而《直斋》史部分类中如起居注、伪史、典故等,也是《四库》所缺少的。但事实证明,这些补充或是同类事物的转换,或是概念上的包含,均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如:“《四库全书总目》能够根据类目内容上的共同特点来合并类目,并根据类目内容来考虑类目归属。”这一点在证书类和诏令奏议类上得以体现。“‘诏令奏议之明确标目设类,是《四库全书总目》考察历史,结合实际,博采众长而创立的一类”。据李致忠检《旧唐书·经籍志》史部,并无此门,只在“起居注”类中间著录了《晋书杂诏书》一百卷,《晋太元副诏》二十一卷等11部诏令之书。
“‘政书类目之创始者,乃钱溥《秘阁书目》。‘政书类对应的是《隋书· 经籍志》之‘故事、‘仪注类,也有称‘旧事的,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称‘典故,其实说穿了指的就是旧时的典章制度。”
针对四部分类法,李致忠在《三目类序释评》中作了详细的阐述。据他所言,任何一张四部分类表都有它的局限性,其类目设置和部居都还有不尽科学和不尽人意的地方,所以说必须先下力气对类表进行调整,并就如何调整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在史部分类法中,他介绍了《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标准,并结合现存的中国古籍书目实际情况,对原有分类法予以补充和调整。首先针对纪传、正史和编年的分类排序进行论述,然后就正史与别史理当对应的问题展开说明。“与正史相对应的应当是别史。正史一立,作为辅助补充正史的别出之史,即别史,也必须随之而列类。别史之列类标目,始于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用以部居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的别史。”
以上所述,在史部目录编纂的过程中,对于史部分类,围绕着删繁就简,主次分明的原则,考证学术源流,尽可能地编写一部全面而系统的目录书。
(二)取材精慎,删减得当
《四库》的这些史部分类中也有一个特例——谱牒。虽然把它列入类目中,却未对其进行收录。而《直斋》虽为其收录,但评价甚少。
关于谱牒一门,在《四库》史部中并未被编纂。“谱系,或曰谱牒,或曰氏类,《四库全书总目》无此类名。”谱牒是古代记述氏族世系的书籍,也是伴随着家族制度而来的记录家族血缘关系的文献。古时谱牒作为维系家族凝聚力的纽带,是一部见证家族宠辱兴亡的变迁史。它也是世家大族进行选官和通婚的依据,记录着婚姻是否门当户对等。
针对宋明二代私家记载居多,原因在于当时世系分明,好议论朝政,因政见不同而分门户,立朋党,由此结下私怨。得志时则被朝廷排挤,失志时则以笔墨反击报复,以致于是非颠倒,只有合众证而质之,亦必得其情。
(三)言简意赅,总领全文
《四库》史部分类中收录的书目,首先要为其编写提要。介绍作者字号,家乡,官职,学术源流,师承何处等,尤其与本书相关联的思想流变。主要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评价此书,举例说明它与同类书的区别与创新点,以及评价它在整个学术史上的地位。
撰写史部提要,不仅需要客观地评价历史,更贯穿惩恶扬善、以史为鉴的价值取向。“在四库馆臣的史学思想中,记录一代政事的史书可以垂鉴奕世,而缺乏鉴往知来意识的史家,著述谬误,识见浅薄,无益当世,贻误后人,必然会阻碍史学的发展。这表明四库馆臣对史学借鉴功能的高度重视,认同以史为鉴的价值取向。”而且要有理有据,考证本末,辨析得失,实事求是地对此作出评价。《四库》之史书提要从上作出了总结:“千古之是非,系于史氏之褒贬;史氏之是非,则待于圣人之折中。”它明确提出治史需要惩恶扬善,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出中肯的道德评价,而褒贬的理论依据,则是圣人的道德伦理标准和封建理论原则。所以不违背史实,还原历史真相是每个史学家基本的道德规范。
例如:《四库》正史类一《补后汉书年表十卷》的提要首先交代作者熊方家庭背景及成书缘由与书的内容,收录原则。因司马迁作《史记》始立“十表”。班固“八表”,实沿其例。而范晔作《后汉书》,独缺斯制。遂使东京典故散缀于记传之内,不能丝联绳贯,方因作此编,补所未备。凡《同姓侯王表》二卷,《异姓诸侯表》六卷,《百官表》二卷。并且举例说明,评价其优缺点。凡此数端,皆为所短。要其经纬周密,叙次井然,使读者按部可稽,深为有裨于史学。
总之,研究历史,编纂目录,寻考史源应该是首要问题。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因而在真伪未辨,是非不明,史实不清的情况下,不要匆忙下结论。尤其在学术领域,保持一份谨慎的态度,小心考证,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以免贻误后人。
注释:
崔述:《考信录》收自《续修四库全书》455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魏小虎:《四库全书总目汇订》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441页。
魏小虎:《四库全书总目汇订》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442页。
顾红:《<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类目的设置》,广东图书馆学刊1985年第3期,第27页。
李致忠:《三目类序释评》,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李致忠:《三目类序释评》,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李致忠:《三目类序释评》,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何发甦:《史部类目的变与不变——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延安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106页。
罗炳良:《<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的理论价值》,史学月刊2006年第9期,第18页。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卷八八《御制评鉴阐要提要》。
参考文献:
[1]崔述.考信录.续修四库全书455史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61-298.
[2]魏小虎.四库全书总目汇订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李致忠.三目类序释评[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4]顾红.《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类目的设置[J].广东图书馆学刊,1985(3):26-29.
[5]何发甦.史部类目的变与不变——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J].延安大学学报,2009,31(1):105-107.
[6]陈高华,陈志超.中国古代史史料学[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7]罗炳良.《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的理论价值[J].史学月刊,2006(9):12-20.
[8]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