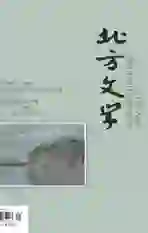论徐渭《狂鼓史》主题取向与戏剧体制之新变
2016-11-10贾倩
贾倩
摘要:徐渭杂剧《狂鼓史》在杂剧史上具有新变意义,在主题取向上表现为对个体生命在时代环境下不自由的普遍性的探讨及对传统道德判断标准的超越两个层面,与此同时,戏剧体制在独折和内部叙事结构断裂两个层面与之呼应。
关键词:《狂鼓史》;主题取向;戏剧体制
《狂鼓史》为明嘉隆间人徐渭所作,作者空有才华无处施展,借祢衡为曹操所杀,因受阴间判官之敦请,面对曹操亡魂再次击鼓痛骂,历数曹操全部罪恶的故事,行藉古讽今之实,以此文抨击社会之不公不平,抒发郁积之愤恨。然细观其文,其主题取向与戏剧体制实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此奠定徐渭在戏剧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主题取向之新变
就《狂鼓史》杂剧情节看,这绝非一个具有新意的故事,祢衡击鼓骂曹,徐渭借此旧事而抒胸中郁闷,此写法颇似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用事”,借典故与现实文本的叠加,以极尽简省的笔墨而创造出更多的意味,从两重跨越时空的故事中照见一种殊途同归的况味,发现其精神关联。人间冤屈于地下阴司得到了补偿,个人才华在另一域界获得包容欣赏,这似乎是徐渭剧终时的愿景。然而,此剧种种细节又仿佛暗示着作者更深层次的思考。
(一)对个体生命在时代环境下不自由的普遍性探讨
此处所说的不自由,不仅局限于弱势人物在时代环境下不自由,还表现为强势人物在时代环境下也要受到束缚,因此具有普遍性。元杂剧或明前期杂剧中,有失意书会才人抒发郁结,有不平文人抗拒冷落,他们的笔触涉及到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的纠葛关系,然而这种纠葛更多表现为失势人物对“时不我与”的长吁短嗟,并不足以涵盖普遍个体生命的自由与价值在大时代环境下的存在状态。《狂鼓史》在此则得到了一次突破,这个主题的表达不以狂生祢衡为首要承载对象,作者一反前人做法,令其配合曹操这位看似成功的人物来呈现新变,从而使得主题在广度及深度上得到新的拓展。
1.强势人物在时代环境中不自由
从人物形象来看,主要人物不过三人,即判官察幽、祢衡、曹操。强势人物的不自由由曹操这一人物来承载。判官察幽将祢衡引为上宾,让祢曹二人重演骂座。在此杂剧中,曹操不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悲恺英雄,也不是《三国演义》的枭雄形象,本为阳间强势人物的角色因为阴司环境的限制转换为弱势,这种弱势由三方面的压力造成。
首先,祢衡对曹操实施了指控与叫骂,因环境允许比现实骂座更加有恃无恐,位置的逆转让曹操不得不收敛强势,自由度随之缩减。面对祢衡一开始骂曹操“这皮是你身儿上躯壳,这槌是你肘儿下肋巴……两头蒙总打得你泼皮穿,一时间也酹不尽你亏心大”的猖狂叫骂,曹操委屈反抗道:“你怎么指东话西,将人比畜?”对于祢衡指责他杀害董贵人和腹中之子,曹操也道出些许无奈:“伏后与董承等阴谋害俺,我故有此举。终不然是俺先怀歹意害他?”祢衡接着以袁公、孙权玄德之事追击指控:“是处儿城空战马,递年来尸满啼鸦。”对此,曹操也似有隐情:“大人,那时节乱纷纷,非只我曹操一人如此。”从曹操畏缩的解释中,我们不难看到,昔日强势人物不自由的程度明显增大。
其次,判官在文中有过一些倾斜于祢衡的表示,使得曹操处于不利的位置,形势反转,自由度缩减。如:“你若是乔做那等小心畏惧,藏过了那狠恶的模样,手下就与他一百铁鞭,再从头做起”,“手下采将下去,与他一百铁鞭,再从头做起(说曹操)”,“老瞒,就叫你自家处此,也饶自家不过了。先生尽着说”,“手下!快把曹操等收监”等等。可见,判官这些论断都将曹操置于弱势的位置。
再次,旧时曹操部下的女乐也在被传唱时对曹操冷嘲热讽,进行背叛,事后面对曹操不解的哀求,还加了句:“道其实,我先首免罪”。这样的落井下石更是使曹操昔日的强势风范有所削减。
面对以上三方夹击,曹操滑入一种尴尬而弱势的位置,现场人物的判断也呈现出一边倒的状态。但这种种罪行经由曹操的辩解,指控力度顿时颓落。曹操的回答与辩解又让我们对其凶残所为有所同情,在兵马纷乱的时代,这些残忍举动也非个人心愿,这也是迫于时代与环境的压力基于人性本能企图保存自己的最理所应当的反应,可见,原本作为强势人物的曹操在其强势之时是不自由的,在时空环境发生改变后转化为弱势人物,这也是不自由的。
2.弱势人物在时代环境中的不自由
徐渭在其画作《墨葡萄图》中,有诗云:“笔底珍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可见徐渭对于个人才华不得实现有很多不甘,在剧中让与己有相似遭遇的狂生祢衡来替自己代言,实在是水到渠成,然而祢衡这个人物形象并不是徐渭在剧中的全部寄托。狂生本恃才傲物,又不被赏识,与曹相比,在阳间的时空环境下处于弱势位置,其自由程度更小一些,终落得被杀头的地步。
然而,在阴司中,祢衡被判官引为上座,又得判官与女乐的舆论支持,处绝对有利位置,逆转为这次骂座表演的强势人物。自由度的提升使其狂放程度有增无减,对此时换位为弱势人物的曹操打击力度便进一步加强。在这场实力悬殊的击鼓骂座表演中,祢衡颇有仗势欺人的姿态,连判官也不得不对他有“这生果然无理”的评判。这不仅因着祢衡原本的狂生性情,更重要的是阴司约束变小,人物自由度加大,可见境遇改变对人物心理产生的重要影响。这使得徐渭在借祢衡言志之外,也会思考:设使阳间祢衡处在曹操的位置,就一定不会变成另一个曹操吗?原本阳间弱势的祢衡是不自由的,但随着时空转变而居强势位置时,其所作所为又随之变化,出现了与先前强势人物如出一辙的行为与选择。由此可见,作为弱势人物代表的祢衡也是不自由的。
综上,徐渭于抨击现实,抒发郁结之外,更以深刻的人生经验和思考探讨普遍的个体生命在大时代大背景下的不自由与不自主的现状,从古至今再及未来,个体生命的无奈与是非成败都来源于此,甚至所谓强势弱势及个人体现出来的价值也在被时代被环境选择性地呈现,在时空环境面前,生命个体本就处于弱势,而个体生命又要独自承担起这一切。徐渭在剧中给人物一次对话机会,将以往被人忽视的深处无奈展现出来,也将个人不自由的普遍问题抛了出来,但他并不下论断,因为徐渭也没有找到出路,这点从剧终曲终奏雅祢衡升天又替曹操求情的情形中则可找出这样的思考痕迹,这是徐渭此剧主题取向之一变。
(二)对传统的道德判断标准有所超越
在这场演出中,判官的评判显然占有着最重要的地位。前文一直把人物的对话称为辩解或辩论,而不称判断,是因为在剧中判官的位置并不起真正的判断作用,这个人物的设置类似于主持人的角色,在关键的时候依靠自己的判语控制引导现场思维方式与对话内容。
1.传统善恶判断的失效
在这个辩论过程里,引人注目的则是曹操的辩解及听闻辩解后判官的几次动摇。面对祢衡肆无忌惮的叫骂与曹操委屈的抵抗,判官不得不说“这生果是无理”,此为判官态度之一变。对于曹操辩解无奈杀掉董贵人与其腹中婴儿时,判官也不得不说:“丞相说得是”,此为判官态度之二变。祢衡就“城空战马,尸满啼鸦”的战后惨景指责曹操,曹操以乱世为由并非独己一人辩护,对此判官也说:“这个,俺阴司各衙门也都有案卷。”虽未从正面给予支持,但我们从此种语气可以看出判官实则是赞同曹的辩解也认同曹的无奈,只不过不愿太过彻底地放弃自己旧有的也是多数人支持的价值观念,此为判官态度之三变。
在判官三次犹豫的动摇中,我们可以发现判官的评价标准已经模糊了,判官在曹操与祢衡两个人物充分的交流中似乎发现传统的善恶是非判断存在着失效的危机。剧中给了两位人物充分的说明时间,随着人物交流内容的增多,判官原本持有的传统的善恶判断遭到侵蚀,甚至于剧终时祢衡为曹操求情,也是对于善恶有报的传统观念的反叛。这使得原本压制曹操的三方力量也出现了动摇。从此处看出,传统的善恶判断存在绝对化的问题,这种绝对化的判断会对人物的评价造成夸张的效果,而这种夸张的效果本身与评价人物的客观性形成冲突,因此在戏剧中传统道德判断中的善恶判断失效了。
2.人性思想的补救与超越
徐渭在传统善恶判断失效时,抛出了第二个问题——人性能按照传统的道德的判断标准从大恶大善的角度完全分离开进行评判吗?对此,徐渭以其人性思想做出对于传统道德判断的补救与超越。
曹操和祢衡在你来我往的对话中,渐渐说出各自隐情,因为人在大背景大时代环境中的不自由势必会造成人性不同程度的改变与扭曲,似乎这样的重责不应全权由个人负责,这是个人所不能选择的自由。这点不能简单归咎于人性本来的善恶,相反,人性会在这样的扭曲与变化中获得丰富,随着曹祢辩论的深入,人物形象越来越饱满,呈现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这种力量会撑破我们之前预先设定的伦理道德标准,这是徐渭《狂鼓史》中主题取向之二变。
这两种主题取向的变化不仅从人物形象的设置中可以看出,从剧情发生的背景场景设置中,也可以看出新变的举措。这个剧情发生在阴司,本身就跳脱出了人世阳间的范畴,那么,在人世阳间的所有根深蒂固的道德判断与不可抗拒的评判标准的权威性就不受保障,权威性的减弱就会造成新思想即人性思想对于之前话语的僭越,也因此判官思想的动摇也会为我们所接受所认可。
从这两重主题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徐渭对于传统的道德标准与价值判断有所怀疑,用回归人性的思想去反思,继而探讨,甚至在剧终甚至有了某种超越,在狂生祢衡应召升天时还不免替曹操有求情的举动。祢衡道:“大包容,饶了曹瞒罢!”而判官说道:“这个可凭下官不得。”这种开放式结局引发了我们对如何客观评判人物的思考,使得这部作品在同时期杂剧中更有厚度,不仅仅限于简单的归咎与批判,而是在人性与自由的高度进行探讨与反思。
二、体制之新变
在此,所谓“新变”是指徐渭杂剧代表明杂剧对于元杂剧体制等方面的新变。《中国戏曲史略》一书对于元杂剧的体制有着很好的概括,大致特点如下:“第一,元杂剧的结构单位,以音乐曲调论是‘套,以戏曲情节论是‘折,每一折戏照例用一套曲子;第二,元杂剧每一本戏照例有四折,安排四套曲子,加上对白独白等,恰好表演一个完整故事的起、承、转、合,在情节不够连贯,或不宜用套曲表现的地方,多加一个楔子,元杂剧通常是‘四折一楔子;第三,元杂剧所用曲调为北曲;第四,元杂剧每一本戏(包括每一套曲子),照例由一个人物来唱”。①元杂剧由于结构的局限与唱法的限制逐渐衰歇,但并未完全退出戏剧舞台,后续的杂剧作家试图打破南、北曲界限,甚至把南曲引进北曲套曲中,寻求体制上的创新。明代杂剧亦有所发展,一些作家如贾仲明、朱有燉、康海、王九思等继续寻求杂剧体制上的创新。就《狂鼓史》戏剧体制而言,对元杂剧也有突破之处。
(一)一折杂剧的应用
此剧全剧都用北曲,但已经与同是用北曲创作的元杂剧“四折一楔子”的体制相去甚远,这在结构上有所突破。戚世隽于《明代杂剧研究》一书中提到:“滑稽调笑都是宋杂剧院本的一种重要标志”,“除了这种滑稽戏谑的风格,我们认为,明中后期杂剧中‘短剧的出现,也极有可能受宋金杂剧院本的影响”,“而明杂剧向宋金杂剧院本的学习,主要是由于院本的两个特点——诨体和短小,正切合了明中后期文人自由随意的表达情感的需求”。②从上述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元末明初,杂剧作家的创新更多体现在南北曲的融合与唱法的变化上,而明初以后特别是明中后期的杂剧作家们学习取法的视野更为宽阔,向宋金院本学习,这当然也是出于渴望获得最佳表达效果的需要。徐渭的《狂鼓史》对于诨体和短小这两个特点都有很鲜活的体现。在祢衡骂座的过程中,判官祢衡曹操的对话充斥着一种戏谑调笑的愤激,而这种愤激也形成一种讽刺的效果,使读者于捧腹之后又有深刻思考。《狂鼓史》在整体风格上一气呵成,相当痛快,这与作者愤激的情绪是一致的,也与作者“本色论”的文艺主张相一致。对事情原委的叙述并非此剧重点,这部剧更倾向情感的表达,过长的体制显然不符合表达的需要,那么一折剧的表达再恰当不过。
(二)叙事结构的断裂
作者在此剧中非常注重情感情绪的宣泄与表达,这对以叙事性再现为特征的传统杂剧有所偏离。虽然全局少不了叙事的因素,但其地位已经退化到为了抒情而服务,所以,整部剧起承转合的痕迹并不明显,戏剧冲突也并不强烈,整体的叙事性比较弱。《狂鼓史》整部戏剧无非是在演绎祢衡骂曹这件事情,但我们从这部杂剧中显然得到了比本来故事要少得多的迭起高潮。三个人物的对话也更为随意更为情绪化,似乎是一场热闹的谈话,每个人阐明自己观点的空间变得更大,作者通过人物想要表达出的思考也更多一些,更接近“诗言志”的表达习惯。这种抒情化的表达,使得杂剧的表演性更弱一些。
这部杂剧有个特别之处,则是在戏中演戏,戏剧作家都希望观众能够进入戏剧所设定的情景,绝不会突然跳脱破坏这种苦心经营才达到的效果,即使有此类情况,也大都是在不关键的时候跳脱出来讲述个道理,以示戒惩。而徐渭此剧在祢衡骂曹咄咄逼人乘胜追击时判官突然打断,说道:“丞相女儿嫁作皇后,造房子大了些,这还较不妨。打鼓的且停了,俺闻得丞相有好女乐,请出来劳一劳。”这样的中止,使得戏中戏的连贯遭到破坏,剧情突然跳脱出来,增添了更多戏谑的效果。这不仅打断了戏中戏的讲述,也破坏了戏剧本身的流畅,但细细想来,又是合情合理,徐渭戏谑的告诉我们刚才是戏,这种打断是现实,这就使戏与戏中戏间拉开了距离,充满了张力。这样的例子后文也有,在曹操被祢衡的追问问的实在无处躲闪时说:“俺醉了,要睡了。”而判官说:“手下采将下去,与他一百铁鞭,再从头做起。”曹操听到后很慌忙说:“我醒我醒。”判官又作调笑之语,回答说:“你才省得哩。”这又使得原本紧张的情节进行临时的缓冲,缓解了刚刚聚集起来的紧张感。这样的穿插与跳脱让戏剧变得有张力,有趣味,在戏与非戏间兼顾,十分有特色。
以上两点,都是作者为了内容更好的表达而做出的形式上的改变,这也是明代杂剧作家对于杂剧体制所做的一种体制创新,十分有意义。
综上,徐渭在叙述的过程中透露人生思考,其杂剧在主题取向上有两重新变:一则为对普遍个体生命在大时代环境下的自由与价值的探讨;二则为对于传统道德判断标准的超越。为了配合主题的表达此杂剧在体制方面也有创新:首先,为一折的杂剧,不同于元杂剧一本四折的规整体制;其次,在戏剧内部结构上造成断裂,此剧语言辛辣而协律,且甚合徐渭在论戏剧创作时所提倡的“本色论”,其本色之处堪拟元人。这些创新之处使其对后世杂剧史产生重要影响。
注释:
①余从,周育德,常静之:《中国戏曲史略》,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②戚世隽:《明代杂剧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
③李德仁:《徐渭》,吉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参考文献:
[1]余从,周育德,常静之.《中国戏曲史略》[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2]戚世隽.《明代杂剧研究》[M].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3]李德仁.《徐渭》[M].吉林美术出版社,1996.
[4]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5]王永健.关于南杂剧的几个问题[J].艺术百家,1997(2).
[6]戚世隽.明代杂剧体制探论[J].戏剧艺术,2003(4).
[7]曽永义.《明杂剧概论》[M].台湾学海出版社,1979.
[8]马晓红,张恩普.心学背景下的徐渭文学情感观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