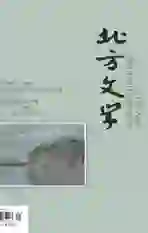民间精神的快意体验
2016-11-10张德军
摘要:莫言是中国当代作家中少有的寻根与先锋精神兼容的作家。莫言小说充斥着狂欢文化的意象个体,这种狂欢意象又通过对匪与酒的民间焦点的论述横贯其中,这些构成莫言作品的言说空间与文本内容。本篇论文以此为论述角度揭示莫言及其电影剧本的民间特质与其间透出的民俗经验。
关键词:匪;酒;莫言;民间
在近30年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莫言这位兼具寻根与先锋精神的作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存在。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透明的红萝卜》、《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四十一炮》,《蛙》等作品持续散发着诱人的艺术魅力。莫言的写作一直是中国当代作家的标杆之一,他奇特的想象力、透明的感觉、高昂的创造精神、挥洒的语言天才、以及其善于营造故事文本的韧性特质,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座丰碑,也被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称之为中国最有可能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的成功源于对故乡山东高密东北乡的持续关注、对中国人隐秘的精神世界的不断深入,其实,这种魅力的持续发散,窥其本质,乃是与“民间”这种审美体验密切勾联。世间最翻腾、最活跃,也最具现代意义、最具生活气息的场景,一定来自于民间。“作为一个在民间乡土文化浸淫中长大,后又参军在大都市生活的作家,他(莫言)又不时脱离民间叙述的轨道,表现出现代人对发生于民间大地中的人和事的看法。由此我们不仅可以触摸到中国本土民间文化复杂性的根底,而且可以体味到源于一方水土的民间艺术想象是怎样凝聚起了相对对立的诸多因素,卑鄙与高尚,美丽与丑陋,善良与邪恶等等,呈现出文本难以阐释清楚的“藏污纳垢”(陈思和语)形态”[1]。藏污纳垢无疑是陈思和对民间内容的经典概括。藏污纳垢在美丑、善恶中寻求着一种共存的文化形态与审美形态,而在莫言的小说中,因为其对民间问题的关注,对民间经验的书写,使得作为“民间之子”的莫言小说中的民间焦点便日益凸显出来。其实际是,莫言身上有着压抑不住的狂欢精神,这种精神又通过匪与酒的个体意象再现出来。匪为人,酒为物,两者都有狂欢文化的性质。“狂欢式——是没有舞台,不分演员和观众的一种游艺。在狂欢中所有的人都是积极的参加者,所有的人都参与狂欢戏的演出,”[2]其实际是这种演出的狂欢主角多有酒相伴,而“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匪性人生便是很好的民间体验状态。
一、酒:民间狂欢精神的诗意体验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酒”字时说: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从水从酉,酉亦声。吉凶所造也。酒就能因人的性格而起不同的作用。因此,酒能造人,亦能误人。但无论如何演义,酒与人是密切相连的。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是西方传统中的具有整合力量的意象。尼采曾说:“肯定生命,哪怕是在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3]这种兼具狂欢文化精神的酒神精神是西方文学的核心思维,而在中国文化中,酒虽与欢宴结伴,但有时可能也要含蓄的影射那种“借酒浇愁愁更愁”的孤独诗人之意象,这使得酒具有一种诗意的共享精神。但这毕竟是酒的一种含蓄的微小的力量。酒更多的是体验一种生命力、生殖力,创造力的世俗激情中的民间意象与民俗维度。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是有对酒的狂欢精神的持续阐述。而此后经过导演张艺谋改编的电影《红高粱》中更是将民间个体意象与民俗形式做了很好的结合,被奶奶取名为“十八里红”的酒,随着爷爷的最后一泡尿成了当年最好喝的酒,这种粗俗与雅致共存的“十八里红”,在酿酒工人高亢的“喝了咱的酒啊,见了皇帝不磕头”的抗争人格映射下,欢宴体验的氛围达到了极致。畅快应该是酒神精神的最好概括,甚至爷爷与奶奶的野合也是在酿造酒的原料红高粱地中完成。“爷爷和奶奶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的还要紧。他们在高粱地里耕云播雨,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丰富多彩的历史上,抹了一道酥红。我父亲可以说是秉领天地精华而孕育……”[4]这段高粱地里的野合如果仅仅是追求在酒壮色胆的层面上便是肤浅的停留而已。奶奶青春的肉体散发了旺盛的生命力,生殖力与创造力,虽然这里有性的裸露,但谁说这又不是生命的必经阶段呢。高粱地中的示爱,就是一种舞蹈,这种两个人的舞蹈伴随着鲜红的高粱,完成了生命的承传,谁又能说这不是狄俄尼索斯酒神情绪的沉醉呢。除了性的畅快,还与之匹配的便是余占鳌的男人如酒的爽朗性格。在小说《红高粱》中,爷爷与奶奶路上相遇,便有了这么一段描写:“路西边的高粱地里,有一个男子,亮开坑坑洼洼的嗓门,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铁打的牙关/钢铸的骨头/通天的大路/九百九十九/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从此后高搭起红绣楼/抛洒着红绣球/正打着我的头/与你喝一壶红殷殷的高粱酒”[5]这段唱词在电影《红高粱》中异常高亢,那种天地又奈我何的水浒气展露无疑,这“一壶红殷殷的高粱酒”为爷爷这种豪迈,潇洒的性格无疑做了很好的注脚,如酒的烈性又如酒的芬芳。
但是,日本人说来就来,通红的高粱被铲平,罗汉大爷被活剥人皮,反抗也就成了民众自发的行为。酒壮人胆,酒壮人气,酒再一次成为联结生命,死亡和重生的公共纽带。这种纽带要“见证在面临日本人入侵集体劳动的荣耀和关于失去的自由和独立的悲剧”[6],当酿酒工人在酒神像前排成一列,再次唱起“喝了咱的酒啊,见了皇帝不磕头”与前面形成对比的是,抗击日本人的喝酒仪式与声音充满了低沉与悲壮,这必将毁灭外族入侵的旧世界,至少在彼时彼地,也必将掀起一轮轮反抗的浪潮。新的世界便是在这种反抗中孕育着、延伸着,巴赫金曾在其关于狂欢节的概念中如此阐述:“狂欢节置身外于并且对立于所有预存的强制性社会经济与政治结构,后者都在庆典时节被悬置了……狂欢节是真正的对于时间的欢宴,是一场关于成为,变化和更新的欢宴。它排斥所有已完成的事物……狂欢节庆祝的是旧世界的毁灭和新世界的诞生。”[7]如果说颠覆和毁灭性在这种所营造的狂欢节中是一种真实存在,那么,莫言《红高粱》中对于酒的穷竭性,不可遏制、摧枯拉朽的欢宴性与悲壮性都展示的淋漓尽致。
酒在中国民间文化中体现了更多的心理,生理、地理、物理的综合元素,是在民俗文化中的不可忽视的民间焦点,世间民俗不少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狂欢性反应,直抵人的生存本相,为神、人、现实、幻象建立一种隐秘的通道。“酒”这种特殊的精神与物质兼容的客体便是这种通道的飞升之物。在《红高粱》中,民族抗争与民间精神确实以这种特殊的物质存在,将一个民族的秘史凸显出来,如此丰厚,却又如此惨烈,如此藏污纳垢,却又如此不可穷竭,正如同莫言身上压抑不住的狂欢精神。在今日人们的生活逐渐散文化,也缺乏诗意的年代,莫言小说中的酒无疑是一种诗意畅快体验。
二、匪:流氓精神的民间繁衍
匪是中国民间文化中的个性主体,是被匡出去的不一般的人。很多民间文本中将匪与流氓混为一谈。其实际是“流氓“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有着十分确定的、明晰的内涵与外延,“从语言上考索‘流氓就是《诗经·卫风》中的《氓》……该“氓”就是“流氓”的雏形,他对相中的姑娘“始乱之,终弃之”,其表现是以“蚩蚩”之貌,骗得姑娘一腔痴情,然后就“二三其德”,[8]据陈宝良《中国流氓史》称“流氓一词起源于清末之上海”,但流氓却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土壤,流氓”一词历史可梳理为春秋时的氓,战国时的游侠,秦汉之恶少年,魏晋时的无赖,隋唐之恶少,宋元之破落户,明清帮闲,青皮,渐渐演义为《水浒传》中之贼寇,又繁衍出土匪,甚至演绎为刘心武《班主任》中宋宝琦和王朔《顽主》中的顽主形象。土匪应该说更多的具有政治色彩,在民族战争的漫长历程中,国共互称为匪,匪是针对本民族另类人的称呼,而这个本民族人或是一族或是中华民族,因此八年抗战从未听到“日匪”一说。匪在民间繁衍,亦在民间蜗居,在中国“匪”具有鲜明的特征,匪皆来自农民,闲时种地,战(抢)时便杀人掠物,攻城掠地,因此匪也分多种,有劫富济贫之义匪,也有杀人越货之恶匪,就因为如此对”匪“的民间态度也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的现象,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匪,一旦民族危亡,外族入侵,匪便回到这个字形匡内,也即回到民族大义的轨道上来抵御侵略,甚至其反抗的烈度与韧性远远超出一般人。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中的各种匪便为读者演绎了一幕幕匪性人生。
莫言在《红高粱家族》的开篇这样写道:“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誉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奶奶着夹袄,送他们到村头,余司令说“立住吧”,奶奶就立住了……,余司令拍了一下父亲的头说“走,干儿”。[9]这个开头清楚地说出了父子的身份,并表述了爷爷后来所做的事。此举,爷爷匪性在《红高粱》这部电影中清晰地再现。无论是杀死劫轿人,还是高粱地中向奶奶示爱;无论是向刚酿出来的高粱酒撒尿,还是义无反顾的带领村人在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爷爷身上的通身匪气展现的淋漓尽致.
在中国这个宗法制国家中,整个社会生活中有渗透着五缘(血缘、地缘、业缘、学缘、亲缘)“借助这五缘,人们延伸和拓展了自身的能力,并组成了各自的微观社会。对于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这些身边的小社会才是真实的和现实的,社会个体成员的主要活动正是在这小小的微观社会中进行的。也正是由于无数个微观世界,才组成了整个社会的繁盛。”[10]按此说,在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下,普遍的民众是逃离不了这诸种缘的。中国社会是在传统农耕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乡土社会,在乡土的社会中,浓缩着先民“安土重迁”的人生理想与不断反省的小农意识本份,在不断畅快和活跃的小农意识中,中国人总是处在对未来充满憧憬,但又绝对安于现实的矛盾中夹缝生存,生之快乐、死之坦然、安抚自己、又在祭奠先灵,这就是乡土。在乡土的社会中是不允许离经叛道的。但是在民间总有那么一些人“不走寻常路”,他们不为别的,就为了心中的那份畅快。《红高粱家族》的叙述者是具有“民间立场”的,这也决定了其对民间价值的认同和坦荡无比、恣意豪迈、天马行空的叙述气魄,“他写爷爷杀人放火、写爷爷与奶奶在高粱地里做爱、也写他们与日本鬼子的血腥战斗以及爷爷抛弃奶奶和恋儿的婚外情和奶奶为报复爷爷投入铁板会头子黑眼的怀抱……与此交织在一起的是他(她)们健壮的体能、强壮的气魄、敢爱敢恨 ,众生轻死的民间情怀。莫言这种恣意妄为的叙述表明:他通过“血缘”为纽带所确立的民间立场、使他在认同民间的同时也认同了他的‘根”[11]。土匪就是这群“把根留住”的人,在莫言的小说中爷爷,奶奶,延及父亲这一辈都是匪性上身。由此,莫言在《红高粱家族》的题首写道:“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12]在这里用及“不肖”表达了莫言的自惭形秽,也延展在我们今天这个人情冷漠,经验缺失的时代中的我们已经更加不像我们的祖辈,他们对生命的热爱,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对自我价值的无上尊崇正是我们缺失的。他们物质匮乏、精神丰富;我们物质繁盛,精神缺失;他们不懂旧词新用、没有具体信仰,却生活有道、个性奔放、我们锐词频出、信仰松动、看似个性,却随波逐流。因此,莫言在题首的“不肖”一词真是点动后辈之七寸。奶奶在临死前说:“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叫善良?什么叫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13]在爷爷、奶奶以及山东高密东北乡的那片土地上流淌的自由精神的血液滋养了这片热土,也昭示后人前行的慢慢路程。
土匪的政治待遇如同农民起义一样总是处在当局者镇压的郁郁形式之下。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写道一个叫曹梦九县长说道:“本县长上任以来,致力于三件大事:禁烟、禁赌、禁匪、禁烟禁赌已大见成效,惟有剿匪一项,收效不大。东北乡乃本县土匪猖獗之地,本县号召良民,与政府通力合作‘通风报信。检举揭发,共致地方太平!”[14]由此,剿匪是历代政府的集体行为,然而无论怎样剿匪,这种敢爱敢恨的自在行为却总是剿不去的。在莫言的笔下匪的欢乐与苦难,表达了他对民间中国的基本关怀,对大地和故土的深情关注。
三、另一种表述:酒与匪的现代意义
单纯就莫言小说中所体现的酒神精神与匪性人生进行探讨总是有旧瓶之感,甚至过高的赞扬土匪的这种自在精神也落入对叛逆人物大唱赞歌之嫌。然而我们这个时代每天都在生产出无数的奇闻与丑闻,制造出很多的悲剧与喜剧,留下太多的忧伤与耻辱。在一个普遍压抑,人人自保又自畏的时代,畅快和热血或者曰狼性精神便成为一种必须。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总是处在边缘与主潮的矛盾更迭中,纵观现在的电视荧屏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怪异现象,往往是时代缺乏什么便流行什么小说或电视剧。婆媳关系日益紧张,《媳妇的美好时代》、《婆婆来了》等剧作便活跃;婚姻脆弱,离婚率高这边便是《金婚》,《新结婚时代》;同学关系淡薄,人情冷漠便又有了《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在这一片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背后留给我们文学评论的背影确是冷漠的,也是严峻的。这些现象凸显了我们这个和谐时代的不和谐因素,人心的被放逐,人情的荒漠化,为了追逐金钱有时不计手段,感情空白,甚至有一些人不知生活在“人世间”。
在如此的现实文化背景下,因为缺失与久违了一种精神的状态与向上活着的证据,都梁的《亮剑》、姜戎的《狼图腾》所引起的持续关注也就在情理之中。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战争题材小说的创作中,敌我双方往往处在“二元对立”的鲜明模式中,尤其是敌我指挥员的形象都是那么明显。我军指挥员,他们“通常是出身贫苦、大公无私、英勇善战、不怕牺牲、不会轻易死去、没有性欲,甚至相貌也有规定:高大英武、眼睛黑而亮、不肥胖等,” 敌军系统指挥员则往往是“喜欢掠夺财富、贪婪、邪恶、愚蠢、阴险、自私、残忍,长相也规定为恶劣、丑陋、有生理缺陷,”这两套语言系统误导了无数中国人,尤其是对恶人长相的规定上甚至三岁小儿都能分辨出何人是坏人。嘴上一撮毛、歪挎驳壳枪、长相鹰钩鼻等似乎已成为坏人的经典造型,但脱离那个革命时代功利性、政治性的宣传,放置今日这种描述又显得如此滑稽,正如民间之话“好人、坏人不写在脸上”,因此还原真实的人、人性便成了文学的需要。读者、观众希望看到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指挥员形象,因此都梁《亮剑》中的李云龙形象的深入人心,便是一种公共需求的真实反映。李云龙虽然满口脏话、脾气火爆、甚至违抗上级命令,也为此几升几落,但他能打仗、会打仗、能带兵,他是血肉丰满的、是真实的。此后,姜戎的《狼图腾》再次掀起了狼性文化,久处“羊病”困扰的国人被这部小说点动了七寸,于是骚动、沸腾……、各种研究狼,表述狼文化的书铺天盖地而来,图书市场好一派“狼来了”的迎合之声。无数的评论家赞扬我们处在一个“众声喧哗”的多声部合唱时代,然而这种热闹的背后却如朱自清《荷塘月色》中所写到的,“热闹是他们的,于我却什么都没有”。
现如今,中国每年年产上千部长篇小说,但仍然呼唤大作家,大作品,读者仍然找不到书读,这种怪异的阅读现象正如皇帝的新衣一样,一语蔽之,作者远离生活,卖弄文字,煽情,矫情,“面向市场为大众生产快餐式的‘知识和文化产品,兜售‘文化口红般的随笔散文,‘心灵鸡汤式的人生哲理和‘擅术弄权的历史故事”[17]这些作品中许多便是无病呻吟的虚伪与做作,我们今天的时代是一个“重变道、不重常道的时代,也是一个欢迎否定、无从肯定的时代。所以,是大时代,也是生命苦闷、灵魂受苦的时代”[18]因此,关心中国发展和命运的人,最好不要醉心于热炒一些空洞的理论概念,最后,笔者用四个字来结束本篇论文,“空谈误国”。
注释:
①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5页。
②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5页。
参考文献:
[1][11][13]王光东.现代·浪漫·民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58.230.266
[2](前苏联)巴赫金:巴赫金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57.
[3]尼采:悲剧的诞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354.
[4][5][9][12][14]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105.109.1.305.95
[6]朱栋霖.范培松主编中国雅俗文学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234.
[7]巴赫金:《拉伯雷和他的世界》[M].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4,410
[8]张乃良.“流氓”的魂幡[J].引自《文艺争鸣》,2005.5.
[10]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301
[15][16]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56.
[17]人民论坛杂志社.中国策[N].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1,14.
[18]谢有顺.文学的常道[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272.
作者简介:张德军(1975-),男,博士,四川隆昌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生态文学及民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