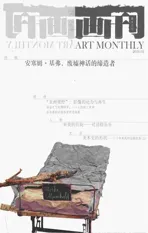蝴蝶效应
—— 亚洲实验影像联动(2009-2015年)
2016-11-01曹恺
曹 恺
影像
蝴蝶效应
—— 亚洲实验影像联动(2009-2015年)
曹 恺
缺失和遮蔽
本文指涉的“实验影像”概念,整合了实验电影与录像艺术两大艺术形态在数字时代同质化的现实,被置于媒体艺术的框架之下,成为“实验媒体”的具体化指称。从艺术分类学角度而言,亦同时波及了当代艺术与电影两大领域,是其交集中一个稳定的阴影部分。
因实验影像在当代艺术领域通过双(三)年展平台的高调曝光,而逐渐已成为具有“显学”特征的当代艺术流行样式,故此本文将着重从电影内在的方向梳理自2009年以降亚洲实验影像的基本动态。
作为一种具有西方先锋艺术内质的电影形态,实验影像因其自身的亚文化特质,一直行走在主流艺术的边缘,常常处在被遮蔽和忽略的状态——这种现象在亚洲地域内尤为显著。在20世纪漫长的时段里,实验影像在亚洲各国的整体状况一直鲜为人知。对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而言,因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实验影像在各自的缘起和发展过程中,都曾经面临过不同的境遇,呈现着迥异的生态。尤其在许多封闭或半封闭的国家里,实验影像甚至是一个长久的缺项。至于亚洲各国的实验影像的作者和学者之间的交流,也长期处在某种断断续续的割裂状态中。
改变这一状况的机缘出现在2009年,是年9月,亚洲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实验影像策展人首聚于韩国首尔,开启了第一次亚洲论坛,缺失和遮蔽的自转形态出现了变化,寻找到一个在亚洲轨迹内的公转模式,从而营造出亚洲实验影像的新气象。这一联动现象具有某种发散性的“蝴蝶效应”,在之后数年中引发众多回应,在201年5年底发生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的“亚洲视野”国际影像论坛,可以看作是这一效应的最新显现。
首尔,第一次扇动翅膀

2013年曹恺主持厦门实验影像论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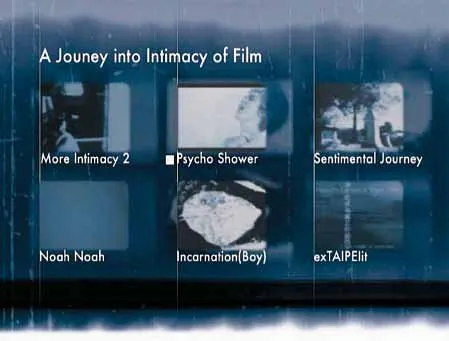
《亲密电影之旅》 吴俊辉 1999-2005年
蝴蝶效应(the Butterfly Effect),亦即“拓扑学连锁反应”,意指亚马逊雨林带的一只蝴蝶偶尔振动翅膀,或许会引起德克萨斯在两周后的一场龙卷风。这是一种意象性比喻的混沌现象,其含义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的微小变化就能带动整个系统巨大而长久的连锁反应——任何事物发展均存在定数与变数,一个微小的变化就能影响事物的未来发展。
以此来指称2009年以来实验影像在亚洲的联动现象,是一种十分有趣的比喻。2009年,在“首尔亚洲实验电影与录像节”(EXiS)上举办的首次亚洲论坛,第一次扇动了这只蝴蝶的翅膀,由此造成了之后的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先后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组织了六次亚洲实验影像论坛。
自2000年始,韩国实验电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实验影像艺术家李幸俊(Hangjun Lee)成立了“对角线电影档案馆”(Diagonal Film Archive),这是一个集放映、传播和研究为一体的实验电影机构,每年编辑出版两期艺术电影与录像的杂志《N’Avant》,并与独立电影放映厅“独立空间”(Indie Space)合作,每个月组织一次实验影片的放映,后来发展成为了一个国际电影节——“首尔亚洲实验电影与录像节”(EXiS)。2009年那次是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活动,并第一次破天荒地举办了亚洲论坛,邀请了八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策展人代表——中、日、新、马、泰、印度及中国港、台一起共同参与,开创了亚洲实验影像的联动局面。
亚洲论坛的讨论激发了许多更为积极与具体的交流计划和设想,譬如如何建立一个各地最新实验影像节目的交流网路;再譬如关于建立一个“亚洲实验影像联盟”的潜在可能性,希望让亚洲各国跨越不同的政治社会文化情景,形成一个结盟关系,互相协助,共享资源,激发整体的创作力,打开更具有前瞻性的视野。
六次亚洲论坛的联动
在2009年首尔亚洲论坛时,马来西亚实验电影人区琇诒(Sow-Yee Au)就宣布吉隆坡将筹办实验影像节。第二年,她与录像及声音艺术家郭小慧策划了“吉隆坡国际实验电影与录像节”(KLEX),在吉隆坡Annexe艺廊和马来西亚电影艺术协会正式举办,作品主要来自东南亚诸国以及更为广泛的西方国际领域。
首尔论坛之后,台湾实验电影人吴俊辉开始在台北运作第二届亚洲论坛。吴俊辉早年参与了“影像-运动”社团组织,后来,他与电影评论家刘永晧在台北世新大学培养了一批实验影像创作的后起之秀,形成了一个年轻的新艺术集群。2010年11月,吴俊辉、姚立群、刘永晧发起了“台湾国际实验媒体艺术展”(EXiT),并举办了第二届亚洲论坛,展览和论坛在牯岭街小剧场与台北当代艺术中心两个替代艺术空间举行。这次的活动在第一次亚洲论坛八个国家和地区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来自中国澳门与印尼的艺术家、策展人及学者。
在台北亚洲论坛上,吴俊辉为论坛确立了一个主题——“书写亚洲”。对此题目的释义,他提出“书写亚洲的英文题目,是从摄影机钢笔论(la)caméra stylo,camera-pen变形延伸而来,除了caméra stylo,现在又多了video stylo,所以‘笔’就广义多了”。
澳门实验影像艺术家李少庄兼具澳门牛房仓库艺术空间的策划人身份,她在参加台北亚洲论坛之后,受到启发和激励,接棒策划了“澳门亚洲实验影像活动”(EXiM),并举办了第三次亚洲论坛,时间是 2011年12月。澳门因地域和人口狭隘因素,缺少能系统地推动实验影像活动的专业组织机构,其主要实验影像创作都出自录像艺术家之手,活动的组织也落在了少数几家当代艺术机构身上,其中澳门牛房仓库就是这样的一个非营利性质的艺术机构。在牛房仓库举办的第三次亚洲论坛由中、韩、马及中国港、澳、台地区的策展人参与。在澳门亚洲论坛上,曹恺作为中国内地的与会策展人,决定了在南京举办第四次亚洲论坛的计划。
由三位新锐策展人张海涛、王泊乔、沈朝方策划的“2012亚洲实验电影与录像艺术论坛” (E E XIN),原定于2012年11月在南京大学和南京艺术学院举办,计划邀请中、日、韩、新、马、泰及中国港、澳、台等地区的策展人与会发言和研讨。但是,在万事俱备的局面下,因某种不可抗力因素,原定的活动在举办的48小时前被迫宣告终止。唯一留下的遗产,是曹恺主编的论坛图录和收入了20多篇专业论文的论坛文集。
又隔了一年,在香港城市大学30周年校庆之际,城大创意媒体学院举办了“2014·香港亚洲实验录影节”(H K E X),并组织了第五次亚洲论坛,中、日、韩、马等地区的策展人与会。策展人是媒体艺术家文晶莹,她认为“随着录像分享网站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很多非主流的、独立的和实验性录像尝试扩大公众的接触层面,并且与艺术、文化和社会相互对话,并在艺术形式方面做出不少实验”。所以,论坛的主题被确定为“掀动社会”,以展示和研究在亚洲与社会相关的实验录像作品。
自从 2012年南京亚洲论坛因故流产后,各个方面一直期待着重新启动南京计划,这一计划部分实现于2013年和2014年的两次厦门实验影像论坛,尤其是以两岸交流为主题的第二次厦门论坛;另外一部分计划则实现于2015年的“亚洲视野:AMNUA 国际影像论坛”,由新锐策展人郑闻策划,邀请了中、日、韩、马等共七个国家和中国港、澳、台地区的策展人,延续了之前的模式,成为第六次亚洲论坛。
设问与自答
亚洲论坛的持续举办,除了探索实验电影自身的历史脉络、现况与对未来的展望外,亦开始思考身处在亚洲的特殊意义。如何跨越国家与地区的局部性,与亚洲其他各国各地区进行互动、交流与合作,来联结亚洲的实验电影,并促进整个亚洲实验电影的发展,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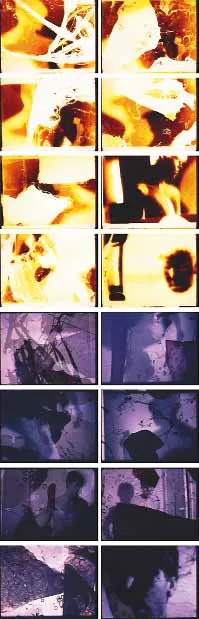
《(男孩)转世》 吴俊辉 16mm 2003年
在2009年首尔亚洲论坛开始之前,韩国策展人李幸俊就发出了八个问题作为论坛讨论的纲要,譬如何为时间性媒体艺术上的关键点问题,亚洲实验媒体情景中的历史继承问题;实验媒体教育、制作、传播和放映的关键因素问题,等等。
次年,台北策展人吴俊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更为细化的17个问题纲要,几乎涵盖了实验影像本体与外部所有能涉及的问题,包括创作、传播、教育、研究、出版、收藏等诸多方面。其中主要问题有:亚洲各国(地区)的实验影像发展的历史脉络与现状问题;各国(地区)实验影像的历史发展与表现形式上,与电影及当代艺术的关系问题;实验电影与录像艺术(新媒体艺术)之间对立与融和的关系问题;实验电影与新媒体艺术社会表现(社会意识的萌发或社会运动的发生)之间的关系问题;新科技的发展与技术的运用与实验影像的发展的关系问题。
以上这些问题,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我设问,虽然各国(地区)所面临的具体社会情景不同,但实验影像内部问题却具有许多相通性,这主要是基于其媒介特质和语言属性而造成的。而若要解释这些问题,其实更多时候是一种自我解答。
实验影像的亚洲考古
以艺术史考古学作为方法,追寻亚洲实验影像历史发生的原点,是近两年来亚洲论坛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2012年,李幸俊发送电子邮件给亚洲各位策展人,提议开始寻找亚洲各个国家实验电影的起源。亚洲实验影像确切可考的源头一般认为是在日本,山口胜弘(Katsuhiro Yamaguchi)和松本俊夫(Toshio Matsumoto)合作于1955年的《银色车轮》(Silver Wheel)成为其起点。刺言爪勾儿(Rajendra Gour)的16毫米短片《眼睛》(Eyes)制作于1967年,被认为是新加坡最早的实验影像作品;韩国的第一部实验电影是金九林(Kim Ku-lim)在1969年制作的《1/24秒的意义》(The Meaning of 1/24 Second),这也是一部16毫米影片,在当时是被作为影像装置作品展出的,后来一直以为拷贝已经遗失,直到近两年才被李幸俊重新发掘出来。
台湾实验电影的创作稍早于韩国,吴俊辉认为《剧场》杂志社在1966年与1967年分别举办过两次实验电影发表会,共发表11部实验电影作品,作者群包括了庄灵、张照堂等早期台湾的实验电影人。
但是另一种说法是两岸共有的实验电影源头,都始自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人刘呐鸥。刘是日治时期的台湾人,他主要的工作都发生在上海。刘呐鸥的电影作品受维尔托夫“电影眼”的影响很大,一些具有“软电影”性质的底片大多已遗失,他在1933年拍摄的一部46分钟的短片《持摄影机的人》却在台湾保留了下来,在近年被重新发现,列入了《台湾当代影像》一书。
一直以来,关于实验影像在中国的源头,始终被定位在张培力于1988年制作的录像艺术作品《30×30》,那是一件单镜头的录像作品,一双手反复地摔碎再黏合一块玻璃,具有鲜明的古典录像艺术样式。但胶片介质的电影系统却一直无法探寻到其开始,直到2013年,笔者通过一系列的考古工作,发掘出了第一部胶片实验电影——郝智强的《风》,一部同样完成于1988年的实验动画片,这一发现把中国实验动画的起源提前了整整12年。笔者的这一考古新论被发布于2014年香港亚洲论坛上。实验影像在香港也是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比内地稍早,以独立机构“录映太奇” 在1986年的成立为标志,早期的“录映太奇”是以研究和推广实验电影和录像艺术为主,之后又扩延到更为宽泛的媒体艺术领域。1996年“录映太奇”创办了“国际微波录像节”,影响力日益巨大。其中两个关键创始人物是鲍蔼伦和冯美华,前者作为艺术总监主持“录映太奇”20多年;后者曾在2001年策划过“自主世代:60年代至今自主、实验、另类创作”的专题,搜寻和研究香港早期独立短片和录像作品,集研究、放映和展览活动为一体。
现在是过去的未来
综观亚洲各国的历史,因各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尽相同,以及地缘版图的巨大差异,呈现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但在实验影像历史的发展上,大都呈现了一部线索不连续的残破的历史,许多时候历史以点状呈现,而缺少线性的串联。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依赖于少数在西方接受了实验影像专业教育的艺术工作者,譬如参加历次亚洲论坛的与会者中,许多人的教育背景都与两所实验电影原教旨院校有关——美国的芝加哥艺术学院(School of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和旧金山艺术学院(San Francisco Art Institute)。
在吴俊辉的十七个问题提纲里,至少有五个问题涉及亚洲实验影像历史发展问题,以及亚洲与西方实验影像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其中尤其提到面对沉重的西方实验电影历史包袱,如何寻找亚洲实验电影的位置?其定位为何?
基于此,2015年12月在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举办了主题为“亚洲视野”的国际影像论坛,“旨在以影像艺术的方式展示亚洲艺术生态与社会生活现实,以及在全球化和媒体时代中的亚洲影像艺术现状,以国际化的视野推动影像艺术发展”,来自中、日、韩、马等国家和中国港、澳、台地区的策展人与会,持续讨论了上述问题中的一部分。
作为中国近年来新崛起的高校美术馆,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开馆三年以来一直保持了对影像艺术的敏锐关注,策展人郑闻认为:“这一系列的工作也将重新定义当代美术馆的社会功能——不仅仅是影像艺术的庇护所与放映厅,同时也是观念与影像生产的兵工厂与制片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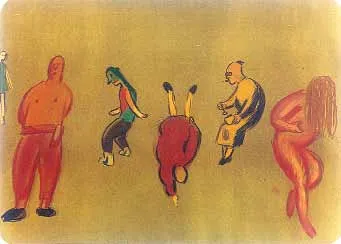
中国第一部实验动画短片《风》 郝智强 1988年
诸多海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策展人不少都有在西方欧美国家学习实验影像的个人经验,这成为其自身知识结构的基础部分。但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内地实验影像工作者的教育背景各异,知识结构也各不相同。以此次与会南京亚洲论坛的发言者为例,来自中国美术学院的管怀宾和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刘旭光都有着在日本留学的经历,接受过比较系统的实验影像理论和创作的知识系统,刘旭光对日本实验电影的历史更是深有研究;胡介鸣属于中国第一代录像艺术家,近年来转向大型录像装置艺术研究,是一位实践型的专家;高世强的创作从录像装置起步,很快转向了纯粹实验电影研究,无论从创作还是教学上都呈现了深厚的专业素养;李振华从电影策展走向当代艺术策展,同时具备了电影制片人和艺术策展人的双重身份,且更具备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思想脉络;曹恺近年来的工作以实验影像的策展和研究为主,筹划了一系列重要的实验媒体艺术论坛和活动;芬雷来自活跃于网络的青年学术机构“泼先生”,正逐步从艺术史研究转向更为专业性的影像艺术研究;郑闻作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的专职策展人,在广泛的当代艺术领域中选择了影像艺术研究作为学术突破口,主持了一系列常规化的实验影像活动。正是在这样迥异的个体知识结构背景下讨论亚洲问题,反而产生了许多新鲜而不同寻常的可能性。
一方面需要探索实验电影自身的历史脉络和源头,另一方面也都需要思考身处亚洲的现实意义,同时,也要跨越自我的限定提出对未来的展望。过去的意义可能正在现在呈现,而现在的意义或许需要未来的认定。蝴蝶效应还在持续发挥着其逐次递增的作用,在当今数字媒介技术高速发展的突变时代,未来的实验影像风暴将会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亚洲实验影像论坛的历史意义也将因此呈现出更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在任何时候,现在都是过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