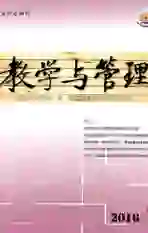语文教育术语体系构建尝试举隅
2016-10-13刘飞
刘飞
摘 要一门学科特有术语积累的数量及其运用的质量直接反映着该门学科的成熟程度与发展体势。反观我国百年语文教育,其并未形成一套独属于自己的术语体系。并且现实中的尴尬窘境迫使语文教育术语朝着统整、体系、科学、规范的方向发展。因此,以语文教育术语中的核心术语——“语文”及其类群术语为思考脚架或研究基点,尝试与期望为构建语文教育术语体系提供一个可资参详的范例。
语文教育 术语体系 语文 语文课程
一、语文教育术语研究的现实状况
1.尴尬窘境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新课改的推进,语文教育无论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是实践研究层面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其中对理论层面的相关概念术语的研究尤为突出。术语学认为,一门学科体系是否完整规范的重要标志恰恰体现在学科术语上。可以说,特有的概念术语积累的数量及其运用的质量直接反映着这门学科的成熟程度与发展体势。我国语文教育界“三公”之一的朱绍禹先生曾指出:“语文教育学科已经积累了最低限度的概念,并由概念联结成了一个具有内部联系的认识系统,这表明它在趋向成熟。但是它的部分基本概念或者被误认或者被混淆的事实,则迫使我们要下工夫,认真地给以界定。”朱老的这段论述已过去近20年,但语文教育的概念术语研究并未发生多少好转,呈现的仍是各说各家的局面。具体表现为研究者们对相关概念术语的阐释往往还是基于自己的理论话语。从阐释方法上来看,缺乏对该术语的历史考察与演进分析;从学理上来说,主观倾向过大,缺乏逻辑辨析。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已成的研究成果更多的是以零散的、不成系统的状态呈现的,形成的往往是“我认为”“我以为”“我觉得”的论断,没有从一个科学规范的角度、或者说是一个逻辑化的标准去界说。
2.迫切需要
早在2010年,蔡明先生就指出:“语文教育中概念术语的模糊和歧见,引起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诸多纷争,导致语文教育实践操作的摇摆不定。辨析和建立语文教育的概念术语,明确和累积语文教育的专业知识,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奠基性工作,必将有助于语文教育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推进。”从教师教学层面来说,是否能够正确而熟练的认识和运用一套完备而又规范的学科术语可以说是考量教师群体专业与否的重要指标。而从教育理论研究角度来看,若研究者们对相关概念术语,没有相对一致的理解,那么也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对话,这不仅有害于语文教育研究呈累进状成长,更不利于教学问题的解决和实践的改善。因此,对语文教育术语进行整合梳理,进而科学考论与界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但我国把术语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是比较迟的,而且发展过程相对有些缓慢,这也就给具体学科内部的术语研究带来一定的难度。“语文”作为我国最古老的学科(古代教育可看做是一门“大语文”教育)之一,发展演进至今,已成为基础教育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一门学科,但“语文学科里却至今没有形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共识性的语文概念,即不仅缺乏具有普遍性的科学定义,甚至没有形成便于人们使用和沟通的一般性定义”[1]。
以上种种,充分暴露出语文教育术语研究的尴尬现实,同时也体现出语文教育术语研究的迫切需要,亟需体系化与科学化——这既是一种目标召唤,也是一种应然追求。
二、语文教育术语研究的理论基础
1.“术语”与“概念”
什么是“术语”?《现代汉语词典》给“术语”下的定义是“某一学科中的专门用语”。《大辞海·语言学卷》对“术语”的解释是:“各门学科中所使用的专门用语。其意义有严格的规定性。”以上两种解释都是在强调某类词语在特定学科中的专用性。我国术语学家冯志伟从语言学角度认为“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叫做术语”[2]。相对而言,这个阐释则更加清楚地让我们认识到“术语”就是一种指称,是用特定的象征符号(语音、文字、图画等)来相应地指称某一领域内特定的“概念”。
那么什么是“概念”?哲学中一般将“概念”理解为“是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而我们平日所说的“概念”则更多地是指人们在感性和理性思辨交织下把一类事物的共同本质、特点抽象出来加以概括,从而形成现在我们所了解的“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概念”大致等同于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所说的“所指”(语言所反映的事物的概念)。换言之,如果“概念”是一个“客观存在”在人的头脑中“究竟是怎么回事”的认知表象,那么表述“概念”的语言文字符号就是“术语”。所以说,“概念”的产生是先于“术语”的,这也是为何会出现“概念术语”这样表述的原因,“术语”就是对“概念”所做的限定和命名。这样的话也就给“概念”命名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提供了可能。这一认识,一方面佐证了我们对语文教育术语进行研究的必要和价值;另一方面又为我们指明:只有对这些错乱纷杂的术语进行抽丝剥茧般的明辨与考论,才有可能显豁出这些术语背后真正的概念本体。
2.“无名”到“释名”
在一个知识领域内,如果明晰了“概念”,人们就能够准确地把握特定事物的特有属性,由之便可将此一事物与彼一事物相互区分,而不至于指东道西、南辕北辙,说话行动不得要领了。而且相类似的“概念”可依据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有机地组合成一套“概念体系”,反之,一套“概念体系”对应着一套“术语体系”,一套“术语体系”又反映了相应的“知识体系”。所以,一旦对相应“概念”进行命名成为特定“术语”后,有利于归纳并重整复杂错乱的“概念”及“概念体系”的完善与发展。而用简洁的语言去准确地解释某一“术语”的“概念”时,这就是“定义”。“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是一种人为的广泛、通用的解释意义”。综上,一个事物从“无名”到“有名”再到“释名”的过程大体可用下图表述。
三、语文术语体系建构尝试举隅
1.思索基点:“语文”及其类群术语
语文独立设科已逾百年,语文教育界对其内部相关概念术语的研究尤为突出。如对“语文”的阐释,目前界内对“语文”至少有过七种阐释,分别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说”“书面语言说”“言语说”“语言文字说”“语言文章说”“语言文学说”和“语言文化说”,此外还有“语感说”“语言文明说”等等。然而细究这些定义阐释,往往出现“概念本体”偏离或错位的现象。故为了剖离理论错乱可能给实践带来的严重困扰,必须想方设法促使语文教育术语朝着统整、体系、科学、规范的方向发展。但语文教育在其百余年的演进过程中,其术语数量是在不断生长的。在如此庞大的术语网中以谁来作为研究的脚手架或思索基点,这是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有学者指出:“语文学科教育理论必须有一个哲学基础,有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3]对语文科教育研究来说,其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无疑是“语文”。研究“语文”,实质上就是在回答“语文是什么”或者“什么是语文”的问题。王尚文曾指出:“语文是什么?实质上这是语文观的问题。有怎样的语文观,就有怎样的语文课程观……”[4]所以,对语文教育术语进行研究首先需从“语文”及其类群术语开始。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有学者总结在整个百余年的中国现当代学校语文教育中,语文课程名称大致经历了一个从“‘文学——作文、词章——中国文字、中国文学——国文——国语、国文——语文——汉语、文学——政文、革命文艺——语文的不断演绎过程”[5],最终定名为“语文”并使用至今。“以‘语文取代先前的‘国语和‘国文,应该说是一次划时代的实质性变革,绝不能看做仅仅是名称的变动或统一。”也就是说,学科名称的变化绝非随意的,其必定潜涵着某种深层次的意蕴。不同的学科名称体现不同的意蕴指向,不同的意蕴指向也就决定着不同的价值追求。但至目前为止,作为学科名称的“语文”到底指什么?其内涵与外延又是怎样的?界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语文”的澄清与明辨可能达不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但是由于她的模糊与歧见引起理论层面的诸多纷争和造成实践层面的诸多摇摆却是个不争的事实。因此,若想建构一套完善的、符合逻辑规范的、能够被大部分人所共识的语文教育术语体系,“语文”以及由之衍生出的诸如“语文课程”“语文教学”等术语应当是首需考量与厘清的。
2.尝试举隅:基于“语文”的体系构架
“我们通常说的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是学校教学的科目,是与基础教育中数学、物理、历史、地理、生物等并列的科目概念。”[6]此时的“语文”指的就是“语文科”或“语文学科”,属于“学校语文”的范畴,更多的是为了与“社会语文”作区别。但细究“语文科”和“语文学科”还是有点区别的。“科”指“学术或业务的类别”,故“语文科”强调的是一种分类意义,为了与其他科目相区别。“学科”指“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可以看出“语文学科”倾向于“学”的重要性,所以其在理论话语中大致等同于语文学或语文教育学;与前两者纠缠最多的应该是“语文课程”,“课程”意指“学校教学的科目和进程”,较之前两者多了一种安排计划的意味。“语文课程”一般意义指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对实施语文教育的一种宏观规划,是将“语文科”或“语文学科”这一知识体系转化为教学内容的实施操作系统。由于现代课程理论是将“教学”内含于“课程”之中的,因而“语文课程”较之前两者更具现代学科意义,这也是将之前的“教学大纲”或“教学纲要”置换为“课程标准”的原因。这样的话也就很容易看出“语文教学”与“语文课程”的区别与联系。前者主要是将“语文科”这一知识体系融入到具体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呈现为一种动态操作系统,并且是内涵于“语文课程”之中的。而在这些概念术语中最具统摄性的应该是“语文教育”。无论是“语文科”还是“语文学科”亦或是“语文课程”,一旦其失去教育意义,也就丧失了研究的必要,自然也就被划分至或融入到“社会语文”之中了。而“社会语文”往往是无法进行系统研究和学习的,更多的是靠自我感知和主体触发。从理论和实践角度来看,“语文教育”就是实现“语文”这一知识体系教育价值的各项要求和活动。具体到学校内部,主要以“语文课程”的形式呈现。此外,所有的不同形态、不同种类的“语文教育”最终都要靠一堂堂具体的“语文课”来实现。“课”意指“有计划的分段教学”或指“教学的时间单位”,故“语文课”就是指在学校教学实践中的一种有计划的分段教学,或者是指具体的某一堂课。如果说“语文课程”是“语文教育”的细胞单位的话,那么“语文课”就是“语文教育”实施中最有价值、最核心的功能单位。
“语文”无论是“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合称”,还是将其理解为“语言文字”“语言文章”亦或是“语言文化”等,其都不是“语文”的内在确切指称。“语文”所对应的是一种知识体系,其内涵丰富、包罗万象。学校中的“语文”主要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根据特定年龄和发展水平的学生实际需要而从多方面、多维度、多领域选择相关知识(主要是关于语言、文字、文章、文学、文化等)进行组织,使之形成科学的逻辑序列,最后以教学科目的形式呈现。在名称上往年主要是用“语文科”或“语文学科”来指代这一知识体系,目前多以“语文课程”来指代。
其中,“语文”是最上位、最核心的术语,它涵概了与“语文”有关的一切知识体系(包括语言、言语活动、言语作品等),基本上是个俗概念。“语文教育”是由“语文”顺延下来的,是“语文”进入教育视域而产生的称谓。“语文教育”从实现的空间范围来讲,它包括“学校语文”和“社会语文”,其中“学校语文”即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语文”,主要以两种状态呈现,一种是“语文科”,一种是“语文课程”。前者主要体现为静态的学科知识体系意义,与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等科目相照应,大体等同于“语文学科”;由于“课程”具有学科知识组织和实施进程的双重意义,故从实践话语来说,后者主要体现为静态课程知识加上动态实施的意义,即涵盖了“语文”作为学科的整个知识内涵体系以及在此体系下生成的各种教与学的活动。“语文课程”进入实施层面则更多的表现为“语文教学”,而基础教育阶段内的“语文教学”则是由有计划地分段分节式的课堂教学组成。
总之,建设与拥有一套较为完善的、符合逻辑规范的、能够被大部分人所共识的语文教育术语体系,不仅能够推进语文教育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完善,更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或预设语文教育的发展体势与未来走向。
参考文献
[1] 史成明.语文科本体论基础[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
[2] 冯志伟.现代术语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 陈黎明,王明建.中国现当代语文课程问题史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
[4] 饶杰腾.语文学科教育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5] 王尚文.走进语文教学之门[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6] 李震.语文走向与主流话语的百年演进[J].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3(5).
【责任编辑 关燕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