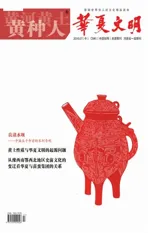关于王振铎复原司南的思路兼与孙机同志商榷
2016-08-22□李强
□李 强
关于王振铎复原司南的思路兼与孙机同志商榷
□李 强
王振铎是中国博物馆界的一名科学工作者,他的工作之一是做出中国古代科技模型,配合博物馆的历史陈列。模型,是博物馆陈列中的一种特殊语言,由于它是立体的、直观的,使观众一望而知,不费口舌,因此是中外博物馆习见的表现手法之一。它与博物馆的图表、绘画、雕塑、标本、复制品的作用一样,是一种辅助展品,配合文物,进行人文历史的陈列,供观众研究参考。他一生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做了百余种科技模型,其中大约可分三类:一、历史文献上有记载,现实生活尚有遗存的,如《农书》中所记载的农业生产工具;二、有文献记载而无实物遗存的,复原时只保留古器物基本构造和外形特征,如《武备志》中的运载工具;三、历史上确有,而后失传了,除了文献考订之外,需要加以实验的,如地动仪、指南车、计里鼓车、水运仪象台。司南的复原即属于第三种。我读孙机批评王振铎先生的文章《简论司南及司南佩》时[1],王振铎先生已作古多年,无法回答孙机同志的质疑。我感到有必要向读者重申一下王振铎复原司南的思路,以解答相关问题。
王振铎先生复原司南的思路是怎样的?这一问题要从20世纪20年代末一场中日学者大论战说起。
一、20世纪20年代中日学者关于指南针发明年代的一场争论
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右翼历史学家为了配合日本军部全面侵华,不仅加强了对蒙满历史、地理沿革的研究,同时也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创造力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目的是证明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已经枯竭。其中,有一名曰山野的日本学者,他有博士头衔,懂汉语,也能看一些中国古典文献,他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文章,涉及指南针与指南车发明的原理和发明年代,由文圣举翻译,发表在《科学》杂志第九卷第四期上[2]。他的主要观点有两个:一、指南针与指南车在制造原理上完全无关,前者为磁性原理所制,后者为机械原理所制。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二、中国在南宋以前,不知磁石有指极性。他的论据是:“指南车既为后汉之张衡、三国时代之马钧所创造,则斯时代之中国人仅知有吸铁之能力而已。彼等何能应用指极性以造指南车乎?即假使能应用,则后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代之记录中,除记磁石之引铁外,当然非论及其特征(指极性)。而何必于宋时记录中始论及其指极性(见《梦溪笔谈》),并指极性之应用(见《萍洲可谈》)乎? ”他的结论是:“宋朝以前决不知磁石有指极性也。”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现在,并影响到台湾,日本的《大汉和词典》与中国台湾的《中文大词典》便不采用磁勺说。
当时被称为“清华三杰”之一的历史学家张荫麟先生(1905—1942),立即发表题为《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作者》一文,进行反驳[3]。指出山野博士“实铸一至少差千余年之大错”! 山野博士“在史学方法上,是妄用默证”。他指出:“在事实上论及磁之指极性者,实不始于宋代;至迟在后汉初叶,关于磁之指极性已有明确之记录。王充《论衡·是应篇》有云:‘司南之杓,投之地,其抵南指。 ’《说文》:‘杓,斗柄也。 ’段注:‘斗柄,勺柄也。’观其构造和作用,恰如今之指南针。盖其器如勺,投之于地,杓柄不着地,故能旋转自如,指其所趋之方向也。”
接着,张荫麟先生进一步指出:现存关于指南针之明确记载,始于后汉初叶,而指南针之出世,则未必即始于此时。细玩味《论衡》之文,毫不暗示司南之杓为当时之最新发明。而先秦之载籍,屡有关于司南之记载。《韩非子》:“先王主司南,以端朝夕。 ”《鬼谷子》:“郑人取玉,必载司南,为不惑也。”《鬼谷子》一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世疑其伪,然不能确断其非先秦之作也。又今本司南之下,有“之车”二字,《宋书·礼志》无之。予按当以《宋志》为可据。从文法上观之,唯《宋书》所引为可通。司南为动词,载之宾词,若其为车,亦何须受载?此等处之司南,其为利用磁之指极性之指南针欤?抑或利用机械构造之指南针欤?以吾观之,前一说或然性为较大,其理由有三:一、如上所阐明,《鬼谷子》所言之司南,既属能受载之物,当是微小之器,绝不能为庞大之车驾;二、战国末叶既习之磁石之吸铁性,学者随意举为譬比,见《吕氏春秋》及《鬼谷子》,可见磁石已成为极普通之物,则当时兼知其指极性,也属极可能之事;三、东汉初叶之前,已有司南之名,已知磁之指极性,唯独无记载利用机械之指南车,并且无指南车之名。似其时人不知有此物者,吾人今日作此言,固可谓受载籍残缺之限制,然梁代博学多闻之沈约,在《宋书·礼志》已云“至于秦汉,其(指南车)制无闻”矣。若夫黄帝作指南车以御能作大雾之蚩尤,若夫周公以指南车赐迷失道路之越裳氏,此等神话,始见于晋崔豹之《古今注》,后一事虽不如前者之荒诞,然一千数百年后之孤证,谁能信之?总结上文,利用磁石之指南针,当已出现于秦汉之世,而利用机械之指南车之发明,反在其后。
这场中日学者之战,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被后来学术界所继承,这倒不是因被中国学者的民族主义情绪所至,实在是为张荫麟先生的史识和史才所征服,为他的考证细密和谨慎所宾服。张荫麟先生有发复之议,一扫唐宋腐儒俗见;只惜其英年早逝,没有成为我国史学界领军人物。本文介绍这些指南针研究的历史背景,说明指南针发明于战国、秦汉之说,始作俑者并非王振铎先生,而是张荫麟先生。本文介绍这场中日学者之战的目的之一,在于从这面历史的镜子里,可以看到王振铎先生和孙机同志各自的观点、立场、方法。

指南车(模型)
二、关于指南车发明的年代
考证指南车发明的年代,是判断指南针是否发明于先秦和秦汉的关键。依孙机同志观点,唐人注释的《韩非子》和《鬼谷子》两书中,注解司南为指南车是正确的;并且他自己根据新发现的资料,考证出王充《论衡·是应篇》中“司南之杓,投之地,其抵南指”中的司南,也是指南车。对此问题,人们不禁要问:唐人也好,宋人也好,这些注家距战国、秦汉已长达一千几百年之久,对于指南针与指南车两物的“名”与“物”能否对上号的问题,究竟研究过没有?如研究过,其结论是否正确?如果没有研究,仅仅是因为“早”,那是不足为据的。事实是,唐人宋人,根本没有研究过这一问题。宋人金履祥撰写的《通鉴前编》一书说:所谓(指南)是“车上,用子午盘以定四方”[4],由此可见,宋人在《梦溪笔谈》发表之后,在此问题上混乱的程度。
应当指出,在近代,继张荫麟先生之后,真正对指南车发明的年代及发明人进行认真考证的,是王振铎先生。王先生在1934—1935年对指南车、记里鼓车复原的同时,对指南车发明的年代及发明人,进行过细密的考证,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把他绘制的《历代制造指南车之人名表》复制出来,进行讨论。

《历代制造指南车之人名表》
依孙机同志见解,为了说明指南车发明于战国,对晋崔豹《古今注》这份材料,给予最重要的寄托。他认为 “对指南车说的尤为清楚,难以作其他解释”的一个论据,是这段材料:“大驾指南车,旧说周公所作也。周公治致太平,越裳氏重译来贡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大夫宴将送至国而旋,亦乘司南而被其所指,亦期年还至。”这其实是所谓“旧说”,是《今本古今注》其中的一种说法;孙机同志借此说明指南车发明久远。另外,《今本古今注》还有一种“新说”:“指南车起于黄帝之与蚩尤战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士皆迷路,故作指南车。”但是,无论今本也好,古本也好,自古以来,《古今注》一直就被历代学者看作是一部伪书,见《说郛·卷十》;近人黄眉云也有论述。这一公论也写进辞海里:“《古今注》,书名,晋崔豹撰,附《中华古今注》三卷,五代马缟撰。二书皆考证名物,而文相同者十之九,不过次序稍有先后,字句偶有加减。《四库提要》谓与《永乐大典》所载《苏氏演义》亦同五六,疑豹书出于后人所伪托,缟书也袭苏书而成。”苏书,是指唐人苏鹗的《苏氏演义》。依《四库提要》的观点,豹书出于缟书,缟书出于苏书,都是唐人的观点。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认为《古今注》与《中华古今注》两书非伪。该书真伪问题,这里姑且不论。但是我们发现,在这里有一个有趣而又奇怪的现象:一个历史故事传播得愈久远,编造得愈精细,愈神灵活现。以周公造指南车的故事为例,故事最初出自《尚书大传·归禾》:“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慑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恐使之不通,故九译而朝。”此处,仅说周公如何怀柔远人,其文并无指南车之语。《汉书·王莽传》记王莽自比周公,有这段关于怀柔远人故事的对话:“太后乃下诏曰:大司马新都侯莽,三世为三公,典周公之职,建万世之策,功德为忠臣宗化流海内。远人慕义,越裳氏以三象重译献白雉。其以召陵、新息二县,户两万八千益封莽,复其后祠,畴其爵邑。莽复奏曰:太后秉统数年,恩泽洋溢,和气四塞,绝域殊俗,靡不慕义,越裳氏以三象重译献白雉。”也不言周公赐指南车之事。到了《古今注》,便增加了新内容:“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译来献,使者迷其归路,周公赐车五乘,皆为司南(车)之制。”到了《今本古今注》,内容更加丰富了。使者贡品增加了新品种,并且有了详细数目;周公赐品也增加了新品种,更有数量和质地的准确描述:“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译来贡,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归路,周公赐以文锦二匹,车五乘,皆为司南(车)之制,使越裳氏载之以南,缘扶南林邑海际,期年而致其国,使大夫宴将送至国而还,亦乘司南而背其所指,亦期年而还。”再到《中华古今注》,周公造指南车的故事仍嫌不古,一股脑儿把它推向远古时代,终于出现黄帝造指南车的神话。由此可以看出,从两汉到晋唐,周公怀柔远人的故事在注家笔下,离时代愈远,水分愈多,为了推崇正统儒学,排斥玄学,不断增溢升华,把后来发生的事情迁移到前代,甚至推到远古时代。故事情节愈来愈复杂,离原来史实愈来愈远。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拂去浮尘,必须采用层层剥笋的方法,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于是王振铎先生将历代周公怀柔远人的故事做成表格,按时代顺序排列,揭示出崔豹增溢的水分。晋人崔豹所处年代离三国的马钧并不远,却将马钧造指南车的事迹,套在一千多年前的周公身上,说明崔豹对指南车性能十分混沌;“车五乘,皆为司南 (车)之制”,尤其说明对两车结构极其茫然;究竟是车底座下面设有指南的齿轮机械,还是指南车上树有屏蔽设备,横棱两可;指南车仅为卤薄仪仗所用,绝无实用的功能,更无送荒外远人的可能性;更何况一制作,便是“五乘”之多;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情况下,一下子做出五辆指南车,此话近似梦话。综合地考察这段注释,可知崔豹的增溢:一、不知指南车的具体结构;二、不知它的真实功能;三、夸大使用指南车的数量;四、将不久前创制指南车的事情迁移到古代。这才是在注释的幌子下,真正“添油注水”,粉饰了历史,从而脱离了历史的基本事实。由《古今注》这段史料推论指南车发明于战国时代,实在是荒谬。由此看出,孙机同志对“五四”以来古史辩派的工作方法,很不熟悉,故将古史中增溢部分当作史料加以使用;另一方面,孙机同志很推崇二重证法,又无法使用二重证法证明战国时代已有指南车。其实,从战国文献里,检索不出任何有关指南车的蛛丝马迹,从田野考古的战国文化层里,也找不到任何有关传动齿轮的遗迹。如何让人相信崔豹所增溢的那段神话呢[5]!
在汉代,两汉书并没有指南车一语,只是在晚出的《魏书·杜夔传》里,才有高堂隆与秦朗关于指南车古有、古无的争论,王振铎先生谨慎地指出,晚出的书姑且不论,因为是孤证,汉代有指南车证据不足。有史可证,真正创造成功的是三国时代的马钧。从此表还可以看出,指南车发明以后,反复失传,到了辽金以后数百年,其制无闻,说明指南车在制作原理和制作工艺上,有很大的难度。指南车是由一组齿轮系组成的机械构造,已知最早的齿轮系机械构造始见于东汉张衡制造的水运浑天仪[6]。就精密而言,指南车比水运浑天仪的水运机构还要复杂,各轮的齿数多一个、少一个,都直接影响最终的结果。把这种难度很大的发明放到战国时代,不是弄乱了科技史中的前后次序么?晋以后的学者,都有这一毛病,对于马钧发明的指南车的工作原理和工艺,无法用语言加以描述;而执史之吏,又不求甚解,只好附会成说,猥习相传。《宋书·礼志》引《鬼谷子》原本只有“司南”二字,而今本《鬼谷子》于“司南”二字之下,又加“之车”二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再以唐人事迹为例。唐初,据《宣和卤薄记》记载,朝廷的仪仗中尚有指南车的遗存,只是因为有残缺,不能使用。“将作大匠杨务廉性巧,奉敕改作,终不能至”。作为当时工程技术最高长官且有巧思的人,尚且不能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补缺,唐代文人却将这一工程技术推移到周公时代或新石器时代,谁人信之?可见这些没有科学知识的唐代注家,不动脑筋,糊涂到一定程度了。能把这些注家的解释当作信史来读吗?仅依从唐人、宋人注作为自己的立论,站得住脚吗?正如梁启超所常说的“尽信书倒不如不读书”。
司南发明在前,指南车发明在后;在没有指南车的时代,作为一种辨向工具,司南这种如勺形之器,投之于地,能旋转自如,其柄可指所趋之方向,它不是一种磁性体的指向工具,又会是什么呢?
有了具体的指南器物,才会有作为一般抽象的指南或司南用语。如刘勰《文心雕龙》:“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杨齐宣《晋书·音义序》:“足以畅先皇旨趣,为学者司南。”李商隐《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为九流之华盖,作百度之司南。”都是作为一般抽象的指南或司南用语引申而来的。层累地缔造指南车与指南针的历史,才能使其史坚实可信。
三、关于磁石指极性的认识
日本的山野博士在20世纪20年代末,因中国人只知磁石吸铁而没有磁石指极性认识的记录,就否定宋以前有指南针。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术界开始活跃起来。吉林师范大学的物理教师刘秉正先生一以贯之,早在1956年就对司南提出异议[7],1986年又从一般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再次提出同样的问题[8]。杭州大学的王锦光、闻人军则考证“投之于地”的“地”为“华池”,也就是水银池,认为司南勺应浮在水银上,并做了复原实验[9];南开大学的刘洪涛认为战国时代的司南是车上的圭表[10];中国科技大学的李志超,也对王充那段话重新做了解释[11]。故宫博物院的罗福颐先生,则认为司南是一种式盘。据说这是他酝酿十年,在1981年弥留之际口授修订定稿的力作。他指出汉代的地盘屡有发现,绝不见磁勺出现;同时王莽时代的勺型,在晚周也罕见[12]。诸家从各自角度,就司南一解,提出各种新的复原方案。这些议论中,除了罗福颐先生和孙机同志外,大都是搞自然科学出身的。
为了说明王振铎先生的研究思路,事情要从两头说起。
在指南车发明之前,依 《韩非子·有度篇》:“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鬼谷子·谋篇》:“郑人取玉,必载司南,为其不惑也”、《论衡·是应篇》:“司南之勺,投之于地,其柢指南。”是根据磁石的性质对司南这一器物进行推理,说明这种辨向器物只能是磁性体,别无它属。这是由于磁石本身性质所决定的。这是一头。另一头,我们细审沈括笔记余韵。他在《梦溪笔谈》里一下子记录了指南针的四种做法,如碗唇法、屡悬法、水浮法、指甲旋定法,他暗示:第一,这些制法不是自己发明的,他在这一条目下,只是一个记录者;第二,也不是自己周围人的发明创造;第三,是因袭方家的做法,记录而成;第四,究其指南原因,方家不知道,沈括自己也不十分清楚,只是说:“磁石之指南,犹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13]当然,沈括不可能真正知道磁石指南的确切原因,直到19世纪人们才知道地球是一个磁场的事。宋人程棨也暗指指南针为阴阳家所专用,并说:“针常指南,偏丙位,是因为丙为大火,庚辛金其制,故知是物类感耳。”[14]他在这里将五行学说与物类相感结合在一起。这里说的方家也好,阴阳家也好,都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道家学派的一个支流,自战国、秦汉以来一直脉脉相传,屡屡不断。他们的宗派复杂,活动诡秘,或精于卜巫、占验、星象,或精于医术、炼丹、采药,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今日的天文、历法、化学、病理、医药等科目的知识,皆在他们手中掌握;他们的知识很少为封建社会主流派文人所注意,所记录;对于他们的剞技淫巧,尤为唾弃,不屑一顾;主流派文人所注意的重点,仍在于经义的阐发、章句的取舍。因此可以说,制造指南针的记录始于北宋,制造指南针的时间就可能往前推移。以西汉为例,方士栾大设棋局迷唬武帝:“取鸡血杂磨针铁杵,和磁石头置局上,即自相抵击也。”抵,相斥也;击,相吸也。这说明这位玩弄雕虫小技的方士栾大,在这类魔术中或许已经知道同极相斥,异极相吸的原理,这一原理也是磁石最重要的性质之一。可是古人从来也没有将此类事记录在案。同样道理,《鬼谷子》已有“若磁石之取针”之语,针受磁之后获有指极性,古代文人也可不录。《淮南万毕术》中有“磁石悬入井,亡人自归”的说法,不管它是属于方家术士的咒语也好,也不管其磁石形状如何,是否便于携带使用,能将悬空磁石的前提与迷途知返的结局形成因果关系,便暗示了磁石有指向性的知识,只不过没有就此问题展开叙述罢了。我们还会看到,我国古人有一个明显的思维特征,即当他探讨到事物本能和本性时,便不再继续深入探讨了。“磁石之指南,犹柏之指西”,也属此类。由此,张荫麟先生所说战国、秦汉之际,举“磁石吸铁”之例为常譬,磁石指极性虽无具体描述,也为古人可知的观点,是完全可以成立的。王振铎先生正是在这一认知的基础上,进行对司南的复原。
四、关于司南的复原
依据张荫麟先生的研究成果,考证了指南车产生的确切年代及发明人,王振铎先生确认了历史上确有其物之后,这才开始了模型的复制工作。
王振铎先生在复原过程中,将司南模型分为两部分。一是磁勺,按传统手工艺用磁石雕琢而成;另一是地盘,用以判断磁勺所指方向的工具。这不过是进一步将张荫麟先生的研究成果具体化而已。我国自秦汉以来,在地理分向中,形成由八干、十二支、四卦组成的二十四向定位法,这是在盖天、阴阳、五行说影响下的产物,汉晋以来堪舆、相宅、相墓都以此为准。由此,地盘选用了汉代式占盘。古代从盖天说的天圆地方出发,以地盘为方形;在航海实践中,方形地盘不实用,所以将二十四向书写成环形,盘也由方变圆。由此可以看出,地盘原本是罗盘的祖形。
司南复原实验是分两个步骤进行的。
司南复原实验的工作首先是在四川南溪李庄进行的,这个小镇是在八百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难以找到的地方,是在战争环境里进行研究的,因此,一切工作只能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开展。案头工作和一些简易的实验,如(1)司南体型的选定;(2)古代司南制法的推测;(3)五种古勺重心稳定性实验;都可以在李庄进行。而司南模型的制作设计和实验,却要分两步走,这是因为在李庄:第一,无法找到有一定磁力的磁石;第二,也没有合适的玉工和相应的设备。恰好“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中央研究院”、同济大学相比邻,可以借用高校和研究院的设备,对钨钢做的勺进行磁化,来做磁勺的指南的实验。做这个实验基于这一认识:人造磁铁与天然磁铁在显示磁性方面只有强弱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差别。目的是要考察磁勺在拨动后,它的磁顽力是否能够克服它底部与地盘的静摩擦力,在其静止时,其柄是否可以指南。不做这一实验,是无法得知它的确切结果的。与此同时,也与近代指南针相比较,司南的指极性肯定比近代指南针差,但究竟差多少,还要看具体数据如何。此外,决定司南指向的准确性,除了磁力强弱以外,还有诸如司南的器形、勺体的重心问题、勺体底部的光洁度、地盘的质地等,都需要在实验中来加以证明是否可行。这是第一步。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做这个实验。在做这项实验之前,还为此做了一组准备性的实验,即在半球面玻璃器皿上,置放钨钢为基体的“人造条形磁铁”和为云南所产天然磁石又经传磁后而赋磁性的条形磁铁。实验的目的,也在于这些条形磁铁的磁顽力,能否克服球面体与地盘的静摩擦力而呈现出指极性。为什么要用云南所产的天然磁石进行传磁,因为此种磁石磁性很小。
在王振铎先生的论文里,将第一次实验称人造磁铁在地盘上做拨动实验,命名为“磁性体司南模型之初步制造”。记住这一点很有必要。第一步,这一实验是在1945年10月李庄进行的。实验报告附录在文章的正文里。第二步,是于1947年8月在南京进行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复原到南京,他在万难中找到天然磁石,用传统工艺制成磁勺,进行了实验,其结论写在《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正文后面的补记里。两次的实验结果基本相符。他说:“拙论上篇之司南初步实验,为在川、滇后方时完成者,今夏去北平工作之便,在万难中购到磁县运到之磁石,矿石面夹杂石榴石,小块者尚纯净,而赋磁性,请玉工依旧法洗机琢珑为司南,以施工手续观之,较解硬玉为简,而易于破裂,信其硬度固较硬玉为低也。在施工实验中,并得一宝贵之证明,为赋天然磁性之磁石,用洗机琢珑为勺形之司南后,其磁性并不因洗机之施工手续而完全消失其磁性,而在理论上必因洗机之连动摩擦而减退,此种勺形之司南,惜无合宜之量磁之仪器,用测其磁性,然吾人藉施工前后之记录得到一结论为:赋天然磁性之磁石顺其南北极向,而用中国旧法琢玉洗机琢珑为司南后,置于地盘上投转之,而仍赋有较强之磁性,因其仍具有指极性之表现,其勺首指南,同前文所述借人工磁铁传磁所制司南表现之功用全合,故根据实验推想古人所制司南之方法,就天然磁石琢珑为最直接而简易也。”这前后两种实验,虽然条件不同,目的也不完全相同,但都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因地制宜完成的。令人惊奇的是,孙机同志只提第一种,不提第二种,而且对第一种实验的目的,也进行了曲解。
五、孙机同志故意扭曲了王振铎先生的原意
王振铎先生上述文字,孙机同志显然看过,有其引文为证。1987年林文照教授重新做了天然磁体司南的定向实验,并发表了报告数据[15]。与此同时,又重新申述了王振铎先生在补记中的结论,孙机同志显然也看过,也有其引文为证[16]。然而孙机同志置白纸黑字于不顾,将王振铎先生的实验过程编造成如下的样子:
王振铎先生根据他的理解制作的 “司南”,是在占式的铜地盘上放置一个有磁性的勺,此勺当以何种材料制作?他说:“司南籍天然磁石琢成之可能较多。”可是天然磁石的磁矩很小,在制作过程中的震动和摩擦更会使它退磁,这是一个不易克服的困难。王先生于是采用了另两种材料。一种是以钨钢为基体的“人造条形磁铁”,另一种是“天然磁石为云南所产经传磁后而赋磁性者”。汉代根本没有人工磁铁,自不待言;他用的云南所产天然磁石也被放进强磁场里磁化,使其磁矩得以增强。这两种材料均非汉代人所能想见,更不要说实际应用了。而后来长期在博物馆里陈列的司南中的勺,就是用人工磁铁制作的。
从上述评论可以看出,孙机同志没有“仔细”阅读王先生原文:第一,他竟然“不知道”王振铎先生司南复原实验分两个步骤这一基本事实;第二,他“不理解”王振铎先生在半球面玻璃器皿上,置放钨钢为基体的“人造条形磁铁”和为云南所产天然磁石又经传磁后而赋磁性的条形磁铁的实验目的,其实是考察这些条形磁铁的磁顽力能否克服球面体与地盘的静摩擦力。如上所述,制约勺首指南的因素很多,除了磁力强弱以外,如司南的器形、勺体的重心问题、勺体底部的光洁度、地盘的质地,都需要进行实验来加以修正和调试。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只能用人工传磁的办法,别无他法获取磁体;第三,他没有弄清王振铎先生原文也罢,也不至于曲解人家的原意,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段,愚惑读者。由此他下了这样的结论:“他动用了几千年后才出现的技术和材料济其复原之穷。违背了进行此类工作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他先是曲解和肢解人家的原意,然后再批评人家。人们只要认真核对一下王振铎先生的原文,便一目了然。
细审孙机同志文章所引的文献,绝大多数是前人用过的材料;在使用关键史料时,如《鬼谷子》《古今注》时,无视版本的选择;但只有一条,是人们很少使用的,被他发现了,即1921年从清内阁档案拣出的宋残本 《论衡》,其中《是应篇》中“司南之杓”的“杓”作“酌”。他说:“通行本中作为王先生立论基础杓字,其实是一个误字。”而他将作为名词的“酌”,训为动词的“行”,将“柢”解释成“碓衡”,再将这一“碓衡”,解释成“一段横木”,绕了一个大圈子,最后将这“一段横木”,判断成汉代指南车上的一根指向南方的“横杆”。读了这段文字,使人如堕五里雾中。世人尚不知汉代指南车究竟是何等模样,其机理如何,也无人对其复原过;假设有其物,也不会是宋代指南车的样子;这“一段横木”究竟如何安排,恐怕连自己也说不清楚。
关于《论衡》的版本,宋、元、明三朝官刻共刊行十三版。第一版是宋庆历五年杨文昌定稿版。第二版是宋光宗年间刊行,是庆历五年版的翻版。第三、四版是在元朝至元年间刊行。明朝共刊行九版,其中最著名的两种版本是嘉靖十二年的通津草堂本和万历二十年的程荣校勘的汉魏丛书本。这两种版本都以宋庆历五年杨文昌定稿版为蓝本刊行的。从清内阁档案拣出的宋残本《论衡》,根据其行文避讳字样,推测是宋熙宁以前的刻本,的确比宋庆历五年版早若干年。但是,孙机同志没有看到宋残本《论衡》发现者,在台湾历史博物馆丛刊第二册载文《馆藏宋本论衡残卷校勘记小序》里,是这么评价这部残本的。序文说:“爰取通津草堂本校勘同异,其间脱误补填,逊于通津本者所在多有。以其为古本,聊复刊布,以俟好古君子详之。”为什么馆藏宋残本不如通津本?盖因通津本以宋庆历五年版杨文昌定本为蓝本刊行。前进士杨文昌从年轻时就醉心于《论衡》一书,他搜集了当时能看到的七种私刻版本,发现这些版本 “篇卷脱漏,文字蹐驳,鲁鱼甚众,亥豕益讹;或首尾颠踬而不联,或句读转易而不纪”,“余尝废寝食,讨寻众本,虽略经修改,尚互有阙遗。意其誊录者误有推移,校勘者妄加删削,至条纲紊乱,旨趣乖违。傥遂传行,必差理实。今研核数本之内,率以少错为主,然后互质疑谬,沿造本源,讹者译之,散者聚之,亡者追之,俾断者乃续,缺者复补。唯古今字有通用,稍存之,又改正涂注。”由于杨文昌的精校,使得宋庆历五年版本远高于从清内阁档案拣出的宋残本,这也是宋残本“逊于通津本者所在多有”的原因。由此证明了戴东原那句名言:“宋本不皆善,有由宋本而误者。”孙机同志以宋残本匡正善本,逆行而为,违背了治学的基本原则。
其实,馆藏宋本《论衡》残卷中的“酌”字,即古写的“勺”字。宋以后已不使用这一古字。按《说文》:“酌,盛酒行觞也。”这里说得很清楚,是汉代一种打酒挹注的工具;从字的造型来看,也能看出问题来。觞是酒器,按《韵汇》:“酒卮总名。”这里的“行”,就是“提取”或是“打”的意思。此物俗称“提斗”,是用竹管裁成斗形,按上直臂提杆,从酒瓮里提取酒后,注入饮酒器具里的工具;过去打酱油、打醋,也用之,现一律改用液压器衡量。斟,也是一种打酒用的工具,《说文》:“斟,勺也。”因此“斟”与“酌”可以互训。由于“斟”与“酌”在容量上还是有差距,是使用“斟”,还是使用“酌”来打酒,总要事先想一想,于是“斟”与“酌”连用,“斟酌”二字便引申为“思考”的意思。久而久之,人们只知道“斟酌”是“想一想”的意思,却忘记了它们原本是瓢、勺之意。按《礼·内则》:“十三舞勺”,注:“勺与酌同。”《正字通》:“酌,亦省作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刘盼遂先生在《论衡集解》将“酌”字从“杓”,不仅有版本的根据,校勘也高人一筹[17]。孙机同志没有认出这个字的本义,并说成“误字”,是否能够再“斟酌”一番,仔细想一想呢?因为一心一意想与指南车挂钩,便不顾词的本义,往旁处推演了。
顺便讲一讲做学问的规范。做学问,不仅要列出与自己立论有利的史料,也要举出不利的史料,以便使读者有判断是非曲折的思考余地。例如王振铎先生在论述王充《论衡》条款里,就举出明刊本有“司马之勺,投之于地,其柢指南”的说法,以备读者另行查考。像孙机同志这样考证“酌”字的用法,就远离了学术常规,误导了年轻学者。其实,以“酌”字训“行”,也可自成一说,但首先应指出它的本意,让读者有判断的空间。这才是做学问的态度。
在博物馆的具体日常工作当中,出土文物、后人复制模型、馈赠礼品是三种不同属性的事物,不容混淆。孙机同志所说的“长期在博物馆陈列的司南中的勺,就是用人工磁铁制作的”。此话不属实。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中的通史陈列里,从来就没有,也没有必要使用人工磁铁制作的模型来做展示。为了慎重起见,从1959年建新馆时的通史陈列起,一直到近年的历史陈列,司南模型从来没有在战国段或秦汉段展出过,而是陈列在宋元段的玻璃柜子里;也不是将其独立陈列,而是作为宋代出现指南针之时的引言,以备观众参考。王振铎先生之所以保持谨慎的态度,是因为模型不同于文物,仅作为辅助展品展出,保持了一个科学家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部新老同志有目共睹,无须我多言。倒是孙机同志自己经常将这三者混淆起来。例如,他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里,便将出土的圭表、漏壶、日晷与王振铎先生复原的地动仪模型、司南模型,放在一起,加以讨论。那能讨论出什么名堂来?这些器物是真假的问题,还是对错的问题,很难加以评论。所以那本书便有体例上的毛病。说到馈赠礼品,也是博物馆工作者经常遇到的问题。礼品是示意性的,又需要包装,因此作为旅游纪念品或馈赠礼品,采用钨钢电流传磁或直接采用具有磁性的镍钢,那也未尝不可,但不可与复原模型混为一谈。至于说到王振铎先生的模型只宜称“造型”,不宜称作“模型”,不知是何道理。“造型”和“模型”在语义上究竟有多大差异,也很难说。但从孙机同志文章整体来看,似乎历史上并无司南一物,完全是王振铎先生一手“创造”出来的,这也算是孙机同志一说。
中国历史上的发明创造,有许多是发明者仅做成一件,如地动仪、浑天仪、千里船、马上刻漏、十二辰车等。制造这些器物也未必一定要当作陪葬品放在坟墓里,等待后来的考古学家去发掘,来加以证实。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那种
以出土文物作为印证古物有无,就没有多少说服力了。这恰好说明我们博物馆研究者与田野考古研究者,对研究历史问题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如何复原这些器物,只能凭借科技史家一步步推理进行,但要达到原创者的模样,绝无可能。人们研究的历史成果只能逼近历史,却不能重新进入历史,这是因为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因此王振铎先生的模型也并非是最终研究结果,随着新资料的出现,还要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司南的情况也是这样。
注释:
[1]孙机:《简论司南及司南佩》,《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 4期。
[2]文圣举:《科学》9卷4期,1924年第 4 期。
[3]张荫麟:《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作者》,《燕京学报》,1928年第3期。
[4]宋·金履祥:《通鉴前编》,转引《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作者》。笔者按,金书全名为《资治通鉴纲目前编》,计十八卷,举要三卷。
[5]王振铎:《指南车记里鼓车之考证及模制》,《史学集刊》1937年第4期。
[6]刘仙洲:《中国在传动机械方面的发明》,《机械工程学报》第2卷第1期。
[7]刘秉正:《我国古代关于磁现象的发现》,《物理通报》1956年第8期。
[8]刘秉正:《司南新释》,《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 1期。
[9]王锦光、闻人军:《司南新考和复原方案》,(未定稿)1987年。
[10]刘洪涛:《指南针是汉代发明》,《南开学报》1985年第 2期。
[11]李志超:《王充司南新解》,《自然科学史研究》2004年第4期。
[12]罗福颐:《汉栻盘小考》,《古文字研究》1985年第11期。
[13]罗福颐:《元刊梦溪笔谈》,文物出版社,1975年。
[14]转引王振铎:《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
[15]林文照:《天然磁体司南的定向实验》,《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4期。
[16]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
[17]刘盼遂:《论衡集解》,中华书局,1959 年。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责任编辑 赵建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