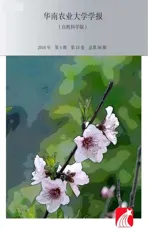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与城乡发展一体化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2016-07-19李顺毅
李顺毅
(贵州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与城乡发展一体化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李顺毅
(贵州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随着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集中程度不断提高,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呈现“倒U型”变化。与过度分散或过度集中的城市体系相比,结构相对协调的城市体系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而且,在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集中程度与城乡一体化水平的“倒U型”关系会得到进一步强化。在结构上过度分散或过度集中的城镇化战略都将更明显地抑制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而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路径更有利于促进城乡一体化。
关键词:城市体系; 规模结构; 城镇化; 城乡发展一体化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快速发展,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增长到2014年的54.77%。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世界城镇化率由30%提高到50%平均用了50多年,而中国仅用了15年[1]。然而,在高速度的同时,中国的城镇化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就包括城乡发展的不协调。近几年来,尽管城乡差距有所缩小,但2014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仍为2.92,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之比为2.38。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协调互动和一体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因此,如何在未来的城镇化进程中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就成为一个值得深入分析的问题。
城镇体系的规模结构布局是城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体系规模结构是指一个区域内不同人口规模的城镇(即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分布状况。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城镇化战略决定的,另一方面它也会通过影响城乡之间的联系对城乡一体化程度产生影响。因此,分析和检验城镇化进程中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与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关系,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城乡一体化影响因素的认识,而且对于制定有利于有效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面对城乡发展的失衡,城乡一体化问题已受到研究者高度关注,在城乡一体化的内涵、测度方法、影响因素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成果。对于城乡一体化的内涵,甄峰[2]、洪银兴和陈雯[3]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具有一定共识性的观点是认为城乡一体化是城镇和农村在各方面逐渐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体。对于我国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测度,现有研究主要采用了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例如杨荣南[4]构建了一个由城乡经济、人口、生活、空间、生态环境5个方面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焦必方等[5]从城乡经济融合、城乡生活融合和城乡医疗教育融合3个角度评价了1999—2008年长三角地区的城乡一体化水平;周江燕和白永秀[6]从城乡空间、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构建了包含35个指标的评价体系,分析了2000—2011年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的时序变化和地区差异。对于城乡一体化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主要分析了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户籍制度及相关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制度等[7];二是地方政府实施的带有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8];三是城市发展受阻、农村经济落后以及城乡二元结构和人地矛盾[9];四是农村人均家庭经营耕地规模、农业技术水平、农业现代化水平等因素[10]。
就我国城市体系规模结构而言,现有文献主要是从城市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两个视角展开研究。在城市地理学视角下,研究者主要关注我国城市体系的结构特征、职能类型、演变规律、区域差异等问题,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周一星和杨齐[11]、顾朝林[12]、王放[13]、高鸿鹰和武康平[14]、程开明和庄燕杰[15]等学者的研究。在区域经济学视角下,近年来一些研究者也开始关注城市体系结构对经济增长、环境污染、城乡收入差距等方面的影响。例如在经济增长方面,许政、陈钊和陆铭[16]实证分析了中国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式”,认为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大城市和中小城镇的发展并不相互排斥;谢小平和王贤彬[17]的研究发现在城市体系中更为“均匀”的城市规模分布有利于经济增长;在环境污染方面,陆铭和冯皓[18]采用省级行政区内部地级市之间的人口规模差距反映空间集聚水平,发现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度提高有利于降低单位工业增加值的污染物质的排放强度;城乡收入差距方面,李顺毅[19]实证分析表明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会产生显著影响,各规模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作用。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看到,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影响作用还没有专题研究涉及到。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实现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的重要方面,在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过程中,提高城镇化率、优化城市体系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3个目标应该得到有机结合。因此,本文将重点探讨城镇化进程中怎样的城市体系规模结构有利于更好地促进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
二、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城乡发展一体化影响的理论分析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在城乡共同增长的前提下,城市和农村在空间、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城乡进入互补、协同与融合的发展状态[6]。从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动力来看,除了消除城乡分割的制度性障碍等,城市发展对农村的带动和城乡市场的联动也具有重要作用[20-21]。而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城乡市场的联系。
城市体系规模结构表现为区域内一系列人口规模大小不等的城市在不同规模等级上的分布特征。在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过程中,各规模等级的城市具有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处于中心地位的大城市需要发挥有力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挥连接大城市和农村的节点作用[22]。对于规模结构协调的城市体系,大、中、小城市的规模和数量适当,形成较均匀的金字塔式层级结构,这种结构将大城市的带动作用和中小城市联系城乡市场的作用都能充分发挥出来,有利于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结构分散型城市体系的特征是大城市规模不足、中小城市数量较多。与协调型结构相比,分散型城市体系中,不仅多数城市规模较小,而且即使是居于中心地位的大城市规模也相对不足,这使整体城市体系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较弱,限制了区域内城市功能的提升和完善,导致城市辐射范围较小,城市对农村商品和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足。这种情况下,即使城乡差距不大,也主要是城市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造成的,并不是城乡协调发展的结果;由于城市规模不足对城市功能和城市需求的限制,城乡两个地域系统的联系相对较少,城乡一体化程度因此也较低。结构集中型城市体系的特征是人口主要向处于中心地位的大城市集中,中心城市规模偏大,中小城市发育不足,城市间规模差距较大。与协调型结构相比,集中型城市体系的突出问题是发挥连接作用的中小城市发展滞后。由于市场具有层级性特征,处于市场层级高端的大城市与市场层级低端的农村之间在经济活动内容、供求规模、经营模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如果没有中小城市的充分发育作为市场中间层发挥中介作用,则容易出现大城市与农村市场间的脱节问题,不仅会制约大城市的辐射作用,而且也难以形成城乡间流动顺畅的统一市场。因此,集中型城市体系也不利于城乡发展一体化。由此可以得到第一个假说:
假说1:随着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集中程度不断提高,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呈现“倒U型”变化。
城镇化率的提高是人口从农村向城镇流动的过程,而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会影响进城人口的流向。如果保持协调型城市体系的结构特征,城市化过程中,人口较为均匀地流向各层级城市,中心地位的大城市规模不会过度膨胀;随着各级城市的规模适度扩大,城市的聚集效应更明显,城市功能更加完善,城市对农村辐射带动作用更强,城乡市场联系将更加紧密,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在分散型城市体系下,由于城市普遍规模较小且中小城市数量偏多,城镇化过程中新增人口更大的比例是分散于数量众多的中小城市,这样不利于处于中心地位的大城市达到最优规模。中小城市的经济活动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中小城市发展必须要以发展大城市为先决条件[22]。大城市发展不足,不仅降低了自身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而且也制约了中小城市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因此,在城镇化率增加时,分散型城市体系与协调型城市体系相比,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提升较慢。在集中型城市体系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人口主要涌向大城市,中心城市进一步膨胀,城市体系的人口规模分布更加集中。一方面,规模过大的中心城市面临的规模收益递减问题将更显著,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会减弱;另一方面,中心城市与原本就发育不足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会出现更大的发展差距,制约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有效发挥连接中心城市与农村的节点作用。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集中型城市体系对于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促进作用也小于协调型城市体系。由此可以得到第二个假说:
假说2: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的“倒U型”影响将会进一步强化。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首先,设定回归模型检验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城乡发展一体化具有怎样的影响,即假说1。由于假说1认为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的影响为“倒U型”,因此模型中加入了城市体系规模结构指标的二次项。此外,刘红梅等[10]的研究发现城乡一体化水平滞后一期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因此,本文也将城乡一体化水平的一阶滞后项加入到模型的解释变量中,建立如下的动态面板模型:
(1)
其中,下标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urdiit代表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urdiit-1是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的一阶滞后项;ussit为反映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指标;Cit表示控制变量,εit为误差项。
为了检验假说2,即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城乡一体化水平的影响会有怎样的变化。本文借鉴Rajan和Zingales[23]在倍差法基础上提出的交互项方法,建立如下模型:
(2)

(二)变量与数据说明
对于城乡发展一体化指标的选取,本文采用周江燕和白永秀[6]测算的中国各省城乡发展一体化指数。该指数是通过包含城乡空间、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一体化4个方面35个基础指标构成的评价体系计算而得。该指数越大表明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越高。
对于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度量,为了使检验更加稳健,本文采用两种方法:
(1)利用空间基尼系数度量(uss_gini)。空间基尼系数是度量空间集中度的常用指标。人口在城市间的集中度反映了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特征,基尼系数越大表明城市体系结构越集中,处于城市体系顶端的大城市规模十分突出,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中小城市规模偏小,城市间规模差距大;基尼系数越小表明人口在城市间分布越分散,城市间的规模差距较小,大城市的规模并不十分突出。本文采用加拿大学者马歇尔(Marshall)提出用来衡量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的基尼系数[24-25],计算公式为:
(3)
其中,n为城市体系中所包含城市的数量;将各城市按人口规模从小到大排序,pi和pj分别表示第i位和第j位城市的人口数量;S为n个城市的人口总和。
(2)利用位序—规模模型的幂律指数ζ进行度量(uss_ζ)。位序—规模模型是已有文献中用于反映一个区域内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特征的重要方法[26],因此,它也成为反映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基本方法,例如梁琦等[27]就运用该模型估计了2010年中国城市层级体系的规模结构特征。
位序—规模模型中幂律指数ζ的基本计算方法是通过回归估计得到的,回归方程为:
lni=A-ζlnSi+ui
(4)
其中,i为城市体系中各城市按人口规模从大到小排序后所处的位序,Si为第i位城市的人口规模,A和ζ为估计参数,ui为残差项。幂律指数ζ反映了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ζ越大表明在城市体系中大城市的规模越突出,而中、小城市规模偏小,发育不足;ζ越小则表明城市体系中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度较低,中、小城市数量较多。如果方程(4)估计得到的R2接近1,则说明用该方法能够较好地反映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特征。
但在小样本情况下,对幂律指数ζ进行OLS估计的结果是有偏差的。Gabaix和Ibragimov[28]提出了改进的回归方程:
ln(i-1/2)=A-ζlnSi+ui
(5)
该方法对位序i进行了1/2的位移。经实证研究证明,使用方程(5)进行OLS估计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小估计偏差[29]。因此,本文也采用方程(5)估计幂律指数ζ。
本文在回归中加入的控制变量有以下几个:(1)经济发展水平,由各省人均实际GDP的对数(lngdp)反映,本文中实际GDP是将各年份的GDP数据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得到。(2)城乡收入差距(ineq),本文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来度量。(3)产业结构(str),本文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来度量。(4)交通基础设施条件(road),本文采用各省单位面积的道路里程(公里/万平方公里)度量。(5)对外开放程度,本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trade)来反映。(6)所有制结构,本文用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比soe)来反映。张永岳[9]、刘红梅等[10]、汪宇明等[30]、陆铭和陈钊[8]等研究均表明上述因素对城乡一体化或城乡差距都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将它们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我国23个省份*样本的23个省份具体是: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2006—2011年的面板数据,其中没有包括城市统计年鉴中所列地级市过少、存在数据缺失的省份以及4个直辖市。城乡发展一体化指数来自周江燕和白永秀[6]的研究。本文计算城市体系规模结构指标的数据来自2007—201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其中城市人口数为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辖区人口数量。对于幂律指数ζ,以省份为单位逐个对方程(5)进行回归估计,138个估计结果中R2全部大于0.75,其中R2大于0.8的占总样本数的95%,R2大于0.9的占66%,因此,幂律指数ζ的拟合优度总体上较高,可以较好地反映各省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特征。其他变量所需数据来自2007—2012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表1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 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描述
四、估计结果分析
(一)估计方法与结果
对于计量模型估计方法的选择,本文采用系统GMM方法尽量克服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系统GMM方法中,将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作为一个方程系统进行GMM估计,使用差分变量的滞后项作为水平方程的工具变量,使用水平方程的滞后项作为差分方程的工具变量,并且同时估计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由此提高了估计结果的有效性[30]。在具体估计中,本文采用了两步法的系统GMM估计方法,这是由于使用两步法进行估计不易受到异方差问题的干扰。
表2报告了回归模型(1)和(2)的估计结果。经有效性检验,Sargan检验中的P值均大于0.1,接受了工具变量为过度识别的原假设;AR(1)检验的P值均小于0.1,AR(2)检验的P值均大于0.1,表明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因此,本文采用两步法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是合适的。
针对回归模型(1),从表2中可以看出,空间基尼系数的一次项为正,二次项为负,而且在统计上显著。这反映出随着城市规模分布集中度的提高,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先提高;但当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程度超越一定水平后,在过度集中的城市体系结构下,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则会下降。即城市体系结构上的集中程度与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这一实证结果使假说(1)得到验证。

表2 回归模型(1)和(2)的估计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L.urdi表示城乡发展一体化指数的一阶滞后项。
回归模型(1)的各控制变量中,人均实际GDP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具有显著性,这表明人均实际GDP的增加有利于促进城乡一体化;城乡收入比的系数显著为负,反映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反映出样本所在时期内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一体化的推动作用不明显,其原因可能是户籍等城乡分割制度制约了产业结构升级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单位面积公路里程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对城乡发展一体化具有促进作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的系数显著为正,反映出对外开放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国有经济比重的系数显著为负,反映出国有经济比重过高不利于城乡发展一体化。伍其亮等[31]的研究表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具有重国有经济、轻非国有经济的倾向,这种倾向会扩大城乡差距。在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的地区这种倾向会更加突出,从而对城乡一体化产生负面影响。此外,城乡发展一体化指数的一阶滞后项系数显著为正,反映出前一期的城乡一体化水平会对当期产生显著影响,因而本文采用动态模型进行估计是合适的。
针对回归模型(2),表2中的结果表明,城镇化率与空间基尼系数一次项的交互项系数为正,城镇化率与空间基尼系数二次项的交互项系数为负,而且都具有显著性。与回归模型(1)的估计结果相比,增加了城镇化率的交互后,空间基尼系数一次项和二次项的系数符号均没有改变,说明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城市体系规模结构集中度对城乡一体化水平的“倒U型”影响将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一实证结果使假说(2)得到验证。
回归模型(2)的各控制变量中,人均实际GDP的系数显著为正,城乡收入比的系数显著为负;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和单位面积公路里程的系数均为正,但都不显著;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和国有经济比重的系数均为负,但也不显著。城乡发展一体化指数的一阶滞后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这里采用动态模型进行估计也是必要的。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估计结果是否稳健,这里使用位序—规模模型的幂律指数ζ代替空间基尼系数作为反映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指标对回归模型(1)和(2)重新估计。在表3中,从回归模型(1)的估计结果可见,幂律指数ζ仍是一次项显著为正,二次项显著为负。这说明替换了度量指标后,城市体系规模结构集中度对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的“倒U型”影响并没有改变,对假说(1)的检验结果具有一定稳健性。在表3中从回归模型(3)的估计结果可见,城镇化率与幂律指数ζ一次项的交互项显著为正,城镇化率与幂律指数ζ二次项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这表明替换度量指标后,城镇化率提高将进一步强化城市体系集中度与城乡与发展一体化水平的“倒U型”关系这一结果仍保持不变,反映出假说(2)的检验结果也具有一定稳健性。

表3 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首先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影响机制,然后构建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基于2006—2011年我国23个省份的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了估计和检验。结果表明:随着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集中程度不断提高,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呈现“倒U型”变化,即与过度分散或过度集中的城市体系相比,结构相对协调的城市体系更有利于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的提高。而且,城市体系结构的集中度对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的“倒U型”影响将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而进一步强化。换言之,在结构上过度分散或过度集中的城镇化战略都将更明显地抑制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而在城镇化进程中,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格局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切实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我国“十三五”时期落实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也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基本目标之一。合理的城镇化路径可以通过人口分布、产业结构、资金配置、土地空间等要素的优化组合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6]。但在我国以往的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特大城市规模迅速膨胀、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对萎缩的两极化倾向[1],根据本文实证分析的结果,这种两极化倾向不利于城乡发展一体化。因此,在未来的城镇化进程中,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我国各地区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就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在现实中,一个区域的城市体系必然是一个规模从大到小的层级结构,城镇化战略的着眼点不仅需要关注单个城市,同时也需要关注区域城市体系的结构优化。在完善城镇化发展战略时不能孤立的看待大城市或中小城市自身的优势与不足,不能片面地强调优先发展大城市或优先发展中小城市。在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过程中,不同规模的城市具有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处于中心地位的大城市需要发挥有力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挥连接大城市和农村的节点作用。因此,需要从整体入手,强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等级有序、分工合理、协调发展中形成的综合优势。
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还将迎来一个新的高速发展时期,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将是我国在城镇化率快速提升的同时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路径。在考虑区域发展需求和资源环境约束的前提下,应该更加注重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协调程度,避免城市规模分布过度分散或过度集中。合理疏解已经进入规模收益递减阶段的巨型城市;积极促进一批有条件的中小城市向大中城市发展,缓解人口向少数巨型城市集中的压力,同时能够更有效地发挥辐射带动农村发展的作用;对于不具备规模大幅度增加条件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着力提升城市的经济社会功能和综合承载能力,进一步完善公共设施,增强产业支撑和人口吸纳能力,使其真正成为联通城乡的枢纽。
参考文献:
[1]魏后凯,等.中国城镇化:和谐与繁荣之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甄峰.城乡一体化理论及其规划探讨[J].城市规划汇刊,1998,(6):28-31.
[3]洪银兴,陈雯.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4):5-11.
[4]杨荣南.城乡一体化及其评价指标体系初探[J].城市研究,1997,(2):19-23.
[5]焦必方,林娣,彭婧妮.城乡一体化评价体系的全新构建及其应——长三角地区城乡一体化评价[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75-83.
[6]周江燕,白永秀.中国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的时序变化和地区差异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4,(2):5-17.
[7]姜长运. 城镇化与“三农”问题[J].农业经济问题,2003,(2):26-28.
[8]陆铭,陈钊. 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4,(6):50-58.
[9]张永岳.我国城乡一体化面临的问题与发展思路[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24-31.
[10]刘红梅,张忠杰,王克强.中国城乡一体化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引力模型[J].中国农村经济,2012,(8):5-15.
[11]周一星,杨齐.我国城镇等级体系变动的回顾及其省区地域类型[J].地理学报, 1986,(2):97-111.
[12]顾朝林. 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3]王放.论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区域差异[J].人口与经济,2001,(4):9-14.
[14]高鸿鹰,武康平.我国城市规模分布Pareto指数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4):43-52.
[15]程开明,庄燕杰.中国中部地区城市体系规模分布及演进机制探析[J].地理科学, 2013,(16):1421-1427.
[16]许政,陈钊,陆铭.中国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式”——地理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2010,(7):144-160.
[17]谢小平,王贤彬.城市规模分布演进与经济增长[J].南方经济, 2012,(6):58-73.
[18]陆铭,冯皓.集聚与减排:城市规模差距影响工业污染强度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14,(7):86-114.
[19]李顺毅.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J].财贸研究,2015,(1):9-17.
[20]吴伟年.城乡一体化的动力机制与对策思路——浙江省金华市为例[J].世界地理研究, 2002,(4):46-53.
[21]方辉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形成机理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10,(1): 137-140.
[22]陆铭. 重构城市体系——论中国区域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0,(5):15-26.
[23]RAJANR,ZINGALESL.FinancialDependenceandGrowth[J].AmericanEconomicReview, 1998,88 (3):559-586.
[24]程开明,庄燕杰.中国中部地区城市体系规模分布及演进机制探析[J].地理科学, 2013,(12):1421-1427.
[25]朱顺娟,郑伯红.从基尼系数看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区域差异[J].统计与决策,2015,(8):127-129.
[26]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城市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123-147.
[27]梁琦,陈强远,王如玉.户籍改革、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层级体系优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3,(12):36-59.
[28]GABAIXX,IBRAGIMOVR.Rank-1/2:ASimpleWaytoImprovetheOLSEstimationofTailExponent[J].JournalofBusinessandEconomicStatistics, 2011,29(1):24-29.
[29]沈体雁,劳昕.国外城市规模分布研究进展及理论前瞻—基于齐普夫定律的分析[J].世界经济文汇, 2012,(5):95-111.
[30]BLUNDELLR,BONDSR.InitialConditionsandMomentRestrictionsinDyanmicPanelDataModels[J].JournalofEconometrics,1998, 87(1):115-143.
[31]伍其亮,史元亭,万广华.投资倾向与城乡差距——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J].世界经济文汇,2015,(1):34-49.
Scale Structure of Urban System and Urban-RuralDevelopment Integration——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in China
LI Shun-yi
(College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The level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is in an “inverted U shape” relationship with the high concentration of urban system. Compare with the cities of excessive decentralization or concentration, a coordinating structure of urban system promotes th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It follows that the higher the urbanization rate, the stronger the “inverted U” effects on the level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would be produced. It is concluded that excessive decentralization or concentration modes of urbanization strategy are not conducive towards an optimal level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Instea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large, medium and small sized cities is a more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KeyWords:urbansystem;scalestructure;urbanization;urban-ruraldevelopmentintegration
收稿日期:2016-03-11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16.04.0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4CJL026);贵州财经大学与商务部联合基金项目(2015SWBZD14)。
作者简介:李顺毅(1984—),男,天津人,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E-mail: nklishunyi@126.com
中图分类号:F2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16)04-00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