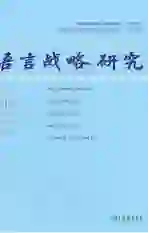从现代汉语规范化角度把脉新兴流行詈语
2016-05-30沈阳
沈阳
提 要 作为流行语的新兴詈语,最主要特点就是“非詈”:要么让詈语在形式上变得“非詈(非詈化詈语)”,要么让詈语在功能上变得“非詈(非詈性詈语)”。本文通过具体语料分析了这两种现象。由于人们表达情绪的需要,作为语言发泄的途径,詈语无非是一种“最终选择”。从语言规范化的角度看,詈语当然肯定是“有害”的,无疑应该采取必要措施加以制止和疏导,不能使其无节制泛滥;但从语言的功能和使用看,也必须承认一部分詈语是“有用”的,至少在表达上的某种作用有时无可取代。因此詈语既不可能自行消亡,也不应一棍子全部打死。
关键词 詈语;非詈詈语(形式非詈);詈语非詈(功能非詈);现代汉语规范化
Evaluation on Newly Emerging Foul and Abusive Language in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Shen Yang
Abstract Foul and abusive language (Liyu) in sociolinguistics refers to taboo (“bad language”) that is associated with swearing or crude expressions such as obscenity, profanity, blasphemy or other cursing utterances that strongly offend the prevalent morality in society of the tim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valuate the semantic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of Chinese Liyu in contemporary soceity. Being rife and ubiquitous in both society and cyberspace, nowadays Liyu is increasingly popular among the teenagers. As a fashionable trend, the distinct feature of Liyu is “neutralization”. Namely, it has to be neutralized either in form or in function when it is actually used. Based on abundance of exemplar expressions obtained from various textual sources, predominantly from the print press and the Internet, this article conducts an in-depth examination of the actual use of Liyu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anguage. Our findings show that, as a means used to indicate a strong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moral repugnance, Liyu serves as an ultimate linguistic device for “extreme op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Liyu is definitely harmful to language management. In order to prevent it from polluting language, measures should be adopted to ban its unstrained circulation or to provide guidance on its use.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realize that Liyu is “useful”; its expressive power is unsubstitutional. Therefore, Liyu will not automatically disappear; it would not be eliminated without prudence.
Key words abusive language; neutralization (in form); neutralization (in function); standardiz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詈语”即所谓“骂人话”或“脏话”,当下产生了不少新兴流行詈语,对它们“叫好”“叫停”的都有。
这些詈语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听上去(或看上去)虽“不脏”,但实际上的确是骂人话,比如“屌丝、逼格”一类,即“非詈詈语(非詈化的詈语)”现象,或者叫 “形式非詈”;另一类是听上去(或看上去)虽是“脏话”,但实际却不是真在骂人,即“詈语非詈”。
本文将就新兴詈语的“非詈詈语”和“詈语非詈”现象做初步分析。通过探讨这些“脏话”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引起大家更多思考,为语言政策制定者和语言行为管理者对新兴流行詈语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提供参考。
一、“非詈詈语(非詈化的詈语)”现象
骂人话或脏话,尤其是涉及性活动、性器官、排泄物等的脏字眼,历来“不登大雅之堂”,通常说话人或写作者也都是“避之犹恐不及”。其实任何语言中都有这一类脏字眼,但一般要么本身不那么明显,如汉语“娘希匹、你丫的”;要么就改换个说法和写法,如汉语把“肏”改成“操”。这就类似“黑钱能洗白”,好像脏字儿只要“换个写法”也就能“变得干净”。这就是前述的第一种新兴詈语,即“非詈詈语(非詈化的詈语)”现象。
我国一直有“非詈詈语”的传统。自秦汉直至明清,因为脏话脏字眼不能以本来面目示人,于是只能想方设法遮遮掩掩(刘福根 2007)。比如“鸟”,鲁迅就曾在《导师》一文中骂胡适是“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在《故事新编·起死》中写道“就是你真有本事,又值什么鸟”。胡适也曾在《胡适杂忆》中说过“最好闭起鸟嘴” “推翻这鸟政府”。《水浒传》中“这鸟不知甚么鸟事”“你那伙鸟人”等带“鸟”的词语多达上百条。据论证(曹德和 2006)“鸟”即“屌”,指男性生殖器,本读作“di2o”,“吊儿郎当”其实就来自这个意思。
事实上“非詈化”也表现在一些普通词语的使用上,有些词语涉嫌人格侮辱或者过于龌龊,在正式出版物中也会受到限制。前些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新华新词语词典》,收录了“二奶、三陪、泡妞”一类词,曾引起争议。有趣的相反现象是,新近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据说是考虑可能会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只收“宅女”,却不收“剩女”,这倒似乎有点儿过头了(毕竟“光棍”词典还是收录的)。这些做法和争论其实都涉及词典中哪些词语可以“登堂入室”,哪些词语要“拒之门外”。具体的词语怎么取舍可以争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词典或出版物肯定不会把生活中所有的词语“照单全收”。
如果说出版物用词或词典收词要有“规矩”,但生活中有些人说话时似乎只要让脏字眼“乔装打扮”一番,就“但说无妨”。《人民日报》2012年11月3日第五版《激发公众前进的力量》使用了“屌丝心态”一词;《成都晚报》2013年2月文章标题为:“亚洲杯预选赛,卡马乔大SB!”①(魏晨 2015)随后多家媒体纷纷使用这类词语,乃至后来这种现象愈演愈烈,有些人常常把一些脏字眼挂在嘴边,甚至成了“喜闻乐见”的流行语。无论男女(甚至公众人士)都自称“屌丝”,都标榜“逼格”,都大赞“牛掰”,还有诸如“碉堡了(屌爆了)、草泥马(“操你妈”的异化)、SB(傻逼)、你妹(“操你妹”的减缩)”,说者居然大言不惭,报纸、广告和电视节目中还出现了“我去、哇塞(其实都是“我操”的变体)”这类词汇,居然还出现在央视春晚中。
从当前非詈化的新兴詈语所使用的词语看,一类是传统詈语的非詈化新变体,另一类是完全新生的非詈化詈语。二者都主要是通过析字② 来实现詈语的非詈化新形式或构造出新兴的非詈化詈语,具体又可分为谐音、借形、转义、新造等形式。
传统詈语的非詈化主要靠谐音换字。如“靠、操、日、吊、逼”即是本字“尻、肏、入③、屌、屄”的谐音字,甚至已基本取代本字。而新兴詈语借助网络的特点,构造詈语的方式更是日益多样化。除了使用同音字,还有诸如数字式的“748、674”,字母式的“TMD、MLGB、MPJ、SB”,汉字式的“我擦、特么、滚粗、碉堡、喵了个咪、屌得一逼”,混合式的“2B、傻X、傻B、牛B、QU4”等多种形式。而更多情况是一个詈语有多个变体,如“肏”一词,可写作“草、艹、屮艸芔茻、CAO、次奥、擦、操、去”等多种形式;“傻屄”有“煞笔、煞逼、傻比、纱布、烧饼、沙壁”等多种写法;“他妈的”,也有“TMD、MD、特么”等多种变体。此外新生詈语还通过借形、转义以及自造来构造新兴詈语,如借形的“靐、槑、兲”,转义的“奔驰250(笨痴的二百五)”;谐音演化的“偶像(呕吐的对象)、天才(天生的蠢材)”,新造的“屌丝、坑爹、我了(勒)个去”等。
与传统詈语相比,新兴詈语的“非詈化”表现为三个层次:一是转写形式多样;二是脏话戏谑色彩增强;三是词语色彩向中性转变。这反映了“非詈化”的不同程度,即脏话的“脏值”逐次递减。
新兴詈语形式的“多样化”,主要表现在同一个詈语有多种变体。即力求避免本字或本字读音,通常同音字优先于本字,字母和数字优先于汉字,古汉语优先于现代汉语,方言优先于普通话。而从詈语的侮辱度看,据有人考证(王明珏 2012):他指低于面指,省略动词的低于保留动词的,字母式低于汉字式,转写式低于字母式。也就是说,詈语词离本字越远,转化次数越高,委婉化程度就越高,侮辱度也越低,使用范围也越广。由于网民对传统詈语的改造,很多詈语在视觉上越来越呈现“求雅避俗”的特征。以“我肏”为例,就有“我操、我草、我艹、我屮艸芔茻、卧槽、我次奥、WC、我cao、我擦、我去”等变体。例如:
(1)a.科比的“狂草”体一如他的性格:很狂,你只能摇头赞叹:我草!(新闻网)
b.我艹,谁把手机调成震动了,吓死劳资了!(新闻网)
c.卧槽!导演,你这么机智,投资方知道咩?(新闻网)
d.我擦……霍芬海姆打空门被后卫挡出去了……(新闻网)
e.——潘长江:喂喂!(打电话)老王大哥,我,小陀螺,你们的千手观音还缺人吗?
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蔡明:我去!(2013年央视春晚《想跳就跳》)
新兴詈语意义的“虚化”主要表现在侮辱色彩减弱,戏谑调侃和话语标记功能加强。本来詈语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辱骂,但在网络传播的过程中逐步丧失了原本意义,逐渐成为一个表达情绪的符号。张谊生(2010)以性詈语为对象,指出詈语意义的虚化经历三个步骤,分别是词汇化、标记化、构式化,即有些詈语充当插入语而叹词化,有些进入词语内而标记化,有些类推定型而构式化。这其实也正是詈语在非詈化过程中本义发生虚化的主要手段。
新兴詈语虚化的“词汇化”,可以“坑爹”为例。“坑爹”从一个动宾词组逐步凝固发展成一个词,如可以不加“的”直接做定语,也可以与其他词语搭配使用,词汇化后的意义主要用来表达埋怨、自嘲等态度。例如:
(2)a.坑爹现象层出不穷,应该说那些当父母的有一定的责任!(《人民日报》)
b.武进某楼盘两三年前样板房竟当精装房卖,真是坑爹!(报业网)
c.西安希尔曼卫浴的坑爹售后让人伤心让人忧。(腾讯网)
d.这坑爹式的虚假宣传,反映出企业对待食品安全的态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新兴詈语虚化的“标记化”,可以“你妹”的用法为代表。这个词最初流行来源于2010年漫画日和《西游记,旅途的终点》中孙悟空的中文配音“买你妹啊,这破烂玩意儿”。而“你妹”一词作为“你妈”的隐晦版可与形容词和动词组合,作为一种略带戏谑的否定,如“看你妹、好你妹、萌你妹、可爱你妹”。随着使用的扩大,又可以带助词,如“你妹的、你妹啊、去你妹的”等,产生了十分明显的标记作用。例如:
(3)a.找不到女朋友,怨你妹啊!(网易新闻)
b.呵呵!决赛票砍半再摇号,摇你妹!(环球网体育频道)
c.时尚你妹!萌妹子都爱小清新 众星都好重口味。(人民网)
d.都火烧眉毛了,还输你妹的验证码!(看看新闻网)
e.过你妹的情人节!(腾讯网)
新兴詈语虚化的“构式化”,可以“我勒个去”为例(类似还有“喵了个咪、X(屌)得一逼”等)。2011年“我勒个去”开始频繁出现在动漫日和《平田的世界》中,此后迅速风靡网络,并成为当年的网络流行语。这个詈语由最初的谩骂和攻讦,逐步转为网络发泄不满情绪的一种表达格式,再到现在成为很多人使用的口头禅或插入语。例如:
(4)a.一个镜头野马就改好了?我去!全程没有氮气增压,我勒个去!(看看新闻网)
b.我勒个去,这个才是真正的功夫熊猫啊!(看看新闻网)
c.我勒个去,敢不敢再浪漫一点你想不到的都出现了。(新浪视频)
d.这个,我勒个去,我都不太明白。(凤凰卫视)
二、“詈语非詈(非詈性的詈语)”现象
前面说的“非詈詈语(非詈化的詈语)”,如果意义进一步虚化或弱化,原本使用脏字眼或带有贬义字眼的词语,就逐渐转为中性词或普通词的用法。从这一点来看,这时的詈语似乎已不再是詈语,即几乎没有了“脏话”的含义和作用:这可称作“詈语的通用化”。此外还有一类是听上去看上去确实是脏字眼,但实际作用不是骂人,还具有打趣或调侃的作用:这可称作“詈语的反用化”。这两类加起来,就是本文讨论的第二大类新兴詈语,即“詈语非詈(非詈性的詈语)”现象。
先看“詈语的通用化”。前面说詈语的非詈化发展到“标记化、构式化”阶段,几乎丧失了脏话作用,并成为中性词,这就是“詈语通用化”。如“货”族词。“货”最早是金钱珠玉布帛总称,后产生贿赂义。《韩非子·亡征》:“官职可以重求,爵禄可以货得者,可亡也。”将人比成物是古人致詈方式之一,“货”变成贬义词正是源于这一点。事实上许多带“货”的词都是詈语,如“蠢货”是骂人愚蠢;“懒货”是骂人懒惰;“软货”是骂人没主见;“骚货”是骂女子行为不端,此外还有“烂货、怂货”等。而随着网络语流行,一方面“货”的感情色彩发生了变化,即不再具有贬义;另一方面使用范围也开始扩大,平面媒体从2011年开始就出现了表达非贬义的新兴“货”族词。例如:
(5)a.即使时下的禽流感让人心慌慌,也丝毫不能挡住“大黄鸭”的风头。这个被大家昵称为“大黄鸭”的巨型萌货,使得整个香港沸腾了。(《人民日报·海外版》)
b.一个二货同学跟同桌轻声谈论自己早上被狗追的糗事,同桌听后淡定地评价了句“狗咬狗,一嘴毛”,二货同学急忙解释到“我没咬它!”(《生命时报》
c.新西兰“史上最大奇异果”,限量直供中国吃货。(《杭州日报》)
d.大妈也会每年想着法儿添几个新菜,让我这个吃货过足了瘾。(《人民日报》)
其实“哇塞”一词也可以看作是这类“詈语非詈”的例子。据考证(魏晨 2015),“哇塞”原本是闽南话词语,相当于普通话“我肏”,是地地道道的脏话。但由于从港台传入大陆后,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个词的来源及用法,而把它当作和“哎呀,哇”类似的词来用,这时这个词就已经完全脱离了本义,成为一个只是表达惊讶、叹服的新叹词。例如:
(6)a.哇塞,那种感觉真的像,电麻了全身,好痛苦。(中央电视台)
b.我觉得,哇塞,你竟然愿意从你的财产里面拿出这样的比例来买。(凤凰卫视)
c.哇塞,坐了趟火车从北到南,身价竟然涨了十倍。(中央电视台)
d.服务员:哇塞,快帮我接一下,我坚持不住了。(北京电视台)
e.我都觉得哇塞,这帮人都真的很棒。(凤凰卫视)
新兴詈语“詈语非詈”的另一大类可统称“詈语的反用化”,主要是指有些骂人话语看似难听,其实不但说话者并非意在骂人,听话者也不觉是在挨骂,交际双方反而会在特定语境下产生亲切感或能够拉近彼此的关系,所以就成了“非詈性”的詈语。这其中又包括“詈语表谦称”“詈语表戏称”和“詈语口头禅”等几种情况。
“詈语表谦称”是这类“詈语非詈”中一种常见的情况。在交际中说话人想取悦交际对象,就要相应贬低自己。人们在谦称时又偏好让自己处于“非人”或“贱人”的地位来抬高对方,因此多以带有骂意的词根构成自称,如“下愚、敝人、卑人、鄙人、贱人、贱士、贱臣、贱姓、贱妾”等,也有一些背称词通过对关系紧密亲属(如妻子、儿子)的降格指称完成贬己尊人,如“贱内、贱荆、贱息、犬子”等。詈称谦用现象从古代起一直延续至今,比如现在常有人自称“屌丝、二货、加班狗、单身汪”,应该也属这种用法。例如:
(7)a. 本屌丝由于是学生,也可以领补助哈,一个月几百刀的样子。(网易贴吧)
b. 当傻逼萌宠遇到二逼主淫,再碰上本逗逼小编,生活因此多姿多彩。(搜狐健康)
c. 我是一个有内涵的二货。(《信息时报(广州)》)
“詈语表戏称”也是这类“詈语非詈”的一种情况。即通过嘲弄和戏谑,营造轻松愉快的交谈氛围,从而拉近交谈者之间的距离。詈语戏称在夫妻情人间多表嗔怪,同辈间多表亲昵,长辈对下则多表喜爱亲近之情。如《红楼梦》中就常见如“傻子、小蹄子、死娼妇、捉狭鬼儿、母蝗虫”之类的称呼。如今新兴詈语的戏用似乎也越来越广泛。《北京青年报》曾发表一篇文章“叫我怎样称呼你——我的爱人”,文章中提到现在男女恋人或夫妻间的称呼无所不用,甚至无奇不有,如“白痴、疯子、傻子、没脑子的、挫人、死猪、傻瓜、笨蛋、呆子、贱人、死人、肥婆娘、放屁虫、懒鬼、懒虫、贱婢、臭男(女)人、混蛋、流氓”等。例如:
(8)a. 猪头,想我了没有?(百度百科)
b. 臭白痴,晚安好梦,早就知道你困了还硬撑。(个性网)
c. 傻瓜,你永远是我最美丽的遇见。(豆瓣小组兰儿)
d. 那是因为我爱你,臭流氓。(百度贴吧)
e. 呆子,你要开心,好好照顾自己,把自己养胖点。(百度贴吧)
而这类“詈语非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产生出了“詈语性口头禅”,即詈语变成了常态的称呼语。2014年微博票选出国人的九大口头禅,“神经病”就位居榜眼,“猪、白痴、变态、垃圾”等也赫然在列。“口头禅”词典解释为“经常挂在口头的词句”。此外“在现实语言使用过程中,口头禅由于高频复现和脱口而出的特点,不可避免地导致语义弱化(semantic reduction)或语义淡化(semantic bleaching),但与此同时,其语法功能或语用功能依然存在甚至更显强大,经历了语法化或语用化的过程”(厉杰 2011)。语言的频繁使用带来语义的磨损,像“神经病、猪、白痴、变态、垃圾”等詈称被用作口头禅时,其指称的内容(即词汇意义)被不断磨损而虚化,之后只是用作语气标记或指称标记,或者说只具备一种语用上的功能——情绪发泄。例如:
(9)a.你这个神经病,你在家不是天天看电视吗?(韩寒《一座城池》)
b.周杰伦平时给自己和旁人最大的赞美就是“超屌”。(鄂东网)
c.“白痴”成了很久以来我的口头禅,并没有认为这是骂人的话。(博客大巴)
d.“变态”这个词经常被用来称呼我的各种朋友,但是没有任何恶意。(豆瓣小组)
e.我的一个朋友最爱说的是“瘪三”,无论对自己还是他人。(豆瓣小组)
三、讨论和结语
综上,排除真正的“恶语伤人”和“口不择言”,而作为流行语的新兴詈语,无论是“非詈詈语”还是“詈语非詈”,一个最主要的特点或者共同点就是“非詈”。即要么让“詈语”在形式上变得“非詈(非詈化)”,要么让詈语在功能上变得“非詈(非詈性)”。如此来看新兴詈语,有的是通过外部“改头换面”来实现非詈,有的是通过内部“摇身一变”来实现非詈。把这个意思反过来说,也就是随着詈语的各种“非詈”,詈语的“形式”势必越来越多,“用处”也可能会越来越大。
事实上由于人们表达情绪的需要,作为语言发泄的一种途径,詈语正是一种“最终选择”。因此客观地说,詈语首先当然肯定是“有害”的,应该采取必要措施加以制止和疏导,不能使其无节制泛滥;但也必须承认詈语是“有用”的,在表达上的某种作用甚至无可取代。正因为大家都知道詈语“有害”,所以说和写的人才都有意无意地尽量弱化“脏值”;正因为大家也都觉得詈语“有用”,所以使用的人和可用詈语的场合才越来越多。
詈语的“有害”不用多说,但对于非詈化或非詈性的詈语的“有用”,现在似乎还缺乏必要分析和认识。江结宝(1999)提到“詈骂”有诸多的功能,包括“伸张正义,指引正道,伤人是非,宣泄情绪,保护自己,关爱他人,兴奋取乐,无意生骂”等。詈语是否有这么多的功能暂且不论,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目前的詈语虽然花样翻新,内容日益多样化,但毕竟詈骂意味逐渐淡化,原本的脏话不但视觉上呈现出求雅避秽特征,意思上也削弱了低俗侮辱功能,甚至成为新造词的来源。露丝·韦津利以英语脏话为例指出:“人们愈常听到某个詈语,其禁忌就愈弱,震惊值也因而愈低。若一个字被过度使用,就导致几乎所有震惊力都流失。语言频繁使用带来磨损,一个詈语的宿命就是不再有禁忌,而这时另一个替代者即将诞生。”可见詈语的最大作用首先就在于“引起震惊”,而这种作用又是其他任何词语和句子所无法替代的。而在“见多不怪”或者“习以为常”之后,随着震惊值的减弱,必须有新的詈语来强化这种“震惊作用”,于是新兴詈语才越来越多,可以说正因为詈语在社会交际中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所以才不但有“市场需求”,而且还“供不应求”。
以色列社会语言学家博纳德·斯波斯基(2011)就提到,有一些语言学家认为“限制不良语言的使用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问题”,“自古以来各地社会就认识到语言的危害性和影响力,因此各地语言都有一些禁忌词(taboo),即一些被限制使用的词语”,“对不良语言的管理,各国政府责无旁贷”。但同时他也承认“有些语言学家认为根本不存在不良语言或禁忌语这种东西”,“比如《韦氏词典》(第5版)就不对词语做任何的判断,只是告诉读者这些词语是如何被使用的”,也就是坚持“使用即标准”。他在书中提到了两个概念:“纯洁化”和“清洁化”。并且认为,或许语言的“纯洁化”是不现实的,但语言的“清洁化”还是应该坚持。
有专家建议,如果要对詈语加以规范,似乎应该有两种:行为的规范和语言的规范。“非詈性詈语”应属于行为规范的范畴,就像“吐痰”一样,有痰是要吐的,但不能随地吐;而“非詈化詈语”则属于语言规范的范畴,这类词语本身格调低下,有违审美追求,有损汉语品位,应该禁止在大众媒体及公众场合使用。我们同意这个意见。从“现代汉语规范化”角度来看待上述新兴流行詈语,一方面要尽可能促使詈语进一步弱化;另一方面要尽可能限制詈语的使用,比如在官方媒体和正式媒体中不能使用詈语,在学校里和青少年中也要劝阻使用詈语。
注 释
① 资料来源:http://www.cdwb.com.cn/html/2013-02/08/content 1791010.htm。
②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对“析字”的解释为“把所用的字析为形、音、义三方面,看别的字有一面同它相合相连,即借来代替或推衍上去,名叫析字”。
③ 李荣《论“入”的音》(《方言》1982年第4期):“‘入读作‘ri,后被‘日取代。”
参考文献
博纳德·斯波斯基 2011 《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张治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曹德和 2006 《詈辞演变与雅化倾向——从“鸟”等的语音、语义和字符演变说起》,《汉语史学报》第1期。
江结宝 1999 《詈骂的动机和作用》,《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厉 杰 2011 《口头禅的语言机制:语法化与语用化》,《当代修辞学》第5期。
刘福根 2007 《古代汉语詈语小史》,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王明珏 2012 《中文网络语言中脏话的使用情况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魏 晨 2015 《主要媒体中的新兴詈语》,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张谊生 2010 《试论骂詈语的词汇化、标记化与构式化——兼论演化中的骂詈语在当代汉语中的表达功用》,《当代修辞学》第4期。
责任编辑:丁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