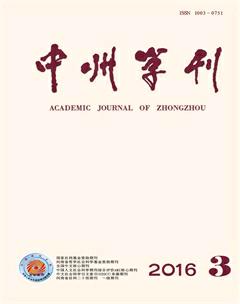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的监管机制创新——兼论我国《矿山安全法》的修改与完善
2016-05-06罗丽代海军
罗 丽 代 海 军
【法学研究】
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的监管机制创新
——兼论我国《矿山安全法》的修改与完善
罗 丽代 海 军
摘要:“三方机制”作为调节劳动基准关系的一项基本制度,其产生和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长期以来,我国矿山安全监管主要通过政府强制实现,存在决策不民主、执行效果不佳等弊端。借鉴国外对话协商、咨询指导、协调监督等“三方机制”模式,我国可以考虑在矿山安全领域建立促进职业安全与健康的“三方机制”,具体路径是修改《矿山安全法》,调整其篇章结构,增设“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三方机制’”一章,完善相关罚则。
关键词:职业安全与健康;三方机制;行政参与;矿山安全法
一、引言
根据我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①的规定,我国生产安全监管主要通过政府运用行政检查、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刚性手段实现。这种以支配—服从为核心的监管制度设计存在明显缺陷:一是决策机制不透明,公众参与渠道有限,导致政策的可接受度和知晓率低下。二是过度倚重政府的强制功能,忽视相关方的配合与协作,不利于激发企业和员工的自我安全管理能力。三是导致政府监管常常处于一种“任性”状态,对企业、雇主及其他相关方的利益缺乏相应保障。②与我国对安全生产实行单一政府监管模式不同,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由政府部门、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代表共同处理有关劳动基准关系的重大问题,维护劳动者生命健康权益的机制(以下简称“三方机制”)。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是劳动关系中的三方主体,三者所追求的目标并不相同,利益也不完全相同,协调劳动关系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平衡三方利益。“三方机制”具有多方参与、集体协商、决策民主、利益兼顾等特色,有利于协调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我国于1990年批准了《三方协商促进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公约》(1976年第61届国际劳工大会通过),并在我国《工会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初步建立了“三方机制”,但该机制主要用于解决劳动争议问题,并不涉及职业安全与健康。③
矿山行业历来是职业安全与健康事故高发的领域,也是我国安全监管的重点。据统计,2014年全国矿山行业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1043起,造成1571人死亡,分别占工矿商贸行业全部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数量和造成死亡人数的18.1%和21.8%。④在矿业领域建立“三方机制”,推动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三方就涉及职业安全与健康的重大问题进行积极对话、协商和谈判,不仅有利于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和职业病伤害,有利于保护职工的财产安全和生命健康权益,而且会促进政府部门关于生产安全的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增强行政的效能,增进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基于此,笔者认为,在目前修订我国《矿山安全法》之际,应考虑在该法中增设“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三方机制’”一章,强化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监管。
二、国外“三方机制”的主要模式述评
1.国外“三方机制”的主要模式
“三方机制”作为协调劳动关系主体不同利益的基本制度,早在1848年就在法国出现,经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简称ILO)大力提倡,目前已经成为一种国际劳工标准,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总结国外“三方机制”的实践经验,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种模式。
第一,对话协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三方通过对话、协商,对关涉各自利益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研究,制定各方均可接受的劳工政策和标准。ILO作为专门处理劳工问题的联合国机构,是一个典型的三方组织,由成员国政府、雇主代表和工人代表组成,三者作为平等的主体进行对话、协商,对涉及劳动者体面、健康劳动的相关问题寻求解决方案。三方代表通过ILO的国际劳工大会、理事会和劳工局进行对话,结果直接反映在ILO制定的职业安全与健康政策、标准和行动计划中。1919年以来,ILO全体大会已经通过了《关于职业安全、健康和工作环境的公约》《促进职业安全与卫生框架公约》等重要公约。对话协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ILO各成员国的职业安全与健康决策及其执行机制,并推动了世界职业安全与健康立法技术变革,包括从规则向政策、从详细标准到综合标准、从刚性规定向比较灵活的规则转变。
第二,咨询指导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府、雇主和雇员三方代表主要为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监管机构提供立法、执法和政策制定方面的意见、建议,分析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并对相关工作进行指导。采用该模式的代表性国家是美国和南非。美国依据1970年《职业安全与健康法》设立了国家职业安全健康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简称NACOSH),该委员会是一个三方机构,由13名成员组成,包括2名监管代表、3名工人代表、2名职业健康代表(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长任命)、2名职业安全代表和4名公众代表(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长任命其中2名),美国劳工部长任命其中一名成员作为委员会主席。NACOSH主要负责向美国劳工部长、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长提供督促职业安全与健康法规执行的咨询和建议,内容包括如何公平、富有效率地执行职业安全与健康法规;相关管理事项;有助于减少工伤和职业病的活动等。南非依据1996年《矿山健康与安全法》设立了矿山健康与安全委员会(Mine Health and Safety Commission,简称MHSC),由5名矿主代表、5名矿工代表、4名政府部门代表组成(其中矿山监察局局长担任委员会主席),下设法规咨询委员会、职业健康咨询委员会和研究咨询委员会。MHSC的职责包括:向政府提供矿山健康与安全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协调常设委员会的活动,接受常设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与采矿资格管理局就健康与安全事宜保持联络;与其他相关法定机构就健康与安全事宜保持联络;促进采矿业健康安全发展;对矿山安全状况进行审查等。
第三,协调监督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府、雇主和雇员三方代表组成独立机构,直接组织制定和实施职业安全与健康政策,开展全国性立法,进行相关协调和监督等。采用该模式的国家以澳大利亚为代表。澳大利亚根据2008年《职业安全委员会法》成立了职业安全委员会(Safe Work Commission,简称SWC),该委员会自2009年11月1日起成为独立的法定机构,主要依据联邦政府理事会2008年7月签订的“联邦政府与州政府间职业安全与健康合作协议”进行运作。SWC是一个典型的三方机构,由联邦和各州(地区)政府代表、工人代表、雇主代表组成,主要职责共14项,包括:制定有关职业安全与健康和工人赔偿的全国性政策;制定有关职业安全与健康的示范法和相关实施条例;制定和修改有关职业安全与健康的行为准则;进行相关数据统计分析和基础研究;向部长会议提出建议;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管理有关职业安全与健康的其他事务;等等。还有一些国家建立了类似于SWC的职业安全与健康机构,如波兰设有劳动保护委员会,由议员代表、工会代表、雇主组织代表和专家组成,主要职责是对国家劳动监察局的工作实施监督;瑞士的三方机构——联邦职业安全协调委员会除了制定职业安全与健康法,还负责协调国家工伤保险机构与经济事务秘书处以及各州劳动监察局的关系。
2.国外“三方机制”的主要特点
第一,三方主体的结构基本相同,人员比例略有差异。尽管体制不同,但各国三方机构通常包括来自工人组织的代表、雇主组织的代表和政府部门的代表。三方主体的地位大同小异,人员组成略有不同(见表1)。在三方代表的选取上,各国通常会考虑其知识背景以及在职业安全与健康方面的经历。代表大多实行聘任制,任期有所不同。

表1 部分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三方机构的人员组成
第二,“三方机制”作用领域基本相同,但机构运作方式各异。国外“三方机制”为政府监管发挥了参谋和助手的作用,其作用领域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为政府提供职业安全与健康方面的政策咨询和建议;二是推动职业安全与健康立法;三是开展职业安全与健康方面的研究;四是参与和协调有关职业安全与健康的活动。澳大利亚的情况比较特殊,SWC的主要职责是制定政策和推动立法,其行为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在机构运作方式上,除ILO外,国外三方机构大多采取委员会制,通过定期召开会议等方式运行。以NACOSH为例,该机构每年要召开2—4次会议,会议记录予以保存以备公众查询。
第三,“三方机制”依法建立,其运行比较规范且向公众开放。国外职业安全与健康三方机构的设置、职能、人员构成、经费来源等均有法律依据,如NACOSH的经费来源于美国职业安全健康监察局,MHSC的经费来源于南非矿产资源部,SWC的经费来源于澳大利亚就业、教育和劳动关系部,这体现出政府严格依法行政的特点。此外,各国还制定了三方机构的章程和相应的工作计划。国外“三方机制”具有开放性的特点,三方机构的相关会议和文件向公众开放。如美国职业安全健康监察局通过官方网站发布NACOSH的会议通告,公民可以通过邮件或在线提交个人意见。
3.国外“三方机制”总体评价
总的来看,作为调节劳动基准关系的重要手段,“三方机制”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形成和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一方面,三方机构的代表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学科的专业知识,弥补了政府部门专业知识的不足,起到了思想库的作用,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另一方面,非营利性、开放性和第三方的特点,决定了三方机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比较客观公正,保证了政府决策的可接受性,有利于减少行政执法和政策执行的阻力。国外“三方机制”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在ILO的推动下,“三方机制”虽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大部分集中在欧美一些工业发达国家且主要是由解决劳资关系问题的机制拓展而来,发展中国家是否适用值得研究。此外,在政府监管机构之外增设一个三方机构,不仅可能出现新设机构与现有机构的协调、摆位等矛盾,还可能带来行政成本和工作效率方面的问题。实际上,“三方机制”的作用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的态度,并与机制本身的松散程度密切相关。有批评者认为,ILO的执行机制中缺乏真正有效地保护劳工权利的条款,该执行机制与国际人权法的执行机制一样显得疲软无力,不能令人满意。
三、我国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监管现状及《矿山安全法》修改建议
1.我国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监管现状
我国幅员辽阔,矿山数量庞大,矿业历来是安全监管的重点和难点。据笔者调研统计,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共有各类煤矿13380处、非煤矿山75937处、尾矿库11946处。以非煤矿山为例,不但矿种多,而且从事开采的是大量的中小企业,安全保障能力较差,容易发生生产安全事故。为了应对复杂的矿山安全形势,我国各级政府一直对矿山安全保持着严加监管的态势。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受全能主义治理思想影响,我国矿山安全工作被简单地定位为政府执法+企业守法。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将行政权力的触角几乎延伸到了每个角落,在遵行《矿山安全法》《煤矿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前提下,政府安全监管部门通过日常检查、“三同时”审批、发放许可证、责令停产整顿等手段监督义务人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规定,对违犯规定的义务人实施严厉的行政处罚措施。受职业病潜伏周期长、危害发生不明显等因素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矿山职业健康监管工作一直未受到应有重视,虽然2006年国家将卫生部门承担的矿山职业健康监管职能划转到安全监管部门,加大了矿山职业健康监管力度,但实践中相关工作的开展还需要借助于部门之间的联席会议,面临较大困难。此外,受制于立法滞后等因素,实践中矿山职业健康方面的日常检查、行政许可等工作均与安全生产分开进行,不但增加了企业负担,而且影响工作效率。
2.我国《矿山安全法》存在的问题
与国外对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进行统一立法不同,我国采取的是对安全生产与职业健康分别立法的模式,矿山安全生产适用《矿山安全法》,矿山职业健康适用《职业病防治法》。由于立法背景等已经发生变化,这两部法律中的许多内容亟待修订,以适应当前工作的需要。以《矿山安全法》为例,该法制定、实施于20世纪90年代,立法目的主要是防止矿山事故,时至今日,矿山安全立法的目的和调整对象、矿山安全监管机构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矿山安全法》的滞后性越来越凸显。(1)矿山安全监管机构已经调整。根据《矿山安全法》第四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对矿山安全工作实施统一监督,实践中,这一监管主体早已被各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所取代。(2)《矿山安全法》的规制内容和手段滞后。《矿山安全法》的适用对象是固体矿山,主要针对大型国有矿山企业,对于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大量私营小型矿山、液态和气态矿山缺乏相应的规制手段。同时,《矿山安全法》的内容没有体现地下矿和露天矿的不同特点,存在“一刀切”的现象;缺乏与职业健康相关的内容,不利于对劳动者的安全与健康进行全面保护,也不符合国际上对职业安全与健康统一立法的潮流。(3)《矿山安全法》确立的监管体制不合理。依据《矿山安全法》及其他法律规定,我国在矿山安全领域确立了综合监管与行业(专项)监管相结合的监管体制,煤矿实行垂直监察,非煤矿山实行一般的行政管理。由于《矿山安全法》对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与地方煤矿安全监管部门之间的职责界限未予明确,导致二者对企业重复监管以及监管错位、不到位等问题,不仅没有形成监管合力,还给企业带来额外负担,造成行政资源浪费。(4)《矿山安全法》导致矿山安全监管者的职能定位出现偏差。由于《矿山安全法》对安全监管机构的职责规定得不明确,矿山安全监管机构迫于事故追责压力等,往往对企业进行事无巨细的检查,作为责任主体的企业则忽视了其应当承担的义务,导致政府安全监管与企业安全管理混淆不清,企业对政府安全监管的依赖性非常严重,不利于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健康开展。
20世纪90年代我国矿山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普遍较低,导致矿山生产安全事故频发。如果说20年前矿山安全主要通过政府规制有其合理性,那么,时至今日,我国矿山企业自我安全管理的能力和水平有了显著提升,矿山生产安全形势已总体趋于平稳。与此同时,我国矿山职业病发病率和职业危害程度居高不下并有上升趋势,相关数据失真、底数不清等情况逐步凸显,加强矿山职业健康监管、对劳动者的安全与健康进行全面保护的现实要求十分迫切。特别是在强调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提倡社会治理的今天,以往那种以遏制矿山事故为主要目标的单一、刚性的行政管理模式越来越突显出定位和功能上的局限性,发挥第三方的功能,加强政府部门与矿山企业及相关方的协商与合作,对涉及劳动者安全与健康的事项进行一体化管理,已成为新时期矿山安全监管的内在要求。
3.我国在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监管领域引入“三方机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第一,在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监管领域引入“三方机制”是我国主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具体体现。《三方协商促进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公约》第二条明确要求:“凡批准本公约的国际劳工组织会员国,承诺运用各种程序保证就下述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国际劳工组织活动的有关事宜,在政府、雇主和工人的代表之间进行有效协商。”我国是ILO创始成员国,一直在ILO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发挥重大影响。根据《三方协商促进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公约》的要求,在包括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监管在内的劳动保护领域建立“三方机制”,是我国主动承担缔约国义务、落实相关责任的具体体现。
第二,我国在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监管领域引入“三方机制”具有宪法基础。劳动权是各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包括休息权、获得报酬权、劳动保障权等权能,而且包括健康权等相关内容。我国《宪法》第42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作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责任主体,政府有义务采取直接参与等形式,为公民提供管理国家事务的途径,而“三方机制”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民主政治有密切联系,体现了劳动者对行政民主的价值追求。
第三,我国工会法、劳动法等相关立法及其实施,为在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监管领域引入“三方机制”提供了规范样本和现实路径。我国2001年修订的《工会法》第34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我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八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会同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劳动争议的重大问题。”上述立法确立的“三方机制”适应我国劳动关系的基本情况,其运行十余年的实践为我国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监管领域引入这一机制提供了宝贵经验。
4.我国在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监管领域引入“三方机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第一,我国在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监管领域建立“三方机制”,需要协调和理顺三方机构与现有组织、“三方机制”与现有机制的关系。从国家层面看,国务院早在2001年就成立了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来自17个部委,此后陆续成立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技术委员会、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等机构或机制,加强对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中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问题的研究,发挥专家对安全生产工作的支撑作用。但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这些机构或机制总体上没有走出“政府控制”模式,组织结构比较松散,人员组成和比例不够合理,制度化、规范化的运行机制尚未建立,活动呈现碎片化等。如何建立科学的“三方机制”,有效协调该机制与现有机制的关系并克服现有机制的种种弊端,考验着决策者的勇气和智慧。
第二,“三方机制”的核心内容是三方独立,各自发出不同的声音,这就需要雇主和工会高度组织化,我国目前这方面的条件尚不成熟。澳大利亚三方机构中有两名雇主代表分别来自澳大利亚工商协会和澳大利亚工业集团,他们可以与政府平等对话。我国目前似乎还没有类似的组织。以行业协会为例,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对社会团体实行主管单位“挂靠制”,致使不少行业协会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俨然成了“二政府”⑤。
第三,我国在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监管领域引入“三方机制”,面临制度在移植中“水土不服”的风险。国外“三方机制”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其民主决策传统与现实制度之间经历过漫长、渐进的磨合。我国与这些国家在政治制度和文化上的差异决定了我国《矿山安全法》在借鉴国外“三方机制”的过程中,既要把握其精髓,又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
5.我国在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监管领域引入“三方机制”的模式选择
事实上,国外“三方机制”模式各有特色,很难简单地认为谁优谁劣。如前文所述,对话协商模式并未建立以惩罚为后盾的执行机制,总体上显示出较为疲软且没有效率的特征。协调监督模式能否得以建立和运行与各国体制及相应的机构设置密切相关,如澳大利亚作为联邦制国家,SWC是其独立的法定机构。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不可能另设一个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或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平行的机构。相较而言,咨询指导模式可能更适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笔者建议从完善顶层设计入手,建立国家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定位于国家级的第三方协调机构,活动经费从财政单独列支,成员由政府、矿山企业和矿工三方代表按一定比例组成,设主席一名,所有成员均由国务院任命。三方代表的人选应充分考虑其工作经验、所属行业等因素,并保证政府代表中有一部分来自地方。考虑到我国行业协会发展尚不健全、工会的职能较弱等实际,建议在企业和职工代表的选取上保持适度的弹性。对于国家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咨询委员会的活动方式,建议采取定期会议制,每季度召开一次;遇有特殊情况,经委员会主席提议,可以召开临时会议。该委员会下设秘书处,负责联络代表、对外协调以及其他日常工作。
6.我国《矿山安全法》修改建议
实现上述设计的前提是做好矿山安全立法,为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监管领域引入“三方机制”创造法制条件。当前,我国《矿山安全法》正在修订中,建议该法增设“三方机制”的内容,充分体现该机制的开放性、协商性、主体利益相关性等特征。(1)顺应安全生产与职业健康统一立法的国际潮流,将《矿山安全法》的名称修改为《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法》。(2)借鉴南非1996年《矿山健康与安全法》的立法经验,调整我国《矿山安全法》的篇章结构,增设“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三方机制’”一章,具体包括四个条文。第一条:国家设立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咨询委员会,负责向国务院提供有关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的意见和建议。第二条:国家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咨询委员会对负有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进行协调、指导和监督,依法履行以下职责:参与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方面的决策;提出完善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立法的建议;开展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调查研究,分析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形势;组织和推广全国性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活动;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第三条:国家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咨询委员会由负有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监督管理职责的政府部门代表、矿山企业代表和矿工代表三方组成,实行平等协商、公众参与、共同治理。第四条:国家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咨询委员会开展工作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矿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3)完善相关罚则,强化法律责任。针对国外“三方机制”的执行效率不高等弊端,建议完善我国《矿山安全法》的法律责任条款,增设对不执行国家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咨询委员会决议的处罚措施,强化国家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咨询委员会行为的约束力。
注释
①我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规定: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对全国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②如在无上位法依据的情况下,一些政府规范性文件随意增设安全生产许可的前置条件,一些地方通过行政强制手段关闭手续合法的矿井,实施吊销许可证等行政处罚措施缺乏听证程序等。③“职业健康”一词源自英文,国内学者对这一词语的使用较为混乱,有的用“劳动卫生”,有的用“职业卫生”,有的用“职业健康”,笔者倾向于第三种。④参见《中国安全生产年鉴(2014)》,煤炭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488页。⑤现实中一些行业协会已成为安排政府庸员、转移部分政府权力为自己谋私利的组织。
参考文献
[1][美]约翰·W.巴德.人性化的雇佣关系——效率、公平与发言权之间的平衡[M].解格先,马振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美]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M].孙柏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3][美]杰瑞·L.马肖.行政国的正当程序[M].沈岿,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江必新.行政规制论丛(2012年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5]卢剑峰.行政决策法治化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
[6]马超俊,余长河.比较劳动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7]雷鹏.国外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的发展及启示(上)[J].人事天地,2014,(4).
[8]赵祖平.欧盟劳工政策三方机制的发展及其启示[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1).
[9]李丽林,袁青川.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现状与问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5).
[10]蒋建湘,李沫.治理理念下的柔性监管论[J].法学,2013,(10).
[11]江必新,邵长茂.社会治理新模式与行政法的第三形态[J].法学研究,2010,(6).
[12]张康之,程倩.民主行政理论的产生及其实践价值[J].行政论坛,2010,(4).
[13]牛胜利.国际职业卫生法规发展历程[J].劳动保护,2010,(4).
[14]代海军.南非《矿山健康与安全法》述评——兼论我国矿山安全监管法制的完善[J].行政与法,2015,(1).
[15]杨松才.国际劳工组织执行机制评析[J].求索,2008,(6).
[16]刘俊杰.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的五大关系[J].中州学刊,2015,(1).
责任编辑:邓林
Study on Tripartite Mechanism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in Mines——Also on Amending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Safety in Mines
LuoLiDaiHaijun
Abstract:As a basic system regulating labor standard relations,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ipartite mechanism has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and realistic rationality. For a long time, China has supervised and governed mine safety mainly by compulsion, which led to un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the poor implementation effect and other defects. In general, tripartite mechanism includes three mod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functions. They are modes of dialogue, supervision and coordination, and counseling. China may consid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ripartite mechanism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in mines according to the pattern abroad. These include modifying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Safety in Mines, adding a chapter of tripartite mechanism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in mines, and improving the articles on penalty.
Key words: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tripartite mechanism; administrative participa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Safety in Mines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3-0055-06
作者简介:罗丽,女,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1)。
收稿日期:2016-02-06
代海军,男,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北京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