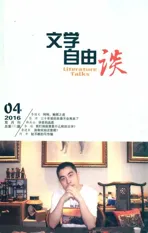《百年孤独》对于我们的意义
2016-03-16邵振国
□邵振国
《百年孤独》对于我们的意义
□邵振国
30年过去了,我们回首拉丁美洲那场所谓“文学爆炸”,咀嚼它之所以冲出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伊比利亚”藩篱,而获得世界声誉,我们对这个启示意义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那个根本的“启示”,即作为创作思想上的方法论,也就是它“魔幻”的内在动因,却往往被我们所忽视。加西亚·马尔克斯文本究竟想说什么?那些离奇的生命状态、情结心结,含着怎样的艺术鹄的?对于我们产生了多少个体“独立”与社会、历史的宿命之追问,而命运地诉诸文学“虚构”?
马尔克斯想说什么
《百年孤独》让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人不能掌握自身命运。人之每一个个体,沉沦在社会、历史的宿命中。那个有着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的哥伦比亚缩影——马孔多,既有着原始田园的宁静美丽,又有着愚昧落后和种种怪异,诸如它的创始人阿·布恩迪亚和乌尔苏拉夫妇,所生后代都长着一条猪尾巴。这“猪尾巴”在漫长的“百年”中始终无改。马孔多该不该存在及怎样存在,就摆在了历史、社会面前,需要人们认识它的存在状态。我们不能不记起“全世界的蚂蚁一起出动,正沿着花园的石子小路费力地把他拖到蚁穴中去”的细节,这可能是作者的一种愿望,也是主人公奥雷里亚诺上校所希望的吧。奥雷里亚诺发动过32次起义,都失败了,他也躲过了14次暗杀和一次行刑队的枪决,后来当上了革命军总司令,并成为政府最恐惧的人物,最终还是在内战中死去。我相信他至死也不明白自己的“死因”,就像他不明白他跟17个女人生了17个儿子,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全部被杀了。我们当然很容易会意主人公的命运与社会、历史的对抗关系,但是我们容易忽视的是那个“个体”的存在状态,它却是社会、历史宿命的深层根源。作者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既开篇写到“多少年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上校将会想起,他父亲带着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下午”,又在全书结尾,叙述马孔多被一场飓风卷走,天方夜谭般地消逝。这两者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是什么让他在行刑前会想到“去见识冰块”?
我不知道这种书写是不是指向了那个作为宿命根源的“个体”。窃以为那行刑前的回眸顾盼,不仅是在看他一家人的凄惨历史,而是将目光觅向那更深层的渊薮。我们知道,哥伦比亚于16世纪沦为西班牙殖民地,于1819年独立。独立并非就是它的福祉。马孔多的人们仍生活在独裁专制统治之下,对此没觉出什么不适。殖民者会带来西方文明,也会掠走人们的财富,一块磁铁和一只望远镜能换走布恩迪亚的一头骡子和一群山羊。但这不是决定个人命运的因素,关键取决于这个“个体”对自身存在处于怎样的认知状态。
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人,把家中的小便盆也统统打上家徽,以为那是不能丢弃的“传统”。村民们普遍地得了一种传染性的不眠症,甚或失去记忆,记不住自己的历史,乃至给牛挤奶也要贴上标签,以提醒记忆。如是人们对自己的存在状态都模糊不清,你还能希图他们存有改变自己的希冀吗?人们在无所事事中备受孤独,无以打发漫长的时光。人们寻找各种得以“体面”的事由:阿玛兰妲天天在家制作她的裹尸布(也就是葬衣),但她白天织好晚上又拆掉;蕾梅黛丝则每天都把自己泡在浴盆里,等等。人们无暇思考这种状态的由来,更莫说时局和政治了。奥雷里亚诺背井离乡去参加那场战争,其实他也不明白在为谁卖命。战争并未给他带来多少利益或荣耀,相反他却得到人们的冷漠和唾弃。战败归来,他也给自己找了个“事由”:炼金,制作小鱼,也是做了又化掉,化了又重做……这些,都呈现出一个又一个无存在意义的“非个体”。
我想,这是否就是《百年孤独》的主旨意蕴呢?
拉美作家取材的政治指向
这一节我想在一个更大的文本范围,来看《百年孤独》的创作思想。
应该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一位有着清晰创作想法的作家;在这一点上,拉美著名作家莫不如是。魔幻为现实所使然,所谓“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这个“真”,窃以为就是真实的历史叙述。马尔克斯在他的文学谈话录《番石榴飘香》中说,这本书写了18年,可谓苦心经营;作家的职责就在于提醒公众牢牢地记住容易被人遗忘的历史。
由此看出,他的种种创作想法是由那个“真”制约着、选择着。《百年孤独》把目光更深重地凝注于人的个体心灵的罹难,用神秘的、幻想的民族色彩——那是加勒比海自身海潮翻涌所泛起的颜色——在民族独立之后,似乎更加凸显了人的心灵一片荒芜、无物的貌态。作家们不可能不对反专制独裁、要求民主和改革的那片心灵有所担当。虽然他们多采用神秘曲折的、隐喻寓言的文学叙述,却都是拉美历史、社会和政治现实的折映。
马尔克斯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家长的没落》,用多人称独白,讲述共和国总统尼卡诺尔之死。此前总统已经“死”过一次,让替身阿拉贡内斯躺入棺材,他在暗处观看人们得悉他去世后的反应。人们欢喜若狂,冲进总统府,拖出尸体,暴弃街头,朝着尸体唾唾沫、泼屎尿。他在窥视之后,施以残酷的报复,造成尸横遍野,引起瘟疫。尼卡诺尔有一亲信——国防部长德阿吉拉尔,为他出生入死。但他怀疑这位亲信会暗算他。一次总统遇刺,他便怀疑是国防部长指使。三天之后,他宴请他的私人卫队的时候,端上来一盘菜,即是德阿吉拉尔将军——他已被烹饪为菜了。这种情节,在专制独裁国家不为鲜有,却给予我们这位有担当的作家以取材视野。文学绝不是什么可以脱离政治制度的东西,因为是这种政治把人导入了“人生的迷宫”。
危地马拉作家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所著第一部长篇小说《危地马拉传说》,即是广泛关注、涉猎该民族历史、社会和玛雅-印第安神话及民间传说之作,他因此成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先驱,并于1967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代表作《总统先生》,同样塑造了一个独裁者。他通过幻觉,叙述出印第安-基切人同意了托依尔神说的“建立在人猎捕人的基础之上”的统治。在这里,阿斯图里亚斯也把取材视野投向了人的命运的由来。
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弗的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写了一个庄园主发迹的过程。佩德罗·巴拉莫剥削工人,偷移地界,通过与女债主结婚等等手段扩大他的地盘,逐渐把科马拉地区的土地全部占有。他随意蹂躏妇女,专横跋扈,但内心空虚。被他百般追逐的女人苏珊娜后来神经错乱,抑郁死去,而他却被私生子阿文迪奥杀了,科马拉庄园也神秘消失。作者叙述笔法惊人,从巴拉莫与女债主多洛雷斯的儿子胡安·普雷西亚多,遵照母亲的遗嘱,到科马拉寻找生身父亲开始入笔;而此时,胡安·普雷西亚多已经去世,是他的魂灵在讲述自己寻父的经历。母亲多洛雷斯,是与巴拉莫结婚后又被遗弃而死的。当胡安·普雷西亚多的魂灵长途跋涉寻到科马拉庄园的时候,生父巴拉莫早已不在人世了。
是的,这一拉美魔幻范本《佩德罗·巴拉莫》,的确在叙述技巧上给予我们极大的美学借鉴,从过去时到现在时,从现实到梦幻,富有悬念地融为一体。但是这里要谈的,仍是这一情节给予我们的思想启示,也就是它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魔幻的原因。
胡安·普雷西亚多是在母亲遭遇不幸之后才诞生的,所以,他的寻找也就是对于母亲命运的追问。其次,作品之所以在胡安·普雷西亚多死后来讲述那漫长的经历,是要表达人的命运是漫长持续的——这与《百年孤独》所表述的是一个意思。在作者眼里,这个科马拉庄园主与“总统先生”所建立的“以人猎捕人的”统治秩序是具有同一性的。在西方价值观里,个体的存在是第一位的。个体的存在状态和性质是一个民族、国家、社会存在状态和性质的前提,个人是否拥有自由本质,是否是一个自在的、自为的存在,决定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本质和存在。因而,我们可以说,《佩德罗·巴拉莫》是对人的应然命运的呼唤。
把握人的应然命运
我们在众多文本及其现实中看到,拉美的民族独立并没有带来个体的独立。那么,什么才是民族主义的真正出路?国家、社会的进步性质靠什么来确立?在这里,我们说,文学虚构不是为了魔幻技巧,而是担负着探寻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的重任。
虚构是文学的生命。这道理非常简单,因为现实中不存在人的应然命运的对应,它只存在于作家的使命中。
戈达尔在《小说使用说明》中,论述了文学史上多种小说写法,强调了其中之一的“虚构”。20世纪的法国小说试图反虚构,在中国当下也有“非虚构”文学的聚讼纷纭,这反而让我看到了虚构所具有的难以抵御的力量。人的应然本质的建构远未完成。而虚构恰似拉美的魔幻在我们心目中的位置,依然崇高地存在着。针对法国当代另类小说,戈达尔评论道:
最不起眼的虚构也会触及我们的本质。大部分时候,我们都盲目地活着,在等待、恐惧和短暂的任务中消耗生命,受困于无所事事的时间和无足轻重的事件,屈服于偶然性的统治。我们最终失去了对某种目标明确的生活的渴望。这种渴望打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而且不管怎样都不会彻底消失,因为虚构会按照它所设想的生活的模子,令渴望重新点燃。一边是逝去的时间,其中的每一刻都充满着不确定性,另一边是对这时间的整体意图和意义的确信,虚构通过在想象中实现这两者的几乎不可能的联结,在我们身上触及了人类生存的条件。
这段话说得太精彩、确切了!尤其那“在等待、恐惧和短暂的任务中消耗生命,受困于无所事事的时间”,不正是《百年孤独》的主旨表述吗?我们说,虚构永远不会在我们人生的地平线上消失,不正是因为“虚构会按照它所设想的生活的模子,令渴望重新点燃”吗?在中国当下,人们需要怎样的文学,文学如何创造有益于人的应然本质的建构,难道拉美魔幻文学没有给予我们启示吗?
康德认为,人的本质和人性,在其完全完成的意义上,不是现实中既有的,而是我们的理性直悟到的那个“应当”。黑格尔把个体的本质与现实视为对立的,他说:“由于个体具有这种自由,现实世界就有可能具有这双重意义”,“现实对个体的影响就有绝对相反的两种情况,个体既可以听任现实的影响之流对自己冲击,也可以截住它,颠倒它或改变它。”
黑格尔所言,正是拉美文学的内在动因;这也是它之所以魔幻的缘由吧。